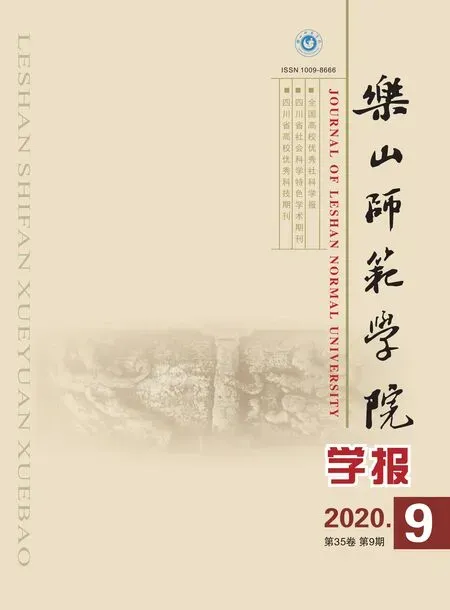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范解读
2020-03-03魏晓欣
魏晓欣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区域生态文明与环境法治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国家安全的保障和人类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维护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生态功能与文化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何种法规范以及为什么此种法规范更适合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内外背景
为了解决全球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两项条约以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与《二十一世纪议程》等三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规范。《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通过,标志着从以往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转入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履行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规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依照相关国家立法,维持、尊重、保存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因为它们不仅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而且体现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1]。
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领域,关于环境保护,中共中央相关的政策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精神和“201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的要求,体现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由政府单维管制向社会多主体共治发展的趋势”[2],为本文所研究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主要运行主体——政府与公众共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
另外,依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项目39“关于民间团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建立及示范33”之规定,“应建立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3],中国开始尝试共管实践,《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00年)》中,明确提出“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区事业”,并且开辟民间集资渠道;广泛开展服务合作,争取国际资助;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和保护点,采取多种形式发展自然保护区事业[4]。
二、何以民族地区?
本研究建立在笔者作为主研人参与的前期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的基础上[5],通过对民族地区的实证调研,掌握了大量有关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范的鲜活材料。研究范围之所以选择民族地区,是因为,与汉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于:其一,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是比较贫困的地区。而贫困和经济发展如果过分地依赖生物多样性资源,这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一定的困难[6]。与外界相对隔绝、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而传统相对保留完整,因此,作为宏观背景的传统中国的社会运作实践和文化价值对笔者研究今天的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其二,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民族地区一般位于江河的源头,其环境通常比较脆弱,中国大部分的野生动植物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其三,民族地区的文化具有特异性,其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密切关联。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殊性在于保护规范的多层次,保护方式的多样化,保护与发展冲突并存等。可是由于社会变迁,以及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一切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一体、有序。民间法的功能在一些民族地区慢慢呈弱化趋势。如何把有益的民间法纳入法治轨道以及加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等是待探讨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生态价值
民族地区大多属于我国国家规定的重点生态作用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如生态功能区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在一定面积的陆地和水体范围内,制定特殊的保护政策,并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而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7]。如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腹地,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发源地及涵养区, 周边与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等接壤。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四川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8]。云南省西北部的三江并流地区,这里是中国最为偏远、最具生态多样性和遭受环境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拥有独特的地质环境和动植物区系。这里有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川的世界著名大河——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和怒江(萨尔温江)[9]。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宗教保护方式圣境——神山、圣湖位于长江、黄河和国际河流澜沧江、怒江的发源地和上游,它们的保护对于中国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10]。
(二)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
“据统计,西部自然保护区所保护的生态系统和物种系统约占全国的70%,面积约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85%。西部地区现在是全球关注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11]
与汉族地区相比,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都特别丰富,不管是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还是生态系统多样性。而且民族地区大多数是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地区、关键地区、热点地区,特别是云南省、青海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地的民族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等。云南省也堪称是全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2]“四川省不仅是黄河上游和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而且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宝库”。[13]“云南省也是遗传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一”[14]。
(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联性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以来,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里约举行后,国际和国家保护方法必须与社会的需要和发展议程相协调。以前基本上排除了人,侧重于“自然”,今天越来越多的保护区专家承认自然资源,人和文化存在相互联系[15]。
传统文化知识,习惯法和体制,生物多样性名称及其使用与当地语言和方言相互关联且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原住民和当地居民的语言继续流传并保持活力,就会保持整个文化和生物知识的活力。[16]所以语言的挽救,避免它们消失的努力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例如,马来西亚沙巴实施了一个方案,将当地的语言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并且配备了与幼儿园语言教育相关的书籍。为了实践这一点,老年志愿者每周一次,向有意学习母语的村民教一次当地语言[17]。 因为当地的语言对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传统知识与民间法联系密切。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创作和革新的源泉。”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自然保护管理体系,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知识体系所发挥的保护作用[18]。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与保存的区别,本文保护的含义主要指保育。生物多样性的保育(conservation)包括“对人类活动进行控制或限制与保育并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等两个方面”[19]。
三、法律多元理论对“法”之解读
所谓法律多元,是指“在同一社会中,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共存的一种状况 ”[20],这是梅莉( Sally Engle Merry)在其提出的多元化规范性秩序中提出的概念。埃利希[21]( Eugen Ehrlich)则提出了“权力多元与秩序多元的概念,法是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一系列法条”。通过对国家主权优越性与国家法中心主义的除魅(disenchantment),发展出了法律多元主义理论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界,对民间法的研究是其区别于传统规范法学的重要特征[22]。
传统法理学切断法律因素和非法律因素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联系和影响,孤立于国家法领域中,而法律多元理论承认正统法理学拒绝的“非法律因素”,民间法、习惯法获得合法性,法学研究对象范围得到扩展[23]。法便包含了民间法和国家法等[24]。既然民间法的产生是“一个共同体的事实”[25],国家法与民间法都起到相应的规范作用,并且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26]。法律多元论,如吉尔茨的法律的地方性理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等等,这些西方后现代学术观点在中国法学界型构起了民间法的新形象[27]。梁治平先生认为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遮蔽了广大民众实际的生活规则;而民间法研究的进入,突破了传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28](自序:2)。
法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法只是社会需要的产物”[29]6,因此,要注意保留传统中根本的东西,法治的现代化应当是本土化之上的国际化[30]。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霍贝尔说:“法律仅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它调节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并且惩处违反这些准则的方面。”[29]4另一法人类学家——日本著名的千叶正士指出:“法律多元在当代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31]“国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即使是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大量的非正式法律还存在,在所谓正式的法律之外。”[28]32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百余年前就意识到, 美国的“普通法体现了一个民族多少世纪发展的历史”[32]。
在法社会学看来,“法律规则也起源于社会本身,而不是立法者或法官的造法行为”[33]。众所周知,“法条主义并没有穷尽法律 ”[34]。结果是“司法实务界又不得不适用民间法,面对法律漏洞,目标是使判决为社会所尽可能的接受”[26]。
从国家法的视角观察,显然民间法不能称之为法。从传统社会通行的与之相联系的名称如规、例、则、禁、章程里面,可以明确无误地读出法的意味[35]。民间法一样发挥着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的利益、定分止争的功能[28]32。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仅仅需要很少的法律或者不需要法律。”[36]因为,传统社会,“国家无意或者没有或者不能,提供一套民间日常生活所需的规则、组织和机构”[28]28。于是,各种补缺、替代性的民间法规范便应运而生(当然,民间法自身也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和延续性,并非每朝每代新生出),各种形式的排解纠纷的“权威”也相伴而显。明清时期,民间调解纠纷的渠道众多,族社村邻、耆老缙绅实施着行政、司法上的“间接管制”,“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被解决了,它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成万成千农民之间的问题”[37]。民间法的存在是事势所需,但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法”安定秩序的作用[38]。
我们应该重视民间法 ,亚里士多德曾说:“与‘成文法’相比,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往往在实际上更有权威。”[39]相对于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书本上的法”或者“纸面规则”等,法社会学家更加重视民众的生活中真正对他们的权利与义务起调整作用的活生生的各种规则,如埃里希所称之“活法”“生活中的法”或者“实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