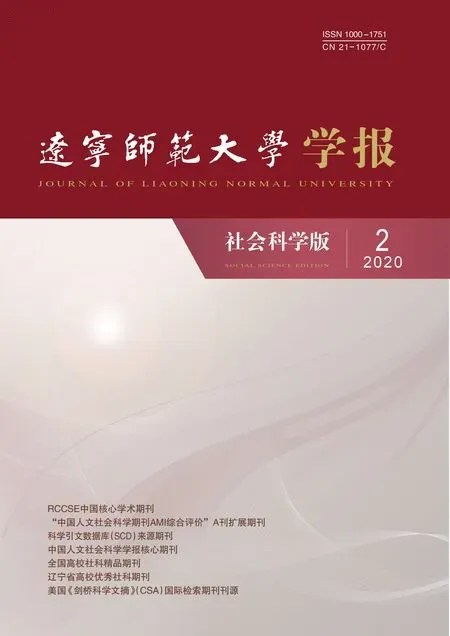辽朝海盐产业研究
2020-03-03田广林
田广林, 韩 笑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海盐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是辽朝海洋产业开发的核心内容,因此成为辽代海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地注意到辽朝盐业及辽宋双方通过海上运输发生食盐交易往来的是陈述先生。他在1963年出版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一书中,曾对辽宋对峙期间沿边开设的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中所涉及的海盐生产及其交易情况有所述及(1)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63:125-132.。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辽朝盐业的专门论述时有出现,其中对辽朝海盐产业的开发与管理问题多有涉及(2)郭正忠.契丹盐业及盐务管理[J].社会科学战线,1993(5):185-189,167.③郭正忠.辽代盐业体制的变化[J].社会科学辑刊,1993(6):90-92.④吉成名.辽代食盐产地研究[J].盐业史研究,2006(4):27-32.⑤王欣欣.略论辽朝的盐酒专卖[J].兰台世界,2012(10):53-54.⑥彭文慧.辽代盐业经济与州县城市发展[J].赤峰学院学报,2016(9):17-20.。近年,随着辽代海事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关辽代海盐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如2011年,孙玮、张宏利、陈晓菲在以辽朝东京、中京、南京海事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分别就辽东京、中京和南京地区的海盐产业开发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证(3)孙玮.辽朝东京海事问题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⑧张宏利.辽朝中京地区海事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⑨陈晓菲.辽南京地区海事问题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不过,时至今日,有关辽代海盐产业的专文研究,尚属鲜见。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拟在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试就辽朝海盐产业的起始上限、主要产地和管理体系与制度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一、辽朝海盐产业的起始上限
关于辽朝海盐产业的起始时间,按照《辽史·食货志》说法,始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所谓:“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4)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0.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朝之事发生在辽会同元年(938,后晋天福元年),《辽史》卷4《太宗纪》记载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后晋“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此事在中原典籍中的《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有记载,而犹以《新五代史》的信息最为完整,文字与《辽史》所载完全相合。该书卷8《晋高祖本纪》载天福元年(938)十一月丁酉,“皇帝(石敬瑭)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市,莫州治今河北省任丘市,两地均隶属沧州市。从会同元年(938)后晋割地至应历九年(959)周世宗北伐,瀛、莫二州在辽朝治下前后历时凡22年。辽应历九年(959,后周显德六年)夏四月,“周拔益津(故址在今河北省霸州市)、瓦桥(故址在今河北省雄县西南)、淤口(故址在今河北省霸州市东信安镇)三关。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5)脱脱,等.辽史·穆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75.。后周这次北伐从辽朝夺得的土地,除了上述三关二州之外,还包括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和宁州(治今河北青县)在内。《旧五代史》卷119《周书·世宗本纪》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夏四月,周世宗北伐,“至乾宁军,伪(辽)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五月,后周“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奏,攻下易州,擒伪(辽)命刺史李在钦来献,斩于军市”。又据同书,这一年的五月,周世宗从辽朝手中重新夺得三关四州之地后,遂“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0载:“雄州、霸州,周显德六年(959)五月,以瓦桥关为雄州,割容城、归义二县隶之;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成二县隶之。地望并为中州,时初平关南故也。”此事在《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第三》中的记载更觉详明:“雄州,周显德六年(959)克瓦桥关置。治归义,割易州之容城为属,寻废。霸州,周显德六年克益津关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为属。”
曾经一度属辽的瀛、莫、雄、霸等州,地濒渤海,均盛产海盐。《宋史》卷181《食货志》载宋朝“煮海为盐”的海盐产地共有“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宋朝曾在瀛、莫、雄、霸等州所在的河北路置“滨州(盐)场,一岁煮二万一千余石”。由于瀛、莫二州地近沧州横海军,而瀛州治在河间,故《辽史·食货志》称辽朝获得瀛、莫二州之后,“始得河间煮海之利”,又由于瀛、莫二州入辽不久即被后周攻取,于是便有了“燕、云迤北,暂食沧盐”的说法。
《辽史·食货志》并非辽人旧作,而是出于元人手笔。该《志》以辽取瀛、莫,“始得河间煮海之利”为辽朝海盐产业上限的认识并不客观,因为早在瀛、莫海盐产地入辽之前,辽朝就已经占领了盛产海盐的渤海北部陆域岸线。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史实,今人吉成名把辽朝海盐产业的上限定在天显元年(926),辽太祖兼并渤海国以后。认为由于渤海的并入,辽朝“才有了辽东地区的海盐产地”,取得幽、云十六州地区以后,又把海盐产地扩展到了渤海湾西岸一带(6)吉成名.辽代食盐产地研究[J].盐业史研究,2006(4):27-31.。相对于《辽史·食货志》的说法,这种观点无疑要客观得多。不过,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拥有辽东海盐产地的时间并非始于攻取渤海之后,早在契丹建辽之前的遥辇汗国晚期,辽东地区就已经为契丹所有,这个问题笔者曾经有过初步考证(7)田广林.契丹时代的辽东与辽西[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6-61.。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辽朝建立的第二年(908),就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境内修筑了镇东海口长城,同时设立了兼管东南海疆和商贸往来事务的镇东关(8)田广林,王姝.论辽代大连地区的行政建置[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2):126-129.。所以,辽朝海盐产业的起始上限,应该始于908年修筑镇东海口长城之前的辽朝初创之际,而不是兼并渤海之后。
二、辽朝海盐的产地
关于辽朝海盐的产地,据今本《辽史》,在辽朝濒海的东京、南京和中京地区,均有生产。
(一)辽东京的海盐产地
1.原渤海盐州海阳县
《辽史·食货志》所列举的辽代“一时产盐之地”中有属于东京地区的“渤海”和“海阳”(9)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0.。这里的渤海,应指渤海故地濒海地区。《辽史》中所载的海阳县有两个,一属中京润州,另属东京盐州。辽东京道的盐州,系南迁原属渤海龙原府盐州(即后文龙河郡)遗民而建,治今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西土城子。《辽史》卷38《地理志》:“盐州。本渤海龙河郡,故县四:海阳、接海、格川、龙河,皆废。户三百。隶开州。相去一百四十里。”辽盐州虽然地属海滨,但未知其是否有海盐生产。不过,辽属原渤海盐州的海阳县,入辽以后,虽然州、县建置并废,但其海盐产业,应该依然存在。
2.辰州
辽辰州治今辽宁省盖州市,地濒渤海,富有渔盐之利。《辽史》卷38《地理志》:“辰州,奉国军。节度。本高丽盖牟城。唐太宗会李世勣攻破盖牟城,即此。渤海改为盖州,又改辰州,以辰韩得名。井邑骈列,最为冲会。”据刊石于辽寿昌二年(1096)的《孟有孚墓志》,孟有孚生前曾“为辰渌盐院使”(1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70.。这里的“辰”,即指辰州,“渌”系渌州,“盐院”,应为榷盐院,是辽朝设在产盐地区的官营专卖盐务管理机构,置院使和都监以主其政。辽朝设在东京地区的辰渌盐院信息还见于乾统七年(1107)刊石的《梁援妻张氏墓志》:“长男庆先,监辰渌盐院。”
3.渌州
辽渌州系迁渤海渌州遗民于辽南地区而建的节度使州。《辽史·地理志》:“渌州,鸭渌军。节度。本高丽故国,渤海号西京鸭渌府。城高三丈,广轮二十里,都督神、桓、丰、正四州事。”今人向南据辰、渌两州共置辰渌榷盐院考证,辰州和渌州相去不远,距离甚近。辰州故城在今辽宁省盖县(盖州市),则渌州必当在辽阳府之南、海辰两州以西近海之地(1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70.。
(二)辽中京的海盐产地
1.润州海阳县盐场
辽润州(治今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为来州(故址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古城)支郡,此即《辽史·食货志》里所载的海盐产地海阳。海阳县为润州依郭县,“(东)南至海三十里”(12)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26):494.。《辽史·地理志》:“润州,海阳军,下,刺史。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统县一:海阳县,本汉阳乐县地,迁润州,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
2.隰州海滨县盐场
辽隰州(故址在今辽宁省兴城市西东关站村)也为来州支郡,海滨县为其依郭县。《辽史·地理志》:“隰州,平海军,下,刺史。慕容皝置集宁县。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隶与圣宫,来属。统县一:海滨县,本汉县。濒海,地多碱卤,置盐场于此。”(13)脱脱,等.辽史·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89.
3.榆州红花务盐场
红花务是辽人设在榆州永和县(治今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安昌岘村)境内的一处制盐场所。该盐场《辽史》失载,始见于北宋许亢宗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出使金朝所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寺去海半里许,寺后有温泉二池。……第十九程,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此一程尽日行海岸。红花务,乃金人煎盐所,去海一里许。……第二十程,红花务九十里至锦州。”(14)赵永春.奉辽金行程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152.
许亢宗北使金朝的宣和七年(1125)为辽朝保大五年。他是在辽朝亡国的当年路经金人煎煮海盐的红花务的。由此可以肯定,金人“煎盐”的红花务煎盐所应是接管的辽朝盐场。
关于这处盐场,金人王成棣在所著《青宫译语》一书中也曾有所记述。据该书,金天会五年(1127,宋靖康二年)三月,金兵灭宋之际,王成棣奉命随珍珠大王设野马等遣送所俘获的宋徽宗皇后韦氏一行赴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四月)二十九日,至来州。……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初二日,王(珍珠大王设野马)令驻屯一日,共浴温泉。……初三早行,抵盐场。初四日,至锦州”(15)傅乐焕.辽史丛考·青宫译语笺证——宋高宗母韦太后北迁纪实[M].北京:中华书局,1984:319.。
(三)辽南京的海盐产地
由于南京地区海岸线较长,加之该地有着悠久的煮盐传统,其海盐产地相对偏多。目前可考者,除了《辽史》所载的滦州石城县、析津府香河县盐场之外,还有《辽史》失载的和芦台军盐场和景州永济盐场。
1.滦州石城县盐场
辽朝滦州(治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为平州(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支郡。《辽史·地理志》:“滦州,永安军,中,刺史。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统县三:义丰县,本黄洛故城。黄洛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于濡水。汉属辽西郡,久废。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户四千。马城县,本卢龙县地。……石城县,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徒置以就盐官。户三千。”(16)脱脱,等.辽史·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501.《辽史》卷60《食货志下》所载辽朝食盐产地之一有阳洛城,但未载其所属何州。陈晓菲等有关研究者均谓这里的“阳洛城”应即滦州“黄洛城”之误,宜为可信。从辽朝南向“徒置”石城县治五十里“以就盐官”的记载可以明晰地看出,辽朝在濒临渤海的滦州石城县境内肯定置有盐场。滦州倚郭为黄洛城,石城县为滦州属县。《食货志》所载阳(黄)洛城产盐与《地理志》所载石城县有盐官(榷盐院之属),二者所记应为一事。
2.析津府香河县盐场
辽香河县(治今天津市宝坻区)为南京析津府属县。《辽史·地理志》:“香河县,本武清孙村。辽于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香河、潞三县户置。在京东南一百二十里。户七千。”这里的新仓榷盐院,始建于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金刘晞颜《新建宝坻县记略》载后唐庄宗命赵德均镇守芦台军,“遂因芦台卤地置盐场。又舟行运盐,东去京国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阔,因置榷盐院,谓之新仓,以贮盐。复开渠运盐,贸于瀛、莫间,上下资其利”。幽云十六州之地属辽之后,辽朝升幽州为南京,“因置新仓镇。其后,居民渐聚成井肆,遂于武清北鄙孙村度地之宜,分武清、漷县、三河之民置香河县,仍以新仓隶焉”。金朝天德三年(1151),“诏建都于燕京。於时畿内重地,新仓镇颇为称首,以榷院自赵德钧创始以来,历辽室及国朝二百年,每岁所出利源不竭,以補国用故也”(17)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869.。
刊石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的天津宝坻西街《广济寺佛殿记》碑文有“属以新仓重镇,……而复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1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76-177.之语。《大金国志》卷3《太宗纪》载辽朝灭亡的“天会三年(1125,辽保大五年)冬十一月,斡离不军至燕山府盐场”。这里的“燕山府”即为辽朝南京析津府,金人攻取后,更府名曰燕山,改军名曰永清。所谓“燕山府盐场”,自然是辽时旧有盐场,或与香河榷盐院所属盐场有关。
3.景州永济盐场
辽景州(治今河北遵化市)为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支郡。《辽史·地理志》:“景州,清安军,下,刺史。本蓟州遵化县,重熙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据大安九年(1093)沙门志延撰文的《大辽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辽景州“北依遵化城,实前古养马之监;南临永济院,乃我朝煮盐之所”(19)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这里位于遵化城南的“永济院”,应指辽朝设在永济盐务的盐院。元孙庆瑜《丰润碑记》:“古蓟界曰永济务,闻之父老云,在昔金大定间始改务为县,至大安初避东海郡侯讳更名丰润。”据刊石于重熙八年(1039)的辽《赵为干墓志》,出身世宦之家的赵为干曾受“命监永济盐院。任循一载,课余万缗”。辽朝税率与宋朝相比,要明显偏低。北宋谏官余靖在一次写给仁宗皇帝的报告中称:“臣常痛燕蓟之地入于敌中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以外域(指辽朝)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3852.赵为干在较低税率的社会环境下,任永济盐院都监一年,即可实现“课余万缗”的税收政绩,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永济盐务规模之大和产盐数量之多。
4.芦台军盐场
“芦台军”又作“卢台军”,始建于唐朝末年刘守光割据燕地之时,治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古时以地当蓟运河入海口,因于此置海口镇。前引金代刘晞颜《新建宝坻县记略》:“唐末刘仁恭帅燕,其子守光僭称燕王,置芦台军于海口镇。以备沧州。后唐庄宗命大将周德威破燕军于平冈,复收芦台军。(后唐)同光中(923—925),以赵德钧镇其地,遂因芦台卤地置盐场。”《旧五代史》卷113《周书·太祖本纪》载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壬子,沧州奏,契丹幽州榷盐制置使兼坊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张藏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据《宋史》271《张藏英传》,张藏英为范阳人(今北京市),初为后唐幽州节帅赵德钧部下。入辽后,“契丹用为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领坊州刺史。周广顺三年,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兵千余人,及煮盐户长幼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关于中原典籍所载张藏英曾任职的辽“幽州榷盐制置使兼坊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在今本《辽史》中未留任何信息。考赵德均系于辽天显十一年(936)十二月于后唐败亡之际率众降于契丹,作为赵德均部下,张藏英很可能也是于此时被一起裹挟入辽的。《辽史·地理志》不见坊州,则其所担任的坊州刺史可能属于虚授。既然卢台军是后唐庄宗时(923—925)由赵德均攻取于刘守光之手,且“以赵德均镇其地,遂因芦台卤地置盐场”,则张藏英所担任的“幽州榷盐制置使”和“知卢台军事”很可能是原在后唐时的职务,入辽后仍司其职,并保留原来的职衔未变。张藏英投奔后周时,所率煮盐户长幼多达七千余口,于此足见辽卢台盐场生产规模之巨。可以肯定,卢台盐场尽管于《辽史》失载,但如此规模的盐场,绝不会以张藏英的奔周而停业关闭。元人王鹗《三汊沽创立盐场旧碑》所谓“燕京所辖有县曰宝坻,芦台,越支,畴昔之盐场也”(21)王鹗.三汊沽创立盐场旧碑[M]∥续修四库全书:第8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即其证明。
三、辽朝的海盐产业管理
在古代中国,盐铁均属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秦汉以来,历代政权均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制度,辽朝自然也不例外。大体说来,辽朝实行的盐务官营专卖管理内容,在上京道、西京道所在的内陆地带,以池盐为主,而在东京道、中京道和南京道所在的濒海地区,则以海盐为主。
(一)辽朝的海盐管理体系
迹象表明,有关辽朝的盐务管理体系,在辽人耶律俨主持官修的《辽朝实录》中,没有留下专门性的记述。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元人修撰《辽史·食货志》时,只能从散见于《纪》《传》《职官》等辽人旧史中钩沉辑录相关信息。因此,荒疏粗陋自然也就在所难免。该《志》曰:“(辽于)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22)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3.又曰:“盐策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其煎取之制,岁出之额,不可得而详矣。”(23)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0.
根据上述史文,可以大体知道,辽朝的海盐管理体系,主要有设在诸京的计司和设在州县的榷院两级管理机构。
1.诸京计司
辽朝设在诸京的计司之官,是为国家的最高财政税收机构。其名称各异,并不一致。《辽史》卷48《百官志》:“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具体名目见有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亦曰燕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
诸京计司的最高行政长官称“某京某使”。如王棠,重熙中为上京盐铁使。或称“知某京某使事”,如张孝杰,清宁间曾知东京户部使事。副职称“某京某副使”,如刘伸,重熙中曾为南京三司副使。又称“同知某京某使事”,如道宗大康三年,挞不也同知中京度支使事。使、副以下,分掌各类具体事务的官员称“某京某判官”。如马人望,曾先后“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转南京三司度支判官”(24)脱脱,等.辽史·马人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62.。至于中原文献所载后周广顺三年(953,辽应历三年)自辽朝回归中原的张藏英所担任的幽州榷盐制置使一职,在今本《辽史》和辽人碑铭中,迟到辽圣宗朝以后才有零星记载。所以,不宜视为辽朝盐官系列的常态,更不宜视为辽朝设置的最高盐务官员。
上述诸京计司称谓虽有不同,但其职掌却基本相同,均主管一京之地的财政税收。所谓“(契丹司会之官)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25)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5.。其中设在东京的户部使司、中京的度支使司、南京的三司使司、转运使司,其基本职责之一便是对所属之地的海盐产业实行统一监管、统一运输、统一作价,计值征税。
辽朝的税制,是随着契丹帝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而逐渐完善起来的。《辽史·食货志》:“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辽朝的田租地赋,主要参照唐末税法,奉行以钱计征,因宜折纳的两税法原则,即以货币计价,视各地物产的区别,折变成刍粟或绢帛交纳。这种税制原则,同样通行于工商之税。所谓“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三司税钱折粟”(26)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6.。史言统和四年(986)“六月,南京留守奏百姓岁输三司盐铁钱,折绢不如直,诏增之”(27)脱脱,等.辽史·圣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
中京道所属居民及其盐场,分别向东京户部使司和中京度支使司交纳盐税。锦州所辖居民和盐场,辽朝规定其输盐税于东京户部使,“东京置户部使,辽西、川、锦等州隶焉”(28)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5.。有如此规定,当是因锦州设置于太祖时期并有人民定居于此,位于安昌县境的红花务盐场极有可能在太祖时期已经存在,而中京行政建置晚至圣宗时期才得以完成。锦州所统居民和红花务盐场,由东京户部使司统领并对其征收盐税。余靖记锦州赋税归属于东京户部使司一事,是辽兴宗时期(1031—1055)所见情形,此隶属关系可能持续到辽朝灭亡。当然也存在改归中京度支使司管辖的可能,但可能性极小。中京道所统辖的其他各州,当向中京度支使司纳税。来州所属之民和海阳盐场、海滨盐场,受中京度支使司管辖并向其交纳盐税。中京度支使司设有盐铁判官,专门负责中京境内的盐税征收。马人望曾任此职,“帝问以外事,多荐之,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29)脱脱,等.辽史·马人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62.。
2.榷盐院
史书和石刻材料明确记载,辽朝对盐业实行官营专卖制度,于各地海盐产地置榷盐院专门负责盐业的生产、管理、转输和销售。目前可考者,辽于东京地区设有辰渌榷盐院,主政者分别为院使和都监。墓志材料记载孟有孚曾为辰渌盐院使,梁庆先曾“监辰渌盐院,其刚清秉训于官课外,酬数有八”(3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568.。
又据辽《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张检曾为甜水盐院都监、知东京警巡使、兼辽阳少府(31)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661-663.。所谓甜水,是指相对于海水的淡水。这是居住于濒海地域居民的常用语汇。这位张检的主要任职背景都在东京地区,据此可以认为,这里的甜水盐院,似乎也应在东京地区。
辽朝设在南京地区的榷盐院有永济盐院和香河榷院。赵为干曾监永济盐院“任循一载,课余万缗”(3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20.;“(李继成)监都盐院,煮海繁司,羡余倍积”(33)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87.;王泽“前后两督盐务,膏奋无润,常调之外,□缗二万”(34)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5.;刘祜“再督榷盐院,聚帛镪五十余万”(35)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236.。
关于榷盐院使、监的行政能级别,史无明文记录。考赵为干监永济盐院一年后,辽廷认为其“盖负贞材,复迁列郡。重熙七年,使持节沂州诸军事、行沂州刺史”(3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20.,茹雄文在榷盐院都监任上期间,以政绩显著,“上旌其勋,改授安德州刺史”(3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184.。孟有孚“曾知泰州乐康县,甚有佳政,朝廷亦闻之。及受代,为辰渌盐院使”(3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47.。辽制,州一级刺史秩比县令。由赵为干等人的任职履历,能够推知辽朝设在各地的榷盐使、监品级与刺史大体相当。辽朝除设榷盐使和都监主管盐院外,还应设有专司海盐生产、贮存、征税、销售等职能的盐务官。只是限于史料记述,其具体官职名称不详。
(二)辽朝海盐的产量与收益
有关辽朝海盐的产量与收益,今本《辽史》失载。所谓“其煎取之制,岁出之额,不可得而详矣”(39)脱脱,等.辽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0.。《三朝北盟会编》卷14《政宣上帙》收录有金人攻陷辽朝南京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天辅七年(1123)致书宋朝皇帝,要求北宋出资赎取幽燕之地。其计资的依据和筹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辽宋结盟之际,宋朝每年向辽朝输送的50万两银绢再加上燕京所属州县“每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计钱100 万贯文”。
二是原辽南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随院务课程钱,及折算所辖人户输纳税色,依约见值市价做钱共5 492 906贯800文(含课程钱1 208 416贯,税物钱4 284 860贯800文)。金太祖在致北宋的国书中称上述钱数由原辽三司使司课征的“计4 913 120贯文(内有房钱诸杂钱1 158 789贯文是院务课程钱,榷、永两盐院合煎盐22万硕,合卖钱39万贯文。诸院务合办卖随色课程钱433 212贯文,3 754 422贯是人户税租正钱)”。由南京制置司课征的“计579 687贯800文(官民税钱49 348贯,课程钱530 438贯800文)”(4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1.。
据笔者核对,金太祖在致宋朝国书中所开列的原辽朝南京计司每年所课税钱的几笔收入数据均不准确,究竟是传抄之误还是一开始就误,不得而知。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这里最关心的是金人国书中透露出来的辽朝灭亡之际,辽南京地区的海盐产量及其收益信息。
其一,金人国书中提到辽南京三司使司岁征课税4 913 120贯。其中院务课程钱1 158 798贯,内含榷、永两盐院所产海盐总值39万贯。这就是说,辽朝南京地区的海盐收入约当三司使司全部收入的8%。由此可以窥见辽朝海盐收益之一斑。
其二,据金太祖致宋朝国书,辽南京地区岁产海盐约22万硕(石)。以此类推,则辽朝东京、中京和南京地区每年所产海盐总量当不会低于50万硕(石)。宋代一硕(石)谷物约当现在120市斤,海盐的比重要远大于谷物。即便是以120斤计,50万硕(石)也得6 000万斤。由此可见辽朝海盐产量之大。
其三,据金太祖国书,辽南京岁产海盐22万硕,合卖钱39万贯。若以每硕120斤,每贯1 000钱计算,则当时的辽朝盐价约为每斤14.78文。又,《三朝北盟会编》载《陷燕纪》为辽时盐法“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4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6.,按这个数据标准计算,则当时辽朝海盐价格约为每斤11 .7文。总体看来,辽朝的盐价确实很低。这种情况,与同时期宋人的辽朝“盐麴俱贱”(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3852.说法正相吻合。
以上所论辽朝海盐产量与收益,只是对照的官方数据。至于民间和私盐生产与销售,情况更为复杂。在《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等中原典籍中,有关辽人走私海盐的记录,可谓连篇累牍:“北人或由海口载盐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边吏因循不能止”(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4671.,“(契丹民)后又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44)脱脱,等.宋史·赵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496.,“今沧、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45)脱脱,等.宋史·张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934.。基于这样的现状,北宋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写给宋仁宗榷河北盐时的劝阻报告中说:“今未榷,而契丹盗贩不已,若榷则盐贵,契丹之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契丹获福也。契丹盐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46)脱脱,等.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28-4429.由此观之,辽朝人由海上贩卖私制海盐至宋乃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常态行为。
以上所论,虽然远谈不上全面深入,但从中却足以看出契丹开创的草原帝国所蕴含着的至为重要的海洋人文因素。在辽代二百余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辽海地区还同时存在着一个海洋人文的小系统。在传统的辽朝史观中,辽代历史始终是按照北部推行契丹式的部族制、南部实行汉式的州县制的内陆人文路向发展。其实,这样的史学定位,并不能概括辽朝历史发展的全貌。辽阔的海域空间与广袤的陆域草原,都是辽朝借以实现非凡军政运作的重要历史舞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海陆互动,使拥有悠久海洋文化传统的辽海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实现了与中原内地的深层整合,因而能够在金元之际,最终与中原内地融为一体而不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