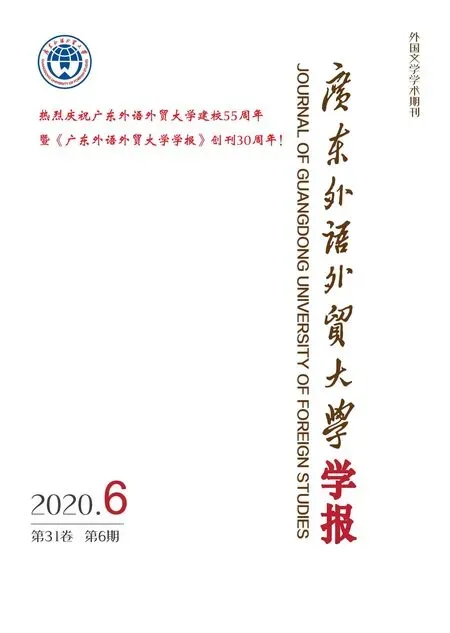从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到构建伦理共同体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共同体思想研究
2020-03-03肖旭
肖旭
引 言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以多产和深刻反映美国现实著称。在作品中,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特质的欧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作家创作与前人传统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评判。格兰特(Mary Grant)结合此类主张概述了其小说中城市内社群缺失的三大原因:“流动性所打造的‘陌生人的国度’,个性缺失所导致的异化,与其他人联系过少加剧了疏离感”(Grant, 1978: 80)。克莱顿(Joanne Creighton,1979: 144)则总结:“处于欧茨思想及作品核心的是她关于人类经验的远见卓识,即她相信我们文化中的自我意识能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得到超越”。科隆-布鲁克斯(Gavin Cologne-Brookes, 2005: 228)指出欧茨并未将个人主义与社会行为看作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着眼于呈现个体行为的可控性。欧茨的此类主张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林斌(2003)以《奇境》(Wonderland, 1971)和《婚姻与不忠》(MarriagesandInfidelities, 1973)为基础分析其创作过渡时期的艺术观,认为这两部作品宣告了她旨在颠覆“孤立艺术家的神话”从而在艺术与社会、公众以及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关联的艺术观的诞生。刘英、栾红敏(2008)以学院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主题顺应了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转向,“在意义消失、信仰沦落的后现代沙漠上,重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欧茨关于个体与社会、艺术与公众之关系的主张契合了西方思想界自十八世纪以来兴起的共同体观念,此类思考可以统一概括为她关于个体与社群之关系的共同体思想。然而,国内外学界对此还未上升到共同体思想的高度审视,还未与其跨度达五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系统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以欧茨在不同时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为基础,归纳其共同体思想,并结合其部分作品,审视这一理念是如何体现的。
用社群意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藩篱
欧茨对个体与社群关系的思考始于对英国女诗人普拉斯的评论,她认为在其诗歌及私人生活中,她代表了一种濒临死亡的旧意识,文艺复兴以来腐朽的理想及其“自我”性,这与其他意识均不相容,只能被取代,否则就会给“自我”带来痛苦。这一极具男性气质、好战的“自我意识”在文明发展的某一阶段能让“自我”区别于其他“我”——同时也区别于自然界——对于把人从对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的苦思冥想中解放出来,并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但是在现今社会其存在则是多余的,这一意识已然成为一种病态,任何还执着于这一过时理念的人都将灭亡(Oates, 1973b)。她认为只要这一孤立与竞争性的“自我”神话存在,我们的社会就依然会迷恋于那些高人一等、征服与毁灭的幼稚的想法(Oates, 1973e)。“自我中心主义”始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解放,从强调神的重要性转而强调人的重要性,尽管它把人从对上帝的崇拜中解放出来起了积极作用,但过分强调人的重要,及由此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则给社会及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超越,她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正在朝着社群意识转化。对此她充满信心:“从自我中心的人性向更高级、超验的人性的‘转化’不可能是人为的、由外力影响的过程,应当是自然发生的”(Oates, 1972)。她的超越论断,绝非凭空捏造,是在博览群书,对西方社会体察后得出的。西方世界对自我的崇拜与看重由来已久,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常有对英雄般的个人描写,但往往忽视个人成功原是依赖他人相助。欧茨赞同超越“孤立的自我”这一西方长久以来粉饰的神话,主张“自我”与“他者”联合,超越自身局限。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有助于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没有这一结合及随之而来的转变,人类注定要灭亡”(Oates, 1973d: 5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她又进行了深入思考:“人类不仅要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贪婪的主张,还将命运同一条与其内心所求并不相关的绝对真理联系到一起,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悲剧”(Oates, 1978: 560)。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剧,由工业化带来的商品的极大丰富,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人类的欲望,导致“自我”膨胀。她指出,如果曾经存在过人与所属社群及自然的和谐,那么现在,这一和谐一去不返了。这就将人类社会的悲剧总结为“自我中心主义”影响下的“小我”与“大我”的分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她又将这归结为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社会影响的投射,受此影响,艺术“聚焦于个体,或相关的某一群体,进而对危险的人类自我大加赞颂”,她感叹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处于显著位置,我们的重要性无以复加”(Oates, 1999: 50)。
的确,由文艺复兴解放了的个体所带来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扩张催生了竞争性的人际关系,随之而来的私欲膨胀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悲剧。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及商品的大量生产又刺激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扩大欲望的投射范围,加剧自我与非我的分裂。现代性商品经济带来的竞争性关系则表现为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社会关系上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资本主义兴起,再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欧茨系统回顾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历程,可见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持续且长久的。她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认为艺术“能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Oates, 1973c: viii)。这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功用之一,也是作家的职责。在她看来,“艺术应该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并最终通过唤起他人潜在的同情心以达到提升的目的”(Avant, 1989: 31)。通过小说唤起情感共鸣,进而实现对人的提升,她将提升的标准界定为对人道德提升的层面,认为艺术作品有道德和“非道德”之分:“使人终身受益(的作品)对我来说是道德的;对人有破坏性的(作品)则是非道德的”(Cologne-Brookes, 2006: 549)。她强调文学的“宣传和教化功能”,期望“作品能够启迪与自身经历完全不同的读者”(Oates, 2014)。欧茨通过反思,想到用文学来实现超越,通过文学对人的情感、道德影响,唤起社群意识,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类的提升。从发现弊端,到提出解决方案,实现超越,达至提升,她渴望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这便是她的共同体思想。
用社群意识构建作家与前人、作家与读者的共同体
如果说用社群意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主张有稍显空洞的嫌疑,在创作中,欧茨则自觉践行这一理念。在创作上,她不主张孤军奋战,强调艺术与社会、艺术家与所属社群的联系,这与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共同体思想的倡导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不谋而合。麦金太尔(2011:281)指出,“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一般而言,无论我是否喜欢它,无论我是否承认它,我都是一个传统的承载者之一”。的确,艺术创作不是孤立的,是汲取多方营养,综合而成,艺术家个体的声音即群体的声音,虽然“每个故事都各具特色,但也是更大群体叙事的一部分,好比大河都是由无数支流汇聚而成的”(Oates, 1986: vii)。欧茨认为作家是其所属文化的一部分,是其所在的文学与知识遗产的传承者:“我认为自己身处浓厚的(文学)传统中,其他作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今日的我”(Clemons, 1989: 35)。她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在汲取前人丰富的文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部长篇《抖落》(WithShudderingFall, 1964)有向《呼啸山庄》致敬的元素;小说《人间乐园》(AGardenofEarthlyDelights, 1967)在标题上借用了荷兰画家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同名画作,结构也存在一致性,该画以三联式的结构呈现,小说也通过相应的三部分展现了女主角悲剧的一生;小说《奇境》(1971)能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影子,同爱丽丝一般,主人公杰西在家庭遭遇父亲持枪杀戮后,也经历了自己的奇境漫游;《任你摆布》(DowithMeWhatYouWill, 1973)则通过戏仿童话《睡美人》的情节隐喻了主人公女性主义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查尔德伍德》(Childwold, 1976)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洛莉塔》(Lolita, 1955);《光明天使》(AngelofLight, 1981)借用了古希腊神话阿特柔斯之家的故事,背叛与复仇的主题被巧妙地嵌入到这部关于华盛顿上层政治与家族复仇的小说中。
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更是如此。她有部分短篇改写了同名经典作品,包括詹姆斯的《拧紧螺丝》、卡夫卡的《变形记》、乔伊斯的《死者》和契诃夫的《牵小狗的女人》。在改写过程中,她重新设置了背景并部分改换了叙述视角,这就在对经典致敬的过程中体现了创新。文学创作不可能不受影响地在真空中进行,作家正是在汲取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是个体叙事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时代叙事的洪流,“正是由于个体视野的结合以及打造出群体乃至共同视野之渴望的存在,艺术与技法得到了融合”(Oates, 2003: 126)。她的文学生涯体现了作家个体的文学创作与前人遗产之间的紧密联系,她也身体力行地实现了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超越,构建作家与前人的共同体。
其作品内涵上,更多体现对“自我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思考。小说《人间乐园》(1967)的克拉拉、《阔佬》(ExpensivePeople, 1968)的理查德、《他们》(them, 1969)的朱尔斯以及《奇境》(1971)的杰西都是自我欲望过分膨胀,给自己、家庭及社会带来损害甚至毁灭的反面教材。而在小说《不神圣的爱情》(UnholyLoves, 1973)中,“竞争性自我”意识使得其中的伍兹利大学教员为了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不择手段地排斥他人、争权夺利,在一出出闹剧中这所大学俨然成了人性异化的荒原。《大瀑布》(TheFalls, 2004)则凸显了她对由这一意识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思考,人类对物质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忽视了自身与环境的联系,给他人的生存带来威胁。《诅咒》(TheAccursed, 2013)展现了种族主义、保守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认为特定群体的排他行为是“自我中心主义”在种族及人际关系影响上的扩大化。
她的小说存在很多暴力、血腥、乱伦等非道德的场景描写,这大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膨胀带来的人间悲剧,她期望展现悲剧,让读者反思如何不再让悲剧发生。通过文学作品的反向作用,引发读者正面的思考,这是她对小说的期望,也是她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构建作家与读者之间共同体的体现。她认为,“小说当然对人的精神与道德有指引作用;有时,从伟大的古典悲剧(如《麦克白》)中我们得到的是不去怎样生活的正面指引”(Cologne-Brookes, 2006: 547)。这也可看作其作品暴力描写的注解。她曾说过,作品中的暴力对她来说并不丑陋或是带来道德上的不快,仅仅只是真实(Oates, 2005: 351)。正是由于作品中极具真实感的暴力场景描写所带来的恐怖及深远影响,使读者反思在现实中不去施行暴力,从而减少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悲剧的可能,实现道德提升。
对于自己大多关注社会现实题材在当今的文学语境下稍显过时的论断,她回应:“美国主流文学对社会弱者和穷人的同情,十九和二十世纪小说极力展现社会不公的努力依旧是我们最突出的文学传统,即便在过度强调自我的后现代也毫不过时”(Oates, 2016: 25)。展现不公是为了让读者反思不公,进而实现超越,这便是艺术对受众的反向影响。她解释道:“艺术应该能激发我们的情感,唤起同情,且是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产生的”(Oates, 2000: xx),暴力与社会不公及唤起读者情感波动,进而反思的作用,恰恰是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产生的。这是她期待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也是艾略特和劳伦斯提到的“情感延伸”,她对此特别推崇,认为“如果理想读者通过严肃小说体会了经典的‘情感延伸’的话,那么据此可以断定,沉浸于实现这些情感的作家,也经历了同样的视野的延伸”(Oates, 1988: 23)。这是她对自己作品能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期待,也渴望作品能成为构建作者与读者之间共同体的桥梁。当然,她不总是对读者进行反向影响,小说中有个人意志过于膨胀而给自我、家庭和社会带来危害的例子,也不乏积极向上的故事:《大瀑布》中的律师波纳比为了探寻污染的真相,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狐火》(Foxfire:ConfessionsofaGirlGang, 1993)中反对歧视,以暴制暴,试图匡扶正义的少女;《牺牲》(TheSacrifice, 2015)中秉持种族正义立场的女检察官,他们趋向于用社群意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给读者带来正面影响。此外,《玛雅的生活》(Marya:ALife, 1998)以及《泥女人》(Mudwoman, 2012)的主人公无不是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穿过暴力与恐惧,获得了成功。这些都对读者有积极向上的指引作用,让作者与读者产生真正的联系。她的文学创作是其共同体思想的最佳诠释。
改造世界:欧茨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性特征
西方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对人的影响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悲剧的“净化”功能。欧茨同样重视艺术作品对人的心灵的治疗作用,她认为,艺术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且以我们难以理解地方式发挥作用。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超越主人公所在世界局限,甚至是超越小说本身美学局限的“经历”(Oates, 1973a)。在她看来,“在受众中唤起共鸣,及随之建立的艺术家与社群的联系,还有艺术家在社群之反馈下的重生,对我而言是毋庸置疑的”(Oates, 1999: 53)。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到悲剧唤起观众怜悯的功能,欧茨比亚氏更进一层,除了唤起怜悯外,她展现暴力与不公是为了让读者反思由此带来的悲剧,进而不去施暴,因此更具现实意义。强调小说的目的性,对读者的影响作用,在表达文学主张上的超越性,加上赞同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净化功能,唤起读者怜悯,使得她的主张具备在现实文学创作中可操作的实际意义。
欧茨通过相互联系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主张的思想渊源也可追溯至西方近现代以来对“个人主义”过度膨胀给社会、个人带来危害的思考上。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崇尚个人主义和自决权力,正是这一完全的自由,使人勇于去开拓地理、社会的未知领域,从而对欲望与能力产生了加倍要求,现代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大多与此相关。但欧茨与一些社会学家着眼于理论建构不同,她倾向于用文学创作来影响读者。其超越“孤立艺术家的神话”、通向社群意识的主张,融入一部部深刻的文学作品中,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她尝试对这一社会问题开出药方。
在谈及所属社群对个体行为之影响时,加拿大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002:86)指出,“具有构成特征的社群,为有意义的思考、行动和判断提供一种大体上是背景性的方式,一种生存在世界上的方式”。欧茨思考并行动的最大背景是她身处的美国社会,作为一个美国人,她的创作是基于美国社会现实的。她的文学创作深入美国社会的多个层面,堪称当代美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但她的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现实,还要通过现实触及人的内心,构建作家与读者的共同体,并参与文化的构建。她坦言,“我相信我们渴望超越有限而短暂的人生,去参与那神秘、共同的,称之为‘文化’的东西”(Oates, 2003: 1)。她渴望超越自我,通过作品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渴望与不同作家、读者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这正是她对社群意识之渴求的体现。她相信“伟大艺术家的重生只能经由与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且全情投入的读者的联系而实现”(Oates, 1999: 295),这说明她渴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产生影响。殷企平(2016)指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无数优秀的文学家,他们在倡导/想象共同体时并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实践”。欧茨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同马克思等哲学家一样,注重实践,意在改造世界。突出小说对读者的影响,特别是对其伦理、道德层面的提升,虽然在后现代注重写作技巧的时代让她显得些许另类,但恰恰是强调对读者的影响,与读者建立共同体,是美国文学传统在她文学创作上的延续,也是其共同体思想立足美国现实的具体体现。
欧茨(Oates, 1990: 159)曾坦言,“我们写作确实怀着改变世界的期望,尽管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但她接着反问:“难道改变单个读者意识的行为,不管有多么细微,不正是朝着改变世界的方向努力吗?”把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是她在文学创作中体现的共同体思想。尽管小说中充满了暴力元素,那是她对这一混沌世界的真实再现,但她绝非一位悲观至上的作家,而是对社会、对人类发展充满信心:“人类是唯一可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物种,(作家作为)其中最具想象力的一群人不仅会想见自己的未来,也会预测整个社会的未来,这一想象并不是被动地受时下某些思潮的影响,而是基于对未来的独立思考”(Oates, 2009)。这是作为作家对时代、对人类发展的使命,也是其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性特征。
结 语
欧茨怀着对文学的乐观期望,渴望超越西方社会长久以来的诸多弊端,特别是“自我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试图在文学生涯及作品中实现超越,在道德层面对读者有所提升,进而构建与读者的伦理共同体。她曾谈到心目中伟大作品的标准:“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视野的深度与题材的广度,应当关怀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情各种不同的人们,通晓并关心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了解政治、宗教、经济及社会道德间的相互作用,关心美学,也许要有形式与语言的实验,但是最重要的要有预见性——作家不单单为自己写作,也要把通过作品传递信息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Sjöberg, 1982)。通过作品传递信息来影响读者从而改变世界是她的文学主张,在她看来,伟大的文学都有道德意义,都具有示范作用。作家不可能脱离前人传统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与个人、与社会存在紧密联系,文学作品要通过影响个体来影响世界,要通过提升人类的道德实现文学改变世界的目标,继而构建起伦理共同体。作为作家她做到了,她的作品也影响了成千上万读者。这便是欧茨的共同体思想,是她作为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