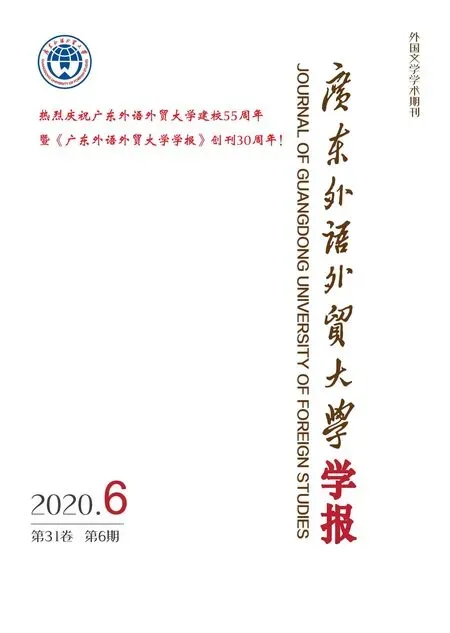纪伯伦《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母题言说
2020-03-03车明明
车明明
引 言
黎巴嫩诗人哈利勒·纪伯伦(Kahlil Gibran)与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齐名,二者并称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纪伯伦的代表作《沙与沫》写作手法独特,“借鉴了西方诗歌中常见的梦幻和象征手法”,同时“大量运用传统比喻手法”(关偁,2011:6-7)。最为重要的是,其中充盈的隐喻性语言具有极强的讽喻性,体现出非凡的人生哲理,《芝加哥邮报》这样评价《沙与沫》:“哲学家认为它是哲学,诗人称它是诗”。得益于诗性隐喻的运用,《沙与沫》句句箴言,字字珠玑,既有诗歌的精练,又有散文的灵动,是一部理性思考与诗性浪漫珠联璧合的佳作。
迄今为止,作为耳熟能详的文学名篇,《沙与沫》更多的是被当作美文来阅读和鉴赏,学界的研究十分寥落,只有汪克慧(2019)、张宗莹(2017)等。目前的研究态势与该作品在文学领域的经典地位不相匹配,在文学、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学术缺口。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针对其作品《沙与沫》进行文学和文体学相结合的研究,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互输和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性隐喻考辩
所谓诗性,除了诗意化的语言、意境、修辞及格调等,更是“一种难以把握,甚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社会生活、自然状态和精神感觉的复合体”(陈剑晖,2009:5),故诗性的捕捉和领悟“需要借助于超拔的想象力,需要融进诗歌的艺术感知方式,比如意象的营造、意识的流动、时空的跳跃、音乐的旋律、节奏,乃至通感、隐喻、变形、倒错,等等”(陈剑晖,2009:6)。概言之,“诗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范畴,它既指作品的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也指作家的心灵外化和情思洋溢”(车明明,2020:106)。
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是人们借助具体的事物来理解较为抽象的事物,或利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未知的事物(Lakoff、Johnson,1980:5)。隐喻的另一本质就是所谓的“隐喻法则”,即“比喻意义源自字面意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字面意义”(Leech,1969:15)。事实上,利奇(Leech)的以上定义揭示了隐喻的“相似性”(程琪龙,2002:48)本质,即本体(tenor)具有喻体(vehicle)的某些特征。由隐喻的以上两个特点可以看出,隐喻从表面看是在判断、叙述或者说明,但在本体与喻体之间暗含着比喻关系,具有“托物言志”的作用,往往“言近意远”,意义隽永。
作为特殊类型的隐喻,诗性隐喻具有有别于规约隐喻的鲜明特征。首先,诗性隐喻比一般隐喻更具抽象力和表达力,更具“言近意远”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学特征,这是由诗性隐喻的特征决定的。“凡是在本学科中出现一个不落俗套的,从其他学科或义域引入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表述,都被视为诗性隐喻。诗性隐喻的核心成分是创造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突然性、新颖性、美学性等”(胡壮麟,2003:3)。诗性隐喻的这些诗学特征“增添了作品的含蓄性、新奇性、生动性以及启发性”(黄曼,2013:147)。
其次,诗性隐喻较之规约隐喻更具有创造性。诗性隐喻的创造性特征源自诗性思维,“诗性思维利用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机制,但远远超越了它们、阐释了它们,并将它们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组合在一起”(Lakoff & Turner,1989:67),这种基于诗性思维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便形成诗性隐喻的超常规性。超常规性是作家或诗人寄予作品思想感情和人生哲理的重要手段,而且诗性隐喻“效果的达成离不开差异性或距离”(束定芳,2013:46),因而,诗性隐喻的常规性越低,其隐喻性就越高。由于诗性隐喻的超常规性,文学文本便具有“神秘的吸引力、鲜活的生命力、真诚的灵魂感召力和自由的语义创造力”(隋刚,2012:107)。同时,其超常规性也“让作品的奥义得以升华,更让文学作品充满了想象的空间”(黄曼,2013:147)。故而要理解具有突出诗性特征的诗性隐喻也需要诗性思维,需使诗性隐喻和人类体验处于一种交互模式,亦就是认知方面由抽象到具体、再通过具体来构想和构建抽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抽象的时空维度传输到人的感官,与人的思维与精神产生认知互动,从而使人对抽象的对象产生全方位的体悟。
再者,诗性隐喻具有认知性。诗性隐喻通过认知思维,能够帮助读者探索文本的诗性和生命的奥秘。文学作品中往往运用大量的诗性隐喻,作者能够“利用诗性隐喻表达幽默,唤起共鸣,解释抽象,阐述科学,抒发胸臆”(李良彦,2012:99),而读者也能够通过诗性隐喻“探索世界万物存在着的自然的辩证联系,也从这种自然的联系中更为广阔、更为深邃地理解同类,理解自己,反思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徐健,2014:42)。
从以上对隐喻和诗性隐喻的剖析可以看出,隐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它“不单是一个纯语言的问题,而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扩展,即从基本经验到非基本经验范畴的扩展”(刘立华、刘世生,2006:74)。认知诗学强调文学审美过程中文本的审美对象与读者认知之间的互动性,即倾向于在阅读过程中体验文本的审美对象,包括诗性隐喻。据此观之,隐喻一方面具有诗性,另一方面具有认知属性,因而,从学术框架来说,诗性隐喻属于认知诗学范畴。纪伯伦的散文诗主要运用诗性隐喻来实现作品的母题,从而达到托物寓意并举、抒情劝谏兼备的艺术效果,其《沙与沫》是由诗性隐喻织缀的瑰丽诗篇,只有从诗性思维出发,才能有效挖掘其深刻的诗意内涵。
《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母题分析
作为文学用语,母题(motif)指的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并具有传承性因子”(夏延华、陈红薇,2014:89),是特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与主题类型化特征相关的因素,它将抽象的哲思具体化、模式化,构成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重要元素。母题往往以一致的,始终如一的主题、原型、象征、意象等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母题是主题”“母题是原型”“母题是象征”“母题是意象”。总之,母题是文学作品的主题或本题,是表达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是统一整个作品的主体线索和纽带,“没有母题,主题思想也无从表达”(赫云、李倍雷,2017:137)。散文诗《沙与沫》中诗性隐喻俯拾皆是,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诗性母题。
纪伯伦的生命始终被孤独缠绕,也与自由的现实和梦想相交织,更是浸没于生与死的思索当中,因而,“自由”“孤独”“生死”形成纪伯伦作品的三大主题。一方面,自由的人是无所牵绊的,但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孤独,此为生命的悖论。纪伯伦是孤独的,他的孤独赋予他自由的躯体和灵魂,可当人自由到与世界无可瓜葛,便只剩下孤独了,故而自由的人会感到倍加孤独。纪伯伦孤独的缘起在于他孤苦的出身和因孤苦而形成的性格,或曰他与生俱来的秉性,因为“人生而孤独”,这是人生的真谛,概莫能外,天才和诗人尤甚。另一方面,死亡也是纪伯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对于纪伯伦来说,一个人死亡了,世间其他的生命依然生生不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死亡恰恰彰显了生命的厚重;更主要的,“对于弱小者,诸如受欺压的穷人、被凌辱的女子、寂寥一生的诗人,死亡是精神的救赎”(马征,2010:216)。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自由”“孤独”“生死”三个方面来剖析《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母题,以期阐释这些诗性隐喻所蕴含的深奥哲思。
(一)自由
纪伯伦终生歌颂自由,他对自由的追求永不停歇,而他所谓自由的内涵也因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年少时,他对自由的追求是盼望摆脱压迫奥斯曼帝国残暴统治、获得人身的解放和自由的强烈愿望;成年后,他对自由的追求是对人类精神的解放之和灵魂的自由,成为更大范畴的自由。下面通过《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例子来欣赏他对自由所吟诵的赞歌。
(1) 一粒沙是一片沙漠。
(A grain of sand is a desert.)
(纪伯伦,2016:169)
这里,“一粒沙”映衬着卑微的生命,这生命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像浩瀚无垠的“一片沙漠”一样不可忽视。“一粒沙是一片沙漠”,这正是诗集《沙与沫》母题的由来,是诗集之诗旨的高度概括。这个看似悖谬的隐喻论断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沙粒虽然微小,但它是整个沙漠的化身和象征,微小代表着庞大,所谓“见微知著”。在纪伯伦笔下,一如渺小的生命可蕴含伟大的灵魂,人无论尊卑都享有自由,所有独立的生命个体在心灵上都是自由的。
“一粒沙是一片沙漠”,该诗性隐喻透出怡然自得、自我洒脱的人生真谛,也是整个诗集关于“自由”母题的绝好例证。
(2) 每一颗种子都是一个渴望。
(Every seed is a longing.)
(纪伯伦,2016:181)
如上所言,童年遭受压迫的纪伯伦向往人身的解放和自由,而作为不羁的诗人,他更是渴望灵魂的自由。纪伯伦渴望冲破精神上的藩篱,渴望精神自由的种子在纪伯伦的内心发芽,犹如种子渴望破土而出一样,他的自由之花经过浇水、施肥、时间的洗礼,穿过石块和泥土,露出枝芽,最终在阳光下欢笑,在微风中舞蹈,在细雨中歌唱。“每一颗种子都是一个渴望”“信仰是心灵的绿洲”(纪伯伦,2016:231)、“春天的花儿是天使们早餐桌上所谈论的冬天的梦”(纪伯伦,2016:233),这些诗性隐喻都是纪伯伦渴望灵魂自由的深情呐喊。
(3) 你若满嘴食物,怎能开口唱歌?你若满手金钱,怎能举手祝福?
(How can you sing if your mouth be filled with food? / How shall your hand be raised in blessing if it is filled with gold?)
(纪伯伦,2016:189)
这个诗性比喻看似直白质朴,其蕴含的道理却栩栩如生:贪婪的欲望是奴役自由的本源,物质的羁绊会束缚人的身体,让人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傀儡。纪伯伦通过诗性隐喻的形象类比告诫人们,人一旦成为物质世界的奴隶,便无法得到精神的超逸和自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不应被物质所奴役,或被金钱所驾驭,而应摆脱物质的负累,使自己享有精神的自由。
在该诗性隐喻中,第二人称的使用让人感觉到俨然纪伯伦自己正在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的睿智淡定也似乎会悠悠然传递给读者,这正是诗性隐喻独有的美学性所绽放的力量。纪伯伦不露凿斧地鞭辟了自由的内涵,歌颂了自由的母题。
(4) 我们全都是囚徒,不过有的关在有窗户的牢房里,有的关在没窗户的牢房里。
(We are all prisoners but some of us are in cells with windows and some without.)
(纪伯伦,2016:207)
生命的禁锢无所不在,一如“人是囚徒”,生命本身也是囚禁的过程。如是观之,人的自由自然弥足珍贵,而热爱自由的人总会在囚禁中寻找自由,探寻自由的希望,寻找“牢房里的那扇窗”。在该诗性隐喻中,“有窗户的牢房”犹如黑暗中的曙光,表达了纪伯伦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虽然在寻求自由的道路上障碍重重,虽然“自由是最坚实的锁链……它的链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伯伦,2016:79),但人永远要追求心灵的放飞、精神的解放,永远不能放弃希冀。纪伯伦用“囚徒”及“牢房”的诗性意象形象地喻指了“自由”的无奈,而用“窗户”生动地表现了自由的希望。
(5) 我是个旅行者,也是个航海者,我每天在自己的灵魂中发现一个新区域。
(A traveler am I and a navigator, and every day I discover a new region within my soul.)
(纪伯伦,2016:223)
纪伯伦以“旅行者”与“航海者”自喻,彰显他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对他来说,生命是自由的,灵魂与精神同样是自由的。对于自由,纪伯伦向往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自主、灵魂的自由、精神的超然。他既是“旅行者”,也是“航海者”,可以在精神的世界里纵横驰骋,开拓自由的“新区域”,这正是他奔放不羁的诗者之心的诗意体现。
有别于“生命是个旅途”(Life is a journey)这个常规隐喻,纪伯伦以“旅行者”“航海者”这种超越经典的诗性隐喻表达了他追求自由的内心诉求,拓展了隐喻的外延,展现了诗性隐喻非凡的美学性及超常规性。
(二)孤独
孤独似乎历来都是哲人和圣者的特权和独享。“孤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生存方式。孤独是智者的知性生活达到超出常人境界时的独特感受”(宁一中,2010:151)。纪伯伦孤独的个性与他的经历有关:一九○二年,贫穷和病魔先后夺去了他的妹妹、哥哥及母亲三位亲人,使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母亲的去世让他彻底失去依靠,陷入孤苦伶仃、孤独绝望的境地。作为诗人的纪伯伦是一位孤独的智者,而孤独的纪伯伦并没有颓废沉沦。他在孤独中探索生命的奥秘,并在孤独中追求爱与美,他尽情地享受着孤独带给他的人生沉淀和精神升华。对他来说,孤独就是力量。
下面将对《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例子进行剖析,解读其有关孤独的诗性母题。
(1) 我又一次把手握起张开,掌心站着一个人,满面愁容,翘首仰望,我再把手握起,张开时,那儿空荡荡只有雾。
(And again I closed and opened my hand, and in its hollow stood a man with a sad face, turned upward. And again I closed my hand, and when I opened it there was naught but mist.)
(纪伯伦,2016:165)
纪伯伦的孤独可分为三层。首先,于他而言,孤独是人类的内在本质。他认为,人人生而孤独,概莫能外,“我感到我的孤独并不比别人更深更甚。我们大家都是孤独的”(纪伯伦,1995:284)。在诗集的最开始,纪伯伦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孤独的内心,他如此孤寂忧愁,以致“满面愁容”。只是他虽“满面愁容”,也未忘“翘首仰望”来思索人生的真理,追寻心灵的寄托。然而,在他看来,生命最终似乎难逃孤独的命运,虽苦苦求索,人生依然犹如迷雾,虚无缥缈,因而倍感空虚孤独:“我是一团雾,在雾中有我的孤独,我的寥寂,我的陌生,我的饥渴”(纪伯伦,1995:268)。
(2) 诗不是观点的表达。它是从流血的伤口或是微笑的唇间涌出的一首歌。
(Poetry is not an opinion expressed. It is a song that rises from a bleeding wound or a smiling mouth.)
(纪伯伦,2016:185)
在本例中,纪伯伦将诗比作“从流血的伤口或是微笑的唇间涌出的一首歌”,他独出机杼地将“流血的伤口”与“微笑的唇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联想起来,说明在即便欢乐的生活中,他的孤独与忧伤也如影随形,生活对他来说是哀伤而孤独的,诗歌就是这种孤寂的流露,因而是“从流血的伤口涌出的一首歌”。纪伯伦总有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忧伤,而正是通过这种充满诗性的隐喻化表达,才使他咏叹出深刻的关于孤独的诗歌母题及人生哲思。
(3) 他们说我疯了,因为我不愿意拿时间去换金子。/ 我说他们疯了,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时间会有标价。
(They deem me mad because 1 will not sell my days for gold; / And I deem them mad because they think my days have a price.)
(纪伯伦,2016:211)
纪伯伦孤独的第二层面是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如例(4)所示,在世人眼中,纪伯伦就是一个癫狂之人,一个疯子。其实他有一股砭清激浊的力量,即使被误解、被孤立,纪伯伦依然不畏世俗、不落俗套、坚持真理。他“不愿意拿时间去换金子”,而且他还“在癫狂中……发现了自由和安宁:由孤独而来的自由,由不被人了解而来的安宁”(纪伯伦,2008:36)。所幸,像纪伯伦这般特立独行的诗人,纵使世人无法理解他的内心,也无法与他感同身受,诗歌也可成为其精神寄托。
(4) 诗人是一位被废黜的国王,他坐在宫殿的灰烬里,试着从中造出一个形象。
(A poet is a dethroned king sitting among the ashes of his palace trying to fashion an image out of the ashes.)
(纪伯伦,2016:185)
在这里,纪伯伦将诗人比作国王,如果诗人是国王,那他便应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然而,在孤独的纪伯伦那里,这个国王只不过是“被废黜的”国王,他的宫殿也是充满“灰烬”。“诗人是国王”,从如此豪放自大的通告可以看出,纪伯伦的孤独是石破天惊、排山倒海的。该诗性隐喻貌似狂妄无度、目中无人,实则充满荒凉无望,充分映射了纪伯伦内心深沉的孤独感。
从本质来说,隐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一个对应集或曰映射,这种映射是“两个义域之间语言发生学对应的固定格式”(王军,2011:53)。然而,当一个隐喻是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始创性映射时,其比喻效果便具有很高的超常规性。此处,超常规性赋予该诗性隐喻深奥的内涵和非凡的诗意,它所表达的恣意的狂想及狂放的诗意让人震撼无比,其诗性母题显而易见:纵然洒脱,纵然诗意,纪伯伦终究无法摆脱孤独的牵绊,致使他的人生“空虚”寂寥。通过该诗性隐喻,纪伯伦孤独寂寞的思绪得到无以复加的抒发,诗歌孤独的母题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纪伯伦孤独的第三层表现就是他“渴望”孤独并享受孤独的力量。
(5) 孤独是一场沉静的风暴,它折断我们一切枯枝;/ 但它却把我们活的根更深地栽入活的土地的活的心中。
(Solitude is a silent storm that breaks down all our dead branches; / Yet it sends our living roots deeper into the living heart of the living earth.)
(纪伯伦,2016:213)
对纪伯伦而言,孤独的破坏力虽然能摧毁一切,但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也代表着强有力的希望。纪伯伦似乎很享受自己的那份孤独,并在孤独中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纪伯伦(2000:327)在孤独中寻找到了生命的美好:“我喜欢隐居、孤独!我喜欢与世隔绝,我喜欢这一切。我喜欢心灵的喃喃自语和我的直觉意识”。可见,孤独能让纪伯伦更自由、更纯净地与自己的真实自我对话,是孤独让他保持了自我的本真,孤独也使他仿佛能得到爱的陪伴。
作为一位狷介的孤独诗人,纪伯伦拥有广阔无垠但又孤独沉寂的诗歌王国,他以《沙与沫》为代表的举世闻名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心智的盛宴上掉下的碎屑”(纪伯伦,2016:187),而这些碎屑都体现了纪伯伦真实的孤独心境。从《沙与沫》中纪伯伦对孤独的吟唱和赞誉中可以看到,孤独是其崇高超逸的人生信条。
(三)生死
在《沙与沫》中,纪伯伦对于“生”与“死”的哲思是作为同一命题的两极进行辩证阐发的。在纪伯伦看来,人生的美好是没有生死之限的,生与死是生命自然存在的两种状态,生固然代表了美好和希望,死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毁灭,它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一个环节。下面的例子说明纪伯伦是一个热爱生命、不惧死亡的达观诗人。
(1) 是的,涅槃是有的。/ 它就在领你的羊群去绿原,它就在哄你的孩子入睡,它就在写你的最后一行诗。
(Yes, there is a Nirvana; / it is in leading your sheep to a green pasture, and in putting your child to sleep, and in writing the last line of your poem.)
(纪伯伦,2016:231)
纪伯伦用温暖的目光捕捉到生命的美好,在他眼里,生命具有永恒的美,且生命的美好无处不在,它可以在“放羊”或在“哄孩子入睡”这样平常而琐碎的事务中,抑或在“写下诗行”的浪漫过程中,这些美好会“涅槃”,会永远存在。这里由平行修辞构成的诗行充满了音韵之美,宛如天籁,纪伯伦以诗意的情怀、以纯美的诗性隐喻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和热望,赋予平凡的生活美好的诗意,他质朴而超然的美感、美学性和诗意只有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方可体会得到。
(2) 千年之前,我的邻居对我说:“我恨生命,因为它纯粹是痛苦。”昨天我路过一个公墓,看见生命在他墓上舞蹈。
(A thousand years ago my neighbor said to me, “I hate life, for it is naught but a thing of pain.” And yesterday I passed by a cemetery and saw life dancing upon his grave.)
(纪伯伦,2016:213)
在该诗性隐喻中,纪伯伦斩钉截铁的生死观跃然纸上:个体生命总归会死亡,这是无法逃避的自然现象,所以,人们需要有超越生死的态度。既然活着,就必须直面生活的痛苦,最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和坦然接受死亡。因为即使一个人“恨生命”,觉得“它纯粹是痛苦”;即使他憎恶一切,愤愤不平地活着;即使他藐视人生,丧失生命,世间的万物依然生生不息,世间的花草依然艳丽绽放,犹如生命会“在他墓上舞蹈”。该诗性隐喻给读者呈现出生命法则中人们不忍想象的真相和出人意料的生命真谛,乍看似乎自然无奇,实则激荡人心,充分证明了“诗性隐喻最突出的力量……在于隐喻思维所具有的天然的、不经意间的巨大创造力”(Lakoff、Turner,1989:80)。
(3) 当你解开了生命的一切奥秘后,你就盼望死亡,因为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又一个奥秘。
(When you have solved all the mysteries of life you long for death, for it is but another mystery of life.)
(纪伯伦,2016:223)
这里的“盼望死亡”只不过是纪伯伦以诗者所独有的“向死而生”的态度来看待生死。该诗性隐喻表明,人生是在生与死的循环往复中走向永恒。一个人若深谙生命,便会走出生死的桎梏,对生命的完结便会泰然视之,便能洒脱对待死亡;当他活得丰盈,活出风采,完成了人生的使命,便会不惧死亡。另一方面,该诗性隐喻也有告诫作用:如果人要死得其所,首先要活得有意义,因为死亡的意义就在生命当中:“你们想知道死亡的秘密。但你们若不在生命中去寻找,又怎能发现它呢?”(纪伯伦,2016:137)
(4) 欲望是半个生命;/ 冷漠是半个死亡。
(Desire is half of life; / indifference is half of death.)
(纪伯伦,2016: 231)
该诗性隐喻告诉人们:人生就要有愿望,要充满热情地对待生命;如果冷漠,抑或缺乏生活的激情,那便无异于死亡。由此可见,纪伯伦是坚强的乐观主义者,他热爱生命、享受生命,时刻追随着生命的脚步而奋勇向前。
实际上,《沙与沫》处处表现出纪伯伦生死一体的哲思,即生死互化、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有生则有死,有死则有生,生死相互依存,首尾相连,构成生命的完整过程”(李霞,2007:17)。正如纪伯伦(2016:137)所说,“生死一体,犹如江河大海”。
(5) 我看见一个妇人的脸,便能看见她所有尚未出生的孩子。/ 一个妇人看看我的脸,便能知道我所有的祖先,他们在她出生前早已去世。
(Once I saw the face of a woman, and I beheld all her children not yet born. / And a woman looked upon my face and she knew all my forefathers, dead before she was born.)
(纪伯伦,2016:169)
该诗性隐喻揭示了生与死循环交替、周而复始的过程,即生与死是万物的自然转换,就如同昼夜更迭、四季变换,这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 Wordsworth)“孩子乃成人之父”(The boy is father of the son.)所表达的生命永恒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时,该诗性隐喻还蕴含了“生死同源”的道理,那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孕育着新生,昭示着生命的神圣与不朽,正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
在该诗性隐喻中,纪伯伦从哲思的角度指出生命的本质是生死相接、循环往复、绵延不息,死亡不是结束,而是通向永生的大门,因为“诞生与死亡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纪伯伦,2016:223)。纪伯伦通过生动的诗性隐喻刻画了“生与死”的母题,传达了“生与死”的真谛,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死亡的达观,道出了诗人洒脱超逸的人生哲理。
通过对《沙与沫》中“自由”“孤独”“生死”三种诗性隐喻的母题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发现,诗性隐喻是纪伯伦表达其“崇尚自由”“享受孤独”“直面生死”之人生信仰的有力武器。本研究对纪伯伦其他作品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首先,本研究以诗性隐喻作为着眼点,该研究思路对于纪伯伦其他作品的文学理解和文体学鉴赏具有联动作用,研究者有望借此达到鉴赏和审美上的触类旁通。其次,本研究对于探索纪伯伦作为诗人之心路历程的嬗变大有裨益。《泪与笑》(1908)、《先驱者》(1920)和《先知》(1923)这些早于《沙与沫》的作品凝结了纪伯伦对世界的满腔热忱,《沙与沫》则体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深邃哲思,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和结果。反之,透过《沙与沫》中的深沉和达观,我们更能感动于纪伯伦早期作品中的赤子之心。
结 语
作为富有想象力的、超常规的语言表达方式,诗性隐喻赋予《沙与沫》深远的诗性内涵。纪伯伦通过诸多新颖独特的诗性隐喻,阐述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实现了广阔的诗性母题。对《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认知性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品鉴纪伯伦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探赜其诗歌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与哲学内涵。
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出生地、他所生活过的美国现实语境以及他留学的法国之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其多重文化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位跨文化的作家,因此“东方书写”(马征,2010:126-135)是其创作的原动力,西方语境是他生长的沃土。鉴于纪伯伦的跨文化身份,学界针对其作品的未来研究可着眼于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ality)(马征,2010)视角。文化间性既坚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也与其他文化相融、相涉,从而达到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这将有利于深入探究纪伯伦作品中生命哲学和人生主题的文化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