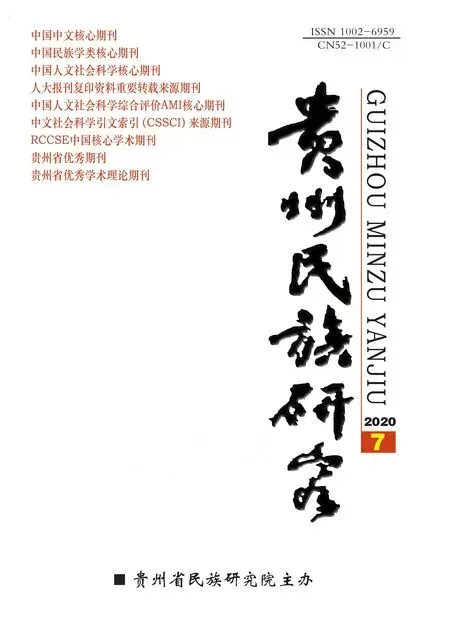鄂西南土家族灯歌考源
2020-03-03吴涵
吴 涵
(中南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湖北·武汉 43400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北省(鄂) 西南部地区,包括恩施市、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咸丰县、宣恩县、来凤县、鹤峰县八个区域。鄂西南恩施(后文简称恩施) 地处长江三峡腹地,“上收蜀道三千之雄,下镇荆襄一方之局”。此处是东部低山丘陵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区,属于二级山区,和湖南的西北角、重庆东部相毗,自古就是荆楚、巴蜀的交通要道。境内河流有清江、酉水、沿渡河等汇入长江与湖北各地、四川、重庆水道相连。人口中半数以上为土家族、苗族,其余为汉族等。从已有研究来看,恩施先民特别是当地土家族人的正史记录较星散,故地处鄂西南的土家族族源问题仍有待商榷,但据当代学者考证,鄂西南土家族族源以巴人为主体又融合众多族群的复合体。
早在公元前11世纪《华阳国志·巴志》[1]就记载了巴人的音乐的盛况,随着人民创造与历史文化的沉积,再加之文人才子的再度创作,共同缔造了这个“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族。如上所述,鄂西南音乐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又独树一帜的特征。鄂西南土家传统音乐浩繁,譬如恩施灯戏、恩施扬琴、巴东峡江号子、巴东撒叶儿嗬、来凤哭嫁歌、来凤摆手舞、利川灯歌、利川肉连响、宣恩薅草锣鼓、鹤峰打溜子、鹤峰傩戏等都已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恩施众多民歌歌舞体裁中,灯歌是遍及全州,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皆喜的乐种。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恩施灯歌音乐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2]《恩施地区民歌集·下册》[3]中所录107首灯歌乐谱为数据支撑,考镜源流。
一、鄂西南土家灯歌与远古南音
远古时期,黄河与长江水系纵横、阡陌交通,因而水患频繁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涌现了崇伯鲧、夏伯禹等治水领袖。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湖北为其一。《吕氏春秋·音初篇》[4],为南音之始。《古汉语字典》载:“‘兮’表示停顿或舒缓语气,相当于‘啊’‘呀’”;“‘猗’为叹词,表示赞美”。这首短小的民歌虽只有四字,却将“兮”“猗”两个语气助词衬于尾部,四个字虚实相错,叙事与抒情相间,使涂山氏歌声吟咏回旋、高下往复,将其思念之情表达得更为恳切。而据笔者统计鄂西南土家灯歌中咏唱爱情的灯歌为43 首,占总数的40.19%。
一曲南音便是长江流域音乐独具匠心的滥觞,亦可看作是鄂西民歌夹衬的发端。尔后,楚地《诗经》 《楚辞》均用感叹字“兮”“猗”,显示出与南音同宗联系,故鄂西有“南音导其源,楚辞盛其流”之说。 《汉典》 载“衬字”释义:“曲家制曲时,每加添虚字于曲谱应有字数之外,称为‘衬字’。一般用以补足语气或描摹情态。”[5]在灯歌这类民歌作品中使用的方式不像诗词那样严苛。
鄂西南土家灯歌夹单一语气衬字作品不枚胜举,如恩施市灯歌《穷富莫交》 《奴家门前一条河》均用“喂”“哟”“哎”等语气助词为衬字,与南音“兮”“猗”所表示的“啊”的感叹,一脉相承。如恩施市灯歌《闹五更》,从歌词来看,第一乐句中腰运用“哦”“哟”衬字扩充语句,句尾运用“哎”衬字加深感叹,第二乐句句尾再用“哇”“哎”扩充乐句,第三乐句为反复段,夹衬方式与前乐句相同。此类只使用单一语气助词为衬字的作品在《民歌集成·湖北卷》 《恩施地区民歌集》107首民歌中有28首,占总数的26.1%。可见鄂西南土家灯歌夹衬字之频繁。
二、鄂西南土家灯歌与《诗经》
东周时期,相传孔子周游列国采十五国风,经过其慎重甄选编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周南”“召南”系南音遗风。《诗经今注》载:“周南疆域北到汝水,南到江汉合流即武汉,其中地带”,“召南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的地带”[6]所包含的25篇歌谣大致应产生于今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一带的地区。古荆楚有“尹吉甫”者,其诗作为《诗经》所编撰,其事迹为《诗经》所歌颂。可见荆楚文脉与《诗经》文化的关联。
鄂西地区婚丧咏唱《诗经》 为主的“歌诗”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翻开清代荆楚各地府志、州志、县志,映入眼帘的不乏有楚人婚仪“酒三行,歌《关瞧》 《桃夭》 《麟之趾》三诗毕,拜天地、祖先……”等记载。今鄂西十堰市尹吉甫镇还有其遗址、点将台等,此地姐儿歌仍然保留咏唱《诗经》的传统,在门古寺镇甚至还能听到数十种《关雎》的变体,如《关关雎鸠向前走》 《关关雎鸠声闻天》 《关关雎鸠一双鞋》 等。 《桃夭》《汉广》 《东方发白兮》,这些表现鄂西风光、男女爱情的民歌传承方兴未艾。
在鄂西南土家族灯歌结构中也能看到《诗经》的遗存,一部分《诗经》 在主乐段后接副乐段,形成歌词上的“换头合尾”,如《驺虞》 《殷其雷》等,如《桑中》的三次反复中,主乐段歌词均为:“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副乐段歌词则同为:“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而鄂西南土家灯歌中此种“换头合尾”歌词结构更是层见迭出。譬如,来凤灯调《十二月逢春》。在《十二月鸟名》的十二次反复中,主乐段1—2乐句,歌词均为“X月逢春好(喂) 看花(呀) 好看花……”,副乐段3—4 乐句均为“精打蜜蜂安吊金银花(哟哇衣哟哦) 件件花儿红啊”。《桑中》与《十二月鸟名》除了歌词结构无差异,衬字使用方式也雷同,均为乐句中腰、句尾衬以语气助词。
鄂西南土家灯歌这种歌词“换头合尾”式副乐段屡见不鲜,且其中的副乐段多为无实际意义或帮腔齐唱以和声、男女对唱等,如建始县喜花鼓《二十八宿闹昆阳》。主乐段将数词换为一、三、五……十七,在保持乐段句式情况下将咏唱对象换为杨二郎、杨六郎、楚霸王等任务,副乐段则是同样的男女打情骂俏唱段。据笔者统计,此类“换头合尾”灯歌有19首,占总数17.76%,且名大多以“十想”“五更”“十绣”“十二月”等数词作为乐段反复的标志。
《诗经》 中还有部分“合头换尾”的歌词结构,如《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等,与《国风·周南·樛木》比较,鄂西南土家灯歌歌词也有此类“合头换尾”的形式,如恩施市耍耍《奴家门前一条河》,此段副乐段由男女对唱,乐段结构与《诗经·周南》部分诗歌类似。
受儒家文化的价值导向影响,自春秋至今《诗经》 总是“雅”文化的典范,是文人阶层专享的经典。难以想象它依然传唱在鄂西婚丧中,还能在灯歌这类乐种的歌词体式、内容上看到它的基因。灯歌与《诗经》我们很难从现有文献中追溯它们孰先孰后,但在历史长河中它们曾相互融会是可以笃定的。
三、鄂西南土家灯歌与《楚辞》
《楚辞·九歌》是战国时期屈原依据湘鄂土苗民歌收集整理并填词的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九歌》系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进行修改加工,而“更定其词”。胡适在《读楚辞》中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不论取何说法,均能看出《九歌》创作灵感来自湘鄂西部文化的浸润。
战国时期巴楚文化交流频繁,《文选》卷四十五所载屈原弟子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7]此处《巴人》便是鄂西南音乐的泛称,从“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盛况来看,战国时期巴地之音为楚人所传唱,因而巴楚民歌中不乏有同样的基因。
在鄂西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演唱《诗经》 《楚辞》的传统,《宜都县志》载:宜都“绕棺游所”仪式[8]是传承已久的“旧习”。
《楚辞》 与古朴的四言体诗《诗经》 相比,它不再拘泥于规整对称。如《楚辞·九歌·东皇太一》[9]描绘了楚人鼓瑟吹笙祭祀天神的盛大严肃场面,其中“兮”在《楚辞》中这种比较固定出现的模式,多衬于中腰与尾部,增添歌词的韵律感、节奏感,也孕育了一种更为活泼的体式。无独有偶,被称之为《楚辞》艺术之源的楚地《越人歌》[10],亦打破了《诗经》的规整束缚,其中“兮”字使用方法相同,调整音节,加大语气跳跃、转折。
以《楚辞》为代表的先秦楚声,歌词多衬有“兮”“些”“只”等,这与南音一脉相承,与前文所述鄂西南土家灯歌中衬字“哟”“喂”“呀”“也”等,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加深语气的意义。譬如:巴东花鼓子《十个凤凰》,在“呀”“子”等衬字多出现于乐句中腰,“哦”“哇”“啊”则多出现于乐句尾部使用,而此乐段中间垛句“郎往那里走(哇),扯住郎的手(哇) ……”均以语气字缀于尾部,也显示了鄂西南土家灯歌衬字穿插结构与先秦楚声所具有的内在联系。此作品在句体结构上也与《楚辞》结构相呼应,特别是垛句的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性的平仄压韵,综上使得灯歌旋律更富于律动感,歌词抒情达意。
《楚辞》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倒反修辞,如《楚辞·九歌·湘夫人》[11]这种本末倒置的倒反修辞在鄂西南土家族灯歌、儿歌、情歌也能找到相同的基因。譬如咸丰灯歌《颠倒歌》便运用此类修辞,“清早起来不对头,鞋子穿在袜子头,”这种有违常识、不太正常的行为,将主人公清早起床迷茫、呆懵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刻画得惟妙惟肖。我们还能视及文学、音乐等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本真,同时这些艺术创作又因提炼生活场景中的点滴而精辟超然于生活场景本身。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文艺工作者与每天靠土地吃饭的百姓形成既区别又交融的两个部分。
四、鄂西南土家灯歌与汉乐府
秦汉以来,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以供统治者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应运而生。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文人阶层的文化断层,只能从民间的膏壤中汲取养分。若嬴政的《祀洛水歌》还能看到《诗经》 的遗存,那么项羽《垓下歌》与刘邦《大风歌》则是《楚辞》“兮”衬字使用的延续。统治者们的诗歌创作、审美癖好,预示着叙事诗体从先秦的发轫走向汉乐府民歌的纯熟。
现存乐府诗中体现人民婚姻爱情观念的叙事性作品约占总数的1/3,且多以爱情婚姻中的真实情感与琐事为要旨。譬如,《上邪》为爱情所发的惊心动魄的誓言;《有所思》敢爱敢恨,爱而不得则毅然拂袖而去的洒脱等。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亦能在《楚辞·九歌·湘夫人》 中发掘原型。该作品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酣畅淋漓。勤劳的土家族姑娘亦是如此热辣果敢。来凤花灯《十想》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位十七八岁“恨嫁”的姑娘。这位土家族姑娘已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适合婚配的对象,看到亲朋夫妻恩爱,嫁不出去的自己便像“守活寡”的“女和尚”,心痛难当便想“悬梁高挂一根绳,早死早托生。”此处有艺术创作的夸张成分,但又曲尽其妙的歌咏了坦率娇憨土家女儿形象。从汉楚歌到灯歌,我们不难瞥见艺术创作对中华儿女醇厚质朴真实情感的侧重咏叹。
基于儿女情长、生活琐事朴拙情感所孕育的乐府民歌具有长歌当哭特质,此特征在《诗经》《楚辞》 《汉楚歌》、土家灯歌中多见,田野工作中笔者发现许多婚姻爱情类的叙事性作品,如恩施耍耍《只怪我婆妈》,这位土家妇女正月里独自携带礼物与尚在襁褓的幼子回娘家,雨天路滑不慎摔倒,手忙脚乱地捡拾礼物,慌乱中安抚幼子,孩子的啼哭促使这位年轻妈妈想起自己“丧偶式”的婚姻生活,婚后生活的一地鸡毛让她抱怨起母亲不该让她所嫁非人。这首灯歌以七言四句为1乐段组成5段,运用叙事体结构详实地描摹土家儿女的生活琐事,无论是辞藻使用还是叙事体结构都显示出汉乐府诗与楚文化的陶染,同时也是土家人民生活景象的真实写照。
在汉乐府叙事体诗歌中还有一些描绘婚嫁自由的儿女形象,譬如《孔雀东南飞》中为追求婚姻自由双双殉情的焦氏夫妇。在《诗经·卫风·氓》中亦有从婚姻缔结到离婚全由女子理智支配的敢爱敢恨的形象。在土家灯歌中也能看到一些大胆泼辣反映婚姻自由的作品,如宣恩灯调《闹五更》,以叙事体形式描绘了两位突破封建礼教的男女,男主夜半在女主家外守候,二人苦于相思的情景。
从《诗经》 《楚辞》 《汉乐府》 再到灯歌,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作品,淳朴至臻的“婚姻爱情观念”总能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有相对稳定的承袭。土家灯歌在婚恋内容上的创作更是形成了“无粮无曲不成酒, 无郎无姐不成歌, 情歌出自心窝窝”的俗语。
五、鄂西南土家灯歌与清商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326首,后者142首。这些作品在文学形式上与汉乐府一脉相通,内容则全聚焦于儿女情长。所谓“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清商乐习惯采用隐喻、双关等修辞手法,描写礼教之外的男女私情。在表达爱情不会欲语还羞,扭捏作态,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尊重爱情,拥抱生活。这与前文已述土家灯歌“山歌不离郎和姐,离了郎姐不成歌”的创作方式不谋而合。灯歌中也不乏表现两性关系的作品,且部分不是法定夫妻关系,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爱情的表达大胆、热辣。例如来凤灯调《绣荷包》,便以女子的口吻,描绘自己与情郎以荷包定情、私会等情节。值得一提的是,此作品还多用“梭阿龙冬哥啊”“幺姐咚咚飘”等衬句来呈现男女之间眉目传情。再如,利川灯调《唱起山歌送情郎》第一乐句先以太阳、扇子等实物起兴,点睛之笔则在第二段,女子拉住情郎腰带问郎几时来?完全不拘泥于封建礼教的含蓄,以此映现土家女儿大胆泼辣、爱憎分明的性情。
魏晋清商乐擅用虚字、实词做衬腔的方式亦在灯歌中找到留存。吴声歌流行于江浙一带,其歌词常五言一句为主,尾部有虚字如“啊、哦、哟”等衬字唱出的送声;西曲歌在吴声歌之后流行于今荆州一带,尾部有实词如“家庭、女儿”等衬词唱出的送和声。例如《巾舞歌》中的“吾”“何来”,《上邪曲》中的“夜乌”,《战城南》与《巫山高》中的“梁”,《蛱蝶行》中的“之”和“奴”等,杨慎《升庵诗话》:“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慎按:‘艶在曲之前,与《吴声》之和,若今之引子;趋与乱在曲之后,与《吴声》之送,若今之尾声。羊吾夷伊那何皆辞这余音弱弱,有声无字,虽借字作谱而无义,若今之哩啰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读古乐府矣。’”[12]杨慎认为这些“羊无夷伊那何”字在文本中幷无特定的语言涵义,但由于清商乐的演唱乐调曼长,歌辞若过于简短,要突出这种曼长则需加上衬字才得以扩充乐句,使得词与乐调合拍。
此种加衬字土家灯歌作品数不胜数。前文已述在灯歌中以衬字、衬词使用扩充乐句、凸显情感的作品有占本文研究灯歌总数的26.1%之多。土家灯歌在歌词内容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婚恋观,其衬词对于乐句扩充的创作途径上都表现出与清商乐殊途同归。
六、鄂西南土家灯歌与竹枝歌
竹枝歌又名竹枝曲、竹枝子,发源于长江三峡流域一带。唐贞元、元和年间滥觞于文人阶层,从杜甫、顾况、刘商、于鹄、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的《竹枝词》 可见是当时盛行诗体之一。竹枝词原为环三峡武陵巴楚人民的山歌,唱于民间迎神赛会、祭祀祖先与节令求偶场合,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后经汉族文人挖掘、倚声填词形成一种诗词文体,是西南、中南交界处古代巴人、楚汉人民共同缔造的产物[13]。
竹枝词的衬字即“和声”系统是其最具点睛之处,在诗句的四字句处和七字句处的自由“垫字(音)”的和声处理,譬如皇甫松的《竹枝词》,很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的“竹枝”“女儿”是表示竹枝歌每句第四字后和句末的衬词,即胡震亨先生所说的“和声”。土家族的民歌中依然保持竹枝歌这种规整的夹衬方式,其演唱形式与竹枝词如出一辙,如鄂西南跳丧“撒叶儿嗬”[14],其衬词的使用规律与竹枝相同,正是这种规整的夹衬使用,使得鄂西南跳丧有了新的官方命名“撒叶儿嗬”。在鄂西南土家灯歌中也不乏此种夹衬规律,譬如咸丰灯调《十把扇子》,以“一把扇子”“二面花”等领唱作为送声,再以“连连儿”“溜溜儿”加衬作为众唱的和声。一领众和加衬的方式改变了歌词原本的规整语言节奏,使得演唱朗朗上口,乐句形成起承转合四句式,更有音乐性。
此外,灯歌中也有把加衬和声集中放在乐句腰部和尾部的,如咸丰灯调《车灯调》,“小巧车哇”“溜溜车小巧,哥哥你前去哟妹妹我转来……”作为中腰处超长衬句,不仅扩充乐句结构,并使得乐句的押韵和内容更加贴切,使灯歌更富有土家灯歌的韵致。
鄂西南土家人民从方言口语、生活琐事中共同创造并口耳相传的民歌孕育了巴蜀竹枝歌,隋唐文人又在竹枝歌的基础上文化加工萃取形成文学性的竹枝词,此后文人竹枝词的创作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而竹枝歌的民歌形式则依然活跃在鄂西南民间的沃壤流传至今[15]。
七、结语
千百年来,鄂西南土家族音乐文化线索清晰,传统延绵。巴蜀荆楚交汇地域先民的方言口语、婚姻观念、生活遭遇、逻辑思维、审美选择孕育了南音等歌词性文学形式,这些文学作品本是民间咏唱的民歌,其曲调因传播方式的局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又以政府的采集与文人笔触幸存于文化典籍中,因而民歌可以被看作是文学音乐等艺术创作的基础。同时文学创作的浸染又造就了形态多样、质朴纯真的民歌,表现在歌词的文学性、曲体结构、衬字的使用上极为突出。鄂西南土家灯歌是先秦南音、 《诗经》 《楚辞》,汉魏时期乐府、清商乐,隋唐时期竹枝歌承继延续的产物,并形成了“无生无旦不成戏,无郎无姊不成歌”的文化风格。从现存文学作品与灯歌音乐,我们很难辨识出是文学与音乐谁是先驱者,但我们依然能明晰发掘今夕土家民歌与先秦巴楚之声精神统一,亦能从歌词中看到巴蜀荆楚混融性风格。但混融并不意味着失去本真,灯歌虽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又独具土家族纯真质朴的坦率性情。土家灯歌是土家人民的审美选择,更是土家人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知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