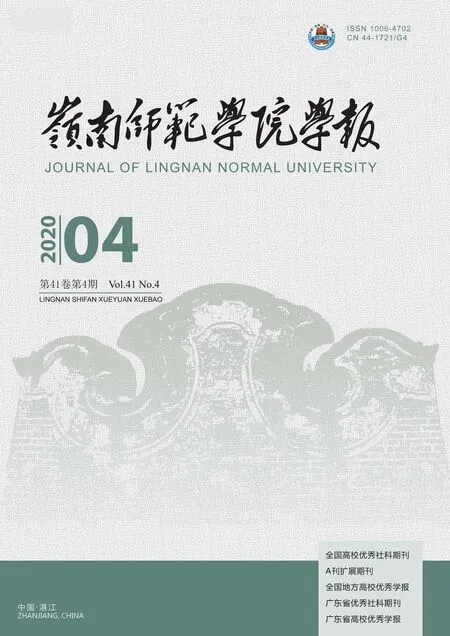论韩愈“道”之诠释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2020-03-03吴斌
吴 斌
(1.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全州大学,韩国 全州 55060)
中唐之际,“佛老蕃兹”的社会局面不仅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影响着儒学的生存环境。韩愈肩负“儒之为儒”的历史使命,构建“道统”思想,直面佛教挑战。但与初、盛唐儒士“坚决排佛”不同,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实融”,“表辟”是基于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佛教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要重塑儒学的独尊地位,必须标举道统。“实融”是基于佛教的传播受到了儒学在思想、理论上的渗透,为丰富儒学的内在理论,可以以释合儒。换言之,韩愈“道”之重构式诠释体现为:仿佛之法统创建儒之道统,效佛之教法倡导儒之教化,融佛之义理补充儒之心性。韩愈“融佛以尊儒”这一思想层面的转向,不仅和中唐儒学的复兴表现出内在一致性,而且为宋明道学的承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仿佛之法统创建儒之道统
“道统”一词虽由南宋大儒朱熹正式提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1]14,但是儒家“道统”观念由来已久。孔子以“仁”释“道”,将“道”区分为“仁”与“不仁”两个方面;孟子继承孔子“仁”的理论,补充“仁、义”为“道”的内涵,并且梳理出儒家之“道”一脉相承的统绪:“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1]385由此可知,儒家“道统”思想在孔孟时期早已发端,孟子则初步确立了一个由尧、舜、禹、汤、文王至孔子“先王之道”的传授谱系,即“道统”的雏形。然而,儒家“道统”之说的创造者并非孟子或朱熹,而是千百年来所公认的中唐儒士韩愈。韩愈提倡“文以明道”的思想,不仅明确梳理了儒家圣人以“道”为核心的传承谱系,而且指出荀子和扬雄“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20,不能理解圣人之“道”的真义,导致了儒家“道统”的中断。因此,韩愈以孟子传继者自居,盛赞孟子为“醇乎醇者”[2]41,从而证明了其“道”的正统性和延续性。
韩愈“道统”思想的阐发,以两篇文字最为著名,一是贞元十九年春作的《送浮屠文畅师序》:“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2]282二是同年写的《原道》篇:“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2]20韩愈不仅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而且认为这一谱系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有德有位”的古代君王之间的“亲传口授”;二是周公、孔子、孟子等“有德无位”的古代贤臣之中的“精神传承”。“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2]20从“事行”到“说长”,韩愈显然继承的是后者——一种抽象化的“道”。由此,韩愈论述“道”的内涵:“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为之德。”[2]15韩愈以“博爱”解释“仁”,以“行宜”解释“义”,以“仁、义”解释“道”,“德”依附于“道”,为本性所固有,其不仅确定了儒家圣人之“道”以“仁、义、道、德”为核心内容,而且进一步界定了“仁、义、道、德”的关系是:“仁、义”是确定的内容,为“定名”;“道、德”是抽象的形式,为“虚位”,“道位虚”则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20之“道”提供了继承的前提。
韩愈“道统”思想虽在内容上继承了孔孟之道,且其一再声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2]190但是韩愈之“道”在形式上或多或少的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成分。因此,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指出:“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3]105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钱穆先生的认同:“此一观念,显然自当时之禅宗来,盖惟禅宗才有此种一线单传之说法。”[4]988唐朝中叶,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主流宗派纷纷完成了创宗和完善了教理。尤其是禅宗,不再是“在中国的佛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一方面积极调和儒释之间的关系,吸收儒家思想以充实佛教理论;另一方面自称为“宗门”,有别于其他“教门”。在禅宗看来,自身不只是接受了佛教经典,更体悟了释迦牟尼的“心法”传授,而这一“以心传心”之法将其佛学源头追溯至佛祖。“禅宗的传承以佛陀灵山会上拈花,迦叶会心微笑为启始,言其教外别传,心心相应。迦叶以至于菩提达摩,共传二十八人,称为西方二十八祖……在中国,则有东土六祖。他们分别是: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慧能。”[5]111由此,比较韩愈“道统”思想和禅宗“法统”体系,不难发现二者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其一,都有一个所尊崇的始祖。韩愈尊崇“尧”为儒家的始祖,禅宗尊崇“菩提达摩”为禅宗在中国的始祖;其二,都有一个由始祖向下一线单传的谱系。韩愈“道统”确立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的传道体系,禅宗“法统”确立了“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传承体系。并且,在时间上禅宗“法统”体系的确立早于韩愈“道统”思想,这也为韩愈借鉴佛教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邓广铭先生认为:“隋唐时期,佛教的各教派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自称本派为正法,受真传,借以争正统地位,这种佛教内部‘定祖’和争道统的风气,也给予晚唐以至宋代的儒家们以极大的影响,韩愈也位列其中。”[6]167
二、效佛之教法倡导儒之教化
“内圣外王”的命题最早渊源于道家,但却被儒家一直所提倡,反映了儒者通过修养内在以成圣人和内德外化以成王道的精神传统。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治国者由管理自我身心,到管理各级官吏,再到管理平民百姓,体现了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修养上升到“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的过程。孟子以“不忍人之心”的“仁心”行“不忍人之政”之“仁政”,强调“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和“浩然之气”的理想状态,并由此上升为现实社会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法——“王道”的政治论。荀子由“天命”之情性为“恶”,提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和“所积而至”的成圣之道,而成圣的作用在于“使天下皆出于治”——“隆礼重法”和“强国裕民”的“外王”理想。西汉董仲舒构建“天人相与”的神学体系,由“人副天数”的感应思想,推出与之相符合的“尊君、一统”的政治理论。韩愈继承了先秦以来“道”在“内圣外王”层面践行的范畴,其在《原人》篇指出:“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2]28在他看来,“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是“天道”“地道”都归于“人道”,因为圣人可以“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2]28。而圣人重视“仁”,“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2]282,韩愈将“仁义”视为“道”的内在核心,“礼乐刑政”视为“道”的具体教化,体现了韩愈之“道”由“内圣”转换为“外王”的政治倾向。
韩愈在《原道》篇指出:“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2]19-20在他看来,“道”的具体内容为“文、法、民、位、服、居、食”等七个方面,并界定了“道”与“教”的关系:“道”的内容越明白,“教”的执行就越容易。由此可知,韩愈“道”之诠释外在于“教化”层面,表现为“相生养之道”:“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2]17韩愈认为,古时候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各种不利因素,圣人身为君、师教民以为衣、为食、为宫……为礼、为乐、为政、为刑等“相生养之道”,而圣人的“相生养之道”作为一种“教”的具体实践将“道”的“将以有为”完美体现在现实之中,使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同时,韩愈又指出“道”与“师”是密切相关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其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2]47-48在他看来,圣人愈加圣明,在于不耻下问;愚人更加愚昧,在于耻学于师。韩愈在《师说》中倡导师道,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旨在通过强调“师”的职责“授业解惑”以论证“道”在“教化”层面得以体现。
由此,钱穆先生在《孔子与春秋》中指出:“西汉人所重是‘王道’;韩愈以下所重是‘人道’。”[7]293钱穆先生之主旨在于论证:韩愈“道”之诠释的重心,由儒家一以贯之的“内圣”上升至“外王”的路径发展为“外王”回归到“内圣”的转向。在钱穆先生看来,汉代儒家之“道”侧重于“治”,即“外王”的层面,“西汉人所重是‘王道’……认为王道是人道最高的表现,最大的实践。”[7]293与此对应,孔子被视为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在于其所作的《春秋》一直被奉为“王官学”,“春秋是当得一王之法的”[7]272,因此孔子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帝明王”并列,但其有德无位,孔子又有“新王”“素王”之称。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且流行,“佛学只重‘教’,不重‘治’,若用中国古代道家言来说,佛学只重‘内圣’而绝不理‘外王’”[7]292。钱穆先生认为,在佛教重视“教”的影响下,儒者对“道”的理解,开始由“治”转向“教”。与此对应,孔子不再和“古帝明王”相并列,而是“和佛陀与老聃并列了”[7]292。由上可知,钱穆先生通过区分“治”和“教”两个独立的领域,对佛教传入前后儒家之“道”所侧重的内在含义及外在表现予以界定,最终指出:“韩愈重‘教’不重‘治’,他把治道包括于教道[7]294。反观韩愈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中唐儒士群体对佛老文化开始秉持一种基本判断:释老与儒教思想只是侧重点不同,而不是相互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儒学的教化。“然三教俱设,各有所务,而行之者,不可过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即代之务。”[8]791面对“三教同归”的现实情境,韩愈“道”之诠释不得不发生转向。因此其在《原道》篇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2]20,韩愈此意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实际上将儒家置于与佛教、道教相同的“教”的领域,而孔子的身份则变为了“教主”。同时,也正是因为强调“教”,“道统”谱系上才得以增设一孟子,即是“统”之所以为“一线单传”的内在原因。
三、融佛之义理补充儒之心性
心性论中关于人性的探讨,是儒家一直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虽然没有直接以善恶论性,但是排除了善之与不善或不善之与不恶的矛盾,为其后四种人性思想流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告子提出了“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性无善无恶论;世硕提出的“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的性有善有恶论;孟子提出了“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到两汉时期,性无善无恶论发展为扬雄的“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性善恶混论。性有善有恶论发展为董仲舒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和王充的“正性、随性和遭性”的性三品论。而不同于汉儒的“性三品”论,韩愈人性的观点实质上祖述孔子,扬弃孟子。就前者而言,韩愈作《论语笔解·阳货篇》处理了“相近”与“不移”之间的矛盾。“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习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习而迁也。二义相反,先儒莫究其义。吾谓上篇(《季氏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与此篇二义兼明焉。”[9]遗文3/ 15上在韩愈看来,“移”与“不移”,关键在于“学”而“不学”,“困而不学”才是“不移”的原因。由此,韩愈同先前儒者一样,不仅肯定了孔子所提出“每个人的天然本性是相近的,只是受后天习染而产生差异”的观点,而且确立了“性”为先验,试图打通“道”与“性”的隔阂。从后者而论,韩愈“性三品”论直接对孟子“性善论”展开扬弃。孟子主张性善,并以先天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引发“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来表明人性本善,但人之恶从何处来却难以解释。韩愈对孟子人性理论的改造,不只是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增加了“信”,而是视五常之性作为人的本性是一个天然的存在,又以每个人所禀赋五常之性的不同而划分人的个性为三品。
韩愈由“道”谈“性”,由“性”论“道”,而“道”在“心性”问题上的诠释见于其《原性》篇:“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2]22韩愈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五种德行充实具有,则为上品之性,是至善的;中品之性“仁”有欠缺且四德混乱,但可以通过引导为善为恶;下品之性缺少“仁”且有悖于四德,所以是恶的。由此可知,韩愈以五常之性与人的存在同一,界定仁义礼智信为人的天然本性,又以五常之性的具备与完善划分人性,强调仁义礼智信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从而,韩愈不仅将儒家之“道”移植到人性当中,而且为其“道”在“治心”层面寻求了一个天然的合理的根源。同时,韩愈由“性”及“情”,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要素的控制程度划分“情”为上、中、下三等,“性”与“情”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2]22-23
心性论是佛教思想与儒家哲学旨趣最为契合之点。早在东晋时期,慧远等人就基于伦理纲常和社会作用的层面,指出儒家与佛教不同的是名称,相同的是本心,两家都以 “不昧本心”为宗旨。隋唐时期,佛教不再沉迷于“空有之论”,而是转向“涅槃佛性”,对佛性、人性的追问成为佛教徒们的精神旨归。中唐之际,南禅宗的崛起更是把个人的自心自性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求得外在的“涅槃寂静”升华为向内求得的“直指人心”。反观儒家,虽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将儒士的视野集中于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但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一直为儒学所倡导。当佛教“明心见性”思想散发出无法抗拒的诱惑,“其时的儒学家们有鉴于此,便也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6]168,梁肃、白居易、刘禹锡、裴休等一流士大夫开始参禅礼佛,由“入世”转向“出世”,柳宗元更是道出了当时儒者对佛教深邃理论的直观感悟:“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10]751显然,韩愈也是“儒学家们”中的一位。据宋诗论家刘克庄统计,与韩愈保持书信往来的唐代僧人共七名,并作《送文畅师北游》《与大颠师书》《送浮屠令纵西游序》《送僧澄观》等篇目,尤其是在韩愈贬潮期间,与大颠往来问道、留衣作别,成为千古佳话,佛教徒甚言韩愈已归佛门。韩愈归释说当不足取信,但是韩愈受大颠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与孟尚书书》中其称赞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2]237-238对此,司马光《书心经后》中认为:“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11]504司马光之意在于说明韩愈之所以能出此言论,是因为其对佛学“有相当之知识”[12]。更重要的是,韩愈“性三品论”中进一步提出“仁”为“义、礼、智、信”之主,“主于一而行于四”,把“仁”与“四德”由并列关系上升为主从关系。韩愈界定“仁”与“道”为体用关系,不仅是对《大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理论发挥,其后更被演绎为宋明理学“儒之仁,佛之觉”一个新的命题。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3]107看来,韩愈之“道”在心性层面的诠释与佛教义理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韩愈“道”之诠释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仿佛之法统创建儒之道统、效佛之教法倡导儒之教化、融佛之义理补充儒之心性——是出于其内在思想的逻辑性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性使然。换言之,韩愈在实质层面上“融佛以尊儒”不仅体现出儒者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自觉坚守,而且蕴含了儒者对“释道”异质文化的改造意识,从而走出了中唐儒士“复兴儒学”的第一步。因此,置韩愈于唐宋文化转型的视角下,其可谓是“承先启后转旧为新捩点之人物也”[3]114,韩愈“道统”思想从形式上确立了与佛教法统相类似的儒家一线单传的传承谱系,其“道”之教化、心性思想从内容上开启了儒释之间“入世与出世”的相互转化,为宋明理学发展成中国儒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