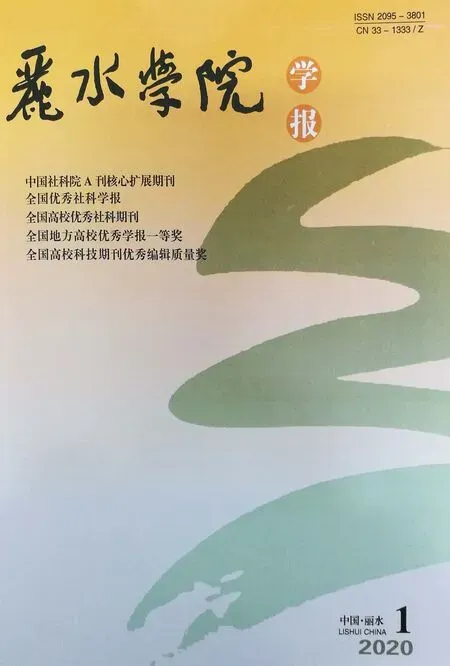赵树理创作“大众化”之策略及借鉴价值
2020-03-03朱庆华
陈 俊,朱庆华
(1.丽水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丽水323000;2.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 丽水323000)
“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着民族化、大众化这一严峻使命”[1]。尽管五四文学革命伊始便有陈独秀、周作人等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20世纪30年代执文坛之牛耳的“左联”在其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旗帜鲜明地“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2],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期“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3]199。但凡此种种用力,均是入门无径,难成正果,大众化可望而不可及,直至赵树理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通俗故事”不胫而走,大众化才真正开花结果,破茧成蝶,实现了新文学从高不可攀的知识分子的“文坛”走向引车卖浆之流的华丽转身。探究赵树理创作大众化成功之秘诀,之于当代文艺界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4]不无裨益。
一、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之特殊意义
文学创作“是个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精神劳动”[5],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并借助恰当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小说等将其物化。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的海洋浩瀚无边,文学表现生活的样式也是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即便是天才般的作家,也只能是熟悉某些生活领域、掌握某些文学样式而已。这就势必赋予作家在创作时,“对内容和形式有个人选择的充分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以便运用自己最熟悉的艺术形式,去反映最熟悉、最理解的社会生活”[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自由是一个作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写什么?怎么写?只能是作家自己说了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是常态下的文学创作。时逢非常之际,文学创作就应有非常之为,就得有“权变”。所谓的创作自由,与其他一切自由一样,归根结底都只是“有限”的自由而已,绝不存在“无限”的绝对自由。自鸦片战争以降,曾经四方来朝的东方大国却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猛虎斗我前,群魑瞰我后;上有危石之颠堕,下有熔岩之喷涌”[7],危如累卵,濒临亡国灭种之境。仁人志士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苦寻救亡图存之良策。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之洗礼,先贤们终于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当务之急既非科学革命,亦非政治革命,而是“新民”,是改变国人之思想观念,至有五四思想革命。五四思想革命“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3]5,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最佳的思想启蒙、让“科学”“民主”这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深入人心呢?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一开篇便作振聋发聩之声,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8]。李大钊则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9]。鲁迅则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0]。五四文学革命由是应运而生,成为五四思想革命之重要一翼,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树起了旧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碑。由于是借文学以新民图存,因此,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学必须与言文不一、尽传封建之道的旧文学彻底划清界限,于是,另辟蹊径的新文学就只能是师从西方文学,从外国文学中窃得火种以燎原文坛。这就使得借外国文学之力破土而出的新文学难免洋腔洋调,深深烙上了“欧化”的印记,因不接地气、不合欣赏口味而被中国寻常百姓无情地拒之门外——且不论20世纪20年代尚在长治就学的赵树理暑假兴冲冲回家向父老乡亲热情传播新文学惨遭失败,即便时至40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文学依然缺乏市场,不为民众所接纳,民间广为流传的仍然是《太阳经》《增删卜易》《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之类的封建读物,这样的书籍,几乎家家都有,即使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马伕、勤务员手上拿的,也是这种小本本,而不是当时那些业已投身革命的作家们所写的印了1~2 000册的所谓的“真正的文学作品”[11]144-145。思想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新文学乃是开展启蒙、传播新思想的最佳平台,而寻常百姓则是最为广大的启蒙对象,但倘若新文学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那么,先贤们借文学改造国人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的初衷便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大众化”兹事体大,意义非凡,攸关中华民族之生死存亡、兴衰荣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将亡,何以安身立命?时逢国难,身为作家,又有何理由心安理得地去要求他的“创作自由”权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肩负着特殊的时代使命,是时代使然,对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这也是创作自由在非常时期的“权变”。
二、赵树理创作“大众化”之秘诀
如上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是时代之必然,一定意义上攸关着中华民族之生死存亡。所谓“大众化”,按照当下最通行的释义,即是指“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12]。具体到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即是要在内容上“投大众之所好”,情感上与大众“同气相求”,形式上让大众“喜闻乐见”。赵树理正是认认真真地将其付诸实践了,所以,他的“大众化”成功了,取得了丰硕成果,甚至是获得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之殊荣。
在创作内容方面,赵树理真正做到了“投大众之所好”。“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13]。赵树理明确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小说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事关民众之切身利益,抓到了民众的痒处,因而每每能博取民众之“眼球”。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通过阎家山的故事,赵树理幽默而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主义对群众利益的危害。“减租减息”本是共产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举措,但在恶霸地主阎恒元的暗中操控下,阎家山是阳奉阴违玩手段拒不执行,致使阎家山东头老槐树下的穷人们并未能真正得到“减租减息”的实利。然而,在官僚主义作风的章工作员手里,阎家山倒成了本县的“模范村”:“阎家山编村各干部工作积极细致,完成任务甚为迅速堪称各村模范,特传令嘉奖以资鼓励。”后来,在深入群众的农会主席老杨的带领下,阎家山才真正取得了“减租减息”和改选村政权的两大胜利,广大群众比过大年还高兴。由于反映问题切中时弊,具有广泛的警示意义,《李有才板话》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在后来的整风学习、减租减息以至土地革命中,《李有才板话》成了干部必读的一个参考资料。”[11]170
在情感方面,赵树理与人民大众可谓是“同气相求”。作者与读者之间,唯有情感相通,方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作品为媒介实现心灵的对话,否则就很有可能“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以说,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了解农民、最懂得农民的一位始终为农民鼓与呼的作家:“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的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14]身为著名作家的赵树理,对文艺工作的热情,甚至反不及其对农村工作的钟爱:“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工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与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11]283正因为赵树理与广大农民群众是如此地亲密无间,是农民群众真正的贴心人,因此,他总能够时时处处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其所创作的作品,总能在农民群众中找到知音,总能获得农民群众的共鸣。
在艺术形式方面,赵树理力求让“老百姓喜欢看”。因此,在创作时,他总是充分尊重中国百姓的文学口味和欣赏习惯,最大限度地融入中国传统的艺术元素,使得中国百姓一接触其作品便顿生“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而爱不释手。以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为例,个中的传统艺术元素可谓是琳琅满目。“大团圆”模式是为中国百姓所钟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兰芝与焦仲卿等等,即使生前不能白头偕老,死后也要比翼双飞。牛郎织女,即便天人永隔,也需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尽管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对“大团圆”是口诛笔伐,极尽贬斥:“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15]“中国人的精神,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16]。但赵树理理直气壮地为“大团圆”辩护:“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17]赵树理作品的故事结局,十有八九都是“大团圆”,《小二黑结婚》的素材原本是个悲剧,赵树理却将其处理成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喜剧。“才子佳人”故事是中国百姓津津乐道的,一曲《西厢》悦万人,一部《红楼》传千古。二黑是青抗先队长、特等射手,也是刘家峧的大帅哥;小芹则是村里第一大美人,比当年的三仙姑还漂亮。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又何尝不是“才子佳人”故事在新时代的复活?“清官”是封建时代中国百姓心中的神明,清官断案的故事中国百姓代代相传,清官断案的故事通常由“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三大板块串联而成,《小二黑结婚》则由“婚姻受阻——区长公断——喜结连理”三大板块串联而成,其情节之演进与清官断案故事岂非如出一辙?此外,中国传统小说重故事、以言行刻画人物、善用“绰号”、巧设“扣子”等等特点,都在《小二黑结婚》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正因为作品中富含如此众多的传统艺术元素,为中国百姓备足了口味,因此,《小二黑结婚》一经刊行,便“立即被抢购一空,在短时间内一再印行,仍是供不应求,仅太行山区,就发行三四万册。各地剧团还竞相把它搬上舞台”[18]128。
三、赵树理创作“大众化”之成功经验的启示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4]。在当下,如何使作家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赵树理创作“大众化”之成功经验,也许可以给我们良多启示。
其一,过好“创作理念”关。当年尚在求学中的赵树理,暑期回到家乡,兴致勃勃地将《阿Q正传》等新文学作品介绍给父老乡亲却遭到无情拒绝时,他真切地感受到:新文学作品尽管有进步的内容,但其审美情趣却与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格格不入,百姓们所津津乐道的依然是那些代代相传、具有浓郁民族风的通俗读物,思想进步的新文学根本打不进群众的圈子。于是乎,碰了壁的赵树理立下宏愿:“不想当文坛家,决心做‘文摊家’,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为广大农民所热爱的通俗文学家。”[19]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是有了这样鲜明而坚定的为老百姓创作的理念,赵树理才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部部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今天的文艺家,要创作出广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首先也得有正确的创作理念,心中有人民,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4]。
其二,过好“思想感情”关。赵树理,出身于农民,从农村走来,尽管后来成了名人,也进了城,但他始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农民情怀,一辈子视农民为兄弟亲人,先农民之忧而忧,后农民之乐而乐,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永远是其“剪不断、理还乱”的深情挂念。他一生节俭,但面对群众困难则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当年回到家乡,得知村党支部书记赵国祥正为缺钱修水轮泵站抗旱而发愁,就主动说:“国祥,别发愁,我手边还有一些存款,咱社里需要多少,你吭气,我捐献。”[18]290《三里湾》完稿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都伸出了橄榄枝,但作者最后选中的却是通俗出版社,目的是为了降低书的成本,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投桃报李,赵树理以赤诚之心,赢得了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也打心里视赵树理是自己人,是最忠诚可靠的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正因为赵树理与广大民众情深义重,心意相通,所以,其创作能充分反映人民的心声,从而获得民众热烈的欢迎。今天的文艺家,也只有情感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群众心贴心,其创作才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
其三,过好“读者需求”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求,包括内容与形式两大方面。“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描写当时人们普遍关切的事和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的特色之一”[20]。在创作内容上,赵树理总是及时地将做群众工作时所遇到的敏感问题予以艺术的呈现,如创作《邪不压正》,是为了“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21],可以说,赵树理的这些“问题小说”是及时雨,搔到了广大农民的痒处,因而每每风靡一时。在艺术上,赵树理总是最大限度地融入中国传统的艺术元素,尽可能地尊重民众的欣赏习惯,因而其作品十分切合寻常百姓的审美口味,广大读者陶陶然乐于接受。今天的文艺家,也只有牢牢把住时代的脉搏,紧扣民生热点,采用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