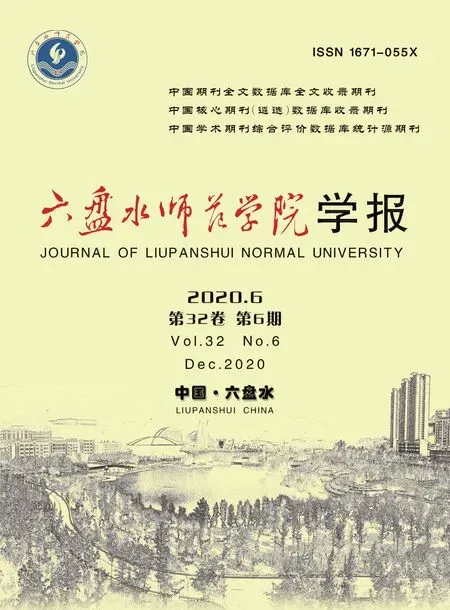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域下《绿野仙踪》评点谫论
2020-03-03谭志轩
谭志轩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近年来,关于清代中叶李百川的小说《绿野仙踪》抄本系统中署名“虞大人”的评点到底出自何人之手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陈新《<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它》[1]认为所谓的“虞大人”就是作者托名,小说中所评点的文字就是作者的自评,即使不是也与李百川有相当亲密的关系。卿三祥《<绿野仙踪>散论》[2]反对陈新所提出的论断,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疑点,他指出作者与评者在扬州停居的时间不合,评者并不完全了解作品中的诗词,并对作品提出了反对意见以及文中的部分赞语不应为作者本人所出。由此可见,评点者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此外关于评点内容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尽管《绿野仙踪》中所载的评点文字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争议,但其毕竟构成了小说面向读者所得到的反馈的第一手材料,评点者成为小说的“第一读者”。“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3]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中所载的评点文字是评点者作为接受者对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做出的评判和理解,并且还成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引导其他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一、接受群体:“我”与“同寓”
就目前学界的讨论,《绿野仙踪》的评点者到底是作者还是另有其人尚无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评点文字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做出推论,小说的评点者为作者以及与他熟识的朋友等,也就是说《绿野仙踪》的第一读者并不是某一个人,这场阅读活动是在多人的共同讨论中完成的,最后再由某一位评点者做出具体的评点文字。
首先,从小说所载的自序中就可看出,作者在创作《绿野仙踪》的过程中就与他人同读。自序中有言:
旅邸萧瑟,颇愁长夜,于是草创三十回,名曰《绿野仙踪》。付同寓读之,多谬邀许可[4]2。
可见,至少在前三十回中,就有读者参与到小说的阅读当中,可以推断大多是同寓于旅社的朋友,并对这部小说持认可态度。此外,陶家鹤序后所载的补识也提及:
通部内句中多有旁注批语,而读者识见各有不同。弟意宜择其佳者,于抄录时分注于句下,即参以己意亦无不可[4]6。
从这段序言可以推断,陶家鹤所看到的《绿野仙踪》应是完整的本子,并且已经存在旁注批语,并且旁注批语并不是一家之言,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此可以得出,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不止一位,并且还公开探讨过,陶家鹤还建议作者对已有的评注做一些挑选,择优而录。其次,小说中的批语有明确显示出群体阅读的内容,例如第十回中有夹批:
昔余友田景虞读之此秘授句,笑问曰:“既有指间至意口诀,何不明写出来?盖作者欺人耳!”旁一友王锦云代应曰:“若明写出来,你亦可望成仙矣!”时同坐者皆大噱[4]107。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参与小说阅读的有“余”“田景虞”“王锦云”以及“时同坐者”,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读者群共同参与的阅读过程。再次,小说中的评语出现过明显的“回应”痕迹,第四回中:
何不将此话说在一见面收礼物之前?必问及明家道始及,我于献述不能无小人之疑矣。以上诸评,献述未必有其意,评者之批亦太刻矣[4]43。
很明显这段批注存在两个以上的不同的主体,最后一句即对“以上诸评”提出的回应,但是否为作者发出的还尚待考证。通过这些例证不难看出,作者在创作《绿野仙踪》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是和“同寓”等众位读者一起阅读探讨的,评点者参与了这些群体性的阅读过程,总之参与这部小说评点的不止一位读者,并且作者李百川也极有可能参与其中,最终将阅读活动的内容形成评点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是与作者个人经验非常相似的且关系非常亲密的“同寓”之一。
《绿野仙踪》抄本系统中所载的评点文字是这部小说中初次面对读者所记录下来的内容,它真实地涵盖了文本与读者互动过程中的阅读体验,评点者作为小说的第一读者,他所记录下来的文字构成了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接受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陈文忠先生所言:“读者不仅是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而且是创作活动的最后完成者。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经过读者的欣赏和分享,它的潜在价值才会转变为现实价值。”[5]虽然《绿野仙踪》北大本中所署名的“虞大人”究竟是何人还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我们从已有的文献资料中能够明确,文本所载的评点文字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群体性的阅读记录,从这份记录中我们可以探讨出这部小说在接受美学层面的相关内容及意义价值。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学在西方兴起,开始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小说评点是独具特色的文学接受的重要形式,我们可以借助这第一份感官资料探讨出接受者与文学作品在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的重要价值。
二、情感共鸣:评点者的物我感应
“文学解读中的共鸣指读者心中的喜怒哀乐情绪为文本对象蕴含的情绪结构所拨动,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叩彼应、一击两鸣的情形。……是读者喜怒哀乐的情感运动形式的波峰和极限。”[6]140共鸣是文学接受进入高潮阶段的重要标志,是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感应现象。小说的评点者要在阅读体验中产生共鸣体验需具备三个主要的条件:一是读者个人的思想观念要与小说的作者或作品中所蕴含的观点态度相同;二是读者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与作者或者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经验相同或相似;三是读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作者或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致寻求心灵的契合。从《绿野仙踪》的评点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评点家与作者李百川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例如第四十三回中写到萧麻子形象后评“余昔荣华时亦有此友”,第二十回写到连城璧在金不换家避难却遭金妻苛责时评到:
余南北作客最久,皆系身经其苦,非就事论事作莫须有之谈也[4]215。
由此可见,评点家与作者李百川一样经历过家道中落并风尘南北,并且评点者对道教理论相当熟悉,此外还了解小说命名为《绿野仙踪》的含义。由此可见,就接受主体而言,小说的评点者完全具备产生情感共鸣的相关条件,因此能够与作者及作品本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感染力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纵观百回本中所保留的评点,我们可以看到评点者所获得的情感共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行文手法的赞叹。评点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及故事的进程一步步揭示文本的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手法的,“小说评点不仅关注小说字法、章法问题,而且还从叙事学角度探讨了叙事视角和叙事节奏问题,拓展了小说批评的空间”[7]。金圣叹、毛宗岗等通过评点的特殊形式将形式分析与审美感悟结合起来,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小说批评方式。在《绿野仙踪》中,评点者对小说语言修辞、叙事文法等内容的赞叹非常繁多,包括结构、章法、纹理、字法、句法等,这是在小说艺术手法层面上所获得的共鸣。苏兴指出:“但他能结合《绿野仙踪》作品,具体也予以点出,这对读者认识小说手法的通用之妙,还是可赞许的。”[8]评点者对小说中叙事艺术的赞叹承袭了金圣叹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例如“大文字”是金圣叹用以评点字词的批评方法,它指的是长篇小说中每个情节段落的高潮,例如第四十三回中写到温如玉离开省城来到试马坡遇见一人后评道:
以下欲起十数回大文字,先出此一要紧脚色作引,巧为连合,使章法贯穿,浑无一丝斧痕[4]471。
再例如金圣叹用“关锁”指称作品的结构,《绿野仙踪》的评点中也有出现,第九十二回中:
书名《绿野仙踪》而不曰《朝野仙踪》者,缘冷于冰系通部大关锁人[4]1049。
此处评点者将冷于冰称为“大关锁人”意在强调冷于冰是串联小说结构框架的关键人物。诸如此类,评点者通常将小说中所运用的叙事技巧与金圣叹、张竹坡等评点大家的批评实践联系起来,表示对行文手法的肯定与赞叹,包括评点文字中直接出现的“好”“奇”“妙”等感叹词,这些都是评点者在小说艺术形式层面上所体验到的共鸣。
其二即是对黑暗现实书写所激起的共鸣。虽然小说是以冷于冰师徒的求仙历程为主题内容,但其中所叙述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为世情书写,作者将笔墨投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官僚党派中的中间斗争,小至市井生活中的家庭琐事。作者在对世情生活的描绘中毫不保留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对污浊世情发出强烈的劝诫和感慨,而评点者在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时,通常显现出与作者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态度。第三回中严嵩赞赏冷于冰才学并邀他来相府后评到:
今人或少有财产,或有些小功名,一见面便欲着人奉承他,真是不知分量之至。还有一种污卑匹夫,名位才德一无所有,于钱之一字,怜疼入骨,他还要处处抽尖拔毛,占人便宜。此辈理合埋头屎尿中,与尘世断绝交往才是。偏他还最爱人奉。有不将他物色者,他便怒形于色,指摘人狂誖。这种不知天地大小的杀才,犹之疮癣病狗,没见生客至,还作轻起掀牙状,欲人惧怕回避他,全不想自己是何物料!真令人笑亦不胜笑,怒亦不可怒,可怜也不足可怜也[4]24。
此处写到奸臣严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小人行径,便激起了评点者的情感共鸣,更是借严嵩之行径骂尽天下见利忘义的小人,字里行间中显现出评点者愤怒、憎恶的情感态度,此类评述在评点中比比皆是,通常是切齿痛骂、言辞犀利。可见评点者对小说中所叙述的生活情状有相当强烈的共鸣,他能够体会到作者在行文中所暗含的批判态度,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态度顺势发泄出来,形成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
其三是对崇道贬佛的认同。《绿野仙踪》这部作品是以冷于冰及其弟子求仙访道的历程为主要线索的,概括来说即是主人公们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受挫然后迷途知返,放弃追求世俗尘欲,转而悟道并修炼成仙,体现出鲜明的向道倾向。而对于另一大宗教佛教,小说中显现出明显的排斥情绪,小说中的和尚多为小人形象,全然不见念佛之人的善良心性。面对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鲜明的崇道贬佛态度,评点者也表现出相同的看法。第九十六回中写到连城璧进入幻境当中,评语说:
余读各家道书,大要以割爱为首务。像这些爱亦难割也[4]1083。
可见评点者读过大量道书,文中还有多处直接介绍道教理论的相关内容,并且对冷于冰求仙的人生选择表示出肯定的态度。然而另一方面评点者虽未直接表明对于佛教的强烈排斥,但在一些评语中能够看到评点者是与作者站在同一立场之上的,例如第十一回中写到冷于冰遇见性慧和尚,评者道:
奈余南北奔驰三十年来,所遇者皆性慧此类,还有比他更势利数倍之流,因此余佛亦不深信。没见布施和尚人,心窃笑其痴愚[4]115。
第四十六回有评语:
见佛而何等庄严,通为不肖僧人作营钱财、害相思地也[4]507。
显然,评点者对于道佛两教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思想方面,评点者也能体验到与文本主体倾向相契合的共鸣状态。
“从根本上讲,阅读共鸣是发生在心灵深处、触及灵魂的一种整体心灵震撼,它是读者在一刹那的‘高峰体验'中将作品意义融入至自己的精神世界。”[9]《绿野仙踪》的评点者似乎成了作者的代言人,他能够发掘出小说中所暗藏的“真理”,并且与其产生心灵上的契合,即所谓的情感共鸣,这种激烈的心灵感应状态使评点者的阅读体验达到了高潮。
三、评点者的自我意识与价值评判
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提到:“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讳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务》诗,可劝薄妇敦。”[10]白居易在这里强调的是他阅读张籍的古乐府诗歌之后所获得的净化和感悟的心理状态,这指的是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所打动所实现的一种人格提升,包括领悟到某种人生真谛,提升自身的思想、精神境界等。在《绿野仙踪》的评点文字中,我们常常能发现评点者从文本中所获得的净化和领悟的阅读体验,其中不仅包括评点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升华,还有对作品思想内蕴的价值评判。
死亡是每一个自然人都无法逃脱的必然命运,《绿野仙踪》这部小说对死亡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且由死亡所带来的焦虑心理成为冷于冰等修道者追寻仙界的原因。小说中叙述了各种类型的死亡缘由,例如突染疾病,意外而死,报应死亡以及悲剧性自杀式死亡等等,在小说中所叙述的种种有关死亡的因果之中,意外之死是颇具审美意蕴和哲学内涵的,并且作者有意识地突出死亡的突然发生,例如王献述的突然暴毙为冷于冰带来巨大震撼并且也成为促使冷于冰悟道修仙的直接原因,正因为王献述的突然离世,促使冷于冰在极度伤心之余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再联系到自己初入相府所经历的不平之事,这才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追寻仙界之中。可以说恩师的离世使得冷于冰重新规划生命的转向,是死亡这一生理现象引发了冷于冰心理上的焦虑,从而构成了追寻长生的主要原因。小说中对于王献述死亡的书写构成了一个强烈的转折,评点者也发表了自己对于死亡的见解:
盖人至于死而万年灰矣。太史公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如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假而死,贲育之勇而死。死固人所不免,然死能名显当时,传闻弈冀。如是而死,死复何恨。其次位兼将相,锦衣美食,姬妾环绕,儿女盈阶,享耄耋期颐之年,死亦足矣。惟是年末三十、四十,一旦天夺其魄,二竖作祟,富贵者抱歉泉台,贫贱者衔悲冥府。名利两未畅意,是有生反不如无生为愉快耳。甚至死于非命更是难堪[4]49。
在评点者眼中,死亡并不单单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它是含有不同价值的,最令人意难平的在于意外之死,突如其来的死亡使得“名利两未畅意”,这样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反不如“无生”来得愉快。接着评点者又指出:“此丹经、道术之书所由传,服神、御气之士所由作也。”这句评语将对于死亡的考量引入到道教的范畴,为意外之死找到了解决方式,也揭示了道士、道法存在的缘由,道教长生之术的存在正好为避免“天夺其魄”“二竖作祟”提供了最简明的指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于死亡而产生的焦虑心理。《绿野仙踪》中这段评论一方面表达评点者个人对于死亡这一永恒的哲学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为冷于冰放弃世俗尘欲转而求仙访道的选择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作出价值评判。再例如第二十九回中讲到朱文魁夫妇卖弟妇一段时,评点者道:
可见天地间事无大小,总不出情理之外。……所猜等话,句句如见。正俗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4]321。
这里评点者指出了世间万物统归于情理的朴素道理,领悟到在人情世故之中需正大光明,不可背后使坏的道德准则。再例如第六十九回中温如玉入甘棠梦境刚刚享受荣华富贵,却又遭遇帝国叛乱,正要走投无路惊慌失措之时,评点者说道:
妄想人人俱有,也该量自己才能。才能多大,方可想多大的富贵。即或终身穷苦,亦命运使然[4]761。
这里评点者仔细分析了温如玉的性格、行事以及为何落得如此人生下场的因果始末,指出命运的未知性与不可抗拒的特征,领悟到人活一世应量力而行,不可痴心妄想贪名图利的道理。
龙协涛指出:“文艺欣赏就是从审美对象中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找回你自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对象之间某种本质联系的惊奇发现。”[6]230从评点者对《绿野仙踪》的评论中不难看出,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评点者总是能够从作品的叙述内容出发,找到其中所暗含的有关于主体意识的某些东西,或是对小说中某个人物、某种言行的简单看法,也或者是对于文本中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的判断和思考,总之这种阅读体验激发了评点者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阐发。不仅如此,评点者在接受活动中所获得的净化、领悟等心理感应状态也印证了叶朗先生所指出的“小说欣赏是情感、理解、想象、品味等多种因素的心理功能的交融和统一”[11]。正是凝聚了多种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评点者能够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唤醒及对作品内蕴的价值评判。
总的来说,百回本《绿野仙踪》中多达七万余字的评点文字从侧面展示了文学接受活动中的某些内容,从接受对象上来说,小说中的评点为后来的读者展示了一个多人参与的群体性阅读活动,最终由作者某一位熟识的友人或同寓写下评点文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绿野仙踪》的评点记录了评点者对文本内容产生心理共鸣以及净化、领悟的心灵感应状态,之后的读者也能够从评点者所书写的评点文字当中领悟到作品、读者、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杨义先生在论及评点的叙事学意义时提到:“评点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阅读学,或读者学,它是评点家反复阅读的结果,又成为其后的读者开卷阅读的先导。”[12]因此,评点者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读者不仅将个人的阅读体验真实地表现出来,还成为后来的读者的阅读向导,这也是评点这种文学接受形式的价值所在。
四、结语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绿野仙踪》抄本系统中所载的评点成为这部小说面对读者并记录下来的重要材料,我们通过探讨文本中所夹杂的评点文字,进一步了解到评点家作为接受者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体验。文学评点的过程正是阅读接受的过程,评点家也是读者,因此,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对《绿野仙踪》的评点进行阐释,我们能够探讨出小说评点在文学接受过程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并且这也有助于对《绿野仙踪》这部小说之外其他文学作品的评点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