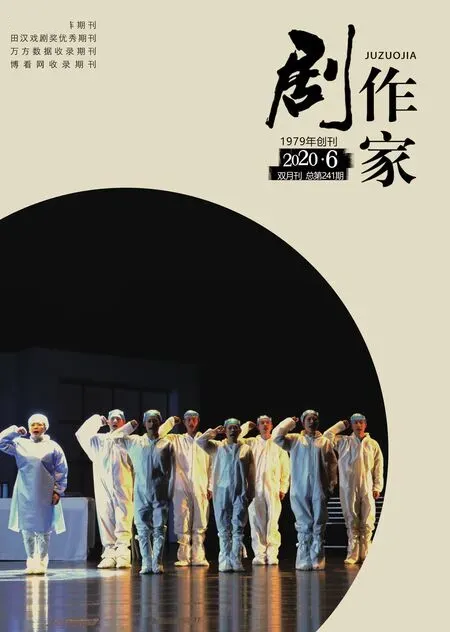浅谈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的“种子”
2020-03-03林连城
■ 林连城
演员创造角色的依据是什么?形象是怎样在舞台上产生的?应遵循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或手段?解决问题的步骤是什么?笔者反复地揣摩自己的艺术实践道路,大量观摩,学习经典,从而得出一点体会。
首先,确定人物形象体系。这个形象体系就是细节与总体、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建立在对剧本的整体理解、对人物性格分析和人物特殊经历把握的基础之上。如高甲戏《玉珠串》通过一串玉珠的失而复得过程,串连了平民、无赖、乡绅、官吏等一批人物,目的是通过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呈现出来的举止,揭露出人性善恶的根本不同,从而达到扬善弃恶的目的。人物和事件的总体趋向都必须为这样一个主旨服务。
其次,确定主次人物关系。一出戏人物的主次不是人物的正反定位。《玉珠串》的主角是柳青、银娘,同时也是无赖丁四。从表现上看,丁四的戏份比柳青多。但却始终邪不压正,尽管有暂时的低潮,但低潮只为后来的高潮迭起起到了一个欲扬先抑的作用。所以,所有舞台的调度都很好地迎合了这种主次人物关系和为矛盾冲突服务。
从单一角色来说,戏曲人物塑造的“种子”其实是从表演的角度、从表意结构入手,塑造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外在形象,它借助形象塑造和表演美学,让这个人物角色更为准确、生动、形象和活泼起来。在增加观众审美兴趣的同时,寓教于乐,寓庄于谐。这是舞台观赏和人物塑造的可看性需求。
“种子”是案头的也是场上的,是分析人物后得出的“形象总和”,在案头就开始,于正式排练之前形成。修正是在排练过程中,仅是准确性的修正,而非颠覆。
个人天性的“质朴”是最基本的底色,所以才有“本色演员”与“演技派演员”一说。但更多的情况是本色的比重占更大,但不绝对。从本色到技巧就是要克服“质朴”,进而去寻找那些属于当下、剧本所提示的那种环境的艺术自我与自觉。因此这种“自我与自觉”是可以培养的,它的形成是自由、主动和幻想地创造。
演出“种子”贯穿行动的一致性很重要。作为人物的贯穿行动,必须与角色特质契合,从而达到行动与角色的一致。
那么角色的“种子”与演出的“种子”有何区别?笔者认为,角色的“种子”是一种定性,演出的“种子”则是从量上去拥抱和围绕角色;角色的“种子”为里,演出的“种子”为表。表里互为依存,表演要服从和服务于我们的角色。
演员的“质朴”气质和时代、生活有关,也与个人的生活体验相关,是会随着演员自身理解与体会的深入、不断地开拓角色的精神空间和内在韵味而变化的。所以,不同人、不同时段塑造的同一角色会有差异。这也是师徒传承中,徒弟从揣摩学习和自身体认、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艺术体验和创造。既有阅历与经验的制约,也应注重技巧和演习经验的积累。
从形象塑造来看,过去的、业已定型的人物或角色“种子”,不是不可以颠覆的。它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被后人摒弃,以新的理解与阐释,产生更加生动和具有说服力的形象。这种变异是挖掘的解构,是观念裂变的结果,也是事物的另一面的透露。可以是直接的、正面的动作,也可以是间接的、反面的,由简单而复杂,由表面到本质,由粗糙到细腻,甚至是倒过来的荒诞和再创造。这一切不应该受到抵制和扼杀,反之,它正是我们舞台艺术创造力无穷的表现。
节制与夸张是艺术表现的两个方向,任何的过犹不及和缺乏激情创造力,都会让舞台失色和缺少生动。我们的经验是有抑制的冲动,应该更艺术地、思索地表现我们的故事与题材,才会有更好的艺术效果。同时,节制并不是反对夸张,夸张是一种艺术手段,尤其戏曲。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作为戏曲的虚拟性要求,正所谓的“歌之不足,舞之蹈之”。
尊重戏曲自身规律。一切的舞台创造要围绕戏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展开,作为戏曲中心事件的人物如何体验与表现,是我们选择人物形象“种子”的始点。一切由此开始,并由此展开。检验成功与否,标准就是成功地运用戏曲艺术的特征和手段,来达到人物的塑造及典型化,从而为舞台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