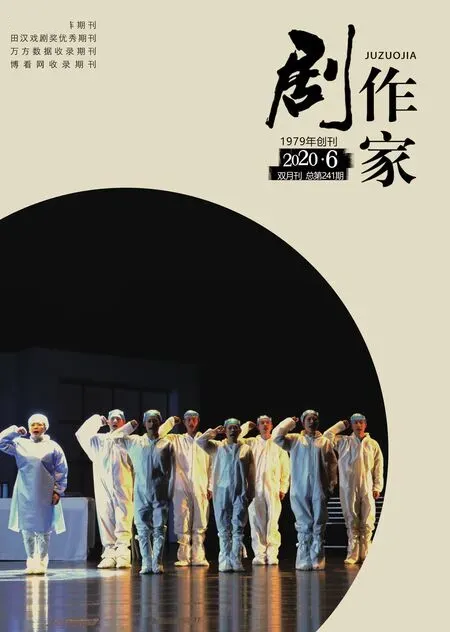“从自我出发”在话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以《风声》白小年为例
2020-03-03王佳韩芸霞
■ 王佳 韩芸霞
演员创作人物的基本任务是塑造出有血有肉且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了使演员在舞台上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提出了“有魔力的假使”这一说法,要求演员在塑造角色时问自己:“如果自己遇到与角色相似的问题,我会怎么办?”[1]并要求演员用行动进行回答。后经过多方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有魔力的假使”说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从自我出发”这一舞台实践理论帮助演员在角色创作初始阶段就与自身真情实感相挂钩。
话剧《风声》是中国现代作家麦家于2007 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悬疑推理谍战长篇小说,2009年9月由陈国富将其搬至电影银幕,同年11月,陈薪伊指导的话剧版《风声》开始陆续在各大舞台上进行演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笔者在话剧作品《风声》中塑造白小年这一角色。作为日本军官肥源的爪牙,白小年不惜牺牲中国同胞抓出老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角色。在以往的戏剧影视作品中,白小年一直以男性角色存在,而这次由女性演员塑造,性别的改变使角色的典型性格、人物关系、行为动作等都发生了变化,为演员塑造人物形象增加了难度。“从自我出发”创作角色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当中最实质的理论归纳,虽然明确了人物形象塑造发自演员的内心,而非单纯的外部模仿,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角色的精神生活,但对转变性别的角色塑造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理论指导。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表演经验,笔者试图通过“从自我出发”这一理论,指导完成本是由男性演员塑造的人物形象,提出笔者在塑造这类角色时所遇到的问题,并总结归纳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方法。
一、演员与角色的关系
演员与角色之间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究其根源,是因为“自我”。“自我”原是一个心理学词汇,指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是单独的个体对于自己存在的认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提出的“从自我出发”这一舞台实践理论中,“自我”始终存在着两个意义: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第一自我”指演员,“第二自我”指角色。在创作过程中,演员如何处理好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即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对于树立正确的表演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而演员三位一体的特性就决定了演员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在解决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关系。
在舞台戏剧表演过程中,演员既是创作者、创作工具与材料,也是创作成果。话剧演员三位一体的独特性决定了戏剧舞台演员有别于舞蹈、音乐类演员。演员在创作角色时要认识和分析角色,以自己的专业技巧为塑造人物提供技术支持,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主导创作的方向。因此演员要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也就是“从自我出发”去创造舞台上生动的人物形象。然而,由于年龄、性别、职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于创作者(演员)来说,与被创作者(角色)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这就要求创作者,也即演员,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自身条件与文化、艺术修养去创造被创作者,也即角色时,需要演员以自身的条件作为创作的工具和材料,充分认识到“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矛盾,从自我出发,创造出一个与自己不同或者说很不同的人物形象来符合戏剧舞台的人物形象。
演员在开始创作时,创作者(演员)与被创作者(角色)之间的上述矛盾会贯穿舞台表演之始终。演员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之中,一要认清剧作家通过对于真实生活的提炼与浓缩创作出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和作为自然本态的演员与所塑造的角色存在着多少差异,还要了解演员不同于角色,演员要通过对角色不断的分析与研究,调动情绪记忆与生活体验,弱化自身与角色不相符的部分,积极发展与角色相似的地方,不断地靠近角色的要求,才能最终“化身为角色”。让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辩证统一起来,遵循“从自我出发”这一舞台实践理论统一创作者(演员)与被创作者(角色)之间的矛盾。
二、“从自我出发”在话剧表演中的特点
演员塑造角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角色在演员的情感与体验中不断发酵,演员利用自身内、外部的条件及素质,经过漫长的自我磨合,最终塑造出角色形象。而在这一过程中演员要付出极大的艰辛。而“从自我出发”便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解决演员角色情感体验问题的舞台实践理论之一,具有角色不离自我、角色制约自我及自我作用于角色这三种特点。
首先,戏剧艺术的核心与基础是演员扮演、塑造角色。演员是表演艺术的前提和主体,角色不仅存在于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更应被生动形象地立在舞台上,而后者更能让受众有直观的感受。演员三位一体的特性决定演员在舞台表演中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舞台上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能离开“自我”,通过演员自我的行动与台词完成角色的塑造及戏剧情感与人物情感的传递。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国家、民族、肤色的人在行动、思维逻辑上都有共通之处,而在舞台创作中,演员一方面要从自我出发遵循人的普遍规律,塑造出真切生活在舞台上的“人”,另一方面还要遵循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法则,让观众体味从自我出发下的角色魅力。笔者在塑造白小年一角时,首先要肯定的是我所塑造的角色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创造脸谱化呆板的角色形象。其次,白小年在话剧《风声》中为反面角色,在创造这类角色时要避免舍弃自我对于角色情感的体验而刻意丑化角色,将外在的像与不像作为角色创作的唯一准则,其结果必然会造成角色内外部脱节。在创作过程中要立足于自我,角色的塑造离不开自我。
其次,角色由演员来塑造,演员在舞台上诠释角色时,既要考虑到与角色的关系,也要控制好“自我”。“自我”是为了塑造角色而存在的。演员在进行舞台创作时,不能仅仅追求典型环境中演员个体的自然与真实,而忽略了舞台角色的存在,这会导致演员无法创作出富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戏剧人物形象。“千篇一律”不仅会使得演员没有创造力,同时也会使得角色失去生命力,因为角色制约着自我。
最后,观众在观摩戏剧作品时经常感慨“演得太好了”,这体现在自我作用于角色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即创作角色时演员的情感体验与外部表现。演员在舞台表演中,一方面要真情实感地投入到角色的规定情境中,另一方面又要将体验到的情感通过表演技巧表现出来,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角色的魅力。白小年作为“和平军”淞沪司令部秘书,是一个反面角色。笔者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在体验白小年情感的基础之上,寻找最能够表达其内心体验的台词及形体动作,凸显白小年这一角色的人物性格。如在序幕中的一段台词:“……如果各位破译了这份加密的电码一定是前途无量啊,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我白小年啊!”在处理这段表演时,一方面要符合反面角色的人物形象特点,让观众准确判断出白小年这一角色是好还是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角色塑造类型化。这就需要肢体动作与台词的互相配合,因为此时的台词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台词,而是需要给观众传递信息的潜台词,因此在处理这部分台词时笔者着重强调“前途无量”“提携”两个词语,以便让观众感受到白小年话中有话。在说台词的同时微微欠身,略带笑意地看着四人,更好地展现出白小年这一反面人物虚伪的性格特点。
三、“从自我出发”在白小年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一)“从自我出发”接受角色
斯特拉斯堡曾说过:“演员需要不断应对想象出来的事端,因此演员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可依赖的东西,为了在舞台上完成一件事情,他必须首先让自己相信做这件事情是合情合理的。”[2]笔者要接受角色,接受白小年“卖国贼”这样的身份,就必须在创作过程中找到一个突破点,为这样一个反面角色在舞台上的出现赢得一个值得表演的价值。如何吃透白小年这样一个“卖国贼”身份的反面人物角色?因为无论是人物性格、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爱国情绪等,我都与她完全不同。在借鉴观摩了诸多谍战题材的话剧作品并分析了其中反面的人物形象后,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自我出发”去接受角色,接受白小年,接受自己是一个“卖国贼”身份的人。这就要求我必须将人性中的恶通过台词、肢体动作等方式来展现在戏剧舞台上,让观众去“恨”。
结合舞台表演,笔者将通过人物台词与舞台行动两个方面来论述自己的理论实践意义。
1.台词
笔者将通过分析剧中白小年的台词向观众传递角色的情感。
白小年初次登场时所说的台词:
“对不起了诸位,着实不想扫了各位的雅兴,上峰有上峰的难处,实在是有一项紧急的军务需要各位马上去办,还希望不要有什么怨言啊!”
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将吴、金、李、顾四人召集的原因,同时还刻画了白小年这一“笑面虎”的人物性格特征。因为吴金李顾四人的官衔、家世背景都在白小年之上,笔者要以相对尊敬的语气去处理台词,但同时白小年又深知四人走不出裘庄,语气中必定夹杂着小人得志的腔调,所以笔者以阴阳怪气的语调去展现了这句台词。
同样是在序幕中:
“吴部长对匪情了如指掌,可以算是匪情活地图了……至于小顾参谋,年轻有为,敢说敢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以我敢说,你们四个人加起来绝对顶得上一个破译大师了……”
这段台词表面上是对吴、金、李、顾四人的夸赞,但其中却包含大量的潜台词。笔者在处理这段台词时,运用舞台语言的基本表现手段,对“了如指掌”“活地图”等词语重读,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白小年话里有话,在“至于小顾参谋”后停顿,表现白小年对于顾小梦不满的态度。
2.舞台行动
最初处理白小年这个角色时,笔者将外形的“像”与“不像”作为角色创作的唯一准则,将人物形象极度“外化”,对上司点头哈腰,对下属趾高气扬,没有心理支撑的表演不仅导致笔者演起来不舒服,而且给人一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感觉。
后来,笔者通过分析角色的内心活动,去丰富角色的外部行动。如在《风声》序幕中,白小年有段台词:
“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淞沪战区特高课机关长龙川肥源,想必各位都听说过吧,他托我给各位送来一份礼物。”
在处理“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这句台词时配合谦卑的语气来进行表达,身体微微弯腰以表尊重,但在说到龙川肥源时,腰板挺起并向前迈了一步,一方面是表示作为军人的白小年对于龙川肥源的尊敬,另一方面还展现了白小年“狗仗人势”的状态。
再有,为了配合序幕中“至于小顾参谋,年轻有为,敢说敢想”这句台词的处理方式,笔者的肢体语言也进行了改进,白小年在给顾小梦电码时,没有直接递给她,而是充满玩味地在她周围转了一圈,才慢吞吞地将电码递上。
笔者通过对台词与舞台行动的处理,让观众感受到白小年这一反面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同时,还丰富了次要角色的表演,完成了戏剧故事的展开。虽然白小年在话剧作品中的经历与命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选取怎样的角度去接受其命运,就是笔者的主观选择。在角色创作中离不开自我,让演员明白角色所做一切都是“情有可原”,不断地理解和接受角色,并通过台词及肢体动作将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及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情感传达给观众,使观众产生共鸣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
(二)“从自我出发”诠释角色
笔者在肯定角色之后,在创作人物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作为演员拿到剧本首先要对剧本进行分析,并对人物进行“小传”式的阐释与理解,但是案头工作做得越多,反而对角色的塑造越糊涂,要塑造的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明明很清楚,但却并没有代入感。究其原因,就是演员将所扮演的角色及角色周围的一切都当作“旁物”,忽略了演员最终是以角色的身份去面对观众,即角色制约自我这一特点。角色变得“千人一面”,使演员也丢失塑造角色的冲动和欲望。
演员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人物的分析无疑是“孤立静止”的,舞台上的戏剧人物形象应该是“行动着的人”,角色只有处在人物关系中,才能相互行动,并且起到推动剧情、表现戏剧人物价值的作用。通过分析白小年与其他角色的关系,加深对白小年这一角色的理解,同时丰富塑造角色的表现手法。按照“从自我出发”创造角色的原则,演员体验规定情境中角色的情感去把握与认识角色关系,从而更好地塑造白小年这一人物形象。
1.理清角色关系
笔者以一种“全知的角度”去解读戏剧人物之间的关系,即演员从自我出发,以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规定情境中的事件和人物关系,研究思考每个戏剧角色的身世经历、想法动机、可能发生的心理活动及其与其他舞台人物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会减少或避免笔者在对白小年人物进行舞台塑造时的失误。在《风声》第五幕中有一处白小年的独白:
“……像肥源这样心思缜密的人当然把该想到的全想到了,但是他就是没想到李宁玉会拿起我的枪打向金生火,就这样金生火就到地狱里生活去了……我太了解肥源了,他自视甚高又太追求完美,在任何智力游戏中一定要占尽上风否则就夜不能寐……”
这段独白一方面交代了剧情,另一方面向观众传达了白小年在思想意识中对于肥源的认识。
龙川肥源是罪恶的凶手。他一方面给白小年无限的信任,让其周旋于众人之中,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将她推向死亡的深渊。白小年深知抓出“老鬼”是龙川肥源最终的目的,而自己不过是他众多棋子中的一枚,但是她却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沦为了他的“弃子”。生命对龙川肥源来说如草芥,一声枪响就了结了她的性命。龙川肥源太骄傲了,骄傲到认为仅凭一己之力就可揪出潜藏的“老鬼”但是最后还是错了,而白小年也成了他自大的牺牲品。
通过对剧本的分析,同样可以梳理出白小年对其他角色的认识与理解。
李宁玉是母亲。白小年原以为有孩子的羁绊,就可以排除她是“老鬼”的可能,但却错了,她既是母亲,也是革命者,两个身份集于一体。作为母亲的她想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作为革命者的她又想拯救千万的同胞。李宁玉知道白小年逼迫她承认是“老鬼”的那天是自己的死期,而她的誓死抵抗,也换来了白小年的死亡。
顾小梦在白小年的眼里既是千金小姐,也是游离于名利场的交际花,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顾小梦唾手可得,所以白小年讨厌她。本以为像她这样的弱女子会在裘庄这个充满恐怖氛围的环境中慢慢崩溃直至死亡,却不承想顾小梦却成了白小年和肥源失败的关键一环。
理清角色关系,不但能使演员更加容易打动自我,还会帮助观众加深了解角色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帮助建立该角色与其他角色之间的戏剧关系。白小年性别的改变使她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或多或少也发生着变化。如在原有剧本的提示中,白小年对顾小梦有爱慕之情,那在现有的规定情境中,这种关系就是不成立的,这就需要笔者在不影响剧情发展的前提之下,转变白小年对顾小梦的认识。
2.丰富角色表演
演员塑造角色时,决不能局限在仅仅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角色形象的模式上,必须超越这个模式,这样的表演才具备创造力。每个演员创造出的角色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角色的最终目的就是给这个人物输入新鲜的血液。演员为了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角色的表演,可以运用独特的视角诠释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吴志国是白小年畏惧又仇恨的对象,畏惧是因为相较于金、李、顾三位,吴志国是一个实干家、带兵打仗的剿匪英雄,少了旁人拐弯抹角的油滑,多了一分“硬汉”的气质,因此白小年对于这个有着战绩功勋的硬汉部长,自然会有畏惧之情。因为畏惧,白小年表面上对吴志国以礼相待。而另一方面吴志国也是白小年仇恨的对象。吴志国被诬陷后,白小年对其进行了审问,这让之前就看不起白小年的吴志国对其更加嗤之以鼻,用吴志国的话来说“白小年就是条没用的狗”,这让白小年加深了对吴志国的仇恨。
笔者分析白小年与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不仅为人物关系的呈现提供了更多可能,而且也帮助笔者在塑造白小年时,不管是对表演节奏的把握,还是对更加台词气息的控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三)借助“假使”作用于角色
在话剧《风声》第六幕中,作为龙川肥源秘书的白小年,为了帮助其找出潜藏在军事机要处的间谍“老鬼”,上演了一出“捉鬼大戏”。但作为老鬼的李宁玉誓死不招认,这与肥源让其亲口招认的想法极不相符。面对肥源的施压,白小年处于一种恐惧的情感状态之中。笔者在排演这一幕时主要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体验白小年这个本是由男性塑造的角色在这一规定情境中的情感;第二,怎样通过演员的表演技巧来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借助“假使”去帮助演员进行创作。就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提到:“……当实在的现实、实在的真实还存在的时候,创作还没有开始。……但对于虚构想象的真实,演员也会同样真挚地相信,就像小孩子相信自己怀中的洋娃娃是真实有生命的一样,从‘假使’开始的那一刻起,演员就从他真实生活的领域中进入到了另一领域,这一领域是由其想象出来的,演员相信了这种生活,就可以开始创作了。”“……假如我今天,此时,此地,处在所扮演角色的位置,我将要做些什么。”如果把剧本中所提供的规定情境当作“实在的现实、实在的真实”,那我们的创作必然要从“假使”开始。
如何体验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情感,笔者将自己放置在“此时、此地,所扮演角色所在的位置”,铺垫得当的戏剧情境需要借助“假使”展开想象。白小年本想在肥源面前通过“捉鬼大戏”立功,没想到“老鬼”迟迟不肯招认,在恼怒之余也忌惮肥源会因此迁怒于自己,同时白小年深知肥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为了抓出“老鬼”任何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而且在此之前肥源已经除掉了吴、金二人,这就使得白小年加深了对肥源的恐惧。
体验到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情感后,演员如何将其内心体验转化为外部表现,并区别于由男性演员塑造的白小年形象?笔者通过台词、舞台行动等表演技巧,比较原来由男性演员塑造的白小年这一人物形象,试图将角色的内在情感通过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比如:
“……想不到吧,花容月貌的司令太太竟然是老鬼的同党!你们想去看看她吗?我是不忍心看的,我天生怜香惜玉,最见不得一个美丽的女人被打得体无完肤……”
在处理这段台词时,要区别于男性演员对白小年的形象塑造,并且确保可以展现出白小年的典型性格。男性演员在表现这段台词时,突出自己男性的强硬感,比如在说“我天生怜香惜玉”这句话时,可以夸张并且着重地强调,以表现白小年的虚伪,并配合相应的肢体动作,如抚摸女人的脸等。但是此角色换为女性演员塑造时,表现方式就要有所改变,如将“我是不忍心看的,我天生怜香惜玉”这句话删掉,加重语气处理“竟然是老鬼的同党”这句话,突出白小年抓老鬼的目的,削弱角色的男性特征。
笔者借助“假使”,从自己所能理解的生活经验或是语境出发,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白小年这一角色的情感,在完成角色任务的同时,区别于男性演员所塑造的这一角色,并且通过台词、肢体动作等外部表演技巧将体验到的情感表现出来。
“从自我出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舞台实践理论之一,这是经过长时间舞台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得出的演员在舞台上如何塑造出真实可信人物形象的有效方法。笔者力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之下,结合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从《风声》的排演,讨论“从自我出发”去创作角色的方法。首先,笔者以《风声》白小年的人物设定为例,白小年作为反面角色是剧本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选取怎样的角度去接受这一设定便是演员的主观选择,不断地理解和接受角色,为塑造角色奠定基础。其次,笔者以《风声》中白小年的人物关系为例,提出在探寻角色关系时避免人物形象脸谱化,应该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语境出发,真实地去体验生活在角色规定情境中自己的情感,并总结出理清角色关系、丰富角色表演两种方法。最后,笔者以《风声》第六幕“捉鬼大戏”为例,实际演绎了如何借助“假使”去帮助自己体验到性别转换后角色的情感,并在体验到情感的基础之上通过台词、肢体行动等外部技巧将其表现出来。
注释:
[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罗伯特·科恩:《戏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