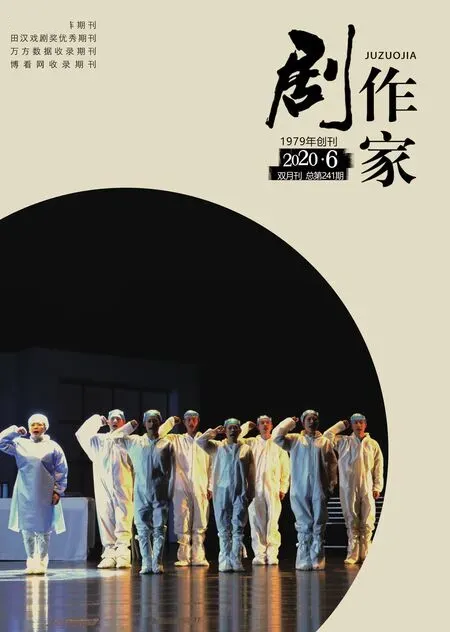关于川剧“泸州河”的形成、流变及艺术特色的研究
2020-03-03乔官瑞
■ 乔官瑞
川剧又称“川戏”,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早在唐代时期,民间就流传着“蜀戏冠天下”的说法,其地位可见一斑。川剧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厚的剧目积累、精妙的表演技艺、完备的声腔体制,使它成为巴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成就了它在中国戏曲史上显要的历史地位。川剧是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剧种。在川剧的演唱形式中,高腔是最主要、也是最具地方特色的唱腔,而在川剧各流派分支中,“泸州河”是最能体现出川剧这个特点的一个分支,因此,泸州也被誉为川剧高腔的发祥地。2007年,“泸州河”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第一个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川剧剧种。泸州市于2012年4月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川剧传习、展示基地。
一、川剧“泸州河”孕育、形成的渊源
川剧界为区别地区性的性格、特色,各分支不称流派,而称“河道”,“泸州河”便是川剧的一支。
由于四川地域辽阔,省内陆路交通不便,戏班演出一般沿水陆码头在一定的区域内流动。至清代中晚期,川剧逐步形成以资阳河、川西坝、川北河、下川东为代表的四大流播区域,在艺术上也受师承关系和地域文化的影响,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四大流派,俗称“四大河道”。各条“河道”主要以擅长的声腔、剧目的不同为特点,其打击乐和表演的风格也有一定差异。而“泸州河”原本是资阳河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在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演变为单独的一条“河道”。以泸州为中心的川南一大片地区,包括四川南部长江、沱江、赤水河、永宁河流域,辐射到川、滇、黔、渝大部分地区的川剧剧种,统称为“泸州河”。
(一)自然与人文环境为“泸州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泸州自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江阳县以来,基本上是郡、州、府、道和专署、行署所在地。同时由于扼川滇黔渝之结合部,控长江、沱江两江之汇合处,泸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尤其在主要依水路运输的古代,使之自然成为交通的枢纽、 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晚唐至北宋时期,泸州境内江河运输繁忙,整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川江号子不绝于耳。作为水运码头和已是“万户赤酒流霞”[1]的酒城,时时迎来送走演出杂剧的“子女”“丈夫”。
明代,泸州被列为全国26个重要城市之一。张船山咏诗道:“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红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洲好,十指寒香给客橙。”[2]泸州“西连僰道、东接巴渝、南望夜郎,控云南之六诏,疆连井络之三边。维泸州之大邦,控三巴之百蛮”,已成为宋时之西南要会,“疆分巴蜀,人杂汉夷,环江带水,控制边界,最为重要”[3]。更由于盛产稻米、盐、茶、马匹等,岁输米二万石以供军,草市镇发达程度仅次于成都地区,再加上与蛮互市加速了城廓的建设,终于在南宋时泸州博得“雄壮甲两蜀”的美誉。交通发达、商贸繁荣和频繁众多的流动人口,促进了泸州文化艺术的发展,为孕育出以擅长高腔的“泸州河”川剧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
(二)丰富肥沃的民间文化土壤孕育了“泸州河”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说:“戏曲肇自古之多傩。”在“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地方宗教文化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远征汉代,巫觋祈神这一宗教文化现象在泸州地区就很盛行。到了唐代,“信者众多,有病不延医服药,辄谓鬼祟,请巫逐之,乡间尤甚”。后来,“每岁仲春,各署都官祠均设醮庆坛,城中及乡场建清醮,……讽经拜忏,祈禳祷祝,乃弭毒驱瘟之意也。惟庆坛则用巫觋装演百神,扬戈执盾,歌舞一堂,棘矢桃弧,祓除邪祟”[4]。其形式接近于戏,流传已久,相习成风。
在泸州城区及其所属合江等县出土的汉代石棺上所刻的《巫术祈祷图》, 就记载了当时“以酒祈天”的生动场面,印证了当时以歌舞侍神的巫觋、“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以及男觋女巫被视为神灵的使者和化身而受人尊崇的历史事实。“月令所谓,国有大傩,孔子朝服立阼阶。圣犹从众,盖亦未可厚非也。”[5]至于唐代所建的真如寺内所塑“百子图”中的“说书俑”“抚琴俑”“杂技俑”等,更说明当时各种艺术门类在泸州已普遍存在。泸州是民族杂居的地方,古蔺、叙永两县,尤以苗、彝二族最多,历来以巫为业者有之,民间称为“苗端公”“莽道士”。有关苗傩、葬傩的活动,都有本民族的特色。在祭祀活动中,古有八蜡之祭。“每岁建亥之月,田功告成,则合聚八神而报享之,谓之八蜡,又称为祭八蜡坛”[6]。另在泸州乡村还盛兴“秧苗戏”,每年四月栽早秧之际,阡陌之间,各列咂酒效坛,鼓歌聚饮,乡民们唱“秧腔”,敲“镗锣”,自栽秧到打谷期间献演。宗教文化赋予了“泸州河”戏曲先天的秉赋。
此外,泸州地区在民间久远的“闹元宵”节目中产生的古蔺花灯、合江“下河灯”及遍布各县的车车灯、扭扭灯等独特地方小剧种,对“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也产生过较大影响。自隋唐以来,每逢正月初一至十五是年节。这时百业休息,鲜衣、盛食,亲友团聚,互相拜年,极欢娱游晏之乐。城乡寺庙、道观皆立灯杆,以绳引灯,火树银花,锣鼓喧闹,游人如织,这就是所谓的灯节。到了元宵之期,“居民结棚张灯,敲锣鼓,童子女妆唱采茶、跳竹马,城乡各作龙灯、虾灯,彼此互迎”[7]。自灯节开始,“城乡鱼龙车马之纷起,有龙灯、虾灯、狮灯、花灯诸目,至上元之夜而极盛”[7]。其中,“最令人轩渠者为花灯,昔称车车灯,以男扮女,项黄腰大而嫣然。别扮小丑,左执汗巾,右秉蒲葵扇以戏之,婆娑蹀躞,唱采茶歌,余人和之,金鼓为节,彻夜乃息”[7]。不管是“出折子”“说正书”, 或者“灯夹戏”“戏夹灯”,均颇受民众欢迎。其舞蹈、唱腔和表演的节目,不少都为“泸州河”川剧所借鉴。
戏剧学中,“巫术说”观点认为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发生于人类原始巫术活动中的扮演和模仿。“巫觋祀神”其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观赏则是“泸州河”戏曲的原始形态,宗教神祀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会馆戏楼为“泸州河”演出提供了空间
明末清初,经历过战乱的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康熙帝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向四川移民,这便是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此后,四川成为“土客错居,五方杂处”的移民省份,因此各种移民会馆也应运而生。在泸州,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们与泸州本土艺人们一道,先后建有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山西会馆、陕西会馆、浙江会馆、江南会馆的八省会馆。
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的繁荣,而戏曲的发展,每每又与当地的迎神赛会、风俗习惯密不可分。庙台,自明洪武、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年间,陆续都有兴建,如常清寺、普济寺、清源宫、禹王宫、文昌宫、紫云宫、东皇庙等。入清以后,戏楼修建尤多,家祠、私宅均有营建,另有专供演出的万年台,更为戏曲广泛活动提供了有一定规模的场所。
遍及泸州各地城镇的“九宫十八庙”,多为供奉移民原乡神祉,如湖北籍建禹王宫,广东籍建南华宫,江西籍建万寿宫,四川土著则建川主庙。各类娱神娱人的演剧活动,如神会戏、吉庆戏等,以及演唱不同声腔的戏曲班社,在各移民会馆及宫庙的戏台(俗称“万年台”)中频繁演出。如清嘉庆年间《成都竹枝词》有“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的描述。
据不完全统计,遍布在泸州各地的各种会馆戏楼,属明代建筑的有40余座,属清代的有300多座。在泸州民间流传着“正二三月撵灯杆之灯戏,四五六月好下田之秧苗戏,七八九月收上坎之会戏,十冬腊月好庆坛之傩戏”的说法。人称泸州是个“戏窝子”并非虚语。
二、川剧“泸州河”在流变、发展中形成自身体系
乾隆时期,在四川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随着入川诸腔四川化的演变进程,逐步形成发展和繁荣兴盛的川剧艺术。承中华戏曲之传统,融巴蜀艺术之精华,兼收并蓄,自创一格,以南北一体、五腔兼备、文野交融、雅俗共赏为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梨园中一枝别具异彩的艺术奇葩。
(一)“泸州河”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
“湖广填四川”造就了泸州多元交错的文化景观。在这种人文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川剧艺术,与生俱来地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而这种吞吐万象的吸纳功能,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它在形态构建中的综合特征。“泸州河”作为川剧的一个分支,其一个表现方面是对中华戏曲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扬。
第一,在剧目上“泸州河”对传统戏曲兼收并蓄。在“泸州河”现存的大约上千个传统剧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宋南戏、元杂剧、明传奇及清代的花雅部剧种。如宋南戏的“荆、刘、拜、杀”, 元杂剧的《窦娥冤》 《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 明传奇的《投笔记》《红梅记》《玉簪记》《绣襦记》, 清代花、雅部的传奇故事剧、历史演义剧等等。如经由赵景深梳理的弋阳腔剧目,在川剧中几乎无一缺满。加上巴蜀地方艺人、文人的自创剧目,“泸州河”构成了一套涵盖古今、包容南北又极具地方特色的剧目体系。
第二,在音乐上,“泸州河”吸纳“五腔”。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昆山腔、弋阳腔就通过长江流域流入四川。自清初以来,随着各省移民大批入川,昆腔、弋阳诸腔、梆子腔、皮黄腔等相继出现于四川,使四川舞台呈现“诸腔杂陈”的局面。嘉庆年间,各声腔剧种的“四川化”演变已基本完成,苏昆变成了川昆,胡琴腔变成川胡琴,秦腔变成川梆子戏,乡土灯戏也纷纷进入城市。“泸州河”以高腔为主体,将昆腔、胡琴、弹戏及泸州灯调熔为一炉,形成了南北一体的声腔体制,兼具了明清以来中国戏曲的主要声腔。
第三,是各类表演功法程式的交融。川剧舞台上的众多角色分为小生、旦角、须生、花脸、丑角五个行当,每个行当之下又可分为若干人物类型。“如旦角行可分为闺门旦、青衣旦、正旦、花旦、奴日泼辣旦、鬼狐旦、烟花旦、刀马旦、武旦、摇旦、老旦、娃娃旦、丑旦等;丑角行可分为袍带丑、官衣丑、龙箭丑、褶子丑、襟襟丑、武丑、方巾丑、婆子丑等。”[8]每个角色行当均有其系统的功法程式,各个人物类型也有其特殊的技术规范,它们主要由各古老剧种的行当划分及技术规范综合熔铸而成,“泸州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而且在具体表演中更注重人物情感的表现。
第四,是舞美的综合展示。“泸州河”川剧在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特别是在人物化装造型上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其服装多源于明代服饰,舞台场景也多沿袭于一些古老戏曲剧种的传统规制。“泸州河”脸谱虽然有鲜明的剧种特色,但其本源仍与一些古老戏曲剧种有很深的渊源。道具中的以鞭代马、以桨代船、以旗代轿、以杯代宴,以及一桌二椅及刀枪剑戟的使用,与一些古老戏曲剧种也是大同小异,其传承性显而易见。
当然,“泸州河”对中华戏曲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巴蜀民间艺术的广采博纳,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兼容后成为了自身生长的元素,融入到了“泸州河”的魂魄之中。比如扬琴、清音曲调被“泸州河”吸收之后,均已失去其原有的品种属性。
(二)“泸州河”从地方戏到官戏的演进
外来剧种在被“泸州河”继承和吸纳的过程,也是从地方戏到官戏的演变过程。
泸州早期 “走州串府”、漂泊于水陆码头的戏班,人称“江湖班子”, 通常在庙宇、会馆、宗祠等戏台演出献艺。一些江湖戏班在驻留城市后,逐渐发展成行当齐全、衣箱完备的戏班。到光绪末叶,茶园大兴,遂有舞台艺人联合票社组织定时定地的川戏坐唱。从票友去舞台正式做演员的,名叫“下海”。
明清时期,“泸州河”最早跃上城市剧场,巴蜀大地当时就流行着“要能跑得滩,泸州河去搭班”的民谚。茶园式剧场的出现,标志着川剧从广场艺术向剧场艺术的转变。清雍正二年(1724年),泸州20余名川剧艺人到成都棉花街,成立了“庆华班”,“泸州河”率先于全省从“火把剧团”进入“城市剧场”[9]。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川剧班社大发展的时期,有官班(官署戏班)、家班(家庭戏班)、乡班(乡村戏班)、科班(学、演结合的班)、玩友班(票友自愿结合的自娱班)等多种组班形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 “变法自强”,推行新政。受当时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四川官绅联合提倡戏曲改良,从而开始改良川剧[10]。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警察总局以“正俗”为名,用惩戒与奖掖的办法,对从艺伶人、戏园、戏班以及剧本刊版进行监管、督导,清除淫靡怪诞的演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川商务总会筹办戏曲改良公会,由商务总局向总督部堂呈送会章及有关司、局的审查决议,申请立案,次年9月总督部堂批复“应准如详立案”。该会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会址设华兴街老郎庙。戏曲改良公会聘请名士耆宿编写改良戏本,颁发四川各地排演。并举行伶工考核,借以提升伶界地位和人格[11]。
1952年2月,泸州群力川剧社由泸州市政府秘书室领导,1958年11月,群力川剧社由泸州市委、市政府批准为国营剧团;泸州群光川剧院由泸州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提案决定,由市文教科直接领导,给了川剧“泸州河”官办的名分。
从堂屋院坝、田间草台、庙台戏楼到城市茶园这一观演场所的变化,由端公班、师道班、灯班、秧苗戏班、钻青杠林的班而到登大雅之堂的剧社、剧团,这一演出机构的改换,即能看到“泸州河”川剧艺术从民间艺术到职业演出、孕育形成到早期发展的全部过程。
“泸州河”川剧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故事经过各代人不断的演变,逐步进入文野交融和雅俗共赏的境界,如源于梆子腔的《鸳鸯绦》改编为高腔本《拉郎配》后,即一改原作凶犯杀人、包公断案、三女共夫的陈旧套路,以辛辣的喜剧风格表现悲剧主题,注入了四川人不甘屈辱、以退为进的人格力量和斗争智慧。传奇本《玉簪记》 中的《秋江》一折,改编者也将江南一带的平缓河道化为川江,设计出一整套解缆、登舟、行船、过滩的表演程式,以推进陈姑与艄翁的性格冲突与心理冲突。
(三)科班的涌现标志着“泸州河”进入鼎盛时期
“‘泸州河’在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形成后,在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 有20余名艺人由泸州到成都,住棉花街之药师殿,招徒授艺,成立庆华班,以注重高腔而别于舒颐班(昆曲)而另树一帜。”[12]由此,标志着“泸州河”作为整个川剧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正式形成。“川剧高腔的形成就是以庆华班为标志的。在历史上‘泸州河’为川剧界创造了四个第一:第一个创办戏班,第一个开办川剧科班培训,第一个最长时间的科社,第一个使用女子帮腔。”[13]庆华班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方解体,传习170余年,为“泸州河”的传播、发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川剧名角康子林、周名超皆为后期弟子。
在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泸州合江县的邓德珍兄弟于家祠内创办了鹤龄班、大鹏班,之后兄弟二人又相继创办了全胜班、凤仪班、贵华班等戏班科社,其中名角辈出,饮誉川南。而至今被川剧界引以为荣的三字科班,乃泸州人谢维孟创办,其为“泸州河”川剧培养了一支生力军,生旦净末丑角均有成名者,其演唱实非他人所能及,对泸州地方戏剧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后来居上的作用。地处古蔺边远地区的绍俊科班,建班虽稍晚,但毗邻滇黔,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宣扬川剧、广吸人才,使“泸州河”川剧艺术走出四川,走向了云贵。
同时,曲艺中清音、扬琴的弹唱也开始由家庭自娱走向社会同乐。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从丹岩雅集开始,天然雅社、律音琴社、蓝田琴社相继成立,在民众中造成极大的影响,曲艺确唱风靡一时,民间艺人钻格子、跑码头,呈现出“大街小巷唱月琴,茶房酒肆客盈门”的盛况。市井中,专业艺人争相献技,与业余小玩友共同切磋研习。在泸州叙永一带,逐渐形成了“中河调”扬琴、清音的流派风格。特别是扬琴唱本,生旦净杂,各角俱全,其唱腔已初具戏曲音乐规模。有三国、水浒、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近百个节目。清音中部分曲目也同样具有不少的戏剧成分,这些都为“泸州河”川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从“坐唱”发展到“化装表演唱”,进而发展成戏曲剧目创造了条件。市民的增加和戏班之间的竞争又促进了剧目的建设,新戏频出,规模倍增,光是聊斋故事剧就有50多个。至于“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金印、琵琶、红梅、班超”四大本等经典话本演出,更是久演不衰。“搬目连”数十本连台,使当地观众为之倾倒,昼谈夜论,在民间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泸州在清代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及民国年间先后建立过数十个科社、戏班,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泸州河”川剧人才。这些人才,除大部分留在泸州市及所辖县、区川剧团外,另有相当部分到了川南、川东的乐山、自贡、宜宾、内江、永川、江津,以及重庆和云、贵的威信、镇雄、贵阳、遵义、毕节等地。他们多成为当地川剧的艺术骨干,进一步推广和发扬光大“泸州河”川剧艺术,扩大了“泸州河”在整个川剧界的影响。
三、川剧“泸州河”的艺术个性特征
“泸州河”在对中华戏曲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巴蜀民间艺术的广采博纳中,形成了自身的艺术个性和综合特征,其声腔完备,行当齐全,功法严谨,舞美规范,多姿多态,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蕴,表现出泸州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独树一帜的高腔艺术
高腔是最能体现川剧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腔形式。“泸州河”素有“高腔窝子”之称,以高腔艺术与其他地方的川剧拉开区别。“它的唱腔,基本上保持原‘苏昆’的特点:腔调曲折婉转,节奏较缓慢,特别讲究发音吐字的准确性。伴奏乐器以笛为主,打击乐中必须加上苏锣、苏钹。”[14]同时,“泸州河”也保持了古朴的“击节而歌,一唱众和”的徒歌式,吟咏性很强,半讲半唱,似讲似唱,因而观众听得清,听得真,感到亲切。另外,高腔的曲牌也有一定的规范格式,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理解和修养充分地表达,唱成多种多样大同小异的曲调,这使它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也给演员的创造发挥提供了广阔的酣畅淋漓的表达方式。
高腔的曲牌丰富多样,总共有三百多支,常用曲牌也有近百支。“曲牌的结构,包括起腔、立柱和扫尾三部分,另外,高腔曲牌中还有所谓‘重腔’‘犯腔’‘钻腔’‘滚腔’‘飞腔’‘咿腔’‘呜腔’‘啊腔’的区分。”[15]
常演剧目如“楼”“院”“配”“记”等,全是高腔。创作的剧目,最早的当属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泸州人高树创作的《思子轩传奇》,就是高腔戏。在其《序》中云:“少时观泸州梨园曲本,有《山坡羊》《懒画眉》等小词,伶人拍板唱之则高腔也。恍然悟高腔顺乎天籁,解必如词曲家之按谱填词,而音调常合乎词曲,甚有整调可入高腔者,亦有断乎不可入高腔者,唯蜀中老曲师能辨之。”[16]
“泸州河”的高腔戏,除《黄金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四大本之外,还有“九楼”“十八院”“四计”“四记”“十二配”等。同样的剧目,在其他流派中用胡琴或弹戏演唱,在泸州地区则用高腔。如《凤仪亭》《临江宴》《苟家滩》等剧,川西坝子唱胡琴,川东则高腔、胡琴,弹戏一齐下;折子戏《五台会兄》,川东、川西唱胡琴二黄,以生盘净为主,突净角的唱功和表演,而“泸州河”的老本子则以双盘为主要情节,先是五台山主持盘六郎,三问三答唱高腔,然后六郎盘五郎,才改唱胡琴二黄;又如《三击掌》,“泸州河”都唱高腔,川西则有唱胡琴的。
“泸州河”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它的帮腔。川剧帮腔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可起到定调、描述环境、制造舞台气氛、表达剧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揭示戏剧主题的作用,在戏曲高腔音乐中堪称独步。
在帮腔部分,其他分支的川剧多只用同一支曲牌,而“泸州河”则要根据剧中人演唱的曲牌来帮。例如,当演员唱的是[红衲袄],如需帮[没词歌]时,就必须用[红衲袄]来帮;演员唱的是[锁南枝]则帮腔也用[锁南枝]。另外,在帮腔时,演员多采用独唱和帮腔相结合,即一唱众和,不用丝竹伴奏,属于徒歌形式,使用打击乐器伴奏,不用丝竹管弦乐器伴奏,并且腔调紧密结合地方语言,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泸州市川剧团在1953年首次打破由鼓师领腔和男声帮腔的传统,招收了四名女子帮腔人员。随后,泸州所属各县剧团也相继仿效,大大提高了帮腔的艺术质量,并逐步推广到了整个川剧界。
(二)堪称一绝的“泸州河”打击器乐
“泸州河”为更好地表现剧情,特别注重对锣鼓、唢呐的运用。民间有“三分唱、七分打”“半台锣鼓半台戏”的说法。锣鼓是高腔音乐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他声腔川剧的打击乐器主要有板、小鼓、大锣、钹、小锣、堂鼓、铰子等几种,有时也用酥锣、酥钹、酥铰、二星、当当、低音锣、包包锣、低音鼓等。这些乐器只有相对音高,音量和音色各不相同,但配合起来演奏,却能收到非常协调的效果。“泸州河”川剧与其他剧种相比,更注重效果的渲染。“泸州河”川剧锣鼓曲牌分为五大类:牌鼓类、通用锣鼓类、声腔锣鼓类、唢呐套打类、效果类。
第一,在高腔戏中,要求飞、钻、重、犯、合同、尾声、尾煞、转煞,都要做到板眼明亮,套打清澈,轻重入理,文武有序,变调自然,喜怒哀乐以乐动人[17]。如《三跑山》一剧的孤舟令,属流水腔的高腔,“泸州河”则按流水腔完成此剧,而不同于别的河道之用江头桂为主旋律。因为用流水腔更适合剧中人离家避祸、露宿荒野之情。再如《钟馗送妹》中,“泸州河”打的是挂板扑灯蛾,合同转三查子,中间再套品锣儿、道士令,一气呵成。第二,“泸州河”讲究对不同的口戏安排不同的锣鼓,每演出一台戏,必须打十余支以至数十支不同的锣鼓牌子和唢呐曲牌。第三,在演奏方法上强调节奏的变化多端,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似小桥流水。杀场鼓时紧时慢,震聋发聩,扣人心弦。在鼓点锣鼓上更为讲究,把水荷花分为挂板水荷花、大打水荷花和双扦子干打水荷花;亮子分快、慢、烘、提。不论是文场武场,一律“借母怀胎”, 自然韵律的转换运用在不同的地方,使锣鼓更具活力,有效地同舞台上的不同剧目和人物结合起来。第四,“泸州河”的打击乐要求大锣要打出七个半韵(半音),突出高昂、豪迈之气概,以更有效地烘托出剧情环境。
(三)“泸州河”刻画、塑造人物形神交融
在调动表演程式套子来塑造人物形象问题上,“泸州河”不生搬硬套,强调在使用功夫时要“用功不见功、耍龙不现爪”,演员不能离开剧情需要和人物性格来卖弄技巧。
自志科班出身的花脸邱文成(志愚)在演出《东窗修本》时,把秦桧那种心狠手辣、陷害忠良的奸诈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他稳健的身段技巧、出色的表演,凸显他在运用程式套子上的独到之处,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奸相的典型形象。又如著名生角杨松林在《单刀会》中饰演关羽时,特别重视表现关羽的气质、形体的威严、眼睛的神韵。在演到关羽下船时,他以稳健的身段来表现关羽高深的功夫和大将风度,在演到关羽刚上岸时运用猛一侧身的身法,既在观众视觉中产生了双影的视觉效果,又表现了关羽“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理活动。光绪年间的花脸刘猪儿虫在演出《把宫搜诏》饰曹操时,则重在气度上下功夫,一出场就要求鼓师以重槌铿锵的“慢亮子”来烘托气氛,以显身价。此外,他对蟒袍、玉带、翎子的运用,无一不是为着刻画曹操的形象而下功夫的。自志科班出身的小生泰斗张志举在《放裴》一剧中饰裴生,他的手指弹功能使文生巾的飘带定位。在摸钗一段表演中,他以“鳌鱼旋转”之式使褶子铺盖舞台。在《水牢摸印》一戏中表演出水牢时,将褶子紧裹全身,俨然水渍淋淋,随后逐渐抖伸,全无做作痕迹。曾荣华在《铁龙山》一剧中饰铁木耳,他在剧中成功地运用了翎子功来塑造这一人物。如他在《飞邦子》中的表演中使用了翎子功,随着鼓声一阵紧似一阵,观众的情绪被悬在心口上,他头偏向左侧,左侧的翎子自然低垂下去,右侧翎却慢慢自立向上,单翎颤抖,出神地表现出铁木耳气得发抖、不可理喻的心境。他还运用了“飞椅子”的特技,表现了铁木耳怒火冲天,急于班师镇国锄奸的急切心情。
“泸州河”语言风趣幽默,就如川江号子一样,表现出泸州人不畏艰辛、豁达开朗的性格。 “变脸”“喷火”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脸谱可以不停地变化十几种,功底扎实,技艺深厚,不留痕迹。
“泸州河”锣鼓打发、唱腔旋律与其他“河道”相比,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所谓千里不同音,近山音浊,近水音清。区域不同,则声腔各异,无关河道宏旨,而是腔调的特色、剧本的安排以及表演的独特、班社的建立等方面赋予了地方剧种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自川剧“泸州河”形成以来,通过一代又一代川剧人的探索、传承、创新,这朵艺术奇葩越开越灿烂,涌现出了陈巧茹、孙勇波、刘萍、崔光莉等川剧艺术的拔尖人才,先后获得国家级戏剧大奖——梅花奖。还有余开源、阳运志、刘光树、包靖、沈敬东、刘蕊梅、文莉、雷敏、张怀玉等人,获得全国各类大奖,成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重要传承者、弘扬者。这些“泸州河”的传承者们先后被选调进四川川剧团,成为四川川剧舞台的台柱子,至今仍活跃在川剧舞台上,担起弘扬“泸州河”的使命,使“泸州河”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发扬光大。
四、结语
“泸州河”川剧艺术是外来剧种和泸州民间文化交融的集大成者。它的产生,由泸州的地理人文环境所决定,受泸州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影响。它起源于泸州,又辐射到川、滇、黔、渝大部分地区,是川剧流派中极具特色又富有代表性的河道。它的水系特征明显,流播于四川南部长江、沱江、赤水河、永宁河流域。泸州又是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在孕育过程中,地方宗教文化赋予它先天戏剧的禀性。“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使“泸州河”川剧艺术与生俱来地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泸州河”川剧艺术承中华戏曲之传统,融泸州艺术之精华,兼收并蓄,自创一格,以南北一体、五腔兼备、文野交融、雅俗共赏为文化特征,以高腔独树一帜,打击乐堪称一绝,语言表现泸州人火辣、豪放的性格,又风趣幽默。在表演风格上,其注重形神一致、情景交融,“用功不见功、耍龙不现爪”,就是形象生动的体现,其精、气、神渗透到泸州民众的诸多生活领域,具有涵盖古今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瑰丽的川剧大观园中,“泸州河”以艺术创造的独特性而占有显耀的地位,是第一个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川剧剧种。从民间剧种到官方成立剧团,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多次获得梅花奖等大奖,其演出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在新的历史时期,“泸州河”川剧艺术在一代又一代川剧人的保护、继承、改革、创新之下,将继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注释:
[1]赵永康著:《人文三泸》,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4页
[2]高承(宋)著:《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443页
[3]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江志(1986—2005)》,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673页
[4]泸州少数民族志编委会编:《泸州少数民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242页
[5]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灯节》,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57页
[6]邹锡汇撰:《泸州川剧起源、特点和艺术成就》,《四川戏剧》,1997年第4期,21页
[7]泸州百科全书编委会:《泸州百科全书》,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541页
[8]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川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16页
[9]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泸州老城》,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9,301页
[1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川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5页
[1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川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4页
[12]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川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3页
[13]泸州市文化局撰:《泸州河川剧艺术发展概述以及濒危状况和保护建议意见》,2000,7页
[14]冯树丹著:《四川戏剧轶史》,四川省戏剧家协会,1992,116页
[15]付贵著:《谈川剧高腔的飞句及犯腔》,《四川戏剧》,2015年第4期,25页
[16]泸州文化局编:《泸州市文化艺术志》,1995,220页
[17]《泸州戏曲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