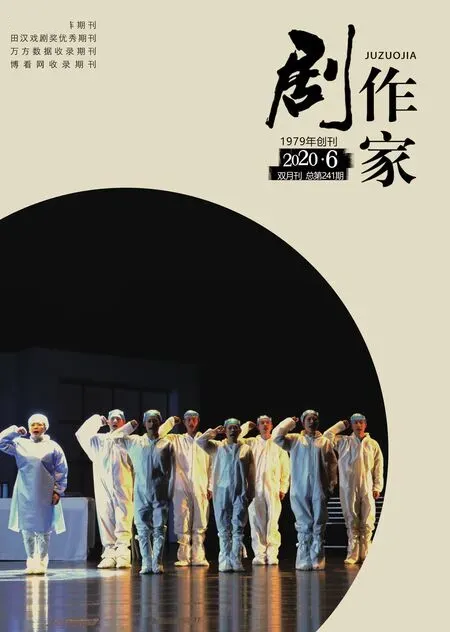现代戏剧非线性叙事时间研究
2020-03-03刘哀
■ 刘哀
近代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往的美学观念被不断颠覆,新的美学观念层出不穷。反映在戏剧领域中,新思想、新流派纷纷涌现,戏剧理论、叙事范式、表演理念、舞台技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戏剧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现代戏剧在叙事范式上与传统戏剧相比呈现出巨大差异。本文旨在探究现代戏剧非线性叙事时间的特征,总结其在舞台表演中的呈现方式。
一、线性时间观与传统戏剧叙事时间
1.亚里士多德《诗学》:行动模仿当前
传统戏剧中的事件一般按线性的时间序列展开,这一特征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牛顿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时间的存在依赖运动的存在,运动的存在也依赖时间的存在[1]。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称:“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它均一地流动,且被另一个名字称之为持续、相对的、表面的和普遍的时间是持续通过运动的任何可感觉到的和外在的度量(无论精确或者不精确)……”[2]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从过去经由现在向着未来均匀地流逝。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在”和运动物体相连……我们凭运动物体认识了运动中的前和后,作为可数的前和后就是“现在”。“现在”是时间的一个环节,连接着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它又是时间的一个限:将来时间的开始,过去时间的终结。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中,“过去”“现在”“将来”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现在”[3]。这种观念无疑影响了他的戏剧叙事理论,他对“现在”的高度强调在《诗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诗学》称“模仿者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4],这便意味着悲剧是从人物当前的行动中展开的,叙事时间以现在为起点。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完整”且“具有一定长度”。“有头,有身,有尾”,也就是说戏剧情节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既然叙事从当前开始,而情节又包含过去,那么过去发生的事件便必然要通过剧中人之口从当前往前追溯。人物通过追溯,“发现”了隐藏在过去中的事实并因而形成“突转”,戏剧性得以产生。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剧情开始于忒拜事件即将结束之时,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历程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是通过牧羊人的叙述展现出来,它的叙事时间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成为了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完美典范。
2.“三一律”:整一的时间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称,“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即故事的叙述从开始到结束,时间不超过一天。这一理论并没有被古希腊戏剧家严格遵守,却在后世引起了广泛反响。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将这一理论深化,提出时间、地点、情节三要素高度集中、统一的“三一律”。
“三一律”要求故事的时间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因此剧作家需要将故事的前史体现在人物对话或独白中,借人物之口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以此构建戏剧冲突。现实世界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在漫长的过往中逐渐形成的。如果剧作家不通过剧中人的追溯而是直接从矛盾形成的源头开始叙述矛盾的起因和演变,那么戏剧的高潮便会被延宕,剧作难免会变得冗长、乏味,让观众提不起兴趣。“三一律”对时间集中、整一的要求,是为了让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甫一开场之际就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观众得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戏剧的前史并迅速进入故事的高潮阶段。另一方面,早期的戏剧舞台较为简单,舞台技术远远不足以支撑时间和场景的频繁变换。为了确保观众不至于被变换的叙事时间扰乱,分不清演员正在表演的究竟是前史还是当前,传统剧作只能尽可能地少变换叙事时间或者不变换叙事时间,在舞台上只展现当前发生的情节。因此,戏剧“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这句话便可以理解为戏剧舞台上的动作只模仿当前发生的情节,过去的情节不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展开,即只能通过人物的语言进行讲述。“三一律”对当前的强调可视为是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继承。
3.历史剧:弥散的时间
“三一律”虽然影响广泛并一度成为戏剧届的金科玉律,但其机械、刻板的限制条件严重影响了戏剧的发展。它对前史的排斥使得戏剧既无法展现矛盾形成的过程,也无法叙述复杂事件的演变,而只能讲述一个单一的事件。当剧作家需要叙述复杂事件时,他不得不打破“三一律”的限制。
英国戏剧诗人的先驱克里斯朵夫·马洛无视时间的限制,他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历史》叙述了浮士德将灵魂卖给魔鬼直至下地狱的二十四年中的一系列事件。[5]这种戏剧结构被莎士比亚所继承,他的历史剧展现出了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复杂剧情,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以《亨利五世》为例,剧作围绕1414年至1420年间的英法战争,先后讲述了战争前英王铲除内奸、哈弗娄的被围和投降、阿金库尔大战、两国缔结和约、亨利五世向法国公主求婚等一系列事件。剧情中并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而且除了战争进程的历史主线之外,莎士比亚还设计了匹斯特尔等小人物的虚构主线,两条叙事线索互相交叉、此起彼伏。[6]
历史剧打破了时间整一性原则,其叙事时间不是连贯的、绵延的,而是间隔的、弥散的、跳跃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并没有突破线性时间观。其叙事时间虽然是跳跃的,但仍然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往前发展,并没有从现在跳回过去。舞台上的人物动作仍然只模仿当前,而不模仿过去。因此不管是恪守“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戏剧还是突破了“三一律”的历史剧,传统戏剧都遵循了线性的时间叙事,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牛顿的线性时间观。
二、现代戏剧非线性叙事时间特征
戏剧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现代戏剧理论家意识到戏剧中事件的叙述序列不必遵循线性的时间安排。弗朗索瓦·若斯特指出:“为了产生叙事,不仅需要记录时程,尤其需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修饰时间,例如删略时间,采用倒叙方法,重新安排时程等等。”[7]现代戏剧摆脱了线性时间观的桎梏,其叙事时间往往呈现出跳跃、交融、多维、循环、静止等非线性特征。
1.跳跃性
在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下,传统戏剧中的叙事时间如同一条河流,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从开头流向结尾。“三一律”强调叙事时间的整一性,尽管幕与幕之间存在时间间隔,但间隔通常较为短暂,叙事时间仍可以视为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历史剧突破了“三一律”的时间整一性要求,其叙事时间是间隔的、跳跃的,但这种跳跃只向前跳不向后跳。过去的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追溯出来,而过去的动作并不出现在舞台上。因此,可以认为传统戏剧在舞台上只展现人物当前的动作。
“三一律”确保戏剧情节紧凑、矛盾冲突激烈,但它无力展现前史,在前史漫长且重要的情况下,这种缺陷变得尤为致命。史诗剧虽然适用于展现前史,但无法克服情节杂乱、散漫的弊病,结构显得臃肿,叙事时间频繁向前跳跃,难免会使得故事犹如流水账。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剧情的当前时间是推销员威利六十多岁的一天。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他不时地回想起往事,叙事时间随即跳回到遥远的过去。与“三一律”通过对话或独白展现前史不同,《推销员之死》直接将前史展现在舞台上。年轻时的儿子、年轻时的妻子、去世前的哥哥先后出现在场参与演出。叙事时间不停地从当前跳回过去,又从过去跳回当前。现实与记忆交织在一起,使得时间不再是连续的、单向的进程,而是在过去与当前之间来回跳跃的片段。[8]
2.交融性
过去发生的事件影响人物当前的所思、所想、所为,并间接地影响事件未来的走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传统戏剧中,过去影响当前,但它并不直接作用于当前,过去已经逝去,人物无法与过去的事物进行任何沟通和交流,它只是为当前的情节提供背景,即过去仅仅提供故事发生的环境以及一个存在矛盾冲突的人物关系网络。而在现代戏剧的舞台上,过去可以被外化为可见、可感、可交流的情景。记忆中的人物被表现为舞台上的视觉形象,当前人物在内心中与记忆和幻想中的人物的交流被直接呈现出来。过去直接和现在关联在一起,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变得明确可知。
在约恩·福瑟的《Rambuku》中,年老女人站在客厅里讲述她对Rambuku的憧憬。Rambuku时而指的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时而指的是记忆中的一个男人。年老女人一面喋喋不休地说今天Rambuku将会打开,她和丈夫将离开无法忍受的此处,前往那里生活,一面又承认她当年之所以看中男人,是因为他很像Rambuku。当女人回想起当年初次见到丈夫的场景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名叫Rambuku的男人出现在舞台上。往事与当前交叠在一起。女人和Rambuku对话时使用了过去时,仿佛舞台上的这一幕发生在记忆中的过去。但随后她又改用了现在时,将时间拉回到当前。这便意味着这一场景同时存在于过去和当前里,是过去和当前的融合。[9]
在过去和当前的交互中,二者相互影响。不仅过去形塑着当前,当前也在对过去的审视中重塑对过去的理解。人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件往事会有不同的看法。人会以当前的认知重新解读过去,甚至会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篡改过去。这种篡改并非有意,但却无法避免。事实层面上的过去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对过去的重新认识本身就意味着过去在心灵层面上被当前改变了。当前能够影响过去,这是传统的时间观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传统戏剧叙事中不可能发生的。
3.多维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是对于一个……行动的模仿,整个剧作应围绕一个中心故事展开。“三一律”继承这一观念,强调情节整一。历史剧突破了情节整一性的要求,叙述漫长时间跨度里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剧虽然讲述多个故事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故事单元,但其故事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上一个故事是下一个故事的起因,下一个故事是上一个故事的结果,故事与故事如同铁链一样环环相扣。传统戏剧要求戏剧中的每一部分都与剧情的主干相关,如果部分游离于主线之外,那便是冗余的部分,应该被剔除。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多线叙事手法和巴赫金的复调叙事理论影响了现代戏剧的叙事范式。复调叙事允许作品在同一主题下叙述多个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既可以相互交叉、关联,又可以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完全无关。戏剧作品由此展现出了具有多维性和平行性的叙事时间。
汤姆·斯托帕的《戏谑》中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达达主义者查拉和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关于现代艺术的争论,另一条是列宁听闻俄国爆发革命后想方设法返回俄国。小人物卡尔参与了两个故事,两条线索因他而交会,但卡尔既没有对剧情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也没有参与到其他人物对艺术和革命的争论中,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见证者。两条线索是完全独立的,各有各的时间和空间。[10]
戏剧导演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将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进行了创造性的拼贴,两部完全不相干的作品被糅合在一起,舞台上呈现出了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其叙事时间具有平行性的特征。[11]
需要注意的是,莎士比亚的部分历史剧同样有多条叙事线索,例如《亨利四世》中,亨利四世的经历是一条线,威尔士亲王及其朋友是另一条线,但两条线索互为彼此,并不独立。而在多维性叙事的现代戏剧中,各个叙事线索之间可能完全无关,剔除其中一条叙事线索并不影响对另一条叙事线索造成影响。
4.循环性
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一样,是被先民普遍接受的时间理念。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类似佛教“轮回转世”观念的循环时间观。
尼采提出的“永恒轮回说”认为,宇宙时间是无限的,而物质的组成方式是有限的,在无限的时间中有限的组成方式会重复出现,即为轮回。[12]因此,“你目前正在经历、往日曾经度过的生活,就是你将来还不得不无数次重复的生活;其中绝不会出现任何新鲜亮色,而每一种痛苦、每一种欢乐、每一个念头和叹息,以及你生命中所有无以言传的大大小小的事体,都必将在你身上重现,而且一切都以相同的顺序排列着”[13]。
“永恒轮回说”让个体直面“最大的负重”,使得人的每一个选择,哪怕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都具有沉重的意义。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个体被困在麻木和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面对这一沉重的问题。与其面对它,倒不如去逃避它。“宗教和哲学的神话……作为美丽的幻觉使人们无法看到荒诞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受习惯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进而远离荒诞。他们用一系列熟知的、构建的意义把自己包围起来;同时,他们又培养出了一种回避进一步思考的技能,从而使自己远离人类状态的阴暗面。”[14]尼采提出“永恒轮回”原本是要让人审视存在的意义,做出能够经受轮回考验的选择,但它实际上却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荒诞与虚无。
人被困在了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中,忍受着西绪福斯式的痛苦,时间便具有了一种死循环的特征。在《等待戈多》里,每天都有送信的孩子告诉等待者:“他(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可是明天晚上准来”[15]。时间循环往复,事件的起点便是终点,情节如同咬住尾巴的蛇一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结构。而在《秃头歌女》中,结尾的人物对话与开场时完全相同,人们在进行了一堆毫无意义的自言自语后,仿佛兜了一个大圈回到原点。贝克特和尤内斯库用循环的时间展现生活的荒诞性。
5.静止性
赫拉克利特称:“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衡量物体运动的尺度,它无时无刻不在流逝,物体则在流逝中运动、变化。近代物理学也认为不存在不运动的物体,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传统戏剧中时间是戏剧冲突从爆发到解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事件被解决,人物的性格发生变化,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重构。现代戏剧对思想性的强调高于对戏剧性的强调,不再将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视为情节的必要属性,戏剧情节、戏剧动作可以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叙事时间仿佛停止在某一瞬间一样,不再向前追溯,也不再向后发展。
萨拉·凯恩的《4.48精神崩溃》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部作品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剧情,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角色。它展现作者精神崩溃之际的内心活动,其混乱的叙事语言如同一长串毫无逻辑的呓语,前后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在作品的叙事过程中,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人物的病情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人物与世界的关系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凌晨4点48分在医学上被认为是人的精神最为脆弱的时间,萨拉·凯恩患病期间经常在这一时刻醒来。剧作描绘的即是她醒来一瞬间的内心体验。时间似乎停留在了这一刻,丧失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分别。静止的叙事时间传达出作者在一个瞬间里对生命的无穷思索和感受。[16]
三、非线性叙事时间的舞台表现方式
近代以前戏剧舞台技术较为贫乏,如果频繁地变换叙事的时间和地点,观众必然会摸不到头脑,难以辨明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看不懂演员正在表演的事件究竟发生在过去还是发生在当前。在小说中作家可以明确地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很早便得到应用。但戏剧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戏剧既是文学的艺术又是舞台的艺术,当它脱离文字而存在于舞台上时,演员难以通过表演区分时态,戏剧家受此制约无法在叙事时间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革新。
现代声光电技术在舞台上的应用深刻改变了舞台的环境,舞台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因而具有了更多的容量,叙事时间的复杂化由此成为可能。
1.光线
高行健、刘会远的《绝对信号》通过灯光的变化区分当前和过去。在叙述当前事件时舞台上使用正常的灯光,在叙述过去事件及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使用光束。在叙述黑子的回忆时,“两束追光打在黑子与蜜蜂的身上……少顷追光灭。一束蓝绿色顶光投射在车体前方”。在回忆被打断时,“蓝色的光圈骤灭”。在表现蜜蜂和黑子的一段内心对话时,“车厢灯光都压灭,只有两束追光投射在二人的身上,间隔心理与现实空间”,“两人都站在白色的光圈中,互相凝视”。当内心对话结束时,“白色的光圈跟着消逝”。现代戏剧在以光束区分叙事时间时,往往也伴随着对光色的使用。如上所示,《绝对信号》以蓝色灯光代表过去时间,讲述黑子和蜜蜂记忆中的事件,营造出一种忧伤、梦幻般的舞台幻觉。而在进入小号的想象中时,“后方平投两束紫光”,体现小号的嫉妒和愤怒。[17]
2.音乐
《推销员之死》通过多种舞台技术区分当下和过去,音乐的使用是其中的一种。第一幕,威利想起已故的哥哥本时,本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同时响起了本的主题音乐。当威利和本聊起久远的往事以及他们的父母时,舞台上响起了新的音乐,高亢、活跃的调子。第二幕,威利再次想起本时,音乐声起……先是遥远的乐声,然后越来越近。当威利开口的时候,本自右方上。不仅是本,其他角色如霍华德、伯纳德等人出场或退场时,同样伴随着或欢快或刺耳的音乐。这些音乐明显不同于远处传来的长笛、房间里的收音机、广播等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制造出幻觉(过去)和现实(当下)的强烈对比,使得观众可以明显区分出叙事时间的变化。
3.空间划分
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将舞台划分为两个区域:前部略低,后部略高,形成一个大平台。全部发生在现时的情节都在舞台前部展开;过去的插曲在稍高的后部演出。作品的主要情节是雅克及其主人的闲谈。对话发生在当前,演员在舞台前部表演。当两人谈到往事的关键之处时,往事中的人物从舞台后部的平台上登场表演,雅克和主人走上平台参与到表演中。在走上平台和走下平台的过程中,过去和当前发生更替。[18]
在《推销员之死》中,阿瑟·米勒同样对舞台的区域做了划分。每当戏发生在现在时,演员都严格地按照想象中的墙线行动,只能通过左边的门进入这所房子。但是当戏发生在过去时,这些局限就都打破了,剧中人物就从屋中“透”过墙直接出入于台前表演区。
4.旁观者叙事
小说中叙事时间的变化通常由作者直接道明,读者通过文本提及的日期和时刻判断事件发生的序列,并由此还原事件原始的前后顺序。戏剧则不然,传统戏剧中的剧作者通常不会出现在文本和舞台上,他们和观众拥有完全相同的视角,他们更像是舞台上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见证者而不是操纵者。这种现象在现代戏剧中发生了改变。现代主义文学的“元叙事”不仅影响到了小说叙事,也影响到了戏剧叙事。桑顿·怀尔德在《我们的小镇》中加入了“舞台经理”这一角色,通过舞台经理之口介绍人物,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串联几个不相关的事件。这一角色俨然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作者借助“舞台经理”之口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像回放一段影片一样“命令”时间跳跃或倒转。[19]
除作者现身说法之外,现代戏剧还通过戏剧中的旁观者转换叙事时间。如《白颈鸫不再歌唱》和《枕头人》,故事通过法官、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问推动情节发展,《野兔的嘴唇》里记者对案件的调查揭开了事件的真相,审问和调查发生在当下,而其揭示的对象发生在过去,这就使得审判和调查的过程成为过去和当下的叙事时间不断变换的过程。[20~22]
旁观者叙事是对古希腊歌队的传承和发展。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往往是作者的发声器、传声筒,起着参与事件、推进事件、评论事件的作用,但他们不会改变作品的叙事时间。现代戏剧中旁观者的评论作用被削弱,作者希望观众自己去感悟戏剧作品传达出的思想而非由作者本人亲口道出,因此旁观者往往被更多地赋予了其他的功能。
5.并置
在挪威当代戏剧家约恩·福瑟的作品中,过去和当前经常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但他很少使用上述声光电技术,而是直接将二者并置。《Rambuku》的末尾,年老女人回忆起多年以前她和丈夫初次见面的场景时,名叫Rambuku的男人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一幕似乎是发生在记忆中的事件,可是女人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为你盛装打扮/你/你将带我和你一起/前往Rambuku”又表明事件发生在当前。剧作中Rambuku时而是一个地名,时而是一个人名,福瑟在结尾处的这一处理则让观众无法分清演员表演的事件究竟发生在当前还是发生在过去,作品由此呈现出了朦胧的诗意之美。
《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的第二幕,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女人坐在餐桌边自言自语,精神濒于崩溃却又在一遍遍地重复絮语中自我安慰。于此同时,男人和二十多岁的女孩坐在餐桌边用餐,享用女人准备好的食物和美酒。从表面上看,女人独自处在一个时空中,男人和女孩处于另一个时空,二者互相看不见对方。而实际上,女人的自言自语“快回到你的女孩身边”这一细节,正暗示了女孩其实就是当年的女人。男人和女孩用餐的情节既发生在当前(男人出轨了,和年轻的女孩有了外遇)也发生在过去(多年以前女人也曾这样和男人约会)。[23]
福瑟不用任何技术手段区别当前和过去,使得二者没有明确的边界。两个时空发生的事件被强行并置在同一时空下,作品变得难以解读。正是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引发观众去思考和深究。
现代戏剧在叙事时间上的突破和转变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结构,以跳跃、交融、多维、循环、静止等特征的非线性叙事时间使得戏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此同时,现代声光电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戏剧舞台上,通过光线、音乐、空间划分、旁观者叙事、并置等手段,观众得以直观地辨别出频繁更替的叙事时间,重新梳理故事原本的发生次序,复杂多变的叙事时间的舞台表现由此成为可能,舞台的容量和表现力得到极大扩展。
注释:
[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赵振江译,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杨河:《时间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罗念生译, 亚理斯多德:《诗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5]孙惠柱:《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6]朱生豪译,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7]刘云舟:《弗朗索瓦·若斯特谈当代电影叙事学和电影符号学》,《当代电影》,1989年第3期,19~26页
[8]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9]Jon Fosse. Plays: Six[M]. London:Oberon Books, 2014
[10]杨晋等译, 汤姆·斯托帕:《戏谑:汤姆·斯托帕戏剧选》,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5
[11]叶书林:《是否应该删除一切?看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上海戏剧》,2018年第2期,66~67页
[12]孙周兴:《永恒在瞬间中存在——论尼采永恒轮回学说的实存论意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5(05),1~9页
[13]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4]理查德·坎伯:《加缪》,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71页
[15]施咸荣译,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6]胡开奇译, 萨拉·凯恩:《萨拉·凯恩戏剧集》,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7]高行健, 刘会远:《绝对信号》,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18]郭宏安译, 米兰·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9]但汉松译, 桑顿·怀尔德:《我们的小镇》,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20]马政红译, 法比奥·鲁本诺·奥尔荟拉:《野兔的嘴唇》,《戏剧的毒药: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现代戏剧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1]马政红译, 古斯塔夫·麦撒·威瓦:《白颈鸫不再歌唱》,《戏剧的毒药: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现代戏剧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2]胡开奇译, 马丁·麦克多纳:《枕头人》,《枕头人:英国当代名剧集》,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23]邹鲁路译, 约恩·福瑟:《秋之梦》,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