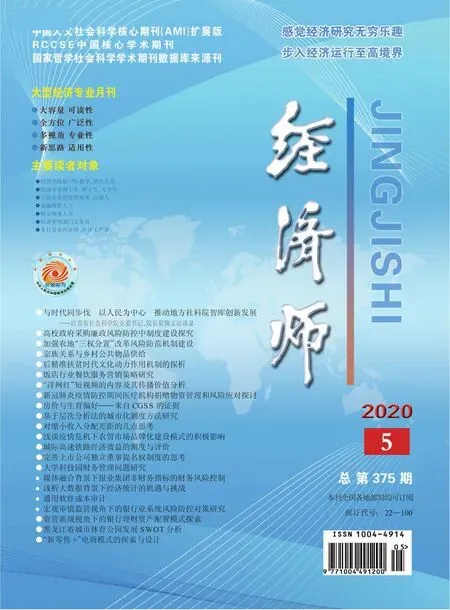后精准扶贫时代文化动力作用机制的探析
2020-03-02刘士寻
●刘士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时代高度,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地位,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精准扶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模式作用下,我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与地理等因素影响,我国贫困地区致贫、返贫等风险交错叠加。因此,如何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提高我国相对贫困治理能力,本质上激发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内生动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一、后精准扶贫时代的由来及特征
1.精准扶贫模式的历史登场。贫困问题历来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疮疤”,无论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都对此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之时,新生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但囿于“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状况,虽当时的扶贫工作开始尝试实施城乡差异的社会福利分配政策①,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主要实施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集体救济扶贫模式。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缓解我国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支撑,而此时的扶贫主要是解决广大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1982年中央提出专项扶贫政策,将扶贫对象的确定作为工作重点,并在西北贫困地区提出“三西”农业建设。随后,中央确定了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宣告区域扶贫的开始。1986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标志着国家专项扶贫开发的开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记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②,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了新时期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模式的新丰富、新发展。它强调“将扶贫对象瞄准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体,谁贫困就扶谁,实施精确化扶贫,做到对贫困人口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精确化配置,解决‘扶谁’‘谁扶’‘怎样扶’‘扶得怎样’等扶贫关键问题,实现扶贫模式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确保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③。简而言之,精准扶贫即要实现扶贫对象的精准把握、贫困原因的精准分析、扶贫措施的精准选择,它极大提升了中国社会对扶贫的认知水平。
2.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精准扶贫的提出,推动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和重大历史性成就。“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④。党中央提出力争到2020年历史性解决我国绝对贫困问题。从当前全国整体来看,绝大部分地区已实现了脱贫。后精准扶贫时代,是指2020年全面脱贫之后,广大农村贫困特征、贫困治理格局、精准扶贫政策等均呈现出新的特点情形下,我国相对贫困地区的长期治理进入的新时期。然而,如何在全面脱贫之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其一,由于文化与历史等因素,部分贫困户不思进取形成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依赖,并逐渐丧失了自主脱贫的能力与想法,这种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现象,极易引发隐形返贫。其二,持续跟进的具有明显科层制逻辑的扶贫政策,注重包办式扶贫,强调物质帮扶,但忽视贫困帮扶对象的精神塑造,不利于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从而影响政策施行的延续性。其三,国家政策具有强制性,往往易忽略其文化基础。而精准扶贫政策具有规章性,这与不同贫困地区的乡土伦理文化存在张力,扶贫政策能否将其伦理关怀与不同区域的乡土伦理文化实现有机融合,拓宽扶贫政策的文化空间,关乎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二、后精准扶贫时代文化动力的作用机制
1.文化动力的内涵释析。在现代社会学看来,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缘由文化的出现而得以发展。因此,文化是人类在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精神积累,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文化”一词,最早指向以农业耕作和园林艺术为主体的物质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逐渐引伸至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培育、教育等多重含义。对于文化理解,爱德华·泰勒最先提出了经典理解,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⑤。可知,文化本质上涉及到诸多领域。随后,不同学者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赫斯科维茨将文化一词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分解,指出文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中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具有特定结构,其既是动态的可变的,也是相对静止规律性的⑥。而随着社会分工以及知识的发展,文化被具体细分为物质与符号两大类,具体包含着“思想、知识(正确的、错误的或未经证实的)和处事规则;人工制造的工具;社会行动所产生的产品,并且能为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利用”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多义与丰富的,既包含着科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知识,也涵盖社会制度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既是知识观念、观念意识形态,也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力与人类社会实践生活成果的总和。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关系出发,将文化视为构筑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而从更为显现的功能出发,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可为社会发展起到导向作用,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活的灵魂’,是潜藏于社会生活深处的‘观念的表征’”⑧,并以观念、价值观和态度等主要形式展现。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作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20世纪80年代伊始,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一旦形成,便能以无形力量渗透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多种形式发挥作用,文化动力开始进入研究范畴。被称为文化力研究之父的贾春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并指出文化力应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以及传统文化等内容。胡鞍钢等强调文化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动力⑨。西方学者劳伦斯·哈里森认为“文化与价值观念是发展的灵魂。他们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便利了进一步发展所需的途径……各种价值观不是发展的仆人;他们乃是发展的源泉”⑩。而芝加哥学派对文化动力提出了解释,他们将城市研究中的场景理论应用于文化动力研究之中,被视为对传统城市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作为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之一,Terry N.Clark将场景从社区、物质结构、多元化的群体、特殊组合以及由此构成的活动、特定符合与意义、公共性、特定场景中的政治学与政策等7个层次予以剖析⑪。可以看出,“场景理论研究一定社区环境和都市设施蕴含的价值观与创造性群体等优秀人力资源的内在关联,强调了创造性群体等优秀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作用,以探讨后工业社会区域发展的文化动力”⑫。而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文化动力应是指人的思想范式、价值观、生活态度、文化认同感等在社会发展中所表征的作用与功能。
2.文化在后精准扶贫中的动力价值分析。在精准扶贫战略推动下,我国扶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精准扶贫之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实现突破。如上所述,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其一方面有可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进步文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文化。从当前情况来看,持续的扶贫攻坚助长了贫困地区某些人的懒散和放荡(大卫·休谟语),即将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脱贫攻坚,面临着人的精神、思想以及态度等消极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精准扶贫中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是着眼于此,必须发挥先进文化在后精准扶贫中的功能价值,为后精准扶贫时代提供动力。
(1)以文化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精准扶贫战略指引下的贫困治理,具有明显的至下而上的“科层治理”理性,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追求行政效率,往往以钱财物质等外援式扶贫,极易在贫困帮扶过程中催生包办式扶贫现象,而忽视扶贫对象的精神扶助。正如大卫·休谟所言:“给普通的乞丐施舍自然会受到赞扬,因为它似乎给穷困潦倒的人带来了宽慰,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做会助长懒散和放荡,我们就会认为这种施舍与其说是一种德性,不如说是一个缺点”⑬。这无形之中助推了“贫困文化”的形成,贫困人口不愿意脱贫,甚至有人认为国家结对帮扶是理所应当之事,久而久之,不思进取、散慢懒惰等精神懈怠现象便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然而,贫困文化下的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持久,可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必然倾向于永存,贫困的生活状态会在代际或周边关系中自然传递”⑭。这些精神极易剥离脱贫攻坚中贫困人口的主体性,无法激活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国家扶贫资源撤离,返贫现象便不可避免。文化得以被人创造,而又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人是文化的存在实质,文化蕴含着明显而又强烈的“以文化人”特点,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无声滋润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⑮。易言之,人能依据主观意愿进行生产,而生产生活的延续需精神世界的支持。由此可见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扶贫过程中,各级党委、驻村干部要注重“以文化人”,充分认识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其一,抓住人是教育的主体这一根本。在扶贫过程中,要通过帮助贫困户明确脱贫主体意识,用社会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脱贫的典型案例和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来对其进行引导教育,激发贫困户主动性。其二,抓住文化教育这一途径。着眼于精神需求,以文化教育为载体,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思想意识与自觉意识,为其提供价值导向与精神营养,提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匡正文化价值观。其三,抓住提升文化素质这一内容。贫困文化与穷人心态的充斥,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文化素质缺乏,继而对诸如工业革命、大数据等物质精神生活缺乏认知,长久则养成提炉晒太阳、不思进取等思想。因此,文化能赋予贫困对象必要的精神知识与技能,使其精神生活更加丰富,重拾创造美好生活之勇气。
(2)向文而化:提高人的精神力量。精准扶贫在于使贫困群体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亦即人是文化存在的实质。生活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生活是文化生成的基础,而文化则是生活的灵魂所在。唯有人拥有文化、有精神,方可实现真正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既包括住房、医疗等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包括对生活价值的追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以及道德素质的提高等,而后者均属于文化、精神层面。因此,实现美好生活必然要求文化的塑造与引领。然而,生活的实现和维系是建立在人的观念推动之上的,因为人的观念能指引人的生活。换言之,只有用思想观念指引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否则,人无法认识自我,也就无法反思自我,充分理解美好生活的真谛。文化塑造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精神力量。
文化之所以能教化、规范与凝练个体思想,在于其与个体生活有着互动关系。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中一大思想桎梏便是贫困人口的不劳而获、不思进取的思想。他们总是寄希望于赌博、施舍等违法行为使其能一夜暴富,这些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精神鸦片。因此,要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内生动力,一则必须教育他们维持生活就必须谋生以及进行有价值的活动,等靠要无法真正实行美好生活;现有的懒汉形象是一种耻辱,与社会脱节、与时代相悖。二来强调文化内化,增强脱贫信心,夯实自力更生的精神斗志,使贫困人口树立“人世间的一切美好,只有通过奋斗才能实现”的生活斗志,帮助其养成文化道德自觉,抛弃庸俗化与颓废化。再有加强宣传教化,引导广大贫困人口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本质以及魅力,凝聚思想、激发情感、规范行为、生成自信。
(3)以文赋能:筑牢贫困治理能力。中国特色减贫实践成就世界公认,近年来通过以“精准扶贫”模式有效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样扶等问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扶贫治理能力。将我国精准扶贫治理模式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框架下,可以得知脱贫攻坚的成功,有赖于贫困治理能力的保障。我们将视野回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治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的指引下,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制度、行动体系以及根本价值取向。随着2020年全面脱贫的日益临近以及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我国即将进入相对贫困的新阶段,无论是贫困对象,亦或是扶贫环境,均将体现出新特点。因此,贫困治理模式也随即发生转变,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从目前来看,地方各级政府贫困治理能力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专业化贫困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在当前某些地区的脱贫攻坚中,往往以经济物质等“保姆式”扶贫方式,但在后续扶贫中,更多地是需要一种综合性贫困治理能力,如心理帮扶能力,地方政府要针对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心理贫困问题予以有效解决。再如经济帮扶能力,简单的物质扶贫已无法保证脱贫攻坚的持续性与彻底性,因此当面对贫困户提出的专业知识诉求时,有些地方政府、扶贫干部显得手足无措。二是扶贫攻坚的精细化治理能力有待增强。过往,我国精准扶贫是在“大叙事”语境下进行,但后续贫困治理中,不仅仅需要对扶贫对象、扶贫手段的精准,也需要根据扶贫对象的需求加以细化并提供针对性方案。如贫困地区老年人需要社会持续稳定的关注于保护、适龄儿童需要稳定的社会教育资源的扶持、就业群体对技能培训的需要等。三是贫困整合治理能力亟需提升。部分贫困地区之所以出现前述福利依赖、精神懒惰等现象,在于贫困政策与地方伦理文化之间的脱轨。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的扶贫方式集中于简单地将国家政策不求理解执行,而忽视政策执行需要的文化情景,也就无法充分理解政策的精髓。另一方面,碎片化治理严重制约贫困治理能力,如何将愈发有限的扶贫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将多元主体能力有效整合,精准治理何以会失准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文化因素在制度主义学者看来,是促使组织制度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组织的转型与发展发端于文化认知,其次才是组织行为习惯的变化。组织与制度变迁在文化因素的缺席时能发生,但缺乏长久的精神动力,改革往往陷入停滞或疲软境地。因此,文化是组织与制度改革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但往往容易被人遗忘。在后精准扶贫时代,文化赋予深度脱贫治理能力。其一,文化通过价值塑造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精准扶贫虽取得历史性成就,但贫困地区官僚文化、对技术治理的排斥等仍较为普遍存在,催生大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文化通过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价值取向,精准理解、执行国家政策,匡正扶贫中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其二,文化通过重塑治理思维,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贫困治理是一个整体性行为,先进的行政文化能有效割除官本位思想、转变传统行政思维,追求贫困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能拓展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思路,将先进技术运用于贫困治理,突破简单的“输血式”扶贫模式。
三、后精准扶贫时代文化动力作用机制的效应
无论是从脱贫攻坚维度来看,还是从乡村振兴的视角窥探,文化将始终扮演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以及改善动力结构最为重要的思想动能。从脱贫攻坚、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维度来看,文化是破除精神懈怠、思想僵化的催化剂,是提升地方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发动机,是以文化重塑贫困地方思想价值,以精神文明之力重建贫困家庭自信,更是以文化叙事构筑美好生活图景的过程。因此,强调文化动力框架来推动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脱贫,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议题设置。
从理论视角来看,文化动力以实现美好生活向往为价值理念,在寻找后精准扶贫时代的新动力机制同时,也在尝试着从另一种区别于纯粹物质质量的贫困地区发展指标。贫困地区遏制返贫,既不能完全扬弃传统扶贫治理手段,因为扶贫需要经济层面的大幅度提升,也不能丢弃文化因素,因为小到原子个体,大到国家民族,均需要一种基于文化的力量精神支撑。因而,基于文化动力的贫困治理,通过制度架构与精神理念的有机融合,能实现贫困治理的思想和行动合一。
从实践维度来看,文化动力在后精准扶贫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决贫困地区亟需的精神文明、文化素质、优秀人才,引导这些地区贫困人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劳动观、消费观。二是借助于文化动力推进贫困地区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乡村发展的转型。因此,要真正走向文化驱动的脱贫攻坚时代,首先要注重加强贫困治理机制建设,提升文化认同、文化凝聚能力、文化共治能力,以贫困地区先进性的文化夯实思想引领。其次,优化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努力强化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真正使贫困人口享受文化带来的快乐与享受;要克服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碎片化,满足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对多层次、多样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提高贫困地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再次,要注重健全完善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体系。加强文化产业资金投入,将文化产业资源整合,加大宣传力度,培育文化产业实体,创制文化产业品牌。
注释:
①③莫光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2).
②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3/11-04/260965.shtml.
④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刘永富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扶贫成就与经验[EB/OL].[2019-04-26].http://www.cnfpzz.com/index.hp m=Archives&c=IndexArchives&a=index&a_id=37095
⑤[英]爱德华·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⑥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⑦霍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⑧韩美群.马克思文化概念的多维透视[J].江汉论坛,2007(3)
⑨胡鞍钢,张巍,张新.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⑩[美]劳伦斯·E·哈里森,严春松译.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0
⑪TERRY NICHOLS CLARKAND COAUTHORS,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the arts and development[M].Emerald Group[10].Publishing Limited,2014:22-23.
⑫徐晓林,赵铁,〔美〕特里·克拉克.场景理论:区域发展文化动力的探索及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2(3)
⑬[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M].周晓亮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⑭赵迎芳.当代中国文化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理论学刊,2017(5)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