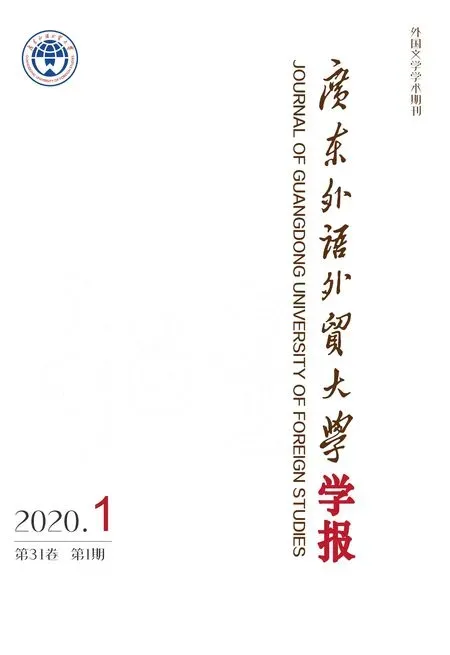朱迪斯·巴特勒的文学评论与主体解放话语批判
2020-03-02孙颖
孙 颖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最前沿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被人熟知的成就是以女性的性别身份、身体为切入点,层层推进地宣告了在后现代语境中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理论界对巴特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述行理论以及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伦理转向。巴特勒的理论以“性别”为起点,希望抵达的是对生命的深层次思考——探寻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主体、主体性如何可能,“人”如何存在。在“主体”迷宫的游走,并不仅仅意味着逻辑推演,理论总结,散落在巴特勒数部著作中的文学评论在其理论大厦中也同样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新的理论之下,文学作品被赋予新的生机;同样,借由文学作品的分析,巴特勒的“主体理论”也走向明晰。
主体的失败与希望
不论是文化角度或政治角度,知识、权力、话语、规范、可理解性框架,各种理论术语如同汹涌的潮水淹没了现代人文知识的基石——绝对自足、能动的主体。个人主体遭遇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证伪,被揭示为“镜像之我”的异化认同和“社会之我”遭遇的暴力强制;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体系中“人”成为“人的科学”的产物,“生命”则是“生命技术”压制、生产的对象。西方现代性最璀璨的成果——大写的主体——被宣判了死刑。拉康将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改写为“我非我所思,我思非我在”(I am not where I think,and I think where I am not.)。福柯(2001:506)预言“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自此,现代主体的话语幻影性成为后现代主体理论的前提与出发点。
一九八一年初版的《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作者弗莱德·R·多尔迈(Fred R Dallmayr)(1992:1)在“导论”中引用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写道:“假如这个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应该予以取代的话;假如有一种更深刻更确实的观念会使它成为无效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二○一四年出版的《后主体性》(Post-Subjectivity)论文集中,克里斯托弗·斯密德(Chirstoph Schmidt,2014:2)指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Der Mensch ist ein Versprechen der Sprache”被众多主体解构者译为“man is a slip of the tongue”,并奉德尔菲神谕作为他们解构的出发点。殊不知“德语动词‘versprechen’兼具‘slip of the tongue’、‘promise’两层意义,因此海德格尔的这句神谕应该理解为‘人永远都已经既是失败又是希望Man was always already both a failure and a promise’”。
失败意味着希望。“主体之死”的论述并非对主体的全盘否定,否定的只是那个笛卡尔所开创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完全自足、能动的主体。“主体”范畴并未被拒斥。相反,理论家们将理性主体面临的危机视为“人”的机遇,对他者凝视、话语压抑的揭示被视为“颠覆”“救赎”“解放”的曙光。在“大写的主体”轰然倒塌之后,理论家们需要做的是对“主体”做出新的理解,进行新的阐释,并在新的主体理论基础上建构新的解放话语。
站在笛卡尔式的理性自足主体、理性能动主体崩塌后留下的废墟上,朱迪斯·巴特勒将去探求关于主体、主体性更深刻的理解。她的理解,首先是对两条主体重建、解放路径的批判——本质主义路径和前话语路径。前者以本质论为基础,认为主体的内在原初本质在话语规范中遭到压抑,从而坚信解放之路必然在于重新发现、释放主体的内在原初本质。后者则认定权利话语如铁板一块,声称面对如此独白式的规范体系,颠覆、解放的微弱星光只可能出现在前话语的化外之地。两条路径都憧憬着一个“故乡”——原初的、自然的、未被话语污染过的“故乡”。巴特勒却将向我们宣布它们的失效。对这两条主体重建、解放之路的消解正是巴特勒对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两篇作品——《在法门前》①、《在流放地》②进行评论的目的之所在。“故乡”,如小说中门后的律法、流放地完美状态的行刑器具,在巴特勒看来永远回不去了。
虚构的内在原初
无论在著作或是采访中,巴特勒多次提到她对《在法门前》的评论受到了德里达的启发。因此,在进入巴特勒的思想前,我们首先对德里达的评论稍加总结。在一九八二年那篇同样以《在法门前》为题的论文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思索了门与法、守门人与乡下人之间的比喻,并通过寓言的延伸探究了文本与读者、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他的思索、探究始终围绕着一个词——延异“diffêrance”。寓言以推延开端。乡下人试图一窥法貌的请求被守门人以延期(adjournment)的形式加以拒绝。乡下人决定等待,毕竟他的请求并没有被拒绝,不过是被“推迟、延期、延缓”;而“正是在在场的推延中时间出现”(Derrida,1992:202)。推延中寓言得以继续。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通向法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但法却也始终无法得见。事实上,德里达(Derrida,1992:192-207)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在法门前》是一个关于无法得见(inaccessibility)的故事”,因为“法是在非知中被生产”,而且“通过延迟自身而生产”。
在德里达的分析中,隐而不见的法因非知、推延而得以存在;所谓的内在原初在不断地推延中被维系,从而持续在场。德里达看到了法律守护者那句“可能”产生的延异力量,而巴特勒则把目光移向了乡下人,审视他的那份期待。在这样的审视中,因为存有而期待的时间逻辑在巴特勒的理论框架下被颠倒、翻转。如果德里达揭示了内在原初的不可得见,那么巴特勒更进一步揭示出这看似先来,实为后到之内在原初的虚假人为。
无论从标题,还是全文的第一句——“在法门前,站着一个卫士”,寓言中的“法”具有不证自明、内在原初的合法性存在。乡下人来到这门前,径直“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至于“门里有法吗”“法是什么”,任何对“法”的质疑似乎都是多余而毫无必要的,因为法就在那里。然而,法就在那里吗?整个寓言故事中,“法”从始至终都隐而未宣,可它的存在却又仿佛毋庸置疑。这份不容置疑的必然存在让乡下人跋山涉水地前来求见;也正是这份必然让他甘愿为之付出一生的时间去等待。对乡下人而言,事情的发展逻辑在于“法”内在原初的存在赋予了他求见与等待的合理性,然而在巴特勒看来这样的逻辑顺序却是本末倒置,因为不是对象引发期待,恰恰相反是“期待召唤它的对象、使之成形”。“法”的真理性设定需要乡下人的期盼来加以确定。他的“请求”、他的“弯腰探身”、他的“张望”、他“还是再等一等”的决定,无不反向地建构着那个遗失的开端。期待的在场不仅替代了“法”本源性的缺失,甚至建构了关于“法”本质存在之真理性的虚构设定。没有什么先在的原初内在激发了期待,相反正是这份期待“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我们对某种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巴特勒,2009:8)
期待不仅生产了“法”的内在原初,更赋予它权威。从乡下人坐在大门前的那一刻开始,“法”就被赋予了真理性的力量。随着乡下人的那份期待在时间的流逝中日益迫切,这力量也越发壮大而膨胀。他“几乎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守门人”,“他还大声地咒骂着自己的不幸遭遇”。他请求、他送礼,他甚至指望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帮他说情。他逐渐老了,不能再大声咒骂自己的不幸,“只能独自嘟嘟囔囔几句”。“他的视力变弱了”,周围的世界变得暗了下来,“可是,就在这黑暗中,他却看到一束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的永不熄灭的光线”。
在乡下人的世界里,门里的“法”因其内在本质而光芒四射;巴特勒(2009:8)的理论逻辑却转换了角度——“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正是那个权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在颠覆中,“法”的内在本质、权威力量沦为被建构的虚幻,沦为乡下人不断期待盼望的述行效果。巴特勒的思考并不仅仅止步于解构寓言中乡下人对法之内在本质的期待、对法之权威力量的崇敬,她更试图通过分析乡下人与法之间的关系揭示本质主义主体解放路径的无效。作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开端标志的“第二性”理论(波伏娃,2011:5)——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oir)以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为理论基石所提出的基于身份政治的解放话语,遭遇了巴特勒的挑战。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轫之初即是对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论探索,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以反抗的态度试图通过话语革命,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反抗与颠覆中,对“女性主体”概念的理论追寻、以“女性身份”为基础的女性主体解放纲领的制定成为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理论家的首要任务。正如《性别麻烦》开篇巴特勒(2009:1-2)所写:“大体来说,女性主义理论假设存在有某种身份,它要从妇女这个范畴来理解,它不仅在话语里倡议女性主义的利益和目标,也构成了一个主体,为了这个主体追求政治上的再现”。换而言之,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理论倡导的女性主体解放奠基于对“女性”这一身份范畴的确立和调动,因为理论家们相信只有确立了本体,认识、解放才可能随之得以想象。
波伏娃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正是此等追求的理论表达。在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中,对性别的生理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属性的区分被视为女性摆脱从属他者地位的主体解放事业的重要理论资源。对社会性别建构性的揭示,让“生理性别先于社会性别”这一论断成为波伏娃女性理论的当然假设。不同于社会性别的话语性、文化性,生理性别原初而自然;这样的原初自然被视为女性主体真实、稳定的内在,成为性别本体身份不容置疑的基础,也成为女性解放想象的起点,因为女性主体解放话语正是对这一性别身份的表达。由此,波伏娃为女性解放描绘的美好愿景是女性改变从属地位,遵从自身意愿,淋漓尽致地在生命中实现内在独特的女性气质。
这样的理论表达似乎充盈着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气质,然而在巴特勒看来,波伏娃主体解放话语的深处却潜伏着本质主义的回响。生理性别的内在原初赋予了女性身份合法性,也同时成为女性主体性的内在原初。当波伏娃(2011:546)写下“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将女性主体的解放目标设定为让女性身份显示它的本真意义之时,我们读到了笛卡尔式近现代主体哲学对确定性的追求,看到在这样的追求中,女性被视为了实体,在生灭变幻的表象之后被赋予了某种身份本质。
尽管波伏娃否定了本质主义式“永恒的女性气质”,却并不否认“基础”“本源”此等本质主义概念,甚至试图以对内在、原初的追溯作为战场,吹响女性主体解放的号角。然而,她对构建女性身份内在原初之基础本源所做出的努力和《在法门前》中乡下人对“法”的深深渴望,在巴特勒看来却毫无二致。如同乡下人的渴望之于“法”,“对于性别,我们是不是也役于类似的期待,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巴特勒,2009:8);波伏娃所致力于回归的建基于生理性别的女性身份会不会正是一份被期待本身所生产的对象?波伏娃对女性主体解放必须要有一个内在原初普遍基础的坚定,正如乡下人对“法”的存在与权威不证自明、不容辩驳的信仰;而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性别身份,也正如同乡下人苦求一见的“法”,从未在场,却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辉。苦苦追寻那个原初、内在的本真女性身份主体的波伏娃,成为卡夫卡笔下那个在“法”门前终其一生等待的乡下人。
在巴特勒的理论审视之下,自然、内在、原初的稳定女性身份主体的主张不过是主体概念的本质主义虚构。波伏娃笔下以内在原初为名的主体基础性身份范畴,在巴特勒的理论推演中是看似先来,实为后到的神话建构,更是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识体制物化的结果,是某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产生的效果。波伏娃希望通过自然、文化,内在、外在,原初、建构的区分寻找“独特的女性气质”的身份主体,却忽视了这样的区分,正是性别话语赖以运作的生产机制;如此的二元架构正是创造自然、原初、内在诸如此类话语的生成机制。女性身份主体的合法性并不来自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本质区分,而源于性别得以成形的异性恋话语矩阵,毕竟女性这一范畴只有在异性恋矩阵中才能获得稳定性和一致性。然而,这样的稳定与一致不正是对性别关系的管控和物化(refication),“这样的物化不是正好与女性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吗?”(巴特勒,2009:7)
支离的前话语起源叙事
《在流放地》整部小说几乎都是军官的独白,作为如今岛上最熟悉这架机器的人,同时“也是老司令官这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唯一的支持人”,他迫切地讲述着这架机器的故事。文学评论家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关键词——机器、暴力、刑法、人性,巴特勒(2009:49)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看到这是“叙述一个无可挽回的过去”的故事。
随着老司令官的离世,新司令官带来的新秩序意味着机器所代表的旧秩序的失效与非法。军官试图从美好的过去证明他所追随的秩序的合法性,并寻找揭竿而起的潜在资源。面对第一次来到岛上的旅行家,军官首先要做的是让他信服,信服于这套程序,信服于旧有的秩序。
巴特勒(2009:49)认为“压抑或宰制性律法自我合理化的手段,几乎都是建立在一套故事逻辑上:述说律法建立之前情况是如何,而这个律法又如何以现在这样的必要形式出现”。因此,为了这份信服,军官竭尽全力地呈现在旧日美好日子里“完好无缺理想状态中的机器”,以讲述那关于起源的故事。然而,在他尽力向旅行家还原美好过去的时候,却发现“当叙事试图重述历史,将那个工具尊奉为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时候,叙事一再地迟滞不前”(巴特勒,2009:49)。军官神采飞扬地讲解着各个部分的名称,但“阳光热辣辣地洒在这光秃秃的谷地上,人很难把精神集中起来”。旅行家心不在焉地听着,对这机器丝毫提不起兴趣,倒是军官偶然提到的判决犯人的形式吸引了他,但这显然不是军官叙述的重点。他不得不中断关于机器的介绍,回答旅行家关于判决的问题。他抱怨现任司令官的失职,又“看出他解说机器的事有被耽误的危险”,简单扼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叙述了犯人所犯之事的始末。“他再次把旅行家按到椅子上坐下,回到机器跟前又开始讲起来……摆出一副准备做最详尽解说的架势。”但这计划中的详尽解说仍然持续被迫中断——旅行家突如其来又无关主题的发问;那一句也听不懂外语的犯人也要出来捣乱。时间的浪费,让军官不得不“只拣最重要的说”。当叙述不能流畅进行时,军官试图借助实际操作,不过“要不是那个轮子‘嘎、嘎’地响,那可就十分完满了”。最终,伴随着机器的轰隆声,他的演示以对着旅行家耳朵的大声嚷嚷结束。当叙述、演示都无力呈现那个起源之时,军官祭出了珍贵的老司令官的图样。“旅行家本想说几句赞许的话,可他却看到满纸尽是像迷宫一样乱七八糟交错在一起的线条,要找出个空白点都不容易。”军官看来“写得很清楚”“写得非常高明”的图样,旅行家却“读不了”。如此这般,一再停滞不前的讲述零乱而破碎,无论是流连于部分零件、细节操作的演示,或者军官眼中清楚、高明的图样,都无法呈现那“完好无缺理想状态中的机器”。一次次叙事的失败让巴特勒(2009:49)断言:“那个器具本身是不能完整地被想象的,各个零件不能凑成一个可以想象的整体”。
无法“以一种单数的、权威的陈述来叙述一个无可挽回的过去,以使律法的创制看起来像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巴特勒,2009:49)之时,军官只能陷入他那乡愁般的追忆,试图在那追忆中找到摧毁现有秩序的期许。过去的日子总是美好的。机器被维护在最佳状态,一笔专用的款子,一个堆满零配件的仓库;处决场面气魄恢宏,“行刑前一天,整个山坳里人挤得满满的,都是来看热闹的;一大早,司令官和他的女士们就到啦;军号声响彻营地”。
在这力图推翻现有秩序、重建旧秩序的军官身上,巴特勒看到了前话语主体解放路径的策略。前话语解放路径的理论家们,如同流放地的军官一样,试图“从前法律的过去找到一个乌托邦未来的蛛丝马迹,一个颠覆或是揭竿而起的潜在资源”(巴特勒,2009:49)。在这样的解放叙事中,理论家们将主体解放的可能性放在了“话语之外、之前”,仿佛“之外”“之前”为解放叙事提供了天然的合法性、正当性。
在巴特勒看来,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主体解放叙事正是动员了前话语的策略。在《系统与说话主体》(TheSystemandtheSpeakingSubject,1986)一书中,克里斯蒂娃从符号学的角度宣布了主体的死亡。如同神话、仪式、规范、习俗,主体同样被架构于各种意识形态背后运作的符号系统与意指法则之中。死亡只是新生的序曲。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娃为这个只能依循其所置身其中的话语规则发声的主体描绘了以符号态(the semiotic)、母性空间、内驱力为关键词的解放之路。
克里斯蒂娃将母性划归为一种前文化的真实。母性身体,作为起源的意义,代表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先于意指本身,是“一个滋养孕育未定型的语言之前的‘母性空间’”(刘纪惠,2003:XI)。象征秩序正是通过对母性的拒绝、排斥、压抑而建立。如此被拒绝、排斥、压抑的对象,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借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被构建为符号态——一个为象征秩序所压抑,而由原初的、代表浑然一体的母性身体所承载展现的语言维度。在这个语言维度里,克里斯蒂娃宣称,母性成为与象征秩序截然不同的语言意义领域——“它‘先于’意义,或者出现于意义‘之后’”(刘纪惠,2003:XXII)。在这个语言维度里,象征秩序所压抑的原初内驱力——母性内驱力迂回显示,而母性内驱力正是“‘某种非象征秩序、非父系因果关系’的展现”(巴特勒,2009:118)。
在克里斯蒂娃将符号态建构为文化颠覆、推翻压抑场域的理论推演中,巴特勒看到了和《在流放地》中军官同样的渴望。一如军官竭力拼凑那“完好无缺理想状态中的机器”的美好旧日时光,克里斯蒂娃试图构建一个以原初的母性空间、前话语的符号态为关键词的故土。军官对往日的追溯源于对揭竿而起合法性的追索,克里斯蒂娃同样将原初、前话语视为对象征秩序发动颠覆、获得解放的源动力。两者都怀着一份乡愁竭力描绘一片净土,从前话语的化外之地寻找反抗的可能性,但所谓的“化外之地”是否真的外在于压抑它的文化规范?抑或“这颠覆性的行动究竟是开启了一个意义的领域,还是,它在某种依据自然和‘前父系’因果原则运作的生物返古主义(biological archaism)的展现?”(巴特勒,2009:119)
军官面对起源叙事的无力源于权力的弥漫使之无法作为一个封闭体系的整体而存在,所谓起源叙事依赖的正是其奋力瓦解的现行律法。巴特勒(2009:107)对克里斯蒂娃所代表的解放路径的质疑也正在于“她的理论似乎依赖父系律法的稳定及其再生产,而父系律法却正是她所努力寻求置换的”。
在克里斯蒂娃的主体解放理论中,具有先于语言的本体身份、异质性的母性内驱力构成了文化颠覆的场域,即前话语的力比多经济。然而,这一话语、前话语间压制与反压制的对立关系在巴特勒的分析中不仅被消解,甚至被逆转为相互依赖的同存共在。一方面,尽管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理论有效地暴露了父法的局限性,但符号态相对于象征界屈从地位的人为设置意味着符号态的理论推演假定了象征界所代表的等级秩序的无可怀疑。当以符号态为推动反抗与断裂可能性的理论设置不过是为象征界重申其霸权提供的又一例证之时,对前话语反抗起源的追溯产生了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另一方面,符号态所对抗的父法,恰是其合法性的来源。首先,任何前话语的理论预设实质上都是当下历史权力话语的产物,对母性内驱力的前话语建构忽视了母性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建构效果的事实。其次,虽然被象征秩序所压抑、由前话语母性身体所承载展现的符号态被设想为通过诗性语言得以重返与恢复,然而,作为母性重返的诗性语言,由于母性身体意指同一身份的丧失,而处于精神错乱的临界点。为了让这样的语言得以在象征秩序中展现,克里斯蒂娃(1975:240)认为,“说话者只有借由称之为‘艺术’的这个特殊的、话语的实践,才能达到这个边界”。面对这样的理论表述,巴特勒(2009:114)指出克里斯蒂娃的“战略任务不是以符号态取代象征秩序,也不是将符号态建立为一个可与之抗衡的文化可能性”,而是在等待,等待象征秩序给予在象征秩序和符号态的分界地带的那些经验得以展现的合法性。换而言之,被克里斯蒂娃寄予解放、颠覆厚望的母性、诗性语言只能通过父系律法得到合法性,只能通过父系律法方能得以重现。如此在外围等待,等待被表达、被理解、被确认的姿态意味着对律法、权力的屈从。这样的屈从又恰恰合法化了象征秩序的权力,重申了父系律法的霸权地位。
结语
内在原初在场的虚构,让乡下人到生命终结之际也不明白“为什么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前话语叙事的不可达成,让军官只能在追忆中感慨“要让别人相信那个年月的事是办不到的”,并最终为了“要公正”祭献自己的生命。面对本质主义主体解放路径、前话语起源叙事的主体解放路径,巴特勒(2009:124)认为,“如果颠覆是可能的,那么它将是从这个律法的框架内部,通过这律法在自相抵触而产生了它自身未预期的变化时所出现的可能性而形成的一种颠覆,这样文化建构的身体才能得到解放:不是回归到它的一个‘自然的’过去,也不是回归到它的原初快感,而是面向一个有着各种文化可能性的开放未来”。这一未来的可能首先建立于对二元对立思想秩序的舍弃。正是二元对立的思想秩序设置了文化与自然、建构与真实、社会与本原相对立的二元框架,并将主体回归之可能的立足点放置其中进行论述。奠基于如此思想惯性之下的是关于“律法”“话语”的单数概念。换言之,在本质主义解放路径、前话语解放路径理论家的论述体系中,“律法”“话语”被理解为静止、恒定,是一种凝固的权力表现形式。这样的价值判断正落入了话语自我自然化、霸权化的圈套,让旨在反抗的理论演绎反而为权力话语找到一个形而上学的场域、起因。在对主体、主体性希望何在的理论探索中,巴特勒正是以对人为虚构的内在原初、支离破碎的前话语起源叙事的拒绝,更以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拒绝为起点,探索在权力话语内部开启主体之未来的可能。
注释:
①②本文《在法门前》的引文全部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一二年出版《审判·城堡》(译者:韩瑞祥),《在流放地》的引文全部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二○一八年出版《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译者:张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