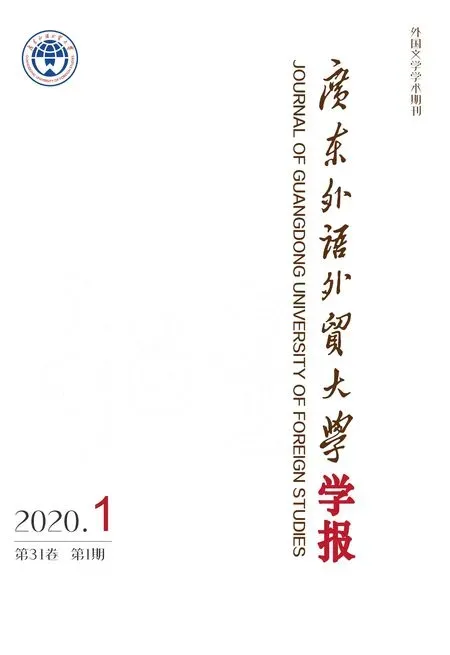责任的缺失:奥尼尔戏剧家庭伦理叙事解析
2020-03-02王占斌
王占斌
引言
亚里士多德(2014)认为,家庭生活是依靠严格的伦理关系维系的,家庭伦理关系主要是由夫妻关系、父(母)子关系构成,其中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所有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伦理关系的延伸。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是由血缘维系的,是发自天性的本能,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宋希仁,2010:370)。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一旦发生扭曲,家庭将不会幸福。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美国社会家庭的变异,通过剧本表现了他对美国家庭伦理缺失的担忧。
奥尼尔笔下的家庭雾霾沉沉、危机重重,家庭成员悲观绝望、苟延残喘。王占斌(2018:84-105)认为,奥尼尔剧中的家庭缺乏家庭应有的温情、爱情和亲情,经常是夫妻情断、父子陌路、兄弟反目、相互迫害,令人不寒而栗。奥尼尔剧本表现的是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疏离与异化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再现了家庭小社会的“道德矛盾和冲突”(聂珍钊,2007:5)。本文基于伦理学批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挖掘奥尼尔戏剧中家庭面临的伦理道德危机及其渊源,追索奥尼尔的家庭伦理选择和伦理理想。
家境与伦理意识
作家的家庭价值观,除了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很大程度上和作家个人的经历、遭遇有关。倍倍尔(1965:2)曾经说过,要想了解一个人的伦理观,就需要“了解他的经历,尤其要对其童年和青年时代有所了解”。奥尼尔出生在一个演员家庭,从小就随父亲的剧团走南闯北,过着颠沛不定的生活。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脏乱拥挤的火车厢和三教九流寄居的下等旅馆,没有享受过家的温馨,也没有“家”的概念。奥尼尔羡慕其他孩子有一个“固定的、有规律的家”,而他却是一个“流浪的弃儿”(Richard,1991:17)。
奥尼尔的母亲埃拉·昆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对爱情和家庭有美好的憧憬,然而与演员詹姆斯·奥尼尔结合并非她曾经梦想的那种浪漫温情。她不得不放弃过去舒适安逸的生活,随剧团颠沛飘荡,昆兰厌倦这样的生活,选择了逃避和轻生。
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背井离乡移居到美国纽约,长期经受家庭生计的困扰,对贫困极度恐惧,而且养成吝啬的生活习惯。詹姆斯有表演天赋,他的演艺生涯随着不断出演《基督山伯爵》而蒸蒸日上,但事业的成功换来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房子和温暖的家,而是更多的漂泊,更严重的恐穷心态。
哥哥詹米·奥尼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有很高的文学天赋,詹米把自己对亲情的渴望投到弟弟尤金身上,对弟弟给予了父亲般的关怀和爱护。但詹米嗜酒成癖、玩世不恭,他嫉妒弟弟得到父母过多的呵护,千方百计抹黑尤金的形象,带尤金去妓院嫖娼,教会尤金酗酒等恶习。
奥尼尔生活在一个阴郁惨淡的家庭,父亲视钱如命、冷漠无情,缺少父亲的责任和热情;母亲抑郁寡欢、消极空虚、颓靡沮丧,俨然一具行尸走肉;哥哥性格分裂,充满了妒忌与仇恨。生活在这个不和谐的家庭和所遭遇的痛苦带给奥尼尔的是辛酸的回忆和心灵的创伤。奥尼尔希望自己变成“一只海鸥”或“一条鱼”(Richard,1991:17-18),这样就能找到温暖的家和归宿。死水一般的家庭促使奥尼尔毕生追寻幸福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
奥尼尔剧本的背景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家庭,家庭伦理是奥尼尔剧本中最庞大的主题,奥尼尔的四十九部剧作中约有四十部戏剧都或多或少以家庭伦理为主题。奥尼尔除了亲身体验家庭的疏离和失衡外,也目睹了二十世纪工业化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异化和家庭结构转型,他用戏剧表达了消费社会导致的家庭伦理异化,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情怀。本文选择奥尼尔不同时期创作的三个剧本进行分析,分别是:《早餐之前》(BeforeBreakfast,1916)、《榆树下的欲望》(DesireUndertheElms,1924)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Day’sJourneyintoNight,1941),希望以一斑窥全豹,从星星点点之中捕捉奥尼尔渴望建立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伦理关系,建立在以“相互关爱为基础的代际伦理关系”和以责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张生珍、金莉,2011),批判美国二十世纪初金钱诱惑下不健康的家庭道德取向,倡导家庭伦理道德的回归。
《早餐之前》:婚姻责任的缺失
《早餐之前》是奥尼尔早期的一个独幕剧,全剧自始至终只有罗兰太太在独白。罗兰太太一大早起来就喋喋不休地辱骂在旁屋睡觉的丈夫阿尔弗雷德,嘲笑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理想是不务正业,指责他“整天闲逛,写些无聊的诗歌和小说,都是些没有人买的货色”(奥尼尔,2006;217)①。罗兰太太的丈夫阿尔弗雷德·罗兰是百万富翁罗兰的独生子、哈佛大学毕业生,随着父亲的去世,他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甚至债台高筑。阿尔弗雷德没有设法去改变这个境况,他由过去的啃老变为现在的啃妻,妻子既做家庭主妇,又要赚钱养家。
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夫妻关系中,男女双方应具有“平等的人格”(罗国杰,2014:311),这是夫妻之间伦理关系赖以维持的基础。如果在夫妻伦理关系中双方享有“人格的同一化”(宋希仁,2010:370),就能达到夫妻伦理的最高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罗兰太太一家的状况就比较容易了。首先,维系家庭关系或者说使家庭关系处于稳定和平衡的杠杆就是夫妻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位置,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特别是双方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决定的。罗兰太太抱怨自己“每天去到一个闷热的房间里干活,真够丢人现眼的”,她觉得丈夫没有承担责任,让一个女人干活养家。
罗兰太太辛勤劳动,赚钱养家,她在家庭生活中自然享有话语权。而阿尔弗雷德先生整天写诗创作,也许未来某个时候能够赚到大钱维持家庭生计,但就目前来说他没有经济收入,在夫妻关系中没有平等的人格可言。罗兰和阿尔弗雷德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根基不稳定,因为家庭关系中的一方人格缺失,导致家庭关系整体失衡,家庭伦理大厦摇摇欲坠。
黑格尔(1982:177)认为,婚姻的实质是伦理关系,婚姻的内容是客观内容的爱,而不是主观抽象的爱,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双方人格的同一化。黑格尔“具有法的意义”就是强调爱情、婚姻和家庭中包含的责任和义务是用伦理关系构筑起来的。罗兰太太与丈夫的爱情、婚姻走向人格异化,因为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义务,他们的爱情婚姻不具备法的意义上的伦理爱情和婚姻,家庭必然支离破碎。
《早餐之前》整剧以罗兰太太独自抱怨进行,阿尔弗雷德一直处于隐身状态。阿尔弗雷德对罗兰太太的辱骂保持沉默,他厌倦这种生活,但又无可奈何,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任其絮叨罢了。虽然罗兰太太也一样厌倦这个不幸福的婚姻,但是她宁愿烂在死水一潭的婚姻里也不愿意离婚:“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的婚姻不美满。我知道,她们同情你……指望我跟你离婚,让她来跟你结婚吗?……你别指望我跟你离婚,你心里很明白。”
这桩婚姻已经危机四伏、千疮百孔,阿尔弗雷德夫妻只有名分,没有爱情,失去了人格同一性,丧失了作为婚姻伦理关系的基础。阿尔弗雷德的冷暴力和罗兰太太的喋喋不休,说明他们都已经忍耐到婚姻的极限。双方摆脱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目前家庭的阴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婚姻是人自由意识的体现,夫妻不仅有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离婚的自由(罗国杰,2014:311-312)。婚姻的双方建立在爱情和自由的基础上,阿尔弗雷德暗恋海伦,他们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罗兰太太应该放手,这样就不会导致丈夫割喉自尽。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弗雷德结束了生命,也是挣脱婚姻伦理危机走向自由的一条出路,只是结局显得有些凄惨。
我们同情处于婚姻“他者”的阿尔弗雷德,也理解罗兰太太的处境,但是我们都应该把罗兰太太和阿尔弗雷德置于家庭环境中,从家庭伦理关系中看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奥尼尔深刻体悟了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通过剧本进行形象表达,让我们在观剧的同时,思考家庭问题,反思家庭成员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早餐之前》是悲剧结尾,悲剧的根源是夫妻双方共同造成的。阿尔弗雷德没有家庭责任感,以创作写诗为借口,整天与所谓圈子里的文人墨客谈诗说画,不顾家庭生计。阿尔弗雷德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属于缺少伦理责任的一方。罗兰太太虽说承担起养家的义务,但是对丈夫阿尔弗雷德的事业没有丝毫的理解、关注和支持,而且对自己的丈夫没有丝毫的信任,担心丈夫与海伦和其他女性有暧昧往来。罗兰太太尽管在家庭中奉献得多一些,她仍然属于家庭伦理关系中不道德的一方,特别是婚姻走向危机时,她依然发誓要阻止阿尔弗雷德与海伦结合,导致丈夫自杀。
《榆树下的欲望》:父亲责任的缺失
《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中期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剧。农场主伊弗雷姆·凯勃特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唯上帝是从,妻子、儿子都是上帝赐予他会干活的奴隶,任他自由支配。彼得和西蒙的母亲勤勤恳恳地为田庄付出二十年,伊本的母亲在田庄任劳任怨干了十六年,她们最后积劳成疾而死,但是凯勃特对他逝去的两任前妻并无半点思念之情。他向刚娶进门的新妻爱碧指责前妻:
这么多日子我一直是孤独的。我有过一个老婆,她生了西蒙和彼得。她是个好女人,干活从不怕苦。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她在农庄干活,可根本不懂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懂我的心。我一直是孤独的。后来,她死了,打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暂时不孤独了……结果我娶了第二个老婆,她就是伊本的妈……她也不懂我的心,和她生活如入地狱,我感到更孤独。过了十六年,她死了。
凯勃特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忠实信徒,能听懂和领会上帝的意思,随时能够得到神的召唤和指引,他在这块石头遍地的土地上开垦出良田,完全是上帝指引的,包括他娶妻生子也是上帝的旨意,岂能冒犯。而他的妻子、儿子都是异教徒,他们没有思想,是上帝放在他面前的物件。当西蒙的母亲劳累之后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的时候,凯勃特认为她不可理喻。当他与新妻爱碧一起时,总觉得屋子里缺少温暖,凉气袭人,他便不自觉地去楼下的饲养场与动物去沟通和交流,他认为与家人相比,“它们懂我的话,它们懂得这个田庄,它们会给我带来安宁。”
凯勃特是个地地道道的清教徒,他信仰上帝,敬畏神灵,坚持勤俭持家,信奉艰苦创业,谨慎做人,严谨行事。那么,这样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的家庭应该是符合伦理纲常的,不应该发生妻子不忠、儿子不孝,甚至母子乱伦的可耻现象。然而,老凯勃特把清教伦理推向极端,他在家庭用残酷的清规戒律约束和管制每个人,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剥夺了前任妻子和三个儿子的权利,他们只能为他服服帖帖地干活,所得到的只是一日三餐而已。他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哪怕是产生怀疑都不行,因为这是对上帝和上帝使者凯勃特的挑战。
清教伦理珍视父子和夫妻的亲情和爱情伦理关系,强调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可以用上帝赐予他们的权力管理好妻子和儿女,这点吻合凯勃特的行为。但是清教伦理同时又强调丈夫和父亲要把这种权力当作责任,要用神赐的爱和智慧,营造一种和谐的环境,让妻和子真心爱你,并不是由于惧怕你而服从你。这就与凯勃特的家教大相径庭,他只具神赋予的权威,根本没有神赐的爱,他不是以爱感动和感染家庭成员,而是用父权压迫全家。凯勃特是个虚伪的、极端的清教徒。
家庭生活的重要方面是丈夫与妻子抚育子女,这种生活产生最为“自然的一种友爱”(亚里士多德,2014)。凯勃特的两任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他理应对他们投以全部的关爱和教育的责任,但是,对于怀有极端清教思想的凯勃特来说,儿子只是他可以任意支配的个人财产,强迫他们为自己干体力活来创造财富,让他们从早到晚给他耕种、除草、收割、养猪、喂牛、挤奶等,剥夺了他们的教育、娱乐和其他生活权力。由于常年干农活,西蒙和彼得灰头土脸、身体佝偻,老气横秋,缺乏三十多岁青年人应有的活力和朝气。凯勃特把家庭变成了人间地狱,给两任前妻和三个儿子造成了身心伤害,结果是两任妻子被活活累死,儿子未老先衰。彼得和西蒙无法忍受父亲的残酷统治奋起反抗,准备去加州淘金,再也不想为凯勃特的庄园出卖苦力。儿子离家出走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哀伤和痛苦,也没有丝毫的内疚感,更没有反思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的缺失,他觉得可惜的是少了两个强壮的劳力。
凯勃特视其妻子和儿子如奴隶。“如果父亲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儿子,这种关系就失去了任何德性而蜕变为君主制式的”(宋希仁,2010:78)。奴隶没有尊严和地位,奴隶是主人的私有工具或财产,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保留也可以随意抛弃,根本谈不上同它有道德伦理关系。凯勃特没有尽到父亲应有的责任,也不具备一个伦理父亲的资格。凯勃特父子成仇、妻离子散是必然的,父亲伦理的缺失注定祸及家庭的幸福。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家庭成员责任的缺失
剧中的主人公詹姆斯·蒂龙是美国物质主义的受害者,个人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增长,但他视钱如命,甚至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詹姆斯活在“绝对的自我”的狭隘笼子里,他的自私不会上升到理性关照下的道德情感,只会变本加厉。在妻子生产小儿子埃德蒙时出现产后病痛,詹姆斯由于吝啬钱财随便请了个江湖医生为玛丽治疗,庸医注射过量的吗啡来为她止痛,使她染上了毒瘾,毁掉了玛丽的身体和精神。詹姆斯的吝啬使玛丽的人生从此判若两人,她由婚后的孤独恶化为产后的绝望,由美丽的天使变成了烟鬼。
玛丽染上毒瘾后,詹姆斯并没有对自己的自私和守财奴行为导致的后果后悔,他仍然抱怨和责备妻子,却没有想一些有效的办法帮助妻子戒毒,任毒瘾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儿子埃德蒙对父亲的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实在忍无可忍,他指责父亲:“在您发现她吸吗啡已经上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送她去治疗呢?您才不那样做呢,那样做就得花钱啊!”
詹姆斯对自己妻子的吝啬、自私和漠不关心与西方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婚姻伦理背道而驰。那么他是否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呢?詹姆斯从小就带着詹米四处奔波,甚至小儿子埃德蒙就出生在下等旅馆里,孩子们没有固定的家,他们经历的就是日复一日的“流浪”。每当詹米和埃德蒙有点身体不舒服时,詹姆斯不会带他们去看医生,而给孩子“喂一茶匙威士忌”,使他们安静下来,不至于影响他的休息。等到埃德蒙被确诊为肺痨面临死亡的时候,詹姆斯舍不得花钱,硬要把儿子送到一家下等的慈善机构“山城疗养院”治疗,这件事情惹怒一贯温顺的埃德蒙:
可是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啊,您今天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头了吧!简直使我想要恶心了!并不是因为您待我怎么坏。他妈的,我倒不在乎!……可是您得想想,为了您儿子患痨病住院的问题,您居然现了原形,在全城人的面前显露了这样一个臭气熏天的老守财奴的面目。
詹姆斯对儿子的教育更缺乏责任感。詹米和埃德蒙都聪明过人、才华出众,两人酷爱文学艺术,但是他们一直处于痛苦和幻想之中,生活很不幸福。父亲詹姆斯并没有教育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致使詹米和埃得蒙都耽于幻想,缺乏行动。埃德蒙找不到归属,只求长醉不醒;詹米玩世不恭,酗酒作乐。他们没有赚钱生活的能力,依靠父母过日子,始终龟缩在家庭的一隅,不敢面对世界。
玛丽由于丈夫詹姆斯的自私和吝啬染上了毒瘾,詹姆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玛丽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从此一蹶不振,放弃了在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玛丽的失责首先表现在她不能面对现实,一直活在过去,借助吗啡逃避现实,用梦幻支撑生活。玛丽在家庭里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缺少归属感,她把理想的家庭王国当作现实的存在,忘不了少女时代是爸爸掌上明珠和修道院音乐老师的宠儿,她想永远陪伴在圣母身旁。一次当儿子埃德蒙用哀求的手去拉她时,处于毒后恍惚的玛丽脱口而出:“不要拖住我。那是不对的,因为我希望去当修女”,这是玛丽潜意识的流露。玛丽一直没有做好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准备,她不负责任的表现也应该受到谴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她不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妻子和母亲,她的行为和态度是违背道德伦理的。
玛丽的不负责任还表现在她总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她把尤金的夭折归于丈夫硬要她去剧团陪他,使孩子传染上天花而死;把自己的孤独归咎于丈夫没有给她营造交际的环境。儿子的夭折也有她未尽到母亲呵护孩子的责任,而交际环境是靠自己营造的,她的贵族小姐性格使她鄙视与周围普通人的交往。当女仆凯斯琳问她是否登台演过戏时,她的回答让人震惊:“你那个脑子里怎么会出来这个怪念头?我是在很有体面的家庭里长大成人的,而且在中西部最好的修道院接受过教育”,言外之意,登台演戏在她看来属于下三流的事情,丈夫等演员也是下三流的人,她自然不屑于交往。玛丽不敢面对现实,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她为自己筑起一座高高的围墙,这正是玛丽可怜又可恨的一面,善良的背后隐藏的是恶,即缺乏家庭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感。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詹米和埃德蒙在现实生活中消极沮丧,悲观厌世,整日借酒消愁,逃避责任。詹米把自己逛妓院、进酒吧等醉生梦死的不道德行为归咎于母亲的堕落。他爱护弟弟,但他嫉妒父母亲对弟弟的疼爱,故意带着弟弟学会酗酒、嫖娼,要把弟弟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魔鬼,来慰藉自己的嫉妒心灵。他甚至希望弟弟病死,这样可以独占家产。詹米不希望埃德蒙取得成功,因为埃德蒙成功更显得他窝囊,所以老是盼望弟弟失败、堕落甚至死亡。他恨自己,所以要在别人身上报复,求得心理平衡。他酒后不无廉耻地告诉埃德蒙:“一个人已经麻木不仁,所以他才不得不把他心爱的东西弄死。”
詹米缺少自由独立的人格,对母亲过于依赖,甚至表现出一股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这虽然与缺少父爱分不开,但更多的是与其软弱无能和缺少独立性有直接的关系。他与父亲争夺对母亲的爱,对父亲恶语相加,把父亲看成想象中的情敌。
埃德蒙深受哥哥詹米的影响,家庭责任感严重缺失。埃德蒙活在幻想中,总希望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上航行。跟詹米一样,埃德蒙也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小男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靠父母的支持和供养维生,缺乏“伦理生活的基础”(黑格尔,1982:176)。埃德蒙和詹米都不属于完整伦理的人,没有家庭责任感,所以在家庭陷入困难时,他们便会退避三舍、躲而远之。例如,埃德蒙在家庭危机面前,不是承担起一份责任,而是喟然长叹自己的可怜处境征得别人的同情:“我生为人,真是一个大错。要是生而为一只海鸥或是一条鱼,我会一帆风顺得多。”
詹姆斯全家四人都有善良的人性,但是他们都缺少责任感,这种自私的伦理取向最终毁掉了这个家庭,毁掉了本应该享有的幸福生活。奥尼尔告诉我们,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是在爱的基础上诞生的,是父母和子女用爱创造的,但是光有爱的基础是不够的,要把爱变为责任,每个人都是家庭中伦理的人,家庭成员需要用责任和义务维护家庭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责任和义务就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磨合剂,是建构幸福家庭必需的基石。
结语
家庭是由夫妻、子女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家庭幸福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以爱情为标志的精神生活上。从伦理学角度看,爱情是婚姻家庭的调节阀,是家庭道德调解等领域的基本道德范畴。爱情是人们认识两性之间道德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掌握夫妻之间道德关系极其重要的纽结。奥尼尔剧作中的家庭成员之间缺少牢固的爱情和亲情的维系,每个成员都活在自我的笼子里,致使家庭变成冰冷的库房,里面储藏的物体没有联系,也没有生命,只是上面贴有标签的存在而已。
奥尼尔目睹了二十世纪工业化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异化和家庭结构转型,他用戏剧形式体现了消费社会导致的家庭夫妻关系、父子等伦理关系的恶化,以及由此给家庭和家庭成员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奥尼尔以家庭为细胞透视了整个社会伦理的滑坡,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情怀,告别了美国戏剧的商业娱乐和低俗时代,奥尼尔的戏剧叙事是伦理的叙事。奥尼尔认为只有建立在责任、义务和关爱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才能建立幸福婚姻和和谐的家庭,奥尼尔一生为之奋斗,一生为之努力。
注释:
①本文例子均出自郭继德编的《奥尼尔文集》(第1-6卷),后面来自《文集》的引文不再一一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