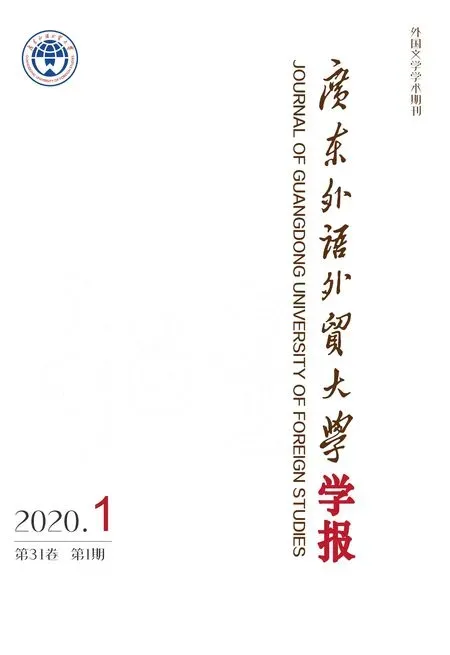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疾病解说者》中移民的身份建构
——以舌尖上的隐喻解读为视角
2020-03-02黄新辉
黄新辉
引言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满足生存需求的基本自然行为,同时又是深受文化影响并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席焕久(1994:68)指出,“饮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更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最基本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文化研究角度看,饮食的一系列过程:准备、烹饪、食用,远非其表层意义那么简单,还给读者传递出所谓“胃口的政治”(Parker,1998),隐含着意识形态的色彩。国内学者陆薇(2001)说,胃口是一种受文化约束、表达社会关系的代码,它既象征着主体(人)与客体(食物)之间的关系,又是“自我”与“世界”间的桥梁。就是说食物作为隐喻性的语言代码,具有丰富的个体性和交流性的功能。英国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98:204)曾经这样总结食物的象征属性:如果食物有一个确定的属性的话,那就是它不仅仅是食物,它是可以无限阐释的人类物化的情感。换句话说,食物与我们的属性、价值观、情感体验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是我们身份属性和情感需求的隐喻。于是饮食符号延伸出深刻的意涵,充当文化符号和社会编码,发挥复杂的社会文化沟通与情感交际功能,构建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关系体系,成为族裔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食物作为文化隐喻符号在族裔文学中广泛存在,印裔作家拉希莉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中,充分利用食物的隐喻功能,在其中的三个短篇故事中对主人公的饮食方式和食物选择反复进行描述,传达出人物的情感命运、身份认同以及作者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验。在《停电时分》中,饮食方式的变化是年轻夫妇情感婚姻归于失败、身份归属失落的象征;在《森太太》中,食物选择是全职主妇缓解乡愁压力、坚守民族文化身份的渠道;在《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食物是无名主人公接受美国生活、构建全新文化身份的载体。在这三个故事中,食物作为隐喻性的语言资源,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反映了印裔移民在异域文化中身份建构的矛盾与纠结。
饮食方式与婚姻情感、身份归属
如弗洛伊德(1918:174)所言,用餐者与某一个人一起吃喝,既可能是在确认用餐者之间属于同一个团体,又或是在履行用餐者之间的某种义务。确认团体身份或履行相互义务,意味着食物起到拉近用餐者情感的作用,用餐者利用吃喝行为进行人类情感的交流。在小说集《疾病解说者》的开篇故事《停电时分》中,拉希莉借由叙述用餐者吃喝行为的前后变化,展现年轻夫妇婚姻情感的亲近与疏离,彰显出食物对人类情感层面的重要作用,亦指向印裔移民的身份归属问题。
尽管生活在海外,年轻的妻子修芭显然受到印度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约,努力用食物维系着海外印裔家庭的幸福稳定。修芭负责照顾家庭的各类杂物,尤其热衷于保持厨房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通过对修芭购置的各类食物细致的描述,拉希莉(2005:8)再现了这对夫妇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她添购食品,总会多买几瓶橄榄油、玉米油塞进食物柜……那食物柜里堆满一盒盒各式各样的意大利粉,一袋袋拉锁封口的印度大米……无数个塑料袋中冷冻起来的羊肉”①。可以说,食物象征着妻子对婚姻情感的付出与牺牲。可惜的是,对于这一切,丈夫苏柯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夫妻关系的转折始于孩子的流产,然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丈夫长期以来的疏离、冷淡才是导致他们婚姻危机的根源。流产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后,厨房的食物储备悄然起了变化。粗心的苏柯玛似乎对此并未察觉,继续享用着修芭储存的食物,丝毫没有发现妻子不再添加食物,更不必说自己去添置了。在此处,苏柯玛贪婪地耗空妻子存储的食物显得意味深长,暗示苏柯玛在不断地耗空修芭的情感。深受流产打击的修芭处于心理情感的危急时刻,丈夫却只顾着自己的温饱,丝毫未表现出应有的关心和呵护,深处异国他乡,修芭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连月来,他们直接从灶台上分别盛饭添菜。苏柯玛端着盘子踅进书房,任饭菜变凉,然后三扒两扒胡乱塞下肚去;修芭则捧着盘子占据客厅,或边吃边看电视里的比赛,或捏着彩色笔校对文稿”。婚姻的疏离感和交流的挫折感逐渐在这对夫妇的饮食方式上明显表现出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事故成为这对夫妇修复婚姻关系的契机,他们所在街区连续五个晚上都要停电一个小时,迫使这对夫妇在黑暗中点着蜡烛一起用餐。“今晚断了电,他们非得一块儿吃不可了”。但是这回做饭的功夫落在苏柯玛身上,他竭力准备精美的晚餐。“停电的第一个晚上,苏柯玛铺上了餐布,做了丰盛的晚饭,开了一瓶红酒,点燃蜡烛。修芭见到时感到异常惊讶,赞扬了丈夫,并感谢他”。显然,苏柯玛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努力尝试去修复他们的关系。“每一顿饭都充满着爱意和关怀,每一顿饭都比之前一顿更丰盛”(Mannur,2010:158)。在细斟慢酌和饮食飘香的作用之下,他们的关系似乎有所好转,甚至边吃边袒露各自心里的秘密。拉希莉借此传达出食物对人类情感交流的作用,可以短暂缓和日渐紧张的婚姻关系。当所有的沟通渠道都归于失败的时候,唯一的媒介就只剩下食物了。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当电力恢复之后,婚姻走向破裂。第五个早上传来了“噩耗”——电力提前恢复正常。苏柯玛的绝望之情再次体现在食物上:“他有些沮丧。他原本打算做马来虾给修芭吃的,可人到了店铺却没了情绪,也提不起劲儿做晚餐”。一旦生活回到往常轨道,食物就失去了拉近他们夫妇距离的能力。透过饮食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已然失落的爱,无论这爱曾经多么美好温馨。苏柯玛“耗空了修芭那填满食物的橱柜而不往里面回添食物,这就意味着他已逐步将妻子的爱意和耐心消耗殆尽。他曾天真地以为他们的婚姻问题只是暂时的” (William,2007),并未及时修补关系,导致婚姻走向失败的结局。妻子修芭准备的食物是舒适生活和幸福婚姻的隐喻,而苏柯玛只顾埋头索取,丝毫未曾考虑回报,直到为时已晚才来匆忙补救。
作者在这个故事中花费大量的笔墨对人物的饮食态度、饮食方式进行深入描述,这些看似“琐碎”的叙述折射出人物情感关系的变化过程。烛光晚餐的火光无法照亮婚姻的前途,情感交流的失败导致婚姻的黯然收场。表面上看他们婚姻破裂是因为孩子胎死腹中和夫妻情感交流的失败,实则背后指向移民群体不得不面对的身份归属问题。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才华横溢,考入美国名校;女主人公显然也受过高等教育,既操持家务,又要打拼事业。这些移民精英来到美国,却依然面临着移民们无法逃避的身份问题。这种身份问题,不单指学历、财富、工作或绿卡,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异域文化里营建家庭,生儿育女,真正实现落地生根的过程。这个过程犹如漫长的妊娠。每一个在海外漂泊的新移民,他们就如一粒粒种子,异国他乡就是子宫,能否实现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考验,继而影响他们婚姻家庭的幸福。或许在他们内心里面,能否拥有美国出生的孩子,与是否真正成为美国公民密切相关。就故事中的夫妇而言,女主人公所怀的孩子就是他们落地生根、融入美国的象征,可惜他们未能如愿。饮食方式的选择使作者所要表达的移民身份问题有了具体的依托,隐喻出移民落地生根的艰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印度食物与母国文化身份
在《食物与归属:异国厨房里的回家感》中,印裔文化批评家柯图·卡托克(Ketu H.Katrak,1997:270)认为:“充斥着思乡情感的食物叙述常常操控着移民的记忆,使他们想象回家的感觉”。悬居海外的离散者思念家乡,将对家乡和母国的思念转移到“想象的家园”,利用所能获取的各种资源,构建自我社区文化归属感。食物作为族裔文化的具象化符号,也是较易获取的物质资源,成为离散者疗愈思乡之痛、构建“想象家园”的不二之选。
在印度传统文化习惯中,丈夫常外出打拼事业,妻子则大多待在家里,于是,留守的女人们成为海外印裔乡愁的主要承担者和演绎者。她们将对家人的爱浓缩为印度“食物”,烹饪食品既是她们传达爱意的方式,也是她们缓解乡愁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森太太》中,藉由故事中的主人公森太太,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孤悬海外的印裔女性坚守民族文化身份的艰难与幻灭,言说移民女性所经历的酸楚与彷徨。
拉希莉对森太太生活的描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食物和吃喝因素展开的。她尤其热爱切菜,切菜用的菜刀是专门从印度带来的,“一条长长的刀片,弯弯的仿佛一艘海盗船,正待驶向远方大海参加战斗似的”,在这里,菜刀是森太太加尔各答文化的重要符号。她跟白人男孩艾略特说:“只要家里有喜事……妈妈都会在傍晚放出话去。邻里所有的女人,都会带上跟这把一模一样的刀来,在我家房顶上围成一个好大的圈,说说笑笑地,一晚上要切五十公斤蔬菜呢”。然而,在美国,她只能独自切菜,因而非常想念加尔各答的家人朋友。于她而言,菜刀是她在美国保持其母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切菜活动给予了她归属感和回归的乐趣。通过切菜这一仪式,她试图重温往日的欢乐时光。
印度食物作为故事中的核心意象,是森太太自我安慰和缓解乡愁的重要手段。来到美国后,强烈的思乡情绪使她对印度式的食材鲜鱼喜爱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她告诉所看护的小男孩艾略特,超市里的鱼不能称之为鱼,无头无尾,只是一些碎片,“在加尔各答,人们早上一起床就吃鱼,晚上睡觉前还是吃鱼”,那儿的鱼“有头有尾”,才是“完整的鱼”。为了买到最新鲜的鱼,还不会开车的她甚至冒险开车去市场,结果导致车祸。她一次次地带着艾略特去海边买鲜鱼,在买鱼、做鱼和吃鱼的过程中回忆、感受和重温在加尔各答的印度生活。鲜鱼具有高度浓厚的隐喻色彩,作为加尔各答地区日常最重要的主食,鲜鱼就代表着加尔各答——她的母国、她的社区、她的家人和朋友,给予异国他乡的她亲切和慰藉。“在创建与母国文化相联系的归属感过程中,烹饪和饮食扮演着关键的作用”(Caspari,2014)。治疗她乡愁的唯一药方就是印度食物,以及相关的菜谱、菜式、餐具、佐料。当她得到这些印度食物时,她就满心欢喜;当长时间得不到时,她就孩子气般闷闷不乐。就这层意义上讲,食物就是印裔家庭主妇们离散生活的隐喻。
对于旅居海外的印裔而言,“印度性”这一观念与他们在寄居国所吃到的食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许文英(Xu Wenying,2007:167)在《食物身份:阅读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食物》中指出:“告诉我你吃的食物,我会告诉你你是怎样的人”。因此强调食物成为亚裔美国身份的重要能指之一,“食物叙述成为亚裔美国文学中经济、文化和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之一”。在美国土地上烹饪印度食品本身就有一种对抗美国文化的意味。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寄居国的文化,他们必须利用所能获取的资源,构建自我的社区文化归属感。对于喜欢印度热闹生活的森太太来说,美国生活太过安静,有时甚至安静得让人难以入睡。森太太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是许多第一代移民的共同经历,他们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印度情怀,难以适应美国的社会文化,倔强地坚守着自我传统文化身份。食物与这种母国文化身份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其独特族裔文化的图腾符号,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感性的重要内容。然而,离散者与家园之间渐行渐远,这些失去传统文化之根的异乡人就如无米之巧妇,难以长期和持久地绽放(云玲,2016:79)。母国家乡毕竟遥不可及,异国他乡却始终咫尺天涯,导致旅居美国的印裔女性对传统文化身份的坚守归于失败,最终过着痛苦、失落、无助的生活。对于森太太们而言,食物意味着跨越时空距离的沟壑,失落在夙愿难尝的大洋彼岸。文中的森太太,不顾一切坚持自己开车去市场买鲜鱼,结果导致一场交通事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场交通事故隐喻着美国文化对她实施的惩罚,似乎在警示她坚守印度文化身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食物与全新文化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2003:225)在《文化身份与离散》中提出对文化身份的看法,认为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经历不断变化,是在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博弈”中形成的。拉希莉在书写印裔移民离散的过程中不停探索人物文化身份的转变,并不断进行勇敢的尝试。与森太太们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相反,拉希莉在该小说集的尾篇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对美国文化适应性极强的印裔留学生形象,标志着拉希莉对于流散经验所持态度的微妙变化,较之前的两个故事显得积极得多。
拉希莉开始从现实的角度去审视和反思生活,着眼于现实生存和未来成长,打造了一个经历文化身份的蜕变、急于认同美国文化的印裔留学生形象。《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叙述的是“我”移居美国新大陆追求“美国梦”的过程。“食物是一种抵制美国化的重要媒介”(Ho,2005:3),尤其对于印裔流散者而言,食物更突出其标记个体身份的意义,而“我”对于食物的选择明显体现出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从先前的抵制到认同美国文化,拉希莉对笔下主人公的转变处理既受到时代文化变迁的影响,亦有着眼于现实生存的务实考量。拉希莉叙述了一个无名的主人公,获得英国学业证书之后,很快在美国找到工作并安顿下来的故事,以此展示时代的变化与印裔移民的成长。在这位无名主人公的成长转变过程中,食物再次扮演着见证者的重要角色。拉希莉对主人公的匿名处理,同样具有隐喻的色彩,“我”作为一个匿名的个体,指向更为庞大的年轻一代印度移民群体开始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拉希莉操控着食物,可以通过玛丽·沃特斯(Mary Waters)和托马斯·吉梅尼兹(Tomas Jimenez,2005)在社会学研究论文《评估移民同化:新经验、新理论挑战》中提到的“基准的同化”,让读者理解这个新移民人物。拉希莉在这个故事的第三页中就开始提及食物,以此传达“我”对美国文化的急切认同心理。刚在美国安顿下来,“我”便急于外出寻找最近的便利店,购买“我”来“美国后的第一餐”。“我”选购了牛奶和爆米片,而非“我”不太喜欢的“汉堡和热狗”;购买“我”认定的美国餐,清晰地表明“我”已然准备好接受新大陆的第一个“基准的同化”。“我”急着购买牛奶和玉米片,实则是“我”急着拥抱新文化的外显。许文英(2007:2)指出,食物是联结我们身体内部和外部,组织、表征、合法化地建构自我独特性的最重要载体。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尝试当地食物,建构这种食物所携带和表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作为一个刚踏入美国的印度人,“我”就开始效仿美国人的饮食方式,借此来拥抱全新的文化身份。而当新婚妻子考拉为“我”准备印度式的早餐时,叙述者却说,“她以为我会像大多数孟加拉丈夫一样早餐吃米饭,我告诉她麦片就行”。可见“我”潜意识里对民族食物的否定与抗拒,对以此为表征的民族文化的排斥。“我”对食物的选择似乎暗示着,在强势美国主流文化的俯视下,新一代移民主动放弃印度文化,自觉接受美国文化的同化来融入主流社会,按照 “他者”的价值观来拥抱全新文化身份。
诚然,对于移民而言,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而食物作为这个同化过程的表征符号,是移民在新大陆较易获取认同感的媒介之一。表面看来,这位新移民是在购买牛奶和玉米片,实则是“我”在尝试经历美国人真实的日常生活;“我”对食物的选择,实则是“我”对文化身份的选择。这意味着“我”开始构建符合美国文化理念的新身份。拉希莉用食物揭示了新一代留学生对于文化身份的选择,他们不再执着于印度食物,反而对美国食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流露出自我选择美国化的明显倾向,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又或者可以这样说,《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明确了移民的普遍追求,“我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第一个远离家园追求幸福的人”。正如拉希莉在访谈中所言,“毋庸讳言,对大部分的移民而言,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就是要安身立命,要获得成就,要得到承认……我认为人的一辈子会有许多的追求,其中之一就是得到承认,获得美好的生活”(Patel,1999)。他们脱离原生的生活状态,来到陌生的国度,经历着疼痛、失落,更期待着再生,这既是年轻一代移民的生存策略,也传达着拉希莉本人对生活的期待。
结论
在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中,食物作为图腾般的存在是贯穿始终的,以上三个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拉希莉在这些故事中的食物书写并未让人反感,而是成功吊起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事实上,拉希莉对于饮食习俗和吃喝行为的描述证明“食物是人物情感和身份的代理,协助他们应对主流文化” (Williams,2007:70)。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故事中,食物成为表达普通个体婚姻情感、印度民族文化情感和全新美国文化情感的载体。对苏柯玛和修芭而言,食物是他们婚姻中流金岁月的象征,苏柯玛坐吃山空,将修芭充足的食物储备消耗殆尽,表明他们婚姻关系的溃败;对森太太而言,食物是她缓解乡愁压力、寻求母国文化的隐喻;而对于无名的主人公“我”而言,食物代表着“我”对新文化身份的适应。通过三个故事中主人公行为和心理的变化,拉希莉将笔触伸向异质文化空间,书写印裔移民如何通过食物获取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再现了海外印裔移民的真实生存状态。
由此可见,食物是海外印度移民流散经验的隐喻。作为三个故事中出现最多的隐喻符号,它既穿针引线,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又寄托人物情感,反映社会时代变迁,隐喻印裔移民的命运哲思。拉希莉在不同的人物生活中来回穿梭,不光用食物审视印度传统文化,同时用食物表现印裔美国人在异国他乡的适应过程,隐喻作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种见解。漂泊离家之人常常念着过去,活在当下,盼着未来,通过食物这一承载历史意义的象征符号,他们将过去的记忆融入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当中,为他们的异乡生活获得情感的滋养和继续向前的力量,也成为他们异域文化新身份的构建基础。
注释:
①引文出自拉希莉的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以下引文不再标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