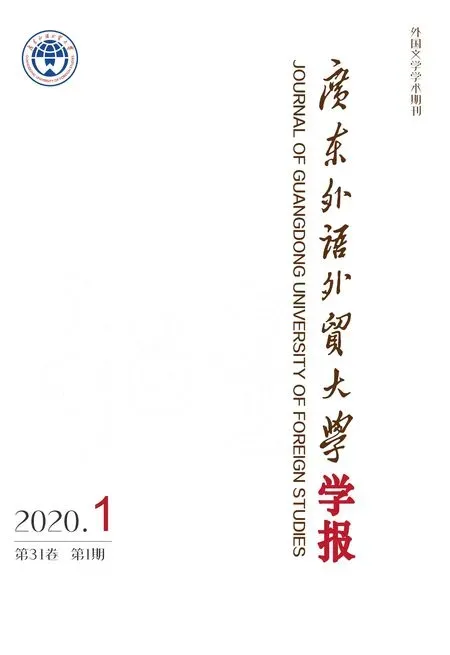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迷失在开心馆中》的后现代元空间
——一个空间批评的新视角
2020-03-02梅笑寒
梅笑寒
引言
自西方空间理论勃兴以来,“房屋”作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空间意象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房屋空间不再简单地被视为故事发生的场所和背景被一笔带过,而是得到了批评家们更深层次的考虑。其后的文化地理学派、后现代地理学派、建筑现象学派都从自己的角度不断地将“空间”这一概念逐渐展开。“空间”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摆脱了由康德发轫的“先验空间”体系,开始向“知觉空间”体系转向,这为文学作品中作者对空间意象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思作为当代美国作家,其作品的后现代特征向来为人称道。在《迷失在开心馆中》这篇小说中,巴思既延续了欧美文学传统中对于空间的重视,同时也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利用多样的手法,变换了小说中开心馆作为空间意象的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开心馆的基础上,着重刻画了主人公在这一空间场所中的活动,使小说中开心馆这一空间意象具有了独特的后现代特征。本文从小说文本入手,意图对开心馆这一空间意象进行分析,从而证明以开心馆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意象在这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试图由此开拓一种研究文学作品中空间意象的新思路。
作为观念的“开心馆”
“Funhouse”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是一种新兴的娱乐设施。最初,开心馆可以被视作室内游乐场,是各种大型娱乐玩具的集合体,游客可以在其中自由穿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机器体验。但在此之后,“Funhouse”经历了无数更迭,或在入口之后加入黑暗走廊;或在内部放置镜子形成迷宫;或在其中加入活动楼梯和滑梯,使人们在内部穿行更加艰难。从这时开始,“开心馆”脱去“Fun”这个外衣,开始让人感到惊惧与害怕。开心馆最初出现在作者元叙事式的插入语中:
开头部分应该描述安布罗斯在下午刚开始时第一眼看到开心馆起到傍晚跟玛格达和彼得一起进开心馆之间的那些事情。中间部分应该叙述从他进去时到他迷路时之间所有有关的事;中间部分具有双重的、相互冲突的作用,一面推迟高潮的到来,一面给读者思想准备,引导他去迎接高潮。接着是结尾,将讲述安布罗斯迷路之后干些什么,他最后如何找到出路,还有别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Bath,1978:55)
作者似乎在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和盘托出,但目的却是为了混淆小说中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一面讲述小说中主人公的冒险,一面提示读者为这个故事续写一个结局;一面预叙主人公进入开心馆,一面又表明到目前为止并无任何主题和线索可言。开心馆是一个庞大的漩涡,要将角色、作者与读者都困于其中。对开心馆在语词层面的优先呈现,将空间展示为观念的集合:规则与秩序受到挑战,人们在其中的感受只有“纳闷”,这是对在开心馆中可能体验到的景象的惊奇,以及对这一观念集合所表现的含混和无序的惊讶。
与之相反,此后作者对开心馆的描写却显得十分零碎,一面描写安布罗斯已经进入了开心馆,在黑暗的通道中东走西晃;一面又指出“他们还没有进入开心馆”(Bath,1978:62);转而又写开心馆中废弃的隧道和损坏了的游乐机;而后又写他们离开了欧欣城。时间在小说中完全让渡与角色在开心馆中的空间体验,读者难以在直观上为故事的发展阶段排列次序。巴思数次强调小说发展的常规序列,但又反其道而行之,使作品中开心馆的空间秩序被彻底消解。现实中的开心馆尽管力求新奇,但空间上仍旧依照相应的秩序排列。而在小说中,开心馆应有的空间序列被彻底破坏。
在小说中,有些情节是在读者的“选择”下发生的:作者虽然将这些情节都写了出来,但读者既可以选择相信,亦可以选择不信,因而这些情节以及伴随着这些情节发生的空间,都在以“或然”的形式存在。因此,作为作品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场所,开心馆的秩序被消解、意义被模糊、存在的样式被遮蔽,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对其进行“直观”。
将开心馆书写为既是观念的空间意识,又是实在的空间场所,使得空间的模糊性和二元性得到展现。观念空间与场所空间的交错,使读者不得不从一个“观赏者”变成一名“参与者”,消解了读者和故事中的空间场所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被迫进入故事中的空间场所中,并在其中活动行进。优先对观念空间的呈现将有形的空间场所存在的确定性付诸阙如,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开心馆”的空间特征
在传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空间的表现方式丰富多彩。既有人为生产空间场所,诸如房屋、住宅、商店;同样也包含于对自然空间的描写传统之中,譬如对森林、群山、湖泊等诸种空间的书写。与此同时,空间的流动性特征被纳入文学作品的考虑范畴,空间随着人的游弋而变得具有了不定性。在此基础上,都市文学也从原来对于都市的静态描写开始向动态都市的方向发展,进而表现出当代城市空间的特征。这些建筑、自然图景和都市景观历来为诸种空间理论流派所关注,取得了大量的成就。
然而这些作品在处理场所空间时大都局限于对有形空间实体的描述与人们精神之中的空间感的表现,将空间与空间精神寓于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中。巴思创造的开心馆则表现出独到的空间特征。通过对固定空间的拆解和自由组装,对镜子和光影的运用,对幻觉在空间之中的骤现,巴思在小说中打破了旧有的空间特征,从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空间场所——开心馆。
(一)空间精神的迷惑性
在对场所空间的分析中,空间的确定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场所空间意义的产生,一方面来自在空间中的人对空间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来自空间本身秩序的确定性。庞蒂(2001:350)强调“空间平面”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相适应的“景象”,以及 “景象”之中的物体对“我”的作用:“空间的各个部分都被包含在我们的身体对世界的一种唯一的把握之中”。建筑现象学派强调“人类的生活是具有二元性的运动:一种是永恒地回复到熟悉、温暖、具有庇护性的和‘家’一样的庇护所;一种是不断向外探索的活动”(沈克宁,2008:23)。舒尔茨(2010:17)则更青睐空间的可生产性和对主体的表现,将建筑空间描述为个人意识的“表达”与个人经验的“转换”,将具有生产性和表意性的空间置于空间研究的首位。小说中开心馆的空间特征表现得十分含混,这是小说含混的表达与开心馆本身复杂的空间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小说中的空间是一种 “双重编码”下的空间结构,它不仅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使人在其中不断迷失;同时又诱使人对空间本身进行探索与发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特征使巴思笔下的开心馆充满张力。
开心馆空间的迷惑性首先寓于其内部结构的不确定性以及开心馆作为观念集合的不确定性中。巴思在该篇小说中常常会用到“不知”之类的字眼,用以表达陷入开心馆中的安布罗斯的惶惑与不解。安布罗斯在面对空间中的一切事物时都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态度,而其周遭的事物也会显得模糊不清:
安布罗斯偏离了正道,走进了开心馆的某个新辟的还不知是报废的部分,那是不准备让人游玩的;它凭借着千载难逢的机会偶然走了进去……他们没法知道他的下落,因为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一部分像螺壳般围着自身盘旋,连设计师和经营者都把它忘了。它像墨丘利神节仗上那两条蛇,盘绕着那开放的部分。(Bath,1978:60)
这条“似乎是”新辟或是没人使用的小路使“他们”无法寻找安布罗斯的踪迹,引文中“track”一词兼有“小路”与“监视”之意,此处既指安布罗斯误入岔道,又指安布罗斯摆脱了“他们”的定位,因而变得无从寻觅;既描绘了开心馆的迷惑性,又将读者自身引入开心馆之中,使读者一面替安布罗斯的命运担忧,一面又要顾及自己宛若“监视者”般的身份。而后将开心馆缠绕的隧道比作“墨丘利的节杖”更是作者的得意之作。吴劳先生在译本注中言其是“医务界的标志”实为误读,墨丘利之杖的含义继承于赫尔墨斯之杖,是为“谈判”之意,而医务界使用的蛇杖则源自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这种意义的含混恰巧是开心馆本身含混性的隐喻。开心馆作为观念空间与场所空间的集合体所具有的意义上和空间结构上的双重含混使其中的空间变得十分模糊,而安布罗斯自身“位置”的丢失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模糊感。
(二)空间“探索”的内转向
单纯的模糊感无法表明开心馆作为后现代空间的独特性,以詹克思为首的后现代建筑学派总是力求探索空间意义的多元性,因此,开心馆所具有的空间的“探索”特质同样值得瞩目。空间理论流派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探索首先要摆脱遮蔽自身意义的空间,但安布罗斯的探索活动却从委身于开心馆这一空间场所开始。巴思放弃了对开心馆外部特征的描写,着重刻画安布罗斯在内部的冒险经历。在此过程中,叙述者、人物、读者对开心馆的整体空间都没有清晰的了解。开心馆并非一条“单向街”,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空间迷宫,其内部空间形式既在探索过程中被发现,也在主人公的认知过程中被逐步构造。
在安布罗斯发现一台吉卜赛预言机时,作者写道:“假如安布罗斯使用了那台吉卜赛预言机,也许会预示这个故事的高潮的来临”(Bath,1978:61)。吉卜赛人在西方文化中的先知形象根深蒂固,许多文学作品都将他们当作探索开拓的标志,而开心馆中的吉卜赛预言机却对吉卜赛人的形象进行了解构。吉卜赛人和预言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祛魅”,但巴思却说它“可能可以预示这篇小说的高潮”。巴思同时用虚拟语态模糊了这种可能,安布罗斯未必使用了这台预言机,从而使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陷入了不可知的谜团: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从知道这种对于未来命运的知晓在开心馆中是否可能。
对开心馆的探索还包含限制与变化。安布罗斯一行人刚进入开心馆时,一位老手叫他们不要向上看,而要横向移动,限制了安布罗斯等人对上部空间的探索,他们只能在面前的区域内构建空间。但开心馆的空间并不固定,而是时刻活动的,这与传统固定的室内空间形成了强烈反差:人们对活动空间的探索十分困难,甚至无法形成对有限空间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困难阻碍了主人公们对开心馆空间的探索。“布满了黑色蛛网的昏暗大厅”通过光影或是人工控制变换的空间结构进一步加深了探索的困难程度。但这样消极意义的空间变化也使安布罗斯在探索空间的过程中对开心馆的了解不断加深,他开始意识到开心馆的空间并非是完全“自足”的,而是人为的、可以精心设计或是人为的改动变化,这样的认识是在安布罗斯的空间探索过程中得到的。由此,开心馆作为实在的空间场所,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房屋空间的单向性特征,将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截然的二元对立打破,从而建立了空间精神中的模糊性与探索性之间的妥协,使其具有相当的空间张力。
(三)标志与方向的消失
空间的定位性本质是空间与知性和经验的联系。康德哲学强调空间“绝对的大”被人类活动基础上的生产性空间取代。建筑现象学派在这一维度上继承了知觉现象学的观点,凸显了空间的地标性与方向性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舒尔茨(1990:52)指出,人们想要了解空间,就必须先理解空间的定位功能,“在某个场所”成为现代空间意义“在场性”的直接来源。
小说伊始写道:“一旦从五种官能之一,譬如说从视觉得到的一个细节,和从另一种官能,譬如说从听觉得到的一个细节‘相交’,读者的想象力便会也许不知不觉地被引导到现场”(Bath,1978:53)。有意强调知觉系统内诸感官的协调作用,这表明巴思对多重知觉能力和空间感之间形成关系的看法,同时也暗示:正是由于开心馆中缺少地标与方向,使安布罗斯的知觉能力在这一空间场所中遭到遮蔽。这与杰姆逊的 “超空间”概念类似,它具有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和空间内部功能的统一性,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参照的“标志”来判定自身的距离,四处充斥的指示方向和位置的路牌本身变成了解构空间秩序性的工具:人们因为过于杂乱的指示而丧失了自身的空间感,旧有的时空坐标体系濒临崩坏。
开心馆的地标与方向感的消失首先来自空间结构的有序性的解构。传统小说中建筑空间的基础大都具有固定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在被叙述的时候往往会对各个部分的位置进行标明,而空间的意义也往往来源于这种有秩序的空间。巴思声称完美的开心馆应当是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下去,但又将欧欣城开心馆的这种单一性完全消解。传统文学作品中建筑空间存在的“必然性”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场所空间内部的“或然性”:安布罗斯也许会死在某个无人的通道中,然后在若干年后拆除开心馆时才被发现;有可能永远在开心馆中迷失;也有可能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一同找到出路。在前两种故事进程中,开心馆的内部空间应当是封闭而没有出路的;而在后一种故事进程中,开心馆拥有开放性的余地。
其次,空间标志与方向感的消解体现在对内部空间各要素之间位置关系的消解中。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几何关系作为空间知觉的基础,为人们提供对于空间的感知,但巴思没有对开心馆中各部分空间结构先后顺序的任何叙述。小说中各种空间形式:入口、一分钱游艺馆、哈哈镜走廊、黑暗长廊、活动通道、迷宫走廊、无人使用的通道,这些空间标志难以简单地以他们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主人公行进的顺序置入整体空间序列中。巴思在描写主人公的行进过程中既没有对其与空间的方位进行指示,也没有描写主人公在何种空间中穿梭,主人公在空间中的活动没有方向、没有始末。大部分空间昏暗、颠倒、没有光线,视觉丧失了功能,听觉进入到空间中。彼得的“哇哇大叫”以及开心馆中播放的“记录好的人声”(Bath,1978:66)都是在视觉感知的迷乱状态下对知觉系统的补充,或是表现在如下的叙述之中:
安布罗斯打眼角上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情,所以正是他瞥见了有个五角硬币在离滚筒式房间不远的板条路上……他第一次听到有些人在不远的一条走道上走动的声音,决定不开口叫唤他们,因为生怕人家看出他害怕,拿他开玩笑……另外有一次,如果不是心理作用的话,他听见单独一个人的声音,好像就在夹板墙另一边……他的前途,轮廓分明地叫人胆战心惊。他拼命屏住了气,想达到失去知觉的地步。(Bath,1978:64)
安布罗斯的视觉能力被限制在他的眼角之上,因而必须仰仗听觉来辨别自己与他人的位置,但即便听觉上的辨认也模糊不清。他一方面希望通过声音寻找帮助,完成对自身所处的复杂空间的认知;另一方面却只能将知觉让渡与空间场所,进一步使自身的知觉能力受到限制。在这个“滚筒式”的空间中,知觉的方向感被消解,空间的标志性受到局限,而空间的方向性由此无从谈及,知觉的杂多对空间的辨明只有负面,这与他明晰的前途形成了一对悖论。
开心馆是对空间的“方向” 与“深度”的悖离,方向的消失造成知觉对象的杂多。庞蒂(2001:356)认为“空间知觉”必须建立在“一个无偏向的主体能够从物体和物体的几何特性之间的空间关系获得的认知”。无偏向主体意味着主体必须依靠先验的知性对事物的空间位置作出判断,这必须依赖于诸物体在空间中方向上的排列考虑。而空间深度则需要让“主体离开他的位置,他观看世界的位置”。超空间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混淆人们对这一空间表象的判断,同时用更多的标志来解构人们旧有的对方向的认知。知觉现象学所倚重的对以方向为基础的空间知觉与以表象为前提的空间深度,在开心馆中受制于空间的无序性,被遮蔽或误导,由此导致知觉空间系统的解体。
(四)“镜室”对知觉空间的混淆与模糊
在开心馆的“镜室”中存在大量的镜子,这些镜子或是普通的镜子,或是哈哈镜,都时刻提醒主人公观看自己。罗兰·巴特说:“如果我坐在车窗里透过窗户眺望窗外的美景,我可以随意地或观赏景色或凝视车窗。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玻璃的存在和风景的距离;在另一瞬间,相反地,意识到玻璃的透明和风景的深度;然而下面这种交替变换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不间断的:玻璃一度对我而言在场而空洞,风景虽不真实却丰盈”(Mellencamp,1990:203)。玻璃的“在场”阻碍了主体直观,这是“透过某物看”所带来的必然矛盾,意味着知觉空间深度的消失。芒福德(2009:118)对玻璃“意义”的质疑进行了二元性的回答:玻璃及其衍生品的使用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必经之途。镜子在自我认识方面给予人们看见自己“像”的机会,推动了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这种被芒福德称之为“内省性”的冲动在人与镜子的“交流”中凸显了人们对自我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苛求,是对海德格尔(2005:157)“天、地、人、神,四方一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玻璃建筑的产生可以形成一种两可的筑造效果:一方面房屋空间是人们谋求自身意义的途径;另一方面,玻璃以“无意义之在场”的身份表明了这种空间区分绝对性的阙如。
开心馆中的镜室将传统的场所空间导向建筑空间与表象空间共存的后现代空间体式,表现了处于其中的“人”在面对自身在镜中的“像”时的自我之思。安布罗斯在尚未进入到“镜室”时,小说就开始表现出其对自身存在的质疑:
长日将尽。你以为你是你自己,可你的身子里有的是别的人呢。一个安布罗斯变得冷酷无情,另一个安布罗斯不愿这样,倒过来也一样。安布罗斯眼看他俩意见不一致;安布罗斯眼看他自己在眼看着。在开心馆的哈哈镜间里,你始终没法眼见自己一路走下去,因为无论你怎样站,你的脑袋总是挡住你的实现。即使你有玻璃潜望镜,你自己眼睛的影子也会遮蔽你真心想看的东西。(Bath,1978:61)
作者刻意用斜体表明了“长日将尽”,这既表明时间的流逝,也意味着外部世界的光线与人自身“像”的消失,因此安布罗斯只能在“镜室”这一空间中认识自己。镜室中的镜子造成了安布罗斯对自身身份认定的“或然”,因为在一个人的身体中“还有许多个你自己”存在,形成了“复身”的效果。人存在的意义在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是多元的复合。安布罗斯“看着自己正在看”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安布罗斯作为认知的主体,试图还原镜中的“像”来认识自己;另一方面,镜中“或然”存在的他也在不断含混着真实的安布罗斯的存在。巴思说“你自己眼睛的影子也会遮蔽你真心想看的东西”并非虚谈,而是因为在镜子的反射下,人的视线往往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而非现实空间中的道路。与此同时,镜中的自我也会混淆对现实世界空间的认知。这段话的最后,巴思说“你眼睛的影子会遮蔽你真心想看的东西”,这是对“镜室”空间精神的最好诠释。正是由于在空间中引入了可以制造幻象的镜子,使人们在构造自身意义的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困难。确定的意义被镜中之像所取代,意义的生产由此受到了阻碍。人们想要追寻自身的意义必须回到“自我”本身,但是镜子中对于自身表象的呈现则“遮蔽”了这种可能性,消解了现象的深度,从而使镜中的自我之像也一同变成无意义的在场。因而鲍德里亚(Baudrillard,2000:73)才会声称“幻像,或者说是幻像之镜像,是对于这种不可见的、反质的东西最好的命名。这种事物与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交互意味着,在纯粹的光晕的生产过程中所含有的物质性的灭绝”,这正是对这种充满幻像的空间生产真正纯正的“光晕”遮蔽的抵制。而这种对真正“光晕”的遮蔽在开心馆的“镜室”这一空间中则表现为对主体认知和意义生成的遮蔽。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巴思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元小说”的创作手法,通过自身以及读者对文本的介入混淆了开心馆作为空间场所的实在与单一的特征,从而使这一传统建筑空间具有极强的后现代意味。这不仅表现在对空间内部标志与方向感的消解中,也表现在人们对内部空间探索的同时引发的对于自身的怀疑与思考。
苏贾(2005:41)认为“‘meta-’在希腊语中既指‘在……之外或之后’,又指地点或性质的改变”,他提出空间意义上的“本体论三元辩证法”和空间中心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将人的存在看作是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统括,把空间性视为感觉的、构建的和居住的。这种对空间本体论意义上的重构使后现代空间具有与传统空间不一样的新范式。苏贾(2005:82)认为,空间“要同时被看作真实的和想象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实在的和隐喻的”,这应当被认为是对后现代元空间意蕴的最好解释。
巴思笔下的开心馆既是被“筑造”的空间实体,又有留待其中的游客去发掘的空间意义;既有与人们的身体密切相关的具体可感的空间场所,又有各式各样的抽象空间形式。开心馆在促使人们完成对自身认知的同时,又阻碍人们对单一主体的建构行为,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结构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对立。前文中提到开心馆是一个“或然”的空间,意味着这一空间的呈现方式和意义必然是“既此又彼”的,这种呈现方式当然会造成空间意蕴的丰富性和含混性。
因此,开心馆这一“后现代元空间”不仅是一种对空间的构造形式,同样也可以启发我们对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再一次进行思考和回眸。“后现代元空间”不应当被认为是仅仅针对某一空间实体而提出的理论概念,而应当被回溯到文学创作的历史中。诸如开心馆之类的“后现代元空间”的形成并非空中楼阁,而势必具有清晰的思想脉络与丰富的历史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