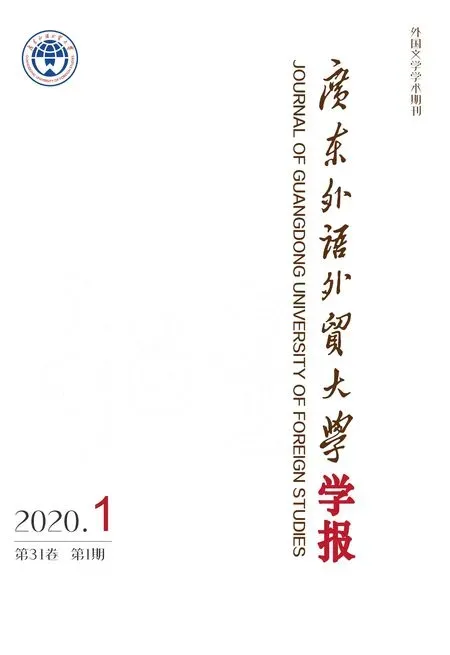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标本师的魔幻剧本》
——对大屠杀的非写实言说
2020-03-02彭绍辉麦永雄
彭绍辉 麦永雄
引言
当代加拿大著名作家扬·马特尔(Yann Martel,1963-)曾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斩获二○○二年度英国曼布克奖。他在八年后推出的另一部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2010)将创作的目光转向犹太人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旨在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非写实的风格探究人性的灰暗、创伤记忆的言说以及真实的再现问题。
这部小说匠心独运地对大屠杀进行非写实言说,以动物寓言式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故事:享有广泛知名度的作家亨利因最近的一部关于大屠杀的作品遭到了出版商否决,在沮丧和气恼之下举家搬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同时他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里面包含了福楼拜《圣朱利传奇》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份剧本手稿。在好奇心的引导下亨利找到了标本师,然而与标本师的交流过程中,他却发现这个怪异老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可怖的老纳粹分子,他的剧本的主要角色是一头驴和一只吼猴,分别叫作碧翠丝和维吉尔,喻指被纳粹压迫的犹太人,两个角色一直在讨论如何对自身遭遇进行言说的问题。小说的名字(BeatriceandVirgil)取自《神曲》,但丁在进入地狱之后,先后得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和他的梦中情人碧翠丝(Beatrice)的帮助,从地狱一路游历到天堂,见证了地狱、炼狱的恐怖以及天堂的神圣,自身也得到了升华。马特尔以维吉尔和碧翠丝给标本师的两个动物命名,意在借《神曲》来影射标本师意欲凭借两个动物作向导来洗刷自身罪孽的企图,同时也是作者特意安排以引领读者穿越地狱的向导。马特尔对于以动物充当小说角色有独到的心得,动物“对他而言具有无穷的象征潜力”(Yeung,2010)。他认为人们对于同类总是带有戒心,而对动物则不如此,因此《标本师的魔幻剧本》借助动物角色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故事,凸显关于大屠杀文学的政治寓言色彩。
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马特尔延续了他的成名作的风格,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别人的故事,并在整体上设计了两个叙事层面:第一个是以作家亨利为叙述者的层面,亨利将他个人的所见所闻呈现出来,这是小说的主要叙事层面。第二个是标本师的动物寓言剧本,属于主要叙事层面中的嵌入部分,但并非简单依附于主要层面,而是与其形成一种对照关系——标本师的剧本以隐喻的方式借犹太人大屠杀来表现人类对动物的屠杀,而从主要层面来看则是作者马特尔以剧本中的动物屠杀来表现犹太人大屠杀,两者恰好相反。马特尔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诸如元小说、互文性、隐喻、多体裁拼贴等,都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效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法则是互文性和隐喻。
互文性叙事与经典文学作品的关联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主要指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包括对其他文本的转述、化用、戏仿等等,这个文学概念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并逐渐发展壮大。从互文性叙事角度看,长篇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与众多欧美文学经典如但丁《神曲》、戈尔丁《蝇王》和奥威尔《动物庄园》等构成了互涉互阐关系。碧翠丝和维吉尔这两个名字化用了但丁《神曲》的寓意:碧翠丝一译“贝雅特丽齐”,是《神曲》中象征信仰的圣洁女性,维吉尔则是古罗马最杰出的诗人,在《神曲》中代表着理性,是引导但丁游历地狱、炼狱的向导。而在《标本师的魔幻剧本》中,他们却变成了驴和猴的形象。由此,小说与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初的著名文学文本形成了互文性关联,引发读者关于西方黑暗世纪和人文主义曙光的文化记忆。就动物寓言来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与《蝇王》和《动物庄园》遥相呼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小说还大量地与大屠杀相关的文学作品形成互文性联系。马特尔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母是加拿大的外交官,他本人既不是二战时期那场浩劫的亲历者,也不是亲历者的后裔,原本对大屠杀这一事件并不熟悉。为了创作这一作品,他阅览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的艺术作品(包括档案材料和影视资料),这在他对互文性的应用上有所体现,阅读小说时常常可以找见许多与大屠杀相关的文本或资料的踪迹。小说开头部分,作家亨利讲述自己创作大屠杀文学的种种考虑,由于不想使用大屠杀文学一贯采取的写实风格,他想写作一本“翻转书”,兼具写实和虚构两种风格。为证明这个想法的价值他引出了众多关于大屠杀的作品来给自己张目,如称斯皮格曼的漫画《鼠族》以及当代同为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小说《证之于:爱》是“另辟蹊径”的(扬·马特尔,2018:8),可作为效仿的对象,这一部分也是作品元小说特性的主要体现。尽管“翻转书”被出版商否决了,但亨利仍然坚持以非写实风格创作大屠杀文学的想法,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表现,最终写成了《标本师的魔幻剧本》(与本小说同名)。马特尔并不忌讳让读者看出这部小说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他把参考借鉴的部分作品名直接写进了小说,如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马丁·阿米斯的《时间箭》、阿尔贝·加缪的《鼠疫》、福楼拜的《圣朱利安传奇》、莱辛的《智者纳坦》、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等等,这也是其元小说特性的表现;另外还有以潜藏的方式关联着的文本,如写着字母U的六角星,使人联想到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的《这是不是个人》,“与古斯塔夫的游戏”的多个片段则有着法国导演朗兹曼的纪录片《浩劫》的影子。马特尔借鉴了众多文本尤其是与大屠杀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的内容或表现形式,以互文的形式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文本中。
法国文论家热奈特提出了文本之间的两种相互关系,一种是共生关系,意指两个或多个文本内容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直接引用就属此类;另一种是派生关系,即一个文本的内容经过转换、变化之后出现在另一文本中,从进行过变化处理的戏拟、仿作,到合并、粘贴,都属派生关系(萨莫瓦约,2002:18-23)。引用在文学作品中极普遍,很多小说家都会引用经典名篇来丰富内容或彰显自己的学识,这部小说却是引用了比较小众的《圣朱利安传奇》,因为这部描写基督教圣徒朱利安的短篇作品是作为对剧本进行辅助说明的工具而出现在标本师寄给亨利的信件中的,当然马特尔对这部作品的利用远不止直接引用这么简单。与引用相对,戏拟、仿作则不是对其他文本内容的直接吸收,而是对其进行了转换、变形等,使之与原来有所区别,同时也使吸纳的文本内容更贴合自己文本的要求;而仿作关注的更多是风格,对互文本原作者风格的模仿,可使自己文本的风格得以多样化,从而令多种风格呈现于同一文本。不论具体使用哪种方式,互文性的目的都是利用其他文本来表现自己的内容,小说的名字(BeatriceandVirgil)就是对《神曲》的戏拟化用,这两个故事有一定内在相似之处,但是但丁和标本师之间却有善恶之别。此外,标本师的剧本是典型的仿作,它模仿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对话风格,一只猴和一头驴在树林里进行着表面上漫无目的的对话,时而谈论梨子、香蕉的形状,时而思考如何形容他们所经历的恐怖,嘴上说着想离开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并不时地陷入沉默,这样的话语风格使剧本透露着一种茫然而绝望的内心情绪。就总体而言,与《圣朱利安传奇》的文本关联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互文性应用,不仅在于直接引用它的大段内容,而且在于对它的变形、化用。首先,标本师的剧本想表达的主题是爱护动物、谴责人类对动物的暴行,而《圣朱利安传奇》正体现了人类对待动物的残酷无情,是剧本主题的反面案例。标本师还将其中朱利安屠杀动物的段落都用黄色笔标出,以引起亨利的注意,希望借此引导亨利关注到剧本的主题,所以原本意在表现圣徒朱利安弃恶从善的故事被转化成体现人类屠杀动物的证据。其次,标本师以朱利安为原型,创作出剧本中那个残忍的男孩,两个年轻人都是同样的狂躁嗜杀;同时,马特尔也以朱利安为标本师的原型,这两个人物的手上都鲜血累累,不同的是朱利安是屠杀动物,标本师则是谋害犹太人。再次,小说还借鉴了《圣朱利安传奇》的故事架构,再加以改换,形成一个与之相反的架构。朱利安因屠杀动物而被下诅咒,导致后来亲手杀死了父母,于是选择自我放逐,最终因无私地为一位麻风病人(基督的化身)奉献自我而得以化解罪责、成为圣徒,然而他自我放逐只是因为杀了双亲,却不是因为屠戮了动物,为人类而牺牲自我便升天成圣,屠杀动物的罪行似乎就被一笔勾销了。标本师也想复制朱利安的成功经历,但他的行为恰与朱利安相反——朱利安以对人类的无私大爱抹去了对动物犯下的罪行,标本师则是企图借对动物的关怀来洗涤对人类犯下的罪孽。他的“老纳粹”身份的背后是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人类(尤其是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众多现实中的纳粹分子,如“死刑执行者”艾希曼,在战后也没有对自己个人的所作所为作出忏悔,而是选择了推卸、逃避。马特尔在小说中再现了这些罪犯的自私冷血行径,标本师避重就轻地借动物来掩饰罪行,寄望于一只猴和一头驴作为向导带他度过地狱和炼狱,就是在躲避他们真正需要赎罪的对象。
隐喻对大屠杀的深化表现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一般是以一个词或词组代替另一词或词组在文中出现,换而言之,隐喻涉及两个不同类别的事物,一个作为本体,另一个作为喻体,这两组词或词组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可以暗示彼此,从而起到隐藏真正含义的作用,或使文章表意更加委婉。如马特尔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并未直接说明老虎、鬣狗、斑马、猩猩四只动物是分别对应四个人,而是给出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让读者自己去寻找对应关系。过往由大屠杀亲历者和亲历者后裔写作的大屠杀文学,基本是偏向纪实性的,他们拥有切实的经历,能够表现也想要表现事实的真相,读者也希望他们展现历史的真实,而后来的既非亲历者也非亲历者后裔的作家在写作大屠杀文学时,则多是以间接的方式来指涉大屠杀,表现的是艺术的真实,“每位艺术家都选取了一个浩大的悲剧,找到其核心,然后用一种非写实的,言简意赅的形式加以表现”(扬·马特尔,2018:9),马特尔也秉持避实就虚的原则,以隐喻来间接地指涉大屠杀史实。从尝试形容梨和香蕉的外形开始,碧翠丝和维吉尔就一直在关注描述和表达的问题,他们不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到悲痛,也为如何言说自己的经历而苦恼。尝试了多种形容方式后却发现寻常的词语无法传达自己所要表现的意义,他们最终选择了隐喻的形式,将苦难的记忆融汇成了一系列隐喻词语,称之为“针线包”。“针线包”里的内容从表面看来也是混乱而无意义的,如“一声嚎叫”“一只黑猫”“网球课”“奥基茨”“诺沃利普基大街68号”(扬·马特尔,2018:147)等,让人不明就里。这正是隐喻作用的体现,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事物来说明或替代原本的事物,具有间接性的特点,需要深入了解才能明晰其中的真正含义,所谓“奥基茨”(aukitz),不是作者凭空生造的单词,而是奥斯维辛(Auschwitz)的改写形式;“诺沃利普基大街68号”也并非虚构的地方,它真实存在于华沙的犹太人区,也是主人公亨利发现真相的关键线索。马特尔使用了许多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来作为隐喻,以影射犹太人大屠杀的史实:维吉尔和碧翠丝所在的国度叫“衬衫国”,这还让亨利误以为标本师写的是儿童故事,然而此“衬衫”是“竖条纹”的,即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竖条纹囚服,暗示此地就是集中营;写有字母U的六角星则是指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的大卫之星,根据佩戴者国籍的不同写有不同的字母。标本师的剧本正是以这种方式在犹太人和两只动物之间建立联系,他并非直接道明动物像犹太人般悲惨,而是以诸多影射犹太人的隐喻穿插其间,避免了表达过于直露而让人轻易看穿他外表慈悲、实则以动物为工具的真面目。
在隐喻中,词之间或词组之间的相似性可分为物理上的相似和心理上的相似,相似的程度也有大小之分,有的隐喻一眼便可看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有的隐喻原本并不存在人们熟知的相似性,而是由它创造出来的,故而隐喻不一定局限于机械的表面相似,“对隐喻的解释很大一部分在于‘寻找’隐喻之喻底,即隐喻内潜在的理据。不管该隐喻是‘死’是‘活’,步骤都是一样:我们寻找两者共同的特征。但这一特征不在于本体与喻体的直接相似,它也可以产生于人们对两者的共同态度”(束定芳,2000:159)。貌似风牛马不相及的词语也可以组成隐喻关系,且不从已有的相似性中选择词语,而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中选择词语往往更能组合出绝妙的隐喻关系来,以猴、驴喻犹太人便是如此。以隐喻的作用和特性来看,将猴和驴作为犹太人的喻体,就说明这两组不同的生命种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人们会联想到猴子的聪明、精细,驴的坚韧、隐忍,是犹太民族也具有的特点,同时,犹太人作为本体,其性质特征也传递到了喻体身上,两者并非单向传递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隐喻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是由英国语义学先驱、修辞学家理查兹(Richards)提出的,针对传统的理论仅仅将隐喻看作词与词之间进行转移、置换的语言现象,他认为隐喻还是人类一种思维的方式,使用者在隐喻中加入了关于本体和喻体两种不同的思想,两种思想相互作用就产生了隐喻的完整意义(束定芳,2000:152-157)。根据互动理论,只看到喻体的特征传递给了本体并不够,还要看到本体的特征向喻体的转移渗入,犹太人在欧洲近千年来被当作异类、受尽压迫的历史,也是与动物相似的遭遇。由于宗教信仰有别、人种差异等原因,欧洲对犹太民族一直抱有敌意,致使犹太人在数个世纪的长久岁月里经常受到排挤和压迫,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众多犹太人迫害事件的其中一例(Hilberg,1985:5-9)。尽管受尽欺凌,犹太种族却没有在欧洲灭亡,依靠坚忍不拔的精神得以存活,与之相似的,犹太人的苦难和坚韧也见之于动物的身上,猴子作为野兽被驱赶,驴被人类用作家畜尽情驱遣,它们同样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求生。本体和喻体的涵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形成了完整的隐喻意义。
马特尔擅长使用隐喻,尤其是动物隐喻,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成功基础上,马特尔继续采用这一手法,在动物和犹太人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隐喻不是马特尔的首创,希特勒就曾用明喻的方式把犹太人比作老鼠,以凸显犹太人过街老鼠般的品性;美国犹太裔漫画家斯皮格曼借用了希特勒这一隐喻,创作了《鼠族》,讲述犹太人在迫害之下颠沛流离的逃生之路。不过作为一个原本与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作家,马特尔的这一做法招致了争议,如同库切笔下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由于用犹太人的遭遇来形容动物的悲惨命运而被攻击,马特尔也因为用驴、猴比喻犹太人而受到批评,原因在于这样的隐喻被视为是对犹太人的矮化。后殖民主义认为以动物来比喻少数族裔,实际上是把犹太人他者化了,“动物形象对于殖民者而言已经成为贬低被殖民者的强而有力的工具……这就是后殖民批评要反对类似于假设受压迫的动物与受压迫的人有着相似命运这种简单对等的缘由”(Bartosch,2013)。然而,以动物喻人在文学世界里并不罕见,远有荷马以狮子形容勇猛的阿喀琉斯,近百年来的各种现代、后现代主义流派则用这种手法反映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动物隐喻这种手法不是马特尔第一次使用,他也不仅仅对犹太人使用,《少年Pi》里无论是Pi的母亲、无辜的水手,还是吃人肉的厨师,都变成了动物,在最近的作品《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甚至把十字架上的基督描述成黑猩猩。动物隐喻的艺术手法并非专门针对犹太人使用,它已成为马特尔的一种写作特色。
审美政治蕴涵与非写实言说
在标本师的世界里,表面上他是在关心动物命运,为动物制作标本以作为它们生命的见证。不过揭开堂而皇之的表皮之后,事实却是动物都处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只是用来掩饰自己、涤清罪行的工具。维吉尔和碧翠丝对于但丁而言是向导、挚友和梦中情人,对于标本师而言却是奴隶。动物与作为“统治者”的标本师之间,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角度观之,形成了一种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的对立关系,马特尔的大屠杀言说也呈现出一种审美政治的形态。
意大利左翼学者阿甘本吸收了施米特的法之例外思想、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批判理论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生命政治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通过类似于祭祀仪式等进行“排除”的方式,在人类共同体内建立一个特权空间,这个特权空间被阿甘本称为“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之域,由此将俗世与神圣区分开来,确立了政治权威所需要的神话属性和必不可少的暴力。阿甘本认为,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是由法律和法律的例外部分构成的,也就是俗世和神圣之域两个部分,作为个体的人可以被祭祀而进入神圣之域,即被排除出俗世之外,也可以被“玷污”而离开神圣之域,降回俗世。当人同时被俗世和神圣之域排除出去时(阿甘本称此为“双重排除”),这个人就成为“神圣人”(homer sacer),他的生命即是“赤裸生命”(bare life)。神圣人被排除出俗世法律之外,因而享受不到俗世的权利和法律的保护,可被随意杀死而杀人者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同时又被排除在神圣之域这个特权空间之外,彻底成为神(主权者)的所有物,为他们所捕获、控制。至高权力可以生产赤裸生命,作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唯有无条件地屈服于手握生杀大权的主权者面前,集中营便是这种生命政治的典范(乔吉奥·阿甘本,2016)。小说中的标本师标榜自己对动物的仁慈和爱心,声称自己从未杀过动物,然而他迫害的不是标本店里已死去的动物标本,它们所象征着的犹太人才是真正被标本师掌控的赤裸生命。猴和驴的动物隐喻不仅表现出动物和犹太人在聪明、隐忍等品质方面的相似,而且表现了两者同是没有人权、不受俗世法律保护的赤裸生命的一面。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动物就与人类区隔开了,它们既然不是人类,那么本就是处在俗世和神圣之域之外,从这一点来看动物天然地就是不受保护的“赤裸生命”。小说中,政府出台“关于市民与非市民的新分类”(扬·马特尔,2018:138),即由统治者行使权力宣布例外状态,原本还是普通民众的维吉尔等瞬间被排除出市民的行列,成为赤裸生命。随后他们进入了“衬衫国”,也就是穿条纹衬衫的集中营,遭受了非人的虐待,最后被随意地杀死,这是小说对犹太人真实遭遇的隐喻化表达。在《等待戈多》式的话语和动作风格映衬下,碧翠丝和维吉尔陷于茫然无措且毫无希望的氛围中,置身在被双重排除的场域里,其最终结局就是被至高权力推向死亡。
居于特权空间的诸神,他们是人类共同体的主权者,是至高权力,他们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又在司法秩序之内,因为法律赋予他们决定是否悬置法律、宣布例外状态的权力,这是主权的悖论,也是这些人被称为“神”的原因,他们既统治神圣之域又统治俗世。主权者用法律规制普通民众,他们也可以宣布例外状态悬置法律,把普通民众双重排除出去,使其成为赤裸生命,“在该领域中,杀戮是被允许的,不会犯杀人罪,但也不颂扬祭祀,而且,神圣生命——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生命——便是已被捕获在这个领域中的生命”(乔吉奥·阿甘本,2016:118)。标本师对于他的动物而言,就是作为至高权力统治者的存在。马特尔引入的《圣朱利安传奇》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正是标本师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对应,朱利安正是极具至高权力特征的人物,主要体现于他对动物生命予取予求且不受惩罚:由于朱利安具有高超的狩猎技术和无穷尽的杀戮欲望,只要他想杀就能杀,动物就是被他肆意捕获、杀死的对象,并且由于动物本就被排除在俗世和神圣之域之外,完全不受保护,面对压迫无从反抗,朱利安可以任意杀死他们而不受法律惩罚。以朱利安为原型的标本师同样是至高权力的化身,为动物制作标本的职业掩盖不了他冷血暴力的本质。在与标本师的数次交流中,亨利首先得到的印象是冷漠、神秘,他沉默寡言,与亨利对话时总是只有三言两语,对于不合他意的问题直接无视,让人很难看清这个人物,他的冷漠也传染给了整标本店,陈设的动物标本尽管被制作得栩栩如生,但亨利看出它们似乎是被恐怖的力量震慑住了,标本店里蔓延着死气沉沉的氛围;其次是强势、粗暴,标本师写信请亨利为自己写作剧本提供帮助,当亨利来到他的标本店时,他既不惊讶也没有表示欢迎,而是立即拿出手稿直奔主题,仿佛亨利的到来理所当然,且在与亨利交流剧本时,他总是想掌控话题的方向,要求亨利专注于写剧本这个中心,在谈话的过程中一直以冷酷的命令式的口吻对亨利说话,如同强横专制的独裁者,想把任何人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至此便可看出,通过对小说互文性和隐喻手法的分析以及借助于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观照,小说展现了文学言说与客观现实、生命政治三个层次的对应关系:“标本师——纳粹——至高权力”“驴和猴(动物)——犹太人——赤裸生命”“衬衫国——集中营——至高禁止之域”,从而显示出小说在大屠杀言说中隐含的审美政治元素。
结语
综上所述,马特尔给这部小说设计了两个叙事层面,通过运用互文性吸纳了其他文本尤其是大屠杀文学文本非写实性的表现方式,并化用《圣朱利安传奇》为小说提供了架构,同时以隐喻为主要手段间接地指涉大屠杀史实,使小说在无形中呈现出了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审美政治题旨,形成了马特尔所追求的非写实、言简意赅的表现形式。
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使得对大屠杀创伤的言说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原本与大屠杀相离甚远的马特尔选择扬长避短,从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里跳脱出来,抛开历史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魔幻现实主义来言说自己对大屠杀的体悟,他希望创作的正是一种不同的言说方式,“能应用于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也能应用于那些发生在卢旺达、南斯拉夫的暴力事件”(Sielke,2003),将目光置于全人类的层面。这不是一种取巧的伎俩,马特尔为写作此书也花费了多年时间走访实地和查阅资料,他深知艺术表现的真实与客观的真实有所不同,以非写实的魔幻手法来表现真实比起回忆录式的纪实更有艺术的优势。同时,他所创造的当代动物寓言还通过隐喻等形式,将生命的哲理层面导向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的审美政治关联,从而以自己独特的非写实言说在大屠杀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