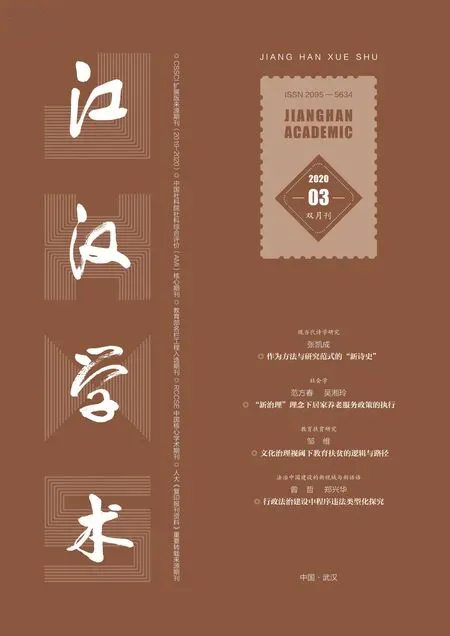巫师、史官与建筑师
——论叶辉诗中的物象与抒情主体
2020-02-28李倩冉
李倩冉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在一篇十几年前的笔谈中,叶辉自述:“我宁愿像个巫师,在一定的季候里完成他的仪式。”[1]这部分道出了诗人之于语言的秘密。尽管在比喻的意义上,所有诗人都应该是语言的巫师,道场各自迥异,法术也各不相同,但这一身份对于叶辉尤甚。作为一位深居高淳乡镇并对世间隐秘怀有特殊兴趣的诗人,几十年来,叶辉专注于探究南方小镇的日常物象,从中悟到了一些世事的奥秘。他以简省、可靠的语言道破它们,构筑一种神秘的氛围,为日常物象在当代汉语诗歌中的激活和生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向度。近年来,叶辉寻求自我风格的突围,在日常神秘的存在中引入对时代历史的思考,而组诗“古代乡村疑案”则将经由物象虚构历史的兴趣推向一个完成度较高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新变中,早年凝练的结构仍在发挥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在历史编纂所可能导向的具体繁复中进行镂空,这又为我们思考南方轻盈诗学的涵纳能力提供了启示。
一、先知语调的获得
就作品的语言来看,叶辉几乎没有学徒期,早年的诗作就已具备了成熟、凝练的语言形态。但倘若仔细考察叶辉诗歌中神秘性的延展方式和抒情主体语调,仍会发现它们经历了一个逐步生长的过程。
有一回我在糖果店的柜台上
写下一行诗,但是
我不是在写糖果店
也不是写那个称秤的妇人
我想着其他的事情:一匹马或一个人
在陌生的地方,展开
全部生活的戏剧,告别、相聚
一个泪水和信件的国度
我躺在想象的暖流中
不想成为我看到的每个人
如同一座小山上长着
本该长在荒凉庭院里的杂草
(《在糖果店》)[2]67
作为叶辉早期的代表作,《在糖果店》或许构成了很多人对叶辉的第一印象。诗中并没有太多神秘的色彩,仅仅再现了一个灵魂出窍的美妙时刻,构想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如草一般疯长的愿望,它的茂盛发生了不在此地的位移。整首诗带有温暖熨帖的调子,因为“糖果店”和“想象的暖流”自带的安谧温馨的气息,诗人对于“另一种生活”的冥想丝毫不意味着对此地的厌恶或逃离,而只是对异在空间片刻的冥思神游。这种“神游”在同时期的另一些作品中增加了物象本身的神秘感:
我们经常在各自的阳台上交谈
他看着对楼的房间说:那里像是存有一个
外在空间,因为那里的人很缓慢
……
我低着头在想。但他总是把头伸向望远镜
在深夜,脸朝上
像个祈雨的巫师
附近的工地上,搅拌机如同一台
灰色的飞行器,装满了那些可能曾是星星的砂石
(《天文学家》)[2]84
树木摇曳的姿态令人想起
一种缓慢的人生。有时我想甚至
坐着的石阶也在不断消失
而重又出现在别处
(《树木摇曳的姿态》)[2]78
乃至一位“家神”的出现:
雨天的下午,一个砖雕的头像
突然从我时常经过的
巷子的墙面上探出来
像在俯视。它的身体仿佛藏在整个
墙中,脚一直伸到郊外
在水库茂盛的水草间洗濯
要么他就是住在这座房子里的家神
在上阁楼时不小心露出脑袋
这张脸因长期在炉灶间徘徊
变得青灰
(《砖雕》)[2]79
正如这首《砖雕》由墙上的头像想象它被遮蔽住的身体,叶辉对小镇日常物象背后所隐含的神秘的想象,大多紧贴这些物象进行延伸,与祈灵于宗教而获得的神秘性大相径庭。用叶辉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用日常的手边的事物来呼唤‘神灵’”[1],这构成了叶辉诗歌的基本模式:由身边某个日常场景或物象起兴,通过联想和想象,将与之关联的另一个世界召唤进来。或许是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又或许是物件的前世来生,这些冥想带有一种鬼魅的气质,与肉眼所见的日常景象几乎不加过渡地榫接在一起,成为生活中“通灵”的时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靠在一棵树上/另一边靠着/一个小神,如果他离开/我就会倒下去”(《空神》)[2]57;“鸟飞过来了∥那些善意的鸟,为什么/每次飞过时/我都觉得它们会投下不祥”(《飞鸟》)[2]47;“它树叶中的那只黑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说不定/曾衔走过某个人的灵魂”(《考试》)[2]15;“癞蛤蟆的表皮起了泡/是因为他们古老的内心/一直在沸腾”(《魔鬼的遗产》)[2]30;“这时一个我一直以为已经死去的人/向我们走来。他蹲下系鞋带/可是我突然觉得,他像是/在扎紧两只从地下冒出来的袋子”(《我在公园里讲述的故事》)[2]37;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在相册里有三张挥手的照片,仿佛“再三道再见是为了/最终永不再见”(《合上影集》)[2]39……这些灵光乍现、“脑洞大开”的时刻,对微妙瞬间的捕捉,与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奇想”颇有共鸣——电车上后座人的报纸边沿像是在切割前座人的脖颈(《判决》)[3]160、不知哪颗星球的光正敲打我的墙壁(《镜框》)[3]162……
但叶辉并未止步于这种灵光一现的想象方式,在对命数持久的研习与观察中,他愈发专注于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是独属于古中国南方小镇的世代如常、因果报应。它首先呈现为对隐没于现代线性时间之下的循环时间的揭示:“我知道每棵树上都有/附近某人的生活,一棵树被砍掉了/但生活仍在延续/它变成木板,打造成一张新婚的床铺/在那里生儿育女,如此/循环不已”(《量身高》)[2]69。这种循环往复正如《遗传》中那道“桌沿上的压痕”[2]74,与楼上女同事漂亮的眼睛一样,来自一种世代的层累。或如《老式电话》中那些相似的下午、远处酷似父亲的男人,《砖雕》中与这一天相似的“以前的一些时刻”,欢乐、梦、悲哀会像天气的巡游一样在每个人的脸上风水轮转(《天气》)[2]53,一根木头在斧头的作用下可以不断变成椅子腿、衬子、楔子(《一个年轻木匠的故事》)[2]71……在一种几乎静滞的时间中,常与变,万物的转化、消长、盈亏,散布在叶辉所构筑的江南小镇上,几乎消弭了时间性与地域差异性,正如诗人在《一首中国人关于命运的诗》中所写:“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无论我在哪里/总是同一个地方”[2]81。而《萤火虫》在以更为笃定的语调讲述世代如常的命数时,将其推入一个互相关联的命运之网中:
在暗中的机舱内
我睁着眼,城市的灯火之间
湖水正一次次试探着堤岸
从居住的小岛上
他们抬起头,看着飞机闪烁的尾灯
没有抱怨,因为
每天、每个世纪
他们经受的离别,会像阵雨一样落下
有人打开顶灯,独自进食
一颗星突然有所觉悟,飞速跑向天际
这些都有所喻示。因此
萤火虫在四周飞舞,像他们播撒的
停留在空中的种子
萤火虫,总是这样忽明忽暗
正像我们活着
却用尽了照亮身后的智慧
(《萤火虫》)[2]61
这首诗以先知般的语调,从容地处理了视角的转换,尤其是不同时空的联结。“我”在机舱中俯瞰城市,小岛上居民仰望天空滑过的飞机,诗人并不过问两者间是否有联系,而是将这一动作中隐含的离别以一种时间的加速度带过——“每天,每个世纪/他们经受的离别,会像阵雨一样落下”,使之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命运。这几乎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笔下那幅命定的、永恒的图景:“他们的脚陷入像天空一样荒凉的大地的尘土里,他们露出注定要永远抱着希望的人们的逆来顺受的表情缓慢前进。”[4]人类的孤独、离合、悲悯、希望、失落,星辰的感应、昆虫的自在、命运的起伏、挣扎……它们被布设在短短数行诗中,各安其位,又仿佛冥冥之中互相作用。而叶辉对不同人命运之间隐秘联系的驾驭,在诗集《对应》的第一辑中愈发臻至成熟。
每一个人/总有一条想与他亲近的狗/几个讨厌他的日子/和一根总想绊住他的芒刺∥每一个人总有另一个/想成为他的人,总有一间使他/快活的房子/以及一只盒子,做着盛放他的美梦(《关于人的常识》)[2]3
要知道,人在这世上/会有另一样东西和他承受/相同的命运”(《一棵葡萄》)[2]4
征兆出现在/天花板上,我所有的征兆/都出现在那里∥……∥每个重大事件/都会引起它的一阵变形(《征兆》)[2]9
我们的记忆/有时,如同你那些懒得整理的抽屉/上个月我听人说:如果/人失去一种爱情、就会梦到一个抽屉/失去一片灵魂(假定它像羽毛)/就会捡到一把钥匙(《信》)[2]31
我的生活,离不开其他人∥有些人,我不知道姓名/还有些已经死去∥他们都在摇曳的树叶后面看我/如果我对了/就会分掉一些他们的幸福(《飞鸟》)[2]46
在这一批诗作中,叶辉的想象力主要集中于对事物之间因果、对应、影响关系的演化。尽管“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5]等道理早已在《老子》《庄子》《周易》等典籍中被道尽,但叶辉在当代汉语诗中重新发明了它们。他以极度简省的语言建构这些关系,容纳了生灭、世变,无限循环又无法穷尽,构成了一种氛围、一个微型世界乃至一种诗歌风格,给人以既奇妙又惶惶然的感受。而他也从中获得了“莫若以明”的观照事物的方式,创造了与之相应的语调。
如果说《在糖果店》中,叶辉对异在空间的想象还带有一种温暖迷濛的调子,那么在这批作品中,他逐渐习得了一种笃定、沉静、中立的先知语调。这首先体现在诗句中大量条件关联词和全称判断的运用中,俯拾即是的“如果……就……”“每一个……总……”“所有……都……”增加了抒情主体的自信和通透,让抒情主体逐渐成为一个宣喻的巫师或先知。叶辉越来越娴熟地制造诸多事物之间的对应和联结,仿佛不再需要依赖有形的存在,万物之间的联系早已了然于胸,以先知的口吻一次次说出,成为一个遍在的真理。而诗中结论之外的具体场景,即便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片段,也由于抽离了具体的时间性,而似乎变成了为这些结论提供印证的例子。诗中许多由“如同”“好像”连接起来的比喻,不再起到一种增加诗歌感性肌质的修饰功能,而是负责串联起一些有着隐秘相似性、关联性的场景。尽管丰富的细节和奥秘仍不乏迷人的感性,比如妇人梦中的葡萄树和远方男子梦中前来啄食的黑鸟,但往昔小镇生活具体的日常不再成为一个绝对的触发由头,而是在一个渐趋稳定的抽象结构内部成为起着说明作用的软性存在。这些基于“对应”结构的诗歌,在经由抽象、普遍化而获得一种似真性的同时,它们的迷人,也暗含了可能滑入“迷人的惯性”的风险。
二、历史的试触
或许是意识到万物消长的结构在诗中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而过于顺滑的写作容易导向风格的危险,在2010年往后的一批诗作中,叶辉开始了一些突围的尝试,在他所熟悉的结构中,引入了对现实的触碰和对历史的重绘。
一些惊诧的元素开始陡然出现在安宁恒常的景物中,比如《远观》,在用寺院、暮霭、溪水、农舍、土豆等搭建起的古朴宁静的气息中,诗人突然写到“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除了不久前,灌木丛中,一只鸟翅膀上的血/滴在树叶上”(《远观》)[6]75。这让人联想到洪磊的摄影作品《紫禁城的秋天》(1997)中那只卧于血泊中的鸟,或《中国风景——苏州留园》(1998)中那片血色的池塘。相似地,在《广场上的人群》中,诗人由小镇广场上跳舞的人群、玉兰树上的布谷鸟,陡然宕开一笔:“透过窗幔,广场显得神秘/有一会儿我觉得/我们之间隔着时光、年代/人群四处奔跑、焚烧/叫喊”(《广场上的人群》)[6]76。或如《新闻》中将“我”开车路过的风景与收音机里的新闻交叠在一起:灾难、凶杀与远处的河流,政治家的登场与“我”经过的危险路段,朋友在暴雨中等待救援的联想与广播里“渡过危险期”的儿童以及“火势仍然旺盛”的别处……[6]77还有从萦绕的蚕丝想到“大革命前/江浙一带,被缠绕着的/晦暗不明的灵魂”(《蚕丝》)[7]8,某个风景地“海鸟飞离,码头躺在血和腥味的/晚霞中”,“在镜头之外,一条狗掉入深渊/棕榈立刻烧毁了自己”(《留影》)[6]76等等。从叶辉诗歌惯常的结构来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由手边的平常物象、场景开始,在诗行的行进中,这些物象开始升腾,或发生一些变化,或产生一些喻示。而变化、喻示延伸的方向,就是其诗歌意义提升的向度。由此可以推断,这批诗歌中突然加入的灾变场景,或许是诗人着意冲破以往诗中世代轮回、波澜不兴的氛围,将其导向复杂和动荡,造成“混响”。而顺着这些作品继续往下看,又会发现,这些意外的变数在突然闯入之后又倏忽而去,诗歌的结尾往往又回落到“空无”的音调上。上述几首诗的结尾几乎都呈现了这样的特点:“大雾看起来像是革命的预言/涌入了城市,当它们散去后/没有独角兽和刀剑/只有真理被揭示后的虚空”(《远观》)[6]75;“不知从何而来的人群/他们正一个个走向夜空∥只有空荡的广场感到茫然∥一条流浪狗不抱希望地/检查着人们丢弃的垃圾袋、果皮/有如十分可疑的历史事件”(《广场上的人群》)[6]76,以及《留影》结尾剩下“浮动于尘世”的“寂静的教堂”[6]76;《新闻》最后遁入“思想快乐的晦暗之处”、逐渐含混的声音、记忆中一张模糊的脸[6]77……这或许说明了叶辉的历史观,即永远在一个宏阔的时间线索上去考察历史,即便有偶然的惊异,也仍然遵循旋起旋灭、忽明忽暗的规律,历史的记忆又未尝不可以是未来的先声。这种生灭无常的古老东方智慧,在《遗址》《邻居》《隐秘》《回忆:1972年》《在展厅》等作品中,进一步发展为人类历史的短暂、速朽与草木自然世界的恒常、无情之间的对举,前者正如《拆字》结尾那个落入门外深渊的“拍翅的回声”[8]47。
这一历史观念,在2016年的组诗“古代乡村疑案”中,被移置到一个远古的时间点。诗人从当下日常生活显影出的历史遗存里,虚构出一些古代南方生活的故事(以及它们的最终消亡),发展了《浮现》一诗尚未充分展开的主题。诗人在组诗的题解中认为:“所谓疑案也只是我对以往生活的一些想法”,“关于南方生活的由来并不是历史书能给出的,有时它就在我们附近,就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地流露出来。当我走在旧城中,看到古老的石凳上放着一只旅行箱,或者在泥土里嵌着一小块瓷片(有些可能是珍贵的),细想后你会觉得惊讶,以往的一切时时会浮现出来,在地下。”[9]33这组颇为整齐的作品充分发展了虚构历史的兴趣,情节性前所未有地增强。
县令
没有官道
因此逃亡的路像厄运的
掌纹一样散开,连接着村落
在那里
雇工卷着席被,富农只戴着一顶帽子
私奔的女人混迹在
迁徙的人群里
道路太多了,悍匪们不知
伏击在何处
但县城空虚,小巷里
时有莫名的叹息,布谷鸟
千年不变地藏于宽叶后面
无事发生
静如花园的凉亭,案几上
旧词夹杂在新赋中
最后一个书吏
裹挟着重要,可能并不重要的文书
逃离。也许只是一束光
或者几只飞雁
带着并不确切的可怕消息
但无事发生
火星安静,闲神在它永恒的沉睡中
县令死去,吊在郊外
破败寺庙的一根梁上,在他旁边
蜘蛛不知去向
县内,像一张灰暗下来的蛛网
一滴露珠悬挂其上
如圆月。而记忆
则隐伏于我们长久的遗忘中[7]13
《县令》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将一个县城的败落和人们的逃亡写得张弛有度,极富戏剧性和节奏感。人们逃荒的张皇失措、县令吊死的在劫难逃、悍匪伏击的威胁,与空无一人的县城里“无事发生”的永夜的安宁、闲神和死寂彼此交织冲撞,构成张力。结尾,县内蛛网般荒芜的道路和上空永恒的圆月再次将动荡的历史凝定在千年不变的图景中,而末句“记忆/则隐伏于我们长久的遗忘中”则再一次重复了历史循环往复、生灭不定的主题。这组作品中,还有一个村民诡秘又平凡的失踪(《绣楼》)[10]260-261;一具溺水的美丽女尸和一个县官的恋尸癖(《鳗》)[9]31-32;一次古代的审讯与落在邻村的流星之间隐秘的关联(《流星事件》)[10]258;一只木偶逃脱后狗和葫芦的异象(《木偶逃脱》)[10]260;《驿站》[9]30中古代城池的闪现;或者乡村先生的起居(《先生》)[9]33,无论朝代更迭仍照常生活的村民(《新朝》),偷伐树木的要领和禁忌(《偷伐指南》),儿童看到故去的老族长时水中钻出的乌鱼(《儿童》),青蛙般在井壁上来回浮现的记忆(《青蛙事件》)[10]259……这组“疑案”因为丰富的故事情节而获得了具体的时间性,不再将万物间隐秘的联系抽空为普遍的“对应”定理,而是以散布于不同年代、时间的具体情节展现它们,作品的感性程度大大增强。但万物的应和、消长,历史波澜的生灭等观念仍在背后隐隐地起着作用,使得叶辉对历史的虚构并未落得很实:一方面,所有这些历史均由一个物件引发的想象构成,就像《县令》从一条已经消失的驿道虚构出逃窜、动荡的历史,《穿墙人》[9]31的故事极有可能只是从墙边的一双鞋延伸开去,其目的并非真正的历史记述,而在一种美学趣味、一种气息的建立;另一方面,叶辉在建构的过程中也不忘时时对历史发出怀疑和消解,他不断泄露出这些物件、历史消亡的结局,同时表现出对文字构成的历史的不信任——历史可能就像《一行字》[9]32中没有几个人能读懂的布告,以及香案灰尘上的一行字,随时会被识字的“意外新故者”伸手抹去,而无从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历史虚构中,叶辉诗歌中抒情主体的角色也悄悄发生了位移,不再是《对应》系列中始终持握真理的巫觋或先知。他大部分时候是记录乡村逸闻的史官,是传说的讲述者,偶尔也会成为故事中的角色:“我”有时排在古代县衙受审队伍中,是个身负小罪、偷听到秘密的草民(《流星事件》)[10]258;有时是在宇航员探索太空时“正在给朋友写信”的小镇居民(《在太空行走》)[8]46;参观外地一尊佛像时,“我”突然丢失了自己——“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池塘、桥、小庙,几只仙鹤∥我是什么?/内心没有痛苦、只有焦虑/仿佛此刻田里闷燃的麦秸”(《解说》)……以往诗歌中仅作为功能性存在,且永远静观、沉稳、不介入的“我”突然出现了主体情绪,而这种情绪在《鳗》的结尾得以喷涌:“我决定任其腐朽,我要看着/窗口狼眼似的眼光渐渐暗淡/任奸情的状纸堆积成山/而人世的美竟然是如此深奥莫测”(《鳗》)[9]32,面对女尸的美,老年持重的内心突然焕发出少年般狂暴的激情,压倒了有关断案和兴衰的所有理性,爆发出对美毅然决然的耽溺和挥霍,这一被激活的县令形象,在这部虚构的史册中搅出了轻微的震荡。
或许可以认为,“古代乡村疑案”对村庄佚史的虚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叶辉在《对应》系列中面临的抽象、空泛的危险,从“先知语调”到“史官语调”的转变,使得他在处理以往熟稔的消长、转化主题时更为从容。尽管内心仍然持握宇宙万物相互生化、历史生灭无常的认知,但抒情主体不再直接地宣告出联系、对应的秘密,而是节制地待在具体物象或场景的内部,通过描摹它们的形态变化、空间挪移、想象它们的前身后世来表现这一切,乃至随物应和,角色化为其中必然消失的一环。
这一变化也体现在近期的几首新作中。《在暗处》《划船》《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涉及了物象明暗、光影的变化,并在其中看到往世与来生、记忆与遗忘的秘密。这似乎是对以往主题的回归,但诗人并未急于用背后或许隐含的定律来统摄它们,而是耐心地沉浸于光线变化本身的美妙,比如,“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而阴影靠得太近∥我记起一座小城/五月的气息突然充斥在人行道和/藤蔓低垂的拱门∥在我的身体中/酿造一种致幻的蜜”“几只羊正在吃草,缓慢地/如同黑暗吃掉光线”(《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7]8,“……犹如在湖上/划船,双臂摆动,配合波浪驶向遗忘/此时夕阳的光像白色的羽毛/慢慢沉入水中,我们又从那里返回/划到不断到来的记忆里”(《划船》)[7]12,而站在露水中秘密交换种子的树木、地平线后面滚落进海洋的半个世界、中世纪女巫“艳如晨曦”的长裙内衬、驱动我们的“沉重的黑色丝绒”、感到喜悦时身体内可能会出现的一道闪电(《在暗处》)[11]7……也将驱动万物的神秘力量写得绚丽感性。《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佛像》则是关于地理空间拓展的诗作中较为成功的一首:
没有人
会在博物馆下跪
失去了供品、香案
它像个楼梯间里站着的
神秘侍者,对每个人
微笑。或者是一个
遗失护照的外国游客
不知自己为何来到
此处。语言不通,憨实
高大、微胖,平时很少出门
……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佛像》)[7]5
整首诗较长,写了一尊中国佛像在异域的博物馆中微妙的“违和感”,并想象了它从中国的无名村落运到英国的旅途,曾拜倒在它脚下的村民由信徒摇身变成中介人,而他的脸与旅客、学者、另一展区的肖像画彼此酷似……结尾处,闭馆的博物馆外,“水鸟低鸣,一艘游船/莲叶般缓缓移动/仿佛在过去,仿佛/在来世”,将地域迁徙、历史文化的流动收纳到带有佛教意涵的莲叶中,凝定为世代生灭轮回的永恒图景。正如《候车室》试图展现“我们的生活很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影像,可能是历史生活的影像,也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影像”[12]这一类似于博尔赫斯《环形废墟》的主题,叶辉或许正在尝试通过空间上的延展继续探索现时、此地与别处“过往人类的反光”间的关系,《高速列车》《上海往事》《临安》《异地》[11]6-8等作品或可看作是同一尝试的初步结果。此外,《在北京遇雾霾》《大地》《高速公路》《蜘蛛人》[7]5-7中引入的现代城市意象,以及《灵魂》《笑声》《卷角书》[11]5-7中对“神性失落”与“历史混沌”的喟叹,亦可视为叶辉新一轮的试触,其美学效果还有待更多的作品提供观察。
三、轻盈的奥秘
就总体风格而言,叶辉是当代汉语诗歌中为数不多地成功发展了“轻盈”特质的诗人。在语言的简洁、瘦硬与附着于物象的想象、虚构之曼衍间,叶辉总能获得一个较好的平衡,像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在稳固与空灵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形态。尽管文学中的“轻盈”概念经由卡尔维诺和昆德拉的著名论断,已传播甚广,但汉语新诗中能够真正窥得此奥秘并成功熔炼为作品风格的诗人着实不多,以致于这一词汇反而常常成为中国评论者面对能力不足的“轻飘”作品时的粉饰托词。然而,须知真正能够掌控自己航向的“轻盈”,必然不同于“轻飘”,要以足够的内在力度为支撑。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叶辉对日常物象的观照总带有一种探究其背后隐秘的兴趣。这让他能够快速地离开物象表层的迷惑与牵制,迅速抓住事物的内核。叶辉自己也承认,他有一种“对于事物探究的执迷”[12],这一定程度上成为他诗歌轻盈的奥秘之一。这种探究,首先意味着对事物的倾听。主体清空自身的偏见,清除凌驾于物象之上的欲望,让事物自身所携带的气息被主体充分感知,主体也得以突破自身的个体有限性。而基于这种感知对事物间关联的发现,由于并非主体强加上去的,因而不必依赖对事物繁冗的捏塑、涂抹或修饰,而是直取世事秘密的核心,获得一种遍在的结构、一个独特的视角。叶辉正是在一个“被动”的层面上理解诗人使命的:“诗人的命运,似乎也是这样,最终,你只能以某种‘继承者’的身份出现,但这也不是你努力能够能做到的,是它找到了你,而不是你自己,所以所谓独特和创造都是不重要的,关键是你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中找到回响,看到自己远久的样子。”[1]这颇有些济慈“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影子。他声称自己是诗歌的“练习者”,只是记下了“对生活的觉悟”,且不论其中自谦的成分,其中对主体“我执”之局限的放弃,对更广阔命运的体察,或许是抒情获得轻盈飞升力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尽管崇尚对事物的钻研,叶辉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并不太依赖书本所提供的知识。作为一位“研究《周易》数十年”、对地气、风水、运数非常着迷的诗人,叶辉诗歌中的智性元素,更多是基于一种类农耕时代的生活经验的累积。这让他有效避免了知识的围困。在与木朵的访谈中,叶辉流露出对诗坛论争术语和理论“大词”的抗拒,表示对1990年代诗人提出的理论策略和当代诗歌的年代变迁并不太关心。与处于“中心”的诗人相比,深居在高淳石臼湖边的叶辉呈现出较少与外界联系的封闭状态,尤其是在网络进入之前的1990年代。但有时,“常常是貌似远离的东西更具有吸引力,远离即主见,自我放逐、沉迷和隐匿正是一种态度,一种自我选择”[13],正是偏居一隅的叶辉敏锐地发现了时代的谎言:“我的整体印象是:1990年代的诗,仿佛只是言论的引用部分,言论似乎更重要了。”[1]的确,1990年代诗歌的泡沫之一,在于阅读资源的堆砌和理论建构的空洞成为诗人才华平庸的掩体。很多在这时开始经营自己声名并显赫一时的诗人,往往将经由他们所提出的“叙事”作为诗歌复杂性的必然保障,但充其量只是以分行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拉杂的事体,使得这些作品显得表面繁复,实则缺乏精神内力。与这一风潮相比,叶辉的轻盈,在于他不会遁入理论和修辞的旋涡。他对日常物象的亲近和研习,并不意在于导向某种知识的炫耀,而是着力于一种美学趣味和气质的养成——“要紧的是你是否有能力离开诗,进入真正的生活”[1],这让他的诗中留有足够的缝隙供语言和物象自由呼吸。
但需要说明的是,轻盈并不意味着简单和怠惰,它仍然有赖于诗人足够的创造力,在语言中塑成风格。尽管在前文中,叶辉强调了自己聆听物象背后可能性的“消极承袭”能力,但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形态上,轻盈的诗风仍然是他在语言中主动创造的结果。其中,意象与关联词的关系值得注意。一方面,叶辉诗中意象众多,往往并不具体展开,但每个意象都自带一种气息、一个自身的小宇宙,构成了一个丰盈的世界。他认为,《易经》中强调一个事物的变化带来整体变化的观念和写诗很像,给他以很大影响。由一个字、一个意象的改动来带动诗歌整体观感的变化,比如2010年之后一批试触现实的诗歌就以现实意象突入的方式,充分发挥了汉语诗歌中“意象”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叶辉并未简单地将这些意象堆叠在一起,而是用关联词将它们组合起来,因而有效地控制了诗歌内部的张弛度,连接词的果决、简省,乃至通过否定词达成的多重转折,比如《县令》中的“但”“而”,《远观》中的“除了”,或《在糖果店》中的“不是”“也不是”,使得诗歌内部的层次和褶皱丰富起来,构成了一个紧凑的内部空间。但这些关联词并非强加上去的,而是基于诗人对物象间联系的发现或构想,正如前文所述,这有赖于诗人对事物自身声音长期的倾听和思考。时下与叶辉同被归在“江南”名下的几位诗人,诗风也大多简洁。但一个显见的问题便是“轻”造成的失重感。他们当中有些以呼天抢地的家国指涉,有些以声色绮靡的江南营构,形成了各自的写作特征,但主体往往是怠惰的。他们经常只是以排比的方式摆放、堆叠出了一些意象,由这些意象自身携带的暗示力,组合成一幅似是而非的图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江南想象;又或者过于紧贴物象的浮表,亦步亦趋地织就景物,而仅仅在诗歌结尾腾空一跃,砸下喻指。相比之下,叶辉以更为持续的深入,呈现了主动镂空的姿态和诗歌结构上的平衡。他通过精准的描述、视角的选择、繁简的调配、臻于极致的概括力来抵达诗歌的轻盈,而非依赖或此或彼的暗示。如果确乎存在一方南方小镇,它绝非仅仅是一团似有还无的雾气,它包含着更多的复杂性——循环、静滞中的冲撞,奔突之后的陡然柔弱,或无数世代的诞生与寂灭,均需要写作者去主动建筑起来。这提示了即便是一种轻盈的诗学,也永远是透澈的产物,而非懒散的结果。
“我将不断吃,不断重建/一些飞鸟、一些野蛮的东西”(《树木摇曳的姿态》)[2]78。就已经呈现的作品来看,叶辉以一种轻逸而富有力度的方式,构筑了时代、世变、无常,以及属于东方古老智慧的此消彼长的奥秘,并且,他仍在不断地建筑和吐纳着他的南方,或某个他处。他的小镇空灵,但并非完全神秘莫测,那些雕镂得当的诗行至少构成了某种召唤:放弃永远有千百种滑落的方式,而唯有持续掘进的诗人,才具有偶然窥得轻盈奥秘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