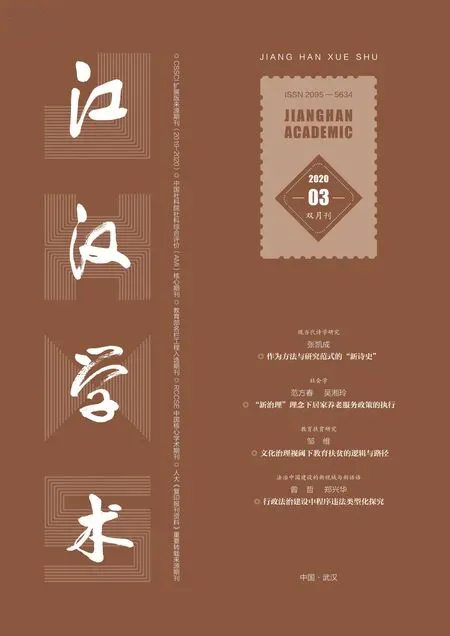吕坤思想的荀学理路探析
2020-02-28张泰
张 泰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吕坤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思想虽以理学为本,但却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品格,《明史》本传称他的著述“多出新意”[1],这一“新”就体现在对理学的突破上。他学宗程朱,又没有落入空谈心性的窠臼,而是对程朱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分析吕坤的思想理路,我们发现他与荀子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吕坤对荀子从思想理路层面的接受是一种隐性的接受。荀子在宋明理学时代被排除出儒学道统之外,理学家多以荀子为儒学之异端,直到明中后期才出现以李贽、周汝登为代表的肯定荀子的声音。吕坤对理学的认知实乃纠正程朱之偏,试图以外在事功融入儒学道统,恢复原始儒学“内圣外王”的完整面貌,这正是先秦儒学由荀子所传承的一脉,是荀子思想最显著的特色,也是被宋明儒者所抛弃的一脉。
一、对“道”与圣人的体认
吕坤在学术上坚持独立的人格,不以道学为宗,注重阐发自我的思想价值。在吕坤主要活动的万历年间,思想界已出现很多与主流理学相悖的思想,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之道”,降低了圣人与百姓之间的等级差别,而将道的主体降为百姓。泰州后学李贽则公然与道学反叛,讽刺道学家的虚伪,自称“异端”。吕坤生活在这样一个启蒙思想已经萌生的时代,本就在学术上有自我认知的他,自然不拘于理学乃至儒家的门户之见,而从更广的层面理解“道”,他认为:“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底。”[2]642“道”不仅存在于古今历史中,也存在于各个层次的人中。荀子将“道”理解为宇宙间统领万物的根本,“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3]377。他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与儒家的学术旨归相结合,将道的根源上溯到自然之天,认为“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3]464。道能穷尽世间一切变化,是万物所共通之根本。原始儒家对道的理解是从人的维度展开的,即便追溯到天,也会从天人相交的角度赋予天以德性,而荀子则开创了儒家体道的客观路径。从这一角度来看,吕坤的道论正是上承自荀子。
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3]158圣人是道的枢要,总领天下之道。但道在后世的内涵越来越狭隘,宋明时期理学家宣扬道统,将道限定在儒家内部,成为圣人的专属,这是对道的私化。吕坤认为:“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2]642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关键不在“道”,而在“庸常”,他说:
尧、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个天然自有之中行将去,不惊人,不苦人,所以难及。后来人胜他不得,却寻出甚高难行之事,玄冥隐僻之言,怪异新奇偏曲幻妄以求胜,不知圣人妙处只是个庸常。看六经四书语言何等平易,不害其为圣人之笔,亦未尝有不明不备之道。嗟夫!贤智者过之,佛、老、杨、墨、庄、列、申、韩是已。彼其意见,才是圣人中万分之一,而漫衍闳肆以至偏重而贼道,后学无识,遂至弃菽粟而餐玉屑,厌布帛而慕火浣,无补饥寒,反生奇病。悲夫![2]641
“天然自有之中”指“事物之理”[4]411,即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是道的范畴。圣人是顺应事物之情理的人。荀子也说:“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3]366吕坤对圣人也持尊崇的态度,并非像李贽一样否定圣人的地位,但他反对理学家将圣人神化的做法,而主张理性看待圣人。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5]。历史上有“大道至简”的说法,这不仅适用于道家,同样适用于儒家。理学家所宣扬的道学已经偏离了真正的道,为此吕坤曾明确提出“我不是道学”,与道学划清界限。宋明时期所流行的道学是极为繁琐的学问,名义上尊圣宗经,实际上却以佛老等融入儒学,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戴震曾批判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6]。
在理学的话语中,由于对道的体认不同,出现了很多“异端”,吕坤认为:“异端者,本无不同而端绪异也。千古以来,惟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脉是正端,千古不异。无论佛、老、庄、列、申、韩、管、商,即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异端,子贡、子夏之徒都流而异端。”[2]654这实际上是对当世道学惟周孔是从的反讽,吕坤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庸俗与虚伪:
人皆知异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见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骋浮词以乱真,或执偏见以夺正,或狃目前而昧万世之常经,或徇小道而溃天下之大防,而其闻望又足以行其学术,为天下后世人心害良亦不细。是故有异端之异端,有吾儒之异端。异端之异端,真非也,其害小;吾儒之异端,似是也,其害大。有卫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辩哉?[2]645
这一观点与荀子对儒家内部批评的论调基本一致,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评的第六家即子思、孟子一派,他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3]110-111他认为子思与孟子打着先儒圣贤的旗号,却流于邪僻与晦涩,不了解先王却装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与圣王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由孟荀思想理路的不同所导致的,思孟一派强调由内向而入,注重心性修养,而荀子一派则注重外向,重视现实与社会事功。这两种对道不同的体认路径决定了两派的发展方向。荀子对儒家内部的批评是尖锐的,在那个时代具有难得的理性精神。吕坤正是继承了荀子这一精神,才能深刻揭露理学的弊端,结合社会现实对儒学进行正本清源。
二、社会事功的追求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道在自然和社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荀子》全书论及‘道’者有32处,几乎涉及自然观(天)、认识论(辞、论)、政治法律(法、势)、社会生活(用、俗)等天道观、人道观的所有领域。”[7]荀子说:“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3]367“守道”就是掌握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8]。在政治层面,荀子说:“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3]280以道为统治之根本,这是儒学对道的基本认知。吕坤所讲的“道”与荀子所讲的“道”都具有超越儒学内部思想体系,又回归原始儒学之根本的意义,这也是他们思想理路共通的基础。
吕坤认为无论从学术还是事功层面,都应回归圣王的时代探求真谛。他说:“求道学真传,且高阁百氏诸儒,先看孔孟以前胸次;问治平要旨,只远宗三皇五帝,净洗汉唐而下心肠。”[2]629从他与门人的这段对话可清晰看出其思想的特质:
一门人向予数四穷问无极、太极及理气同异、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语,予亦能剿先儒之成说及一己之谬见以相发明,然非汝今日急务,假若了悟性命,洞达天人,也只于性理书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语,讲学衙门中多了一宗卷案。后世穷理之人信彼驳此,服此辟彼,百世后汗牛充栋,都是这桩话说,不知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见在得济否?我只有个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处事接物、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本小节都事事心下信得过了,再讲这话不迟。[2]644
吕坤对于理学中的“无极、太极、理气、性命”等观点没有什么兴趣,认为这些无非是纸面上的空谈,对现实无所裨益。儒者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这就是他注重事功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体现。社会事功表现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州县编审差役如何均平,地粮如何清楚,盗贼如何消弭,风俗如何转移,仓廪如何充实,荒歉如何救济……至于世道之汙隆,国家之理乱,漕河之通塞,马政之修废,军伍之盈虚,战守之机宜,边计之得失……”[9]。他始终以民为本,将这种事功精神应用于政治实践。吕坤的仕宦生涯开始于万历二年(1574)入京应殿试,被任命为山西潞安府襄垣知县,结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以病乞休。在二十四载仕宦生涯中,他始终“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10]209,刚正不阿,恪尽职守,为民谋利。他认为,作为儒者,在注重自身修养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外在事功,他以“尧、舜事功,孔、孟学术”作为君子终身奉行的准则,实际上就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余敦康先生说“内圣是对天道的理解,外王是把这种理解运用于人事”[11]。“尧、舜事功”之要就在于“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2]707,这正回归了道的本原。
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也比较一致,荀子曾指出仁人当致力于“上则法尧、舜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3]114,这是针对当时十二子学说乱天下的现实,从事功和道义两个层面对仁者提出的要求。吕坤仅将荀子所推崇的“子弓”换成了“孟子”,这是唐宋以来孟子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亚圣”的必然结果,从根源上讲都是对儒家先贤的认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方面,荀子曾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论政于燕、谈风俗于秦,在推动儒家社会理想实现的路上不断努力。韩德民先生认为,荀子所代表的儒家现实主义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极度艰难的,因为“儒学发挥规范作用的环境的极端恶劣,及它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走向自己反面的悲剧性事实,反过来刺激儒生使之向内在心性领域寻找寄托”[12]21。这也是内向之学逐渐占据儒学主流,而荀子则沦为异端的原因。
吕坤同样认为,儒者建功立业是比著书立说更困难的事,“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2]810。历代儒者多以思想扬名于世,而缺少事功的追求,现实关照性不强。吕坤之所以会有这种感慨,也与明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有关。万历年间,朝堂上朋党林立,吏治腐败,政治危机日渐加深,而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走向了空谈性理之末流,理学家不问世事,只知虚饰文辞,高谈阔论。对于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现实,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多次予以抨击,他指出:“世之病讲学家者,其说有二:曰伪,曰腐。伪者,行不顾言;腐者,学不适用。”[10]90他指责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为“腐儒”,他对这类人进一步描述为:“起念便觉天地万物不亲不故,与我无干;不痛不痒,与我罔觉。及其聚会讲求,不过理会古人多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细索,无了无休。此人即置之庙堂,只可作一迂腐之儒,坐镇雅俗,了得自家耳。”[10]210“士君子高谈阔论,语细探玄,皆非实际,紧要在适用济事。”[2]808
荀子也曾多次对儒者提出批评,《劝学》中说“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3]17。“陋儒”指的就是囿于书本纸面而不懂践行礼义的浅薄之儒。《儒效》中说“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者也”[3]164-165。“俗儒”指的也是不懂先王礼义之道的沽名钓誉之辈。荀子还曾在《非十二子》中称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为“贱儒”,原因就在于三子之后代门人偏离了儒者的本色,不懂得“宗原应变,曲得其宜”。荀子对当时儒者的批评是从礼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那些“陋儒”“俗儒”“贱儒”没有将礼义之道应用于政治实践,而是以之谋生存,其行为已失去儒者的本色。吕坤所面对的明中后期理学空谈性理的局面,虽与荀子时代不同,但其批评的立足点与荀子是一致的,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儒者应当具备现实的关怀。
三、礼与法的交涉
历来政治统治有礼、法二端,儒家重礼,法家尚刑。在理学时代,理学诸子从天理出发,主张德主刑辅,使德刑论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刘泽华认为:“作为儒家道统的维护者和倡导者,理学诸子都是德主刑辅、礼本刑末论者。他们从礼法即天理,德刑致中和的观点出发,主张把‘为政以德’和‘为政以刑’结合起来。”[13]朱熹对《论语·为政》的解读可以视作这一观点的代表,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14]54从历史上来看,儒家对法持谨慎的态度,虽未曾否定法的意义,但有重礼轻法的主张。荀子是先秦儒家中对法论述最为详尽的,在荀子的话语中,法与礼常常同时出现,如《君道》篇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3]282,《成相》篇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3]545。相较于孔孟来说,荀子对法的重视程度更高,但与法家一断于法不同,荀子的基本立场还是儒家的隆礼,“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3]14。礼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高于法,礼是法的根本原则,法的施行也要以礼为准则,要赏罚得当,防止刑罚泛滥。
吕坤的思想虽然出于理学,但他对礼法的看法源自对社会事功的追求,和理学面对礼仁的哲学思辨有所不同,而更近于荀子的实用主义。他吸收并继承了荀子对礼法的认识,尤其重视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将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礼与法不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一体之两端,趋近于平等。法表现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就是“刑”,刑与礼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相通,即教人向善,“刑、礼非二物也,皆令人迁善而去恶也,故远于礼则近于刑”[2]834。二者在国家治理中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礼重而法轻,礼严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权也。故礼不得不严,不严则肆而入于法;法不得不恕,不恕则激而法穷”[2]855。礼虽然以和为贵,但要主于严,惟有严才有规范意义,而法则主于恕,避免过分严苛而激起人民的反抗。治理国家实际就是在礼与法之间寻找一个中心点,防止步入一者之极端。从这一点来看,他批评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伪、今世是非”[2]810,则是以现实为出发点,更具现实意义。
对于“王道”,吕坤并不刻意强调礼治的根本地位,而是将法也视为王道的一方面:
申、韩亦王道之一体,圣人何尝废刑名不综核?四凶之诛,舜之申、韩也;少正卯之诛,侏儒之斩,三都之堕,孔子之申、韩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尝不申、韩哉?故慈父有梃诟,爱肉有针石。[2]851
吕坤对王道的描述相较于先秦儒家要更务实,他认为王道政治也应该包括法治,这与孔、孟显然是不同的,即便荀子重法,但也以“粹而王,驳而霸”为原则,王道只能靠礼义实现。显然这是吕坤面对社会现实的妥协。他以圣人舜与孔子为例,说明圣人不曾废刑名,甚至,他将自然界的雷霆霜雪现象喻为刑罚,来说明社会存在刑罚的合理性。孔子对于刑罚一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孔子家语》载有孔子之言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15]。但刑排在礼、政之后,用刑的条件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15],所适用的对象乃是极难教化之人。他极力主张为政以礼,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14]53;同时又说“君子怀刑”[14]71,在鲁国任大司寇时更是执法严明。其实,不曾“废刑名”,不等于“重刑名”。孔子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蓝图,在现实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才会有执法严明之事实。面对现实社会,也需要有刑罚的辅助治理。对孔子的这一思想,朱熹的解读当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刑政耳”[4]3200。这一思想是经由荀子而发扬光大的,但在朱熹看来,荀子乃是申、韩之流,“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4]3255。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吕坤的法治思想离不开人治。他说:“治人治法不可相无,圣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继之以规矩准绳、六律五音,此治法也。”[2]864圣人与法是彼此依存的关系,从法的起源来看,“制礼法以垂万世、绳天下者须是时中之圣人”[2]755。法由圣人产生,圣人依靠法来治理社会。他进一步强调,法治的关键就在于人:
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须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结绿非不良剑也,乌号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资敌。予观放赈、均田、减粜、检灾、乡约、保甲、社仓、官牛八政而伤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余罪矣。[2]821
圣人创制立法的说法在历史上很常见,韩愈也曾说“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除其强梗”[16]。在历代的政治实践中,对“治人”的强调实际就是对贤明君主的渴求,古代社会的“以法治国”其实都有一个主体,即君主。君主在法之上,君主的德行决定了法的命运。这与荀子的主张是一致的。相较于法,圣人君子在荀子的话语中地位更重要。荀子也将法的起源归于圣人君子。他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3]272作为统治手段的礼义与法度均由圣人产生,圣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3]179由此可知,荀子的礼法观本质上还是人治,即“有治人,无治法”[3]272,对此,刘泽华认为荀子所讲的人与法“不局限于论述人与法律的关系,而是讲人在整个政治诸种因素中的地位问题”[17]。吕坤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圣人至上的理念,与荀子一样,认为在国家治乱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法。
圣人至上的理念反映了儒家尊君的政治主张,但与道相比,圣人亦不能凌驾于道之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3]295,韩德民指出“所谓‘从道不从君’,就是当现实的君主与理想的秩序构成原则发生矛盾时,臣子可以而且应当为了道义原则而违背君主”[12]198。关于这一点,吕坤也说:
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2]645-646
道并不为圣人所专属,而是万物的根本原则。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圣人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吕坤所说的圣人之理,就是社会政治层面的“道”。在圣人之理与帝王之势的选择中,势要服从于理,这也是儒家与法家的根本区别。马涛认为“吕坤所倡导的‘以理抗势’的政治精神,是先秦儒家‘以德抗位’精神的延续和发展”[18]。从这一点来看,吕坤的论述正是以荀子“从道不从君”为基础的,他从理与势的关系出发,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原则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四、天与人的分殊
吕坤的社会政治思想注重事功,对礼法有明确而具体的追求,其思想基础在于对天人关系的客观认识。上文提到,吕坤认为道乃“天下古今共公之理”,具有普遍性与历时性,道表现为“当然”与“自然”:
道有二然,举世皆颠倒之。有个当然,是属人底,不问吉凶祸福,要向前做去。有个自然,是属天底,任你踯躅咆哮,自勉强不来。举世昏迷,专在自然上错用工夫,是谓替天忙,徒劳无益。却将当然底全不着意,是谓弃人道,成个甚人?圣贤看着自然可得底,果于当然有碍,定不肯受,况未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处。[2]647
“当然”与“自然”分别对应人与天。“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妇随,兄友弟恭,此之谓当然。”[2]772“当然”是人依据一定的规范而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人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社会意志。“阳亢必旱,久旱必阴,久阴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谓自然。”[2]772“自然”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属于客观世界的范畴,本身并没有意志,也不受人的意志的支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吕坤的哲学体系中,天与人具有明显的分殊。
面对客观的“自然”,吕坤主张“任自然”,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但也主张“夺自然”,利用自然:
天地全不张主,任阴阳,阴阳全不摆布,任自然。世之人趋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夺自然者,唯至诚。[2]768
吕坤思想中的“天”是由气构成的自然之天,“天积气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2]764,“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2]772,因此对于理学家所主张的天人相感,他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应当建立在顺应自然,掌握规律的基础之上,对自然进行充分利用。他还说“圣人学问只是人定胜天”[2]787,把这一思想的主体定位为圣人,以圣人的权威确定天人关系中人的主导地位。
吕坤的天人观与荀子是一脉相承的。在荀子之前,天是一个与人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概念,具有一定的主宰性与神秘色彩。天道与人事、宇宙与社会有着复杂而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荀子视天为客观的存在,抛却了天的宗教与德性特征,还原天原始的本质的面貌,主张“天人相分”,天道与人事不可混为一谈,主张改变人对天消极适应的状态,而是“制天命而用之”,这正是吕坤“任自然”与“夺自然”的理论来源。
吕坤说:“万籁之声,皆自然也。自然,皆真也。物各自鸣其真,何天何人,何今何古?”[2]646《庄子·齐物论》载子游问子綦“天籁”,子綦答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9]吕坤所谈的自然与道家有些相近,但对于道家的“无为”,他并不认可,他对庄子有这样的批评:“庄、列见得道理原著不得人为,故一向不尽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2]647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他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杨倞注“庄子但推治乱于天,而不知在人也”[3]464。道家重天道而轻人事的观点也一向为儒家所反对。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吕坤与荀子思想理路的相通性根源于对“道”的客观性的认知,由此出发,他们对天与人的关系有着明确的界定,天与人各司其职,才能保持稳定的宇宙与社会秩序。他们都主张利用自然,注重社会事功,在政治生活中重视礼法,发挥儒者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吕坤的思想体现了明中后期士人对荀子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荀子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影响逐渐加深,为清代荀学的复兴开辟了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