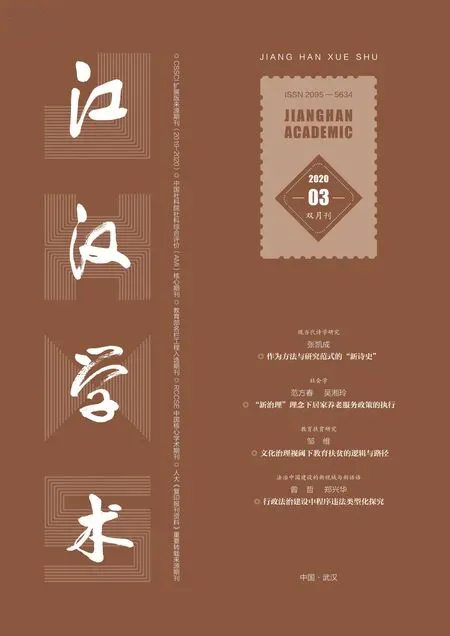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多维透视与前瞻
2020-02-28山丹,侯颖
山 丹,侯 颖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24)
儿童校园小说,是“指表现儿童校园生活,反映儿童在学校中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的小说”[1]。校园空间浓缩了儿童生命形态,能够集中地表现儿童的生活现状、情感困惑与生存真实,占据着儿童文学的重要篇章。正如刘绪源所说:“在童书畅销的黄金十年,有一个阶段,儿童文学就只剩了两个品种,一是校园小说,二是青春文学。”[2]可见,儿童校园小说从创作主体到接受主体的认同度之高。回顾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儿童校园小说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如张利芹[3]、李晓茜[4]、李彦之[5]等,分别对杨红樱、秦文君、王巨成等儿童校园小说作家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语言特色等进行分析;李学斌[6]、李彦之[7]等针对畅销儿童校园小说《君伟上小学》、“贾里”校园系列小说等作品进行了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谈凤霞[8]从比较视野的角度总结了美国的校园小说中对主体形象的塑造方略,为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视野。
从建国初期开始,以表现“少先队员校园内的生活题材”的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占据着儿童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创作范式。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校园小说形式的探索与内容的革新,儿童校园小说开始注重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本主义的发掘。1990年代前后,儿童校园小说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作高峰,并出现了一批以杨红樱、秦文君为代表的校园小说热潮。同时,以张之路为代表的作家将“幻想”带入了校园,也为儿童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时代变迁和生存方式革新,文学大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而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了更为多元的发展趋势。
一、校园小说题材意蕴界域的延伸
纵观中国儿童小说的发展历程可知,儿童校园小说一直以教育性作为创作的基本立足点。特别是随着“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9]创作理念的提出,更是强化了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教育价值。因此,校园小说因其自然地负载着对于儿童、学校,以及教育问题的思考而紧密地与校园生活本身联结着。然而,从班马的作品《六年级大逃亡》表达少年要冲出校园生活的束缚,到殷健灵小说《野芒坡》在历史想象中建构出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少年对校园生活的断想,再到新生代作家葛竞的作品《魔法校园》用魔法元素在幻想的世界中搭建奇特的校园景象来突破校园本身的桎梏等,一次次题材突破和尝试都表明了儿童校园小说题材对“走出校园”的渴望。正如吴其南所指出的,随着新时期以来一元化的教育视角被消解,中国少年校园小说作家在选材上有了一次革命性的突围,他们从“传统的学校、家庭题材”向“现实社会主题”做出了一次大胆迈进,开辟了一个走向自然、走向童年、走向神话与巫的儿童小说创作新世界[10]。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依然在不断地延伸题材意蕴的界域,而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创作形式和表达手法的改变,还体现在对儿童主体的内化追寻,具体表现为:
一是尊重儿童精神自身的教育力量。中国儿童校园小说作品中,时常存在一个“引路人”。在生理层面上,他/她是少年身体认知的启蒙者;在心理层面上,他/她是少年自我同一性建立的鼓励者。在校园小说中,这个有教育意义的角色常常由老师来担当,如张之路《题王许威武》中独特又可敬的许老师,黄蓓佳《草房子》中亦师亦母的刘老师等。而新世纪以来,这个“引路人”不再以教育者身份自居,而是尊重儿童精神本身所具有的教育力量。如顾鹰的小说《轻尘》中的“引路人”是一个在学校不善言辞的中学女生林晓音。她很难融入同学之中,却有一个众人不知的秘密,即她是笔名为“轻尘”的、全校同学都十分仰慕的小诗人。从表面来看,这个缺乏自信、默默无闻的女生是很难得到众人的认可,树立自我价值的。作品以“诗”作为构建同学间心灵沟通之桥,不仅使这个才华横溢的自卑女生赢得了同窗的掌声,也使她成了实际意义上儿童心灵的引领者,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启发人心,彰显儿童校园小说的教育性。
二是呈现对特殊儿童个体更为深切的关怀。儿童校园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总是具有一定的映射效应。如张天翼笔下的“罗文英”代表了有坏习惯的孩子们,杨红樱笔下的“马小跳”是现代都市儿童的代言人。然而,正如作家黄蓓佳所指出,“儿童文学的阅读主体是一群含着金汤匙,拥有锦衣玉食的城镇孩子,但是他们并不是儿童群体的全部,还有一群和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孩子们。”[11]新世纪以来,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开始将笔触更多关注到了特殊个体儿童,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的窘境,还有身体的残缺以及心理的缺失,能够正视他们的存在是文学的悲悯也是人性的深沉。如,余显斌的小说《瓷熊猫的泪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看待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同学。“我”与几个同学对待这位“特殊”同学时,表现出了轻视、嘲笑与捉弄,也因此对“她”造成了一次次伤害等等。通过视角的置换,作品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特殊群体儿童的情感真实和生活困苦。这是儿童文学作家对校园小说中特殊个体人性关怀的觉醒。
三是逐渐重视儿童主体人性的多面化。儿童一直以来都是“真善美”的化身,无论是秦文君笔下的“贾里”“贾梅”,还是曹文轩笔下的“青铜葵花”,他们都被描摹成内心洁净和性格纯良的形象。然而,“儿童的自我力量来自个人与集体的互相确认”[12],正视儿童的存在本身,需要肯定与尊重每一个体生命的人性之复杂。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校园小说逐渐重视了儿童主体的个性化以及人性的多面化,展现出了他们更为立体化的心理和多面性的人格。如,张之路在充满幻想色彩的小说《他没有影子》中,描写了一个贫穷高中男生刘豆豆通过卖掉自己的名字得到钱财的故事。名字作为一个形式符号,在这场高中生的灵魂赌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名字所换取的金钱,荒诞化地为少年带来了他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可是,不正当地交易后,却带给他作为“名字”曾有者的羞愤与耻辱。主人公面对失去了影子与灵魂的双重失守后,渴望找回自己用以交易的“名字”。可悲的是,找回自我的方式是占有他人名字,而这个过程也类似一场新的灵魂交易。在这部小说中儿童形象不是“真善美”的简单象征,而表现出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殊性和多面性。作家精准地表现出的小说中多种不同人物性格,以及拓展到社会空间的复杂感,表明了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在题材上的重要尝试。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题材意蕴的延伸化现象,是儿童小说创作在以“儿童本位”的原则下深化理解儿童所迈出的重要脚步。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伴随着儿童小说对回归文学、回归艺术、回归儿童的不断探索,从儿童群体、儿童个体到特殊群体,以及对他们生活可能性的关照上,都体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生活的生动写照以及儿童精神的敏锐挖掘,并使得“儿童本位”成为可能。然而,在对儿童心理内化的探索中,儿童文学作家也在试图建构一种他们所认同的“儿童”。儿童文学作家是基于他们认为儿童应有的样子以及需要成为的样子来书写的。他们很难真正地感知儿童的生活,倾听儿童的情感。因此,文本在童年生活现实感、童心情感真实性的呈现方式上是存在疑问的。
二、校园小说的价值认同呈现丰富性
考察一部儿童校园小说的价值取向就是在追问其文本所彰显的“儿童观”。正如朱自强先生所提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持有着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走进儿童生命的空间,在认同和表现儿童独特的生命世界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自我生命的扩充和超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自身人性中的可贵品格。”[14]也就是说,作家在对儿童的生命世界进行观照的同时,应当将自身人性、人格融入其间。与建国期儿童小说所呈现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不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在价值认同方面呈现出了丰富性。
一是更为宽容地对待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矛盾。儿童校园小说对儿童的关照,往往会在作品中展现为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习惯将成人的价值凌驾于儿童之上,并建立一种驯化式的高标,所以对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中顽童王葆的创造力和好奇心的认可,总是没有指责他不劳而获的声音洪亮。近年来,儿童心理学家在重新审视儿童在校园的心理时,指出:“孩子们在学校是处于一种个人竞争的环境中”[15],他们在校园中不仅是一个需要被教育的整体,而且是拥有鲜活内心世界的独立个体。尽管老师及家长期望儿童的心理成长处于可控状态,但是被误读和被无视却常常在所难免,所以儿童的烦恼、苦难以及情绪都很难被认同。新世纪以来,儿童校园小说呈现出作家在对待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价值矛盾的宽容心和同理心。如在彭学军的小说《今天要写的作业》中,当女生施诗出现了心理问题时,老师对她的关心反转了之前严厉的态度。曾经的那个因为学生失误而严厉指责、施以惩罚的严师转变为宽容的慈师形象,而对学生的关怀体现出一种成人式的责任感。放下成年人的价值偏见,是成人打破与儿童二元对立壁垒的重要途径,更是与儿童建立真正接纳与沟通的开始。
二是更为真实地揭露现实生活的多面性。有学者提出,“儿童文学的写作立场应当以儿童的有能力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适宜给儿童看的内容。”[16]如果说,曾经的成人作家试图用文学为儿童的世界筑起保护色,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信息的传播,儿童的生活经验和适应能力也在不断积累,他们已经很难不直面更多的生活现实。当下作家所书写的校园暴力以及探讨应试教育的利弊等更为真实的问题,也是儿童们的亲身经历。难能可贵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能够勇敢地表达出对成人世界冷漠与误解的反抗态度。如常新港的小说《女生苏丹》中,肖萍老师对待刘之锐的态度,使作家对刘之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作品中这样写道:“男生刘之锐很不幸。他是一粒掉在地上的瓜子。他呼吸的空气中,缺少尊严这种很重要的物质。他真的不幸。”[17]作家反复运用了“不幸”这一词,是对成人忽视和践踏儿童尊严现象所流露出的一种愤懑与悲悯,以及亟需珍视儿童生命尊严的强烈呐喊。当儿童校园小说从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角来讨论教育问题时,是对儿童的生命力量的尊重,并给予他们观察和理解生活的窗口。而正是能够更为真实地展现儿童所处生活之貌,不回避现实的阴暗,才使儿童校园小说拥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三是更为客观地给予儿童自觉判断问题的机会。佩里·诺曼德认为:“儿童文学文本的简单性只是其真相的一半,它们还有一个影子,一个无意识——对世界、对人的一种更加复杂、更完整的理解。”[18]因此,隐藏在文本中的成人叙述者,一直以来都在参与着对儿童小说价值观的引导。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在呈现童年生活真实的过程中,也在尝试将用客观的笔触描写社会现象,并给予儿童读者判断现实的机会与可能。如在周羽的小说《走过拐角才长大》中,初三女孩杨柳依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使她的性格从原来的阳光开朗变得冷漠坚强。在作品中,表现这个独特女孩的成长经历时,作家通过刻画了杨柳依面对出轨的父亲、懦弱的母亲、家庭破坏者、有势力的姑姑等人物的不同态度,真实地呈现了成人世界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择校、送礼、走后门等一系列社会怪象。对于现代都市儿童来说,这些怪象是生活中多多少少可能会接触到的“现实的一种”,而作家用零度叙事的方式将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社会现象客观还原。儿童校园通过留白,把处于人生观与世界观形成期的儿童判断是非的自觉性归还,并通过小说给予了他们接触社会一角的机会。
一部儿童校园小说,也是成人作家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校园”作为社会的缩影,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描写校园主题的儿童小说,也必然面临着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包括了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式的,对学校制度和社会现象“外冷内热”式地嘲讽和批判;也包括秦文君式的,对世界和现实的充满关切的坦白和真诚,同时,也期望作家与儿童读者在作品中能够形成一种更加亲近的互动与对话。
然而,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今天,作家自身的社会认识也会以潜在的方式在小说中呈现,并对儿童自身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建构起作用。由于主观世界的多样性,作家的社会判断、文化辨识以及生命体验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表达。应当指出的是,当下的儿童校园小说在展现校园、家庭与社会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上依然存在缺憾,特别是作家简单地把问题儿童的成因归结为“家庭离异”“师生冲突”以及让儿童接触片面化、符号化的社会真实。事实上,被作家们所省略掉的人际之间的多重互动和社会生活的立体面貌,才是能够让儿童读者感悟自我与他者的现实存在。
三、儿童校园小说审美追求的新质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模式正在悄然改变。朱自强指出:“在儿童文学这里,如果说1980年代的作家和出版人主要是为了精神生产而创作、出版着儿童文学的话,到了1990年代,人们则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谈论儿童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作家们和出版人纷纷联手为自己的出版品促销(签名售书、进校园讲演等),有的作家在各种媒体面前,发表宣传广告式的言论。”[19]而商品化时代也带来了儿童校园小说审美追求的新质,具体而言:
一是“类型化”的创作态势已经蔚然成风。商品经济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儿童校园小说的成功推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1990年代起,畅销作家杨红樱带有教育反思与贴近儿童生活的作品——“校园小说”系列:《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等,既成为市场化写作的销售神话,也影响着庞大的儿童读者群。因此,新的生产机制改变着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方式与美学追求。在商品化市场的作用下,畅销意识使得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商迷失在数字表象式的迷阵中,出现了“通俗化”“娱乐化”“类型化”的写作现象。新世纪以来,在儿童校园小说中“类型化”的创作态势已经蔚然成风。如“最励志校园小说合集”“校园幽默小说系列”“畅销校园小说三部曲”等,以各种捆绑式销售的方式,迎合了销售方一次性卖出多部图书的盈利需求以及购买方省略掉图书鉴别的惰性心理。面对各种复杂的市场乱象,中国儿童校园小说作家们如何自觉地保持对文学审美的坚守与艺术品格的坚持变得格外重要,而能否在标签化的儿童文学创作体制下保留创作初心,更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严峻考验。
二是理念设想高于人性之真的创作现象。方卫平指出儿童小说“在美学上的核心概念应该跟青春期联系在一起”[20]。儿童校园小说可谓是青春期文学的一种。也就是说,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在表现儿童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特质等方面应趋于更为复杂的呈现。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儿童在摆脱“童真”的成长过程中,对儿童化的趣味与思维的一种主动舍弃;另一方面,儿童在面对复杂的成人世界时青涩与懵懂的一种被动承受。其应以塑造具有青春期特征的儿童为主要描写对象,并具有“真诚地为儿童心理服务”的特征。因此,儿童校园小说文本创作需要谨慎地对待青春期在儿童化与成人化方面的选择矛盾,以及掌握和拿捏复杂的少男少女心理特征。然而,成人化的市场阅读需求对于塑造“完美少男少女”理念的期待,使得作家容易背弃对儿童的心理情感真实的追求。如于立极的校园小说《美丽心灵》中,讲述了一位意外失去双腿却拥有一个坚强心灵的女孩贺敏,为同龄朋友解开成长中心结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有渴望解除儿童成长中心灵之痛的美好意愿。因此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家希望借助主人公与困惑同龄人的年龄身份,来拉近自己与他们的心理距离。可是,这个堪比成人心智的少女贺敏却完全失去了儿童本身的“童心”与“童真”。她过分从容地对话同学,淡定地宽恕了过往,显然是跨越了人性和情感真实,硬生生地将少女推到了“神坛”。可见,儿童校园小说作家的创作一旦背离了人性之真,反而会拉开与儿童读者的心理距离,失去他们的信任。
三是对文学作品文学性与艺术性追求的缺失。“类型化”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以追求审美生活化和轻逸化作为艺术创作的目标。这类文学作品在书写校园时,更加注重于幽默化、日常化的书写风格,也因此赢得了儿童读者的喜爱。如周锐的校园幽默小说,通过神奇的想象和搞笑的语言将校园生活描绘得充满趣味和生机。但同时,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校园小说忽视作品在文学性和审美空间方面的深度展现,这便造成了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对轻松幽默与艺术审美追求间的失衡,使儿童读者在阅读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供不应求。事实上,文学性应当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对于高学龄儿童读者而言,他们的文学品味和审美格调都不仅仅满足于“低龄化”的幽默式小说。他们完全有能力感受《红楼梦》中文化品格和文学诗意,能够理解《哈姆雷特》中隐藏在语言与对白中的智慧和奥秘。因此,当下的儿童小说应当尊重“去儿童化”的读者群体的审美渴求,对小说文学性的要求必然不能停留在“浅语”的艺术,对文字的敏感不应停留在《淘气包马小跳》式的童言童语和校园狂欢。所以,如何回归儿童校园小说中的诗意与智慧值得深思。
儿童校园小说在美学追求的变化,离不开商业文化语境对作家群体的考验。当下的儿童校园小说创作正从儿童读者中心走向了市场中心的创作语境中。而以市场为中心的创作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带来的创作动力刺激了儿童校园小说的繁荣;另一方面,以市场为标准也意味着儿童校园小说创作走入满足市场阅读需求的桎梏中。而新的文化现实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造就了儿童校园小说创作的新格局,特别是市场反映作为文学作品评价体系,严重冲击着儿童校园小说创作的艺术鉴赏空间。多重的审美选择带来了阅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同时也暗含着深刻的反思性与警惕性。不可否认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应当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且并绝不能放弃坚守儿童校园小说中“塑造少年性格与人性”为己任的文学阵地,坚守其审美内涵。
四、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发展前瞻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校园小说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发展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可圈可点的作品还是有限的。儿童校园小说与儿童读者的情感交流依然缺乏打破壁垒的真实;儿童校园小说在面对童年生存问题时的价值判断依然忽略了儿童的声音;儿童校园小说在走进儿童阅读审美空间时依然缺乏恰当的满足。当然,成人作家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儿童的思维模式中,但是通过对“儿童本位”的坚守,成人与儿童依然可以实现精神世界的共鸣,让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离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近一些。在这种考量下,本文对其发展趋势提出如下思考:
一是需要坚守对待儿童内心的“情感之真”。尽管在儿童校园小说创作中成人作家无法真正地“去成人化”立场,但是以关注儿童的生活日常、理解他们的精神之痛和保护他们的尊严梦想,则是必不可少的创作立场。因此,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要保持与儿童对话时的那份真诚之心。在这方面,潜心儿童校园小说创作的三三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她的作品《骑单车的少女》《仙女的孩子》等,都能够以不同角度走进儿童内心,用极大的尊重观照着儿童的成长。在《骑单车的少女》中,面对心酸生活与苦难心灵的两个女孩子,在彼此身上寻找精神支撑。作家三三运用平行的视角将两个女孩隐秘的内心世界轻轻拨开,用一种近乎温情的观照使她们找寻到了彼此,作为成长中相互慰藉的力量;在《仙女的孩子》中,关注的是三个渴望亲情与关爱的留守儿童进城寻亲的故事。作品中对几个孩子的节制的怜悯与深刻的理解,使这个悲伤的故事涌动着浓厚的爱。但这种情感强度并非一种书写的放纵,而是“艺术创造过程的强度”[21]。只有真正尊重与理解儿童成长阵痛的作家,才能够真切地表达出对他们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苦难的凝视,对于他们的终极关怀也是对于成人自身的审视。无论是表现多样的校园生活现实,还是深挖儿童内心的深度,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意图始终指向对儿童灵魂的净化,因此作家更应展现出对他们的接纳和包容。同时在教育意指的驱动下,作家应对真实的儿童生命怀有更为深切的关怀与理解。这便是儿童校园小说作家需要坚守的对待儿童内心的“情感之真”。
二是需要坚守价值认同的“生命之爱”。对于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儿童来说,要使他们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与阴暗面,并不应该采用“瞒与骗”的方式。因为儿童拥有的认知社会的能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往往是高于成人想象的。如何学会用勇敢与善良的人生态度来包容世界的纷繁,如何学会用智慧与仁爱的价值认同来追求生命的纯真,便是儿童校园小说作家通过作品给予儿童读者最好的馈赠。安徒生曾说过,“爱与同情是每一个人都应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情感”[22]。儿童校园小说并不是为了让儿童的价值判断同一化,而是竭尽心力地播撒在他们心中一颗爱的种子,使他们在面对价值观的考验时,能够对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充满尊重与同情。如在徐玲的小说《全世界请原谅我》中,“全世界”便是一个青春期男孩身边所有关爱他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用耐心和爱来包容问题男孩的醒悟,让他拥有了成长中的自觉;在吴梦川的小说《尖叫的海棠》中,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少女依然找到音乐作为认知美好生命的渠道,在学会接纳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张国龙的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中,处于青春期的迷茫少女感悟到唯有爱与宽容,才能带领她走出生活阴霾。童年生命的韧性以及青春智慧的光芒,让儿童在面对生活的考验和磨砺时拥有了正向的价值认同。而儿童校园小说则需要点燃“生命之爱”的火把来帮助处于迷茫与痛苦的儿童走出阴暗,传递给他们直面生活和尊重生命的向上之力。
三是需要坚守文本创作的“艺术之美”。儿童读者在阅读审美上的需求使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感有着更高的阅读期待。这完全符合他们心理特质中对生活事物的敏感与体悟。诗意化的语言表达、意境化的气氛呈现以及朦胧化的情感诉求等等,都是儿童读者与儿童校园小说作品的双向期待。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在文本叙事贴近日常化的同时,更加注重艺术美感的追求。值得欣慰的是,当下一些儿童校园小说作品中已经呈现出了这种艺术美感。如在徐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写作美感的坚守。他的小说《少年识尽愁滋味》在关注少年的日常生活时,不断地用一些意味深远的优美词句,契合儿童的内心世界,并用艾青、席慕容等诗人的诗歌、高尔基的名言、古典诗词,以及儿童自创的诗歌,点缀在其行文中,为作品增添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内蕴和明快的节奏美。另外,找到兼顾生活化、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艺术表达形式,也是当代儿童校园小说创作需要的文学品质。在这方面,谢倩裳的小说《草长莺飞时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作品在表现女孩柳莺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面对生活,面对痛苦,面对成长时,运用意象化的语言展现生活的诗意。如莺莺面对乏味的课堂,闻到“春天变了味道”;在漫长的夏季里看到了“橙黄和绯红”排列的颜色等等。作家让莺莺在成长中,重拾了“阳光明媚、风儿香醇、鸟儿啼鸣”等生命间的感动。这种对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不仅增添了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渲染力,亦增添了儿童文学生命力。
徐调孚在《〈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序言》指出:“我们应给儿童的生活以愉快;我们应满足他们游戏的精神;我们应给予他们正确观察的能力;我们应扩展他们情绪的能力;启发他们想象的能力;训练他们的记忆,运用他们的理性;我们应增加他们对社会的关系的强度……于是,我们要给他们文学——适宜于他们的文学,他们自己的文学。”[23]当代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便是在“为儿童”的理念支撑下不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在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中,拓展了题材选择的边界,展现了价值判断的包容,重审了阅读需求的导向。创作的革新一方面代表了儿童校园小说在文学文本价值上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于儿童主体价值地位的某种隐忧。而能够坚守住创作精神的情感之真,生命之爱和艺术之美,便使得儿童校园小说创作拥有了对儿童内心世界探索的自觉,展现多面社会现实的客观以及平衡创作初心在市场化导向中的智慧。总之,中国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只有以“儿童本位”为根基,建立对于儿童生命的关照与尊重,才能创作出更具精神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