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巴蛇食象”的文本解读及其演绎
2020-02-27熊贤品
摘 要:《山海经》“巴蛇食象”传说,与《楚辞·天问》“一(有)蛇吞象,厥大何如”故事有关,都是指“长蛇吃象”。“巴蛇”与“一(有/灵)蛇”意思接近,均指异蛇。从出土文献看,汉代前除以“郙”表示“巴”之外,尚无明确的“巴”字,《山海经》“巴蛇食象”应是上述《楚辞》内容的异文,句中的“巴”可能原应读为“甫”(意为“大”),全句意为“大蛇食象”;或由于读音接近,后世传抄中改用字“甫”为“巴”,从而导致用字及字句理解产生分歧。后世在此改写基础上,将所谓“巴(一/有)蛇食象”故事地点,进一步落实到湖南岳阳或者四川地区,实则缺乏说服力。
关键词:山海经;楚辞;巴蛇食象;故事;考订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1-0059-07
俗语有“人心不足蛇吞象”,古诗有“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明罗洪先《醒世歌》),都用来形容人性贪婪。而如果追溯其渊源,则大概与《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的传说有关: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但关于“巴蛇”该如何理解,历来意见不一。现在梳理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撰为此文,并请同好赐正。
一、“巴蛇食象”的历代记载
《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之典故,在历代多有沿用,如晋左思《吴都赋》有“屠巴蛇,出象骼”之语,也见于后世《金楼子》等诸多文献,及唐柳宗元《天对》:
问:灵蛇吞象,厥骨何如?王逸曰:南方有灵蛇吞象,三年然后出其骨。灵,或作一。骨,或作大。
对:巴蛇腹象,足觌厥大。三岁遗骨,其修已号。觌,一作观。《山海经》:南海内有巴蛇,身长百寻,其色青黄赤黑。食象……。
其后宋《太平广记》卷四五六引张华《博物志》“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等文献,也多有记载。
后世文献也有对此故事的进一步演绎,如宋《太平广记》卷四四一载有唐代蒋武应象之求救、而屠巴蛇之故事:
宝历中,有蒋武者……忽有物叩门……见一猩猩跨白象……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中有巴蛇……象之经过,咸被吞噬……”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一发而中其目……俄若……蛇跃出蜿蜒……至暝蛇殒。
上述蒋武杀巴蛇之故事,无疑是从《山海经》“巴蛇食象”演绎而来。同时,历代文献也间或引用一些异事,来证明“巴蛇食象”的可能性,《太平广记》卷四五九引五代《玉堂闲话》: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干枯……见一物圆如大口……细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中,野火烧燃,坠于山下。所谓巴蛇食象,信而有之。
相似故事也见于《酉阳杂俎》、《北户录》等文献中。此外,清代《海东札记》卷三:
蛇之毒者不一种。闻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钩蛇,能以尾取物,则又巴蛇之亚也。
这里则是用“钩蛇吞鹿”,来证明“巴蛇”的可能性。上述均是引用“蛇食鹿”的异事,来证明“巴蛇食象”的可能性。不过严格说来,鹿、象之间,尚存在差别。因此有学者认为,由蛇吞鹿,来推断蛇也能吞象,稍显武断[1]433。
二、“巴蛇食象”的理解
从前文的梳理来看,历代关于“巴蛇食象”一直都有关注,一直不绝。从故事细节来看,蛇与象,一大一小,蛇如何能吃掉象,是核心所在。因此,在围绕《山海经》“巴蛇食象”之“巴蛇”的理解上,出现了不同解释,大致看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思路。
(一)物种学视角
持这种思路的学者,多认为“巴蛇”是某种具体的蛇名,其中主要是“蚦(蟒)蛇说”,晋代郭璞《山海经·海内南经》注认为:
今南方蚦蛇(按,《藏经》本作“蟒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其类也。《楚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说者云长千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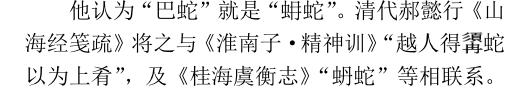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蟒蛇说”。近代学者章太炎《文始》中认为:“《说文》无蟒字,盖本作莽,古音读如姥,借为巴也”,《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工具书等也采用“巴蛇”为“蟒蛇”之说。此外,邓廷良认为,“冉字应即是巴蛇之巴的本义,所谓黑色巨蟒是也……冉即蚺字的省写”[2]144。还有学者认为“巴蛇”是五步蛇;或认为“巴蛇吞象”指蚕蛹吞食蚕茧。
(二)地理学视角
从“巴蛇”名称来看,或认为“巴蛇”就是“巴地的蛇”[3]150,进而演绎出一些“巴蛇”故事,逐渐表现出故事地域化的趋势,落实故事发生地。依笔者所见,主要有如下:
1.“巴蛇”故事发生于湖南岳阳地区。
《淮南子·本经篇》记载“羿断修蛇于洞庭”,而至晚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已经出现将“巴蛇”故事和洞庭湖地区相联系的趋势,宋《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六朝宋庾仲雍《江源记》(即《江记》):
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
唐代李白《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修蛇横洞庭,吞象臨江岛”,及张说《巴丘春作》:
日出洞庭水,春山挂断霞。江涔相映发,卉木共纷华。湘戍南浮阔,荆关北望赊。湖阴窥魍魉,丘势辨巴蛇。
至宋代,相关故事情节进一步丰富,记载也更多。宋《路史·后纪十》以“修蛇”作“长它”,罗苹注“长它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
今巴蛇,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象骨山,《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二记载,“吴人闻诸葛亮卒……增巴丘守兵万人”,胡三省注:
此巴丘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有天岳山,临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谓之巴蛇冢,相传以为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因谓之巴陵。
同书卷94记载“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胡三省注:
江陵偏在江北……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属长沙郡,后置建昌郡。《水经注》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也。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
明代《夜航船》卷二《地理部》“巴丘山”条记载,“岳州府城南。羿屠巴蛇于洞庭,积骨为丘,故名”。《水经注疏》卷三十八“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清代杨守敬按语:
《通典》巴陵,古巴邱也。宋本《寰宇记》引《江流记》“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县界有古巴邱。今巴邱山在岳州府城内西南隅,亦名天岳山。
总体而言,从六朝开始,逐渐将“巴蛇”与今湖南岳阳相联系,并影响至今。
对于岳阳地区的“巴蛇”传说,历来也有学者提出疑惑,如清黄本骥曾提出:
象出缅甸南掌诸国,中华罕有。今巴陵有象骨山、象骨港,相传为巴蛇吞象,委骨于此,山港由是得名。其说似难凭信。
但同时,他又有所动摇,他依据“《文献通考》既载唐上元间,象见华容事”,与“《华容县志》亦载,宋乾道三年,象入县城”,又认为“则岳郡有象,及巴蛇委骨之说,皆非无据”。
具体到“巴蛇”故事的湖南地域说,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尚需解释。首先,洞庭地区的“巴蛇”传说起源较晚。段渝曾认为,《楚辞》的相关记载,与《淮南子》“修蛇”、西晋郭璞所说“长千寻”的长蛇,所指相同。但“巴蛇”之说是六朝及以后出现,并非古说,与南北朝时期巴人流布到洞庭湖区域有关[4]3-19。也有学者研究了“后羿断修蛇”、“弈屠巴蛇”故事的演变,同样认为洞庭地区的认为“羿屠巴蛇”之说,是由“后羿断修蛇”演化而来的,与南朝时期巴人广泛分布于鄂湘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5]67-69。其次,从岳阳地区的地理沿革来看,可能早期为“东陵”,而之后才为“巴陵”,清代马征麟《长江图说》曾指出:
巴陵何以为东陵?曾氏彦和曰: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为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今按:巴陵之名、起于《山海经》、《淮南子》羿屠巴蛇之说,孙吴时始为巴邱邸阁,古无是称,谓之东陵而已。
从本段来看,则岳阳地区早期称为“东陵”,到三国时期才开始有“巴陵”之称。由此,则与所谓的洞庭“巴蛇”传说存在时间差。
再次,岳阳地区的“巴陵”古称,与“巴族”、“巴蛇”无关。沈祖緜认为,岳阳的“巴蛇”传说,用《山海经》“巴蛇吞象”来解释,绝不可信,她认为“巴陵”之称应源自地理,“所谓巴者,江水形势三折,故曰巴陵”[6]61。袁珂也认为:
是均从此经及《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亦已久矣[7]281。
由此,我们认为洞庭湖地区的“巴蛇”传说,产生较晚,应当与《山海经》、《楚辞》等的“巴蛇传说”无关。
2.“巴蛇”故事产生于四川地区。
也有学者将其落实到四川地区,认为先秦时期四川境内,完全有可能发生蟒蛇吞食大象的事。而段渝的意见不同,在前引用文中,他认为《海内南经》所说“巴蛇食象”,从《楚辞》等来看,“指古荆州之地,与古梁州的巴蜀之巴无关”。
综观上述立足于“巴蛇”为“巴地之蛇”的相关解释,其实还是有疑问。其中之一,如依据《山海经》的记载,内有各种异蛇,如《山海经·大荒南经》:“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山海经·大荒北经》:“大人国有大青蛇,黄头,食麈。”《山海经·海内经》也有如下记载:
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郭璞注:“即巴蛇也。”
据此,则“巴蛇”之“巴”,也应当是指这种蛇的某种特征,而非地理。其实古人也持有此思路,如晋郭璞《巴蛇赞》“象实巨兽,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由此可见,从地理学视角着眼,“巴蛇食象”故事的湖南说、巴蜀说等解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关键在于:1相关的湖南说、巴蜀说内部,存在一些还需要解释的问题。2作为立论前提的“巴蛇”之“巴”为地名说,也并不牢固。
(三)图腾学视角
潘光旦较早从图腾角度,对“巴蛇食象”进行解释,他认为巴人所在地可能出国一种大头蛇,“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8]195。他认为“巴蛇”是指人与部族,而不是蛇。此后,从此角度进行论述的学者,意见甚多,论证也更为详细,大致也分成蜀地说、湘地说两大类别。
持蜀地说的学者,如张勋燎认为“巴”本意为“鱼”,并提出后世没有注意到“巴”、“蛇”为两个部族的图腾及名称,而误以“巴蛇”为巨蛇。近来白九江也认为,“巴蛇吞象”应解释为以蛇为图腾的巴人,在发展过程中,吞并了以象为图腾的另一个部族[9]45-712-3。
持湘地说的学者,如彭适凡联系到洞庭区古族间的征战,认为“巴蛇”、“象”是不同氏族的图腾信仰、并成为氏族之称,其中“巴蛇”、“修蛇”用来称呼居住在洞庭地区的三苗;而“一蛇吞象”是说以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灭掉了以象为图腾的象氏族。杨华在此基础上,认为“巴蛇”即“巴族”,进一步提出“巴蛇食象”或指巴族捕捉大象而吃其肉,或指洞庭湖区域崇象的部落(象部),被后来进入的巴族所消灭[10]340;55-57。
也有学者在氏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或认为《天问》“一蛇吞象”指的是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即三苗),消灭了舜弟所属的象氏族。余云华则训“食”为“性爱”,将“巴蛇食象”指为“巴蛇”、“象”两个图腾氏族的男女交媾[11]70-71;99-105,但如此一来,则明显无法兼顾其后的“三岁出其骨”了。任乃强认为“巴蛇”即蟒蛇,巴族以巴蛇为图腾。由于蟒蛇主要存在于热带地区,从而提出巴族是从桂林等南方地区迁徙至长江流域的[12]236。也有学者认为,“巴蛇”是洞庭湖湖神,是越族先民图腾崇拜的产物。
关于“巴蛇食象”的图腾说解释,董其祥认为:
能够吞象的蛇是没有的,这是巴人以蛇
为图腾,幻想蛇氏族的威力可以吞象[13]21。
从这种解释来看,关于“图腾说”的运用,其实存在一种“暂且用之”的韵味,也存在一种不用原意,而用引申意的意蕴。细究来看,图腾说这一思路,其实也存在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孙华指出,目前尚未看到相关巴族蛇图腾的相关考古发现,对“巴族蛇图腾说”提出了质疑[14]361-362。笔者认为这一态度是严谨的,并且从一些学者的论述来看,如管维良等学者认为,巴族巴蛇部从巫山走出到洞庭湖北部,而以蛇为图腾[15]319。按照上述论述,则洞庭湖北部地区,应当有相关的巴文化之考古学遗迹发现,但目前其实是得不到支持的。而前引任乃强之说,也存在问题,最关键有二,(1)即使以巴蛇(蟒蛇)为图腾,也不等于直接对应本族为南方民族;(2)认为巴族是从桂林等华南地区进入长江流域的,同样缺乏考古学的支持。
第二,关于依据“巴蛇食象”,来判定巴族以蛇为图腾,此前尚存在不同意见。此外,学者还提出,巴族图腾存在从巴蛇到白虎转换之问题,这种现象是较为奇特的,而这一转换的前提之一,则是认定巴族曾经以蛇为图腾。由此,我们需要反思“巴蛇食象”,是否能反映“巴族蛇图腾说”?
第三,从文献学角度而言,“巴蛇”为图腾名之说,是否符合文献内容,值得注意。宋代吕祖谦《左氏传续说》曾认为《山海经》“巴蛇”,就是《左传》“吴为封豕长蛇”之“蛇”。近来,邹浚智认为“巴蛇”不应当为部落名,评论较为详实,我们转述其意见如下:
因为同一条记录之后还记载了巴蛇的生物特征,从这里来看便很难说“巴蛇”是某种图腾(或氏族)。另外在该条记录的前后,还可看到其他纪录里记载有各式动、植物特产……所以“巴蛇”指称的应
该还是某种蛇类[16]112。
邹先生在这里指出,“巴蛇”应当为物种名,详尽可靠,此从之。
“图腾说”视角的阐释,受到十九、二十世纪以来图腾学说的影响,和此前的角度有很大不同。但是,其问题也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巴蛇食象”图腾说的论证甚夥,实则立论前提其实非常薄弱。
三、“巴蛇食象”的文本考诠
从上述三种视角及解释出现的先后来看,物种学角度最先,地理学角度其次,而图腾学视角最晚。从相关解释的合理性来看,地理学和图腾学角度都有一些问题。相较而言,物种学角度的解释,则要少一些。
笔者以为,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立足于文本的研读。《山海经》上述记载,并非孤立,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楚辞》、《山海经》在内容上的联系,并具体指出《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的传说,与《楚辞·天问》“一(有)蛇吞象,厥大何如”有密切关系。由此,学者也开始着眼于分析上述异文,如胡小石曾赞同“有蛇”比“一蛇”为合适[17]93。
具体而言,《楚辞·天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句,但早期传本中,可能并非仅作“一蛇”,如: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引《楚辞·天问》此句,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表明其所见《楚辞》本作“有蛇”;王逸注《楚辞·天问》则引作“灵蛇吞象”。因此,我们认为,今本《楚辞·天问》“一蛇吞象”,早期或作“有(灵)蛇吞象”。
上述异文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曾进行分析,指出上述异文之产生,是由于其中存在文献错字。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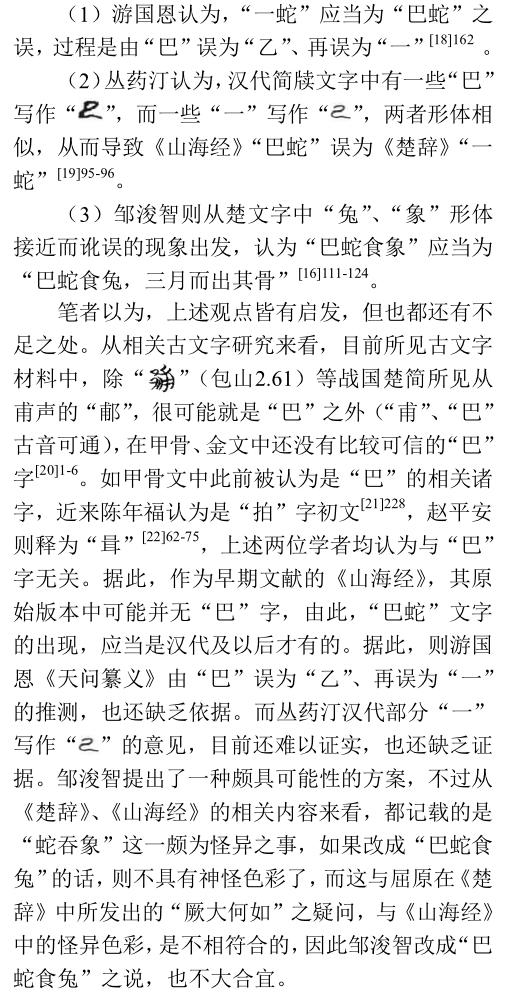
曹定云认为,甲骨文“巴”是一个象形兼会意字,表现为妇女怀孕即将临产的状况,“巴蛇食象”意指胎生的大蛇能食象[23]8-11。此处关于甲骨文“巴”的考释或可待讨论,但关于“巴蛇”为“胎生大蛇”的解释,采取不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巴蛇”的态度,则实有可取。艾露露曾比较上述异文,认为“巴蛇”是固定名词,其中“巴”为形容词,意思和“大蛇”、“长蛇”、“巨蛇”,及《淮南子 本经训》“羿断修蛇于洞庭”之“修蛇”,意思接近[24]77-95。此说颇有道理,由此,如果考虑到如下两个因素:
(1)从“巴”字汉代才出现来看,《山海经》“巴蛇”的文字写定,应该出现于汉代。
(2)“巴蛇”之“巴”应当为形容词,而“巴蛇”与“大蛇”、“长蛇”、“巨蛇”、“修蛇”等意思接近。
因而,我們认为,要理解“巴蛇”之含义,就不应当局限于“巴”的字面,而应改变、扩充思考路径。
上述《山海经》“巴蛇食象”,和《楚辞》“一(有、灵)蛇食象”(意为“大蛇吃象”)之异文,它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其中“一蛇”、“有蛇”、“灵蛇”都是用来指称可以吞象的大蛇,和《山海经》的“巴蛇”意思是接近的,只不过在具体的称谓上有些区别。若此说可以成立,则我们关于上述异文产生的过程,或可做如下推断:
(1)据前引学者研究,秦汉前,除战国楚简所见从甫声的“郙”(“甫”、“巴”古音可通),很可能就是“巴”之外,在甲骨、金文中还没有比较可信的“巴”字。
(2)也就是说,《山海经》记载的这一故事,原意很可能与《楚辞》相同,“巴蛇”也就是“大蛇”之思。从战国文字用“郙”表示“巴”来看,“甫”、“巴”古可互作[25]920,而文献中“甫”有“大”的意思,如《诗经》“无田甫田”,毛传“甫,大也”,由此“甫蛇”也就是“大蛇”。据此,我们推测今本《山海经》“巴蛇”,在古本在中可能作“甫蛇”。
(3)但是从汉代开始,汉人根据读音的联系,将《山海经》“甫蛇”改写为“巴蛇”,从而成为现今的版本,也导致人们误以《山海经》“甫(巴)蛇食象”,和《楚辞》“一(有/灵)蛇食象”(意为“大蛇吃象”)意思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推测,今本《山海经》“巴蛇食象”之“巴”,早期可能读为“甫”、意为“大”,全句意为“大蛇食象”,经由汉代人改“甫”为“巴”,表明汉人可能已经不明白其实际的含义所在,也导致后人理解上的困难。但其实际含义,与《楚辞》“一(有/灵)蛇食象”(意为“大蛇吃象”)应当是接近的。很多学者曾指出,先秦古籍都经过汉人的整理,于此或可以进一步指出,汉人对于先秦古籍的整理,其中存在一些不合适之处,本例或即为其一。
至于《山海经》“巴(甫)蛇食象”之“巴(甫)蛇”为何,目前还难以确定。游国恩曾指出《山海经》的很多记载,不可考实:
纪异物珍怪,则有……不老不死之草,巴蛇食象……种种奇谈,不可究诘[26]141。
我们认为这一态度较为可取,因此本文暂不拟具体考订“甫(巴)蛇”之实。
此前,汪长星曾认为“羿屠巴蛇”是“羿断修蛇”的误写,“巴蛇吞象”是“一蛇吞象”、“有蛇吞象”的误写,并且南北朝以后才将“蛇”、“巴”相互联系,由此他确定“羿屠巴蛇”和“巴蛇吞象”都与巴人没有关系[27]53。从上述讨论来看,我们认为汪提出“巴蛇吞象”与巴人没有关系,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的“巴蛇吞象”,意思为“大蛇吃象”,是没有任何地域信息的传说故事,其实和巴人、巴族没有关系,其中的“巴”也不是地名。由此反观此前运用此材料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包括:
(1)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楚辞·天问》“灵蛇吞象,其大如何”、《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等,均传自印度,与希腊人所传“印度有吞牛之大蛇”相类似。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楚辞》等所见“蛇吃象”的故事,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28]439。其实,依据此前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这一类型的巨蛇神话,在世界范围内甚多[29]549-551,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不同文化间的一些共性故事,而不宜用文化传播论来进行解释,用此条来论证《楚辞》受到印度文化影响,并不恰当。
(2)一些学者运用本条材料来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如有学者以之来探讨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动物地理问题[30]44,也有学者认为嘉陵江流域(亚)热带森林中的一些爬虫,可能就是吞象的蛇;由于自然条件变化,食象之蛇绝迹,而“巴蛇吞象”的传说流传下来[31]54。也有学者引用本条材料,来讨论先秦岭南及广西地区的医疗情况。现在看来,所谓“巴蛇食象”的传说,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地域信息,因此上述有关探讨,其实都是不合适的。
结语
综上,我们首先对《山海经》“巴蛇食象”的传说,进行文献考源,认为其与《楚辞·天问》“一(有)蛇吞象,厥大何如”故事有关,都是指“长蛇吃象”,“巴蛇”与“一(有/灵)蛇”意思接近,均指异蛇。其次,我们梳理历代关于“巴蛇”的理解,认为《山海经》“巴蛇食象”,应是上述《楚辞》内容的异文,从出土文献看,汉代前除以“郙”表示“巴”之外,尚无明确的“巴”字,《山海经》“巴蛇食象”中的“巴”可能原应读为“甫(意为“大”)”,意为“大蛇食象”;或由于读音接近,后世传抄中改“甫”为“巴”,从而导致字面用字及字句理解产生分歧。进而指出,后世在此改写基础上,将所谓“巴(一/有)蛇食象”故事地点,进一步落实到湖南岳阳或者四川地区,实则缺乏说服力。
注 释:
[1] 吴稚晖:《避巴小记(巴蜀考)》,《吴稚晖全集》(卷十一),九州出版社,2013年。
[2] 邓廷良:《巴与土家习俗的比较》,李绍明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3] 沈薇薇:《山海经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5] 朱圣钟:《“后羿断修蛇”为何转变为“羿屠巴蛇”》,《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6] 沈祖緜:《屈原赋证辨》,中华书局,1960年。
[7]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9]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白九江:《巴人寻根:巴人·巴国·巴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
[10]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杨华:《“巴蛇食象”新释》,《四川文物》,1996年第 6期。
[11] 龚维英:《<天问>“一蛇吞象”新解》,《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余云华:《巴蛇食象:被曲解的婚姻神话》,《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2]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14]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 管维良、李禹阶主编:《三峡学》,重庆出版社,2009年。
[16] 邹浚智:《<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新诠》,《<山海经>疑难字句新诠——以楚文字为主要视角的一种考察》,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
[17] 胡小石:《<楚辭>郭注义微》,《胡小石文史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 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
[19] 从药汀:《屈原赋辨译》(天问卷),故宫出版社,2013年。
[20] 罗小华:《试论与“巴”相关的几个问题》,《长江文明》,2014年第2期。
[21] 陈年福:《实用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
[22] 咠赵平安:《从“”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巴方”》,《文献》,2019年第5期。
[23] 曹定云:《甲骨文“巴”字补释》,《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
[24] 艾露露:《巴文化基本问题述略》,《长江文明》,2010年第2期。
[25] “甫”、“巴”均为帮纽鱼部,文献相关用例,如《史记·猼司马相如列传》“诸庶且”,《汉书 司马相如传》引作“巴”,参考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8年。
[26] 游国恩:《先秦文学·中国文学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5年。
[27] 汪长星:《三峡文化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28] [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9] 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30] 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 卫家雄、华林甫:《长江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基金项目:2018年湖南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土文献与屈赋考诠”(18YBQ081)。
作者简介:熊贤品(1986 ),男,湖北鄂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