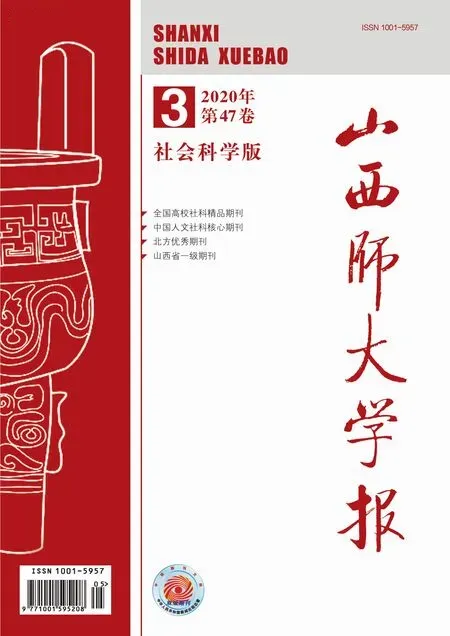康德的实践判断力“失足”的三个根源
2020-02-26王建军
王 建 军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判断力问题是康德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实践判断力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了“判断力的失足”(die Fehltritte der Urtheilskraft)或“判断的失误”(lapsus iudicii)问题[1]A135/B174,在《逻辑学反思录》中也多次提到感性、知性和理性都不会出错而只有判断力才会出错的问题。他说:“知性单独不会出错(因为它不会与自身的法则相矛盾)。感性也不会出错(因为它根本不作判断)。错误的根据必定出自其他的力。纯粹理性也不会出错”[2]250,“真理与谬误只在判断中”[2]244,“谁不作判断,谁就不会出错”[2]287。“对错”问题其实也就是真理问题,这本属于理论理性领域中的问题,但康德的判断力概念比较复杂,它不仅包括“纯粹理论理性的判断力”,还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的判断力”(他也称之为“实践判断力”[die praktische Urtheilskraft]或“道德判断力”[die moralische Urtheilskraft])。此外,康德还将这两种判断力统一于“规定性的判断力”的名下,并将后者与审美领域和目的论领域中的“反思性的判断力”相区分。反思性的判断力不是以“对错”为标准来衡量对象的,因为它并不涉及对外部对象的规定,而只涉及主体内部诸认知机能的协调;至于实践的判断力,由于它依据一定的实践法则来规定一个行为,而这种规定本身又建立在一定的实践知识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与理论理性中的判断力一样,也是以“对错”为标准的,它所做出的判断也是可错的。
那么,实践判断力是如何出错的呢?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外比较重要的相关研究例如比阿特丽丝·隆格尼塞(Béatrice Longuenesse)的《康德与判断的能力》(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罗伯特·威克斯(Robert Wicks)的《康德论判断力》(Kant on Judgement)、道格拉斯·伯恩汉姆(Douglas Bernham)的《康德的判断力哲学》(Kant's Philosophies of Judgment)、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的《道德判断力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等等都未直接触及。其中,芭芭拉提出的“义务的冲突”(conflicts of duty)虽然与此问题有一定的关联,但并未对其做正面的回应。芭芭拉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本身还不是道德规则,而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原则,它们还不能用来“设定”具体的义务,而只能用来对行为者的行动准则进行评价。她把那种与具体情境相关联的道德规则称为 “RMS”,即行为者从先前教育中所获得的“道德提醒规则”(the rules of moral salience),并认为只有它们才能设定具体的义务。由于这些规则与行动者所面对的具体情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它们会导致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从而给行动者的道德判断带来困惑。但这种“义务冲突”是导致实践判断力出错的原因吗?芭芭拉并不这么认为。她说:“对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某个冲突要素缺乏认识,并不是道德判断力的失败,而是道德意识或道德敏感性的失败。”[3]79因此,芭芭拉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实践判断力出错的根源问题,而只是从经验或教育的角度去寻求如何解决所谓的义务冲突问题以及如何提升道德的敏感性问题。关于康德的实践判断力失足的原因,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天生的判断力”缺乏
在康德那里,判断力与知性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说:“如果把一般知性解释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casus datae legis)之下。”[1]A132/B171这也就是说,判断力是知性的应用。马修·麦克安德鲁(Matthew McAndrew)指出,康德从知性规则之应用的角度来界定判断力,这在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判断力’的特殊精神能力。他将其描述为我们应用规则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康德的任何前辈的心理学中都找不到,在他自己的早期哲学中也找不到。”[4]394但这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知性为何不自己应用它所产生的规则,而必须求助于判断力这一“中介者”呢?康德认为,知性规则的应用是指向感性材料的,因而必然涉及感性,而感性是外在于知性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1]A51/B75。因此,知性规则如果要应用于感性直观,就必须借助于一个“第三者”,而判断力的特点恰好就是在一般与特殊之间进行斡旋,即为一般的东西找到特殊的事例,因而可以充当这个第三者。康德在谈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知性是规则的能力,判断力是发现特殊的东西的能力,只要这特殊的东西是规则的一个事例,那么,理性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它从普遍的东西推导出特殊的东西,并因此而按照原则来表象特殊的东西,把它表象为必然的。”[5]199这也就是说,知性只是颁布普遍的规则,而判断力与理性则都涉及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其中理性从普遍的东西中“推导出”特殊的东西,而判断力则在经验世界中为普遍的东西“发现”特殊的事例,并把这些事例“归摄”到普遍的东西之下。一个医生、一个法官或一个政治学家可以记住很多病理学、法学、政治学的正确的规则,但他们在运用这些规则时却很容易犯错,这是为什么?康德解释说:“这或者是由于他缺乏天生的判断力(虽然不缺乏知性),他虽然能抽象地看出共相,但对于一个具体情况是否属于这共相却不能辨别;或者也是由于他没有从实例和现实事务中使自己在这种判断上得到足够的校正。”[1]A134/B172f
康德也把这种天生判断力的缺乏称之为“愚笨”(Dummheit),反之,则称之为“机智”(Witz)。他说:“判断力也是所谓天赋机智的特性”,“判断力的缺乏本是我们称之为愚笨的东西,这样一种缺陷是根本无法补救的。”[1]A133/B172换言之,我们通常说某人很“机智”,这主要是从判断力的角度来说的,即此人善于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寻求联系。不过他又认为,判断力与机智本身还不是一回事,因为机智是从特殊中发现一般,而判断力是从一般中发现特殊。他说:“就像为一般的东西(规则)找出特殊的东西的能力是判断力一样,为特殊的东西想出一般的东西的能力就是机智。前者着眼于在杂多而又部分地同一的东西中察觉区别,后者着眼于杂多而又部分地不同的东西中的同一性。——二者中最杰出的才能就是察觉哪怕是最微小的类似性和不类似性。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敏锐,而这类察觉就叫作精细。……敏锐不仅受制于判断力,而且应归于机智。”[5]201判断力与机智虽然在思考方向上正好相反,但二者毕竟都是在特殊与普遍之间进行斡旋,至于它们究竟以普遍为起点还是以特殊为起点,这从实际效果上看区别不大。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机智本身是知性、想象力、判断力等多种能力参与的结果,而判断力则是一种心灵中的原始的能力。康德说:“机智把往往按照想象力(联想)的法则相距甚远的表象结合起来,是一种独特的类比能力,就知性(作为认识普遍的东西的能力)对于对象作出归类而言,它属于知性。据此,它需要判断力,以便在普遍的东西之下规定特殊的东西,并把思维能力运用于认识。”[5]220
由于判断力是天生的,所以试图通过后天的方式来改善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后天的教育和训练只能有助于判断力的“成熟”,但无法“补救”判断力的缺乏。判断力不成熟当然会产生盲目的轻信,但即便成熟的判断力也并不能弥补判断力的缺陷。这似乎很矛盾:既然缺乏判断力,还何谈判断力的成熟?在这里,缺乏判断力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判断力。在判断力缺乏的情况下,判断力仍然在做判断,而这恰恰是导致判断力“失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指出判断力的缺乏会导致心灵的孱弱和疾病。这种疾病要么是癔症(Grillenkrankheit)或疑心病(Hypochondrie),要么是心灵的失常(Gestörte)或躁狂症(Manie)。癔症之人尚能意识到自己不正常,而心灵失常之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不正常,而且还会坚持自己那些与客观现实背道而驰的主观规则,最后造成了诸认识能力的颠倒。这种颠倒如果是判断力的颠倒,则称之为“胡扯”(Wahnwitz);如果是理性的颠倒,则称之为“癫狂”(Aberwitz)。[5]202在缺乏判断力的这些疾病中,缺乏判断力同时还没有机智就叫“愚笨”(Dummheit),缺乏判断力但有机智则叫“瞎闹”(Albernheit)。[5]204
康德的这些论述是在“论灵魂在其认识能力方面的孱弱和疾病”的标题下做出的,这似乎意味着这些疾病只出现在认识领域之中,而与实践判断力没有多大关系。但康德同时也认为,这些疾病对于实践判断力会产生干扰,并且具有“支配”后者的作用,因此它们实际构成实践判断力失足的一个重要根源。他在论及诗人的气质时就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一种涉及个性的特点,亦即没有个性,而是反复无常、脾气古怪以及(没有恶意地)不守信用,故意地给自己制造敌人,其实却并不恨某人,尖刻地嘲弄自己的朋友,却并不想给他带来痛苦,这种特点就在于一种乖戾机智的禀赋,它部分地是天生的,支配着实践的判断力。”[5]249
二、行动中自由与自然的对立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伦理学的“要素论”划分为“教义学”(Dogmatik)和“决疑论”(Casuistik)两个部分。虽然他强调决疑论并不是一门科学,甚至也不是科学的一部分,而只是对应当如何寻找真理的一种练习,因而只能残缺不全地被织入科学之中,但是,决疑论问题却是一些与道德判断力直接相关的疑难问题,同时也是导致道德判断力陷入困境、甚至失足的问题。康德说:“伦理学由于准许它的不完全的义务有活动余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要求判断力去澄清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在特殊的情况中运用一个准则,确切地说使得这个准则又提供一个(从属的)准则(在这里,总是可以追问把这个准则运用于出现的情况的一个原则);这样,伦理学就陷于一种决疑论。”[6]411这段话不仅指出了决疑论问题与道德判断力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指出了这些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因为伦理学允许“不完全义务”(即可以有例外的义务)有活动的余地。
康德举例说,不可自杀属于完全的义务(即没有例外的义务),但一个人可以为了拯救祖国而自杀吗?这是一个决疑论问题。在这里,“不可自杀”本来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出现的完全的义务,因而对于判断力来说没有任何疑难存在,但是把“拯救祖国”这一不完全义务包括进来,就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了,这导致判断力对此难以做出判断。再如,“不可说谎”属于完全的义务,但一个人能否出于完全的客套而称赞别人所创作的那些平庸的艺术品?对别人的称赞也是不完全的义务,它与说谎结合在一起(通常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会让道德判断力感到左右为难。
在伦理学中准许不完全义务的存在当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这就要求判断力在涉及行为准则的运用时必须具体地考虑各种“特殊的情况”。不过康德强调,考虑特殊的情况并不表示对行为准则的例外情况的特许,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义务准则被另一个义务准则所限制的许可。
在康德那里,不完全义务包括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两个方面;前者包括自然完善性和道德完善性两个方面,后者是指对他人的爱。这些不完全的义务往往是那些用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义务。比如对他人的爱包括行善、感激、同情等,这些都与人的“祸福”紧密联系。这意味着我们即使在履行一项完全的义务时,也要兼顾他人的幸福。因此,在我们的行动之中,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使命:既要通过自由意志按照实践法则行事,同时也要考虑到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类的福祉。但这恰好表明,自由与自然的对立乃是导致形形色色的决疑论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只不过在决疑论那里这种对立是以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出现于人的行动中的自然与自由的对立明确地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判断力的“困境”。他说道:“因此从属于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之下的这种判断力看来就遭受了一些特殊的困境,这些困境来自一条自由的法则应当被应用于作为事件的行动,而这些事件又是在感官世界中发生的、因而就此而言是属于自然的。”[7]80这里所谓“作为事件的行动”(Handlungen als ßegebenheiten)是指发生在感官世界中并从属于自然的行动,但它是由善和恶的概念所引发出来的。对于一个属于自然领域的行动,它怎么可能同时又是按照作为自由法则的实践法则而发生的呢?这是实践判断力感到很困难的地方。因为根据自由的法则,意志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性的东西而仅仅通过一般法则及其形式的表象而得到规定,但现在要在这个永远都服从自然法则的感官世界中找到一种既服从自然法则又服从自由法则、同时又能将善和恶这两个超感官的理念应用于其上的事件,这怎么可能呢?
康德虽然认为这十分荒唐,但他同时也指出,实践判断力在面对这一特殊的困境时也并非束手无策。因为这个“作为事件的行动”毕竟也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即自然法则)进行的,就此而言,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即合法则性(Gesetzmä ßigkeit);另一方面,从自由法则作用于感官世界的方式来看,它也并不要求与特定的感性对象发生直接的关联,而只是与发生在感官世界中的行动发生直接关系,即作为该行动的必然的原因性。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在感官世界中的可能的行动归摄到一个纯粹实践的法则下时,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个行动作为自然事件的可能性,而只需考虑它的合法则性。这样一来,自然法则本身所具有的“合法则性”便可以一方面与纯粹实践的法则相联系,另一方面与感官世界中的客体相联系。由此,实践判断力就获得了一个将自由法则运用于自然的中介,这就是实践判断力的“模型”(Typik)。这个模型与纯粹理论理性的判断力所具有的“图型”(Schema)具有类似的中介功能,只不过前者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的中介,而后者是在感性与知性之间建立的中介。
知性范畴的图型本质上是一种方法的表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践判断力的模型同样也是一种方法的表象。因此,实践判断力的模型是以一条指导行动的规则表达出来的,即“问问你自己,你打算去做的那个行动如果按照你自己也是其一部分的自然的一条法则也应当发生的话,你是否仍然能把它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7]81?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这条规则来评判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善恶的。
这样,康德也就解决了出现在“作为事件的行动”中的自由与自然对立的难题。他指出,实践判断力的模型的提出,既可以有效地防止实践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危害,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实践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危害。在他看来,经验主义把善和恶的实践概念建立在经验性的后果(祸福)上,即它不是把这种后果看成是实践判断力的模型,而是直接看成是善恶概念本身,这就使善恶等同于祸福了。康德认为经验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将德性“连根拔除”了,而且还通过将爱好提升到实践原则的高度从而造成“对人类的贬低”。[7]83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模型只是实践法则运用于感官世界的一个可能性条件,它固然为实践判断力找到了一条打通自由与自然的通道,但这并不代表实践判断力在现实的层面上不会“失足”;相反,康德将决疑论作为德性要素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决疑论问题本身就是判断力的问题,因此包含在“作为事件的行动”中的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仍然是实践判断力失足的一个深层根源。
三、根本恶与道德判断力的“跑调”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善恶概念的论述,重点在于将它们与祸福区分开来,并指出它们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仍然强调善恶出自人的自由意志这一根本立场,但他论证的重点已发生了转变,即从人性中“根本恶”的角度来揭示善恶在人性中的起源。这是他对善恶概念理解的进一步推进,他的道德哲学也由此被引向了“道德的宗教”。
善或者恶原本是通过一定的“作为事件的行动”实现的,但根本恶并不通过行动而是通过动机被判定的恶。如果单纯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恶还可能显得是“善的”(当然只是伪善)。康德说:“如果理性仅仅是为了以幸福的名义,而将偏好的动机通常所不可能具备的准则的统一性引入到偏好的动机中去,而利用道德法则所特有的一般准则的统一性(例如,如果把真诚认定为原则,它就免除了我们对与自己的谎言保持一致,并且陷入谎言的怪圈之中的忧虑),那么,行动就依然可以产生如此符合法则的结果,就好像它们产生自真正的原则似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验性的性质是善的,而理知的性质却始终是恶的。”[6]37从动机的角度而非从结果的角度来判断善恶,这与康德一向主张的“出于义务”的义务论当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既然根本恶是发生在动机层面上的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即便没有行任何恶事,他也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因为当他自以为是清白无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自欺了。康德说:“这种自我欺骗的以及阻碍在我们心中建立真正的道德意念的不诚实,还向外扩张成为虚伪和欺骗他人;后者即使不应该称之为恶意,至少也应该叫做猥琐,它包含在人的本性的根本恶之中。”[6]38康德由此判定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他不仅引用了贺拉斯的诗:“Vitiis nemo sine nascitur (没有人生而无罪)”,而且还引用了使徒的话:“这里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全都是罪人,——没有人(凭着法则的精义)行善,就连一个都没有。”[6]39
人之所以会在动机上无一例外地出现罪错,是因为人作为感官世界与理知世界中的二重性的存在者,一方面由于其无辜的自然禀赋而依赖于感性的动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善的禀赋而对道德法则抱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人在这二者之间不能因为坚持这一个而取消另一个,但这二者毕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人就在自己的准则中将二者的关系变换成了一种主从关系,即把一方看成是另一方的条件。在经过这一番“改造”后,人的行为便会以一种“虽然合乎法则、但本身却是恶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伪善。
康德指出,在根本恶那里实际上发生了多重的“颠倒”:动机的颠倒、道德次序的颠倒、心灵的颠倒。[6]36这些颠倒最终不仅造成了思维方式的“败坏”(verderbt),而且还导致了道德判断力的“跑调”。他说:“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就道德意念而言)败坏了,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6]30。 “由于它(根本恶——引者)在应当把一个人看作什么方面让道德判断力跑了调,使责任对内对外都变得不确定。”[6]38在这里,康德用了“跑调”(verstimmen)一词,它既可以指情绪上的“扫兴、败兴”,也可以指乐器的“走调、跑调、不和谐”。一把跑调了的小提琴当然是拉不出优美的旋律的,同样,一个“跑调”了的道德判断力也是无法对善恶做出正确的判断的。道德判断力之所以会“跑调”,就是因为根本恶将道德次序和人的心灵都作了颠倒,这让道德判断力在面对错综复杂的行为动机时无所适从,从而彻底丧失基本的判别能力。当我们借助于这种跑调了的实践判断力而行动时,我们就会在意念中悄悄地将感性的动机置于道德法则之前,因而在“思维方式”上滑入康德所批判的经验主义伦理学的窠臼,即“以利益来代替义务而强加给意向”[7]83。
既然道德判断力在根本恶面前“失灵”了,那么我们又如何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康德在这里请出了人类的“良知”(Gewissen),让它在道德的宗教领域替代了道德判断力的工作。在他看来,既然人从本性上已堕入根本恶之中,而个体单凭自己的力量即便在道德法则的指引下也无力消除根本恶,那么人类就有必要联合成一个所谓的“伦理共同体”(教会)来不断提防和洗涤恶的意念。由此,康德的道德哲学也就过渡到道德的宗教。在道德的宗教中,人所面临的是“获救”问题,即通过耶稣基督自上而下的拯救,使他们从被根本恶所败坏的人性中重新将自己提升到圣洁的理想状态。不过在这种信仰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理论难题。例如既然人的本性是有缺陷的,那么他能按照圣洁的法则行事吗?他如何坚定自己善的信念而不被恶的意念所侵扰?既然根本恶永远无法根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善人也要永远遭受惩罚?这些难题显然与道德及人的自由意志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从中会引发许多需要做出道德评判的问题,例如教会的规章性法规是我们必须全部遵守的吗?强迫信众相信一些连教会上层人士都不十分确定的东西(奥秘)是道德的吗?异端审判官出于其真诚的信仰而宣判一个异端死刑是正义的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道德判断力似乎无能为力了。但康德认为,我们的“良知”却可以给出响亮的回答,它完全可以接替道德判断力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人担心人的理性借助于良知对自己的批判会太温和,那么,我相信他是大错特错了。”[6]69
什么是良知?康德说,良知就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6]184。把良知界定成为一种道德判断力,这意味着良知接替了业已“跑调”了的道德判断力的工作。当然,良知与道德判断力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良知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也就是说,它是对理性裁决的再裁决,而这显然不同于道德判断力的那种将人的具体行为置于一定道德法则之下的裁决。康德说:“良知的关系不是与一个客体的关系,而是仅仅与主体的关系。”[6]400一位宗教审判官可以裁决一个异端,宣判他死刑,但这一裁决本身仍然要受到这位审判官的良知的裁决。教会上层人士可以强迫(裁决)一个人去信仰一些奥秘,但这个裁决同样也要受到他们自己良知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康德也把良知称为“审判的良知”(richtenden Gewissen)[6]69或“作出判决的法庭(Gerichtshof)”[6]146。
良知之所以可以替代道德判断力而在面对根本恶时完成后者所不能完成的任务,除了它依靠这种指向自身的裁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良知的真正基础在于正直(Aufrichtigkeit)。一个正直的人在面对由根本恶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伪善时是不会被迷惑的。康德说:“啊,正直!你这从地上逃逸到天上的阿斯特赖亚,我们怎样才能把你(良知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内在的宗教的基础)从那里重新拉回到我们这里呢?”[5]190这种以正直为基础的良知虽然本身并不是道德情感,因为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将良知与道德情感、对邻人之爱、对自己的敬重(自重),并列为“心灵对于义务概念的易感性之感性论先行概念”[6]399,但是,良知与道德情感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一书的遗稿中,康德说:“道德情感运用于其自身的行动之上就是良知。”[8]168在《道德哲学反思录》中他也提到,满意(Zufriedenheit)、悔恨(Reue)和谴责(Vorwurf)“在行动之前叫情感,在行动之后叫良知”[9]266。因此,以良知来替代道德判断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将道德判断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
四、结语
实践判断力作为规定性的判断力,作为一种“归摄”的能力,它的根本目标与理论理性的判断力一样,都是做出“真”判断,即它要对道德行为的性质做出真判断。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主客观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实践判断力往往会出错并做出一些假判断。通过上面对实践判断力失足的三个根源的揭示,我们可以发现,判断力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道德判断其实并不容易。普通的人类理性固然不会忘记自己的道德原则并且能够在具体的事例面前分辨出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合乎义务和违背义务,但这是就包括良知在内的整个心灵的诸机能的通力合作而言的,如果单就实践判断力本身而言,它可能会因为一大堆外来的、与事情不相干的考虑而轻易地被搅乱,从而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康德最后用良知作为实践判断力的最后保障,实际上是用一种情感的评判来为理性的评判护航。这对于他的判断力学说来说当然是一种推进,但却是一种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