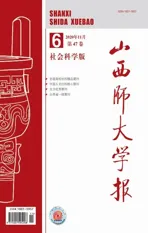社群主义视角下的网络社会信息传播治理
2020-02-26范玉吉何瑞鹏
范玉吉,何瑞鹏
(华东政法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1620)
传播技术逐渐发展为开放而多边的全球性传播网络系统,多重面向的虚拟文化在新场景中共存,传统信息传播权利正在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传播权利的研究范围也从以新闻传播为主转向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传播(1)范玉吉:《互联网背景下的“传播权”研究》,《今传媒》2018年第6期。,从一种特定的单一权利发展成为一种全面且普遍的人权概念。早期以出版自由为基础的表达权是基本人权,如今表达权已扩展到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及思想在内的综合性传播权,倾向于强调集体权利的第三代人权理论,关注的是传播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意义。
围绕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治理,学界进行了多角度、多领域的探讨。本文基于社群主义这一视角展开分析,实际上从传播权到网络空间主权、再到传播主权,不仅是适应现实新信息传播秩序下的权利需求,在社群主义理论层面更有其价值诉求和规范依据。在此基础上,从一种公共哲学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和梳理,为构建规范而理性的信息传播秩序提供可行的思路,进而保护“日益受到技术同质化影响的世界的文化多样性”(2)Howard C. Anawalt,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1985):220.。
一、网络社会的崛起:新信息传播秩序下的权利需求
从古腾堡星系到麦克卢汉星系,大众传媒文化的兴起离不开传播技术的革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普及给传统的传播模式带来了根本性改变。科克哈维(De Kerckhove)曾说过,“互联网与相关的电脑中介沟通网络的形构与扩散,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永远地塑造了新媒介的结构,包括沟通的实际模式、网络的构造以及网络使用者的文化。”(3)Derrick de Kerckhove,“Connected Intelligence: The Arrival of the Web Society”,Toronto: Somerville(1997):141.网络社会崛起的同时,人类信息传播关系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全球化视野下,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理论遭遇了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环境的现实挑战,除却技术逻辑本身催化的信息传播无界性,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也在狼奔豕突般地冲击着信息传播秩序,使得不论是新闻自由或是出版自由等传播权利都陷入了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诸多考验之中。
(一)技术—信息逻辑下传播权的演变
传播权最原始的基础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众所周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自此《世界人权宣言》为传播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人权法上的依据,即把传播权的存在基础与价值导向建立在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除此以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条也规定 “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之权利”。事实上,传播权这一概念最早是达尔西(D'Arcy)在其一篇题为《电视转播卫星与传播权利》的文章中提出的,“总有一天人们将会承认一种比《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基本人权更重要、更全面的权利概念,那就是传播权。”(4)Jean D' Arcy,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s and Right to Communicate(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1977),1.达尔西看到新技术特别是卫星技术的发展在全球通信和人权之间建立的新联系,认为任何个人都可能通过全球网络参与和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横向互动传播的时代,必须在《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内容之上寻求更加广泛的权利依据。
而后互联网技术为信息传播建立起一个无中心的网状结构,国家不再占据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网络虚拟社群间的任何节点之间都可彼此联结,传统的传输者和接收者角色转化成为可能。这印证了1990年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其著作《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中提出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概念,在信息方式的第三阶段,电子传播阶段中持续的不稳定性使得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以及多元化。(5)[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页。大量相互联结的节点削弱了曾经作为信息与舆论中心的权威,大众传播成为带有社会性的人类信息交流活动。为了有效保护传播媒介多元化倾向带来的“近用”权利,传播权较之卫星广播时代有了进一步扩展。
在这个基础上,传播权被诠释为一项基本人权。人权法理学家卡莱尔·瓦萨克(Karel Vasak)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提出了三代人权的划分理论。其中第三代人权被视为发展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权利,拓展至社群权利、民族与国家权利乃至全球公民的权利。传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强调更多的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的,可将其视作一种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产物,但是传播权则更加关注集体的利益,作为一项集体权利体现了社群主义的理念。所以在国际社会,传播权越来越被认为是同发展权、环境权等权利一样不局限于个体权利的第三代人权。从传播主体而言,传播权不但属于个人,而且也属于社群。从传播过程而言,传播权是个人和社群参与社会传播行为,搜集、表达、传输信息的利益诉求。
(二)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冲击中的网络空间主权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希腊语,本意是“无权力且秩序的社会状态”。基于消除政府以及社会、经济、文化上任何占据独裁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其核心观点是对抗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统治权威,提倡个人自由和平等。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先在性,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之一。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裹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之中,把社会的矛盾归咎于国家权威的压迫,认为只有脱离了政府的压制才能保护个人的自由与平等。
在互联网时代,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通过网络空间虚拟社群发现了更加广阔的生存土壤。1996年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发表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展示了自由主义对国家与政府的对抗。于是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秉持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观念,企图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权威、绝对自由的虚拟领域。基于网络的匿名性和开放性,近代以来规范政治生活的基础性理论预设——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打着维护“网络自由”的旗号把整个网络虚拟空间归于“全球公域”,以构建起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
无法否认的是,撇去实质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形态之别,只要国家依然发挥着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职能,能根据国家的根本利益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和享有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国家主权就会天然的存在,政治权威介入当中也是必然之果。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包括美国在内的主权国家都在积极构建自身的网络监管体系,维护国家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在网络社会中,尽管科技文明发展给国家主权的内涵与外延带来了现实挑战,但是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国家主权具有历史性和必然性。“如果看不到网络虚拟空间国家主权具有存在的客观性,那么就等于放任网络空间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网络虚拟力量无序发展,一旦网络空间负面的虚拟力量寻求到现实的突破口和发泄渠道,就会迅速造成社会动荡,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甚至发生革命战争,导致社会秩序失衡,威胁乃至颠覆现有政权。”(6)杨嵘均:《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各个国家都不会因为网络虚拟空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放弃对其的主权管辖。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明确指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我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 2015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强调“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其中就包括“尊重网络主权”原则。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总则第一条也规定该法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毫无疑问,网络空间主权是互联网背景下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传播主权:信息传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说过,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一天民主和国家将会致力于信息的控制,如同他们曾经致力于控制着领土,以及后来又为了攫取和利用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而展开争夺一样。(7)Jean 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5.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电报技术和卫星技术就已经使信息跨越边界线,传递着不同地区的文明,互联网技术则让这种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变化莫测。为了有效地规制跨国界的信息传播,我们必须认识到传播权和国家主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网络空间中虚拟社群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将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权纳入国家主权的范畴之中,使其在网络时代成为与能源、矿产、土地、人口等同等地位的战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传播主权概念并不是拘泥于网络社会的产物,而是保障信息传播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体现。
传播主权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播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对自身信息传播管理享有的最高排他权利,即独立自主占有、传播和处理信息并排除其他国家和其他组织干预的国家最高权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放弃对传播主权的重视而任其肆意流通,无异于在以经济和科技为指标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不战而退。众所周知,国家主权确立的现实意义和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和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安全与完整。基于保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目的,在内部需要发挥国家的政治职能,制定相关的制度规范来约束信息传播,在外部需要有效而合理地规制跨国界的信息传播行为,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分歧。
技术发展放大了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使得社会管理秩序和法律制度建设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人类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和安全产生了巨大冲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亟须解决的问题。网络犯罪欧洲刑警组织发布的《2017年互联网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报告中声称,全球网络攻击在过去一定阶段内的发展规模、危害程度及扩散速度可谓前所未见,机密窃取、网络诈骗、暗网交易等网络犯罪严重地威胁着国家安全。事实上,纵观当今国际形势,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也日渐重视信息的传播,利用高度发展的互联网不断拓宽传统的恐怖主义犯罪武器和犯罪模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难逃网络犯罪的侵蚀。美国著名学者帕特里克·弗兰泽兹(Patrick W. Franzese)曾在探讨网络虚拟空间的国家主权时提出,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一样,网络虚拟空间也需要规制国家主权,捍卫主权和惩戒不法参与者。(8)Patrick W. Franzese,“Sovereignty in Cyberspace:Can It Exist?”,Air Force Law Review(2009):64.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2015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5条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因此,基于社群主义理解传播主权理论必然更好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规范、理性的信息传播秩序。
综上所述,Rut治疗性给药对压力负荷型心肌肥厚同样具有改善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其增加钠钾ATP酶和钙ATP酶活性,降低CaN活性,从而调控心肌细胞内Ca2+浓度有关。
二、网络社会信息传播治理的社群主义逻辑
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 20 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种思潮,其兴起是对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主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应。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哲学的旗帜下,包括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以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内的一批社群主义者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和政治主张的分析和批驳。
当代社群主义理论哲学以社群(Community)本位、集体价值和共同的善(Common Good)为价值取向,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对于忽视整个社会稳定的极端自由放任政策采取的是否定态度。除此以外,社群主义也和新自由主义存在着显著差别。尤其是两者对于基本立场和方法的争论,与新自由主义强调“权利优先于善”“自我优先于目的”有所不同,社群主义把分析和改造社会的重心放在了对共同体的理解上。根据共同体具有优先性推导出社会集体中存在的共同的善应该先于个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社群”是一切解释的根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也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我们都深深植根于我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社会世界。(9)Daniel Bell,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1.个体需要嵌入其社会关系之中,需要同国家与民族紧紧相依。因此借助社群主义理论,我们在规范和治理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从传播权和网络空间主权发展而来的传播主权具有其必然性,更好地理解传播主权蕴含的“社群”属性及其追求的共同利益。
(一)共同的善:网络空间信息传播治理的价值诉求
“善”(Good)历来都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之一。基于人的社会性和社群构成性,社群主义将个人的私善和社群公共的善加以区分,而社群真正的善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即共同的善。共同的善划分为物化和非物化两种基本形式。其中非物化形式主要体现为各种美德,而物化形式则是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或公益。在今天的信息传播生态中,规范而理性的信息传播秩序为所有主体共同创造且被共同享有。这种共同的利益即共同的善,为信息传播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诉求。
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0)[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基于对共同体精神的诉求,网络社会只有依靠对共同的善这一价值诉求,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每一个主体的利益。以信息为连接纽带而形成的虚拟社群,是在网络虚拟空间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使得使用者达到的集群。而社群主义公益政治哲学反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带来的个体化倾向,强调社群的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倡导对于公益的维护和公共关系的关注来维持社会秩序。某种意义上,社群主义公益政治哲学为解决信息传播困境、治理网络空间秩序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源泉。
社群主义公益政治哲学以共同的善取代个人权利的首要性。其价值追求体现在国家和政治权威影响的网络虚拟空间内,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不同于契约精神中个体的理性状态,对于传播主权来说,更具有决定因素的是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共同体,即这里指的国家——一个拥有共同文化传统和情感认同的有机整体。传播主权体现了国家在网络信息传播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地享有管辖权。社群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和价值只有融入社群共同的善才是正当合理的。互联网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保障和巩固传播主权,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传播权利,更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大计和长治久安。
此外,共同的善不再局限于具有某一共同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网络虚拟社群内部,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视域。网络空间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这片领域传播,因此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每个国家命运相关、休戚与共。全球化的进程中,互联网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沟通与博弈的关键阵地。要将目光聚焦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利用开放的话语体系提供一种信息与偏好传递沟通的方式,引导正面的共同情感、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责任,推动网络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真正地让更多国家和人民从中受益。
(二)社群性权利:网络空间信息传播治理的规范依据
在与新自由主义权利观的交锋中,在对其论证的道德权利、个人权利、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批判中,社群主义理论哲学提出了一套包括政治法律权利、集体权利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社群性权利。这种“社群”本位的思想是对原子式“个体”本位思想的矫正,是将个体置于自身传统与历史联系中,致力于不同价值观念的协调。在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从内容到形式,进而到规范化运作,都迫切需要制度给予全面回应,迫切需要权利观给予其规范依据。
此外,社群主义还把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建构起集体权利观。他们虽然承认个人权利,但是更加强调集体权利的基础性和前提性,个人权利只有随着集体权利的达成而实现。其实,作为传播主权的理论来源——网络空间主权——即是脱胎于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因此传播主权天然地蕴含着集体概念和集体属性,它体现的是整个社群层面对于信息传播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此外,社群主义理论哲学在对待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时也采取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由权”一直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个体除了在必须时承担法定义务外不承担包括道德义务在内的任何义务。社群主义理论哲学认为,作为法律权利总是与义务相联系、相对等和相统一的,即个体应该承担双重义务——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即使在非道德语境中。这就意味着,在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治理中,我们应该着重考量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等性,传播主权不仅涵盖国家对外享有的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力,并借此躲避国际法上的义务,还应有保护全体公民信息传播之义务。而个体在享有信息传播权利的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履行对集体、国家的义务。
(三)积极的国家:网络空间信息传播治理的主体考量
传播主权的主体是国家,而国家历来都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命题。合群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把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社群主义也承认国家是极为重要的政治社群,并认为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社群应该承担起维护社群秩序与安全、提高与合理分配共同的善、倡导公民积极政治参与等功能。“国家以为公民提供公共利益为职责,若提供的公共利益数量太少或受众太少,这样的国家也不会被我们的公民认为是善的”(11)[美]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即是积极的国家观。这与自由主义倡导的国家观不同,一直以来,自由主义从“有限政府”到“福利国家”再到“最弱意志国家”,所秉持的都是“国家中立”的观点。约瑟夫·拉茨(Joseph Raz)这样解释“国家中立原则”:一是“排除理想”(Exclusion of Ideals),即国家不应评判生活方式的优劣;二是“中立立场”(Neutral Concern),认为国家应在公民追求不同善时保持中立。因此,社群主义积极国家观更加主张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指导,“国家中立”只会侵害共同的善的达成。
在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治理中,其中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就是国家。不论是网络空间主权还是传播主权,其权利主体也是国家,因此需要我们明确作为社群的国家的职能。在社群主义哲学看来,首先,作为政治社群的国家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为社会、为个体提供必要的公益性物品,例如公民资格、国防、基础设施、社会秩序、法律等物品,规范而理性的信息传播秩序也应是公益物品,应该允许国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维护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协调和有序;其次,国家需要进行公共投资,基于维护社会利益和公共的善,国家不应该因为投资回报低而放弃对信息传播中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再次,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培养公民的美德,尤其是培养公民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和素质品德;最后,社群主义哲学家认为国家不仅仅需要积极关心公民的公共事务,同时也应鼓励和倡导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在信息化社会,信息传播治理光靠国家力量是不足的,需要包括公民在内的各主体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网络社会,技术推动了信息的自由流动,网络空间以复杂的信息和通信为表皮包裹了我们的星球。(12)Ronald J.Deibert, Black Code: Surveillance,Privacy,and the Dark Side of the Internet(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013),11.在社群主义语境下,我们一方面强调国家在信息传播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国家主导建立“开放的话语”来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的协商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社群主义理解的国家不是单纯的权力集合体,国家拥有的传播主权既有利于个体,又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社群,其真正的、积极的价值才能实现。
三、社群主义视角下基于传播主权的治理路径
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技术逻辑影响下的互联网成为社会发展的建构性力量。传统的信息传播规范框架分散而残缺,主权理论在网络社会的新发展——传播主权的提出——正是应对当前种种桎梏的理性表达。同时借鉴刺中自由主义“阿克琉斯之踵”的社群主义理论,从方法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索网络信息传播治理规范和路径。通过对共同的善的追求,以传播主权治理可能性之实践来呼唤信息传播生态中各主体的共同预期、共同信念和共同情感认同,从而产生“共存共生感”,以凝聚治理力量之合力,使之在为人民创造健康、公平、有序的信息传播环境的同时,推动建设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一)法秩序的国家构建:强化传播主权的制度表达
社群主义哲学家认为权利的主体、内涵和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权利是国家社群法律的产物,是法律权利。因此强化传播主权的制度表达,关系到理性传播秩序的构建、文化的多样性等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被大肆宣扬的景象包括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无线通信、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占据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个无限美好的现代性的未来。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合理性占据文化的中心位置。”(13)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技术逻辑带来社会机遇的同时亦带来社会风险,因此要想保证信息传播活动的有序和自由,保障网络社会的规范和理性,离不开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来落实传播权利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主权实质上是一种法秩序的国家构建。
强化传播主权的制度表达,意味着要积极搭建一种法律性主权、制度性主权。要把传播主权从传统政治性主权的宏大叙事中超脱出来,聚焦于灵活性和规范性兼具的主权性权力之上。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上的权力,也体现在国家法视域中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国家内部来说,需要增强网络空间传播主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意识形态的领导必须适应网络社会的实际要求,而不是所谓的“中立立场”。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和政府权力,在社群内部分配机制失调或者失效时,这种权力可以成为划定、维护其分配领域边界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因此国家要强化传播主权的制度设计,体现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必须考虑以下层面:一是要尊重、保护公民正常参与信息传播活动;二是要通过公共支出提供公民参与信息传播所必需的媒介和资源;三是要采取有效预防和惩治措施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非法侵害。增强网络空间传播主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实质上正是立足于公共利益的要求,为的是捍卫稳定有序、规范理性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表达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适时地提升自身的科学性,防止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更重要的是要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深入人心地解释国家的政策部署和现实问题,为政府权力的行使树立积极、权威的形象。同时在日渐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中,大力加强网络现代化和信息安全建设,避免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切实增强网络信息控制力、规则制定力和话语权,才能巩固传播主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于“开放的话语”中培育协同治理责任与利益共同体
社群主义国家观重视作为政治社群的国家发挥积极价值,支持国家积极行使各项职能来为公民提供共同的善。因此在信息传播治理中,不可否认国家和政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关于人的社会性观点认为寻求人类之善的根本构成条件限定社会之中。因此如果脱离开语言共同体和关于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的公共讨论,人就不可能成为道德的主体,不可能成为人类之善成真的候选人。”(14)Charles Taylor,Philosophy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292.共同的善因其社群性体现的是共同体的意志目标,需要的是社群内部不同主体的广泛参与。在这个基础上,泰勒提出的“语言共同体”可为各方主体提供“开放的话语”场域,把共同利益置于核心地位,通过信息的交流与博弈机制,使得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公众能够在其中平等对话和自由讨论。
虽然网络信息传播治理将传播主权赋予了国家,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的其实是各治理主体差异化的利益认知和责任认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势力能够轻易地裹挟主体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信息传播的失序,产生诸如谣言、网络暴力、“后真相”等问题。国家在行使传播主权时,关键任务就是要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当前信息传播治理的一个重要方案,就是寻找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集体情感。这就需要立足于“开放的话语”,在传播主权引导下构架起协同治理机制以培育责任与利益之共同体,即以共同利益凝聚和激励社群中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推动主体通过协商、交流、合作的方式享受主体的权利,并履行对社群的义务,其目的是提高共同体内部“一致行动”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在传播主权优先的引导下,各治理主体积极行动构架协调治理机制。政府层面要做好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要通过其权威性来召集各个治理主体,并且从制度、资金、人员等层面推动协同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实现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资源交换和能力互补;社会层面则要强化信息传播治理组织与机构的建设,尤其在政策制定滞后的情况下发挥行业组织和机构的协调管理作用,鼓励民营的、非营利性的组织参与信息传播治理并提出解决方案;企业层面要进一步规范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接入及应用服务提供商、互联网社交内容与服务提供商等互联网相关企业的运行规则,通过技术手段、自律机制来控制和约束网络社会的信息来源和社交媒介,更好地发挥互联网企业信息枢纽的作用,遏制有害的、非法的信息肆意传播。
(三)在“去中立化”中推进公民美德教育与自律意识
正如前文所述,在社群主义的观点中共同的善非物化形式表现为各种美德。在荷马时代,美德展现的品质既为扮演社会角色所要求,也为某个明确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展现优秀所必须。社群主义理论则在美德中注入了共同体精神、公民与责任意识,并认为公民的美德离不开个体的实践。“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是对公共问题感兴趣,并投身于公共事业之中。”麦金泰尔也曾明确指出社群在公民美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美德可看作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内在于实践的利益”(15)[英]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与自由主义倡导多元论的社会,国家“中立立场”不干涉公民的价值观和美德追求不同,社群主义秉承着“去中立化”原则推进国家的公民美德教育,并推动社群的多主体发挥教育责任。这意味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治理离不开每个公民美德与素质的提升,需要一定的社会公共力量来推动。传播主权的确立与行使不仅需要制度等强制力保障,更需要公民自发的、朴素的情感与理念认同。
构建良好的网络传播秩序仅仅依靠政治宣传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在建设网络文化和信息文明的进程中,同样需要政府联合行业组织、学校共同推进公民的美德教育,充分发挥互联网中虚拟社群的自律意识和自发力量。“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16)[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苗华键、陈体仁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68页。要在网络虚拟空间注入人文关怀,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推进网络普通使用者的伦理、情感和道德与网络社会相融合,将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上升为网络规则,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以有效规范网络中的信息传播行为。“共同的善不是希望和想象力的抽象表达,他不存在于社会需要中……共同的善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永无止境的诉求,对新环境和新观点提出的问题作一种集体的回应。”(17)[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这种善并不是单一而空洞的,是社会当中每个主体的美德素养和价值方向。为了维护网络传播秩序的良好运行,必须推进公民的美德教育,培育自律意识,建立强有力的网络信息管理机制,从而为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构建创造路径和引导。
(四)网络社会共治:推进全球协动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使得互联网日渐成为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深度合作的桥梁,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所言:“信息革命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联系渠道,使国际体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18)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1998):83.如果说现行的国际法是各国集体利益的法律结果,那么在此基础上的网络空间主权性权利则应尽可能促成各国意志和利益的协调,通过建立透明的、公开的以及信赖的国际体制来实现“共同的善”,以促成国家间形成“国际共同体成员”。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时旗帜鲜明地提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质上是传播主权国际层面的行为选择,是为了克服集体行动悖论、化解意识形态分歧,同时也是为了找寻网络空间“共治权利”的规范基础。
因此要使互联网真正地惠及全球人民,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能以沟通、协商、共识的方式享受着权利,同时履行对共同体的义务。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则是将分散的虚拟社群纳入全球共同的机制体制当中协调,实现不同经济文化之间的互通互融,推动世界各国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才能最终推动网络社会的繁荣和多态化发展。只有通过构建以互联网为纽带联结全球社会的合作机制,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传播主权,以和平途径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监督解决网络社会发生的问题与挑战,才能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的公平、公正、有效治理。
在网络社会中,技术—信息逻辑的革新深刻影响着人类信息传播关系的权利构造,作为基本人权的传播权和网络发展产物的网络空间主权,进而衍生出的传播主权对于规范传播过程中的权利要求、确立传播权利的制度安排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将传播主权置于社群主义逻辑中,更能解释和理解其理论必然性和实践可能性。总而言之,将社群主义植入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治理思路中,可以在传播主权的基础上凝聚群体共识,从而为构建规范而理性的信息传播秩序提供更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