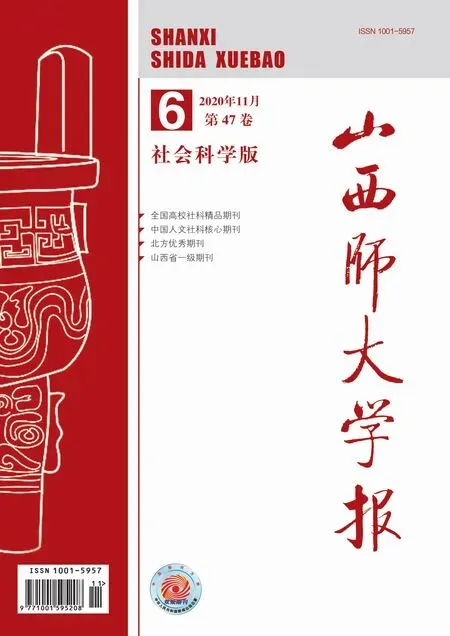通向“生活的艺术”:内哈马斯的生活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启迪
2020-02-26刘悦笛
刘 悦 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当今西方哲学和美学界,出现了一种回归“生活之道”的新的发展趋势,美国哲人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就是这种回归大势当中的重要人物,本文试图对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剖析与反思,探求它给中国哲学的基本定位带来的新的启迪。实际上,中国哲学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
一、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独树一帜的哲学贡献
亚历山大·内哈马斯是当今美国健在的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1946年生于希腊雅典,毕业于雅典学院,后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从1990年开始任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哲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主要教授柏拉图、尼采、艺术哲学、意图和行动等课程,其兴趣包括古希腊哲学、欧洲近现代哲学、艺术哲学和文学理论。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尼采:作为文学的生活》(NietxcsheLifeasLiterature)、《生活的艺术:从柏拉图到福柯的苏格拉底式反思》(TheArtofLiving:SocraticReflectionsfromPlatotoFoucault)、《本真的美德:关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论文》(VirtuesofAuthenticity:EssaysonPlatoandSocrates)、《只有幸福的允诺:美在艺术世界中的地位》(OnlyaPromiseofHappiness:ThePlaceofBeautyinaWorldofArt)和《论友谊》(OnFriendship)。他翻译成英文的柏拉图《会饮篇》和《斐德罗篇》的译本堪称权威,在普林斯顿大学曾任希腊研究项目人文理事会的主席,也是文科研究员协会的创始理事。
在欧美学界,作为当今国际哲学界成就斐然的学者内哈马斯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中国哲学界的知名度并不高,只在已翻译成中文的《当代美国哲学家访谈录》里有他的身影。这个访谈录汇集了《哈佛哲学评论》对包括约翰·罗尔斯、希拉里·普特南、哈维·曼斯菲尔德、威拉德·范·奥曼·奎因、艾伦·德肖维茨、科内尔·韦斯特、斯坦利·卡维尔、科拉·戴蒙德、理查德·罗蒂、迈克尔·桑德尔、彼得·昂格尔等哲学家的访谈,(1)[美]厄珀姆:《当代美国哲学家访谈录》,张郭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内哈马斯以其独特的思想建树也列位其中。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与作为盎格鲁撒格逊主流的“分析哲学”传统的确有距离,或者说,内哈马斯试图在分析传统之外走出另一条“哲学之路”,这种理路与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路径有内通之处。
在中国美学界,内哈马斯也没赢得应有的重视,因为他的思想取向并不属于作为欧美美学唯一主流的“分析美学”传统,就像纳尔逊·古德曼那样纯粹的科学主义立场,也不像斯坦利·卡维尔那样试图在欧陆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建立桥梁,而是深受古希腊罗马生活中哲学地位的启迪,当然也有来自尼采的内在影响,对哲学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一门纯粹的学术学科提出了质疑,认为哲学要为人们提供某种生活方式,同时,美和艺术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并不是仅有少数人感兴趣的分离领域,这使得内哈马斯在学术界之外也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实际上,内哈马斯的哲学基本取向,恰恰迎合了当今西方哲学——回归“生活之道”——的一种渐成主流的趋势。(2)刘悦笛:《走向“生活之道”的当今西方哲学——兼与孔子的“生活哲学”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0期。笔者把内哈马斯的哲学称之为“生活哲学”,并认定内哈马斯的美学具有“生活美学”取向。在哲学与美学之间,内哈马斯的思想也是贯通的。既然美学归属于哲学,一般而言,哲学家的哲学总是深刻地下贯于美学思想当中,但内哈马斯的美学却反过来上升到哲学高度,本文探索的就是其“生活哲学”的“生活美学”之维。
内哈马斯明确反对把哲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理论学科,从而与每个个人的生活失去关联,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就是逐步纯化为学术学科的历史过程,由此可以比照《论语》与《道德经》从古至今对于国人的生活启迪,而且从未失去对于日常生活的践行意义。内哈马斯试图回溯到古希腊,去哲学发源地发现新的源头,所以他在《生活的艺术》这本名著当中,以阐发苏格拉底思想为核心,认定苏格拉底并没有后来那般被哲学定型化,而所谓“生活的艺术就是苏格拉底的艺术”(3)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早期柏拉图所记载的那个“述而不作”的苏格拉底,更接近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思想,在诸如《卡西弗罗》这样的篇什当中,那位“教育”卡西弗罗关于“虔敬”的“智慧”的苏格拉底,(4)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才折射出原初的爱智者那种深邃与宽广的本真形象。因为,苏格拉底的哲学规划的合适描述,并不是被柏拉图所强化出来的“对于知识和美德的追求”(the pursuit of reason and virtue),“苏格拉底的生活的艺术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5)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
二、走向“生活哲学”:一门哲学化的“生活的艺术”
为何把哲学视为“生活的艺术”,或者将哲学之道拉回到“生活之道”上面去,道理其实异常显明而直白——“生活的艺术的哲学目的,当然是生活”(6)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当内哈马斯将生活作为哲学目的,这就是“生活哲学”;当内哈马斯把哲学当作艺术,那就是“生活美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的艺术”,既是一种超出了纯粹哲学之外的爱智之学,也是一种超越了狭窄美学之外的“大美学”。所以,“生活的艺术”,就是一种“实践的艺术”(practical art),也“在撰写当中得以实践”(practiced in writing)(7)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显然前者是要在生活当中践行的,后者则是哲学家们的事业,因为生活在他们那里还是要诉诸撰写,“留下的纪念碑是永久性的工作,而不是短暂的生活”(8)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毕竟哲学家的个性特征是通过撰写而被建构出来的。然而,真正的翻转却在于——“哲学并不仅是读书的形式,而是整个的生活之道”(9)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这才是“生活哲学”的创建所在。而且,在“生活哲学”的建构当中,“创造者与创造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0)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也就是说过程与结果乃是合一的,这个过程与结果的主语皆为生活本身,这是(包括作为一种生活的撰写在内的)生活的创造及其结果的合一。
这种哲学与美学的基本取向,在始终注重“知”与“行”合一的中国智慧那里,非常容易得到理解,而西方思想至少从柏拉图的立场就是“我们所知比我们所做的更好”(11)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生活哲学”,而从未超出生活之外,起码从孔子的“子曰时代”开始就是如此。然而,中国与欧洲思想的最内核的差异就在于,西方始终以“两个世界”的分离而追求另外一个世界,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让哲学活动建构出分离的任务”(12)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5,37,46,8,8,8,43,43,43,47.,其后柏拉图追寻“理念”世界更是如此,而中国思想则始终在不脱离生活的“一个世界”当中存在。这混糅未分的“一个世界”,就是现实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哲学家所建构而成的“另一个世界”。
这是中西思想之间的一种最基本的区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区分甚为关键,那就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始终执着于以理性为内核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中国思想从“巫史传统”脱胎而来就秉承了“情理合一”的传统。所以,哲学从哲学产生以来对于所谓“纯理性生活”(a life of pure reason)的追寻(13)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在中国思想奠基之初就不存在,内哈马斯也质疑,哲学一定是理性的学科吗?这意味着,中国思想始终没有将理性抽象得纯而又纯,理性当中始终浸渍着感性。这就是梁漱溟在兹念兹的中国人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并不是纯粹的理智,而是理化为情、情在理中,这也是晚期李泽厚为何走向“情本体”的理由。
内哈马斯却认定,西方哲学的源头与流变当中,早就有这种“生活化”的趋势,只是后来被遮蔽了罢了,这就是他对于哲学的特殊贡献所在。所以,哲学的活动,不应该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该是与生命融合为一体的,哲学要成为一种生活,即所谓的“哲学生活”。其实, 哲学生活,也是作为值得过的一种“生活形式”而存在的,但是并不是或者绝不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全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洞见的那般,只有思辨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但这种由沉思而来最值得的生活,所过的乃是“脑”的生活,而非身心本合一的生活。即便如此,思辨的生活也只是“经过审视生活”(examined life)的一种而已,这从中国哲学所隐藏的丰厚智慧那里就可以得见。
按照内哈马斯的解析,尽管“生活的艺术”具有各种变化形式,但是却具有三种基本类型,这是通过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精细解析而得出的:第一种出现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早期对话当中,尽管苏格拉底没有展示出他的“生活模式”(the mode of life)对于所有人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被审视的生活却被认定是一种值得人们过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出现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中期对话当中,特别是在《斐多篇》和《理想国》当中大量存在,这种生活模式就是被苏格拉底的生活所激发出来的,并认定这种“单一模式”(a single type of life)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最佳的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都属于这种生活的艺术传统。第三种类型认为,人类生活有很多形式,但不是每种形式都是最佳的。从蒙田、尼采到福柯这样的哲学家的“生活之路”(way of living)只是少数人所能追随的。但是通过对这种生活范式的模仿,每个人最终要成为“自我”,但是某个人与其他人的模式一定有所差异。(14)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
根据内哈马斯的“生活哲学”,尽管人们也可以去遵循与追随一种哲学化的艺术生活,也就是“参与到哲学的生活的艺术的道路”(15)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当中,然而西方那种追寻普遍主义的哲学传统却被他拒绝了。当柏拉图在《理想国》这样的核心文本当中追求理念界的时候,看似是聚焦于哲学的“永恒问题”,但是哲学于生活才是永久性的,哲学终是一种“生活”之道,当今渐居主流的生活哲学家们,就是让人们去走这种生活之“道”。
依据柏拉图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哲学生活”(philosophic life)毫无例外地诉诸每个人,每个人都将之作为最佳幸福并且有理由尽可能地去追随之。于是,“柏拉图的生活的艺术只产生出一种作品,每个人都要模仿之”(16)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柏拉图的哲学规划,由此便显露出一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色彩,但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却是极其丰富而多元的。而且,柏拉图这种“普遍主义方法”(universalist approach)却不能回应伦理、教育、政治、审美、认知和形而上学的大量问题,因为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种“生活模式”。内哈马斯却对“哲学生活”没有西方哲人那般执念,因为生活并不只是一种模式,“哲学生活”只是其中一种值得过的生活,但哲学在西方的确远离生活太远与太久了,所以就要重启生活在哲学当中的核心地位。
总之,哲学对于“如何生活”才是关键的,“哲学可能就是一种发展生活模式的努力,对于每个特定个体而言都是特殊的,而不是对其他人的模仿或者直接性的模式”(17)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然而,当内哈马斯否决普遍主义而走向一种相对主义的时候,其思想自本生根而来的个体主义与自我主义的缺憾,却显露了出来。从蒙田、尼采到福柯这样关注“自我”(self)的“生活的艺术哲学家”,从没有给定而是“建构出统一体”。(18)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当这些近代与当代哲学家“建构自我”“成为个体”,甚至是“自我风格化”(self-fashioning)(19)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的时候,这种“生活的艺术通过考察、批判和哲学观的生产来建构个人”(20)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其实还是坠入了西方思想“自我化”的藩篱当中,而不若中国思想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所保持的“中道”那般。就连苏格拉底本人规划也被内哈马斯视为“自我创造的私人计划”(private projection of self-creation) ,并被认定这种取向乃是被“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的普遍追求所赞美(21)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7,9—10,97,96,97,4,187,6,6.,由此可见,个体化的背后仍是西方理性的强权与霸权。
三、中国哲学即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以孔子哲学为考察中心
实际上,中国哲学,不仅仅是生活之道(way of being),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art of living)。儒家哲学就是“礼者履也”之生活艺术,下面以孔子哲学为例来阐明。
《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一义是履行,履而行之;二义关乎祭祀,“事神”与“致福”是也。这意味着,从本义上来说,“礼”首先是“践履”。“履,足所依也”,“礼”当然就如走路那般而有所依循,“凡有所依皆曰履”也。但这只是字义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含义为,“礼”脱胎于“祭”,从历史形成来看,中国的教是为礼教,同样也是源于“巫史”,但较之其他文明,华夏文明更早地将巫“理性化”从而形成礼制。
正如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所言:“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从示。” “示”是礼字的左半部。这个偏旁,它大概所显露的是,对神所“示”的敬意行为。礼字里面所包孕的“敬神”之义,崭露出了礼的历史根源。再来看右半部。作为繁体字的“禮”,它的右部上“曲”下“豆”,形似盛放食物的器皿,实乃“行礼之器也”。如此看来,“礼器”更是要“行履”的,是在行礼过程当中被使用的。很有可能是造字的古人,眼睛里看到了这些祭器而萌生了这个字。
礼的英文,往往是Rite抑或Ritual,将礼类似于西方宗教的那种仪式、典礼与惯例。中国的“古礼”——升、降、斋、筮、朝、觐、盥、馈、冠、婚、丧、祭、朝、聘、乡、射——无疑都是有一定成规的礼仪活动,甚至被看作繁文缛节,然而,“礼”只是中规中矩的规约吗?为何中国人总是将礼与乐并提?在所谓的“克己复礼”当中,行礼者当然要规范自己并符合于礼,这是没问题的。但与此同时,《礼记》理念所记载的那种“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却显露出行礼过程当中的充沛“美”意。
清末名流辜鸿铭居然一反西学的普遍译法,而坚持将礼翻译为——Art,也就是艺术。于是,孔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当中的礼之行,就被翻译成“the practice of art”,也就是“艺术的实践”。可是,艺术往往是自发的,当“以礼节之”之类强调礼的规范的时候,辜鸿铭则将礼翻译为“the strict principle of art”,意为“艺术的严格原则”。赞同辜鸿铭的也大有人在,《生活之艺术》是周作人的一篇名文。其中,这位大作家就认定:“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据他所言,中国古人之“礼”并非空虚无用的一套礼仪,而是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而且,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所以说,“礼”在这个意义上才是Art。这种生活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
所谓“生活之艺术”就是“微妙而美地生活”。生活被分为两种:“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他路。”(22)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语丝》1924年第1期。由此看来,道学家们倡导禁欲主义,反倒帮成纵欲而不能收调和之功。礼教才是僵硬而堕落之物,而原本的“礼”,虽节制人欲但养成自制习惯,充满了中国人本有的生活智慧: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
礼,就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行礼”,就是在践履这种“生活的艺术”。孔子的生活本身,都充满了生生之“美”意。从孔子小时开始,“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到他开始广收门徒“教之六艺”,直到晚年“西狩获麟”而感叹“吾道穷矣”,孔老夫子毕生都在实践着“礼”的生活艺术,孔子本人也达到了“通五经”而“贯六艺”的境地。
正是这位至圣先贤,“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23)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这一下子,就说出了孔子一生所做的五件事,其日常生活始终不离于“审美之情”。
第一是“树下习礼”。说的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途经宋国的东门外,在一棵巨大的檀树下习礼作乐。孔子师徒之所以过宋国而不入,乃是因宋国大司马桓魋报复孔子说其“速朽”而恐遭报复。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孔子仍不忘演习礼仪,可能主要是祭祀殷人的始祖商汤(因商丘一代乃商汤发祥之地)。这说明,孔子毕生都在践履礼仪,乐始终也是与礼并行的,这就是所谓的“礼乐相济”。
第二是“农山言志”。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东游于农山,让三人各言其志。子路说要在国难时,奋长戟率三军,钟鼓隆隆、旌旗翩翩的战场上力战却敌,为国解难。孔子赞:勇士哉!子贡说要在两军对垒之地,身着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孔子又赞:辩哉士乎!颜回笑而不语,孔子让其言志,颜回说愿得明主相之,广施德政,家给人足,永无战事。孔子当然最心仪的乃是施“礼乐之治”的颜回。
第三是“游于舞雩”。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舞雩咏归”,但“游”这个字,却点明了祭礼过程确实是令人愉悦的。在曾点鼓琴之后,那段“舞雩咏归”的著名场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为后人津津乐道,孔子就赞同曾点这种生活理想的追求。所谓“吾与曾点”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通常又称为“吾与点也”。
第四是“叹于川上”。“叹于川上”,无疑就是那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夫子对于“时间”发出的感叹,生命流逝就如流水,令人思绪万千,但真义仍在于,以水喻君子之德:“以其不息者,似乎道之流,行而无尽矣。水之德若此,是故君子必观焉。”老子似乎站在天上说“上善若水”,孔子脚踏实地在说“逝者如斯”,天地大道,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孔子并不因水逝而消极,他仍执着于践行自己的“礼乐之志”。
孔子的这一辈子,习礼作乐、郁郁从周,积极出仕、以堕三都,周游列国、四处行道,编纂六经、杏坛教学,却只给后世留下一部记载言行的《论语》,而不像春秋战国诸子那样著书立说以求不朽,他到底要干什么?答案就是:孔圣人并不是要立言的不朽,就像西方哲人那样去追寻真理,而是要对于人们的生活道理指引方向。假如孔子本人就是位哲学家的话,要知道,哲学的本意就是“希求智慧”,那么,他关注的乃是生活智慧的哲学。
孔子的哲学,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就是作为“一门生活艺术”的哲学。孔子的观点是要践行与经验的,不仅是知,而且要行。所谓“孔子之学全在乎身体力行。孔子之学是实践乎人生大道之学”(24)梁漱溟:《思索领悟辑录》,载《梁漱溟全集》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孔子将其特定的反应置于对特定视角——所生活的、所学习的和所经验的——的问题之上”(25)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8),5,5.,“孔子的观点是被感觉、被经验、被实践、被生活的。孔子兴趣在于如何践行生活的道路,而非去发现‘真理’(26)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8),5,5.”。中国智慧在于照亮生活之路,西方哲学则重于真理的发现。所以说,孔子才是“知行合一”的鼻祖,所谓“践仁履礼”正是此义。
“践仁履礼”是笔者在山西一古院所见的匾额所书,言说孔子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行“礼”,另一个是践“仁”。“习礼于树下”,是行“礼”;“言志于农山”,是赞“礼”;“游于舞雩”与“独与曾点”,同是崇“礼”,似乎孔子的生活都是不离于“礼”的,但孔子只是以自己为表率遵循与规约了自古即有的“礼”,而他自己更重要的贡献是开启了为“仁”之学。“仁”,是孔子的独特发现。这个字,大家总以为是“两个人”的意思,儒家本来就关注“人际之间”嘛,所以“人与人之间情同一体为仁”(27)梁漱溟:《思索领悟辑录》,载《梁漱溟全集》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但新近发掘的竹简却发现,“仁”字的另一个古写法则是“身”上“心”下,有身心融合为一之义,这就迥异于西方自古希腊而来的以心脑来统领身体的路数。
在孔子的生活那里,行“礼”与践“仁”,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孔子没有直接说出的东西在1993年10月发掘出来的竹简上得到了某种明示。这批珍贵的竹简是在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当中发现的。其中,被定名为《性自命出》的段落说道:“仁,内也;礼,外也。礼乐,共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这意味着,仁是内在的,礼是在外的,礼与乐是共在的。这就同《论语·八佾》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何等的近似?孔老夫子又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不仅指玉帛而言,乐也不仅指钟鼓而言,礼与乐都不能流于形式罢了。
礼,乃是孔子“外在”所行的;仁,那是孔子“内在”所养的。即使祭祀于庙堂之高,那也是外在地“施礼”,即使是隆隆乐舞如此之盛,那也是外在地“做乐”,而非内在地履“仁”,孔子将自己门派的开端,就定位在“仁”的感性基石之上。
在孔门儒学看来,关键是——让人成为人的——那种人文化成之“仁”的提升。“仁生于人”——郭店楚简的这四字,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是“仁濡化人”。中国古人常常以“体与用”关系论之,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礼乐与共,所以乐也是“仁之用”。郭店楚简又记:“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之也。”礼是交往行为的次序,乐则是生出人心或用作教化的。孔子关注的乃是,外在的礼如何伴着乐成为人人内在自觉的“人心”,也就是秉承了“仁心”的人心。
实际上,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28)钱穆:《孔子与心教》,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1—32页。但是,儒家却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准宗教,此乃由于“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中,无所谓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29)梁漱溟:《儒佛异同论》,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43页。,这实际上就是“以审美代宗教”的中国“人心”传统。
质言之,中国哲学就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从这个新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突破西方哲学目前所直面的衰落境遇,另一方面也可以返本开新地拓展出中国哲学的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