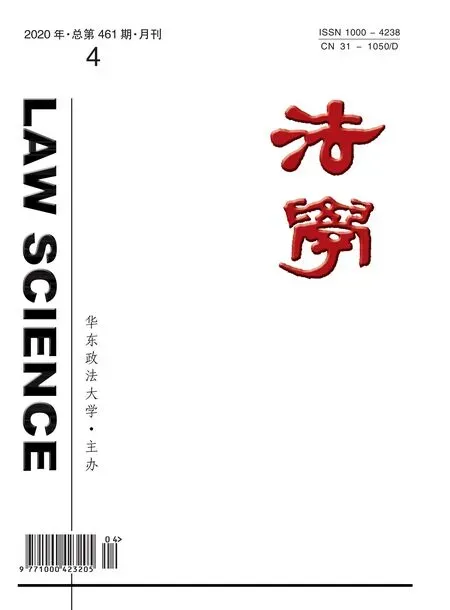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
2020-02-25陈儒丹
●陈儒丹
一、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问题的产生背景
作为国家利益的安全阀,公共秩序例外制度,又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形成于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中。但是,与其在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中的活跃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WTO法中该项制度自1995 年被规定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第14 条〔1〕GATS第14条规定:“在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类似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成员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a)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措施……”GATS原文中对(a)款例外的注释是“只有在社会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2〕TRIPS公共秩序例外规定体现在三处。首先,序言中规定了“认识到知识产权属私权;认识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其次,第8条原则方面第1款规定了“在制定或修改其法律和法规时,各成员可采用对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促进对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部门的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类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此外,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各成员可拒绝对某些发明授予专利权,如在其领土内阻止对这些发明的商业利用是维护公共秩序或道德,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所必需的,只要此种拒绝授予并非仅因为此种利用为其法律所禁止”。序言、第8条第1款和第27条第2款〔3〕See Gregory Shaffer, Recognizing Public Good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ho Participates? Who Decides? The Case of TRIPS and Pharmaceutical Patent Prot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7(2), 2004, p.459-482.和《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第23条第2款中。〔4〕GPA对公共秩序例外的规定方式几乎与GATS中的规定方式相同,其第23条第2款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对条件相同的国家造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要求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妨碍任何参加方采取或实施下列措施:为保护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或知识产权所必需的措施;或与残疾人、慈善机构或监狱囚犯产品或服务有关的措施。”沉寂十年后,直至2006年,WTO争端解决机构才在“安提瓜诉美国限制网络赌博案”〔5〕See Panel Report, US—Gambling, WT/DS285/R, paras.6.463-6.487.中首次“激活”该制度。自此之后,其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逐渐变得频繁,特别是于中国而言,在被诉时会较为频繁地使用公共秩序例外进行抗辩。2007年“欧美诉华金融信息服务案”若未能达成和解则中国必然需要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进行抗辩,〔6〕See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DS372, DS373,DS378; Angela Wang, Will China Prevail Over the Current WTO?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nal, 2009, p.212, 215-221.2007年“美国诉华知识产权案”则明确涉及公共秩序例外,〔7〕See Panel Report, China—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adopted at 26 January 2009, paras.7.125-7.135, n.126;参见宋杰:《公共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0期;Joost Pauwelyn, The Dog That Barked But Didn’t Bite: 15 Yea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t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0, p.14-15.2009年“美国诉华音像制品限制进口措施案”间接涉及公共秩序例外,〔8〕See Panel Report, China—Audiovisual Services, WT/DS363/R, adopted at 12 August 2009, paras.5.11-5.13; 参见彭岳:《贸易与道德:中美文化产品争端的法律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2010年美国意欲诉华的Google退出市场问题也曾考虑援引公共秩序例外,〔9〕参见李晨:《google暴露WTO模糊地带,中国应借机立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9日,第2版;《美官员称拟就中国审查谷歌向WTO投诉》,载新浪网2010年3月10日,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31317195997s.shtml.而中国准备加入的GPA在未来也极有可能引发公共秩序例外的适用。〔10〕参见苏玲:《商务部:希望早日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载《北京商报》2010年6月8日,第2版;《中国递交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新提议》,载新浪网2010年7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721/09508335538.shtml.那么,这些WTO条款中规定的公共秩序特指本国(措施实施方)的公共秩序还是包含了别国(措施适用对象国)的公共秩序?可否为了维护被实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实施贸易限制措施?这些问题也可称为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
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辖。域外管辖是为了本国利益,即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公共秩序而对处于外国的本国人或本国船舶实施管辖权。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则是指为了别国(被实施措施方)利益,例如,A国法律规定A国公民在B国旅游期间如有召幼妓行为,在其返回A国时将会被认为侵犯了B国的公共秩序而被A国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起诉。〔11〕See Nicolas F.Diebold, The Morals and Order Exceptions in WTO Law: Balancingthe Toothless Tiger and the Undermining Mo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7, p.70.很显然,这样一项措施将会限制B国的境外旅游服务贸易。〔12〕WTO所调整的措施并不仅仅限于民商法和经济法,也包括一个国家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刑法与行政法,如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中就涉及了中国管制盗版的刑法和行政法。如果B国向WTO起诉,声称B国不认为召幼妓行为侵犯其公共秩序,那么A国是否还可基于GATS第14条第1款(a)项的规定使该项具有限制贸易效果的措施取得正当性呢?若答案是肯定的,则A国的限制贸易自由的措施违法性显然会被削弱,败诉率就会下降。对此WTO协定中未作规定,而“安提瓜诉美国限制网络赌博案”也回避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
有学者认为:“制定国际贸易多边制度的困难实质上在于如何区分下列两种情况:一方面,一个非保护主义取向的政府不能避免某些国内政策附带地产生针对外国竞争者的歧视;另一方面,一个保护主义取向的政府使用一个合法的目的作为设计能够限制外国竞争的国内政策的借口。所以挑战就在于,设计出对这样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分反应灵敏的规则,使前者豁免,而又可以阻止后者发生。”〔13〕Aaditya Mattoo and Arvind Subramanian, Regulatory Autonomy and Multilateral Disciplines: The Dilemma and a Possible Resolution, 1 Jiel, 1998, p.303.WTO协定中所含的例外制度正是这类具有“过滤器”功能或“纱窗”功能的规则,其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价值与成员国特殊利益价值之间的平衡,孔的大小决定了成员国自由裁量余地的多寡。如果例外制度的立法和司法趋于严格,那么被告自由裁量的余地减少,败诉率就会上升,反之,被告败诉率便会下降。
捍卫被告特殊的各种非贸易价值并因此使被告享有对贸易实施合法限制权利的例外制度散见于WTO各个具体的协议中。在诸多由例外制度予以保护的非贸易价值中,公共秩序价值可谓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选项,因为“公共秩序是指对反映在公共政策和法律中的社会根本利益的维护,这些根本利益包括了法律标准、安全和道德”。〔14〕Supra note [5], paras.6.463, 6.466, 6.467.因此,若有关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例外的援引条件或适用规则都十分严苛,采取措施的一方将很难根据公共秩序例外获得豁免降低败诉率的话,则被告试图根据其他非贸易价值例外降低败诉率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具体到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上,需要以上述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争议措施在适用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关涉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对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认定与解释则关涉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争议措施的正当性能否成立并因此取得豁免,如果能证明公共秩序例外不存在域外适用效力或者对其域外适用效力应该施加严格限制,那么其他例外亦当如是。
二、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问题的学术分歧
就GATS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而言,目前直接谈及此问题的主要有Nicolas F.Diebold的文章,他认为应该拒绝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虽然关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问题几无学者涉及,但是关于与公共秩序比肩而立的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讨论则非常激烈,因为与人权和环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学者都希望将货物生产国与人权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问题,如童工问题、以虐待动物的方式生产货物问题及环境问题等,通过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规定纳入WTO法系统中,通过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促进人权主张的实现。从总体上看,目前这些学者的观点可谓是非黑即白的。
(一)反对的观点及理由
1.实施措施国与争议措施的境外目标无法形成足够强的联系
Nicolas F.Diebold认为,根据WTO的司法实践,域外适用效力通常跟域外的产品制造、加工及自然资源获取的方式(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简称PPMs)联系在一起。如同货物必须经过生产过程、服务必须经过提供过程一样,因此,提供服务的方法与提供货物的方法是可以类比的。但两者的不同在于,货物的PPMs通常是发生在国外,而服务的提供则既可能发生在国外,也有可能发生在国内,这完全取决于服务的提供模式。在GATS规定的4种服务提供模式——模式一跨境提供、模式二境外消费、模式三商业存在和模式四自然人流动——中,调整模式一和模式二的法律规则很有可能具有域外适用效力。例如,上述与模式二有关的这个例子,A国法律规定公民在B国旅游期间如有召幼妓行为,在其返回A国时将会被认为侵犯了B国的公共秩序而被A国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起诉。相反,在模式三和模式四的方式下,服务都在规制国境内提供,因此,就缺乏了潜在的域外适用效力。而且,Nicolas F.Diebold还认为,域外适用效力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争议措施的境外政策目标与实施争议措施国有足够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相关规定,该要求有被满足之可能,因为以不道德的或者对环境有损害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物理性跨越了国境,如在“美国虾龟案”中,海龟是迁移的,会游入美国领海。与之相较,在服务的场合则很难找到相同紧密程度的联系。事实上,模式二下的服务整个在国外提供并消费,与WTO争端中被告境内发生联系的只有消费者的住所和国籍,这样一种联系,紧密程度明显不够。
2.GATS的序言排除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
Nicolas F.Diebold认为,GATS的的序言规定“给予国家政策目标应有的尊重”,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有权采用新的法规,这表明在通常情况下,GATS的例外条款不可能使旨在追求被告境外的政策目标的措施取得合法性,或者只有在存在一种非常强的联系的情况下,至少其联系强度要超过根据GATT情况下保护的客体与被告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15〕同前注〔11〕,Nicolas F.Diebold文,第70-71页。
3.反对赋予公共秩序例外的邻近概念公共道德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
Lorand Bartel反对直接赋予公共道德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认为生产者的不道德生产行为在货物进口到进口国后可以导致消费者的不道德消费行为,因此,以保护本国公共道德的政策目标就可以阻止本国公民消费其他国家以不道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而影响到出口国的公共道德,从而使措施获得事实上的域外适用效力。〔16〕See Lorand Bartel, Article XX of GATT and the Problem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Case of Trad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3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02, p.353.Jagdish Bhagwati认为,WTO不适于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如果将贸易权利与劳工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结合起来的话,制裁效果经常适得其反,那么其作用就像是炮舰外交政策的GATT制裁版,将置落后的国家于不利的地位。〔17〕See Jagdish Bhagwati, Afterword, the Question of Linkage, 96 Am.J.Int’L L., 2002, p.126, 132, 133.Diego J.Linan Nogueras、Claire R.Kelly、Dexter Samida等学者则认为,适用GATT第20(a)条时,允许WTO成员将自己的公共道德概念具有域外适用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既然公共道德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性,适用这么一个主观性的概念使其具有域外适用效力将会使整个GATT保证的具有互利商业性质的优势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18〕See Diego J.Linan Nogueras & Luis M.Hinojosa Martinez, Human Rights Conditionality in the External Trad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egal and Legitimacy Problems, 7 Colum.J.Eur.L., 2001, p.307, 328; Claire R.Kelly, Enmeshment as a Theory of Compliance,37 N.Y.U.J.Int’L L.& Pol., 2005, p.303, 328; Dexter Samida, Protecting the Innocent or Protecting Special Interests? Child Labor,Globalization, and the WTO, 33 Denv.J.Int’L.& Pol’Y, 2005, p.411, 426, n.108.
(二)支持的观点及理由
学者持支持立场的观点与理由如下。Salman Bal和Steve Charnovitz认为,既然WTO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有适用于境外的情况,如GATT第20(e)条适用于外国犯人生产的产品的情况,那么公共道德例外也应可延伸而具有域外适用效力。〔19〕See Salman Bal,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Human Rights: Reinterpreting Article XX of the GATT, 10 Minn.J.Global Trade, 2001, p.62, 78; Steve Charnovitz, The Moral Exception in Trade Policy, 38 Va.J.Int’L L., 1998, p.701.Francisco Francioni则认为,如果承认公共道德例外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彻底的域外适用效力,也就是说,即使货物生产或服务提供与公共道德无直接关系,只要该出口国或服务提供国的国家行为或国家秩序在进口国或服务接受国看来是不道德的,那么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就对所有原产地是该被认为不道德的国家的产品或服务发生效力。〔20〕See Francisco Francioni,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Free Trade, in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rancesco Francioni ed., 2001, p.1, 19-20.
其实,研析上述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灰度的,在现实的复杂性与学界的认知之间存在需要被填补的鸿沟。
三、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问题的立法与司法解读
有关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灰度就在于这个问题在立法层面上并无限制,司法层面上却体现了对其的约束。
(一)GATS在立法层面并未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
WTO上诉机构于“欧盟荷尔蒙案”中认为:“将一个条约条款识别为例外条款,并不意味对该条款就应该采用严格解释或者缩小解释。对该条款的解释仍应虑及上下文的意思和条款的目的按照通常文本意义来进行解释,换句话说,仍应该按照国际法解释习惯规则进行解释。”〔21〕AB Report, EC-Hormone Decision, para.104.对GATS第14条第1款(a)项规定的公共秩序到底是否特指措施实施方的公共秩序,最有说服力的上下文可谓GATS第14条第2款之规定。
GATS第14条第1款(a)项相较于GATS第14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少了特指词“its”。GATS第14条第2款(a)项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a)要求任何成员提供其认为如披露则会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to require any Member to furnish any information, the disclosure of which it considers contrary to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与之相反,GATS第14条第1款(a)项对公共秩序例外的规定是:“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措施(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morals or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比对该两条文可以发现,第14条第1款(a)项少了两个重要的词——“it considers”和“its”。其中,特指词“its”与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密切相关,该字的缺失显然不是疏忽所致,因为WTO协定的每一个用语都可以说是协商谈判的结果,这表明至少从文本上看,GATS第14条第1款(a)项规定的公共秩序的概念在外延上并没有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不应该简单地将概念的外延缩小解释成被告国家,即采取限制贸易措施的国家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是例外条款就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对概念的外延进行限缩解释,排除掉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
(二)GATS注释5和欧盟司法实践证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
虽然GATS立法并未否定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但是根据GATS第14条第1款(a)项注释5的规定,“只有在社会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这表明公共秩序涉及社会某一根本利益,故一般需要效力级别较高的法律允以保护,通常这属于国内公法范畴,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主权行使之体现,意味着以保护措施实施对象国的公共秩序为名限制贸易似乎有干涉他国主权(尤其是他国内政)之嫌。欧盟和GATT的司法实践所体现出的对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某种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规定:“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考察GATS原文中对(a)项注释5的规定,“只有在社会的某一根本利益受到真正的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方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该援引条件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75年欧洲法院关于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案的判决中就已经形成了完全相同的解释。〔22〕See ECJ, Case 36/75 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 [1975] ECR 01219, para.28.
在1974年发生的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案中,欧洲法院首次对欧共体条约中涉及的公共秩序概念进行了司法解释,但表现得十分保守,认为“每个欧洲成员有绝对的独享的权利对本国的公共秩序的概念作出定义。公共秩序是与时空相关的概念,成员有权根据社会的演变而改变其公共秩序概念”。〔23〕Case 41/74, 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 [1974] ECR, 01337 at 01351.在一年后的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I’inte’rieur案中,欧洲法院的态度出现了迥异,认为“成员国可以自由决定本国公共秩序。但是,需要基于本国公共秩序减损条约项下的平等待遇和工人自由移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时,该公共秩序应该被严格解释。此时,不存在不受共同体机构控制的成员国的单边解释。除非另一个国家国民的存在或者其行为导致对一国的根本利益构成一种真正的、足够严重的损害,该国才可以限制另一国家的国民进入该国境内,停留或自由移动”。〔24〕Case 36/75 Rutili [1975] ECR 1219, p.28.也就是说,欧洲法院在1975年就已经形成了与GATS第14条第1款(a)项注释5规定相同的限制性条件,即援引公共秩序例外必须要满足两个特别的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是对一个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侵害;二是损害必须是真实的、足够严重的。之后,在“MRAX案”和“Gattoussi案”等案件中,欧洲法院均一字不改地重申了该限制性条件。〔25〕Case C-459/99 MRAX [2002] ECR I-6591, p.79; ECJ, Case 97/05 Mohamed Gattoussi v.Stadt Russelsheim (2006),ECR I-11917, para.41; http://csdle.lex.unict.it/Archive/LW/EU%20social%20law/EU%20case-law/Opinions/20110614-014309_Conc_C_97_05enpdf.pdf,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在这些判决中,法院认为基于公共秩序例外实施的具有限制自由贸易效果的成员国措施会潜在地削弱欧盟的结构基础,因此即使成员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定义公共秩序的概念,该公共秩序例外对于欧共体条约旨在实现的贸易自由价值所造成的实质影响应该是法院允以严格控制的对象。〔26〕Se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World Trade Agreements: Using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HR/PUB/05/5, p.10-11.
鉴于GATS第14条第1款(a)项并未对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作出明定,但是,如上所述其注释5规定的特殊援引条件源自欧盟的司法实践的影响,所以若要确定GATS第14条第1款(a)项涉及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则就有必要参考欧盟在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上的司法实践。
在欧盟的司法实践中,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1974年发生的“Dassonville案”。Dassonville将一种名为Scotch的威士忌酒从英国进口到法国,然后从法国再进口到比利时并在比利时境内销售。比利时主管机关因Dassonville未获英国海关授权其在比利时境内使用Scotch该特定名称的许可,违反了英国调整工商业贸易的法,故基于《罗马条约》第36条规定的公共秩序例外起诉了Dassonville。Dassonville辩称,比利时的措施具有类似数量限制的效果,违反了该条约第30条之规定。基于双方的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其实在于:比利时主管机关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能否基于保护英国的公共秩序而获得合法性。
欧洲法院没有审查比利时的措施是否与《罗马条约》第36条规定的例外之一相符,而是采取了一条捷径,即认为比利时的措施不能根据第36条获得合法性是因为该措施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形成了武断的、变相的贸易歧视,因为对直接从英国进口到比利时的酒和从英国转口法国进口到比利时的酒实施了歧视性待遇。
但是,该案的总法律顾问明显意识到了争议措施的域外适用效力这个问题,故认为政府要想根据《罗马条约》第36条使其争议措施获得合法性,就只能是出于保护他们自己的公共秩序的目的,而不能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保护商业财产的话,那么只能是来源国,如英国,才有权凭借 《罗马条约》 第36条,而不是进口国,如比利时。为了将其观点论述得更加透彻,总法律顾问进一步认为,一个政府也不能因为要保护其目的国的公共秩序而限制货物出口。总的来说,总法律顾问的观点就是《罗马条约》第36条只允许每个成员国仅出于保护其自己的国家利益才实施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27〕See Case 8/74, Procureur du Roi v.Benoit and Dassonville, 1974 E.C.R.837, 851, 860, 2 C.M.L.R.436 (1974);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oqp=&for=&mat=or&lgrec=en&jge=&td=%3BALL&jur=C%2CT%2CF&num=C-8%252F74&page=1&dates=&pcs=Oor&lg=&pro=&nat=or&cit=none%252CC%252CCJ%252CR%252C2008E%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true%252Cfalse%252Cfalse&language=en&avg=&cid=7948595,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61974CJ0008&from=IT, last visit on Feb.28, 2020.
1977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决定支持了总法律顾问的观点。欧盟委员会认为,即使一个成员国禁止以残忍的方法屠杀禽类,也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限制从低标准国家进口被残酷杀死的禽类。换言之,欧盟委员会认为,对公共秩序的违反只能发生在该残酷行为的实施地。从欧盟的法律实践也可看出,基于《罗马条约》第36条实施的国家行为应该只是出于保护本国的利益,而不能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利益。〔28〕同前注〔19〕,Steve Charnovitz文,第725-727页。也就是说,欧盟的法律实践否定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由此也可以推出,即使赋予GATS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也必须要对该效力进行必要的限制。
(三)GATT司法实践证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
Nicolas F.Diebold认为,基于保护被实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的争议措施要取得合法性,必须在争议措施的境外目标与争议措施实施方之间建立起足够紧密的联系。很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辖问题。因为这两者的利益维护对象是不同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是为了保护被实施措施方的利益,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管辖则是出于维护措施实施方的本国利益。
在GATT的司法实践中,虽未有直接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相关的案件,但被广泛讨论、被认为是与争议措施的域外适用效力相关的案例则有三个——美墨金枪鱼案〔29〕“美墨金枪鱼案”的起因是,适用拖网技术在东太平洋热带海域捕捞金枪鱼时,容易伤害在习性上与金枪鱼结伴而游的海豚。按照美国1972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捕捞金枪鱼时顺带捕杀的海豚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内,否则要允以制裁。1990年美国政府根据法院命令禁止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进口,由此引发本案。、美欧金枪鱼案〔30〕由于美国禁止金枪鱼及其制品进口,涉及“中间国家”金枪鱼制品对美的出口,1992年欧共体与荷兰以同样的内容提出了起诉,GATT专家组于1994年6月作出裁决报告。和美国虾龟案〔31〕海龟是一种濒危物种,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将海龟列为最高级别保护物种。渔民在适用拖网鱼船捕捞海虾时会顺带扑杀与海虾结伴而游的海龟。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海龟驱赶装置(TED),为了推广该装置,1989年美国在其1973年《濒危物种法》中增设了609条款,规定凡未能在捕虾的同时放活海龟者,就禁止该国的海虾向美国进口。1996年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联合指控美国的禁令违反了GATT1994的第1、11、13条。。管辖权基础是这三个案例的共同关键因素。领土原则决定了国家行使管辖权仅限于领土范围,也就是说,一国无权在其他国家的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行为。〔32〕See L.Oppenheim, I International Law §144a (8th ed.H.Lauterpacht 1955); Stanley J.Marcuss and Eric L.Richard,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United States Trade Law: The Need for a Consistent Theory, 20 Colum.J.Transnat’l L., 1981, p.441-443.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中对该原则作出了一定的修正,指出管辖权不能由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依据来自国际习惯或一项条约的允许性规则。而普遍接受的不存在争议的域外管辖的国际习惯只是指国家对其域外的国民和悬挂其国旗的船只行使属人管辖权。〔33〕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38页;The S.S.Lotus, [1927] P.C.I.J., ser.A, No.10, p.150.
在“美墨金枪鱼案”中,美国没有辩称其要保护的海豚在美国的领水范围内,而是声称海豚在海水里游来游去是不属于任何一个缔约方管辖的全球共享资源,这使该案专家组认为美国无权采取措施实施域外管辖。本案中,美国主张保护其领土之外的在回归线附近的东太平洋海域的海豚的政策是依据其对美国人和美国船舶的属人管辖权,对此,专家组认为,美国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美国虾龟案”中,美国所争辩的并不仅限于海龟属于“全球共享资源”,而是“除了平黑类海龟(只限于澳大利亚周围水域,并且其不属于美国609条款设计的种类)外,所有种类的海龟,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或部分时间内都生活在美国管辖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域”。〔34〕朱晓勤:《从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看环境保护单边措施的域外效力问题》,载《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2期。对此,上诉机构认为,受保护的海龟与美国建立了充分的联系,故可将其视为美国管辖范围内的动物。
由此可见,这三个案例所要求建立的关系都不是争议措施所保护的对象与争议措施所适用对象国之间的管辖权联系,而是与争议措施实施方之间的管辖权联系,也就是说,争议措施必须是为了保护本国具有管辖权的人或物或其他利益标的,而不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利益。实施措施国与措施的境外目标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决定的并不是GATT例外条款的域外适用效力取得规则,而只是域外管辖权的取得规则,即传统意义上的效果管辖权的取得规则而已。〔35〕关于效果管辖的一个经典假设性案例就是甲国A国民站在该国领土上枪杀边境对面的乙国B国民。从此角度我们也可认为,这三个案例间接地否定了对GATT例外条款的域外适用效力。
四、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建构
既然一方面GATS文本没有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另一方面GATS注释5规定、GATT的司法实践及欧盟的司法实践又证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的域外适用效力,那么随后要解决的问题便演变为如何在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允以适当的限制,即其边界该如何建构?由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是基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负面效果容易造成对他国国家主权的干涉,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排除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不当性。
根据国际法律责任的一般原理,排除不当性的情况包括同意、对抗与自卫、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以及危难或紧急状态。〔36〕参见《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五章,A/RES/56/83,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2019年8月10日访问。可见,措施实施对象国的同意是最有可能排除掉该措施不当性的理由。但是,事后的同意显然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是事前的同意,而单边的事前同意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此,最有可能排除掉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的不当性的理由就是被实施措施方曾经作出的多边性质的事前同意。换言之,如果被实施措施方与措施实施方在事前已经缔结或参加了一项涉及公共秩序的国际条约,那么基于条约的善意履行原则,当一国未履行已经批准的条约义务时,原则上其他国家就有权纠正该国家的错误行为,〔37〕See Kyle Bagwell, Petros C.Mavroidis & Rober W.Staiger, It’s a Question of Market Access, 96 Am.J.Int’L L., 2002, p.56,73-74.包括通过实施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维护被实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的方式来最终维护国际条约规定的公共秩序价值目标。
具体而言,可考虑允以下述4个条件的限制:一是国际条约必须是涉及公共秩序的;二是措施实施方与被实施措施方都属于该条约的缔约国;三是被实施措施方未履行维护条约规定的公共秩序价值的国际义务;四是措施实施方未从该项贸易限制的措施中直接或间接获利。
关于第一个条件,国际条约必须是涉及公共秩序的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之一。首先,条约中已有明确规定的。试举一个近似的例子作分析,旨在实现信息社会服务的自由流通的《欧洲电子商务指令》第3条第4款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措施减损有关信息社会服务方面的指令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的话:(a)这些措施必须是(i)基于下列理由所必需的:公共秩序,特别是阻止、调查、侦查和起诉刑事犯罪,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和反对煽动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歧视和侵犯个人尊严的斗争……”〔38〕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这些罗列的价值就构成了指令参加国的国际公共秩序。该指令序言第(22)条规定:“为了保证对公共利益目标的有效保护,信息社会服务应该由服务提供国实施监管。有必要保证信息服务提供国的主管机关不仅为了本国公民的利益而且为了共同体公民的利益提供这样的保护……”其次,条约中并未明确规定其目标价值是公共秩序,但是条约缔约国的国内法如果将这些目标价值视为公共秩序以国家根本法或以严格法律程序进行立法的话,那么也可视条约所保护的目标价值构成国际公共秩序。最后,一些众所周知的具有国际公共秩序性质倾向的国际条约,如国际劳工组织的童工指南和联合国灭绝种族罪条约等,这些条约的性质如何可由条约设立的专门组织提供解释性意见。
关于第二个条件,即措施实施方与被实施措施方同属于该条约的缔约国,这是比较容易被证明的,故而基本上无需作出解释。
关于第三个条件,即被实施措施方未实施条约规定的国际公共秩序义务应由措施实施方举证。如果当前与公共秩序有关的国际条约有执行机构的话,那么该执行机构就应该提供一份确认函来确认有义务履行条约义务的国家的履约情况。如果没有执行机构,那么原则上WTO是没有权限对该国际条约的规定进行解释的,于此情形,被指责违反了该国际义务的国家必须违反的是条约中某一条非常清晰明了的无需解释的规范(或条约义务)才行,否则,任何疑点利益都应该归于被指责违反国际公共秩序义务的国家。〔39〕See Mark Wu, Free Trad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Morals: An Analysis of the Newly Emerging Public Morals Clause Doctrine, 33 Yale J.Int’l L., 2008, p.244-247.
关于第四个条件,若措施实施方没有直接或间接从该项贸易限制的措施中获利,则这个条件的举证责任必须倒置,即应由被实施措施方提出措施实施方从该项贸易限制的措施中获利的初步证据,由措施实施方证明其未从该项措施中获利,若措施实施方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推定措施实施方从该项措施中获利,该措施就不能根据GATS第14条第1款(a)项获得正当性。如果措施仍然希望获得正当性,那么就应该考虑WTO协定的其他规定。
简而言之,如果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那么就应该基于这种效力所导致的干涉他国主权的嫌疑,而给予多边主义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定此种效力的边界。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措施实施国没有任何协定依据而单边主义地进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是经典意义上的干涉内政行为,这并非本文的讨论范畴。本文由始至终关注的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的讨论语境不是单边主义的,而是多边(涵盖少边情形)主义的,是讨论在多边协定未曾明确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时,此种效力能否当然存在,效力的产生需要满足何种构成要件或者说限制性条件的问题。例如,在GATS语境下,GATS成员对非GATS成员实施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或者反之由非GATS成员对GATS成员实施均是一种典型的单边主义的域外适用,构成经典意义上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只有措施实施国与被实施措施对象国均为GATS成员,且如上所述GATS条款并未明文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时,才涉及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问题。
由于任何条约的权利义务都是一个让步妥协形成的整体,争端解决机构无权扩大或者缩小解释,从而改变条约的谈判利益格局。而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欧盟的机构,还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均或是回避这个问题,或是在多边的语境下简单套用单边语境下的逻辑框架,或者只是简单地给出一个否定观点却未作相应的论证,这些都在客观上改变了谈判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了条约主导价值与共同体公共秩序价值之间的边界线。
任何条约谈判达成的共同体公共秩序的内涵和外延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模糊性,有赖于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得以逐步明晰与澄清,这也是一个共同体公共秩序观的塑造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被实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措施实施方的公共秩序与条约所确立的共同体公共秩序在概念与外延上应该朝着逐步同一化的方向发展。由条约规定公共秩序例外成为公共秩序的一种宪法性机制,即公共秩序的一种多边证据,在此种情况下,措施实施方基于维护被实施措施方的公共秩序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固然因域外适用效力而有干涉他国主权之嫌,但因多边条约未明确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作为事前同意的证据,条约中公共秩序概念所蕴含的共同体价值底限的内涵在性质上是一种条约遵守行为,这就同时具备了执行条约中公共秩序义务的正当性。
五、结语
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的改革和优化,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将逐步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力量,同时,政府采购也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各个国家服务法规发展程度方面存在的不平衡与国际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私权性与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政府采购协定缔约国范围的扩张与国内生产商及媒体对购买“国货”呼声的上涨之间的冲突,都使得公共秩序例外制度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缓冲地带”。
应当明确的是,公共秩序例外制度的适用结果既不能导致多边贸易制度的崩溃或减损,又不能使国家在争端解决机构的能动司法中被悄然剥夺WTO谈判形成的并表现在文本中的权利。这个双重目的的实现首先要依赖于对公共秩序的合理定位,〔40〕参见陈儒丹:《国家公共秩序还是国际公共秩序》,载《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10期。而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的合理定位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学界在公共秩序例外及相邻概念公共道德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上持有多种学术立场,既有反对意见,也有肯定意见,然而搁置这些非黑即白的立场,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去分析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灰度。在立法层面,GATS并未排除公共秩序的域外适用效力;在司法层面,GATS注释5和欧盟司法实践证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而且GATT司法实践也间接证明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虑及WTO协定的累加适用关系,GATT司法解释无疑也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故此,在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允以适当的限制才是对此种灰度的适度回应。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因干涉他国主权之嫌而被诟病为以公共秩序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为了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必须对该公共秩序施以多边主义的严格限制,即需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国际条约必须是涉及公共秩序的、措施实施方与被实施措施方都属于该条约缔约国、被实施措施方没有履行维护条约规定的公共秩序价值的国际义务和措施实施方未从该项贸易限制的措施中直接或间接获利。唯其如此,才能因为被实施措施方曾经作出的多边性质的事前同意而排除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不当性。
中国应该支持并向国际社会宣扬并强化这种对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的多边化或区域化的限制。因为在当前WTO框架体系风雨飘摇之际,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或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或披着经济制裁的外衣,泛化乃至滥用对公共秩序价值的保护显然也是政策工具之一,所以对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施加严格限制,从防御的角度看对维护中国利益殊有必要。与此同时,应该对中国的国际角色有一个动态的认知,随着中国的境外利益权重日益上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一个区域公共秩序观的共识并维护这种共识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在此方面,欧盟的经验已经验证了这种区域公共秩序观的形成对于区域发展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