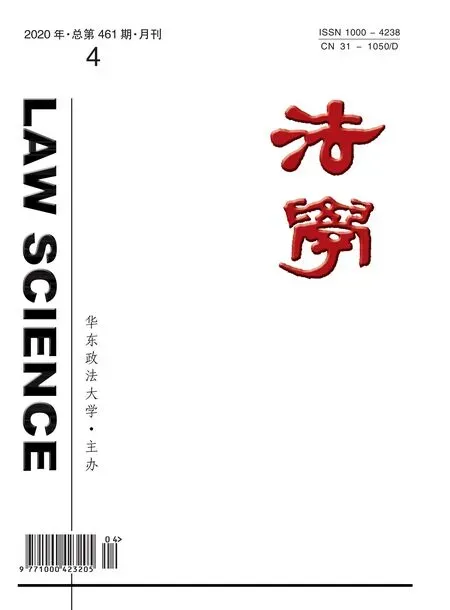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
2020-02-25刘晓红
●刘晓红
当前,全球笼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阴影中。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早在2019年1月30日(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便宣布新冠肺炎的全球性暴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伴随着疫情的愈发严重,WHO于2019年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已经构成全球“大流行”。并在短短一个月内造成全球200余个国家出现超过百万的感染者及数以万计的病患死亡,全人类正在面临一场十分严峻的挑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思考。尤其是在全球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个别国家防控不力,推诿责任,一些国家利用病毒对其他国家污名化,甚至出现国家之间的法律诉讼冲突,国际公共卫生专门机构及其规则作用缺失,又一次暴露了国际法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软肋。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国际组织和各国法律义务的承担,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如同纸上谈兵,其机制和体系形同虚设。由此看来,国际法律义务的规制及履行不啻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中的“阿喀琉斯之踵”〔1〕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指致命的弱点。阿喀琉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之子,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传说他的母亲曾把他浸在冥河里使其能刀枪不入。但因冥河水流湍急,母亲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所以脚踵是最脆弱的地方,一个致命之处,因此埋下祸根。。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治层面探究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问题。
一、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因应
(一)全球治理中的全球规制
当今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全球治理”无疑是一个高频词语。尽管“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学术概念,〔2〕参见托马斯·韦斯、罗登·威尔金森:《反思全球治理:复杂性、权威、权力和变革》,谢来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0期。但抛开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就全球治理的目标和手段而言,全球治理是一个与国际法密切相关的概念。简言之,所谓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可见,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有着密切联系,是针对全球问题所采取的跨国界协同治理,通过网状结构促进信息沟通、决策民主和作业协同。〔3〕参见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从其产生的背景来看,全球治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提出的概念,全球化过程催生全球治理。毫无疑问,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病毒传播、金融危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恐怖主义、人道主义灾难等总是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都具有跨国性或者全球性,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事务,单靠一国或少数几国的力量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基金,甚至个人等共同参与并合作应对,正所谓全球的问题全球解决。这种多主体、跨国界的行动,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合理的组织体系、法律规范和运行机制,从而形成解决全球问题的制度逻辑和行动合力,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在20世纪末的勃兴,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果,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的发展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全球规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且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谈起。〔4〕参见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0页。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手段,它超越了以往的国家治理及国际治理模式,是一套全新且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法规范与体制机制。全球化进程催生了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必然推进国际法变革。
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最佳路径是法治化。〔5〕参见姚金菊:《全球行政法的兴起:背景、成因与现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从该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也就是国际法治理,或者国际法之治。全球治理重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制度的确立,构建能够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对全球公民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是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和前提。
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国家和民族为基石的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国际法治也自此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成长环境和制度土壤,进而实现了迅速发展,现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规则体系。〔6〕参见[美]何赛E.阿尔瓦雷斯:《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蔡从燕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924-926页。然而,国际法虽然约束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际法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平等。作为全球治理主体而言,主权国家间面临的合作困境致使国家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张,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利益难免发生冲突,国际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是单个主权国家所无法应对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法的结构。〔7〕See Nico Krisch,Benedict Kingsbury,Introduc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7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 (2006).“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奠定的国际法体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国际法要想青春永驻,就应当与时俱进。〔8〕参见聂洪涛:《国际法发展视阈下非政府组织的价值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全球性非国家化问题不断产生,同时,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但它已不是唯一主要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一种新型的治理主体,这些均拓展了全球治理的议题与空间。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法治手段,国际法无疑需适应全球治理带来的新的变革需求,不仅需要不断扩大其调整领域和范围,扩充国际法主体从单一国家向多元主体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行为体对国际法的遵守与维护是提高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国际法自身正当性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二)全球治理中的平行规制:传统国际法的延续
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治的核心是规制的效力及执行问题。尽管多年前“亨金命题”〔9〕所谓亨金命题,即国际法大师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教授对国际法是否被遵守作出的判断,他指出:“几乎所有国家在几乎所有时间遵守着几乎所有的国际法规则和他们几乎所有的国际义务。” See Lou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2nd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基本解决了“国际法是否必须被遵守”的基本问题,然而“国际法能否及如何被遵守”长期以来一直拷问着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界。较国内法而言,国际法因缺少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使其呈现出一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平行规制模式。因而国际法在制定与运行的过程中,极大地依赖主权国家的自我约束,以条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协调意志的产物。〔10〕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其也被认为并不具有全然的拘束力,本质上是一种“软法”。尽管对国际法拘束力有限的批评绵延不绝,但从长期的实践看,国际法依然是约束各国行为的有力工具。不可否认,国际法并不像国内法一样存在一个超国家机构来制定和执行法律。但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看,基于协调意志而建立的国际法却时刻约束着各国,没有哪个国家会明目张胆地否定国际法,反而在利益受损后都会依据国际法提出诉求并追求权益。〔11〕参见王江雨:《权力转移、模式之争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
在国际法的制度框架下,其拘束力主要通过构建国际法责任体系加以实现。所谓国际法律责任制度,是指关于国际法责任界定、构成因素确立、免责条件、责任承担形式以及责任实施的法律原则、规则、制度的总体。〔12〕参见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随着战后国际局势的稳定,联合国率先开启了国际法的编纂工作,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第1届会议上就把国家责任问题列为其优先编纂的项目。自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开始对国家责任问题展开研究后,先后历经近半个世纪并于2001年正式通过《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该草案共4部分59条,主要涉及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形及处理、免除国家责任的因素、国家对其国际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国家责任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等。〔13〕Se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 last visit on Feb.27, 2020.
在国家责任的框架下,评判一国是否应承担国家责任大致存在以下几个环节。首先,该国应实施了国际不法行为,该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按国际法规定可以归因于行为国且该行为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14〕参见张乃根:《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其次,是否存在排除行为不法性的因素即受害国同意、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危难和危急情况。当存在上述因素时,行为国的国家责任将会被阻却。最后,在明确存在国际不法行为且不具备相应的免责因素时,依据草案规定,受害国可以主张继续履行、终止不法行为、保证不重犯、恢复原状、赔偿、抵偿和道歉,而超出上述范围的追责内容则不被国际法所接受。
因此,在传统国际法的平行规制模式下,强化国际法的拘束力是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追求。然而在以主权为基石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下,国际法只能试图通过构建国家责任体系来保障国际法的拘束力,但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国家责任体系都具有严格的条件和繁复的程序。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当出现国家主义不断强化、逆全球化有所抬头的情形下,各国通过让渡主权构建起来的国际法协调体系能否顺应全球治理的新趋势是有待观察的。
(三)全球治理中的纵向规制:全球行政法的兴起
在研究“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关系中,对全球治理过程中国际法的作用的认识出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强调国际法的作用,另一方面亦否认国际法的效力和拘束力。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对于全球治理法治化所带来的挑战,人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关系的国际法。然而,国际法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国际法存在民主赤字和参与性不足,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国际法调整范围有限并且不足以调整全球治理法治化所面对的全球行政空间。因此,与传统国际法的平行规制不同,一种强调纵向规制的全球行政法范式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中逐步兴起,其从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过渡到全球行政法的治理,从而赋予国际法合法性与权威性。
国家的行政机关会在国外空间中发挥一定的行政职能,而全球治理主体中的某些非国家行为体有时也会在全球空间中承担着一种类似公共行政机构的公共职能,这种公共职能行为需要监督,因此“国际行政法”应运而生。国际行政法是指调整多种类多层级之“规制型国际行政关系”以及“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规制跨国行政权力的行使,对履行国际公共管理职能的国际机构进行法律治理。〔15〕参见林泰、赵学清:《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然而对于所谓的国际行政法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主权制定并主要规范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法,因此即使行政法中出现涉外因素,其实它仍然属于国内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国际行政法其实就是如同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刑法等同样的国际法律部门,如有学者认为,欧盟法就是国际行政法存在的力证。可见全球治理过程中对多元行为体的治理已经促使国际法的性质出现某种变化趋势。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各种国家行为体以及某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空间中发挥着一种类似国家行政机构的公共行政职能。但是,这种国家式的行政方式是不能在全球层面大规模直接适用的,所以,某种行政法律框架就是必需的,即全球行政法。由正式的国际组织进行的行政管理是全球化行政法规的主要类型之一。〔16〕See Sabino Casses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1, 21 (2004).因此,以全球行政法之新范式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或许是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可取方式。
全球行政法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断增长的全球行政法体系正在塑造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17〕See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B.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5, 37-42 (2005).以弥补现有国际法体系下全球治理在决策程序以及可问责性等方面的不足。全球治理机构只有被公众视为合法才能繁荣发展,现阶段的全球治理决策程序往往缺少民主机制,因而合法性基础就会非常薄弱。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其诸多原则和机制都可以用于全球治理以增强其民主性与合法性,行政法原则与全球治理间具备可对接性。为了应对全球治理的诸多问题,全球行政法将国内行政法机制和理念应用于全球治理之中,进而成为实现全球善治的有效途径。
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发展与缺陷
(一)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发展
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无法独自解决病毒传播、传染病防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无法孤立地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国家利益,这便对全球治理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思考对包括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问题。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需要集体的努力和坚定的承诺,并共同付诸行动,因此要建立共同的治理机制。这必然推动国际组织的发展,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增强,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重要国际组织加强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其中也包含了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制度规则。
传染病全球蔓延是全球化的产物和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18〕[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国际公共安全卫生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国际公共安全卫生全球治理是指国家、国际组织等多元化主体通过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以解决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一种全球性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
在早期,国际卫生法制形式比较单一和零散,主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同商定相关检疫、隔离等制度,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多国相互之间缺乏稳定的协调工作机制。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851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开启了全球卫生法制体系的建立及制度化进程。从1892年开始,控制霍乱的国际卫生公约、处理鼠疫的预防性方法、提供天花和斑疹伤寒的预防、航空国际卫生公约等先后纳入国际卫生法制体系。1946年,纽约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了WHO宪章。1948年,由原有的三大国际性卫生组织合并而成的WHO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法制体系的基本成型和国际卫生公共安全全球治理的勃兴。目前,WHO共设有六大地区组织,有194个会员国, 在全球各地设立了150多个办事处,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WHO的建立和发展加快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法治化步伐,包括1969年通过和1995年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升人类健康水平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国际卫生法治体系。WHO在控制传染病、制定药物标准、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协助成员方建立卫生体系、消灭天花、扩大免疫规划,推动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的实施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就重视利用国际法来控制传染病,构建了大量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但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法在国际传染病控制中的地位下降了。“二战”后,与国际法迅猛发展的整体形势相比,有关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法却显得停滞不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面临着国际法缺位以及一种无序的多元化现象。国家接受国际准则,就必须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公平分担责任,并实施旨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有效措施。然而,国家间诸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阻碍了有效的治理。比如,面对众多的全球卫生行动机构和计划,存在各自为政和相互重叠问题,甚至陷入混乱。卫生部门往往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控制获得外国支持的规划。只有基于良好的管理制度,才能培育有效的伙伴关系和开展协调行动,发挥协同作用,避免恶性竞争。〔19〕See Lawrence Gostin & Emily A Mok, Gr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90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7, 17-18(2009).“多边体制的存在并不象征着传染病控制的有意义的全球规范的存在,相反这些体制坚守了基于各国(尤其是大国)主权至上的一种制度。”〔20〕http://jama.ama-assn.Org./cgieontent/full/291/21/#REF-JLM40007-6, last visit on March 31 2020.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基于《国际卫生条例(1969)》修订而成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目前约束WHO成员国之间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国际法。其全面规定了在应对全球性传染病方面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了《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项下重要的国际法渊源。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WHO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日渐式微,而且在财政问题上也面临严峻的融资和信任困境。〔21〕参见晋继勇:《世界卫生组织改革评析》,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 年第1 期。
(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缺陷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空前关注,2015 年联合国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3项和健康与卫生相关。〔22〕参见高明、唐丽霞、于乐荣:《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5期。但是在这次疫情面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赤字”与“短板”暴露无遗。
1.主权国家间的博弈
全球治理是合作的治理,全球治理需要主权国家在人员、资金、物资、权力等软硬资源方面的投入。然而,国家对让渡部分主权存在天然的反感,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义务和责任往往避而不谈或者消极应付,而仅仅是乐于享有全球治理合作中的权利。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难以从主权国家中获得足够政策资源,建立起充分的具有权威的约束性、惩戒性规则。
虽然同是主权国家,但因各国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程度和科技军事实力差距较大,使得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不同地位。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设计和游戏规则制定中占据绝对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人数众多,却没有话语权。传统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在法律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要求,是旧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物。可以说,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所谓的全球治理实质上是西方治理。这种治理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主导,以牺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种失衡的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少数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理。
进入21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对西方国家呈追赶之势,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盛。国际秩序由此进入转型期,很多国际规则正遭遇挑战,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由它们亲手破坏。在“美国利益至上”价值目标指引下,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到终止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再到扬言退出WTO,甚至猛烈抨击它自己领导的北约和拥有全球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然而,美国的真实意图并不仅仅是“退群”这么简单,而是希望确立更有利于己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从而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巩固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被普遍认为的是,在全球治理的各种结构、机构和实践中获得的权力差异正在被逆转,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23〕See Rita Abrah Amsen,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s in Global Governance, 25 Third World Quarterly 1453, 1453 (2004).进而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主导的单边主义潮流盛行,多边主义体制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受挫。
如前所述,《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国际卫生公共安全治理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法律规则。然而,从WHO在修订该条例时的情况来看,与其他诸多国际规则制定情形如出一辙,该条例立法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各缔约国的权力让与,重点是如何确保会员国主权与世界卫生组织职权之间的平衡,即成员国如何让渡部分主权权力给 WHO,使其能够在公共卫生问题领域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一方面,主权让渡下,成员国不能独享域内的公共卫生信息,不能任意地处理域内的公共卫生事务;另一方面,WHO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源以推动集体行动使成员国获益,但WHO 权力扩张的程度不至于挑战成员国割舍主权的容忍边界。由此可见,《国际卫生条例(2005)》关于主权议题争议的立法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 WHO 在国际公共卫生立法层面上就主权议题获得的利益均衡的博弈结果。然而,该种博弈是否能真正奏效并不在于条文本身,尚待实施中加以检验。正如有学者所言,就主权议题的争议,“需要成员国为了全人类公共卫生健康而放弃或割让国家主权以致使 《国际卫生条例(2005)》成为真正的国际法还要憧憬一段时间”。〔24〕Eric Mack,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ncursion on State Sovereignty and Ill-Fated Response to Global Health Issues.7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5, 377 (2006).
2.规则的缺失、碎片化以及叠加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机构,WHO除了在《国际公共卫生公约》的基础上制定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之外,很少利用国际法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规制。WHO代表了全球性的卫生专家队伍和技术力量,依托《国际卫生条例》等规范指导各国的传染病防治行动。但是,WHO轻法律倾向,以及各成员国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使它没有在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法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
而其他国际组织却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公共卫生治理,全球治理政策规则分散凌乱,难以形成体系和合力。比如,WTO通过其争端解决机制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裁决,事实上成为了国际传染病控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权事务委员会等通过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等对公共卫生治理施加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担当了公共卫生治理的资金渠道;当然,还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等直接分担公共卫生治理的职责。
众多的国际组织看起来能够填补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诸多欠缺和空白,似乎更加有法可依,但是这些具有法律权威的多边组织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扩张和渗透,导致了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法以一种无计划的、多方向的方式发展。尤其是随着过多的国际组织占有公共卫生立法资源,并设定其他主体参与国际卫生立法程序,使得国际立法分散失调和效率低下。2002年WHO的一项布告指出:“由于有许多国际组织分享与卫生有关的问题上的立法权威,发布指令与施加义务的努力容易分散和无效”,〔25〕Coordinating of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at http//www.scielosp.org/se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0042-96862002001200001.last visit on March 31, 2020.规则的叠加和矛盾使国际责任的承担无所适从,或成为逃避的借口。
卢布尔雅那是一座喜爱“龙”的城市,不过这条“斯洛文尼亚龙”和我们的“中国龙”长得可不一样——它有一对大大的翅膀。在古城内的建筑上,经常可以看到以“龙”为元素的装饰物,而最著名的“龙”,是始建于20世纪初的龙桥——这座城市的象征之一。
3.软法缺少拘束力
自成立以来,WHO颁布了大量包括传染病控制、环境卫生标准、反生物恐怖主义及医药方面的各种决议、标准、建议和指南,形成了庞大的软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国际软法”具有制度空间拓展性。由于各国制度差异和价值不同,一些含有人类共同法治理念的高标准国际规则难以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台,对此可利用“国际软法”所具有的多样性、灵活性、协调性等优势特性。然而,尽管软法的影响力实然存在,但其不享有外部强制力的保障。软法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法律拘束力,仅仅靠成员国自愿遵守。这主要基于软法的制定主体一般不是国家,其不具备国家强制力,软法一般是共同体内所有成员自愿达成的契约与协议,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26〕参见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与WHO同步发展起来的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粮农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相比,在当前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WHO对于发展国际条约或协定等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持一种消极的态度,WHO以及成员国都不太愿意用国际法来创设具有约束力和实际意义的义务。在许多关系传染病控制的领域立法空白,没有真正发挥出它在国际卫生法发展上应有的核心作用。
4.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尚不成熟
按照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定义,国际机制包括四个构成要素: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7〕See 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3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85, 186 (1982).其中规制以及决策程序往往决定着国际机制的具体操作方式,确保着国际机制的具体实施。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全球治理不仅要关注民族国家,还要重视国际组织,〔28〕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40页。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治理的牵头者与指挥官。传染病全球化往往推动了国际卫生合作,如前所述,WHO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平台存在多重短板与缺陷。国际法治与规则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国际法在传染病控制中的作用常被人忽视,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仅有的一部关于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条约。目前,虽然WHO已启动关于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工作的新规划,〔29〕有关WH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的问答,参见 https://www.who.int/features/qa/health-emergencies-programme/zh/,2020年3月31日访问。这是WHO的一次深刻变革,其力求在传统技术以及规范作用之上增加行动能力,规划与国家以及合作伙伴一道,共同防范和应对导致突发卫生事件的所有危害。该规划还将领导和协调国际卫生应对行动,以遏制疾病疫情,为受影响人群提供有效的救助和恢复服务。但与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比较来看,由于缺乏决策程序以及缺乏国际法规制,WHO仍存在组织力不强以及号召力不足的现状。新规划效力的发挥尚需时日,新规划是否能够发挥预期作用仍有待考察。
三、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的多维完善路径
鉴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缺陷与问题,如何调和各国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如何界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义务? 如何选择相对弹性灵活的治理工具以达到治理效果最优? 这都是改革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需要思考的问题,完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路径可从多维度开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蕴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频发,SARS以及禽流感的蔓延,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工业化消极结果的逐渐凸显,人类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在面对自然时是一个整体,全球性问题亦无法通过哪一个国家甚至是哪几个国家单独应对,国际社会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即便矛盾重重但又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中国对全球性问题的多边协调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格局里发挥了主要甚至是引领的作用。由中国首次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加强全球治理的原因、目标和路径问题,而成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3月12日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病毒无国界,传染病能够在地球任何地方出现,并通过贸易与旅行迅速蔓延到其他地方,这种威胁是全球性的,没有国家能幸免。各国采取的卫生措施如果出于私利而不顾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无论多么符合国内法规范,也最终会损害国际传染病控制。单凭一国或数国的力量,无法应对它们的挑战,需要全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印证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病毒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如此紧密地相互依存,没有哪一个能够独善其身或者独自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不仅能够增进共识、消除壁垒、加强合作,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时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和帮助,克服自身不足,降低自身风险。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国际关系变革中对于国际法的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制定新规则和建立新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30〕参见黄德明、卢卫彬:《国际法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86页。当前,更需要世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国际法治之中,〔31〕参见李猛:《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3页。推动构建联防联控的国际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体系。
首先,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指导下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各国需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要集各国之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果。要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其次,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G20依托WHO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要发挥G20的沟通协调作用,加强政策对话和交流,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最后,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以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要保护妇女儿童,保护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挑战。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合作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二)多元主体合作中的国际法完善
国家是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虽然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各国让渡部分主权进行国际合作,但最终只有依靠主权国家才能真正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采取相应行动。只有依靠各国对内加强公共卫生建设,采取各种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措施,才能消除传染病国际传播的根源。另外,对于携带病毒的人员跨境、商品流动,只有各国行使采取控制措施的主权权力,才能确保最大限度的安全。因此,在国际法促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过程中,主权国家依旧是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的核心主体。一方面,国家应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切实履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等国际法下的国际义务,尊重WHO的协调机制;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也要从互利共赢、联防联控的角度适当克制自己的主权行动,以保证国际卫生防控措施的协调推进,防止嫁祸他人或祸水东引的行为出现。另外,要强化国际法的责任体系,既要尊重事实和法律充分理解各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同时也要对防疫过程中的脱法行为作出制裁,防止恶性竞争破坏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传统的以各国政府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制在迎接譬如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挑战和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力度不够,或者是力不从心,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实践证明,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32〕参见黄世席:《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探讨》,载《当代法学》2000第2期。应当看到,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很好地弥补了国际合作的空缺,以它们的专业性、广泛性和灵活性活跃在战争冲突后的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健康、妇女儿童保护、传染病控制、灾难救助、环境保护等领域。它们为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可能,发挥着日益重要和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对国际层面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的参与,不仅使得国际立法走向民主化与利益多元化,也提高了国际法的执法与司法的透明度以及合理性,对于克服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律机制的合法性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33〕参见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国际政治中的正义问题》,载《国际观察》2006第4期。因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国际组织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本届虚拟G20峰会之前的集体行动中,国际商会(ICC)、G20和WHO提出了拟议措施,以使全球对有效地遏制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潜在人员和经济损失。在2020年3月23日给G20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公开信中,这三个组织强调了G20在遏制当前危机中不断增加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方面的重要作用。信中强调内向型政策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只有有效的全球合作才能遏制新冠肺炎的潜在人员和经济损失,并提出多项关于疫情防控的建议措施。例如,确保感染控制和医疗产品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确保基本医疗用品和保健服务的公平获得以及扩大财务援助规模等。〔34〕See ICC, B20, WHO issue open letter to G20 leaders, https://iccwbo.org/media-wall/news-speeches/icc-b20-who-issue-openletter-to-g20-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 last visit on March 31,2020.
G20作为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重要平台,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G20就新冠肺炎疫情专门举行峰会,就应对疫情蔓延、稳定世界经济进行沟通协调具有重要意义。G20领导人联合声明公布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卫生措施,寻求确保充足的资金以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G20领导人表示将及时、透明地分享信息,交换有关新冠病毒的数据,承诺与各方共同努力,填补WHO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中的资金缺口。G20致力于恢复信心,维持金融稳定,重拾经济增长势头并实现更强有力的复苏,致力于帮助所有有需要的国家,并在公共健康和财政措施方面采取协同行动。
除了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外,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关企业、团体及个人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建设性作用。例如在疫情初期,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企业与国民便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提供了无私的援助,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当时防疫物资的紧张。之后,中国企业也加大对防疫物资的生产和运输工作,短时间内不仅满足了中国国内的疫情防控,更在新冠肺炎海外蔓延中为塞尔维亚、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同时,包括马云、比尔·盖茨在内的知名企业家也纷纷为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相关药品企业和科研院所也积极攻关,不断地与全球进行信息与技术分享,有力地促进了防疫工作的开展。
在有关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传染病的话语中,“全球村”的概念频繁出现,在这一“陈词滥调”背后,体现了公共卫生全球化迫使人类像一个全球社会一样行动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个各个国家的社会。〔35〕See David P.Fidl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 Materials on and Analysis of Global Health Jurisprudence, Transitional Publisher, Inc.Ardsley, 2000, p.74.非政府组织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与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相互支持合作,〔36〕参见王小民:《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载《理论月刊》2008年第10期。发挥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联动作用是现阶段全球关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多领域规范协调中的国际法发展
应当看到,公共卫生已经超出了狭义的医疗卫生范畴。传染病控制涉及贸易、人权、环境、劳工与武器控制等多种领域。正如WHO法律顾问阿吉拉姆指出,“公共卫生不再是医生和传染病学家的特权。国际卫生法包含了人权、食品安全、国际贸易法、环境法战争与武器、人类生殖器官移植,以及广泛的生物经济和卫生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些现在构成了全球传染病控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决定了全球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多领域规范。”〔37〕Obijiofor Aginam,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unicable Diseases, 80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46, 949-951(2002).
WHO在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方面有着广泛的责任,具有领导和促进国际卫生法律理性和有效发展的唯一授权。因此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WHO要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软硬结合”。一方面,要发挥“软法”技术性、灵活性的优势,弥补“硬法”的不足,〔38〕参见冯硕:《个人信息跨境监管背景下在线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困境与出路——以软法为路径》,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9年第4期。通过建议、指南和技术标准等加强对各国传染病防控的指导。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就政策优先选择存在强烈一致的情况下,在为实现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要实施时,硬性规则被视为合乎要求的。而当各国能够预见特定可能情况并对于在这些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具有明确认识的情况下,它也十分合适。但是,在各国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时,或因条件正不断变动而难以预料可能性的情况下,建议性方针就更可取了。〔39〕See Mark W Zache, International Health Governance-Surveillance Regulation, and Materiel.Assistance: Trend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http//www.smartregulation.gc.ca/cn/06/01/su_12.asp.last visit on Apr.4, 2020.另一方面,WHO要善于和敢于利用自己的立法权,推进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通过完善“硬法”体系,以条例、条约或公约的方式来规定各国的权利义务关系,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合作秩序,增加国际关系中的可预测性,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
WTO在国际卫生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亦需得到重视。在WTO的法律规则中,包涵众多与卫生服务贸易有关的协议。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涵盖了各种服务贸易部门,其中就包括医疗卫生服务贸易。而《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议》更旨在保护人类和动物生命免受污染物、毒素和致病微生物的危害,免受疾病侵袭,免受虫害、病害或致病微生物的危害,食品安全和人畜共患病的防治,人类与动植物健康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涵盖了《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议》以外所有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对食品则涉及除安全卫生营养以外的要求,其原则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议》大体相同,二者相互补充,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更强调成员方技术法规制定、实施及合格评定程序。近年来,WTO、WHO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逐渐通过协调和对话来解决国际贸易与人类健康问题,WTO和WHO努力协调在一些领域中的工作。在政治层面,两个组织都致力于解决国际贸易与人类健康问题。在技术上,两个组织最近成立了关于药品差别定价和知识产权地位的工作组。尽管两个组织的目标不同,但工作中存在互补的可能。
除了对主权国家的协调外,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国际法更应关注对人的保护,这便涉及国际法的正义问题。全球贫困饥荒、全球变暖和国际暴力等问题催生了对国际正义问题的关注,〔40〕参见高景柱:《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批判与捍卫》,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同样传染病的全球化也提出了国际正义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卫生安全中的负面作用,例如,由于专利保护导致的高昂价格阻碍了穷国与穷人获得可改善艾滋病病原携带者生活的机会,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从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来看,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护公共利益平衡是我国政府一贯之主张。快速应对公共健康危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机制,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和应对各种挑战。〔41〕参见田刚:《快速应对公共健康危机,共同完善国际知识产权平衡机制》,载《WTO经济导刊》2008年第7期。
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与环境保护存在天然的联系,因而国际法也应继续发挥在国际环境保护上的作用。恩格斯曾特别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自己征服自然的胜利,每一次胜利,真实确定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随着环境与疾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日益明确化,各国开始从保护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传染病的办法。疫苗是针对个人的一种预防手段,自然环境的保护则是通过改善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来预防传染病,虽不及疫苗那样立竿见影,却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随着环境法在传染病预防中的作用逐步被各国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国际法应该更加关注各国国内或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各国必须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确立对公共卫生特别有意义的环境资源保护的国际规则与标准。预先性环境保护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消除了有利于疾病暴发的条件,公共卫生成本也更低。国际环境法的确定渊源包括: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有关环境问题的习惯国际法,相关司法判例及国际组织、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决议、原则、宣言及建议,从上述层面开展与协调国际环境治理,从规则的层面赋予国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亦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构建全球联防联控机制要做到 “标本兼治”,除了采取有效措施抓紧遏制与解决当前疫情外,更要立足长远,确立“全球生态观”与“大卫生观”,建立维护全球生态系统与提升全球卫生治理能力的长效机制,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国际人权法的不断完善已然成为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亮点。传染病直接威胁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全球公共卫生与全人类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的易感性使得传染病与人权保障处于高度互动之中。如果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传染病人际传播的风险会大大增强。一旦感染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将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反之,如果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就会大大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即使感染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人权与传染病控制的关联,不仅仅涉及公共卫生措施的技术与操作层面,也涉及围绕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包括性别关系、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生活行为方式或种族。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个人或社区能够获得医疗保健与经济资源以及政治、社会生活的自由与权利保护程度,进而影响人们易受感染性的大小。2001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责任宣言》认为,充分实现所有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是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关键因素。融合人权与全球性传染病防控,视国际人权法为衡量公共卫生措施的标准,并作为一种应对传染病的最佳策略,通过尊重、保护与履行人权来控制传染病,并以符合人权的传染病控制措施来保护公共卫生。这种策略被称为传染病控制的 “基于权利的方法”。〔43〕See David Patterson & Leslie London,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and HIV/AIDS, 80 Bulletin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64, 967-969 (2002).“基于权利的方法”的明确与推广,最终使国际人权法得以适用于传染病控制领域,并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治
纵观国际法的发展历史,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单独依靠民族国家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治理现实,不利于实现全球的整体利益。〔44〕See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olity Press, 2002,pp.305-324.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当代国际法面临巨大挑战,其变革势在必行。历史表明,在人类社会的艰难前行中,疾病或瘟疫大流行总是如影随形,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人类正在面临的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此次疫情不仅将影响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还将影响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后疫情时代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
21世纪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新旧动能逐渐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逆全球化潮流和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加剧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国际力量围绕选择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不断展开博弈,但维护多边主义仍是当今国际政治主流,世界正在形成联合反对单边主义的力量。从长远看,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其透支经济和政治信用的行为,只会加速损耗其在物质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实力。中国所倡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一带一路”倡议,都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多边主义所体现的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理念对于消除冲突隐患、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全球互联互通,政治上主动承担负责任大国责任,文化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法治上着力推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规则的制定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如今的国际秩序建构更趋向于依赖非武力性质的国际规则。国际规则不仅左右国家间利益分配,更决定一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其所能扮演的国际角色。事实证明,以国家主权为基石的国家政治疆域并不能阻挡病毒的入侵,国际法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需要检视和反思。当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被传染病全球化所强化,尤其是大国间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卫生合作便有了更坚实的基础。〔45〕参见龚向前:《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
我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今后应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背景下,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世界秩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参加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以“一带一路”为实践载体推进国际合作机制创新,争取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接受者转变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者、推动者,全力塑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治,为新时代构建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公正性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