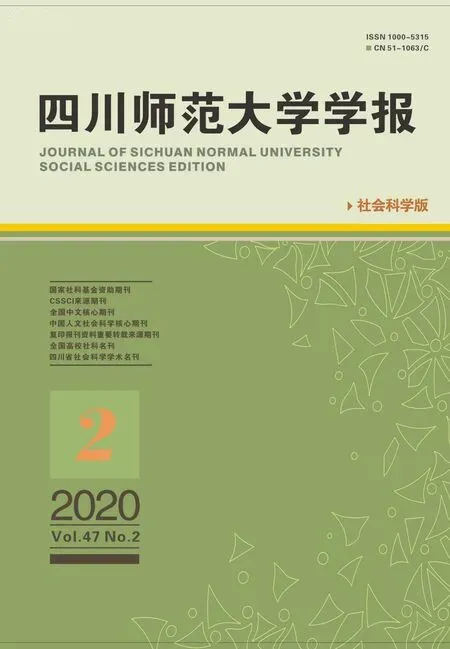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政策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启示
2020-02-25曲铁华
王 美,曲铁华
(1.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长春130024;2.长春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长春130012)
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理性与情感持续交织、追求与反思冲突不断的演进过程。民国政府在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延续了晚清的教育变革步伐,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支持和推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这些政策文本在外求与内生的共同作用下,努力探寻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模式的新思维与新路径,逐步规范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基本形式与发展走向。
一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政策的历史演变
传统学科在清末学堂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开始更新转型。民国建立后,教育部以西方学科分类为标准,开始有计划地对国立大学学科布局和课程内容进行规范和调适,优化和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实现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学科秩序与学科价值理念的协调发展,逐步推动国立大学学科政策向综合化、规范化迈进,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近代学术形态转型。
(一)学科政策的初创期(1912-1926)
1.从“经史为本”转为“七科之学”
中华民国肇建,五族共和宪政体制登上历史舞台,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引擎轰然启动,中国近代大学学科文化的新秩序亟待重新铸建。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阐明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取消了经学科,确立了“七科之学”的学科发展体系。①《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教育杂志》1913年第10期,“法令”,第34页。《大学令》作为民初大学发展和学科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改变了以往经学占主导的学科体系,这传递出民初的大学已经逐渐摆脱清末“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人才培养宗旨和学科发展定位,它的颁布确立了文理学科为主轴,其他五科为支干的学科体系。1913年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规程》,对大学的学科建制进一步规范,确立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为基础的大学学科建制。它将文科列为4门、理科列为9门、法科列为3门、商科列为6门、医科列为2门、农科列为4门、工科列为11门②《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教育杂志》1913年第1期,“法令”,第1页。,确立的科类和所辖之门类课目较为贴近西方大学学科编制,校—科—门三级学科体系初步成形,奠立了近代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基本框架。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满足文理兼通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些大学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学科外部价值,从而逐步打破学科界限,废除学科门类,建立学科系别,使学科教学更具有独立性和学术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改革探索,以“系”代“门”逐渐形成。为了扩大学系建制的影响,教育部1924年2月颁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分为文、理、法、医、农、工、商等科,各科分设各学系③《国立大学校条例》,《教育公报》1924年第3期,“法规”,第1页。,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国立大学的校—科—系的新式学科体系。
2.从“官学模式”转为“教授讲座”
民国建立后,传统的官学教育模式和官衙遗风亟待改变。1912年,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规定,大学各科设讲座,由教授担任之;教授不足时,得使助教授或讲师担任讲座,并设立评议会,审议学科设置与废止以及讲座的种类。④《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法令”,第35页。这一规定改变了之前传统官学机构学科管理的封建性,打破了学科从属于政治的固有格局,使学术所长之人在学科管理上具有话语权和决策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管理由政治本位向学术本位的转换,改变了浓厚的官僚习气,有利于实现教学自主。1917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本校各科各门之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每部设教授会……教授会皆有讨论决议之责:本部教授法之良否,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凡关于本部下列诸事本部(教授会)皆有参预讨论之责: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应用书籍及仪器之添置。”⑤《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1日,第1版。这为北大教授管理学科提供了政策依据。
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崛起,他们逐渐摆脱了依托于政治的附属身份,开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形成个性鲜明、精神自觉的主体。蔡元培作为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为了进一步落实“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1920年4月,在北京大学出台了《评议会规则修正案》,规定评议会的人员由校长和教授互选之评议员构成,要求评议会设议长一人,由校长担任;评议会主要决议设立废止或变更学系及校长咨询事件以及其他高等教育事项。⑥《评议会规则修正案》,《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5日,第2版。这和民初《大学令》中有关评议会的职责几乎一致。掌管北京大学期间,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鲁迅、胡适、钱玄同、黄侃、崔适、辜鸿铭等专家和教授开设讲座和课程,为学生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群体的主体性,促进了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二)学科政策的调适期(1927-1936)
1.从“科系建制”转为“院系建制”
不同于民初的科门建制和科系建制,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科系建制、讲座研究模式已经不适应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地实现学科知识之间的横向整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构建了学科分类基础上的校—院—系的学科政策框架体系。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①《大学组织法》,《立法院公报》1929年第8期,第123页。192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行了《大学规程》,对大学的学科编制、主辅系制度、校—院—系组织以及课程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②《大学规程》,《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9期,第84-86页。,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较大地调动了基层院系办学积极性,强化了基层机构的学术权力。《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大学学科的设置,抑制了原有学科滥设的现象,纠正了“教授治校”制度的偏失和局限,使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走上行政化、世俗化的道路。以清华大学为例,按照院系建制政策调整,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学科专业布局。
2.从“重文轻实”转为“抑文重实”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需要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推动农工商医等实业发展,巩固国防建设。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再过分注重国立大学科系数量的增加,对大学区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避免同一区内国立大学重复学科的设置,并注重自然学科的拓展和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裁撤重复、冗余文科科系的办法来均衡学科内部布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变当时国立大学学科建制重文轻实的畸形状态。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对于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方针是:“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③《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5期,第3页。这对于引领大学学科教育向偏重实用技术学科发展、扭转民初以来实科教育不足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1932年5月30日,陈果夫在《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指出:“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材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以十年为限;三、在各大学中,如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別改办农、工、医等科。”④《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大公报》1932年5月31日,第3版。虽然这项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但是却反映了政府高层欲大力抑制文科、扩张发展实用学科的用意。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科政策取向之所以从“重文轻实”转为“抑文重实”,目的就是改变此前远超出社会实际需要的文科学校和法政科毕业生大量堆积的现象。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大学提倡实科教育的发展,注重学科的实用性和社会推广效应,部分国立大学逐步摆脱单纯性研究高深学问倾向的学术,逐渐与国家和社会化需要相适应。
(三)学科政策的跋涉期(1937-1949)
1.从“三民主义教育”转为“战时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国立大学的学科内容和课程科目具有一定政治性要求。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2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指出:“教育为建国根本大业,各级及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于国防教育各级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智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术人才”⑤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战时青年》1938年第7期,第2页。,要求各级学校增设军事有关学科,加强军事训练与管理。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以适应抗战需要。⑥顾毓琇《抗战建国纲领下的教育》,《时事类编》1938年第18-19期,第11页。鉴于战争形势,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重新谋划了国立大学学科建制格局,以满足战时国家需要。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更提出了“配合政治进程,适应国防与生产建设等需要之教育,此种教育之过程与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密切配合,并头迈进,其鹄的则在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之使命”⑦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编纂《三年来之建教合作》,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1941年版,第9页。的教育建议。这种融合政治因素和国家战略的大范围“建教合作”,使得国立大学的学科建设在艰难的战时环境中获得了发展。
为了增加抗战实效,1939年6月23日,教育部决议《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设战时教程》,要求各院系删除不必要科目,依科目性质酌量增设特种教学内容,合计28项:文科包括孙吴兵法、历史战争史料、随营图书馆、民族运动四种;理科包括毒气化学、精制炭油、国防化学、火药学四种;农科包括移民屯垦、粮食管理、荒政学三种;工科包括兵器学、筑城学、防空学、汽车驾驶、筑路工程五种;医科包括战时救护、军事看护、绷带法、活性碇之研究四种;法商科包括战时经济学、战时财政、战时政府、战时经济政策、战时社会工作五种;教育科包括战时教育、军事心理学、战时中小学课程研究三种。①《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设战时教程》,《教育季刊》1939年第2期,第73页。同年,教育部厘定了《战时教育计划》,决定运用教育设施,协助抗战军事,造就军事人才,同时调整专科以上学校之科系设置与地域分配②《教部新定战时教育计划》,《教育季刊》1939年第15期,第66页。,激发青年学子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知能。在民族存亡之际,面对形势骤变,国家实施应急学科方案来调整教学内容,虽战时色彩浓厚,但也是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必要举措,以扶植动荡中的高等教育。
2.从“零散调适”转为“统一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在初建时期已经讨论过系科设置和课程设置标准问题,但标准还是较为零散、分割。全面抗战爆发后,高等教育遭遇巨大磨难。为了挽救危亡之际的高等教育,落实“战时须做平时看”的教育方针,1937年9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战争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着手令一些沿海高校迁往内陆,采取集中、联合办学的统一调整办法,推动各校传统优势学科实现互补,形成新的特色学科,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时,根据建教合作原则,政府和内迁院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以设立新的院系和学科,支援当地的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同时,国民政府采用国家权威的政策手段对院系名称、学科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进行统一限定,一方面扭转战前全国高校文、理、工等学科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另一方面扭转管理混乱的高等教育局势,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战时制定的一系列学科方针政策,带有明显的统一性、战时性、应急性倾向,以适应后方各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1938年9至11月,教育部颁布了文、理、法、农、工、商六学院共同科目表③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50-52页。,旨在课程内容的文理渗透,以培养学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科涵养。1939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令》,对大学的院所、学系名称进行了统一的规定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9页。。这规范了全国专科以上的国立大学学院专业科目,克服了之前高校院系、学科、专业设置重复,名目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以达到规范管理、教育行政统一化的要求。1944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二次课程会议,对文、理、法、师范院系的必修科目进行修订,逐步规范了大学的课程设置。⑤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上海)1948年版,第15页。除了统一课程科目标准外,作为学科内容传授载体的教材也被纳入调整的范围。战前大学的教材和科目各自为政,零散繁乱。1947年底,课程标准、教材标准得到统一。抗战结束后,为了维护高等教育秩序、促进战后高等教育稳定发展,1948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这为大学学科调整提供了政策依据,一些大学通过调整成为多学科并举的综合性大学。
二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政策演变的逻辑特点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在国家权力、社会需求、经济水平等外在因素的不断碰撞和冲突中由传统向近代延展,在动态的调适和发展中凸显了坚守与融合并举、专制与自治并行、理想与现实并存的逻辑特点。
(一)坚守与融合并举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专制集权的政治防线发生坍塌的同时,封建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强力钳制力量已经动摇,凸显现代政治形态的民主共和体制初步确立。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涤荡,当时新派知识分子逐步克服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狭隘性与封闭性,积极推崇西方先进的学科思想和管理制度,德、美、法等国的大学学科内容和体系得以迅速引入中国本土,这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政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大学的学科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西化了,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传统的学科因素仍然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文化特有的方式根植于大学的学科价值理念中。西方的学科政策文化注重科学与工具理性,中国传统的学科政策文化强调人文和价值理性。在38年的民国社会变迁中,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在曲折的发展演进中保守和融合兼顾,既注重本土传统又注重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引入,既进行自我扬弃又进行外来滤收,使得新旧糅杂、中西竞存的两种教育力量共同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学科政策体系前行,形成一种吸纳了其他文化精华的新的学科教育政策格局。
(二)专制与自治并行
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过程是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影响与作用的过程。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政府出于对自身政权巩固的需要,先后出台系列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政策法规,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面对多重社会价值矛盾和冲突,政府对于国立大学学科层面的积极办理,使其主动承担学科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决定学科发展的定位、路径和走向。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办理和推动,带有较为浓厚的专制和强权色彩和深深的统治烙印。并且,这种统治的强度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政府对于大学的管控较少,规章制定、学科废立、课程设置、专业分配的权力都在大学。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的政体及运作模式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政府严格控制和筛选国立大学的学科选择,由此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学科发展体系,然而,此时政府的介入较多,大学的自治空间紧缩。
一个发展中的体制,往往并存约束和突破的力量。在政府积极控制学科的政策发展过程中,伴随的是教育独立思潮的兴起、大学区制度的践行和院系建制的推进,一些大学亦努力追求独立于政治外的学科自治体制,致力于为专业发展、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提供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和余地。虽然一些政策由于本土的排斥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但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努力,推进了民国时期学科政策的近代化进程,促成了较为自由的学术风气的出现。
(三)理想与现实并存
民初建立的七科之学、教授讲座等学科政策,开启了近代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但这种学术和文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思想和制度层面,对学科实践的推动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润影响太过长久的社会中,仅仅依靠政府和新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学科模式来达致民众思想启蒙的目的,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某些移植缺乏社会根基。即使掌握学科知识新标准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为突破封闭的学科格局积极努力,知识政体也在按照自身的逻辑不断积累、发展、融合、创新,但在这种情况下颁布的学术理想本位的学科政策在执行中势必会遭遇多重困境和阻碍。因此,民国初期新知识分子提出的许多学科构建和政策方案并没有真正实现。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学的政治服务功能日趋加强,院系建制逐渐完善,学科力量逐步发展,学科社会化影响逐步扩大。国立大学不断强调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相结合,实现学科政策的价值取向也从理想到现实不断转换。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大学积极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推动学科建设为抗战需要服务,实践本位成为主导国立大学学科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纵观民国时期,不管是在学科政策初具形态的理想本位阶段,还是在学科政策日趋成熟的现实本位阶段,都是在现实需求基础上进行的思维凝结,都是对构建完善学科制度的美好憧憬。理想的构建基于现实,现实的探索是为了实现理想,因此,理想与现实两种价值取向并存于民国时期大学学科政策的演进过程中。
三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政策演变的现实启示
透过民国时期学科政策发展历史进程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政府和大学努力把握自身命运,努力拓展自身视野,在中外文化强烈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积极构建近代高等教育学科政策体系,在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孕育和开启了近代高等教育学科进程,这对于当下高等教育的学科政策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学科政策建设重视人才、文化及制度供给
毋庸置疑,专家和学者在推进学科政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孕育新的“公众舆论”,构思和推行新的学科发展方案。当下我国的高校积极致力于建设一流学科、一流专业,除了政府的导向和大学的努力外,还需有一批思想先进、眼界开阔、专业精深、信念坚定的精英群体,将这些一流学者组织协同起来,合理划分学科,科学制定学科政策,提升学科政策的理论研究水平,使他们成为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纽带,既影响政府,又惠及民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文化积淀越深、供给越多,学科发展就越充满生机和活力。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学科政策在晚清学科文化的积淀基础上不断演进,形成了特定的语言系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体系。这些文化信息随着学科轨迹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创新,通过内在动力推进大学的学术发展,旧的学科文化不断消亡和转化,整合成近代化的资产阶级学科文化。当下,在新一轮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学科建设者既要注重原有学科文化的积淀,也要注重新的学科文化的创生,通过学科文化传递的理念和精神来促进学科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前沿的推进,从而塑造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政策体系。
有学者提出:“学科建设的本质是学科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使命的确立,其次是一整套围绕使命实现的制度安排,从‘被组织’走向‘自组织’。”①宣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要实现“三个转变”》,《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5期,第6页。民国政府较为注重学科政策的配套制度供给和建设,围绕学科结构的建制、学科规范的设立以及课程标准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人员、条件保障和法治实践。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科政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制度保障还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学科主体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合理分配学科管理权力,规范学科组织秩序,加快学科立法建设,并通过方向引导,完善学科发展的要素供给,实现学科发展的制度投入、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学科建设绩效。
(二)学科政策内容遵循学科、社会及个体逻辑
学科是高校发展的核心要素,学科政策内容的结构、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办学特色和水平,决定了大学的竞争优势。民国时期,无论政府还是国立大学,虽然也注重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来制定学科政策,但这种逻辑较多地渗透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强权话语。而且由于许多学科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仓促的条件下应急颁布,导致一些学科政策内容基础浮薄、指向模糊,缺乏长效性。因此,要实现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远景,我国大学一定要按照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和逻辑设置学科政策内容,呈现学科政策最本质的学术功能。
同时,民国时期大为注重学科发展的社会功能,注重学科建设的拉动效用,大部分政策、法令、规程的颁布都涉及学科调整和发展的内容,并且一直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来调整和完善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几轮学科建设,政府和大学自身也高度重视学科建设的统领作用,但是部分大学的学科布局和结构还不够合理,遴选取向上还存在“择需”不足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科建设主体要在遵循社会逻辑的基础上做好学科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前瞻性的眼光,根据国家重大战略的紧缺急需而选择和设置学科,突出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前沿学科,分层次、分类别、分区域地形成国家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良好生态格局。
学科政策内容的直接供给对象是教师和学生,学科建设主体要充分遵循学科发展的个体逻辑,使学科组织内部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机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价值取向更多地强调工具价值,忽视了教师和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诉求。因此,面对当下深化综合改革的形势和要求,学科建设者要树立以教师发展、学生成长为目标的学科政策设置理念,无论是专业科目的选择,还是课程内容的组织,都要考虑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要求,实现学科与学生互动、学科与科研互动,推动学科体系的动态发展。
(三)学科政策管理实现开放、民主和自治原则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之所以获得较好发展,这与其借鉴和本土化西方的先进学科建设理念是分不开的。“七科之学”“科系建制”“院系建制”“教授讲座”等学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在借鉴德、美等国家大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本土性改造的成果。诚然,这种挽救国家危机、实现民族振兴的工具性移植和融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且自主探索的成分较少,使得学科政策在移植和融合的矛盾中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但确实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政策的近代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化与本土化是高等教育的两重属性,两种促动力量相辅相成。因此,教育行政部门要有一种多元思维和辩证视角,一种包容原则和前瞻心态,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的学科管理模式、决策程序、精华理论,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相契合,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背景和现实条件相贴近,在借鉴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创新,使学科过程管理走向开放、多元。
民国政府虽然思想文化的控制较为严格,但总体来看,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呼吁和奔走下,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的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自主空间。特别是民国初期和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学科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较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辉煌成果,但是由于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大学仍然存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失衡的现象,学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然受到行政的过多影响和干预。为了实现高等教育新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大学的权力机构应该更多地依靠学术权威,践行学术逻辑,遵循民主原则,政府担任调控者、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赋予高校学科自主管理与自主发展的权利,减少政府对高校过多的学科干预,真正实现学科政策过程管理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学科学术精神焕发生机,使学科政策的过程管理走向民主、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