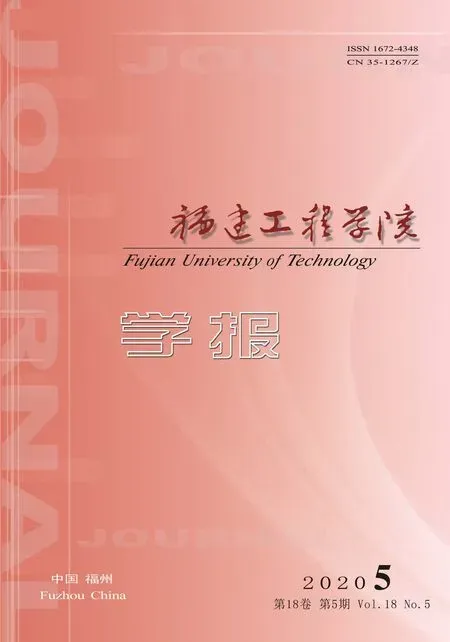黄檗文化概念界定的回顾与考辩
2020-02-25董俊珏
董俊珏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黄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福清 350300)
2015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十七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1]讲话中提到的隐元大师,即出身于福建福清的明末高僧隐元隆琦。南明永历八年(1654),隐元禅师应日本长崎兴福寺的邀请,携徒东渡弘法,开创了日本佛教禅宗中与临济、曹洞鼎足三分的黄檗宗,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对海内外黄檗文化研究以及中日两国基于黄檗文化的友好交流,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此直接推动下,黄檗文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关于黄檗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产业开发也迎来了新契机。但是,大众对于黄檗文化的认知仍然还处于较模糊的状态,尤其 “黄檗文化”的内涵和本质亟需讨论与厘清。
一、黄檗文化概念界定的历史回顾与问题辨析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凡武之用,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2]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是明治维新以后从日本传入的。近代日本学界用“文化”来翻译英语单词culture,“黄檗文化”这一名目也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虽然最初揭橥者尚待考证,但据1972年日本学者林雪光所编纂的《黄檗文化》(日本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发行)及1988年大槻幹郎、加藤正俊和林雪光三人合作编著的《黄檗文化人名辞典》(思文阁出版)可知,在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中,“黄檗文化”已是广为接受的一个概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什么是黄檗文化,怎样界定黄檗文化具体的内涵与外延,包括以上几位学者在内的日本学术界和宗教界,并未给出清晰、确切的阐释。
(一)原有关于黄檗文化概念界定的偏差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试图对黄檗文化这一概念作解释,目前有两种提法。
首先是隐元禅师故里、黄檗山万福寺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的文化研究者的意见。由福清市文联主管、福清玉融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内部刊物《玉融文化》,2016年春推出了一期“黄檗专辑”,收录了黄檗文化研究相关论文八篇。其中,严家梅所撰《敢闯走天下,念祖不忘根——试谈“黄檗文化”之精髓及其现实意义》一文,是迄今仅见的对黄檗文化作定性讨论的文章。该文认为,所谓黄檗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黄檗文化,“在国内指的是汉传佛教禅宗临济祖源黄檗山万福寺的佛教文化,在日本则指由隐元隆琦东传的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宗教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范畴”[3]。广义的黄檗文化,“一般应指受福清地方文化浸染极深的黄檗寺佛教文化和同样被黄檗寺佛教文化影响极大的福清文化的总称”,“其核心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福清地方文化”。[3]作者提出此种定义的依据,一是黄檗山万福寺地处福清境内,且历代住持俗籍多为福清或闽中其他地区;二是福清有悠久而浓厚的佛教文化的传统,临济宗开山祖师义玄的嗣法师,即为在福清黄檗山建福寺(万福寺前身)出家的晚唐高僧断际希运禅师,而禅宗另一大派曹洞宗的祖师之一曹山本寂禅师,也是在福清的另一名刹灵石寺出家的。
严家梅对于“黄檗文化”概念的此种解释,注意到了日本黄檗宗和中国佛教禅宗不可分割的深厚渊源,认为佛教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内的黄檗文化的主体,同时也强调了黄檗文化的地缘特征,并将其与福清地方文化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样的定义,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但仔细推敲,值得商榷的地方也很明显。
诚然,黄檗文化中的福清元素相当清晰,由隐元禅师传到日本的黄檗梵呗,历三百余年未有变化,其读音也是以福清话为基础、混杂了明代官话的发音。此外,日本料理中的卓袱料理,也是由隐元传播到日本的普茶料理发展而来的,有一种说法是,“普茶”即明代福清方言中“福清”一词的音转。然而,在严家梅的狭义的黄檗文化概念中,将“黄檗文化”割裂为“黄檗山万福寺的佛教文化”(国内)和“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能不令人费解。如果中日双方对“黄檗文化”的理解有显著的分歧,那么基于黄檗文化的国际交流,很容易陷入大家自说自话的境地,很难达成共识,也不利于深入合作的开展。再者,将广义的“黄檗文化”的核心定位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福清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一种矮化,毕竟在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中国,福清地方文化所能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至少不能算很突出的。强调黄檗文化中的福清元素,和直接将黄檗文化等同于福清地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多少有一些地方本位的思想。虽然以隐元为首的东渡黄檗禅僧中,俗家为福清人的有很多位,比如即非如一、慧林性机、高泉性潡等,他们也的确为黄檗文化在日本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福建省内其他地方以及浙江、江苏、江西等外省出身的黄檗禅僧亦复不少。例如促进隐元东渡传法的关键人物、长崎兴福寺的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就是浙江钱塘县(在今杭州市)人,且原先是以儒生加商人的身份赴日的。逸然性融的嗣法师、兴福寺第二代住持默子如定,则是江西人。他们一般都被视作是黄檗派的高僧,而他们东渡日本,还在隐元之前(1)日本黄檗宗僧人山本悦心撰《黄檗东渡僧宝传》(日本爱知县龙云寺黄檗堂文库1940年刊),详录由中国东渡日本的黄檗禅僧的弘法事迹。该书所记,始于真圆觉禅师在日本元和六年(1620)抵达长崎,较之隐元东渡,足足早了34年。默子如定东渡,在日本宽永九年(1632),逸然性融东渡,在正保二年(1645),亦均在隐元之前。。默子如定将中国当时高超的桥梁建造技术传到了日本,而逸然性融则是黄檗文化中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再如隐元的剃度弟子独立性易,以博学多才著称,精通诗文、医术、书法、篆刻与建筑等,在推动黄檗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方面居功至伟,但他原本出身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因明朝灭亡而避居日本,然后才在长崎跟随隐元出家。独立性易在禅学上的造诣并不突出,他其实是穿着僧衣的儒者。其他如画家陈贤、雕刻家范道生,都并非佛门中人,却素来被奉为黄檗艺术史上的宗师与巨匠。
因此,可以认为,黄檗文化虽然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种佛教文化。同样,黄檗文化发祥于福清,有丰富的福清元素,但决非一种地方文化所能局限。此种对于黄檗文化概念的解释,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黄檗文化概念初步的正确理解
在福清本地的文化学者之外,国内另有一种对黄檗文化概念的界定,这主要来自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林观潮教授。林观潮是当代黄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版)与《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目前黄檗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成果。在《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一书中,林观潮依据大槻幹郎等人所编《黄檗文化人名辞典》中的相关内容,对黄檗文化的概念作了如下解说:
伴随着黄檗宗的不断发展,大陆僧人接连东渡百年多,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传入日本,影响佛教内外,波及江户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日本学术界称之为黄檗文化。[4]
在此之后,林观潮又在2017年第1期的《佛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隐元大师与黄檗文化刍议》的论文,文中也有对黄檗文化概念的表述:
同样以中国禅宗为源流,黄檗宗崛起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与之鼎足并立,深刻影响日本社会文化思想。随着黄檗宗的发展,大陆传来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超越了佛教层面,波及江户时代(1603—1868)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可称为黄檗文化。[5]
相比较而言,在基本内涵相近的情况下,后一段文字对所谓黄檗文化的界定,显得更为清晰。虽然林观潮在同一篇文章中认为日本佛教黄檗宗仍是黄檗文化的“内核”,但他也明确指出,借助黄檗宗在日本的迅速传播,由中国大陆传往日本的“黄檗文化”,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佛教文化,而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形态”。黄檗文化概念的外延,不仅覆盖了佛教内部的黄檗宗的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还关涉到佛教以外的思想、文学、语言、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茶道、饮食、绘画、书法、篆刻等等,几乎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生活。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说:“到十九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切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6]按照林观潮的解释,黄檗文化正是江户时代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这种大规模的文化的传播,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时间,其具体的传播方式,是以佛教黄檗宗为依托的,但最终突破宗教的局限而弥散到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完成了与日本本土文化的融合与新变。即此而论,林观潮对黄檗文化概念的理解,无疑是较为严谨而科学的。
二、华侨文化、海丝文化和对外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黄檗文化
虽然如此,如果想对黄檗文化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再作补充的必要。
第一,黄檗文化具有浓厚的华侨文化色彩,实现了对华侨文化的超越,是中国古代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端形态。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始终保持着兴盛的状态。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所著《陶瓷之路》一书指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中国出产的瓷器由海道行销东南亚地区,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的晚唐时期。随着船舶制造与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宋元以降,中国对外陶瓷贸易一度非常繁荣。明朝前期,由于倭寇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骚扰,朝廷实行了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但东南地区民间的对外贸易并未停滞,部分浮海通贩的商民,出于扩展贸易关系等原因,往往定居异域,成为所在国的华侨。明朝灭亡以后,如朱舜水等耻事新朝的明遗民也寄身海外。其中,日本是明、清两代华侨最重要的贸易和寄居国。自明中叶以后,移居日本唯一海外贸易港长崎的华侨(尤其是隐元禅师故里、黄檗祖庭的福清人)为数极多,他们中不少人就充当了“唐通事”或“年行事”“目明”之类的角色,在协助日本政府管理通商事务、维持地方秩序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旅日华侨的社会建设,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极大贡献。完全照搬中国式样的“唐三寺”(长崎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的先后建造,是长崎华侨文化圈形成的标志。(2)长崎唐三寺均由华侨所捐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由江西籍侨商欧阳云台于日本元和九年(1623)捐建,该寺开山住持真圆禅师原为江西籍的旅日侨商。福济寺(俗称泉州寺或漳州寺),由福建漳州、泉州籍华侨捐创建。日本宽永五年(1628)中国僧人觉海禅师成为福济寺开山住持,寺中也奉祀天后圣母。日本庆安二年(1649),经原籍福建漳州的唐通事颍川藤左卫门(本姓陈,名道隆)倡议,福济寺延聘泉州籍高僧蕴谦戒婉赴日担任住持。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创建于日本宽永六年(1629),由福清籍侨领何高材、魏之琰等捐建,以福州籍禅师超然为开山,寺中也供奉妈祖与关帝。隐元法系的即非如一和千呆性安先后住持该寺。这几座寺庙起初的佛教氛围并不浓烈,例如兴福寺由供奉海神的妈祖庙改造而成,寺中至今仍供奉有妈祖、关帝和大道公神像。这些寺庙更大的意义是作为长崎华侨的聚集点而存在的,为了更好地发挥在日华侨联系纽带的作用,这几座寺庙开始招请中国大陆的高僧赴日住持。隐元禅师的东渡和黄檗文化的肇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可以认为,没有日本华侨社会的壮大,黄檗文化就完全不具备生存的土壤。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黄檗文化归结为明清以来华侨文化的一种。应该注意的是,隐元禅师在传播黄檗文化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佛学经义、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在于他通过自身精湛的佛学造诣、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以及对黄檗伽蓝建设的辛苦经营、对嗣法弟子的精心培养,促成了日本社会从天皇、幕府到普通民众对黄檗禅风及其背后中华文化的倾心接纳,使黄檗文化真正地融入了日本社会。因而,可以这样认为,黄檗文化是在华侨社会的深厚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是明清时代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华侨文化的巅峰,但又超越了华侨文化,创造出了中日文化融合共生的新形态。
早期寓居海外的华侨,无疑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开拓者与承载者,这自然也揭示了华侨文化与古代海丝文化的内在关联。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黄檗禅僧东渡及其在日本的广受欢迎,在客观上刺激中日民间贸易发展的同时,更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因此,如果将黄檗文化置于中国海丝文化的背景之下来考察,那么完全可以认为,与日本华侨社会关系密切的黄檗文化,因为其内涵的丰富性和综合性,特别是其超越了商品交换关系而在思想文明传播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不仅可被视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高端形态。
第二,黄檗文化是封建时代后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次极大规模的对外传播,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前述山本悦心所编《黄檗东渡僧宝传》,其中收录的第一位渡日弘法的中国高僧是真圆觉,他抵达长崎的时间在日本元和六年(1620),最后一位则是日本享宝八年(1723)来自浙江湖州的竺庵净印,前后时间跨度在百年以上。如果考虑到旅日的中国侨商同样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一般被视为黄檗文化重要遗产的《魏氏乐谱》,即由原为明代宫廷乐官的福清人魏之琰于明末传入日本。魏氏后半生定居长崎,并担任唐通事。,那么黄檗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就是一个长达一百余年甚至更久的持续的过程。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系统的、大规模的文化传播,都是非常罕见的。而日本皇室、幕府对隐元等黄檗禅僧的优礼尊崇,黄檗宗对日本佛教界振衰起敝的推动,以及煎茶道、普茶料理等日本社会生活中至今仍清晰可见的黄檗元素,都足以说明以佛教文化为基本形式和主要介质、以“综合性的文化形态”黄檗文化的面貌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便是封建社会的后期,也仍然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源源不绝地对周边区域形成强大的文化辐射。
非常有意思的是,与黄檗文化的核心人物隐元禅师同样出身于福清,并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在晚明的兴盛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三朝宰辅叶向高,却成为了天主教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推动者。万历三十五年(1607),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又在京师宅邸中款待利玛窦,并与其弈棋论道,讨论中西学术、宗教之异同。利玛窦将此事写入了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另一位天主教教士、素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也与叶向高息息相关。天启五年(1625),叶向高自北京返回福建,道经杭州时,与艾儒略相谈甚欢,于是力邀其入闽。也就是说,艾儒略入闽传教,乃是发之于叶向高的邀请。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亦云:“儒略既至,彼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7]艾儒略传教于福建二十多年,在全省各地建了大大小小的教堂二十几处,受洗教徒达万余人,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传布的全新局面。这种盛况与叶向高的扶持有非常大的关联。如果将叶向高对天主教的欢迎与同时期隐元在异域开宗立派的努力比并观之,那么就不仅会因二者同为福清籍而显得饶有兴味,而且可以发现,在十七世纪那样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节点,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保持着相当开放、自信和进取的姿态。假使中国与世界的这种文化交流能够持续下去,历史的走向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黄檗文化之后,因为古老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和日益闭塞的心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就再也无心、无力进行对外的大规模文化传播了。长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扮演文明传递使者角色的两国僧侣的光辉形象,也终于随着黄檗僧众不再东渡日本而黯淡下去。当然,这也反过来彰显了黄檗文化及其传播者的伟大。
三、结论
综而论之,我们可以认为,所谓“黄檗文化”,乃是发祥于以福清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兴盛于日本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它以佛教文化为载体,同时涵盖了思想、文学、语言、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茶道、饮食、绘画、书法、篆刻等诸多领域,全方位地影响了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并拓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黄檗文化超越了单纯的商品贸易活动,覆盖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直至思想文化的全部层面,是中国古代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端形态,也是中国古代华侨文化的典型。在中国封建时代,黄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次极大规模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