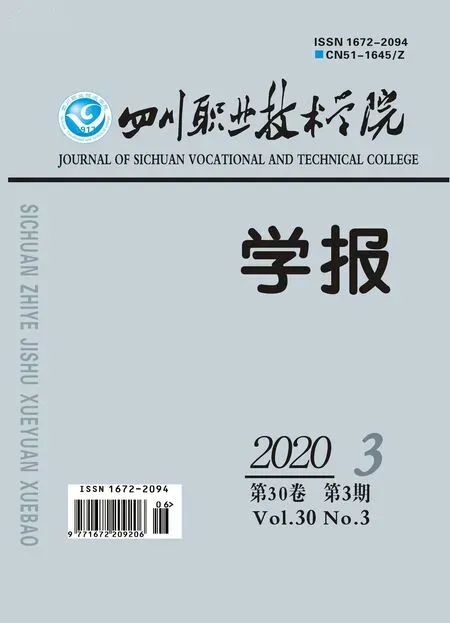鲁迅杂文与文学审查
——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为例
2020-02-25刘平
刘平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引言
1933年,鲁迅杂文在审查中被删节、改动和禁止的情况屡见不鲜。具体到《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收录的都是鲁迅在1933年为《申报·自由谈》写作的杂文,一共108篇,其中16篇被检察官或编辑删改,8篇被禁止。关于本文的论题——《鲁迅杂文与文学审查》,学界有四篇(部)论文和专著涉及到,一部专著是吴效刚的《民国时期查禁文学史论》[1],由于这部专著主要论述的是整个民国时期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在论述中只是附带提及鲁迅有哪些杂文集被查禁,以及简单归纳了官方给出的查禁原因,并没有对具体篇目中被查禁的内容及原因进行深入地探究;一篇学位论文是万春燕的《民国时期鲁迅杂文查禁情况研究》,她比前者做得更具体一些,例举了各个时期鲁迅被删、改、禁的杂文,但仍有被她遗漏的杂文,如《伪自由书》中的《文章与题目》《驳“文人无行”》、《准风月谈》中的《禁用和自造》《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她还详尽地分析了鲁迅为了反审查做出的回应,但却简单地认为“鲁迅杂文查禁的官方原因主要有粗浅平庸、邪说;诋毁当局、诋毁国民党;普罗意识、宣传共产以及不妥、欠妥几种”[2],这让她的论文缺少了理论和思想的深度;再者,她这篇硕士论文只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史学研究法、图表法这三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篇专门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竟然缺少了“文本细读法”;此外,这篇硕士论文的参考文献都是建国后的资料汇编、期刊论文和研究专著,而没有原始报刊资料的引用,众所周知,鲁迅大多数杂文都在当时见于报刊,如果不翻阅第一手资料,很难真实地还原到当时的具体情境。第一篇期刊论文是苟强诗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民国文学研究》[3],他在论文中只用一句话简单提到舆论环境对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二篇期刊论文是潘盛的《民国时期有关文学查禁与文学出版工作探析》,他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的文学审查机关将左冀文学作为重点查禁对象”[4],他的论文只在举例时提到过一次鲁迅的名字。因此,本文先具体分析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的杂文在审查中被删、改、禁的情况,再进一步分析鲁迅杂文被删、改、禁的原因,即鲁迅杂文的社会语境,包括国民党的审查制度、鲁迅杂文的社会影响,最后论述审查下的鲁迅杂文既是社会批判,也是存在诗学。
一、删、改、禁:鲁迅杂文的审查
(一)删节:诋毁国民党当局
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被删节的杂文有10篇,其中《伪自由书》3篇,分别是《王化》《〈杀错了人〉异议》《天上地下》;《准风月谈》7篇,分别是《踢》《帮闲法发隐》《新秋杂识(二)》《同意和解释》《禁用和自造》《冲》《外国也有》。这些杂文被删节之处都是在诋毁国民党当局。
在《〈杀错了人〉异议》中,鲁迅对曹聚仁认为袁世凯杀革命党是“杀错了人”这一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当天见报后,他在文末写道:“记得原稿在‘客客气气的’之下,尚有‘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5]90鲁迅在文中还提到了当时的军阀混战,指出“出洋”的是国民党的下野军阀或军人。
鲁迅在《王化》末尾附记:“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5]131这段附记在《论语》上刊登时被删。此外,“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5]131由此可知,这篇杂文先是经历了被禁发、后转投被删发的命运。鲁迅在文中比较了国民党当局对新疆回民、蒙古王公、西藏喇嘛、广西瑶民、“溥仪亲妇恋奸案”的不同态度,揭露国民党当局推行“王化”的民族政策,是为了拉拢和收买民族地区上层统治者,借助他们的力量去镇压普通群众。
《天上地下》见报后,鲁迅于夜补记:“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5]134见报后原稿中的“背脊生疮”“小便里有糖”被删,这两句话看起来不如“外洋养病,名山拜佛”两句文雅,但却真实地暴露了国民党高官的贪生怕死、敷衍行事。
《踢》写的是中国普通百姓被俄国巡捕踢进黄浦江中淹死之事,被删的句子是:“如果大家来相帮,……,也就是终于是落浦。”[6]54在被删的这句话中,出现了“反帝”这一敏感词汇,与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是相悖的。当局对所谓“反动分子”的“踢”和“推”,足见其手段之残暴。
《帮闲法发隐》中被删的句子是:“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也没有血腥气的。”[6]81笔者在翻阅影印版《申报·自由谈》后发现,在这句话的上两个字——“帮忙”二字后是一个“,”,并非句号,很明显地见出后面有文字被删。从这句话的意思来看,鲁迅写得较隐晦,未点名道姓,这里的“血案”,可能指的是“三一八惨案”,也可能是指近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帮闲们”参与过的“血案”。此句被删,可见血案在当时造成的影响甚大,以至于不能提它。而“主子”则极有可能暗指国民党当局,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正是国民党当局。
《新秋杂识(二)》中被删有三处:“不久还有八岛”“目为反动”[6]89-90以及最后一段。八岛在日本高松东北部。鲁迅在文末的发问,提到“侵略者和压制者”,虽未特指,但读者心知肚明,在当时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者。
在《同意和解释》中,被删的是最后两段文字。在第一段中,鲁迅直接议论“现在的潮流”、各国的政府,并引用宋子文的原话,有理有据,得出政府不需要征得百姓同意的结论;而在第二段中,鲁迅引用韩愈的原话,以秦始皇的做法为例,可见古今皆有权力庞大的政府,鲁迅在讽刺宋子文崇洋媚外的同时,实际上指向的是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的管控,试图一手遮天。
在《禁用和自造》中,“美棉美麦”[6]124四字被删。鲁迅在文中讽刺了广州、广西省当局由于要在贸易中处于顺差,便禁令学生购买进口文具。但是他们禁止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铅笔、墨水笔等,而未禁止进口飞机大炮、美棉美麦,由此可见当局的态度是亲美反日。
《冲》里的“十几龄童做委员”[6]149这七个字被删除,在文中的“能画、能诗、做戏、从军、被凌辱”等事实却不犯禁,只有“做委员”不能说,撇开鲁迅所说事件的真伪,可以见出在当时评论国民党官员是犯忌的。
《外国也有》中被删节的部分是:“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就更加振振有辞了。”[6]155还有文章最后一段。文中内容涉及“上峰”(指上级长官)“外国”“外人”以及迦勒底与马基顿的奴隶制,从这些字眼可看出,鲁迅借外国的情况来含蓄地评论中国的官员,直接讽刺的是国民党当局。
(二)改动:评论时局和触犯“帮忙文人”
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被检察官改动的杂文有7篇,其中《伪自由书》2篇,分别是《迎头经》《文章与题目》;《准风月谈》5篇,分别是《新秋杂识(二)》《“商定”文豪》《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关于翻译(下)》《青年与老子》。这些杂文被改动之处都是在评论时局和触犯“帮忙文人”。
鲁迅在《迎头经》的文末写道:“这篇文章被检查员所指摘。”[5]55对照原文,可以看出被改动之处都是鲁迅在直接评议时局,提到“当局谈话”“报载热河”等时事。至于鲁迅为何不直接点明时间,而将时间用“X”代替,那是因为时间具有特指意义,并和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关联。
鲁迅在《文章与题目》的末尾附记:“原题是《安内与攘外》。”[5]117原标题被改动,是因为其直指蒋介石于1933年4月在抗日和围剿共产党之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时局关联,在审查时不得不被改成《文章与题目》这一与时政无关的标题。
在《新秋杂识(二)》中,“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这句话被改成“于势也有所未能”[6]90,后者比前者更委婉含蓄,“一开口”就会涉及时局,不仅“未能”,亦会有“危险”。
《关于翻译(下)》的原稿本来没有开篇第一句话,那句话是来自《关于翻译(上)》这篇被禁发的杂文。如果这段文字不置于《关于翻译(下)》之前,则会导致该文文气不通。
《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的题目在发表后变成《感旧》[7],没有副标题。鲁迅于10月12日在《“感旧”以后(下)》的开篇写到:“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XX’了。”[6]142由此观之,鲁迅在文中提到了不该提到的人,他举出名字来的都是“帮忙文人”,若见于报刊,极有可能招致他们的攻击。
《“商定”文豪》中写道:“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之处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6]186从这被改动的十五个字可以看出,当时文人评论时局受限,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写作,只能去评议报刊杂志上的广告。
在《青年与老子》中,被删除的是“杨某的自白”[6]188五个字,由于鲁迅直接点名道姓,指责杨邨人发文为自己叛变革命和共产党辩白,用自己的父亲来当借口。杨邨人当时已叛变,投靠国民党,成为“帮忙文人”,鲁迅若在文章中直接议论他,则会引起他的注意,因此这句话不得不被改动。
(三)禁止:议论内政和指责“帮闲文人”
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被禁止的杂文有8篇,其中《伪自由书》5篇,分别是《不求甚解》《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再谈保留》《驳“文人无行”》;《准风月谈》3篇,分别是《关于翻译(上)》《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一九年秋》《归厚》。这些杂文都是在议论内政和指责“帮闲文人”。
据鲁迅日记记载,《保留》与《再谈保留》都是鲁迅在1933年5月17日写成,并于5月20日寄稿给黎烈文;《“有名无实”的反驳》和《不求甚解》则都是鲁迅在1933年5月18日写成,并于5月21日寄稿给《申报·自由谈》,鲁迅之所以分两次寄稿,是与鲁迅写作杂文时认真的态度有关,鲁迅很注意字句的修改,在文章写成之后,他会反复推敲语句,务必使它更加准确、深刻地表达主题。而鲁迅更换邮寄对象,是与当时邮电检查所对书信的审查有关,他们有权检查任何信件,而短时间频繁与同一个人通信可能会引起怀疑,邮电检查员会根据寄信人和收信人来主观臆测,因此鲁迅不得不更换通信人。不过,尽管鲁迅如此认真谨慎,这四篇杂文最终也都没有逃脱被禁发的命运,这直接与杂文所谈论的内容有关。
在写《保留》那一天,国民党高官黄郛正打算北上,其专车驶入天津站台时,被人投炸弹,而只有17岁的工人刘庚生被当即逮捕,他被诬称受日本人指使,并被枭首示众,紧接着国民党政府伪造舆论,来掩盖黄郛北上的真实意图。鲁迅当日便在此文中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认为受日人指使的不可能是儿童和少年,他还指出“谁是卖国者”[5]137且看来日。鲁迅写完该文后14天,黄郛便同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了《塘沽协定》,用行动证明了“谁是卖国者”。七月十九日,鲁迅在文末附记:“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5]137
鲁迅在《再谈保留》中分析了一系列的事实,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即一面下令对侵略者“屏用”“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5]139,一面又栽赃无辜百姓为汉奸的卖国行为,鲁迅认为他们强加在群众头上的罪名,最终会反弄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来。
在《“有名无实”的反驳》中,鲁迅在开篇引用《申报》上刊载的《战区见闻记》的一段记载,接着依次驳斥了报纸所载国民党军官宣泄对战事不满的谈话策略,尖锐地嘲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不抵抗政策,进一步揭露当局不仅不反对敌国外患,反而招引敌国外患来欺压普通百姓。
在《不求甚解》中,鲁迅详细地剖析了美国总统的“和平”宣言和国民党当局“誓不签订辱国条约”的经文,借助日本电报通讯的注解,撕破盖在事实上的黑布,直击国民党政府向百姓隐瞒事实的真相,并在文末讽刺说这类文章“是注释不得的”[5]144,人们只能“不求甚解”。
《驳“文人无行”》写于1933年7月5日,鲁迅当天就寄稿给黎烈文,但在7月17日被退回,后来在出《伪自由书》的单行本时,收录在该书的《后记》里面。鲁迅撰文目的主要是为了反驳《谈“文人无行”》[8],谷春帆在文章中对“文人无行”表示赞同,认为中国文坛“污秽不堪”,并讽刺了曾可今、张资平等人。谷的文章发出后,引来张资平刊登启事,以澄清《申报·自由谈》腰斩张资平小说一事。接着黎烈文刊登启事来解释这件事,鲁迅进而针对黎烈文的启事向他提出了几个疑问,黎在回答过程中又提到“鲁迅的批评”。鲁迅还在文中提到文人“改行”,提及“第三种人”的叛变,倒戈相向左翼,提到当时张资平的“三角恋”小说、手淫小说,直接指出他们的撰文目的在于赚钱,吸引读者眼球,腐化青年。可见鲁迅对“帮闲文人”的反驳是直接而毫不留情的。
在《关于翻译(上)》的文末,鲁迅写道:“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6]106鲁迅在文中论及“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学,并将材料中的事实和观点结合,有理有据,推翻了“帮闲文人”所拥护的“帮闲文学”。
鲁迅在《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一九年秋》的文末写道:“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6]132此文的结构是开篇一段小引,接着是8篇报纸材料的照相式罗列,其中有国家大事、正事、轶事趣闻、奇闻以及日常生活小事,结尾用一句话作结,逻辑清晰、层次分明,鲁迅借过去之事来讽刺当下,也正是这些报纸材料的真实性,让国民党当局害怕,他们想要抹去过去的所作所为,因此禁止刊发此文。此外,鲁迅在写此文当天,还写了《重三感旧》,同样是怀古,后者却能发表在《自由谈》上,由此可知,说远可行,说近不行,议前朝的内政行,议今朝的内政不行。
《归厚》写于1933年11月4日,鲁迅在文末写道:“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发表。”[6]179鲁迅在文中议论当时诸多报刊杂志造谣中伤文人,并直接点名道姓,如提到张若谷写的《婆汉迷》、反动刊物《微言》、杨邨人作的《新儒林外史》,所言所指分外明了,若刊发,势必会引来这些“帮闲文人”的口诛笔伐。
二、为何被删、改、禁:鲁迅杂文的社会语境
许广平曾说过:“鲁迅的修改多半是个别字、句,整段整页的删改是没有的。”[9]那么,鲁迅的杂文在刊发过程中是被谁删、改、禁的呢?鲁迅自己曾在《准风月谈·前记》中对被删改的原因做过解释,他认为“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5]。尽管鲁迅说编辑也参与了删改,但若不是有国民党政府出台的报刊杂志的审查法规在先,编辑们也不会轻易去删改作者的文章。因此,笔者认为鲁迅杂文被删、改、禁与当时的社会语境有关,即国民党的审查制度、鲁迅杂文的社会影响。
(一)国民党的审查制度
关于“审查制度”的定义,中国当代学者将“书刊审查制度”界定为“国家或者权力拥有者利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权力对出版物和其它舆论工具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体系”[10]。根据此定义,笔者查找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出台的有关审查新闻和出版的法令法规,发现为了控制舆论,从1927年至建国前,国民党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这方面的法令法规,犹如一张天罗密网,笼罩在当时的舆论界。这些法令法规的制定者主要是国民党中宣部,而实施者则是书报审查委员会,它下面设有新闻审查处和图书审查处,前者主要审查报纸上刊登的通讯和新闻稿件;后者则主要审查即将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与杂志。二者都归国民党中宣部管辖。
关于1933年的审查制度的具体内容,在文艺方面,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官办刊物刊载10月6日所发布的《蒋介石重令禁止普罗文学》[11];蒋介石于10月16日在南昌通过电报传输给南京行政院,下令要更严密地查禁左翼文学,不能让其漏网;10月30日,国民党当局发布《查禁普罗文艺的密令》;11月6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汗血周刊》上发布《汗血月刊》和《汗血周刊》联名发表的《征求“文化剿匪研究专号”稿文启事》,落实“文化剿匪”这一方案。由此观之,国民党查禁的文章都是在宣传普罗文艺、反映阶级斗争、议论国民党政府等,而鲁迅在这两部杂文集中正是这样做的,如《关于翻译(上)》《喝茶》《电影的教训》《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等杂文。
此外,笔者查阅《民国时期查禁文学史论》《民国时期鲁迅杂文查禁情况研究》等文献资料后得知,官方给出的《伪自由书》中的杂文被删、改、禁的原因是“诋毁当局”,《准风月谈》则是因为“不妥”,而不是例举这两本杂文集违反了哪条法令法规,可见理由之含糊、简单粗暴。从1933年的法令法规还可知,国民党的审查制度相较之前越来越严,也让鲁迅杂文的写作越来越不自由,这一点比较鲁迅《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中的杂文也可以见出。首先,前者被删改的部分少于后者;其次,在前者所收录的杂文中,鲁迅变换笔名不如后者频繁;最后,前者写于1933年1月24日至5月18日,后者写于1933年6月8日至11月7日,鲁迅自己在《伪自由书·后记》所言:“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地不能发表。”[5]153-154由此观之,《伪自由书》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追求自由地写作,《准风月谈》是在“风月”的遮掩下谈论“风云”。
(二)鲁迅杂文的社会影响
在上海写作杂文时,鲁迅已是一个蜚声国内外、受人尊崇的大作家,因此,鲁迅杂文具有社会影响力。正如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北平《读书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书报介绍”专栏发表了凡介绍《二心集》的文章,称赞道:“鲁迅的文字之深刻而老辣,读者大概都知道,不用我们多说。”[12]紧接着,1933年7月,瞿秋白编选并为之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华北日报》在八月十四、十五两日连载了普通读者叶宜评论《鲁迅杂感选集》的文章,他在文中分享买《鲁迅杂感选集》时的兴奋心情,称赞瞿秋白的《序言》“确是值得一读的序文”,还认为鲁迅的杂文“使人感到痛快”[13]40。叶宜的书评反映了普通读者对鲁迅杂文的热烈反响。当时的文学史家也研究了鲁迅杂文,如同年九月份,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北京自印出版,他看到了鲁迅杂文的独特性,认为其“在中国实为特创”[13]41。
除了对鲁迅杂文做整体评价之外,还有鲁迅单篇杂文所引起的创作热潮。鲁迅的《推》于1933年6月11日发表后,新一代杂文作者的跟进,使鲁迅的杂文写作在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影响。鲁迅在大家司空见惯的动作行为当中看出其中的奥妙所在,并由此谈出一番与众不同而又让人心服口服的道理,这种思考与写作的方式极具颠覆性和创造性,易于吸引读者的眼光。最早对《推》做出回应的是廖沫沙。他在《第三种人的“推”》中接着鲁迅所讲到的两种推法,认为还有第三种“推”[14]。读了廖沫沙的文章,鲁迅很快又写了一篇《“推”的余谈》。经过读写双方的互动,类似“推”的文章便在《自由谈》上蔓延开来。7月30日《自由谈》上刊出一篇《从“推”到“拿”》,认为之所以“推”还是因为要“拿”[15];8月8日徐懋庸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揣”》,文章讲的是当时的学生“在为投考前先想到出路”,认为这就是汉朝王充所谓的“揣”,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投机’”。但“世事太复杂,变动又太快,端得着的把握,真成‘几希’了。于是结果只能乱‘碰’”[16]。徐懋庸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但关键是写法和鲁迅如出一辙。8月19日周木斋发表了《拉》:“从推和踢,又可联想到与此相应发生的另一现象,但这一现象的别女身是和推踢两者相反的,那就是‘拉’。”[17]周木斋以满族入主中国对汉族士大夫的“拉”证明:“凡操有推和踢的权位者,都有拉的资格,拉的可能,拉的必要”。《自由谈》上由鲁迅所引发的这种写法渐有侵入其他栏目、甚至报刊的趋势。《大晚报》上何榖天的《忆“推”》讲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上课打盹便被洋校长直接“推”了出来,作者认为这属于“第三种推”[18]。10月26日,周瘦鹃主编的《申报》副刊《春秋》上也有一篇《拔的秘诀》,举出“做人的方法,非仅‘推’‘拉’而已。依我的观察所得,做人的道理,还有一个‘拔’字”[19]。《春秋》上此后仍然有类似的文章,如1934年1月16日的《推上下》等。《申报》的另一个副刊《谈言》上12月19日更有一篇同题文章《拉》,指出“拉”的意义就是江湖上所说的“帮帮场子”[20]。由此观之,有了鲁迅的《推》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揣”“拉”“拿”“拔”等,引发一系列跟风杂文。就当时的舆论反应看,除《推》而引起的讨论外,《二丑艺术》《揩油》等也都曾引发不小的反响。
不仅如此,后来《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出版后,也有许多读者进行评论。例如《伪自由书》在1933年10月出版,李儵于10月21日便在上海《涛声》周刊第2卷第4期上发表了《读〈伪自由书〉》,介绍了鲁迅写作和出版《伪自由书》的情况。可见《伪自由书》在当时颇受读者青睐。再者,《准风月谈》在1934年底由兴中书局出版,1935年1月21日《北平新报》就发表了木山的《读完鲁迅的〈准风月谈〉以后》,称赞道:“鲁迅底文章的老练尖刻,和论人的刮毒,只要看过他的文字,谁都不会加以否认的。尤其是这本书里,他把社会现象和文坛情形,统抓到他的笔下,从正面或侧面的方向,尽情批判,对人对事都观察得晶亮透澈;然后从他们的痛处,一针见血。用很平常的小事,射影到很大的问题。”[21]这段评语反映了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对鲁迅杂文的理解是敏锐而深刻的。
此外,在鲁迅以主要精力从事杂文写作、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后,关于鲁迅杂文的争议也日益增多。有人竭力攻击、贬低;有人看到其战斗性和深刻性,但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还缺乏充分的认识;有些好心人则为鲁迅不专注长篇小说的写作、创作大量短篇杂感而感到可惜,正如沈从文曾在《鲁迅的战斗》中回忆:“在这个人过去的战斗意义上,有些人,是为了他那手段感到尊敬,为那方向却不少小小失望的。”[22]168这都说明鲁迅作为当时的公众领袖,他的杂文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之大。而当权者见此状,对鲁迅杂文则更加仇视,这也是国民党当局或刊物编辑在审查鲁迅杂文时,要多次删改其语言文字的原因。若是他们认为鲁迅的整篇杂文都犯禁,则直接将其杂文查禁。
三、审查下的鲁迅杂文:从社会批判到存在诗学
诚然,鲁迅在1933年写作的杂文没有脱离社会批判。他为了争取一个说话的自由空间,让他的杂文演变成社会良知的载体,扮演了社会批评的角色,恰如瞿秋白曾称赞鲁迅杂文为“社会论文”,即战斗的“阜利通”[23]也如沈从文在《学鲁迅》中认为鲁迅“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22]287。也就是说,杂文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是表达鲁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的媒介。的确,鲁迅正是通过杂文,将他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更直接、更真实、更具行动力的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既充满战斗精神,也催人奋发,更强调对社会的批判作用。反过来,杂文以其高度的现实关联性和巨大的艺术涵容性,让鲁迅从一个体制内的学者脱胎为一个自觉而独立的社会批判者。而这样的社会批判者,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学审查之下,必须无时无刻不准备承担批判所带来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风险,故而也特别能够考验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
尽管鲁迅在杂文中批判了社会,但不能忽视的是鲁迅杂文的主角仍然是社会中的人,是这些人的生命形态和存在状态,如在《爬和撞》《推》《“推”的余谈》《踢》《冲》等杂文中,鲁迅审视了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不仅如此,鲁迅在自己身上也践行这样的审视,如在《电影的教训》等杂文中。因此,文学审查之下的鲁迅杂文也是一种存在诗学,即鲁迅杂文在更主要的意义上是贯穿着一种生命主体的心路历程,使其具备了与社会批判共同存在的诗性,鲁迅在杂文中所建构起来的独具特色的议论方式,不仅形成了鲁迅杂文所特有的艺术修辞,也让鲁迅杂文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诗学力量。一直以来,学界把鲁迅视为文学家、思想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不能否认的是,鲁迅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个体,他的杂文写作首先呈现的也是他自己的生命心路。可以说,在鲁迅批判社会的背后,其深层的精神基础是他自身对抗专制、反对强权、脱离虚无的战士般的生命抉择。换句话说,鲁迅在杂文中批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鲁迅杂文所抒发的感情、所描写的种种意象,都从不同角度有所侧重地展现出精神战士的存在诗学。因此,写作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不仅是一种鲁迅揭露现实社会的方式,还是一种他真正超越虚无、实现自我价值意义的生命方式,也就是说,杂文写作是鲁迅自觉追问与自觉创造并存的一种生命形式,显示着鲁迅旺盛的生命活力。同时,鲁迅杂文作为一种别样的生命形式,蕴含着充沛的诗学精神、浓郁的诗学情感,清晰的诗学思维以及臻熟的诗意语言,恰如冯雪峰曾评价鲁迅杂文是“独特形式的诗”[24]。追本溯源,鲁迅杂文的诗学特征来自鲁迅自身的思想情感、创作观念和写作动机。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不但拥有一双透过事物现象发现其本质的慧眼,还拥有刚正不阿的人格品质,这让他能撕破现实生活的假面具,进而道出人生真相;他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使他在枪林弹雨中依旧淡定从容、冷静旁观;他深刻而驳杂的思想能让他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被掩埋的真理;他广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的杂文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正是因为鲁迅杂文是一种存在诗学,才让鲁迅在国民党政府的审查之下,竭尽全力反抗,并从未停止杂文的写作。也就是说,尽管国民党政府的审查一方面制约了鲁迅杂文的自由写作,另一方面阻碍了其快捷而顺畅地发表,但反过来也刺激了鲁迅杂文的写作,审查愈严,鲁迅愈专注于杂文写作,杂文也愈来愈多。此外,鲁迅自从1926年南下任教后,就没有打算成为御用文人,所以在上海脱离学院生活己五年多的鲁迅,也不可能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当鲁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学审查,面对他的一篇篇杂文遭遇删改禁时,他感到已在逐渐丧失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如果不进行回击,他也将会和叭儿狗一般。他需要坚守他作为自由撰稿人这一身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国民党的审查进行对抗,恰如和鲁迅同时代的人所评论:“对统治者的不妥协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嘲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22]165但鲁迅不像阿尔贝·加缪写作的散文《西西弗斯神话》里面的主人公西西弗斯一般,只凭着满腔反抗的热情而不停地写作杂文。相反,在严格的文学审查之下,鲁迅考虑的是如何将杂文升级为新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他在杂文接受审查过程中反思该怎么继续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国民党的查禁使鲁迅探究出对抗审查制度的五种新模式。其一,更换多个刊物发表杂文,如鲁迅除了在《申报·自由谈》上刊发大量杂文之外,还在《译文》《现代》等刊物上发表杂文,可以说这些刊物在国民党的文学审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在杂文中运用曲笔写作,委婉含蓄,如《观斗》《二丑艺术》《不通两种》等杂文,由此及彼,指桑骂槐;再如《文章与题目》《晨凉漫记》《多难之月》《重三感旧》等杂文,借古讽今,揭露现实。其三,变换多个笔名,尽管鲁迅在《伪自由书》中只使用了三个笔名,但在《准风月谈》中,鲁迅却使用了二十来个笔名,平均约三篇变换一次。其四,将发表时被删节内容加点补充在出版的结集里,如《准风月谈》中的《踢》《新秋杂识(二)》《同意和解释》等杂文。其五,结集出版通篇被禁止发表在报刊的杂文,如《保留》等四篇被禁发的杂文被收录进《伪自由书》中,《关于翻译(上)》等三篇被禁发的杂文则被收录进《准风月谈》中。可见,鲁迅是在与国民党的文学审查周旋,这样的周旋不是出于胆怯和退避,而是一种“壕堑战”、“持久战”、“游击战”,是他对生存与斗争方式的新选择。正是鲁迅在与文学审查的周旋之中,把杂文写作推向了一座前所未有的高峰,并逐渐演变成一种蕴含存在诗学的文体样式。鲁迅也深知妥协是弱者的姿态,盲目是愚者的行为。因此,鲁迅杂文的每一种新的对抗模式既是极具智慧的,也是英勇果敢的;既是直接尖锐的,也是蕴含策略的;既是鲁迅生产杂文方式的独特转变,也在暗中隐藏着鲁迅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背后体现的是鲁迅对生存意义的永恒追求。
探究鲁迅杂文作为存在诗学的起点,可以发现它是以鲁迅的生命体验为逻辑起点的。鲁迅一生多次历经流血和欺骗,如“三一八”惨案、女师大风潮、“四一五”事件、五卅运动等,这些使得他必须用冷眼赏鉴人间百态,并以最快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写作出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不仅如此,由于鲁迅这一创作主体精神的强健,再加上个体生命的桀骜不驯,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并执着地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促使他将自己的艺术素养与创作活力融入进目下的现实生活遭际,进而碰撞出璀璨的思想火花。但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与他的理想愿望、所追求的精神家园不相符合,这就导致他一生陷在孤独、寂寞、焦灼、绝望之中。的确,纵观鲁迅运用生命意识写成的杂文,蕴含着强劲的生命力、荒凉而执着的灵魂,如《帮闲法发隐》《新秋杂识(二)》《同意和解释》《禁用和自造》《冲》《外国也有》等杂文。此外,鲁迅杂文作为存在者的绝叫,蕴含着鲁迅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因此,鲁迅写作杂文则是一种生命意志的抗争。同时,鲁迅杂文蕴含的生命意志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换句话说,鲁迅通过写作杂文,富有深意地向读者陈述了杂文写作与他作为生命主体之间的直接地创造性关系。他似乎在清楚地向读者传达着他的杂文写作已成为他真正在人世中存在过的一个证明。虽然时过境迁,在阅读鲁迅杂文时,读者难免会对杂文所讨论的内容感到有些陌生,对鲁迅文字背后的特指不甚了解,但若是消解了这些障碍,再进入鲁迅杂文,就会发现陌生之中蕴含着鲁迅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接着读者细细品读这些杂文,会察觉到似乎每一篇杂文都是鲁迅在揭露与对抗、反思与否定、批评与进攻,从而实现鲁迅自己生命体验的表现、思想观念的表达、价值取向的传播。这样,当读者与鲁迅一同面对当时的苦难现实,则会感到鲁迅思想的深邃;与鲁迅一起经历绝望时,则会增加读者自我的生存勇气和生命活力。最后读者会发现鲁迅通过杂文创造了一种存在诗学,其核心是冲破现实中的一切精神枷锁,战胜一切扭曲人性的力量,获得释放和解脱。总之,由于鲁迅杂文是对现实人生的议论,是对人的生命本真的照亮,所以它开启了读者对生命的领悟,其蕴含的诗学力量也正在于此。
但是,作为一种存在诗学,鲁迅杂文又不仅是鲁迅的个体生命体悟,还是生存的言说、自我存在的言说。可以说,鲁迅杂文的写作是为了展示自我存在的价值,是一种渗透了存在意义的情感活动,呈现的是一种具有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生命形态。这样的生命形态蕴含着鲁迅这一创作主体对他自身生存状态的体悟,并通过自我存在显现出来。概而言之,鲁迅杂文是一种指向存在意义的写作,是存在着的反思,或反思的存在。鲁迅将自己贯注其中,感受着、挣扎着,探究现实生活中蕴含的真理,让他的杂文不仅具有厚重的现实感受,而且还有一种对现实生活形而上的思考。逐渐地,这样的感受和思考让他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学审查之下,形成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生存形态。也就是说,鲁迅杂文是存在着的启蒙知识分子基于其现实社会中的是非善恶而发出的呐喊,显示着鲁迅独特的生存形态。可以说,审查下的鲁迅杂文,让鲁迅既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也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和存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