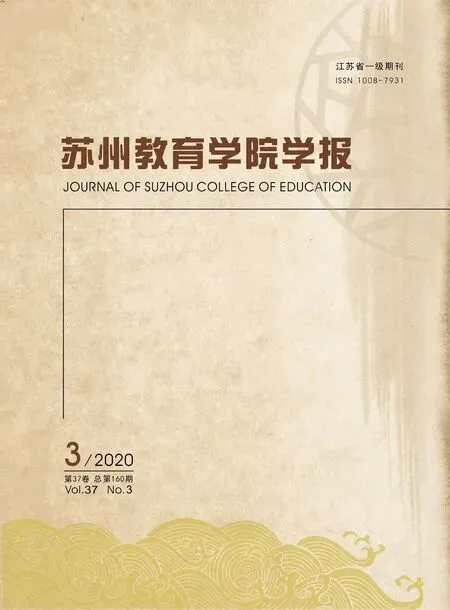虹影《饥饿的女儿》中的不可靠叙述
2020-02-25汪梦玲
汪梦玲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确立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修辞方法。以阿格萨·纽宁和塔马·雅克比为代表的认知派叙事理论挑战了修辞方式以隐含作者为判断依据,提出了以读者规范为标准。在修辞方法的话语体系中,当叙述者偏离隐含作者的规范时,叙述者被认定为不可靠,但“隐含作者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清、不易把握的概念”[2]84,确立隐含作者的规范更是不易。“对读者而言,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或者叙述者的视角与读者自己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叙述者的不可靠。”[3]安斯加·纽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可靠叙述者往往会表现出一些文本矛盾,其中既有故事与话语之间的矛盾,也有文本外围的元素。”[2]91这种偏向于认知方法的界定为探寻文本叙述的可靠性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线索。《饥饿的女儿》[4]是虹影第一本写自己的小说,她多次强调小说内容的真实性,甚至称之为自传。但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在书写时借助回忆,对过往的事实和情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遮蔽扭曲,造成其创作意图和最终文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不可靠叙述,小说人物六六在家庭和爱情方面的叙述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靠。《饥饿的女儿》中的不可靠叙述体现了虹影思想的历时性差异和小说意义的多元。在分析不可靠叙述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窥见虹影创作时思想的游移与分裂,体会虹影对往事矛盾的情感态度。
一、隐含作者关于家庭叙述的矛盾性
自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后,学界产生过偏向“隐含”和偏向“作者”两种代表性的变义,申丹认为这两种解读都是对布思本义的误读和偏离。在谈论隐含作者叙述的矛盾性时,首先应当明确本文所采用的隐含作者的概念为布思的本义,即“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出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5]37,且“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会读到的东西’,作品是隐含作者‘选择、评价的产物’,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5]38,“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分只是在于日常状态(一个人通常的面目)与创作状态(这个人创作时的面目)之间的区分”[5]41。虹影曾在访谈中说起有关母亲的写作:“我不想把她写成一个神话,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母亲,有血有肉,会笑会哭,会叫喊也会容忍,更是软弱无力。”[6]显然,该小说的隐含作者追求叙述的真实,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文本实际上偏离了这样一种规范,构成了一种矛盾冲突,这也符合前文中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义。
首先,隐含作者的不可靠叙述与记忆本身的不可靠有关。《饥饿的女儿》采用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相比“异故事叙述”,同故事叙述更容易产生不可靠叙述,如里蒙-凯南所说:“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述者的知识有限,他亲身卷入了事件以及他的价值体系有问题。”[7]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回忆发挥了重要作用,“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会走向美学化,利用记忆中的某些内容,再加上想象,将自己建构成某种角色”[8]。而从心理学层面看,“记忆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的心理过程……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回忆和再认是提取信息的过程”[9]。在通过回忆进行书写时,一方面叙述者很难将所有相关记忆都呈现出来,会遮蔽或篡改不和谐部分,造成一种错误叙述或者不充分叙述;另一方面,在重组和编码过程中,隐含作者很可能不自觉地作出道德上的修正而破坏叙述的可靠性。简言之,回忆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么在依托回忆的写作中,隐含作者自相矛盾便不难理解。
如《饥饿的女儿》中对母亲外貌的两次描述之间就存在不可靠叙述。首次展现母亲的外貌时,文本正忙于展现母亲与“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4]13,此时母亲的形象是“眼泡浮肿,眼睛混沌无神……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短而臃肿”[4]13。但当展现母亲与养父之间的爱情时,有关一张照片的记忆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照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着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眉眼很沉静,甚至还有一点忧郁……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4]100。需要注意的是,看到照片这件事发生在首次回忆母亲形象之前,那么首次回忆时显然有一种对事实全貌的遮蔽。同样,文本着力展现“我”在家中仿佛多余人的地位时写道:“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4]9但在后文的叙述中,我们得知母亲带着四五岁的“我”去寺庙时:“回过头,发现母亲看着我,温柔极了。”[4]202由“从不”“绝不”等词构成的彻底否定,被这一次温柔的目光所瓦解,读者有理由怀疑有关母女关系的陈述的可靠性。这种前后文本的自相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而隐含作者在初次提及“母亲的形象”和“母亲的目光”时遗漏了部分内容,属于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遇到对应的刺激,叙述者才会唤起某些具体特定的记忆,进而对已有的不可靠叙述进行修正。描写母亲饱经风霜的外貌时剔除记忆中美丽的母亲,描写母亲凶狠的目光时剔除记忆中温柔的目光,这种叙述策略无疑加强了文字的表现力。而当不可靠叙述被揭露时,又产生了一种反讽的修辞效果。
隐含作者的书写意图是对过往生活进行真实记录,如虹影所言:“这是我18岁以前经历过的事。包括讲述的事件、时间、地点、人都是当年的。所以我说是原始记录,像纪录片似的,灵魂纪录片吧。”[10]实际上,作者关于饥荒和“文革”时期的生活的叙述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不自觉地对母亲的形象作了道德上的修正,隐含作者对真实的追求和实际呈现的文本之间形成了矛盾冲突。读完小说,读者由“母亲”从父母家离家出走,又从第一任丈夫那里出走,与当水手的男子结婚后,又在婚内出轨诞下一个女婴的种种事件中可知,母亲是一个在性道德上放纵的女子。但小说有意淡化这一事实,在开头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为了家庭负重前行、身患多种疾病的母亲形象—“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4]12在这段描述中,母亲一生的苦难和为家庭的无私奉献被放大,从而弱化了母亲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在书写母亲与小孙之间的婚外情时,隐含作者突出了大饥荒背景下的迫不得已和情难自禁,两人之间情感的萌动和愉悦都使人觉得这段不伦恋发生得顺其自然。这里文本将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推到台前,为这种反道德的行为进行辩护,实际上与其书写真实这一出发点相背离。
此外,虹影出生于工人家庭,当时的工人有住房、医疗、教育的保障。这个家庭在大饥荒中六个子女都没有饿死,且都接受过学校教育,这足以体现出虹影家庭并没有文本呈现得那般窘迫。在主线之外,隐含作者不时穿插对周围环境、风俗和人物的描写,以图再现当年的图景。在其话语中,这座城市鬼气森森令人战栗,其中的人带有潮湿的鬼祟气和颓废感,组成南岸图景的是肮脏发臭的街道、落后的住房和公共设施,对男性生殖器官和人物吃胎盘吐蛔虫的描写更使叙述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说,《饥饿的女儿》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体现出自我殖民的倾向。虹影坚持写作的真实性,但在实际素材选择以及事件描述中又带有主观化的色彩,造成了小说叙述的不可靠与意义的多元。
二、六六关于家庭叙述的矛盾性
在家庭叙述方面,除了隐含作者的叙述有矛盾冲突,小说主人公六六的叙述也时常自相矛盾,构成一种不可靠叙述。这种不可靠叙述既造成了悬念,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又使人物的性格特点更加凸显。生活在这个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对自己的态度不同于其他兄弟姐妹,而兄弟姐妹对此也冷漠旁观,六六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这个疑惑一直盘旋在她的脑海,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强烈,“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4]42,“他们为什么不肯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4]134。在这种情绪下,六六迫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情感态度也越发激烈。
有关父亲眼疾的叙述最能体现其叙述的不可靠。在第一章六六就交代了父亲病休在家,但父亲为何会患眼疾,直到最后读者也未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最初相关描述是:“他的头摔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断。船从宜宾开到泸州,父亲才被送进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4]40此处,读者和六六一样,认为是工伤导致父亲得了眼疾。直到六六因缺少学费,独自去劳务科问父亲的退休工资时,看到档案上写着“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4]46,六六大声叫嚷不相信。在讲述战争时期父母的故事时,又言:“夜航加班次数太多,加班费不值几文,他的眼睛开始坏了。”[4]105这句话极具暗示性,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过多的夜航班次导致父亲的眼疾。六六并不相信官方的解释,仍然认为父亲的眼疾是工伤。在大姐说梅毒是袍哥头让母亲染上,母亲继而传染给父亲时,六六的反应是:“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呢?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难道爸爸的眼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4]106读者一直被六六提供的错误信息所误导,又在阅读中不断地推翻之前的认知。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最集中的不可靠叙述出现在六六新历生日与旧历生日的错位中。六六与养父记的是新历日期,但母亲和生父记的是旧历日期,因此产生了误会与矛盾。9月21日的早晨,养父给了六六一张崭新的五角钱,思来想去明白今天自己过生日的六六,顿时对去江边洗衣服的母亲心生不满,“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4]59。母亲忘记了六六的生日吗?当然不是。母亲比六六更知道她的18岁生日意义重大,她要在那天向六六坦白她身世的真相。母亲记得六六的生日是一个事实,故而这里六六在事实/事件轴上存在错误报道,对母亲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判断是认知/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母亲为了准备六六与其生父的相认,去城中心找生父一家,因此错过了六六的新历生日。大姐认为母亲是去城中心找二姐,这是大姐的错误判断,而六六相信了大姐所言,“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落我”,“不管新历旧历,她就是故意忘的”[4]78。在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下,六六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她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错误判断,形成了对母亲的错误认知。六六对母亲带有偏见的解读体现了六六对母亲的不满以及母女关系的不和谐。
六六索要学费,但母亲不肯轻易拿出,六六认为母亲对自己有恨:“‘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有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4]135六六赌气说“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4]135,得不到母亲的回应,便认为与她想得一样,在探寻身世一事上,六六对母亲也存在误解,“她认为没必要让我知道家里的秘密,当然我对自己的身世,也不该有知情之权”[4]203,很明显这与母亲安排她与生父见面的事实不符,是事实层面的错误,同样也是认知上的错误。实际上,母亲非常关心这个女儿,除了提前安排六六与生父的会面,小说中巫医一事也能体现。六六左臂扭了筋,母亲带她去看巫医,虽说家贫,但是母亲在得知就诊价格时,二话不说就点了头。在六六离家出走期间,母亲还曾写信让她回家过年。围绕着母亲,六六的不可靠叙述多是在不知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揣测母亲的行为动机和认知情感,这种心理动机一定程度上符合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六六不能准确推测他人行为动机而产生的不可靠叙述,并不仅仅局限于母亲。“大姐也没回家,不知上哪儿去了。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为了避免我的纠缠,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4]139事实上,大姐是去找自己在乡下做知青时的暧昧对象。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叙事进程发生变化。在六六得知真相决定离家出走时,她对母亲有了一次正面的评价:“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我,她真是为我担心。”[4]268这与六六一直以来对母亲的评价相反,却与隐含作者的情感态度保持了一致。
六六的眼光是小说中经验自我的眼光,充当叙述视角的人物眼光是故事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叙事技巧的一部分。当叙述者放弃了本身的叙述眼光,而采用六六的眼光时,读者只能看到六六观察到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当六六产生疑惑时,读者也无从得知事情的真相。虹影在创作时也有意设置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小说第一章便是六六被陌生男子跟踪,却从不疑心那人要害自己,而后写家人对自己微妙的态度。第三章中,六六更是发出了4个疑问,勾起读者探索欲,“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为什么……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4]42-44。六六心中有疑惑,读者心中的疑问一点儿也不比她少。这样的阅读体验比最初读者就知道跟踪六六的男子是她生父,而母亲在饥荒之年有了一段婚外恋,显然更容易凸显出小说情节的高潮。而且,六六的叙述不停地与叙述者、事实发生冲突,营造了紧张的氛围,推动叙事情节不断发展。此外,六六对母亲行为的错误判断,对母亲情感态度的错误认知,在真相大白之时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快感。“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逼迫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4]241此时,六六成为读者嘲讽的对象,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而读者则心领神会地成了接受者。
六六叙述的不可靠凸显了她性格的偏激和母亲的隐忍。在六六看来,她不被善待,总受委屈,家中其他人共享着她不知道的秘密,她在隔阂与孤独中长大,奋力想要“翻身”的她带有反叛色彩与破坏欲。她执意曲解母亲,不信任家人,造成了诸多叙述上的不可靠,凸显了她多疑、偏执的性格。在六六对自己错误的判断或认知坚信不疑时,读者更能理解过往经历对她造成的创伤,对她产生同情。而六六18岁生日还没到来前,母亲一直将她的身世之谜藏在心里,无论与女儿发生多大的冲突,受到怎样的侮辱,也不申辩,而是默默承受整个家庭的苦难和重任,六六对母亲的不可靠叙述反而衬托出母亲的忍辱负重。
三、六六关于爱情叙述的矛盾性
六六叙述中的矛盾冲突在有关爱情的叙述中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六六与历史老师的交往中。在叙述者的眼光中,历史老师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仔细想想,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4]22。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六六眼中成了黑暗中带来温暖的人。两人的交往过程其实很简单:六六在课堂上故意捣乱,课后便走进了历史老师的办公室。一来二去,六六进入了历史老师的私人领域。历史老师有意引诱,六六也乐于接近。最终,在历史老师家中,两人有了肉体关系。而后随着政治清算运动的进行,历史老师忍受不了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六六离家出走后,发现怀孕,便独自去打胎。打胎后,两人的关联才彻底消亡。交往之初,单恋着历史老师的六六在判断历史老师的心理及动机时,常带有恋爱的有色眼镜,平淡的对话被体会出浪漫色彩与情色意味。六六去敲历史老师办公室的门,“‘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在敲门”[4]21。实际上,这只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应答语。历史老师一句“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六六便认为“这么说,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4]24-25“我喜欢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4]26,六六将对方的每一个举动都加上了自己的解读。
这里六六是聚焦人物,读者被限制在六六的眼光里。即使认为六六的判断是错误的,也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有两件事,读者能确定六六的叙述与实际情况有本质的偏离。一是历史老师给六六画的裸体画,另一是历史老师未赴爬山之约的缘由。历史老师给六六画的裸体画最开始在办公室画了头,后来在家里才画了身体。六六的揣测是:“脖子、肩,没有衣领,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纸空了很多,画太顶着上端。”[4]28直到在历史老师家中,他完成了这幅画,六六才知道:“原来他把我的头像只画在纸的上端,就为了等着画我的全身,他一开始就在盘算我。”[4]212读者同样也是在这里意识到,这个中年男人的动机并不单纯。历史老师把《人体解剖学》送到六六家中后,约六六下午去爬山,但他并未赴约,“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4]148。六六认为历史老师欺侮、诱骗少女这不假,实际上那天历史老师被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去谈话,才没能按时赴约,等他赶到约定地点时,六六已经离开。
六六对历史老师行为动机的把握几乎都是不准确的。历史老师是一个相貌、教书都平平的男人,但六六爱慕他,便赋予了他不一样的色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4]113。历史老师因遇罗克的事情对六六发火后,“我气愤又伤心,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4]116。六六对历史老师的认知和态度在不断变化,叙述的可靠性也一直在波动,这是陷入恋爱中的少女患得患失的焦虑心理,也凸显了六六对历史老师知之甚少。读者最好奇的是六六是否真的爱上了历史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以历史老师的自杀为界,六六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这也成了历史老师这条线中最突出的不可靠叙述,“我是爱上他了,他是有妇之夫,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也许潜意识中,这正是我爱他的条件”[4]204,这是六六去历史老师家路上的想法;“我感动极了,脸紧贴他的脸,感到自己爱上了一个值得爱的人”[4]211,这是六六与历史老师发生肉体关系时的想法,此时是六六对历史老师情感态度的高峰。当六六发现历史老师不留一字便自杀后,她对这段关系的评价就跌入了谷底,她重新审视两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就像我那个家,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4]262。
梳理两人的交往过程,读者不难发现,六六后续对两人关系的评价才是可靠的。最初六六以为自己爱上了历史老师,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老师获得六六的信赖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耐心听她讲话的人。至于历史老师对六六的情感,实际上是一种引诱,并不存在六六所认为的纯洁的爱。这一点,其实六六最初就已经察觉到了,第一次被叫到办公室时,六六告诉这个男人,这里有种熟悉感,“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不为人察觉地微笑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和我说话”[4]22,大概从这里开始,这个男人就发现了眼前少女的端倪。六六以为遇到了一生中难得的爱情,认为历史老师也爱着她,读者便也这样认为。直到破绽越来越多,读者才发现并非如此,布思所说的反讽效果在这里也非常强烈。六六下定决心去打胎时,她意识到了自己对“父亲”这一身份的执著,“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者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4]274-275。同时,她洞悉了历史老师对她的态度,“历史老师,在理解我上,并不比我本人深刻,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做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4]275。
多年后,虹影写《好儿女花》时也还是这种看法,经历过婚姻的她对自己的“寻父情结”理解得更为深刻:“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11]“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12],以此为中心的《饥饿的女儿》便成为虹影小说的母本。“私生女情结”“寻父情结”在虹影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这与她特殊的家庭生活有关。母亲外出工作,父亲在家包揽家务,母亲和父亲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私生女情结”与“寻父情结”本出自同一根源,私生女来源于她的身份,而寻父则是随着私生女身份发展而来。虹影本人并未详细阐述过究竟何为“私生女情结”。笔者认为“私生女情结”是指虹影对自己私生女身份的重视与强调,在未发现时,便因为周围人特殊的态度,而对自身身份产生怀疑。发现自己的私生女身份后,又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转而通过写作来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18岁的六六或者说虹影对母亲产生的恨,对父亲的追寻,都可以用这两种情结来解释。
四、结语
《饥饿的女儿》中的不可靠叙述体现了作家思想的游移与分裂。一方面她想要表现出私生女身份对自己18岁那年造成的巨大影响,表现当年的偏执、孤独、多疑;另一方面,她又想写出35岁的自己对母亲的谅解和对家庭的忏悔。“私生女情结”和“寻父情结”对虹影的影响体现在叙述的不可靠中,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与虹影和她家庭独特的政治身份、道德身份与经济身份有关。虹影家庭受打压的政治身份使她的叙述背离了新中国工人叙事;特殊的政治身份导致母亲工作上的被排挤和家庭的贫困,造成了经济身份的特殊;虹影家庭两代女性的身上都发生了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成为性道德放纵的典型。《饥饿的女儿》中的不可靠叙述表面上关于饥饿与贫困,而实际上涉及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在文本中,虹影将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推到台前,为反道德的行为进行辩护,从而造成了小说叙述的不可靠与意义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