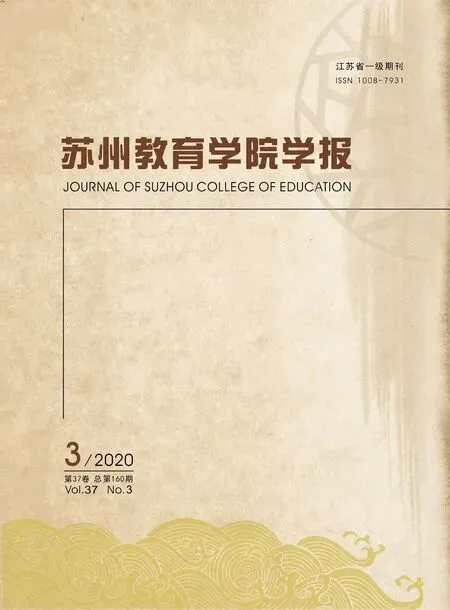远: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
2020-02-25吴静
吴 静
(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远”是中国古人看待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64,形成八卦,从而构成对世界的基本描述。“远”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也是创造时空和心理距离的重要艺术手段。中国古典艺术手段讲究“远映”“三远法”“以大观小”;创作心境强调“心远”“远识”“志远”;美学效果追求“远韵”“玄远”“清远”“幽远”等。可以说,“远”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范畴,远视、远思、远意则是古人看待与理解世界的三种重要维度。
一、远视:突破形质界限
远视是观察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古人常借“登高望远”来表达对无限空间的浪漫想象,而“登高能赋”“登临而悲”更是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重要母题。我国上古时期“远看”概念场就已包括 12 个词项,即“望”“瞻”“瞻望”“瞻言”“望见”“览”“遥见”“遥望”“远望”“远观”“眺望”“观望”。[2]远视产生空间距离,物与物之间清晰的边界在远视中消失,如王维所说:“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如波,高与云齐。”[3]258可见,远视将物体的各种感觉都消解为模糊和色度融合。由于透视无法体现远处山体细节的质感,所以要强调画出山水的“势”,荆浩说:“远则取其势,近则取其质。”[3]266这里的“势”是指在形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视觉“完形”,是一种突破形质界限的视觉延伸。明考斯基指出:“当明亮的和有联系的物体的世界被取消时,与其世界分离的我们的知觉存在就形成没有物体的空间性。这就是发生在黑夜的情况……它就能整个地活跃起来,它是一种没有平面、没有表面、没有它和我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深度。”①转引自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359—360页。这里的“黑夜”是指由于距离导致人的视觉模糊,就像处在黑夜中一样。
中国人常提到“玄”。“玄”的本意是黑色,如“天地玄黄”,后来才发展成深奥、玄虚的意思,如“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4]和“玄者,深远而不可分别之义”[5]。远观世界,天空深邃玄远,世界混沌一片,人的视觉由之前对物体轮廓和形质的物理感知转向对深度的感知。荆浩所说的“势”,指的正是消除了一切空间的物理标准而向深度延伸。中国传统绘画理论有“三远”法,即“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6]。“高远”是仰视,“平远”是平视,“深远”是俯视,“高远”和“平远”反映了静观空间物体并列的物理维度,“深远”则是一种视线的移动,赋予空间以时间感。“高远”展现雄阔凌人的气势,“平远”描绘空阔旷远的天地图景,而唯有“深远”表现了中国艺术最高妙的境界—“玄”。“高远”“平远”若不结合“深远”,画面就会呈现平面效果,难以表现出视觉经验的真实状况。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仰赖于“深远”对深度空间的表现,这是构成写实的宏伟山水意境的基础。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在所有维度中,深度最具有‘存在的’特征,因为—这是贝克莱的论证中正确的地方—深度不标在物体本身上,它显然属于视觉角度……深度显示物体和我之间和我得以处在物体前面的某种不可分离的关系。”[7]326在这模糊了边界的玄远空间里,视觉上的“重叠”与“冲融”带来诗画笔墨上的“重晦”与“清明”,因此形成了诗歌形式的回环与复沓、语言风格的平淡与艰深、绘画笔墨的虚实与开合、建筑格局的“隔中之通”与“通中之隔”。
人的知觉器官在深远空间里不再是对世界的单纯注视,而是一种“介入”,即把自己投入进去,“画家仿佛通过从可见者向自身集聚、回到自身而在事物中得以诞生”[8]。所以远视使人从眼到心都具有感性的自返性,因此这个空间也成了一个以“我”为起点的空间,“我”不是从外部来看它的,“我”就在这空间之中。从字源上看,“远”的甲骨文写为,包括(袁,表示衣物),(又,表示抓、持),(亍,即“彳”,表示行进),即表示带上衣物等行囊长途出行。金文“远”写为,增加了“止”,并将甲骨文的写成。篆文“远”写为,承续金文字形。隶书“远”写为,将篆文的 写成“辵”,也就是。辵,甲骨文写为,是(行,表示四通八达的大道)+(止,表示脚),那么即表示走在大路上。“远”的本意是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衣服等行囊长途出行,走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作为判断的主体。而英语中与之含义相似的几个词,无论是“far”“distance”还是“place”,指的都是客观上两点之间的距离,都没有隐含“一个人”作为判断的主体。所以说中国的艺术空间由于追求深远而成为一种主体投入其中,既是感觉者又是可感者的“主体间性空间”[9]。宗白华称作“灵的空间”,“一种类似于音乐和舞蹈的节奏艺术”,就是“意境”。[10]所以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空间多用“心”去统领,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作者“心”的镜子。市井与朝堂由于“心远”也能“地自偏”,异乡与边塞有了“心”也如家乡与中原。中国古典文学中突出写景抒情的手法,创造了情景交融、心物一体的境界,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11]、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12]、“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13]196。不论是远山、远水、远烟还是远岫、远足、远迹都承载了艺术家深厚的情感。
二、远思:跨越时间进程
中国人的时间观建立在主观深度空间上,而深度空间以“我”的视线为出发点,物体的存在不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为这种视线存在,空间不再是静态的空间,而是一种被赋予了时间节奏的流动且连续的空间。梅洛-庞蒂说:“当我说我看见远处的一个物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留住它,或我仍然留住它,物体在空间的同时,也在将来或过去。”[7]337由远视而远思,从静态的、当下的看,到不断地联想和想象,“思”是对时间的考量,所以中国人懂得回望、绵延、超拔,不会困于客观上的时间流逝,而是赋予空间以时间的节奏,同时也把时间的度量放在一个更长远的视野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升华为永恒。“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13]182、“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14]96、“思接千载”[14]19、“心游万仞”[14]95等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命体验。这样的时间观并非简单的循环,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永恒。方东美曾形象地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时间观比喻为“时际人”“太空人”和“时空兼综而迭遣”。[15]儒家强调时间的“逝”与“变”,《周易》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1]2,“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58,“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65。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6]38因为时间“逝”“变”,所以能远,由远而久,及至永恒,由变化升华到不变。时间之变易、事物之进程都只是趋向永恒的一个步骤,并不是最终的结果。道家认为时间是流逝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7]52,“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18]220,“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18]2,但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时间自然进程的外部体察中,而是将自己从世界万物中超拔出来,站在精神的高处远眺尘世,认为一切进程无非都是“道”的运行,其运行没有始终,万物的进程统统要在生生不息的“道”中失去自己的时间。而佛家则否定时间的流逝,鸠摩罗什说:“凡说空则先说无常,无常则空之初门……本以住为有,今无住则无有,无有则毕竟空,毕竟空即无常之妙旨也,故曰毕竟空是无常义。”[19]“无常”即变化,在大乘佛教中指时间的流动。佛家认为,只有人的“本性”和“本心”才是真实的,如果你的眼光不是聚焦于当下万物变化,而是凝望于未来,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就能相互交融起来,“过去一切劫,安置未来今,未来现在劫,迥置过去世”[20],时间的单向流动被打破,人的想象力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任意穿梭。综上所述,儒家之永恒时间在于变化之生生不息、延绵久远;道家在于精神之旷远;而佛家则在于突破生命短暂的局限而达到佛之超远境界。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经过审美成为情绪的标度和对象。儒家的“高远之志”及“宁静致远”,道家对超越意识的追求成为文人遵循的修养准则及思想共识。如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强调在现实中发扬生命精神,实践理想,落实行动,把个人时间置于生生不息之宇宙,以近推远,以今推古;而咏史怀古型作品则包含强烈的现实意义,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浪漫主义作品富有才情与幻想,具有优游不迫的气度,从当下跳脱出来,将过去的经验直接投射到未来,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8]20的时间永恒。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作品往往从现实出发,目光始终落于未来,往事、今夕、明朝三个时间断面组成一个流动的历史,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从这样的时间流动中感受着历史和人生,生发出喜而复悲、欢而复伤的情绪波澜。
三、远意:超越主客对立
当人远视世界时,空间中事物的边界模糊了;当人在悠远的时间中看待历史时,事物的变化、生死的矛盾消失了,人的心变得不受形质和变化的限制。“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21],时空之远最后引申为人的精神和境界之远,即心之远和意之远。“心远”“意远”可以拉开创作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使内在意志从对象中解脱出来,实现“物我融一”。儒家认为,人生的主要困境是个体不容于社会,如“不用”“不遇”“居隐”“处困”“不容”等,其解决之道在于远离世俗与私欲,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即“见独”。“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1]3,“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1]27,“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8]15,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30从空间上来看,人与“仁”永远有距离,但是只要心理上不远离、不抵制,就能做到与仁接近;道家认为“远”是“道”运动变化的重要规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52,“道”与“大”“逝”“远”“返”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圆形”的轮回,因此,“远”是“道”返回自身的重要途径。肉体与精神想要解脱,想要与“道”接近,就必须要“远身”。道家认为,人生的困境在于人有生死,有“命”,有“时”,有情和欲,而这一切都在于“有身”。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18]12一旦“有身”“受形”,不免受外物牵绊,所以首先要“远身”,即“堕肢体,黜聪明”[18]78,才能“远意”,即“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8]78,此即“心斋”和“坐忘”,从而形成审美心理距离,达到虚以待物、超越现实功利的最高艺术境界。老子强调“涤除玄览”[17]21,“致虚极,守静笃”[17]34,“玄”即幽昧深远,排除主观欲见,保持内心的虚静。庄子强调“远游”,“吾游心于物之初”[18]206,“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18]24,在“游心”中天地由远而玄,形质变得模糊,万有化为虚无,无己、无功、无名,完全把自我融入自然,彻底消解了我与世界的边界。到了魏晋时期,这种“意远”又演化为一种玄风,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其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对抗虚伪的名教观念,追求一种风流玄远的人生境界。在艺术上,这种主体“心远”“意远”的创作心境与品格修养往往形成含蓄、平淡和“韵之远”的艺术审美风格。如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17]91其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的“希”与“无”正是这种淡远和虚静的风格。具体而言,佛家彻底否定世界的一切,认为眼目所见皆是“妄”,只有念念无著,于世间万事万行中不计较执著,心无所拈缚,才是处于解脱状态的“净”。这种解脱,何尝不是一种遍历一切后,重新透过永恒之光,观照法满境界的心远和意远呢?总而言之,儒家“见独”靠的是道德砥砺和人格超拔来制造审美距离;道家“心斋”则是用安时处顺来保持审美心理距离;佛家“无著”是通过否定一切来超越心理距离,三者都是“远意”在中国古代思想上的重要体现。
文学之远意,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意境,无论是《诗格》中的“意阔心远”[22],司空图所言的美常在咸酸之外[14]261,还是严羽“水中之月,镜中之象”[14]320,都是对诗作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最好诠释,也是一种平和、冲淡的审美追求。对于音乐而言,“远”是一种超越具体和有限的弦外之音。在《溪山琴况》中,“远”位列“和”“静”“清”之后,为第四况。[23]389-390它是一种超越感觉之上的神思活动,能让主体充分领略音乐的美妙意趣,“音至于远,境入希夷”[23]390的“希声”之乐,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志趣,尤其是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雅乐”,代表儒家审美理想的“中和”,追求道家审美理想的“淡远”。乐以致远,乐以养气,写出“心远地自偏”[24]名句的陶渊明才会置无弦琴一张,时时抚弄,作无声之奏。中国山水画家讲究“咫尺万里”,“士人画”尤其追求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和“萧散简远”“高风绝尘”的风致,宗炳“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3]252、顾恺之“西去山别详其远近”[3]251,还有沈括的“以大观小”[3]271山水画创作法和郭熙所说的“三远”技法等,都是从绘画创作角度对“远”的精彩论述。总之,远的超越性正是在于超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不和谐,虚化自身的存在性,最终实现内在精神与外在精神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远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家们登高望远、寄情玄远,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3]252中,将自我的潜力发挥到极限,以求身与物化、意与物泯的宇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