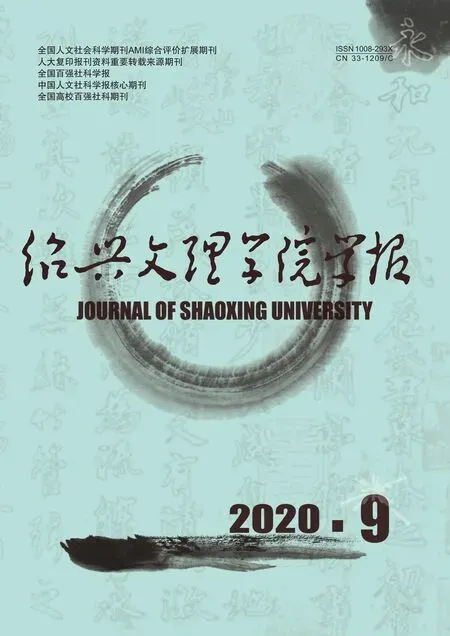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小说史大略》与鲁迅早期的现代小说观
2020-02-24汤昭璇郭冰茹
汤昭璇 郭冰茹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8000)
在1919年时,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知道自己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1]在此前一年里,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而在此后一年,鲁迅走上了讲台,在北京的高校开始讲授一门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课程——为《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由于《史略》本身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从初期、发展到成熟,鲁迅个人的小说观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现今能看到的《史略》在鲁迅生前共印行十一个版次,1935年6月北新社第十版时又进行了改订,自此以后各个版本均与第十版同。其中目前发现的相对早期的版本有1921年发布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以及1923年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铅印本在油印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从原本的十七篇内容扩充到了二十六篇内容(1)详细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版本演变及版本之间的差异,请参考吕福安《〈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变》,见《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61-80页;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技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汪卫东《〈中国小说史略〉的编定于出版过程兼及两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就这两个版本的差异,陈平原也曾评价道:“改动处甚多,远不只是篇幅的大小、论述的详略。”[2]在《史略》的不断再版中,鲁迅不断对文本中的小说史料和内容进行补充、修正,同时也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小说史观。所以《史略》文本的版本选择也极大地影响着鲁迅小说观的呈现。本文主要探讨对象为鲁迅前期小说史观与其早期小说译作、著作的联动,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与其早期小说译作、著作的联动能够更为立体地呈现出鲁迅在现代小说生成之初的小说观。
固然,使用油印本作为鲁迅小说观探讨的蓝本是存在局限的。以课程讲义为主要用途的油印本包含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勾绘小说史观也多采取点评结论的方式,总体并未形成非常成熟的理论形态。同时,如今我们难以见证鲁迅在课堂上的具体实践状态,从而进一步探讨油印本中呈现的小说观的内涵。但依循油印本,我们仍然能看到鲁迅《史略》中小说观的雏形——带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以及对小说文体虚构性的重视和强调。
一、小说观建构背后的进化论思想
在油印本中,鲁迅运用史学的方式将带有“小说”意义的传统叙事文学结构起来,在其文本所呈现的建构形态背后有着鲜明的进化论色彩。
相对于1935年6月后的第十版《中国小说史略》,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并未在一开始就出现对“小说”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梳理和范围确定。在1935年6月版《中国小说史略》中,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开篇解决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名实错位的现象(2)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名实错位现象可参看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一章,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24页。。
在全书最开头,鲁迅就将“小说”这一词语放置到了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之中,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起,讨论“小说”语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意义与内涵。但这样一个对“小说”语词历史内涵发掘的环节在油印本的开篇中是缺失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仅梳理了《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收录,而并没有对“小说”一词的内涵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变化做出阐释。不过,与发展达到成熟状态的《史略》相比,《小说史大略》也并非全然罔顾“小说”这个语词的内在含义解释,而是择取《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文本中对“小说”的界定和解释: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隋书·经籍志》)[3]
即使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修编与调整,这两则材料仍然在鲁迅《史略》的文本中得以保存,可见倘若要涉及“小说”的概念,此两则讨论传统“小说”内涵的材料是无法绕开的。在征引了两段材料后,鲁迅并未对其进行直接正面的分析与阐释,也没有生成日后“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个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3)选自《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记录稿,经修改1925年3月发布于西北大学出版社《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31页。“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4]等论断。而是在整理汉代至宋代史家对小说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展示出朝代更迭状态下史家对于小说态度的转变。
鲁迅在自己梳理史料的过程中也已经意识到了“小说”这种叙事文体边缘化的地位和不断脱离传统史传叙事的生长路径。虽然油印本尚未呈现鲁迅后期相对完善的“小说”概念,但是我们仍能够感受到鲁迅对“小说”概念究竟如何与其所处的历史脉络互动的关注。
将“小说”放置到整个历史中,运用“史法”梳理小说的方式,贯穿了油印本的全篇,并在其后出版的《史略》中沿用。鲁迅曾在1930年的题记中提及“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5],可见他比较认可这种以朝代为限划分小说史的方式。
油印本采用了这种治“小说”史的方式,将“小说”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展示,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试图对中国的传统叙事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关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叙事文体在历史中的各个朝代所呈现出的形态。油印本中阐释神话与传说的形成,汉代、六朝、唐朝以及其后宋、元、明、清的各种叙事文学内容的生成,无不联系到了文学生成的外因。例如,神话传说生成是由于华夏之民生长的“黄河流域”以及孔子“实用为教”的因素;六朝神异之说广泛流传与道教方士的关系密切;唐朝传奇的生成与道释二教的盛行息息相关;宋时通俗小说的诞生与当时市民文化兴起、说话艺术的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狭邪小说”在“士大夫挟妓有禁,然不云禁招优人”的背景下诞生,借用史学的手段,鲁迅描摹的小说文体发展过程呈现出史学与文学的互动,展示了外在的社会因素和具体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但是在这种“史法”所展示的现实社会环境因素的背后,鲁迅更关注到整个具体社会环境因素中生长出来的人们的思想、情感乃至精神状态。以《神话与传说》一章为例,除却关注华夏民族生长的地域环境和“实用为教”的思想体系,这些影响文本的外部因素,鲁迅还关注神话、传说文本中呈现出的时代的精神动态,“然案其实,或当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祉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能为神祇”,在鲁迅看来,在原始信仰松动而未褪尽之时,人们的认知仍处于人神淆杂的状态,所以认为人神鬼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说文本展示出的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互动的关系,也被鲁迅捕捉。
鲁迅以朝代更迭的结构框架创作《史略》,在着重于提高“小说”文体地位的五四时期是极有创见的。此前陈西滢曾疑鲁迅《史略》相关著作有抄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之嫌,也因此引发了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鲁迅本人也就此事回应,认为盐谷温的书虽为参考书目之一,但其内容却有诸多差异。鲁迅对于传统文学作品采取积极吸收的态度,并且吸收在西方思想基础上形成的“诗歌小说独创为贵”的基本观念[6]。反观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虽然从体例上来看与《史略》相近,都是从朝代更迭的框架下梳理“小说”文题脉络,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各时期内部小说的生长状态仍然采取并列的关系,作为“小说”文体本身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更迭演变并没有得到展现(4)关于相关论述详细见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在油印本中,鲁迅也已经表现出对小说文类本身在历史中的演进的密切关注,发现小说随时代演进而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比如讲到唐代传奇文就有“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改进,虽大抵尚不出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发达之迹甚明”“故其传奇,亦多工妙,后之友文人,每始其事为词曲焉”的观点,提及明代即有“明人之讲史,所创作殊无以胜于前人”“似自唐末至宋、元乃渐渐演为神异故事,流播民间,而此种话本及传说,明代或尚有存者……”的表述。可见,鲁迅试图勾画小说文类的历史演进过程,让某一种小说文体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在历史的浪潮中迭进、起伏形成其独特的演进脉络,而这种脉络整体呈现出一种“继承与发展”的连贯关系。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既然这种以小说文类自身演进为主要行文结构方式不是取自鲁迅对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本的借鉴,那么它应当是取材于何处呢?
在鲁迅西安讲学的记录稿中提及:“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例如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7]可见,鲁迅认同文艺的“进化”观念,而这种进化论的思想与他构建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的结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在鲁迅的认知中,作为文艺之一的小说,也如人类的历史一样,处在一个“进化”的过程中,并且这种“进化”是一种带有“反复”“羼杂”特点的进化。“进化”意味着不断地推进、发展、成熟,而这一认识也与其早期的小说观产生了呼应和共鸣。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并非产生于结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期间。早在1903年前后,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两部凡尔纳的小说之时,就已经明确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8]在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之时,鲁迅就已经对于进化论的思想有了一定接受。而这种所谓“进化论”思想,并非直接取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来源于晚清严复等人的翻译著作——赫胥黎“社会进化论”。它所强调的不再是生物层面物种的生长繁衍,而是在社会层面“物竞天择”更迭推进的运作机制。社会进化论所宣传的思想也与当时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密切相连。不难想象,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促使“别求新声于异邦”成为知识分子可见的革新之路。当时中国遭受外来侵略,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如鲁迅一样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更直接地碰撞也认识到了西方于工业革命之后强大的力量。除了在“用”——军事、政治、教育等方面他们支持不断学习西方,在文化和思想方面,他们更为主动地接受和吸收,希望能够通过思想上的启蒙来唤醒群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势。赫胥黎提出的“社会进化论”则一定程度契合了他们的期待和需求,并为他们所接受。
所以鲁迅翻译代表“尚武”的《斯巴达之魂》以及“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希望以此宣传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启发民智,让中国在历史进程中能够与时俱进。也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的思想,鲁迅建构油印本中的“小说观”时,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将小说构建为一个持续发展、演进更迭的过程,而并没有选择各时期小说文类并行的建构方式。随着思想更进一步的成熟,鲁迅也对自己的小说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明确呈现出进化论的特点。鲁迅《史略》中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叙事形式,是在其接受的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和发挥的结果。
二、对于“记虚”的重视
鲁迅在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还展示出对小说文本“虚构”和“想象”成分的重视,从而确立起小说最基本的文体特征。
油印本的目录显示出鲁迅对“小说”文类的内部分类,这种分类非常值得注意。在鲁迅以朝代为界限所划分的章节中,有从文体上分类的,比如“唐传奇体传记”“宋人之话本”,也有从内容上分类的,比如“六朝之鬼神志怪说”“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明之历史神异小说”“明之人情小说”“清之谴责小说”“清之狭邪小说”等。鲁迅后来就将在油印本中属于“谴责小说”的《儒林外史》单独列为“讽刺小说”。随着史料的增加修正,鲁迅对《史略》整体的分类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也说明了依照形式、内容的分类没有办法将各个类别界限清晰地完全区分开来。这种分类方法现在看来并不是十分规范,但是对“传奇文”和“话本”的单列成章说明鲁迅已经关注到了从传统史传文中延伸出的“小说”的形式,明确标识出唐传奇文传记体的形态以及宋话本与当时出现的“说话”“讲史”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
其次,鲁迅承认小说脱胎于史传,也充分认识到小说在文学传统中“补史之缺”的位置,他在油印本中所做的重要工作是辨析出小说的文体特征,从史传的影响中确立起小说自身的文体意义和文体价值。《穆天子》起居注原本被归为“史部”的著作,随着朝代变化,因“以神怪恍忽而黜之”逐渐被剥离,而归置“小说”一脉,以示文学传统中史传“补史之阙”的处境。但比之借用春秋笔法记史之实,鲁迅更强调的是小说中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想象”的部分。比如,鲁迅认为六朝时人创作小说《搜神记》的意图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作者不仅相信鬼神真实存在,而且以小说作为证明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正是因为“不诬”,《搜神记》这样的鬼神故事得以在史传文中有一席之地。但是鲁迅将这些著作归入“小说”却是认为这些神鬼之说“称述怪异”,内容“奇诡”,带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色彩。可以说,鲁迅虽然在构建小说史框架时选择将文本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但其看待和理解文本的观念却非常“现代”。
鲁迅对小说文体虚构和想象的看重不仅表现在散落于各篇的“夸诞无实”“幻设”“虚造”等评价,也体现在他对小说史发展的整体认识上,比如他将《世说新语》纳入小说研究,认为这些文本的出现是因为“晋人崇玄虚”以及时人对“清言畸行”的推崇。对于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他强调“其源出于英贤小说,而并虚构人物,寄其理想者”,这实际上看重的也是小说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化、理想化和虚构化的加工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油印本《史略》对“小说”问题“记虚”特点的强调,与“小说”(fiction)这一名词在晚清之后通过翻译手段转换进入中国现代语境存在着一定关联。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小说(fiction)概念的理解源于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此时的西方文学在经过康德“天才”“想象力”等美学思想影响,通过转译进入中国后,理论和感念本身也经过复杂的嬗变(5)相关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关诗佩《唐“始有意为小说” ——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现代小说(fiction)观念》,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鲁迅对于“小说”的理解,可以说是其处于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将西方文学中的“fiction”平移于中国的文学脉络中,便不难形成强调小说文体虚构性的观点。
除了对于小说情节虚构性的重视,鲁迅在审美倾向上也看重小说的“抒情”性而非“叙事”性。在油印本中,鲁迅讲述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内容,并特别选摘了一个片段:
玉沈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负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霍小玉传》)
鲁迅选择这个细节并非是看重其对情节的推动,而是霍小玉面对李十郎时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表达和十足控诉意味的个人独白。在这一段表达中,霍小玉将对李十郎负心另娶、冷漠无情的控诉和恨意,对于自己相思不得、薄命如斯的不甘和苦楚,通过饱含反抗命运意味的诅咒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引文在鲁迅讲解小说史的油印本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对小说抒情性的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他对小说史的讲解中,也体现在他的其他文学实践活动中,比如翻译和创作。
油印本展示了鲁迅在西方“fiction”概念影响下,对“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其内在的虚构性和想象力的重视,也呈现了他个人带着“记虚”色彩的审美倾向——他对小说,尤其是带内倾性及抒情色彩而非铺陈写实情节的小说的喜爱。这种审美倾向与鲁迅早期译作和著作,同时也是鲁迅早期在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西方文学文本存在一定关联。
三、“小说观”与1918年及之前的小说译作与著作
在油印本出现之前,鲁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外国小说的翻译工作,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本身体现的就是翻译者的文学观念。1903年,鲁迅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意在展示古希腊“尚武”的精神品质。对凡尔纳《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类科幻小说的翻译,体现的是“赛先生”的耀眼光晕。但是这些小说都以文言的形式呈现,试图以传统的文言语体形式展示当时认为是更为先进的西方思想,这种译法明显带有晚清时期“旧瓶装新酒”的痕迹。尤其是《月界旅行》,鲁迅运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以诗句总结全篇,甚至沿袭了章回体的套语,以“究竟为着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作为结语。在该时期翻译宣传西方思想之时,鲁迅仍然保留继承着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体式结构。
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安特来夫的《谩》与《默》都具有非常浓烈的个人抒情色彩。《谩》中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进行叙述,作为主人公的“我”,不断倾诉自我面对心爱的人以及她的谎言全过程的心理活动——悸动、酸涩、愤恨、杀意到悔恨,丰富的情感变化以及复杂的情绪表达都在文章中展示。直至文末,对“谩实不死”极端的憎恶到其后意识到“诚无所在”极端的绝望的情感,带着病态和扭曲的色彩,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心绪,形成一种独白式的叙事形态,让小说也具有了诗歌一般的主观抒情色彩。在《默》中,安特来夫设计了两个互相呼应的情节:妇人含泪带血的求情与牧师伊格那支的沉默,以及伊格那支在亲子自杀后声嘶力竭的辩解和妇人麻木的沉默。安特来夫的文本,展示的正是对于个体心灵、精神和情感的重视,以及倾向于个体抒情的表达方式。而鲁迅也曾表达过他对安特来夫的欣赏并与弟弟周作人一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可见其个人对于带有强烈抒情性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倾向。
《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选取安特来夫的小说无疑具有“记虚”的审美趣味。对于个体内在情感、心理的重视,对于小说抒情色彩的追求似乎使《域外小说集》与同时期流行的报章连载小说有着巨大的差异——销量低,受众少。周氏兄弟在该时期的审美趣味也已经和同时代的人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呈现出鲁迅在小说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的“先锋性”(6)关于鲁迅《域外小说集》文本的详细论述可参考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载003年出版。,而这种先锋性也表现在随后的小说史著作——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
与翻译相关的还有鲁迅的小说创作。1913年鲁迅创作了文言短篇小说《怀旧》(“怀旧”该名为后期周作人赋)。《怀旧》使用文言,碎片式地讲述着一个关于“王翁讲故事”的事件。这种结构方式很像是对中国古代话本传统的某种延续。文中王翁一直担任着“说书人”的角色,但他的故事不断被割裂成一个个破碎的片段,无法连缀成篇。在《怀旧》之中,毫无情节进展的故事本身并不是叙述的重心,“夏夜纳凉时候青桐树下的讲故事的场景”才是小说真正的叙述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怀旧》无疑已经开启了一种与‘讲故事的传统’完全不同的想象(或曰呈现)现实的方式:不追求首尾自足的完整,而是力求‘如其所是’地呈现人生的片段。”[9]《怀旧》展示了五四时期“横截面”[10]小说概念的具体形态,而不再是中国传统章回体、话本小说中传统的“故事”的形态了。按照普实克的说法,“这种倾向(用随笔、回忆录和抒情描写取代纯粹叙事)可以看作是抒情作品对叙事故事的渗透,以及传统叙事形态的衰落”[11]。
在《怀旧》中,当王翁正在讲关于长毛的故事,故事被雨天打断时,鲁迅写下了一段话:“余殊弗愿,大类读小说者,见作惊人之笔后,继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则偏欲急看下回,非尽全卷不止,而李媪似不然。”展现出该时期的鲁迅对“小说”这一文类认知的模糊状态。
1913年鲁迅创作这一篇文言体小短文时,他认知内的“小说”仍保留着传统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色彩,是属于一种讲故事性质的叙事文体。其直接提及“小说”的议论内容,明显与《怀旧》前文中的叙事状态形成分裂。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并没有试图完全告别传统叙事模式以及叙事文体的观念。可见鲁迅虽然继承了晚清以来“小说救国”的遗志,并且对于“小说”的认识已有自己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但是在他的作品展示的思维认知中,传统叙事结构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在看到鲁迅在新旧之间勉力进行文学实践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小说”概念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
1918年,鲁迅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鲁迅在语体、篇幅、体例层面上都有了自我突破和发展。《狂人日记》这篇白话小说在语体、篇幅和体例上都具有创新性,它的开头有一段文言引语,但正文采用白话文叙述故事,使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运用日记体形式记载内容,此外在审美风格上延续了《域外小说集》中展示出的先锋性。《狂人日记》呈现出主人公“我”的精神世界,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文本中反复出现“吃人”“被吃”,像是回旋的咏叹调萦绕全文,带着强烈的内倾性,展示着主人公在批判与自我批判状态中极度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夹杂着恐惧、愤怒、疑虑。在《谩》中“我”手刃心上人之后的悔恨,以及无法收获真诚而产生的绝望;在《默》中,无论憎恶还是宽恕都无法消失的阴郁之感,无法逃脱的苦痛压抑,伴随着沉淀在安特来夫小说中那股沁入骨髓的阴冷,在《狂人日记》中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呈现和表达。
《狂人日记》正文部分展示的带有强烈内倾性和抒情色彩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在这个阶段鲁迅对于“小说”概念在认知上可能已经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在《狂人日记》中,“小说”不再是那个“讲故事的传统”的衍生物,而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自我表达意识,在叙述形式上也基本脱离了传统叙事文学的模式。
从《斯巴达之魂》到《狂人日记》,鲁迅的小说译作和著作所呈现出来的小说观念与1920年后诞生的《史略》文本中形成的“小说观”产生互动和呼应。从翻译到创作,从借取到创新,鲁迅在他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认识,也确立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基本的文体特征。
1921年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体现了鲁迅个人带着进化论和“记虚”性质的小说文体观念。结合中国传统史家的方法,鲁迅建构起了如今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整体框架形态。比之同时期的胡适等人对考据之学的追求,鲁迅更关注作为一种文艺体式的“小说”本身,发掘出“小说”自身的文学特点,强调其“记虚”的特征。
在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形成的“小说观”与鲁迅1918年之前小说翻译和创作的文学实践活动存在着密切互动。我们能从鲁迅的一系列文学实践中看到历史进程中鲁迅在新与旧之间砥砺进行的文学实践的发展状态,看到其处于现代转型阶段时对于“小说”矛盾变幻的认知状态。虽然油印本中并未形成如后期《史略》一般成熟的小说观念,但《史略》各个不同版本的文本之间语言裂痕背后所展示的个体思想的变化也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