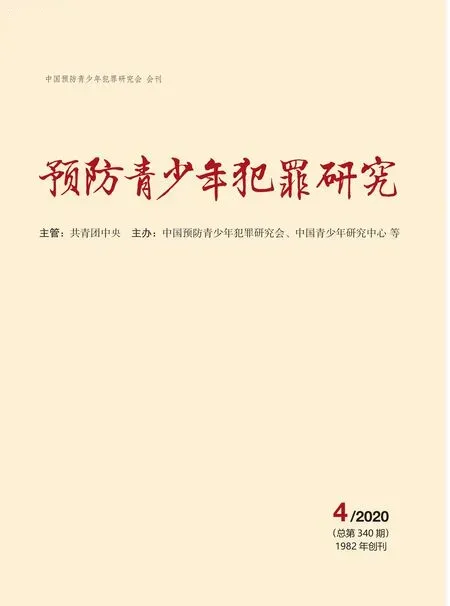英国少年儿童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研究
2020-02-23陈航屈佳
陈 航 屈 佳
目前英国常常把未成年人加以两种区分,青少年(juveniles)是指具有一定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的人,儿童(children)是指那些没有刑事责任的人。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几乎不存在少年和儿童的概念。少年和儿童基本上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它是指身体并未完全成熟同时智力、心理、社会观和道德观并未得到应有发展并且权利应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随着对人权和儿童权利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正视儿童脆弱、依赖和无能以及以权利为基础的儿童福利司法模式并没有很好保护儿童利益的事实。参与犯罪的少年儿童,在认知能力和情感成熟度方面仍处于发展阶段,他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冲动,无法预估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对刑事处罚结果严重性的认识。少年儿童享有特殊权利,以少年儿童权利为基础考虑少年儿童犯罪能力,将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司法系统的两个目标,即预防少年儿童犯罪和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使刑事司法制度转向一个更适应少年儿童身心发育现状的规范框架。刑事责任年龄则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以评估少年儿童的发展。因此,确定刑事责任年龄就成为兼顾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和贯彻公平正义的关键。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数量上升和低龄化的趋势,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发公众与学者的激烈探讨。针对少年儿童所制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是否需要理论和数据支撑以及合适的年龄是什么等问题亟待回应。英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英美法系代表国家之一,也曾面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有关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问题,其处理思路和学说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一、刑责年龄基准的早期构建
(一)刑责年龄意识的萌芽
七国时代威塞克斯国王(The king of Wessex)伊尼(Ine)认为儿童也可以构成犯罪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伊尼法典》(The laws of Ine》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十岁以上的儿童可以构成盗窃罪的从犯。随后第十二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盗窃罪犯罪人被抓后将被判处死刑,除非通过金钱赎回生命。①F.L.Attenborough Russell,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9(1922).由此可见,关于年龄与罪责关系的思考在英国萌发,虽然这一思考的影响只限于单一罪名。由于未成年人也可能因为偷盗被判处死刑,英国早期刑罚不可谓不严苛。盎格鲁-撒克逊法优先考虑采取向被害人和国王支付赔偿金的措施惩罚小偷,但在惩罚时几乎不考虑小偷的犯罪心态和悔罪表现。此类规定表明当时的法律严格维护私有财产权,对侵犯财产类犯罪处罚严厉,即使处罚对象为未成年人也不轻纵。在惩罚时主要责令未成年小偷修复因偷盗造成的他人金钱损失,几乎不关注未成年人的主观方面和教育改造。例如,《阿尔弗雷德法典》(The laws of Alfred)亦规定十岁的儿童参与盗窃视为从犯处罚,需缴纳罚金,并可能进一步承担刑事责任(英国七国时代的法典存在相互借鉴的情况)。①徐良利、段凤华:《<阿尔弗雷德法典>与英国社会的变迁》,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总之,入罪年龄的划定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严苛处罚未成年犯罪人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一时期的设定形成了特有的理念、模式和习惯,为英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了指引和参考。②陈敬刚:《英国法秩序的早期建构——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法律为考察对象》,载《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3 期。统一之后的英格兰国王规定若小偷年龄在十二岁以上且盗窃财物价值超过八便士则应受刑罚,且不允许小偷拥护自己的立场拒不认罪或者逃跑。③Æthelstan’s Ordinances 1.First,no chief shall be spared, who is seized in the act, if he is over twelve years old and more than 8 pence.一方面,国王表明十二岁是盗窃罪入罪的年龄基准。另一方面,若犯罪人拒不悔罪伏法,裁判官则可以突破入罪年龄基准并对犯罪人处以刑罚。换言之,小偷若无良好的悔罪态度,即使年龄在十二岁以下也要接受刑罚惩处,这一规定为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英国早期法律针对个罪设置了一定的年龄门槛,并明确这一规定没有任何人可以破坏。如果说英国早期以保护统治阶级财产权为中心制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中世纪以后,未成年人入罪与否、处罚轻重判断的关键则由财产损害后果转向主观恶性大小,包括犯罪蓄意程度和犯罪的理解能力,法律规定逐渐展现出对未成年人群体身心特征的关注和考量。
(二)双重影响下的刑责年龄
1.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年龄标准
在基督教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时代,英国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犯罪?就教会法而言,1234年格雷戈里九世教皇教令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文中规定,对于没有身体缺陷的未成年人可以定罪处罚,但是相较于成年人处罚更轻。教皇评论,除从十四岁开始成熟的以外,法律不应当规定对犯罪的青少年进行最大限度的处罚。由此,十四岁即成熟即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观念深入人心,但是未满十四岁也不免责,只是在刑罚上进行宽缓处理。④Kuttner Stephan, Raymond of Penafort as Editor: The Decretales and Constitutiones of Gregory IX. Bulletin of Medieval Canon Law 12, p65-80(1982).在十五世纪英国结合教会法的思维方式与罗马法规定,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七岁生日为止的幼年期、七岁至十三岁接近成熟的时期以及十四岁以上完全成熟的时期。七岁到十四岁是基督教中的青少年成熟期,是要求学习社会和宗教规范的时期,也是身心快速发育、开始劳动的时期。自此,在规范意义上根据一定标准划定未成年人年龄段的做法涌现,这为开创阶梯式从宽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提供了思路。
2.无责任能力推定时期
受到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双重影响,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与未成年犯罪人的身心发育情况相关联。考虑到七岁到十四岁之间个人对善恶的理解存在差异,虽然犯罪的未成年人可能会受到与犯罪的成年人同样的处罚,但也形成了刑事责任认定和刑罚减轻的单独判断体系。从现代社会的认识出发,已满七岁即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过于严苛。但是站在七岁应受刑罚的立场上,当时七岁的儿童可以和成年人一样喝酒、赌博和工作,不能拒绝承担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因此,十五世纪以后伴随着以儿童作为劳动力的普遍状况,入罪担责年龄定为七岁。并且,以教会法和罗马法对未成年人的认识为基础,十四岁已达成生理上的成熟。在十四岁之前,行为人若无恶意则推定为无责任能力的做法在普通法上得到维持。
考虑到七岁至十四岁接近成熟期这一年龄层的成长速度和对善恶是非的理解程度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加之当时无法对年龄做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因此接近成熟期的行为人的无责任能力推定采取个别判断的方法。此外,与个人生死相关的户籍制度之类的政府记录长期处于不完整状态,儿童和父母申报的年龄正确与否并不清楚,只依靠年龄无法判断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十六世纪的宗教事务管理者官T.克罗姆威尔对全教区所有的洗礼、婚姻和死亡的事实记录在某种程度上使年龄得以准确确定。①J Charles Cox, The Parish Registers of England, p2-5(2010).然而,事实上不以年龄作为绝对的责任衡量标准并且强调未成年人对所犯罪行为的个人理解的做法有一定道理。
二、社会变迁中趋于安定的刑责年龄
(一)以十四岁为基准的主张
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当时的法学家对七岁即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标准以及在不能推定无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承担全部刑事责任的规定有着不同的主张。例如,Anthony Fitz-Herbert认为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已然形成谨慎的考虑,那么他在那个年龄犯重罪,应当处以绞刑。同时,他认为在刑事领域应当负完全责任的年龄为十四岁,而在财产处分等民事法领域应当负完全责任的是二十一岁。②Boersma,Frederick Lister,Fitzherbert's Natura Brevium: A Bibliographic Survey, Law Library Journal 71(2), p257-265(1978).对英国法产生巨大影响的Edward Coke也认为存在谨慎思考的年龄为十四岁。Coke的十四岁标准虽然独断,但后世的法学家相信并将其理念固化。③Cuthbert William Johnson, The Life of Sir Edward Coke, Lord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James I:With Memoirs of His Contemporaries, p6-11 (1837).此外,在完全成熟的年龄方面,Matthew Hale 认为一般的犯罪和刑罚领域方面的成熟年龄为十四岁,而不应当是更早,并且刑事责任年龄与性别差异无关。已满十四的青少年已经完全成熟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应受刑罚处罚。此外,如果当事人超过十二岁,具有犯罪能力,且在承担刑事责任时能够认识到犯罪行为的性质,他可能会被判刑,甚至执行死刑。如果当事人在七岁与十二岁之间,犯了死刑罪,一般不会认定他有罪,除非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能分辨行为性质的善恶。七岁以下的当事人,由于缺乏对犯罪行为的理解,不承担刑事责任。在当时一名十岁的未成年人,杀了同伴并逃亡很快就被判处绞刑。④Bacon Matthew, Infancy and Age,4 New Abridgement of the Law, p7-9(1832).他们认识到了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年龄的区别,基本形成了十四岁承担全部刑事责任的共识,推行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维持无责任能力推定。但是,年龄只是未成年人犯罪罪责多少的次要判断标准,主要还是根据犯罪者的恶意和行为来判断是否具有刑事责任。实际上,以青少年犯罪心态为主要根据是主观主义在罪责判断上占据主要地位的体现,不仅实践操作难度大,而且存在罪责模糊、难以统一和增大逃脱应负刑责概率等缺陷。一般认为,那个时期受到年龄客观估算不足且信赖度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只能将年龄判断作为次要标准。
(二)不正当行为的发现
此处的不正当行为是指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流氓行为以及犯罪行为。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以城市为中心快速发展,底层阶级迎来了最恶劣的时代,多个城市的犯罪、暴动明显增加。⑤张璞:《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犯罪研究》,云南大学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数据显示,1705-1800年期间英国被起诉的犯罪青少年人数在不断增加。①Clarey Jessie J, Juvenile Crime: Its Causes and Treatment, Police Journal,12(3), p286-300(1939).社会上迁移至城市的家庭贫困问题深化,与此同时对于儿童有利的教育模式和学徒制度影响力衰退,少年儿童违规违法的不正当行为不断增加。17世纪以后,受经济发展和保护纯真儿童文化的影响,家长责任备受关注,父母若不进行妥当监护,少年儿童可能会有恶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将儿童定位为本质上无知的存在,成人有通过经验传授和教育使儿童成为善良、智慧的人类存在的义务。十九世纪基督教新教强调教育和管理,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家庭父权制感到不安,认为儿童应当居于主要地位。相较于之前,人们对少年儿童的权利与特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父母直接抚养孩子而不是交由国家抚养的意识。家长必须对童年的看法和抚养儿童的方式做出个人选择,而且儿童的社会环境因家庭而产生差异。这对儿童的理解力和规范意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父母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尽管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但工人阶级中的儿童周围环境仍然很糟糕。因此他们的不道德和轻微犯罪行为被视为未成年人不正当行为问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由此,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不正当行为从家长责任逐渐转向社会责任。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厂生产和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中产阶级对劳动者阶级革命的高可能性、道德的低水平和高犯罪倾向感到担忧,维持工厂生产的资本家们为了保证劳动者的信用、健康和积极性,将不正当行为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尽快解决。
十九世纪以后,儿童保护和儿童救济运动兴起,在民间卡彭特(M. Carpenter)和希尔(M.D. Hill)提倡对犯罪的青少年采取一些福利措施。②Ashley Henry D, Matthew Hale Carpenter As a Lawyer, Green Bag 6(10), p441-446(1894).卡彭特和其他人最初只是民间志愿组织,但也与政府的少年司法机构展开合作,并对之后的刑事法学产生影响,以儿童为中心的特殊设施、审判和刑罚系统是十九世纪以来的新方式。考虑到社会也负有防控少年儿童不正当行为的责任,有关部门修正并加快变更福利制度。1908年颁布的《儿童法》,设定了少年法庭等保护性和教育性兼具的规定和适用于少年儿童犯罪的程序。尽管少年法庭具有保护意义,但它实质上仍然是刑事法庭,该法在降低少年儿童刑事责任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导致国家崩坏,教育水平衰退,少年犯罪增加。儿童的不正当行为被描述为单纯的家庭和社会两方面蔓延的异常氛围的自然结果。在战争期间,有一种趋势是应安全需要优先考虑惩罚少年儿童,但根据通常理解这样是不公平的。由此,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更低的理由之一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家长与社会都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成年人犯罪不只是一人之责,而是三方之责,刑事审判庭实际上应对三方责任进行分配。
政府少年犯罪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报告书指出:“以七岁为刑事责任年龄标准是数百年以前采用的,自那以后少年儿童犯罪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③Burdiclk,dodd. Juvenile Delinquency.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p1-3(1967).因此,少年犯罪委员会提议以八岁为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在此基础上,将刑事责任年龄定为八岁的《儿童和青年法案》在没有重大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且八岁的标准在1933年的《儿童法》中也得到了施行。选择八岁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似乎存在从福利角度逐步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倾向。
(三)犯罪率持续上升的影响
1.动摇的儿童保护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仍在努力恢复国家福利。为了解决战争中的孤儿问题、规范公权力机构对儿童的保护以及推动其他社会机构营救帮助处境不利的儿童,政府成立了由柯蒂斯(M. Curtis)领导的儿童保护委员会(the Care of Children Committee)。①Masson Judith, The State as Parent: The Reluctant Parent: The Problems of Parents of Last Resort.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35(1), p52-74(2008).该委员会认为,犯罪儿童和被遗弃儿童是战争和社会动荡造成的。柯蒂斯建议为了保护犯罪的青少年,应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十二岁。然而,现实中青少年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在以增加休闲度为中心的亚文化上,社会上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加。②Eekelaar J.M, Children in Care and the Children Act 1975,Modern Law Review 40(2), p121-140(1977).他们的特点是古怪的着装和暴力的行为,其中许多行为包含反社会和反道德的内容。由于媒体的煽动,他们经常被视为具有破坏性的民间恶魔。此外,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每个社区,特别是工人阶级,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均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破坏的担忧。③Scovil,Elizabeth Robinson, The Care of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p664(1902).可见,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与柯蒂斯委员会所认为的不同,因此,前述提议难以施行。
2.1963年和1969年的儿童法
尽管以青少年为中心的亚文化对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反社会和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却引起了社会的厌恶和恐惧。政府为了应对这种担忧,在1956年成立了由英格比勋爵(Viscount Ingleby)作为委员长的省内委员会(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和防止虐待未成年人。④Pratt John, Delinquency as a Scarce Resource.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p293-107(1985).委员会面临的最具有争议性和最终的问题之一是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委员会指出,刑事责任年龄与其认定为八岁不如定为八岁以上更为合理。首先,当前刑事责任年龄远低于其他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次,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少年儿童拥有理解能力的年龄不同,关于未成年人能够认识行为性质和理解犯罪后果而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判断并不准确。并且,缺乏关于身心成熟年龄判断的科学依据,因此无法准确判断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用严厉的刑事手段制裁少年儿童不是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方式,对于少年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国家不能将它作为单纯的刑事问题来处理。国家有必要从儿童时期就全面解决预防犯罪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一项国家义务。而且,委员会还认为,在父母或其他机构没有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法院裁判控制犯罪的少年儿童的刑事责任。委员会建议将年龄提高到十二岁,并呼吁建立新的刑诉程序对十二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出回应,包括减少短期监禁,增强处罚后强制照顾的时间。⑤Anand Sanjeev S,Catalyst for Change: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Juvenile Justice Reform,Queen's Law Journa l24(2),p515-560 (1999).
鉴于委员会的提议,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一项关于少年儿童的新法案。然而,由于少年儿童犯罪人数的不断增加,委员会提出的从惩罚到预防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政府并不考虑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然而,上议院女爵阿宾格(Baron Abinger)提出了一项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十二岁的修正案。最终因为微弱的差异未能通过,但政府方面动摇并提出了十岁的再修正案企图达成妥协。⑥M.Ryan,Penal Polic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ngland and Wales, Four Essays on Policy and Process, p111-112(2003).最后,再修正案被通过,1963年的儿童少年法刑事责任年龄已经是十岁了。第二年政权交由劳动党,劳动党认为儿童反社会行为是由于家庭、学校不负责任导致的,非刑事措施及教育处置十分必要,并且对未满十六岁的儿童少年应当尽量不予刑事处分。1968年的白皮书还建议,十岁至十四岁之间的应罚犯罪应比成年人犯罪的应罚犯罪范围窄。基于该建议的1969年《儿童与青少年法》限制了对十四岁以下少年儿童的可起诉罪名,不包括谋杀罪,但由于专家批评和政府内部混乱,包括该条款在内的其他重要规定仍然没有得到执行。⑦Brit J, Criminology Children in Troubl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2), p112-122(1966).
3.法与秩序的时代
除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外,1970年代英国还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着工会运动和种族主义的挑战。主要政党重视秩序对犯罪的抑制功能,在1979年保守党以“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赢得选举,呼吁采取强有力的刑事措施。十八年来,它已经成为保守党政府的基本理念。自1980年代以来,向公众展示严格的刑事政策和迅速采取预防犯罪的措施是维持政府平稳运作的基本条件。鉴于保守党政府的长期行政管理,其他主要政党认为若要选举成功应坚持严格控制犯罪的理念。自1990年代以来,所有政党都提到了“法律与秩序”。特别是工党借用美国的口号,倡导“严厉惩罚犯罪,严格探寻犯罪原因”,他们开始坚持超越法律和秩序的更严厉对策。在各地都处于暴乱的氛围下,发生了许多震撼英国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在此背景下,没有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余地。
(四)保护与惩处并行
工党在总统选举中呼吁将法与秩序和经济效率融合,受到民众好评,因此于1997年登上了政权宝座。布莱尔政权立即发表了白皮书,提倡严格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考虑将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犯罪预防思想,显示出国家尽早介入的姿态。他认为无责任能力推定容易违反法律,使得本应受到处罚的少年儿童逃避责任,因此,呼吁废除长期维持的该做法。尽管1995年上议院(终审法院)随后裁定了保护儿童免于充分适用刑法的无责任能力推定效力。工党政府谴责了这种无责任能力推定,认为这种推定时常被用于逃避犯罪。根据白皮书的建议1998年制定的《犯罪和秩序违反法》废除了无能力推定,并规定十岁以上的人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该法是英国首部解决法律、道德和社会上的所有脱逸行为的法律。并且出于早期干预的目的,针对十岁以下违法犯罪的儿童采取了公共干预措施,例如儿童禁令。十岁以下的干预当然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以保护儿童的名义进行的一种制裁。但实际上十岁以下儿童犯罪也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导致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形同虚设。据悉,基于这一情况,工党政府时常考虑废除刑事责任年龄。①Stuart Macdonald, Mark Telford, The Use of ASBOs Against Young People in England and Wales: Lessons from Scotlandlegal Studies 27, p612(2007).二十世纪末的工党如此重视与保守党政权时期的区别和有关刑事司法的经费削减问题,为了不过晚介入而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率,试图从正确的方向提出各种对策。
三、稳定刑事责任年龄:基于中国情况的展望
在把握刑事责任年龄特征、目的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基于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担忧与焦虑的背景,探析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来走向。
(一)以社会背景为基础保持稳定
首先,英国刑事责任年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英国刑事责任年龄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调整,引发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更迭,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动向和思想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年龄的下限。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设置根植于社会背景,而不随一些显露的社会现象随意变更。相较而言,其他因素包括儿童的身心发育情况、抑制未成年人犯罪、公众舆论等因素影响力较低。英国刑事责任年龄并非一成不变,但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几乎不存在变化或者仅存在微弱变化。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相关的国际标准,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要求不要将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得太低。而且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劝告英国将刑事责任年龄上调至十二岁,但目前并未得到英国政府拥戴。②Bateman,Tim,“Catching Them Young”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Safer Communities6, p36(2014).但是,英国议会根据联合国的建议,多次提起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升到十二岁的法案,然而都没有获得通过。虽然专家们也有疑问,但是政府明确回答了十岁的标准适当,并维持年龄标准。
其次,英国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从过去以惩罚为主转变为以预防为主。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不是为了保障严惩犯罪,而仅仅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具有犯罪理解力基础上参与刑事审判的统一标准。少年司法制度的中心是预防犯罪、修复犯罪损害并帮助犯罪的未成年人再改造。以汤普森和维纳布尔案为例,汤普森和维纳布尔都是十岁的儿童,1993年他们在郊区一家购物中心绑架了两岁的詹姆斯·布尔格,此前他们曾试图绑架至少两名其他幼儿。他们在一段长达四公里的路上用铁棒殴打他,最后将他留在铁轨上被火车压死。两名男孩在十一岁时接受审判,被判谋杀罪。①Bradley,Lisa,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Revisited. Deakin law review 8, p73-90(2003).男孩们的律师认为十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严肃的审判庭、满是成年人的法院、较强的审判力度等等都违反了法律,男孩们受到了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法院并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只是提供公平审判的基础。②Haydon,Condemn.The Political Context and Rights Implications of the Domestic and European Rulings in the Venables-Thompson Case,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7(3), p416-448(2000).由此引发对设定目的的思考,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究竟是参与刑事审判的简单标准,还是与犯罪能力、犯罪认识有关的惩罚主义的象征?从原因出发,由于未成年人仍处于不理想的非成熟状态,没有健全的人格,缺乏邪恶犯意和对犯罪行为性质、犯罪后果的了解,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之间需要区别对待。用刑罚处罚低年龄儿童犯罪的支持者认为,在个别案件中当儿童对自己邪恶的行为有清晰的认知并积极实施行为时,不需要在刑事责任承担层面上对儿童进行区别对待,因为此时儿童能够认识和理解自己的行为,必须对此负责。但事实上,儿童对于犯罪具有与成人相同的理解能力和自控能力这一结论难以论证。仅从儿童是否有能力或无能力对某一罪行采取适当的犯罪意图这一角度来概念化刑事责任年龄是有困难的。法律体系使用过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依据,一是关于儿童的犯罪能力,另一项是使儿童免于参与刑事诉讼或承担刑事责任,应当强调第二种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年龄理念。③Crofts Thomas, Catching up with Europe: Taking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eriously in Eng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17(4), p267-292(2009).免于参与诉讼或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儿童并非不承担任何责任,仍然会对违法犯罪的儿童采取各项强制措施,并责令家长承担修复损失责任。
此外,上述案件法官还指出,不应将刑事责任归咎于需要游戏放松的人,因此两名被告仅被判刑八年。在1995年,前英国内政大臣麦克尔·霍华德将他们的刑期延长至十五年。但同年,一名英国法官以“腐化的成人监狱不利于两名罪犯”为由又恢复原判。1999年,欧洲人权法庭表示,英国判处两人继续在成人监狱服刑侵犯了正当权益,该法庭督促英国为两名少年犯减刑。2001年,他们获准有条件假释。在服刑期间英国投入超过二百五十万美元为关押和改造他们,给他们安排有质量的教育,还让他们参与戏剧演出、漂筏等活动。受害儿童父母认为凶手得到了奖赏而不是惩罚,因为杀人犯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咨询师和治疗师。④Hay Colin, Mobilization Through Interpellation: James Buldger,Social & Legal Studies 4, p197-224(2005).最终的审判结果并未达到公平正义的要求,这一结果也表明英国少年司法制度以保护和矫正为中心,公平正义只是次要追求。然而,未成年人保护与保护过度仅有一线之隔,过度的保护必然会损害公平正义。这是目前英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弊端,重视预防和保护,却忽视了公正的追求,保护了被告未成年人的成长,却未能保护被害方的利益,甚至传播一种即使犯罪也可以享受良好待遇的观念。
通过对英国刑事责任年龄变迁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而变化,但仍保有稳定性,不轻易受影响而变更。第二,总体而言,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正在逐渐地提升。第三,1996年英国青少年的犯罪率就已高达13%,而中国全国犯罪率的最高年份1991年也不过0.215%,即使较高的犯罪率也没有促使英国运用刑事责任年龄打击犯罪。①张潘仕:《英国的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 年第2 期。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并不仅仅单纯依靠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更多的是依靠制度和福利政策保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对于一个决心犯罪或冲动犯罪的儿童而言影响微弱。因此,落实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才是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良方。
(二)以科学数据为基础保持稳定
近年来,由低龄儿童实施的恶劣犯罪频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以预防和打击低龄儿童犯罪的呼声高涨,反映出报应刑与重典治世的思想。但实际上,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无法一劳永逸的解决低龄儿童犯罪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无法科学判断应降低的程度,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为十二岁,为何不让十一岁的具有犯罪认识和犯罪能力的儿童承担完全刑事责任?难以确定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多少才能有效打击未成年人的恶劣犯罪。第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年人犯罪前大多具有缜密的规划,而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激情犯罪,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也缺少犯罪后果认知。与此同时,让少年儿童承担更多刑事责任,会阻断青少年的成长和自愈,导致青少年在狱中交叉感染。对于青少年的越轨和犯罪行为,不应过早给他贴上标签,这不利于他们之后很好的回归校园和社会,阻断改造之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仅是未成年人本身的问题,更是家庭和社会问题。当父母和社会意识到孩子处于“不成熟的非理想状态”,他们就有义务尽所能来帮助少年儿童走向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中,首先应当界分个人责任、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再划定个人责任的承担范围。第三,《北京规则》中规定,出于保护儿童的需要,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过低。加拿大、欧洲各国等国家刑事责任年龄也有逐年提高趋势,针对邻界的成年人也效仿未成年人来处理。有鉴于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有效方法,应当从根源上思考犯罪低龄化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采取各项管控青少年的措施,例如改革工读学校、建立家长责任制度等,才能有效防止犯罪低龄化。首先,家庭教育不当是青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增强监护人不履行教育监护职责的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②张小华、梁敏、陈立毅、马岩:《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反社会倾向和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 年第5 期。其次,学校教育方面,作为重要的预防与控制青少年犯罪场所,工读学校本应用教育而不是管制的手段来容纳和矫正处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但是,工读学校的发展至今早已偏离原本的定位,改革势在必行。第一,工读学校设定的定位应当明确且统一,只作为矫正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教育场所。工读学校不应当与少管所完全等同,应当兼具职业教育的特征,不能向监狱化的方向发展。第二,工读学校应当明确招收对象,不能将普通学生招入其中,以免招致“交叉感染”。第三,相关规定应当明确强制入读的条件,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实施教育改造,以矫代罚。③姚建龙、孙鉴:《从“工读”到“专门”——我国工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 年第2 期。此外,包括青少年收容教养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在内的其他预防、控制青少年犯罪和教育改造的非刑罚措施均在实体上、程序上以及实际运作上存在许多问题。这些制度本应在防控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上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制度本身饱受诟病和争议,在实际运行中日渐式微。④雷杰:《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困境与完善路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 年第3 期。若要更有效地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上述制度的完善之上。
并且,有必要保证刑事责任年龄的稳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须有理论和科学依据的支撑,不能随意下调。各国的法律规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但刑事责任年龄却不尽相同。因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以国情、本国青少年身心发育情况为基础。设置不能盲目跟风、照搬照抄,不能一味靠拢国际标准。作为一种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的形成与个人的身心发育状况密切相关。而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身心发育状况又与诸多因素相关,比如地理气候条件、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如果青少年的成熟期随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提前,那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有了一定的条件。青少年的成熟期是否已然提前则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否则刑法过早地介入,有违保护犯罪的青少年之宗旨,也与国家责任承担的理念背道而驰。
设定承担刑事责任的门槛是保障公平的考虑,对于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应当适当降低责任或不让其承担责任。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兼顾公平和儿童保护的考虑。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设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一方面是为了有效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另一方面基于成本的考虑,为培养未成年人,整个社会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故有必要给他们一个改变并再次投身社会建设的机会。从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未成年人认识和控制能力都要低于成年人,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对其定罪处罚有违公正观。公平正义与未成年人保护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追求。必须协调公正与保护的关系,目前一些地方过分侧重保护这一方面,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例如,河南省鲁山县检察院对故意杀人案和强奸未成年人案的未成年犯罪分子适用刑事和解,使本需要承担较重责任的当事人重返校园。过分关注保护必然会忽视处罚和公正,导致放纵犯罪。最终,轻纵的未成年犯罪分子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和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很有可能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目前的制度设计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既无法适用刑罚加以处罚,另一方面责令父母严加管教、工读学校等方式又处于失灵状态。只能等到其年满14周岁或16周岁再次危害社会时再加以处罚。社会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相较于之前都会早许多,许多犯罪的青少年与成年人无异。若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则要以大量调查和科学数据为基础。例如,2017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为16.6岁。①路琦等:《2017 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基于未成年犯与其他群体的比较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 年第6 期。不能通过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应当找寻现象背后的原因,以数据为支撑证明当前具有辨认和可控制能力的年龄已然变更为十二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要制定一系列预防和控制措施,即使不承担刑事责任,也要进行单独的教育和改造,并注重教育和改造的效果。对当事人进行长期的考察和跟踪照顾,及时遏制犯罪苗头。若是父母监管不当,并长期放任,导致少年儿童一再走上犯罪道路,也可以考虑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坚持公平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既要做好保护工作,又不能损害公平正义。最后,弹性年龄制度或恶意补助年龄制度难以贯彻,因为低龄儿童本身不具有完整的人格和完全的辨认、控制能力,不能说恶意或者恶行就能补足本身欠缺的能力。并且,主观的恶意难以判断,缺少具体的补足标准,适用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