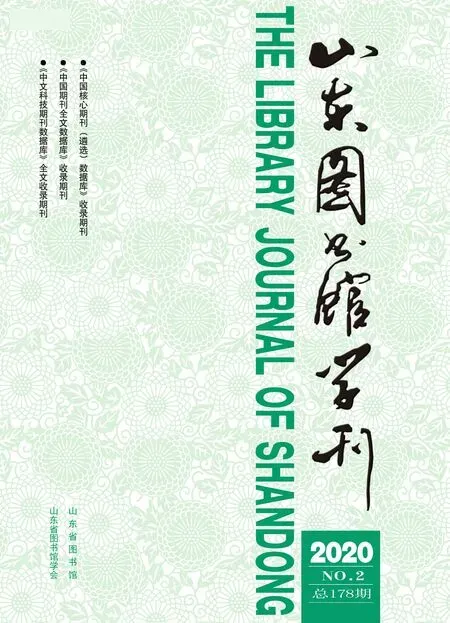何多源致袁同礼书信的史料价值*
2020-02-23江山
江 山
(合肥学院图书馆,安徽合肥 230601)
1 引言
近代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战时购藏的古籍、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图书,曾为避战乱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战时央图暂存于冯平山图书馆的古籍遭日军掠夺,以及其战后归还等问题,目前大陆相关研究并不多,主要有韩文宁《抢救民族文献——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载《图书与情报》,1999第2期)、吴真《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等。因此事涉及面颇广,影响较大,还有必要继续作深入研究。
相对来说,中国台湾的研究还是较为多些,如卢锦堂《国立中央图书馆古籍搜藏与整理》《从抗战期间抢救珍贵古籍的一段馆史说起》《抗战时期香港方面暨冯平山图书馆参与国立中央图书馆抢救我国东南沦陷区善本古籍初探》。2010以后依然有相关成果,如顾力仁、阮静玲《国家图书馆古籍搜购与郑振铎》以及黄文德等《抗战时期央图留港遭日劫掠古籍寻获过程之探讨》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与真相不断浮出水面。以往的研究多将视野集中在郑振铎、蒋复璁、顾毓琇、陈君葆、参与远东委员会的英军博萨尔少校、隶属香港军政府军事法庭的调查官端纳少尉等历史人物上,至于在这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的袁同礼、何多源等,很少有人提及,直接的史料更是缺乏。
其实,199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就有1946年何多源写给袁同礼的信札一通,不过,这则重要的史料没有被很好地发掘研究,一方面说明我们已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史料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因该信札为手稿,也存在辨识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后图书馆史料研究的重要方向,即大量的有学术价值的手稿有待发掘、整理与研究。
2 何多源致袁同礼书信的背景
何多源(1909-1969),又名观泽,[1]图书馆学家,广东番禺人。1926年广州宏英英文专门学校毕业,1929年考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为学习员。1934年9月岭南大学聘任为图书馆中文部主任。[2]后任岭南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广州大学副教授、图书馆主任。建国后历任华南联合大学副教授、图书馆主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图书馆副馆长。著述主要有《中文参考书指南》《图书编目法》《馆藏善本图书题识》《战时经济参考书目》《杂志管理法》《海南岛参考书目》《广东藏书家考》《国学书目举要》《卡片目录使用法》等。关于何多源的生平及著述可参见《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周文骏)[3]《中国目录学家辞典》(申畅等)[4]《中国藏书家通典》(李玉安,黄正雨)[5]《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麦群忠,朱玉培)[6]等。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我国在美专攻图书馆学第一人。[7]1924年回国,任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次年起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又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等职。1929年起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南下长沙,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搜集西南后方文献。1929年起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1929-1942)、馆长(1942-1948)。[8]全国解放前夕去美国,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及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工作。[9]1957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工作。[10]袁同礼对古代藏书等深有研究,主要著述有《宋、明、清私家藏书概略》《西文汉学书目》《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西文汉学目录》《俄文选书目》《俄文汉学书目》《俄文日本研究书目》等。[11]关于袁同礼的生平及著述可参见《中国藏书家辞典》(李玉安,陈传艺)[12]《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13]《读书辞典》[14]《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15]等。
1927年,中山大学聘请了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担任图书馆馆长,并延揽了顾颉刚、袁同礼、何多源等学者到馆工作。因汇集众多专家兼管理有方,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当时堪称一流。[16]广州沦陷前,何多源随岭大迁到香港,未及回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抗战后期,受国立北平图书馆指派,注意收集沦陷区典籍,以图保存文献。抗战胜利后,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驻香港办事处任编辑,后任该馆秘书。[17]
3 何多源致袁同礼书信的内容
何多源对于广东及香港图书馆事业在近代的发展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一直致力于我国图书的收藏、保护等工作。关于这一点,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 年第20卷第4-6期上发表《广州香港各图书馆近况》,就充分说明了他对于广东及香港图书馆的了解状况。[18]同时,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国图书馆界的头等大事是追缴被日军掠夺去的图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多源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致信,对于日军掠夺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图书情况给予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于当时的对日图书追缴工作,乃至战犯的审判等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其他文献史料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为成功追回图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书信的全文如下:
迳复者,顷接四月廿七日大函,嘱将战犯酒井隆在港掠夺书籍情形及证据呈报,自当如命查。香港于民国卅年十二月廿五日沦陷,同月廿八日即有日人竹藤蜂峰治(此人现引入香港战犯羁押赤柱监房,战前在香港任华南商业贸易总经理,一著名之香港通,能说英语。)偕同日军将官、阶级军官前到般含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搜查书籍,一到即上三楼,视察国立中央图书馆准备寄运中国驻美大使馆胡适大使代存之善本图书111箱,此帮全系中国善本古书,并非有关军事图籍。
卅一年二月上旬,即有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着人来馆掠取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之善本古书,全部计111箱。是时,本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装箱寄存该馆一楼之图书,约三百箱,亦一并搬出去。渠当时以为此亦属中央图书馆之善本古书,故并无开箱检验。所有搬走之书均于箱面写明“东京参谋本部御中”,其有意掠夺中国文物,实属无可置疑。至奉命掠取图书之宫本博少佐,系原在广州南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机关任职。太平洋战事爆发时,调往香港担任搜掠图籍。至卅一年二月掠得图书后,又调回广州军部特务机关任职。
此外,本馆有西文图书、杂志计共20箱,于民国卅年十一月由开英轮船运往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船到黄浦江口,以时局紧张不能入口,乃原船开回香港。本馆寄运之图书20箱,即于卅年十二月五日搬入香港西环永安货仓五楼,趸存箱面写寄“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收”。当时,为避免日人注意起见,寄箱人写冯平山图书馆。另有“NLP”标记,箱内图书均有本馆之章。此帮图书亦于民国卅一年间为日军掠去。至掠取详情,因货仓系由日军管理,普通人不能入内,故无从探悉。
迨卅四年八月,敌人投降后,本馆即派人来港调查敌人掠夺图书情形,并往各货仓调查,已不见有本馆藏书。至于掠书物证,则颇能提出。因敌人系属以暴力掠夺,当无收据之理,但冯平山图书馆办事人目睹其掠夺情形。以上所述系当时实情,请即函复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并请中国陆军总部设法在日本引渡经手掠夺图书之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及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少将来京审讯,务须查出掠去图书现存何处,俾我国珍本图书、国家文物得以珠还合浦,是所至盼!此上,国立北平图书馆!
职何多源上 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19]
何多源在给袁同礼的信中,主要叙述两件事:一是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准备运往中国驻美大使馆胡适大使代存的111箱善本图书,被日本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奉命掠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装箱寄存该馆一楼之图书,约300箱也被掠去。二是香港西环永安货仓五楼20箱西文图书、杂志也为日军掠去。何多源在信的末尾要求:“中国陆军总部设法在日本引渡经手掠夺图书之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及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少将来京审讯,务须查出掠去图书现存何处,俾我国珍本图书、国家文物得以珠还合浦”。
在信中,何多源提到的日本战犯酒井隆先后在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于侵略中国的运动,1938年后任驻蒙军司令部附,1939年后任兴亚院联络部长官,1941年任第23军司令官,与土肥原贤二及梅津美治郎等人,为日本侵略政策的主要人物。1941年12月,酒井隆率部攻陷香港。酒井隆唆使、纵容部署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大量残杀无辜的中英人民、对于平民施以酷刑、强奸、对占领区人民施以奴化或剥夺其公民权、肆意破坏财产,可谓无恶不作。其中在文化方面最为令人发指是抢劫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图书300箱,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111箱及存于香港永安货仓的西文图书20箱,分运东京参谋本部及上海两处。[20]
4 何多源书信所述内容与对日图书索回的史料回顾
何多源书信所述的是关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存111箱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被日军掠夺去的历史史料,其所涉及的历史真相相当重要,我们有必要作一下回顾。
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后,用150万元购置图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购书任务,1940年,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凤举等爱国文化名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对沦陷区的善本图书展开抢救工作。此事得到陈立夫、朱家骅、顾毓琇(教育部次长)等人同意,并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来上海协助。[21]
1941年,经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来的35000册珍贵古籍,其中有原版《永乐大典》及明版书籍多种,均在其内。[22]由上海运至香港,连同在港的其他古籍数万册,经叶恭绰安排,存放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由港大教授许地山、马鉴派人保管,准备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23]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藏于香港的这批古籍落入日军之手,[24]继而被运往东京,存放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25]
关于这批图书被日军掠夺一事,郑振铎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竞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竞亡于一旦么?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26]
实际上,这批从国立中央图书馆疏散来香港善本图书是受到了严格保护的,当时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是陈君葆(1898-1983,广东中山人)。1934年起,陈君葆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27]他曾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出面与日方交涉所保管图书事宜,而被日军扣留下来。[28]
由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价值巨大,且大多为明版罕见本或绝本。当时将书运往香港暂时寄存并准备运往美国时,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可谓煞费苦心。需要指出的是,郑振铎与任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私交甚笃,而时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与许地山也交情至深。因此,许地山、陈君葆成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香港图书并负责管理的不二人选。许地山去世后,则由陈君葆一人独自承担相关事宜。抗战胜利后,陈君葆分别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写信、复函,报告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图书被掠夺情况。1946年1月,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陈君葆还请他留意该批图书的下落。[29]
郑振铎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样一批费尽心血收集来的善本图书,对于保存中国的文化意义十分重大,但不幸的是被日人掳掠至日本本土,其被索回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即派人来港调查敌人掠夺图书情形,随后便开始了艰苦的追索工作。
1945年9月8日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就要求:“迄今是否运日尚无从采悉,惟该项图书均系善本,谅系敌人掳略而去,自应向日方索还,否则必行补偿。”[30]同年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呈教育部报告香港存书被劫,请向敌索偿,并表示:“现日本投降,该项图书自应由我追还,以免损失。理合具文。先行呈请备案,以作将来向日本索偿之根据,恳请鉴核示遵,实沾德便。”[31]
抗战胜利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并追回文物,当时的教育部将战区文献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其任务为调查收复区重要文化、建筑、美术、古迹、古物等实况,设法保护,并派员前往日本,调查我国文物被日本劫夺情形。该委员会由军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各派代表一人,及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充任。另外,由教育部部长指派部内高级职员并聘社会热心美术及保存古物之人士5人至9人组成。内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秘书1人,职员若干人,并分建筑、美术、古物、古画四组。[32]
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为调查战争期间中国公私文物之损失,以便向敌追偿起见,先后在京沪、平津、武汉、东北等地成立办事处,实地调查,并举办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编拟损失清单,为将来索取赔偿作准备。该会聘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张凤举(教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会委员)为调查日本劫掠中国文物情形以便追偿,赴日工作。[33]李济、张凤举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开展工作。
李济回国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特于1946年5月18日在教育部举行还都后第一次会议,听取他的报吿。该报告称:“我中央图书馆战前存留香港为日本运往其国内之图书百余箱,业经东京麦帅(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总部转令日政府交还,目前正清点中,两月内可运回。又日人前在安阳及周口店发掘各物,不久亦可交还。麦帅已下令日政府禁止各项文物出口。对于日本自七七事以来在各地以非法手段取得之文物,亦令日政府造具清册,限六月一日以前呈报。李氏曾在东京大阪京都参观日本各公私收藏文物处所,麦帅总部表示,凡我国为日本劫夺或非法购买之文物,均可发还,惟必须提出具体之证明。现该会拟一面向华盛顿远东委员会建议,将追偿文物之时限提早至甲午战争,一面则赶编战时损失重要之文物目录,以便交麦帅总部。惟该会所收各方登记损失函件,多乏具体说明与确切证件,以致调查交涉时诸多困难,望申请者特别注意。”[34]
1946年,战时为日军掳去的中国珍贵古书10箱,计2550册——为1942年自香港掳去中央图书馆书籍25000册的一部分,经驻日麦帅总部平民财产保管处返还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35]并于同年12月间空运回国。此后的107箱,于1947年2月8日由驻日代表团专员王世襄,乘美轮伊兰胜利号押运回上海,国立中央图书馆将图书于11日运抵南京。[36]
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将被日军掠去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大部分善本图书公开展览3天。[37]至此,历经沧桑与磨难,国立中央图书馆当年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已大都完璧,实为不幸中的万幸,为保存中华文化浓重地写上了一笔。值得庆幸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在馆长袁同礼的领导下,在抗战期间并未遭到大的破坏,该馆所藏珍贵版本,于珍珠港事变前由上海运往美国,并于战后被运回。至抗战结束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书50000册。8年抗战期间,仅于美日战争爆发后,为宪兵队封闭2个月。[38]
当我们今天再次阅读何多源写给袁同礼的信札时,虽时隔许多年,但给我们的震撼和感慨还是那么强烈、那么多,为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许多文化界、图书馆界以及其他各界的爱国人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与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