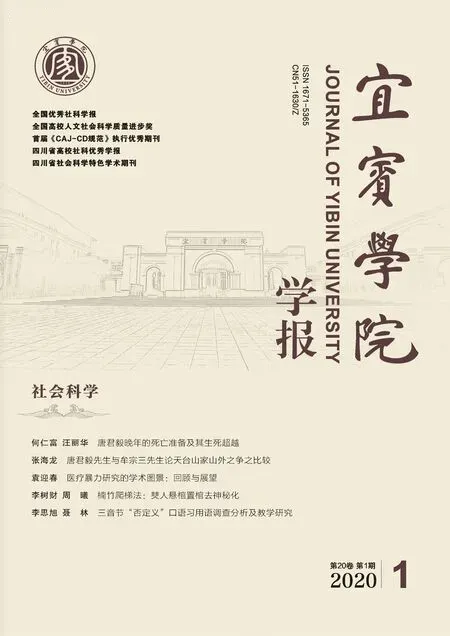圣人西来
——20世纪早期斯宾诺莎与中国的相遇
2020-02-23彭柏林
彭柏林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百余年来,东西哲学之间的比较和融贯性的阐释至今仍如火如荼,并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理论课题。20世纪早期,德国首先在斯宾诺莎传记、档案、书信和文集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带动了世界范围内斯宾诺莎学的复兴。恰逢其时,中国哲学的第一代学人相继开启了留学和归国讲学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运动,包括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理论家被介绍到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微妙的碰撞。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中国化阐释既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竞争性的理论背景,也在客观上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争取了信仰主体,提供了可以理解和对话的平行资源。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是经由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中国化和斯宾诺莎身份的圣人化而实现的。借此我们可以理解,如冯友兰、贺麟等早年神往斯宾诺莎的前辈学者何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比较自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考察斯宾诺莎与中国的早期相遇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些理论问题。
一、身世简述:东西之间
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出生于阿姆斯特丹赛法迪姆(Sephardim,或西葡裔)犹太人家庭,被取希伯来名字叫“Bento”(或Baruch),意思是“祝福”。后来由于宗教思想的分歧与犹太社区决裂,并自己以拉丁语改名为“Benedict”,与“Bento”同义。因此,为了尊重斯宾诺莎的本意,后世学界通称他为Benedict de Spinoza。尽管幼年的名字寄托了宗教的祝福和家人的殷切希望,可吊诡的是,从24岁被逐出教门至死后一个多世纪,斯宾诺莎几乎遭到了欧洲各种宗教派别的狂热诅咒和谩骂。直到19世纪,欧洲学界才开始正视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家的身份,甚至赞誉他是陶醉于上帝的人、是基督徒,对神有真正的热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与中国的早期相遇中,斯宾诺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传统宗教的圣人形象被翻译家、政治家、哲学家们所介绍和阐释的。
当前,我们在结合各大外来宗教在华的传教、影响、接受的过程来讨论“宗教中国化”命题的时候,不应忽视各大外来宗教的意识层面尤其是宗教哲学的中国化维度。涵括宗教信仰的宗教意识是宗教现象最内核的层面,而宗教哲学是以最抽象也最集中的方式表达宗教信仰的形式。因此,宗教哲学不仅应是我们研究宗教学的一个可选择性的二级学科,更应成为宗教学的基础性学科。与此对应,我们的宗教中国化研究更应该赋予宗教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以基础性地位。这一理论定位需要我们自觉地扩大“宗教中国化”命题的外延,即不仅仅应该着眼于传统启示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中国化,还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提出的关于宗教的起源、发展、要素、本质、功能的新观念。这些新的宗教观念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国外宗教新发展、新变化的重要部分,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和接受更是我们理解自身的传统宗教文化、当下宗教现状和未来宗教的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他者”。
斯宾诺莎所处的时代是欧洲宗教纷争和压迫最甚的时代,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犹太教、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都试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斯宾诺莎亲历了标志着宗教改革结束的三十年战争、三次英荷战争、法荷战争等多起宗教—政治的灾难,敏锐察觉到由宗教与政治相混所带来的宗教与政治上的双重堕落,因而提出了一种希望能既不扰乱国家和平、又能促进政治自由的新的宗教观。尽管这种新的宗教观一诞生就不为世人所理解而被斥为“无神论”,但在中国,它一开始就遭遇了美好的相逢。中国学者对它的中国化阐释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也已经使它成为当下中国宗教意识的一部分。
二、章太炎:由儒释道以通泛神论
我国学者中,较早把斯宾诺莎与孔子、老子、庄子、佛陀等传统宗教圣人相提并论的是章太炎(1869-1936)。1906年,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无神论》高度赞扬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将其与佛教哲学作了许多互文性阐释。“近世斯比诺莎(原文如此,作者注)所立泛神之说,以为万物皆有本质,本质即神。其发见于外者,一为思想,一为面积。凡有思想者,无不具有面积;凡有面积者,无不具有思想。是故世界流转,非神之使为流转,实神之自体流转。离于世界,更无他神;若离于神,亦无世界。此世界中,一事一物,虽有生灭,而本体则不生灭,万物相支,喻于帝网,互相牵制,动不自由。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粒飞沙,头数悉皆前定,故世必无真自由者。观其为说,以为万物皆空,似不如吠檀多教之离执着。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为寓于万物,发蒙叫旦,如鸡后鸣,瞻顾东方,渐有精色矣。万物相支之说,不立一元,而以万物互为其元,亦近《华严》无尽缘起之义。虽然,神之称号,遮非神而为言;既曰泛神,则神名亦不必立。此又待于刊落者也。”[1]400-401
在1907年发表的《答铁铮》一文中,为了说明佛教何以能在中国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他找到了佛学与中国德教的相似之处,即在拯救观上表现为依靠自力得解脱的无神论、泛神论。“仆于佛学,岂无简择?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1]369在他看来,孔子作为中国德教的祖师,就是泛神论者,而孔子的学说又来自老子,庄子更鲜明地继承了老子的泛神论。“按孔子词气,每多优缓,而少急切之言,故于天神未尝明破。然其言曰:鬼神之为德,体物而不可遗。此明谓万物本体,即是鬼神,无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比诺沙(原文如此,作者注)泛神之说。泛神者,即无神之逊词耳。盖孔子学说,受自老聃,老子言象帝之先,既谓有先上帝而存者;庄生继之,则云道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而终之以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则正所谓体物而不可遗者。无物非道,亦无物非鬼神,其义一致,此儒、老皆主泛神之说也。及其言天,则本诸往古沿袭之语,而非切指天神。”[1]372
由此可见,经由章太炎,斯宾诺莎宗教学说在中国的初传不仅不是以异端之名被唾弃,反而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宗教中最伟大的圣人们相提并论。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章太炎隐义是:无神论和泛神论在中国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佛教作为一种无神论宗教早就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中国不仅有可以与西方进步思想展开对话的传统资源,以佛教为代表中国宗教更可以承担起思想改良的历史重任。
三、伍光建:初译《伦理学》的中国情怀
我国学者在1929年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斯宾诺莎著作中,也有许多宗教哲学中国化的痕迹。尽管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主要是一部道德哲学著作,极少使用宗教的术语,但在著名翻译家伍光建(1867-1943)的笔下,仍可找到儒释道的术语。我们试举几例:在第一部分附录中,斯宾诺莎说“他们这一般人深知愚昧一经揭穿,则惊怪就会随之消除”[2]39。伍光建译为“此辈明知,一旦扫除无明。(无知无识)则受疑惑之愚蒙。亦同时扫除矣”①。在第三部分命题二十九的附释中,斯宾诺莎说“当我们率然取悦一般人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们作某事或不作某事,会导致损害自己或损害他人的后果。否则,这种行为通常称为‘通人情’(humanitas)”[2]122。伍光建译为“若吾人之欲望取悦于众人。如是其烈。甚至于使吾人之动作或不动作。随以遗害于自身或遗害于他人者。则尤其是如此。不然,则此宗努力。向来称为人道(亦称人情。亦称仁慈。译者注)”[3]2-37。第四部分命题四十说“凡足以引导人们到共同的社会生活,或足以使人们有协调的生活的东西,即是有益的”[2]203。伍光建译为“无论任何事物之资助于人世大同者。(大康,译者注)即谓无论任何事物之使人与人同心相处者。皆是有益之事”[3]3-49。第四部分命题七十三附释有“这些以及类似这些关于人的真正自由的说法,都与精神力量有关,换言之(据第三部分命题五十九附释),均与意志力和仁爱力有关”[2]227。伍光建译为“以上数条。及我所证明与此相类之事之关于人之真自由者。皆与弘毅相关。(见第三卷第五十九题之旁注)即谓毅力及大度(弘愿)”[3]3-83在伍光建译本中其他带有儒释道色彩的还有:“吾人绝不能断言神有所受。(殆谓有施无受,译者注)”[3]1-23“希伯来人谓神。(上帝)”[3]1-66“同时冥想多数之事物”[3]3-107“祯祥(或天福)不是德之赐”。[3]3-138
“无明”是佛教用语,意思是愚痴,是“十二因缘”和“三毒”之一,“泛指无智、愚昧,特指那种不明佛教思想的世俗见解”[4]69。伍光建此处应是取的普通含义即无知,但给斯宾诺莎对常识的批判增加了超世俗的意思。“humanitas”的字面意思是人性、合乎人性的行为、待人以礼,结合上下文应指利己利他的行为。伍光建结合儒家的仁慈、仁爱翻译为“人道”“人情”是比较符合“仁”的原意的。“仁字从人从二, 原意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关系。”[4]130“大同”“大康”在英译本中是“common Society”[5]570。细微差别在于,斯宾诺莎此处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形成阶段,而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理想。但在儒道大同社会的理想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协调的生活”确实是基本状态。“弘毅”(《论语·泰伯》)的拉丁原文是“fortitudo”,直译是勇气,结合上下文应该有待人、待己两层含义,即仁爱待人、坚韧待己。而“弘毅”正好涵括“宽宏坚毅”,于原文颇为贴切。“大度”“弘愿”正好借佛教用语表示慷慨、宽厚,于“generositas”也很传神。[5]657
上述译例不仅表现了我国翻译家理解外国宗教哲学的儒释道特点,更反映出我国传统宗教文化具有很强的接纳、适应和融合外来宗教思想的能力。伍光建的《伦理学》译本尽管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其译文的信、达、雅和译意的儒释道精神都为后世宗教中国化的译介工作树立了典范。
四、冯友兰与贺麟:新儒家对斯宾诺莎的圣人阐释
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中,对斯宾诺莎宗教早有兴趣的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张岱年(1909-2004)等人相继出版发表了对其宗教哲学进行中国化阐释的论著。这与1932年世界范围内纪念斯宾诺莎300周年诞辰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1931年,冯友兰英译的《庄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通过他对庄子的斯宾诺莎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斯宾诺莎其实也被庄子化了。例如,《庄子·养生主》有“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冯友兰将“悬”(suspension)解释为“人的束缚”(human bondage),“悬解”就是人获得自由。这种解释不仅以西方人较能理解的单词宣传了汉语古文中较为费解的“悬”,也看到了双方共有的以理化情、从主观相对的哀乐好恶中解脱出去的取向。但是,斯宾诺莎所谓与人的束缚相对的人的自由不仅仅是要从永恒来看待一时一地的情绪变化,更是要通过不断增长关于自然的理性知识来理解必然性、在理性的行动中遵守必然性从而获得主动的情感或“对神的理智之爱”。这是“悬解”不足以替换“自由”的地方。另如,冯友兰在英译本《庄子》的序言中,引用了当时英语界研究斯宾诺莎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拉特纳(Joseph Ratner,1901-1979)的一大段对“永恒”的论述,用“永恒”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道家追求的自由。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道家与斯宾诺莎都以天人合一、回归自然为自由的宗旨。但是,冯友兰并未指明两点差别:第一,斯宾诺莎的自然有非常稳定的规律可循,而道家的自然是无限变化着的、不可理性把捉、只可体悟;第二,斯宾诺莎是追求永恒的,回归自然不是为了忘我,而是在永恒的自然中保留个体心灵的理智部分,道家则以忘我、逍遥、齐一为最高的自由境界。[6]173-174这本书对庄子的斯宾诺莎化的阐释还有很多,为英语读者理解庄子提供了很好的本土思想资源,也在国际上使庄子与斯宾诺莎互相成为“他者”之镜,形成了中西比较的一大传统。
1932年,为了纪念斯宾诺莎诞辰300周年,贺麟、张岱年都撰写了对斯宾诺莎带有中国化阐释的文章。在《斯宾诺莎像赞》中,贺麟如此称颂他神往已久的圣哲、仙哲斯宾诺莎:“宁静淡泊、持躬卑谦。道弥六合、气凌霄汉。神游太虚,心究自然。辨析情意,如治点线。精察性理,揭示本源。知人而悯人,知天而爱天。贯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与造物游,与天地参。先生之学,亦诗亦哲,先生之品,亦圣亦仙。世道衰微,我生也晚,高山仰止,忽后瞻前。”很明显,贺麟的赞许是以《伦理学》为文本的。第一句写斯宾诺莎的性情和德行。第二句分别称赞他的思想与人格。第三句指《伦理学》第一部分“论神”。第四句指《伦理学》第二、三、四部分的“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力量”。第五句指《伦理学》第五部分“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最后三句再次歌颂斯宾诺莎的道德文章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贯通儒道的境界,并直抒胸臆,以表追慕。
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一文中,贺麟对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有进一步的阐述和比较。他说:“他竟把对于永恒无限的真理之追求与爱好,当作人世苦海的超脱和极乐世界的获得。”[7]124又说:“他的直观法……就是可以使人逍遥于天理世界的罗盘针。这个方法的妙用在于从大自然、从全宇宙,也可以说是从超人或超时间的立脚点来观认‘物性’(essence of things,按essence一字应作性或本性,亦称自性,性即是理,物性即物理——贺麟注)。这种直观法他又叫作‘从永恒的范型之下’(under the form of eternity,sub specie aeternitatis——贺麟注)以观认一切物性的方法。他这种的直观法就是佛家所谓以‘道眼观一切法’的道眼或慧眼,就是庄子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道观法’,也就是朱子所谓‘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的‘理观法’。”[7]133这里,贺麟不仅继续将斯宾诺莎与道家、儒家的功夫论作类比,还联系到佛家的解脱论和功夫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物理。贺麟作以上类比大概有两个理论目的:第一,证明斯宾诺莎是将道德与科学结合得最完美的大哲,如他所言:“斯氏必得自己求得一种……新方法,以建立他的新宇宙观、新人生观,使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的探讨与求安心立命的宗教的生活调和一致,使神秘主义的识度与自然主义的法则贯通为一,使科学所发现的物理提高为神圣的天理,使道德上宗教上所信仰的上帝或天理化作科学的物理。”[7]132第二,证明中国以德教为主的传统宗教儒释道都可以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没有孰优孰劣;并表明自己要以斯宾诺莎为垂范、为中国人建立新人生观的志向。
五、张岱年:比较哲学的垂范
在中国将斯宾诺莎与庄子作比较阐释的传统中,张岱年1933年发表的专论《斯辟诺萨(原名如此,作者注)与庄子》[8]246-249可谓开风气之先。该文结构清晰、论述鞭辟入里、态度客观,列举了斯宾诺莎与庄子的“五同二异”。他认为:庄子与斯宾诺莎都是有定论者,斯宾诺莎讲“无穷的因果连环”,庄子讲“命”;二者对情欲的态度相似,均主张情绪要免除外物的支配,要只从人的本性而发,均以“悬解”或“自由”为目的,都主张通过理解事物变迁的背后原因来消除情绪波动。但是斯宾诺莎提倡积极的感情和重视理智,庄子则排除一切情绪、反对知识;都有神秘主义,斯宾诺莎讲“人之圆满”的境界,庄子讲“与天为一”;都追求不朽和永生,斯宾诺莎有“心之永生”,庄子讲“入于不死之生”;都是自然主义者,斯宾诺莎把神与自然等同,庄子的“大块”与“造物者”并无差别。二者的差别在于:第一,斯宾诺莎重视理智,永生的神秘境界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庄子排斥理智;第二,斯宾诺莎的自由是人积极努力获得的,庄子哲学归根结底则宣扬消极无为。
该文的评价总体上看是冷静中立的,但仍然不乏对斯宾诺莎的赞誉:“庄子哲学较之斯辟诺萨,在条理的明晰上,和论证的细密上,也差得很远,但也要知道,在年代上,更差得很远(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0年,斯辟诺萨生于公元1632年,差不多相距两千年)。”其用意也是很明显的:我国传统宗教哲学在条理和论证上要学习西方,但不应缺乏文化自信,它很早熟,需要今人进行创造性转化。
余论
从以上诸家对斯宾诺莎宗教哲学的中国化阐释可以看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全部以《伦理学》为诠释文本,而主要关注宗教问题的《神学政治论》并未受到重视。这大概有国内国外两种原因:就国外而言,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斯宾诺莎阐释并未取得大的进展。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知识变得更加确切而不是更加深刻。格布哈特捍卫相当弱的宗教哲学”[9]428。这就使得《神学政治论》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忽视。就国内而言,章太炎、伍光建、冯友兰、贺麟分别是日本、英国、美国、美国和德国的留学归国人员,必然会受到海外斯宾诺莎学的影响。尽管诸家都有较强的外文阅读能力,但是国内斯宾诺莎原著仅见有《伦理学》。
第二,主要关注的宗教哲学议题是上帝观、人性论、拯救观、功夫论等人生哲学的内容。这可能有文本与诠释两方面的原因:就文本而言,《伦理学》是主要是一部建构普遍伦理学的著作,新宗教是普遍伦理学建构的一部分;而儒释道正好特别强调以道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尤其是佛教经过几千年的中国化,禅宗以鲜明的内在而超越的思想主张如“不立文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心见性”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尤为深远。就诠释而言,20世纪初是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都试图以学术报国、振兴中华的时代,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汉译西学、寻找传统宗教文化中与西学的相通之处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意识。他们发现了中西之别不仅仅在于器物、制度,更在于思维方式和国民性的差别,因而把构建新的人生观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旨趣。
第三,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和宗教文化自信,他们译介和阐释以斯宾诺莎宗教哲学为代表的西学同时并不全盘否定传统宗教。章太炎把儒释道的无神论和泛神论作为“简择”佛学、学习西学、复兴国学的标准。伍光建自觉使用儒释道的术语译介斯宾诺莎的道德和宗教哲学。冯友兰不仅积极地向海外读者介绍庄子哲学,还以平等的姿态使用斯宾诺莎宗教哲学做注脚。贺麟尽管对斯宾诺莎极尽赞誉,但以儒释道的圣人形象作为最高评价标准。张岱年则客观指出了中国宗教哲学的早熟现象,认为国学与西学可以互补。诸家对斯宾诺莎宗教哲学进行中国化阐释的客观、平等的态度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一,宗教中国化工作要以时代需要为导向,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召能构建新的国民性的宗教,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则需要既具有普世价值、又体现华夏民族宗教优越性的文化和哲学。其二,宗教中国化不仅是要吸收国外优秀宗教文化和哲学的资源,更是要以优秀的本民族文化去理解和消化。以儒释道的人生哲学为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传统宗教资源中有更多的优秀元素可以实现新进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注 释: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伍光建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第一本,第54页。需要说明的是,伍光建《伦理学》译本最早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出版,收录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本文所引均以李天纲主编的影印版“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伦理学”为准。由于1929年的版本将《伦理学》第一、二部分合为一本,将第三部分单作一本,将第四、五部分合为一本,所以在影印版中有三种页码序号。有鉴于此,本文均指出本数和页数,如1-54指的是第一本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