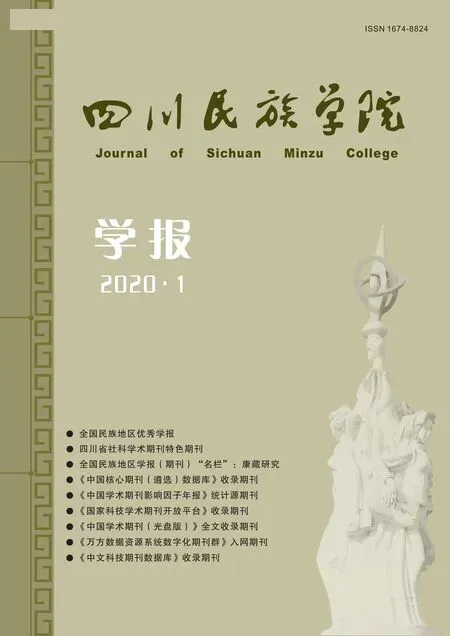汉藏不同语境中的“打箭炉”地名的由来及文化整合
2020-02-23蒲华军
蒲华军
“打箭炉”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康定市的旧称。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也常简称为“炉厅”“炉城”或“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将打箭炉厅改为康定府(1)《康定县志》及郭昌平等著《情歌的故乡—康定》(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龚伯勋著《康定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中均记载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据《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中记载,赵尔丰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在《巴、里塘改土归流请设道府州县折》里,向朝廷建议,拟将“打箭炉改为康定府”,但此时并未得到朝廷应允。“在未定以前,已委员赴各地分理,勘界分疆,清查户口,并发给木质关防一颗,以昭信守。”(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143页)。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赵尔巽、赵尔丰《会筹边务亟待举办事宜折》里又再次奏请拟改“打箭炉为康定府”“康定府设知府一员,管理地方钱粮词讼”,朱批:“会议政务处议奏。”(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207页)。因此大多学者都认为清政府正式批准改设康定府的时间实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然在光绪三十四年之后的许多官方文献中,包括赵尔巽、赵尔丰的奏折中仍称之为“打箭炉厅”“炉城”“炉厅”或“炉”。,康定之名才始见于史。然“打箭炉”的名称仍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在许多官方文献中亦称为“炉”“炉城”“炉厅”,康定城区也因“打箭炉”的缩称命名为“炉城镇”。这里东傍跑马山,东北邻郭达山,西南靠子耳坡,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也是藏彝走廊上的关键节点,历来就是康巴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清代李苞在《打箭炉》诗中写道:“边陲此要隘,建置已永久。”此地古为羌部落所居,汉文史书中将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带统称为“西南夷”“旄牛夷”“徼外夷”等,也有“毛牛国”“木雅”“鱼通”之称谓,藏文文献中则称之为“咯木”“木药”“木雅热岗”等。汉时实行羁縻之制,此地隶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一带),隋时为嘉良地,唐宋时期因与吐蕃的征战,或属雅州、或属吐蕃,元时置军民安抚使司,明承元制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大约在永乐年间成为土司驻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1年)复设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简称“明正土司”),随着茶马互市的高度繁荣与治藏重要地位的凸显,雍正七年(1729年)于此地设打箭炉厅,设置流官,隶属于雅州府,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升为直隶厅,隶建昌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设康定府,隶属川边安康道,宣统三年(1911 年),明正土司徼印改流,“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改置康定县,康定之名沿用于今。此后曾为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别行政区、川康边防指挥部、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西康省省会等所在地。1950年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政府设于康定,1955年西康省并入四川省,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康定仍为州府所在地。201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康定县,设立县级康定市,行政区域不变,驻地为炉城镇茶马路1号。
一、 史学文献中“打箭炉”名称的异写
“打箭炉”之名,旧史曾作“打煎炉”“打折卢”。其中《明实录·太祖实录》和《明史·西域传》是最早有正式文献记载该名的史书,均称之为“打煎炉”。如《明实录·太祖实录》中载“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一八八二·八·一七),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瓦剌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诏赐文绮四匹,帛如之,钞二十锭,衣一袭。”[1]“洪武十六年三月乙卯(一八八三·四·一四),西番打煎炉长河西土官故元右丞剌瓦蒙,复遣理问高惟善及其姪万户若剌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钞锭、衣服有差。”[1]《明史·西域传》载:“洪武时,其地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赍遣还。”[2]由此可知,开茶马互市实在明之前,“打煎炉”的称呼至迟在明代之前已有之。此后,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搜查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的谕令中才有了“打折卢”的称号:“又,刑部侍郎遣冯甦能员赴打折卢地方侦贼情形,仍移书达赖喇嘛,令勿纳残贼入其境内……打折卢地方应移文四川总督,令选贤能人员,不时侦探防御。上曰:此事即如所议行。打折卢等处地方应选堪用之员,如喇都浑其人者,遣往彼地,不时侦探……”[3]而 “打箭炉”之称,目前最早的材料见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刑部奏疏,右侍郎冯甦疏言:“请遣能员赴打箭炉地方侦贼情形……”[1]后《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中记载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乱”中亦写作“四川打箭炉士蛮作乱,遣侍郎满丕偕提督唐希顺讨之。”今存于泸定桥边的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载:“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于康熙后的史料文献均称之为“打箭炉”,再无“打煎炉”或“打折卢”之异写。
二、 汉文化语境中的“打箭炉”由来
在汉文化语境中,“打箭炉”之名的来源大致有四种说法,其中三种与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和郭达有关。打箭炉其地,在东北方确有山名为郭达山,城中确有武侯街、武侯祠、将军庙、将军桥。
一是诸葛孔明派郭达将军于此安炉铸箭(其原一说为南征孟获,一说为与牦牛王会盟),为蜀国征战所用,此说最为普遍,在乾隆年间的《打箭炉志略》《雅安府志》和光绪年间的《打箭炉厅志》等地方史志中均如此述之。在民间的传说中又增加了情节,郭达携工匠于此冶铁铸箭,并赠送牦牛国王以铁制器皿、箭器等,教会百姓冶铁之术,受到边地百姓尊崇,故名此地为打箭炉,名东北的一座山头为郭达山。
二是诸葛孔明“借一箭之地”。传说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南征孟获,约请牦牛王(一说为徼外诸番)会盟修好,提出请借一箭之地作为运输军粮之道,牦牛王欣然应允。诸葛亮命射箭手郭达向西面云中射去一箭,霎时没入云中。(一说将军连夜背箭至此,并插入高山之巅。)藏王率部寻找箭落之处,惊叹一箭至七百里之遥,诸葛丞相真神人也,于是信守承诺借路。此后,箭没之山为郭达山,郭达山下之地称为“达箭路”,讹音为“打箭炉”,简称“炉城”。
三是郭达打箭淬火之地,即“达箭路”之称。相传诸葛孔明南征孟获时,为筹集军器,派郭达率部到西南方向寻一秘密之地打造弓箭。郭达历尽千辛万苦,方觅得这四面环山,二水中流,人迹罕至,山清水秀之地。于是在此安顿下来,设炉造箭。郭达造箭的火炉就砌在一座雄拔陡峭的大山之下,风箱沿河向东而设,二水交汇之处就成了郭达打箭淬火之地。郭达在此造箭日复一日,炉火终日不绝,风箱终日不息,直到有一天郭达因劳累过度在炉边吐血而亡。郭达累死了,但炉火仍燃着,风箱仍然开着,于是后人将此地命名为“打箭炉”,将炉边那座大山命名为“郭达山”。在传说中,老康定人认为康定城时有火灾发生和城东关的大风都与当年郭达死时炉火未熄,风箱未停有关。
四是茶马互市歇足“打尖”之地。(2)打尖,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指行路途中吃便饭,即休息、吃点东西,与坐在房屋中吃桌餐相区别。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根据康定老一辈的说法,“打箭炉”的说法是从“打尖罗”的叫喊、招呼声转化而来。古时康定只是荒滩,牛羊牧放之地。后汉藏交往、茶马互市,藏汉民众到了康定这荒谷地,需歇足“打尖”,停下来烧茶煮饭,出关者需在此吃饱喝足后再翻越奇险的折多山,赴内地者需在此藏汉边界歇息以适应内地气候、打探消息等。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地方叫作“打尖罗”或“打尖路”,后逐渐转音为“打煎炉”或“打煎路”,最后在文献中固化成“打箭炉”。
“诸葛亮借一箭之地”的提法主要见于今人采编的民间传说,详见甘孜州文化局所编的《康定的传说》中《郭达山的传说》,本文不再赘述。而传说的民间性更能展现文化的本来面貌。“民间书写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意识形态’由故事讲述者基于生存环境而萌生,经由故事接受者的认同而形成的集体意识形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特殊的表意过程与民间局部利益合法地联系在一起而建构出来的观念及其话语形态。”[4]从留存下来的文献看,清代文人士子普遍采信“郭达造箭”一说,果青王允礼《打箭炉》诗云:“通华缘蜀相,问俗驻輶车。”其《泸定桥》诗亦云:“蜀相五月渡河艰,宋祖玉斧兹藏锷。”王世睿《进藏纪程》载:“昔诸葛武侯征蛮,曾于此地造箭,遣一军人监之,厥后成神,立庙享祀,此打箭炉之所由名也。”[5]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载:“相传武侯造箭于此,其匠人郭姓,所乘之羊已仙去。炉有庙,形容古怪,夷人敬而畏之。”[6]姚莹《康輶日记》“打箭炉规制”条载:“诸葛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造箭于此,故名打箭炉。”[7]清代的史书、地方志也多有“安炉造箭”的记载。如康熙年间建泸定桥时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中载:“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此后的《雅州府志》《打箭炉志略》《打箭炉厅志》等官方史料均采用这一说法。《西藏图考》和《卫藏通志》中更加详细地指出为诸葛亮南征期间派遣将军郭达在此地安炉造箭。
有清一代文人,唯有清代黄楙材所撰《西輶日记》表达了不同观点,“打箭炉古旄牛国也,俗传武乡侯南征,遣郭达将军安炉造箭,附会无稽。愚按唐宋之世,吐蕃入寇,斯为要道,或尝造箭于此,至于丞相南征,由雋入益。程途各别,非所经行也。”[8]认为“打箭炉”之名与诸葛武侯无关,而是在唐宋之际,因此地在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于此造箭以供军需。清末民初任职于川边的查騫在其《边藏风土记》中,也对此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无证可考,“炉厅以打箭名,不可考。……传蜀汉诸葛丞相南征,于此设冶炉,造箭镞,遂因以名。然无可征冶。”20世纪八十年代由康定县志办刊发的《炉城风物》中对“安炉造箭”一说进行了辨析,从地理与物产等方面论证,认为“这些传说虽广,但确系附会,并无历史根据。”“武侯遣郭达于此造箭或遗箭之说,纯系戏言。”(3)见《郭达与打箭炉》,载于《炉城风物》第一期,1983年9月第3版。无论赞成同诸葛武侯有关的观点与否,在汉史料与文人游记文献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蜀人传”“相传”等词的运用正说明,前人并未真正考证出“打箭炉”之名的真实来源,所记载的都来自街谈巷语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来自蜀地汉人的传说。二是尽管传说无从证实,但至少有清一代文人,大多仍采信诸葛武侯遣郭达造箭一说,以至相沿成习,甚至史志中也未作考证,而是直接沿用。三是“打箭炉”之名的由来都与“箭”有关,此地或确属古时安炉造箭之地,从唐宋以来此地的重要性及大量的优质铁矿来看,此种观点不无可能,如该观点成立,则明史中关于“打煎炉”的“煎”字就是辨音的误写。
三、 藏文化语境中的“打箭炉”由来
“打箭炉”一语,来自藏语(康方言)“打折多”“达折多”“达折朵”“达渚多”或“打折渚”的变音和雅化。(4)因地理、历史、民族融合等多种原因,此地藏语方言较多,发音有所区别。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早有任乃强先生,其在《艽野尘梦》校注中说:“打箭炉三字,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明初即有此译称,清乾隆时始有人附会除诸葛亮的传说。”[9]并在《多康的自然区划》一文中认为,“藏语‘多’字,恒指交通便利,商道四达之地。”《辞海》打箭炉条是这样表述的:“实际其地为达、折二水汇流之处,藏语谓汇流处为‘渚’,故称达折渚,音讹附会为打箭炉。”《炉城风物》进一步认为,“元朝后,许多汉人移居于此,便转音为‘打箭炉’了。”(5)见《郭达与打箭炉》,载于《炉城风物》第一期,1983年9月第3版。从地理上看,打箭炉所在地为“二水汇流”“三山之谷”,黄楙材《西輶日记》中称之为“炉城二水夹流,三山紧抱”[8],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亦云“三山环绕,二水并流”。[6]这里的“三山”指东南的跑马山、东北的郭达山、西边的阿里布果山(其山腰以下称为子耳坡),“二水”就是由北向南的雅拉河与由南向北的穿城而过的折多河,两河在郭达山下汇成炉河向东流入大渡河。
在藏语语境中,“打折多”的字面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雅拉河与折多河两水汇合之处。其中,“打”或“达”是打曲,即雅拉河,“折”是折曲,即折多河,“多”(或“渚”“都”)是汇合之意。主要单纯从地理位置上两河交汇的特点来理解的,今西藏昌都(察木多)地名的由来与此类同。
二是郭达山与折多河相遇的地方。此处的“打”指“打朵郭达”,“折”指“折朵折拉”,“多”是地标。这种理解与民间传说紧密相关,在传说中郭达山与折多河是朝夕相伴、永世相爱的恋人。
三是汉藏通商之唯一适中地。其中,藏语的“打”为发达之意,“折”为第一之意,“多”为商埠或码头之意。这种理解突出了“打箭炉”的经济地位与价值,作为汉藏贸易的重要互市口岸。
四是交易优质丝绸的河谷。其中,藏语的“打”有丝绸之意,“折”是优质之意,“多”指河流汇合之谷地。这种理解更进一步地明确了打箭炉在汉藏贸易中的主要交易范围,藏民们在此不仅可以购买到大量的茶叶,还可以交易到内地生产的丝绸,将“打箭炉”看作藏汉居民交易丝绸的重要口岸。
五是山巅插有经幡的河谷。其中,“打”为印有经文的嘛尼经幡,“折”为山顶,故“打折”是指插有嘛尼经幡的神山,“多”为三山之谷或水流交汇之地。这种理解突出了康人尊崇神山的民间信仰习俗,把“打箭炉”作为藏传佛教圣地的地位紧密相连,在藏传佛教中,“打箭炉”的“三山”被认为是密宗事部三怙主,根据郑少雄先生的说法,这种观点在康定流传甚广,地方文史人员以及康定老人口中随处皆可闻见,“西面子耳坡的阿里布果山是‘降米央’(佛教文殊菩萨),东北的郭达山是‘香那多吉’(金刚部金刚菩萨),东南的跑马山是‘新热色’(莲花观世音菩萨),三座深山共同守护着康定这块吉祥宝地。”[10]
六是射箭的河谷。其中“达折”被理解为射箭,“多”亦为二水交汇的河谷之意。“射箭”之意可能来源于藏族的一个传奇性故事,因一精于射猎的商人罗布绒布在此射鵰而得名,也可能与清代在此驻军时常演练有关,反映了藏民勇武善射民族天性,侧重于表现民族身份认同感。
七是“三山环抱,二水中流”的山水地形。马月华《打箭炉的传说及地名刍议》一文从汉语音译藏语地名的谐音、雅化、赋予含义等各种现象分析,认为“这个地名,在明代的史籍中,写作‘打煎炉’这一事实,不仅能证明这个地名是藏语地名的译称,而且从‘打煎炉’到‘打箭炉’,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地名谐音、雅化并赋予含义的演变过程。”[11]但不赞同“打折多”是“打曲”和“折曲”的说法,认为“折多河藏语从来就叫‘贡曲’而不叫‘折曲’这是事实。只有‘打曲’而无‘折曲’,‘汇合’之说也不能成立。”[11]文章进一步结合“旗幡”“拉则”“将军庙”“护法神殿”“骑羊护法”等藏语,认为“郭达山顶的神奇‘箭竿’,是孕育各种打箭炉传说的基因,同时,也可能就是打折多命名的依据。‘打折多’的全部含义,是否是‘以箭竿矗立的郭达山为标志的三山环抱二水夹流之地’。”[11]民国《康藏研究月刊》第十六期有《川边之打箭炉地区》一文,也认为藏语打折多三字组成一名辞,其义为“旗竽聚合之处”。《情歌的故乡——康定》一书也持此说,认为“‘打折渚’的具体含义是对康定地形十分贴切的概括性描述。”[12]“达”在藏语中有白丝绸或飘忽的白色经幡的含义,当登高观看城内的雅拉河、折多河以及两水汇合后的炉河,在高原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更加耀眼的银色光芒,恰似白色的丝绸、飘忽的白色经幡。“折”在藏语中则有尖顶之意,这个尖顶并非指山巅,而是指两水汇合处的山形。折多河、雅拉河的汇合处,则恰恰是在郭达山“V”字形的尖顶处。“渚”则指汇合之意,“折”是对“渚”的具体补充。
四、 “打箭炉”地名中的文化整合
地名,不仅是反映一个地方、一片土地的自然风貌,储存自然生态档案,也记录着各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历史,反映生存状态、民风民俗,蕴含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地名作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反映一地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留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到认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13]作为表征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常常将最质朴的、最本来的面貌定格在山水大地之间,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往往从地名中便寻找到更久远、更本真的历史,因此地名就是记忆,它蕴藏着一个地方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乃至对宇宙的认识,反映着人们的思维逻辑。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一书中摘选了大量来自康定地区的汉人和藏人的民间传说,将之视为康定地区汉藏民众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解和想象,认为“打箭炉的命名权之争,与其视为族群之间的边界划分或空间争夺,毋宁说是区分与融合、争夺与接纳相互辩证推进的历史进程。”[10]
(一)语言文字的互译与地名的复杂性
打箭炉及其周边地区的语言较复杂,藏语有康巴语、安多语,其中以德格官话为标准语的康巴语是打箭炉城区的官方藏语,安多语主要流行于折多山以西的牧区,又称牛厂话、牧场话。除此外,还有被划入羌族语系的木雅语、嘉戎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普米语、尔苏语、纳木依语等“地脚话”。在藏语中“打箭炉”有“打折多”“达折多”“达折朵”“达渚多”“打折渚”等多种发音,且字面的意思又有以上七种,应是由复杂的语系而造成的。同一地名,不同地域、种群有不同发音。这一“混杂”的局面,使得“一地多名”成为必然,“打箭炉”所使用的语言,在他者的视域中也就显得极其的“不规范”和“多义”。而随着元明以来,茶马互市的兴起,大量汉族民众来到此地,汉语的加入又再次增加了这一复杂性。汉语语言以形音义的统一体为其基本特点,藏语是以拼音为主的语言,在进行语言文字的翻译时,无法做到准确的词义对照,“借用”“替用”“挪作他用”“择字组合”等现象比比皆是,使得这种“不规范”和“多义性”更加突出,但同时也为入藏的汉族民众在对某一地名进行翻译和理解时增加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创造的可能。民国《康导月刊》称:“城内有庙,神名郭达,藏语为铁匠之意。盖旧有铁匠,在西藏习法,奉命来康,得成正果,土人为建庙,称郭达庙。汉人旅居康定者,询知郭达为铁匠之意,又以大折诺音近打箭炉,遂附会其说,谓孔明南征,曾命郭达领军造箭于此。然三国志及他书既未载造箭之事,亦未及郭达其人,事之穿凿可笑,不问可知。”(6)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二·三期《打箭炉——康藏地名小释之二》这一理解大致解释了“打箭炉”这一称号从藏语到汉语的历程。
(二)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自明中后期,川藏道取代青藏道成为往返内地与西藏的主要官道,打箭炉便成为内地通往康区和西藏的交通咽喉,成为汉藏之间交流交往的连接枢纽。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内地汉人大量涌入,他们或因公驻此,或在此经商,或于此营生,或在此远行歇足。清道光年间,姚莹经此入藏,所见“汉蕃互市之所,蕃民数百户”,“汉人贸易者百数,余惟吏役、营兵。”[7]此地成为川边地区汉藏交融最密切之地。长期的民族混居必然在冲突与互动、交流与交融和相互借鉴、相互容纳中带来文化的整合。任乃强先生:“二百年中,此部番民,同化如此速者,汉番混居故也。”[14]又在《打箭炉岁时记》中说到:“打箭炉地介川康,汉番杂处,其俗在华藏之间。据土人言:‘每年有会期六次:三月十八日娘娘会,四月初八放生会,五月十三跑马会,六月二十八盎雀寺跳神,七月初十多吉寺跳神,七月十三城隍会。皆空巷聚观之大集会也’。”[14]明确指出此地民族交流融合的显著特征,在节日庆祝方面表现出了同一性,没有汉藏之别。汉人的“娘娘”与藏人的“度母”本是同一神灵,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呈现出不同的名称而已。人们在保持和认同差异性的同时,通过节庆这一信仰仪式促成文化交融的可能性,于此在众多汉藏民众之间通过仪式的互动与相互作用而实现差异性沟通。而作为藏彝走廊的关键一环,“打箭炉”沉积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要素,呈现出强烈的包容性与能动性。“走廊地带多民族之间的迁徙流动,汉藏之间漫长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使得多元文化在走廊地带层累。在这里,不同身份的人在交流中实现沟通,多元文化在差异性中彼此协调,地方文化在接触中能动再造。”[15]兼容并包、能动地吸收、整合汉藏各种文化要素,从而对本地区文化进行不断更新和再创造,在流动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的独创,从而将过去与现在、历史的与未来紧密连接在一起。“走廊地带的社会互动和文化沟通,既成就了地方,也构建了完整的世界体系。正是走廊地带的沟通与连接,多种身份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多元文化接触、沟通才成为可能。”[15]“打箭炉”地名的变迁过程正是汉藏民族融合、文化互动与交融的见证,是超越历史与空间的存在。
(三)地名认同的内在动力
“打箭炉”地处“中华之极西,西域之极东。”(7)见《打箭炉厅志·炉厅图考》,《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第963页。是汉藏交接之地的著名边城。自明清以来,“打箭炉”这一地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随着历史的发展已逐步实现了自己的文化整合。而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形成的动力是什么呢?任乃强先生曾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同化定律”:“两民族间之同化力,与其文明程度为正比例,与其距离为反比例。汉族同化能力,夙称伟大,附近民族,莫不受其陶镕;独彼西人东来,未被同化,汉族反有同化于彼之倾向;而欧西政府,卒亦不能同化我海外侨民者,似皆可以此定律解释之。其他例证殊多,无庸悉举。然则汉族同化番族之难易,亦即可以此定律推而知之矣。余查番族文明程度,适足与我族周秦之际相当。换言之:即我族较之番族,先进二千二三百年。此番族所以易受我族同化之故耶。然而数千年来,番族竟未受我同化者,交往断绝距离太远故也。(谓人的距离,非谓地的距离。)”[14]在石硕、邹立波《“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一文中,认为这是出自汉人所进行的主观建构与附会,其目的与作用是为了消解汉人入藏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性和文化上的弱势心理,遵循“借用”原则,在妥协、兼容和尊重藏文化特质基础上,通过“求同”途径达成“共享”,并将“共享”发展至信仰层面,实现与藏人的文化整合。[16]简言之,就是入藏的汉人以“借用”的方式来“求同”和“共享”,以最终实现与藏人的“同祀共欢”。这一阐释对解构汉人入藏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非常典型的意义和价值。在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两种相对独立,且均具有自身标准的不同文化在长期碰撞中,有过冲突,也有过包容、吸纳,必然导致文化的混合或同质。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作出著名论断,认为互动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跨文化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一方影响或是控制另一方,而是同化与异化兼而有之。尽管今天在汉藏文献中见不到藏人对“打箭炉”命名方式的抵制,见不到与这种文化“改造”的显性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的涵化、转型、整合的过程完全是和平与静默的。细致的学者会发现,在“让一箭之地”的传说中,尽管藏人折服于诸葛孔明的神明,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曾经捍卫此地文化独立性的努力。而藏人也一直坚持“打箭炉”是藏语的音译,包含了藏语的语义特征。显然,彰显自身的异质性、拒绝成为他者的对抗性始终是每个文化得以确立和独立的本来方式。
在汉文化语境中,“打箭炉”之名为三国蜀汉丞相诸葛武侯“安炉造箭”而来,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从主观上建构此地并非“异乡”的家国观念,以此来消解初入藏地的汉人在陌生环境中的不适和文化上的弱势心理。从现存的清代历史文献来看,包括地方史志、文人辞赋等,无论是否赞同“安炉造箭”一说,从文字的隐喻上均认为“打箭炉”是国之一域,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中的记载即是佐证之一。从官方的层面来看,清代赴藏的官员都是带着向化、教化的职责的,《打箭炉厅志》中亦言:“国朝声教洋溢,向化亦诚。”(8)见《打箭炉厅志.炉厅图考》,《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63页。清王朝以王者的姿态、帝国的中心文明涵化此地,首先从文化上将其纳入中华之一体,这首先是一种接纳,展示的是帝国的声威与胸怀。其次,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通过整合实现了文化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打箭炉”的地名总是与郭达将军这个人名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同时将军庙以及庙中的郭达神像兼具了汉藏特征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涵化的方式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是符合汉藏人民共同意愿和需求的。打箭炉作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埠,无论是商业还是文化方面的共同繁荣,为汉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打箭炉”地名是汉藏文化整合,相互吸纳而形成的,是汉藏人民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的文化互动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