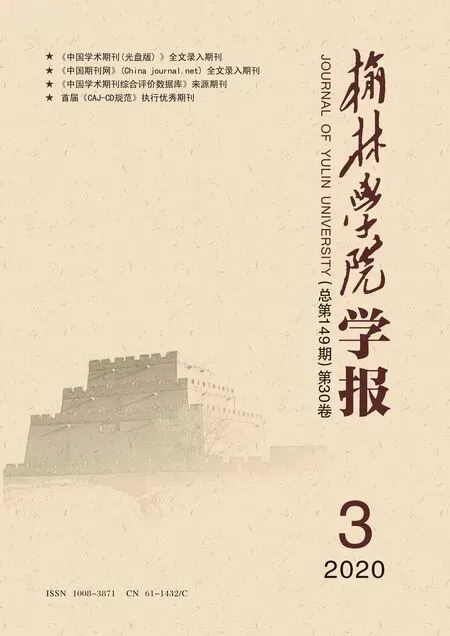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哲学意蕴与时代特质
2020-02-22张波
张 波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自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熟经验,不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鲜的时代特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但自清末进行法治改革以来,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治的主流观点始终对标西方的法治思想、法治理论,这就形成了中国法学理论“表述”与中国法治“实践”之间的错位[1]。本文试图从法哲学视角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进行剖析,对其时代特质进行阐释,以期从理论层面厘清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认识,坚定中国法学本土化理论研究的道路自信。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哲学意蕴
(一)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角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普遍原理与不同时代特殊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进行了科学的论证[2]。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也被两位导师第一次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得到鲜明体现。
在马克思以前的法学理论中,有人认为,法与经济无关,是“纯粹意识活动的结果”;有的虽然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状况决定法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经过长期研究后,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接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4]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5]通过以上系列阐释,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观点振聋发聩,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大厦得以奠基,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由经济决定法律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又对法律的本质、法的特征、法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阐释,形成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体系。在这一科学体系中,法治道路的意志性、法治道路的差别性尤其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法治道路的意志性。 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经济之外对法律影响最大的因素,国家掌控法律。而国家属于能为其提供财力支持的社会集团即统治阶级掌控。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统治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将代表阶级的意志通过形成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时指出:“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6]以国家为媒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在其产生、演变以及目标价值等方面承载的是统治阶级的目标诉求、根本利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中,马克思关于法律阶级性的论述得到了充分验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法治道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然也要利用法律的手段稳定政权、维护统治。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分析工具,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以及阶级实质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意志,是为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第二,法治道路的差别性。在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关于法治道路普适性与差别性的争论一直存在。按照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是由人类理性建构的,因此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法律移植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从社会法学派的角度出发,法不是自上而下对“观念”的模仿,而是从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7]。马克思晚年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研究东方社会农村公社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运行规律与特点后指出,在东方社会中,除国家法之外,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进而提出了法律发展的“东方道路”。
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自清末开始就在“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中摇摆不定。这种“体用之争”背后映射的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分野。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特别指出:“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二)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角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话语特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的内在诸要素总和构成事物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存在方式,是内容的组织和结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又影响作用于内容。中国法治的启蒙发端于清末,以大陆法系的法制模式为蓝本,系统化制定成文法典、重视程序正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先后颁布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民事、刑事)法律,史称“六法全书”。并三令五申地督促各省、市政府印发各区、镇、乡公所及民众教育馆、电影院、报刊等进行宣传。但不顾社会生活发展实际,照搬照抄西方法治思想和模式的做法,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大都存在于纸面,在现实生活中鲜有建树。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批判脱离中国实际,完全移植西方法律的做法为“本本主义”,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不完全拘泥于“据法审理案件”,通过具体案件审判中情理、习惯与法理的交融并用,重视在个案中寻求“定纷止争”与“教育百姓”的双重效果,达到共产党对边区社会治理和改造的目的。时任边区政府主席谢觉哉指出:“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政治需要什么,法律就规定什么”。“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8]。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运用并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用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方式呈现出来,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表达方式宣传出去,并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掌握,才使得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深入人心,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时代基点,继承老一辈革命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论进行科学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特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 “党法关系理论”“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理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系列理论。对于这些艰涩的理论,习近平继承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中国风格”表达方式,进行民族化、大众化的阐释。如在论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时,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9]在论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时指出:“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一个人,没有规矩,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纪律和规矩,就注定成为一盘散沙。”用这样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生活化”语言把依法治国的系列理论范畴表达出来,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主动接受、并在生活中自觉践行,在为中国社会治理与建设提供有效手段的同时,也为世界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角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体现了国家与个人、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释,内涵丰富、结构严谨,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从上至下、由点及面,国家与个人、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承载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形成了党的正确领导与人民的真心拥护的双向化互动性系统整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坐标下,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矢志不渝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10]。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多元主义的法治观”,不仅强调国家法的权威,而且重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礼序家规”等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规范在型塑社会与公民行为方面的规范作用;推崇“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国家治理观,跳出了“人治(德治)”与“法治”二元对立的窠臼。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进一步做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11]、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决定。将政治上的理想信念、社会价值理念以及文化道德观念融入法治体系之中,在实现“法治强国中国梦”的精神统领下,全体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引导带领全体人民实现“执政兴国”与“执政为民”的双重目标;而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服从法律法规,坚持依法办事,在理性与法治的约束下平衡利益、化解纠纷。
(四)从逻辑和历史的关系角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具有一脉相承性
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作为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在具体内容与表述方式方面也各有特色,但两者都是对社会存在的科学反映,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二人从唯物主义史观出发,通过孜孜不倦的漫长探索,终于拨开层层迷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私有制的起源发展与私法的起源和发展的关系后指出:“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12]。在这篇奠基性的论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冲突是法和法的关系产生的根源,法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等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大厦得以科学奠基。马克思与恩格斯接下来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论住宅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两位导师所阐释的法学原理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以往其他法学理论的原则性界限,对当时德国、法国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和动员作用,引起了法学领域的伟大革命,使法学从此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民主主义法制理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随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以及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推进法学的理论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后,从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征程中,习近平在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西方法治文明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十精辟、富有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的科学理论,为法学理论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范式,丰富、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实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时代特质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党性品质
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指出:“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一般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13]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通过领导立法,将党和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来巩固政权,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开始,就在探索建立一种政党主导下的法治模式。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最大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首先在于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负有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并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责任;其次,我们党通过把自己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全过程,将体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法治价值目标具象化为法治运行的严密体系,并为法治的实施提供制度、人才方面的保证,从而构建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后,中国共产党将党规党纪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党员提出了高于国家法律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行为标准,从而使党员成为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模范,引导和带动全体人民守法、护法,自觉践行法治精神。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品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种场合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时,都把“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大厦的强大根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遵循。
首先,法的正义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的正义性是历史性与阶级性并存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超阶级的抽象概念。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就曾明确指出:法的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14]。马克思主义法学从根本目的而言,是为维护和实现“人”这一主体的全面自由和发展而服务的,这是无产阶级法治创制和实施的根本目标,体现了其与资产阶级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场域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正义价值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就确立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创立了便利人民的就地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习近平提出的坚持“依靠法治来保证人民行使当今做主的权利”“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立场更加鲜明,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道路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实践性品质
科学的理论不仅是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鲜活的生活实践中发挥出重大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并一以贯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保障了依法治国战略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必须以中国当前实际为基点开展法治建设。改革开放实施30多年以来,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历史性飞跃,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把握、积极适应国际和国内社会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使主观认识科学反映客观世界。习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15]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向认识提出新的课题,在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的过程中,也推动着认识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重大改革(包括法治)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6]。
最后,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享誉世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由此确立。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变世界,建设法治中国,把法治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从最终目的而言,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