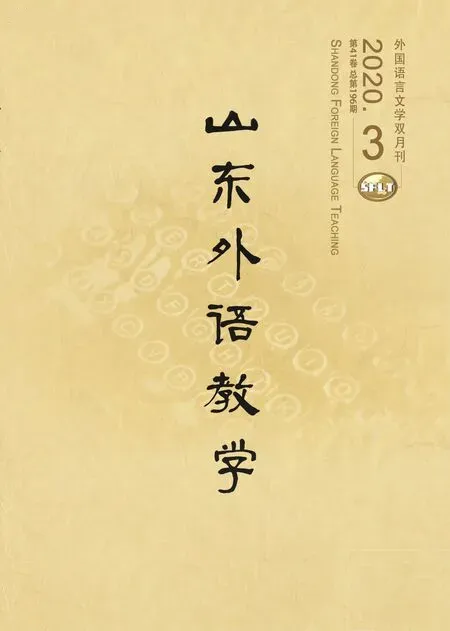“目视是一种权力”:论《土生子》中的“看”
2020-02-22陈后亮宁艺阳
陈后亮 宁艺阳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1.0 引言
对数百年来饱受奴役和剥削的美国黑人民族而言,南北战争是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水岭。当反对蓄奴制的北方联邦赢得这场内战的胜利,罪恶深重的奴隶制度得以最终废止,南方种植园黑奴亦随之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身份。然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并未就此宣告终结。在弥散着白人监视目光的美国监狱式现代社会,“法典化的惩罚权力转变为规训性的观察权力”(Amad, 2013:50)。一种更加复杂精密、经济高效的行为规训和管控技术代替鞭笞等肉体惩罚成为主导性的种族控制手段,继续对黑人民族实施更为全面彻底的精神奴役和征服。
深受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一改传统黑人文学作品中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型黑人形象,在长篇代表作《土生子》(NativeSon)中开创性塑造富于反抗精神的新黑人形象——别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值得注意的是,该形象的最终建构同《土生子》通篇频繁出现的“看”的行为密切相关:白人凭借规训性凝视对黑人他者的想象来巩固和维系以白人为主导的种族社会结构,而以别格为代表的新黑人则反向模仿和利用白人的凝视行为,以一种反抗性凝视向白人霸权宣战,从而能动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事实上,这些复合种族维度的双向性目视行为并非简单的视觉交流活动,它们能够深刻反映美国种族隔离制度背景下白人和黑人之间极度不对称的视觉权力关系。
本文旨在分析白人世界藉由监视网络和凝视行为对规训权力的行使,以及别格的反凝视行为对白人规训目光的模仿和挪用,以期更好理解视觉活动对种族权力关系的建构和支撑。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以街道上印有白人形象的彩色招贴画为例,结合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分析白人世界是如何运用美国监狱式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网络监视机制来行使规训权力,从而调整并规范黑人群体的行为方式;其次以影院的黑暗规训场域为例,揭示白人主流文化操纵下的影视图像话语是如何干预并管控黑人民族的精神生活;最后结合玛丽事件,探究别格如何通过反向模仿和利用白人规训目光,实现对盲视的白人世界的消极反抗。
2.0 “就像关在监牢里似的”:无所不在的白人监视
《土生子》中,主人公别格同白人世界的首次目光交锋并非发生于他与特定白人实体之间,而是在他与印有白人形象的彩色招贴画之间演绎:“他望着那张招贴画:那张白脸胖鼓鼓的,但很严峻;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直指街上每一个过往行人”(Wright,1999:13)。身为“这个世界的监督人”(杨卫东,2002:54),招贴画上的勃克利神情严峻、手势富于威慑意味。特征鲜明的面部表情与肢体动作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这位威严的白人形象——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化身。具体而言,这张被别格视线所捕获的招贴画服务于双重意图:首先,作为一种公众宣传手段,它寄予勃克利本人的政治野望,其目的在于提高声誉、拉取选票。招贴画上方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违法的人不会赢!”(Wright,1999:13)——看似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实则是勃克利为在选民大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而采取的政治谋略。别格深味勃克利形象所代言的社会公正论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毕竟以勃克利为代表的白人上层阶级才是负责校准公正天平的垄断集团。是故,他轻蔑地把勃克利视为受金钱砝码役使的“骗子”——“谁给你钱,你就让谁赢!”(Wright,1999:14)。然而对于源自该法律化身的监视目光及其难以觉察的规训效力,别格未能给予足够的警惕与重视。福柯曾说:“保障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一般法律形式……是由我们称之为纪律/规训(discipline)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福柯,2012:248)。作为一种隐蔽的监视技术,这张招贴画承载着白人“文明”社会对被其视作野蛮暴力、道德意识淡薄的黑人群体的规训性凝视,其目的在于规范后者的行为、遏制违法犯罪活动。
实际上,勃克利的招贴画形象可谓美国种族社会庞大而广延的网络监视体系的缩影,其凝视的双眼犹如一台精密而灵敏的监视设备:“只要你去看它,它就直勾勾地看着你,你一路走着,只要回过头去看它,它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你”(Wright,1999:13)。别格所望见的那张招贴画仅是针对黑人凝视受体所精心编织的监控网络的诸多结点之一,张贴于其他广告牌上的竞选宣传画同样发挥着监视职能,它们将源自白人世界的目光“问候”进行统一分配,投向处于各结点视域范围内的每个黑人过往者。这些沿街排布的彩色招贴画以无形的视线联结,彼此视阈交叠,全方位覆盖着黑人聚居区,从而实现一种连续不断的监视效果。因此,尽管行走在以黑人为主体的街道上,别格依然感受到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的白人凝视。这种“充满规训力量的视觉暴力”(陈后亮,2018:133)调控并规范着黑人群体的行为方式,时刻警示他们切勿僭越白人社会严格划定的种族界线,否则将受到白人统治集团暗箱操控下的法律傀儡的严厉制裁。毕竟种族社会的现况正如格斯无奈的评述般残酷而黑暗:“你[别格]是黑人,他们[白人]制定法律”(Wright,1999:21)。法律的制定、诠释、判决乃至最终执行等各道环节均由白人主导,而“占据成文法(formal law)之外的空间”(Taylor,2016:184),受法律之眼严密监视的黑人对白人专属的法律话语权力唯有遵从的选项可言。
福柯认为:“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权力的效应”(福柯,2012:194)。以招贴画的图像形式作为物化表征的监视网络机制有序扩展为白人行使规训权力的渠道,的确在同黑人受体的结合中衍生出可观的实质性效应:扼杀他们的犯罪欲望、遏制他们的越轨行径。这种源自招贴画的白人监视目光的约束与威慑效力同隐于其后的法律问责与追惩体系的恐惧加持作用密切相关,能够诱导黑人自觉对其行为举止进行监督和管控。例如,在一劳永逸地摆脱经济困窘的物质动因驱使下,别格等四名黑孩子曾计划抢劫白人店铺。尽管这一有利事实得到确证:“下午三点到四点,布鲁姆熟食店所在的那条街上没有警察值勤,将会很安全”(Wright,1999:21),他们却始终顾虑重重。这一流动监视单元的暂时性缺场意味着他们能够安全避过白人警察的巡视目光,顺利实施犯罪计划。然而该人力监视机制的真空期却未能消除他们内心的疑虑与担忧,因为他们清楚:“法律监督的目光时刻在注视着每个人,任何心存侥幸期冀僭越者必定难逃法网”(杨卫东,2002:54)。对于侵害白人利益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与暴力惩罚,他们感到本能的畏惧:“他们依稀觉得,抢劫布鲁姆的铺子将是触犯最后的禁忌。他们一越过这禁区,一个陌生的白人世界将向他们倾泻全部怒火”(Wright,1999:14-15)。这种深重的恐怖意识持续阻滞着他们将抢劫白人的犯罪欲望付诸行动,直至酝酿已久的抢劫计划彻底破产,从而实现行为监管的自动化。
这种监视网络与规训权力沆瀣共谋白人对黑人的全面压制与征服的“吉姆·克劳”隔离制社会可谓边沁所构想的全景敞视建筑的种族政治变体。在别格和格斯眼中,“伸展和耸立在他们面前阳光中的巨大白人世界”(Wright,1999:19)是陌生与神秘的代名词,充满未知因素,即“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福柯,2012:226)。在种族隔离的社会背景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世界全权发挥着中心瞭望塔的监督职能,而被划归至城市一隅的黑带区则对应瞭望塔四周沉浸在监视目光之中的环形建筑。这种看与被看、监视与被监视的视觉关系维持并不断强化着一种极端不对称的种族权力关系:“我们住在这儿,他们住在那儿。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Wright,1999:20)。凭借“中心瞭望塔”的优势视角,居高临下的白人理所应当地成为特权的享有者;而黑人则沦为饱受压迫和排挤之苦的边缘群体,过着囚犯般绝望而痛苦的生活:“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干啥都成,我们干啥都不成。就像关在监牢里似的”(同上)。身为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各项合法权益又被榨取剥夺的黑人大众中的一员,别格就像监狱里的囚徒,苟活于恐惧和仇恨之中,追寻不得未来的希望与生命的意义。
部分出于对捍卫人格尊严的考虑,部分出于对沉重家庭期望的抗拒,别格起初不愿接受白人救济,只得百无聊赖地在街边游荡。然而,即使拒绝白人以行慈善义举之名所提供的救济性工作,他依然无法彻底断绝自己同白人世界的屈辱性联系,而这一残酷现实仅是黑人身体的显著表征属性。“藉由白人凝视霸权,黑人身体经受一种现象学回归,从而被扭曲、固化为一种预先存在的本质” (Yancy,2005:218)。在白人视界里,别格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实体,需要被规训、驱逐到边缘隔离地带囚禁起来”(Yancy,2008:xvi);他那与生俱来的黑色肌体是一种值得引起高度警惕并进行严密防范的潜在威胁,寄宿于这黑色躯体内的罪恶灵魂应当受到持续的监督与规训,以剔除潜伏其中的原始兽性,同时增添理性和文明的白人元素。况且,这种监督与规训的视觉操作易于实施,因为“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福柯,2012: 225):由于黑人皮肤的高度可见性,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自人群中将其析出与定位。罗宾·魏格曼(Robyn Wiegman)的下列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一点:
现代公民身份是一个使某些身体(白人、男性、有产的)的普遍性受到其他身体(黑人、女性、无产的)的无限特殊性保护和对向(subtend)的不对称系统……该系统自身取决于特定视觉关系,其中仅有那些同他者相联系的特殊性可见…… (1995:6)
更何况,“在强烈的阳光下,别格的脸黑得像金属”(Wright,1999:18)。在充足的光照下,他那泛着金属质感、处于高度可见状态的黑色皮肤则使其更易罹受白人目光的辨识、锁定及俘获,从而沦为后者行使规训权力的客体化对象。正如福柯所说:“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福柯,2012:225)。印有白人形象的彩色招贴画不过是美国现代社会复杂繁多的监视技术的一个范例。身处监狱式社会的种族主义阴影之下,黑人无所遁形,因为白人监视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福柯,2012:234-235)。
3.0 黑暗规训场域:影院中的含混视觉主体
生活在充斥着白人凝视的美国监狱式社会,囚犯般度日的别格自然渴望寻得白人监控网络的视觉盲区。而皇家影院——一个能够有效降低其身体可见度的黑暗空间场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他的需求,毕竟“黑暗说到底是保护被囚禁者的”(福柯,2012:225)。也难怪别格的观影愿望相当强烈:“他想看一场电影,他从心底里想看”(Wright,1999:14)。观影实践对于“被剥夺政治、社会、经济和财产权利”(Wright,1999:418)的别格而言助益良多。首先,观影活动替别格消磨无所事事的闲散时光、为其空虚乏味的“监狱”生活增添几分乐趣与调剂,更将别格从温情缺失、令人窒息的家庭生存困境,以及沉重压抑、咄咄逼人的家人期许目光中抽离而出,获得片刻的平静与安宁。再者,“他渴望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刺激,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力,耗尽他的精力”(Wright,1999:30)。观影体验所带来的视觉刺激能使别格将关注的视线转而投向电影画面,有所放松因种族恐惧而时刻高度紧绷的神经,并将自己无处排遣与宣泄的过剩精力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影院场域的黑暗环境令别格感到舒心与安适:“从刺眼的阳光下进来,里面的阴影都很悦目”(Wright, 1999: 31)。对别格而言,这种伴随着显著光影调节的场域转换不但意味着光线强度的骤降和眼部感受的改善,更暗示着他过度可见的黑色身体自阳光下的高敏状态向黑暗中的缓释状态的钝化过渡。置身“黑魆魆的电影院”(同上),别格同黑暗的观影场域自然而和谐地融为一体,从而隐匿自己高度可见的身体属性,暂时将肤色困扰抛诸脑后。影院内部的黑暗观影氛围成为别格身心的绝佳庇护所,使他能够摆脱外面白人世界的监视目光对自己黑色身体的折磨、对“罪恶”心灵的拷问。
影院的黑暗场域亦决定了别格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双重视觉身份的辩证统一。毋庸置疑,别格是将银幕画面客体化为凝视对象的观影者:杰克替他付费购得此次观影体验,因而别格享有观影权利。然而,别格并非配备批判性眼光的主动观看者,而是白人管控的规训对象。这是因为,电影等“大众传媒是一种重复和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的知识-权力系统”(hooks,1992:117)。阿尔多诺曾将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统称“文化工业”,认为“人们的思想,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陈厚诚、王宁,2000:243)。影院上映的影视作品受到幕后白人权力中心的严格筛选与精心安排:其剧情内容和主题思想需同白人统治者的价值体系保持一致,以期“强化使压迫形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Kellner,1995:30)。小说中,名为《荡妇》和《商人角》的两部影片被排在同一场次,此举可谓别有用心。在用于广告宣传的彩色招贴画上,白人与黑人的娱乐消遣活动呈现出巨大差异:《荡妇》的“几张招贴画上画的是一些白人男男女女在海滩上憩息、游泳,在夜总会里跳舞”(Wright,1999:31);而《商人角》的“招贴画上画的是黑人男男女女在蛮荒的莽林前跳舞”(同上)。白与黑两民族的休闲方式相较之下,正如其各异的肤色般反差强烈:前者现代、文明、高雅而又理性;后者则原始、野蛮、低俗且迷狂。即使将活动变量均设置为“跳舞”,两者的场景映射同样差距悬殊:白人“在夜总会里跳舞”,纵享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豪奢体验;黑人“在蛮荒的莽林前跳舞”,显得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后续情节中,透过别格的第一人称观影视角,这种刻意放大的种族差异再次得到强调和凸显:白人拥有自由选择的特权,放松途径丰富多样:名为《荡妇》的“片中有不少喝鸡尾酒、跳舞、打高尔夫、玩轮盘赌等场景”(Wright,1999:36);而黑人娱乐活动形式单一,选择严重受限:“他[别格]看见《商人角》上映,眼看着裸体的黑人男男女女疯狂地旋转着跳舞,耳听着鼓声咚咚”(同上)。而这些正是白人群体为固化种族差异和对立所采取的视觉规训策略。
除将两者并置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外,《荡妇》和《商人角》又各有主题侧重。《荡妇》是一部浸润着阶级主义思想的电影。在其放映过程中,白人目光逆着别格的视线,在银幕上实现一种“远距的、临床的、无形控制的、东方化的以及去人性化的视觉配置”(Amad,2013:53),进而操控别格的凝视:白人统治阶级的认知图式被投射到银幕上,呈现出经过美化润饰处理的上流社会白人生活图景,继而在观影者的视网膜上形成满载“富有白人高贵而优越”信息素的映像,不着痕迹地将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植入观影者的个人价值体系,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并塑造着观影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别格是以“内化的白人视角”(陈后亮,2018:123)凝视银幕画面,从而参与同白人统治者的眼神共谋:当一名“疯狂的小伙子”(Wright,1999:35)打破夜总会的秩序以及别格的美梦,强烈的代入感使得别格竟同电影中的上流社会白人整体产生视角融叠、情感共鸣,“仿佛看到这个疯狂的不速之客后觉得他自己受到了冒犯”(Wright,1999:34)。别格自觉站在白人立场上审视这名闯入者,参与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并与白人统治阶级进行价值认同和对接:“穷白人都很傻。有钱的白人才机灵,懂得如何待人”(Wright,1999:36)。借助影视叙述话语的视觉规训和离间效应,白人统治者得以进一步深化同属社会底层的黑人群体与边缘白人群体之间的阶级裂隙,确保阶级联合的彻底失效。
如果说《荡妇》旨在宣扬阶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商人角》则是白人目光经过种族主义棱镜偏折的投射产物。它以原始的非洲大陆为背景依托,再现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民族的他者想象,影射美国黑人引以为耻的种族源起:他们的祖先是以卑贱的奴隶身份自非洲家园经罪恶的三角贸易被贩往北美大陆。该剧情构思暗示并重温黑人民族被奴役、践踏和凌辱的创伤记忆,委婉地提醒以别格为代表的黑人观影者时刻谨记自己血液中流淌的“奴性基因”,以及他们从父辈那里承继而来的源自古老非洲的黑色遗产——黑人的“野蛮天性”。别格显然不愿依据这种由白人目光投射出的黑人他者形象来审视并定义自我身份,主动选择对这部充满种族歧视镜头的电影视而不见,回归到对《荡妇》所展现的白人生活模式的美好虚拟体验之中:“他看见《商人角》上映……接着非洲的景色变了,换成他自己脑子里一些穿黑色和白色服装的白人男女形象,在那里说说笑笑,喝酒跳舞”(Wright,1999:36)。这种“观看者拒绝‘完全’认同影视话语的‘断裂’时刻”(hooks,1992:117)进一步引发别格对影视图像话语所建构的理想白人世界的憧憬和向往。然而,他不敢心存奢望,企图逾越阶级分野和种族敌对的双重鸿沟,而是转变观念,开始将替道尔顿家工作视为“增加见识,知道内幕”(Wright,1999:36),甚至有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大好机会,打算依附并服务于“有钱的白人”(同上),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
由上述可知,影视媒体是“意识形态隐秘化的渠道之一,具有麻痹(narcotize)‘大众’、使其陷于被动的功能”(Pérez,2011:146)。作为观影“大众”中的一员, 别格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仅对现存的、准许的叙述作出反应”(Gercken,2011:634),而非主动的意义建构者。是故,影院的黑暗场域并非白人目光无法触及的视觉死角,而是一种更为隐蔽高效的监视和规训机制。朱迪斯·巴特勒曾说,“在种族问题上,视觉场域[visual field]并非中立,它本身就已是一个种族结构、一种强制性的霸权知识”(Butler,1993:27)。白人凝视透过银幕,以自身为权力中心点营造出一片由白人主流文化操纵的黑暗规训场域,使别格等黑人观影者再度沦为消极迎受白人规训目光的视觉俘虏。如贝卡·格肯(Becca Gercken)所说,“主流文化的全景敞视主义将其[观影者]置于客体而非主体;被观察者而非观察者;被动而非主动”(2011:633)。
4.0 盲视的白人世界:对白人目光的反向模仿和挪用
黑暗规训场域的影视叙述话语成功说服别格,使其决心接受救济署介绍的工作,前往道尔顿家。在这个“冷漠、疏远的世界”(Wright,1999:47)里,别格深切体会到白人目光强效的异化作用。道尔顿先生饱含种族歧视意味的锐利目光,辅以不怀好意的戏谑笑容,令别格原本的不适和窘迫愈发深重:“那人[道尔顿先生]正凝视着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似的,面带笑容,那笑容使别格意识到自己身体上每一平方英寸的黑皮肤”(Wright,1999:49)。这种穿透肌体、直击灵魂的种族主义凝视能够激发深植别格内心的自我憎恨和自我否定的消极意识,使他在恐惧和耻辱交融的情感泥淖中彻底陷落。后文中,玛丽和简的目光固然真诚而友善,别格却疑心自己充当了白人阴谋的试验品,再度陷入这种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异化状态:“他觉得当时自己的肉体已不复存在,他已成了某种他所痛恨的东西,成了耻辱的象征,这象征他知道是跟黑皮肤紧密相联的”(Wright,1999:73)。
白人不但占领着凝视主体的种族制高点,还殚精竭虑地企图剥夺黑人凝视的权利。赖特曾在作品中对别格在道尔顿先生面前的窘迫表现及其对白人心理的精准揣摩做过精彩描述:
自从他进了这个宅子以后,他一次也不曾把他的眼睛抬得跟道尔顿先生的脸一样高。他站在那儿,稍稍弯着膝盖,微张着嘴,弯腰曲背;眼睛看东西也是浮光掠影的。他心里有数,在白人跟前,他们就喜欢你这样。倒不是有人谆谆教导过他,而是白人的态度使他感到他们喜欢你这样。(Wright,1999:52)
别格同道尔顿先生的目视高度差明确了两者在这次视觉交流活动中的角色分配,从中不难推导出黑白两种族之间严重失衡的视觉权力关系:“白人占据‘看’的主体位置,他们是主动观看者,可以有选择地看或不看。黑人则通常是被看的对象,既无看的权利,也无权决定自己如何被看”(陈后亮,2018:120)。别格清楚:在白人面前卑躬屈膝、诚惶诚恐,对白人惟命是从的汤姆叔叔型传统黑人形象才符合白人凝视主体对黑人民族的视觉预期。道尔顿先生自别格对白人凝视的垂首回避及其局促不安的举止表现中获取积极的视觉反馈,足以确证眼前这个黑孩子对自己白人威权的敬惧和服从。胡克斯说:“目视是一种权力”(hooks,1993:115),这在此处体现得非常明显。杰克·泰勒也认为白人凝视是“一种使人联想到种植园管控模式的政治征服工具”(Taylor,2016:199)。这种规训技术得以生效的事实能使道尔顿先生体会到权力增殖所孕生的充盈感和安全感,而这正是他“仔细瞅着”别格,迫使后者“把目光垂下”(Wright,1999:54)的深层心理原因。
而黑人针对白人女性的凝视目光则尤为白人男性视作无可饶恕的亵渎和冒犯之举,甚至“他目光的一瞥就是一种威胁”(Wright,1999:420-421)。在《土生子》成书的社会背景下,“黑人会由于目视白人女性而被谋杀或处以私刑”;“黑人男性凝视总是罹受强权白人他者的控制和/或惩罚”(hooks,1993:118)。在别格眼里,玛丽是白人性威胁的符号象征、一种致命的视觉诱惑。因此,他惧怕直视玛丽,驾车时只敢以后照镜为目光缓冲介质间接窥视她:“他一边开车,一边从后照镜里注视她”;“他从后视镜上瞅着她”(Wright,1999:68)。当玛丽醉眼惺忪、周围又无白人男性在场时,他方敢将自己的男性凝视目光无所顾忌地直接投射到她身上:“他看着她,几种情感交集:束手无策、爱慕和憎恨” (Wright,1999:90)。玛丽“长得美丽、苗条”(同上),其女性之美难免令血气方刚的别格心生“爱慕”,觊觎这颗“严禁黑种男人靠近的美国禁果”(Williams,1995:66)。但与此同时,“她是白人,他恨她”(Wright,1999:90),恨她过分的亲近与热情给自己造成的“白色恐怖”,恨她的存在对自己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状态的昭示,恨她的白人女性身份对他的男性气质和生命安危所构成的复合威胁。在黑暗的房间,玛丽“眼睛紧闭着”(Wright,1999:92),视觉官能因酒精麻痹而暂时性失效,这愈发助长了别格内心压抑良久的凝视欲望和雄性冲动:“他俯在她身上,异常兴奋,在暗淡的微光中望着她的脸”(同上)。正如贝尔·胡克斯指出,“一切意欲压抑我们黑人凝视权利的尝试均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无法遏制的对观看的渴求、一种反叛欲望以及一种对抗性凝视”(hooks,1993:116)。白人至上主义者既无法彻底剥夺黑人的凝视权利,亦无力实现绝对化白人霸权的妄念。恰恰相反,他们对黑人视线的暴力阻断势必导致黑人对抗性凝视向白人规训性凝视发起有力回击。“对全球范围内受殖民统治的黑人而言,‘凝视’过去一直是且现在仍是一处反抗场所(site)”(hooks,1993:116)。玛丽之死成为别格反凝视意识全面觉醒的契机,其中围绕两个种族之间的视觉权力关系,别格展开比暴力反抗更为行之有效的种族斗争形式:反向模仿和利用白人目光的消极反抗,或者说一种“意图超越(白人)掌权者认知雷达的‘红外政治的’(infrapolitical)反抗形式”(Yancy,2005:251)。
当别格失手误杀玛丽,他并未选择畏罪潜逃,而是假借无辜者和局外人的伪饰继续留在道尔顿家。别格自信不会成为白人的怀疑对象,因为倘若利用得当,白人眼中愚蠢无知、胆怯温驯的黑人他者形象能够确保他掌控局势、安全潜伏:“他们[白人]决想不到一个黑肤色的、腼腆的黑人会干出这样的事来”(Wright,1999:203);“对他们来说,他[别格]只不过是一个黑皮肤的无知黑人”(Wright,1999:230)。身体的黑色曾一度为白人规训目光所标记,给别格造成物质和精神困扰,此时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色。为掩盖犯罪事实、摆脱犯罪嫌疑,别格反向模仿和利用白人眼光,藉以绘就自己设计视觉伪装所需参照的蓝图。具体而言,别格干预并操演白人对黑色皮肤的他者想象,即“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由白人恶意所投射出的黑人形象”(Yancy,2005:218),选择性规避可能引发自身嫌疑的不利成分,强化有益于自己同玛丽“失踪”一事撇清干系的意象要素。例如,当白人侦探布列顿就玛丽与简之间是否发生性关系这一敏感话题审问别格时,他“垂下眼皮,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更好些。他知道白人认为所有黑人都渴望着白女人,因此他要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恭敬样子,哪怕只是在他跟前提到一个白种女人的名字”(Wright,1999:214)。别格有意规避白人具有“象征性阉割”效力的眼光所预先设定并小心提防的性欲旺盛、时刻渴望侵害和占有白人女性的污名化黑人形象,同时强化白人期望视野所框定的谦卑恭顺、对白人威权心怀敬惧的奴化黑人形象,即蓄奴制时期南方种植园黑奴形象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这些经白人目光想象式建构而得的黑人刻板印象曾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用作替种族殖民统治秩序辩护和正名的利器,此刻却被别格反向模仿和利用,竟成功欺骗和蒙蔽了整个白人世界。这是因为,别格所对抗的是一个盲视的白人世界:“简是瞎子。玛丽也是瞎子。道尔顿先生同样是瞎子。道尔顿太太更是瞎子”(Wright,1999:115)。他们选择性无视黑人边缘群体的悲惨境遇,唯愿遵照内心臆想的种族主义图景来审视和定义黑人民族。这些被种族主义惯性思维蒙蔽双眼的白人凝视者自然对别格的真实存在视若无睹。
不同于盲视的白人世界,别格“把一切看得非常清楚,也非常简单:扮演别人认为你应当扮演的角色,但照你自己的意思行事”(Wright,1999:122)。他采取阳奉阴违的消极反抗策略,表面上故作谦恭地迎合白人预期,依据白人目光主动调控自己的言行举止,暗中却伙同情人蓓西制造绑架假象诈取赎金。直至犯罪真相败露、所有不利证据尽数指向别格,白人警方依旧难以相信整个犯罪流程均由这个“黑皮肤的小丑”(Wright,1999:223)一手策划,甚至疑心幕后另有白人主谋:“他们觉得,谋杀和绑票的计划太周详了,一个黑人的头脑决想不出来”(Wright,1999:263)。在他们的种族主义视界里,被赋予原始愚昧、智力低下这等意义解读的黑人他者符号同别格所犯下的“深谋远虑”的罪行无法有效兼容。
5.0 结语
纵观全书,别格的种族斗争实践主要分为两种形式:暴力反抗和消极反抗。前者包括暴力摧毁象征白人凝视威胁的玛丽以及参与白人眼光同谋的蓓西。以法律准绳来衡量,别格的两次杀人皆属非正义犯罪行为。然而对于在白人监视和规训目光包围下“不曾有过机会”(Wright,1999:376)的别格而言,“他这一辈子里在他身上发生的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两次杀人”(Wright,1999:257)。它们更意味着对白人神话的解构、新生和自我实现,是“一种创造活动”(Wright,1999:420)。从两次杀人中,别格汲取战胜种族恐惧的信心和勇气,体验并享受权力增幅的自由与快意,以及命运自主的充实与满足。相较之下,别格的消极反抗对种族平权的早日实现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它为罹受视觉暴力的黑人抵御白人凝视的规训效力提供参考范本,是一次超越白人目光对黑人民族的他者想象和种族建构的有益尝试。对黑人整体而言,他们唯有争取凝视的主动权,打破白人凝视者一厢情愿的种族主义镜像,从白人视界的封锁中突围,才能成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尽管如小说结局所预示:别格最终难逃死亡宿命,沦为种族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他的黑色存在对白人群体的视界侵入迫使“开明”白人重新审视边缘黑人群体的生存境况和真实需求,警示他们白人网络监视机制并非无懈可击。一言以蔽之,别格的抗争能够促进黑人反抗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策略的革新,有所平衡黑人和白人之间长期倾向后者的视觉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