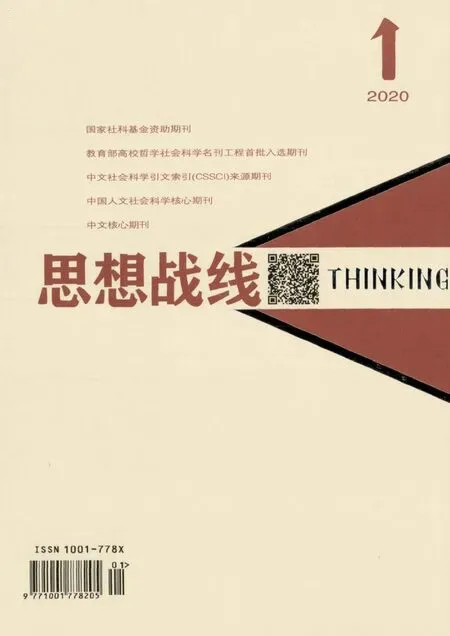明清时期傣、白族名混称的原因、影响及其辨识
2020-02-21古永继
古永继
傣族、白族为云南特有民族中的两大群体,其族名在历史上多有变化。傣族先民,唐代因其生活习俗,被称为金齿蛮、银齿蛮、绣面蛮、绣脚蛮、茫蛮、白衣蛮;元代称金齿百夷,或分称金齿、百夷、白夷、白衣,也偶见僰夷之称;明代多称百夷、僰夷、大百夷、小百夷;清代或沿称百夷、白夷、伯彝、僰夷、僰彝,或改称摆夷、摆彝、摆衣等。白族先民,唐代称为白蛮,元代亦称白人、僰蛮;明代多称僰人,或僰、白交替使用,并有为与外地进入的汉族军屯户“军家”相区别的“民家”之称;清代记载中,白人、僰人、民家互见,同时也有僰子、僰儿子、白子、白儿子、那马等称。而僰人、僰夷,在明清文献中则有时指白族,有时指傣族;有时甚至在同一族称、同一段史料中,其内容一部分指的是白族,一部分指的则是傣族。“僰”“白”两字常相混杂,这对后人了解、研究此时期傣族、白族的历史及相互关系,无疑造成了混乱及干扰。此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实乃罕见,而人们则将其原因片面归结到明代的大理学者李元阳身上。(1)尤中先生言:“白族的民族名称,在明朝前期所有的记录中,仍然写作‘僰人’。但在当时的白族中,尤其是在白族知识分子中,受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使自己的民族与同区域内其他的少数民族一起被视为‘夷人’。因而,白族知识分子李元阳在万历初年编成《云南通志》,便在该书中用‘僰夷’去记录当时被称为‘百夷’的傣族,而把‘僰人’(白族)则写作‘郡人’。李元阳是想把白族的‘夷人’帽子甩到傣族的头上去,使自己的民族不被列入‘夷人’之列。然而,这就使‘僰人’(白族)与‘百夷’(傣族)的书面记录名称淆乱不清。”参见尤 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9~370页。江应樑先生说:“大概以‘摆夷’作‘僰夷’,始自明李元阳所修的《云南通志》,之后,各家著述及地方文献,对于‘摆夷’‘僰夷’便都随意书写而无所分别。”参见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另,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5~119页),对此也有相关论述。但考查两族历史,其名称的混乱实有一定客观因素,将责任全推到李元阳头上,未免过于片面及简单化;而两族名称混乱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面对史载,今天该如何分辨识别?本文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李元阳更改族名有一定客观因素
“僰人”,为对傣族、白族先民族称有着极大干系的关键之词。
“僰人”之称, 最早见于战国吕不韦之《吕氏春秋》:“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2)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第八》,(清)崇文书局辑《子书百家》,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3)许 慎:《说文解字·八上·人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7页。此为“僰”字与族名联系之始。《史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童、牦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4)《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华阳国志》:“僰道县……治马湖江会, 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5)常 璩撰,刘 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85页。说明僰人主要聚居于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西南)僰道县。“僰道”之称因族名而来,僰人则以川南土著身份见于史载。
魏晋唐宋之际,有关僰人的记载一度消减,元时又逐渐增多。元代李京认为,汉代迁移到云南的僰人与当地人融合,形成了云南白族的先民。其《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嶲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则白人之为僰人,明矣。(6)李 京撰,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由于秦汉以后僰人流徙而分布面扩大,今滇、川、贵、湘诸地都有涉及,故其族属现今说法甚多,有汉族说、氐羌说、傣族说、白族说、彝族说等。但元以后僰人的活动主要见之于云南且与白族先民直接挂钩,因而白族说的主张在云南影响甚大而最具代表性。
“僰夷”之称则出现较晚,从元至明清,与百夷、白夷并列,逐步成为了傣族先民的又一称呼。
史载元初世祖时,云南“僰夷与蛮相仇杀,时省臣受贿,助其报仇,乃诈奏蛮叛,起兵杀良民”,云南廉访使朵儿赤上奏朝廷,省臣被查办。(7)《元史》卷一三四《朵儿赤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55页。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也先不花拜上柱国、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阿郎、可马丁诸种僰夷为变,讨平之……”(8)《元史》卷一三四《也先不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67页。元泰定二年(1325年)夏四月丙午,“僰夷及搜雁遮杀云南行省所遣谕蛮使者,敕追捕之……五月壬子,车里陶剌孟及大阿哀蛮兵万人乘象寇陷朵剌等十四寨,木邦路蛮八庙率僰夷万人寇陷倒八汉寨,督边将严备之。”(9)《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6页。《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戊戌,“南安侯俞通源卒……十六年,命守云南。二十一年征僰夷,八月召还京师,至是以疾卒。”(10)《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九五,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1962年影印本,第2937~2939页。经查证,上述5次战事中除第一次具体区域不明外,后4次均发生在当时白夷的分布区,僰夷所指为傣族先民。此为史书中将僰夷等同于白夷、百夷,而将其作为傣族先民族称的最早记载。
《元史》成书于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洪武实录》产生于太祖朱元璋去世新帝继位之后。这说明,明初的人们将“僰夷”代替白夷作为傣族先民族称已不鲜见。但近人著名学者方国瑜、江应樑先生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元泰定时的记载乃明人修《元史》时的错误,或仅是偶尔使用了明代人的称呼。(11)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三《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两先生为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所言自不乏道理,但其对元世祖时的两处“僰夷”之载则未涉及、无评说。值得玩味的是,明初其他史料从侧面提供了另一信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出使麓川归来的李思聪在所呈《百夷传》中说:“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之西南……其种类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缥人、古剌、哈剌、缅人、结、哈杜、怒人等名,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12)陈 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李思聪《百夷传》,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37页。一个“皆”字,表明将“百夷”称为“伯夷”“僰夷”,绝非少数人行为。《元史》问世于《百夷传》之前,李思聪熟悉《元史》或不奇怪,但他与《洪武实录》实无相见之缘。明代定制,凡新帝继位,即诏修前一代实录,有关前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典章制度、官吏升迁、自然灾害、重大事件、民族及中外关系等,都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下来,称为《××实录》。李思聪向明太祖交奉《百夷传》时尚无《洪武实录》之说,当然也就无从预知后来问世的《实录》中会有何种内容,更不可能知晓云南的白夷、百夷是否会与“僰夷”有关。这表明,李思聪所见并明言的“皆非”之说,不可能只有目前今人已知的前述数例。因而我们变换一下视角和思路,是否可以认为:在明初,将“僰夷”等同于白夷、百夷而将其作为傣族先民的称呼实已不少,只是尚未得到社会的共识和认可而已;现在我们不应仅将其视为个别修史者的无心之误或偶有人使用,否则当时的李思聪为什么又要写上这一笔?
明万历间, 李元阳所修《云南通志》载:
僰夷在黑水之外, 即今之所谓百夷也。僰、百声相近, 盖音讹也。性耐暑热, 所居多在卑湿生棘之地, 故造字从棘、从人。滇之西南旷远缅平,滨海多湿,故僰夷居之,虽有数十种,风俗大同小异,统名僰夷也。有大、小僰夷、蒲人、阿昌、缥人、古喇、哈喇、缅人、结、哈杜、怒人等名,皆僰类也。风俗稍有不同,名亦因之而异。(13)李元阳纂,刘景毛,江 燕等点校: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僰夷风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下册,第1486~1487页。
黑水即今澜沧江,外有永昌、顺宁等府,确实分布着众多的僰夷即傣族先民,而黑水之内的大理、剑川等地也居住着包括僰夷在内的众多民族。此处言“僰夷”即“百夷”与“僰、百声相近”,意指两字乃读音相似,常被人们混淆而误之为一。于此可以推断,不言对错,明代从洪武到万历时期2百余年间,人们对两字的相讹相混恐已见怪不怪,李思聪纠谬之类的行为似乎作用不大,以“僰夷”作为傣族先民称呼的现象应只会增多而不是减少,更不可能消失,这或许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李元阳在其著中称呼傣族先民时,公开、明确地以“僰夷”取代白夷、百夷、伯夷,只不过是立足于前人基础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学术承认和记录而已,所反映的绝非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及无稽之谈,因而此后的云南方志,如明末的天启《滇志》,清代康熙、雍正、道光、光绪时的《云南通志》等,在涉及明清傣族先民族称时,才会多有沿袭万历《云南通志》之事。
但是,李元阳此举还涉及到对原有白族先民名称的更改,在书中以“僰夷”取代百夷、白夷之时,为让两族族称有别,又把之前文献中白族先民普遍的称谓“僰人”改为“白人”或“郡人”等,而在介绍云南各族概况的“僰夷风俗”“爨蛮风俗”中,有大、小僰夷,蒲人,阿昌,缥人,古剌,哈剌,缅人,哈杜,怒人,爨蛮,么些,斡泥,野蛮,扑子蛮,罗罗等,却唯独不提与白族有关的“僰人”“白人”而特意将其撇开,对白族先民族称变化的原因缺乏交待,因而对后来云南历史上白族与傣族书面名称的混乱,实负有一份难以推脱的重大责任。
二、傣族、白族族名混称的影响
由于傣、白族名变化及万历《云南通志》的引导,后人在编纂云南志书时多沿用了李元阳的说法,但有的史籍却未完全摆脱长期中形成的习惯,同一书中有的地方改动有的地方依旧,从而导致了存在两族同名的混乱局面。如明末天启时昆明人刘文征所撰《滇志》,虽在傣、白族名基本内容上采纳了李氏观点,但若干地方仍保留着“僰夷”“僰人”与“白人”的关系而难以割断。如称大理府云南县土官杨奴为“僰夷”,张兴、李义为“僰民”,袁奴为“僰人”,杨胜为“乡人”,杨惠为“乡民”,北胜州高斌祥为“僰夷”,等等,(14)参见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三十《羁縻志·土司官氏》,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74~975页、第985页。这些人其实都是当地的白族先民。这无疑与李、刘对两族名称的主流看法相互抵牾而留下了混乱。
清代志书中,更有不少继续保持着称白族先民为“僰”的传统。如康熙《楚雄府志》:“僰种为多,男子以帕为冠,妇女出辄以帕覆顶面。别有乡语。居室器用,与汉人同。性颇淳,勤稼穑,内有为商贾者。自元迄今,间有举贡生员辈出。”(15)康熙《楚雄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人种类》,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这里的“僰种”即僰人,指的是白族先民。大理定边(今南涧)县,辖民五种:“……僰人,系大理府籍,贩绵织纺,亦耕读,婚丧礼与汉人稍异,城市乡村杂处。”(16)康熙《定边县志·风俗》,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七《南涧县卷 永平县卷 云龙县卷 洱源县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页。此僰人,所指也是白族先民。
有的史籍对某地民族的记载,在涉及“僰”字时,往往出现同一段史料中一部分讲的是白族,另一部分讲的实为傣族;有的将白族史料收归到傣族内容之间,有的则将傣族史料混杂到白族之内。如道光《云南通志稿》收列当时云南有关“僰夷”即傣族先民的基本情况,其中有言:《楚雄府志》:“男子以帕为冠,妇女出辄以帕覆顶面。别有乡语,居室、器用与汉人同。性颇淳,勤稼穑,亦有为商贾者。”《楚雄县志》:“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应武童试者,十居七八。俗好讼,破家不悔,有历数世而仍理前说者。好浮屠法,喜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积重难遽反。”陆次云《峒溪纤志》:“僰人,号十二营长。罗鬼、仡佬言语不通,僰人为传译。”(17)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八三《南蛮志三之二·种人二·僰夷》,道光刻本,第11~13页。此3种实为白族史料,则被归到了傣族之中;而陆次云所言之“僰人”,实乃分布于明初隶于云南而后来成为贵州辖区的普安一带之白族先民。《峒溪纤志》此处完整的原文记载是:“僰人,号十二营长。罗鬼、仡佬言语不通,僰人为传译。披毡衫。女吹篾,有凄楚声。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朔望日不乞火。性悍好斗,卢鹿同风。又好佛,手持数珠,善诵梵咒,有祷辄应。”(18)陆次云:《峒溪纤志》上卷《僰人》,载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第83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46页。乾隆《贵州通志》也有相关记述:“僰人,在普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浴,凡倮罗、仲家、仡佬言语不相谙者,常以僰人通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19)乾隆《贵州通志》卷七《地理志·苗蛮》,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影印本,第125页。所言习俗特征中的主要内容,与大理等地白族如出一辙。
光绪时刘慰三的《滇南志略》载楚雄府僰夷:
男子以帕为冠;妇女出,辄以帕覆顶面。别有乡语,居室器用与汉人同。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应武童试者十居七八。俗好讼,破家不悔,有历数世而仍理前说者。好浮屠,喜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积重难遽反。畏暑而喜寒,近水为居,冬入水浴。另有书字。或漆其齿,或漆其身。(20)刘慰三:《滇南志略》卷二《楚雄府》,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此处前面大部分内容讲的是白族,后面“畏暑而喜寒”至“漆其身”之语,反映的则是傣族特征。
民国时期的云南志书,也不乏其混乱踪迹。如民国《禄劝县志》载:“僰人,系土著,男子以帕为冠,妇人出则以帕覆顶面。别有乡谈,性醇务农,朔望不容乞火。见《禄劝州志》。按《南诏野史》:一名百夷,又名摆夷。性耐暑热,居多在棘下。本澜沧江外夷人,有水、旱二种。水僰夷近水好沐……”(21)民国《禄劝县志》卷三《种人志》,1925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80页。此处在“僰人”即白族先民的内容下,又特别用明代《南诏野史》中有关傣族先民的记载为按语来作说明,完全混淆了两者之关系。
以上所引文献,以道光《云南通志稿》之档次、级别最高,作为清代云南省志中最为人所推崇者,尚有此等问题存在,因而他书中可见到若干类似错误,也就不足为奇。
史载中此种混乱不少,上述例子仅为一二,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大,远非一般的文字失误可以相比。后人在相关的学习、研究中对此实难分辨识别,如果都按其记载的引导去理解和使用,难免会造成学术上相当的乱象和失真。
三、如何辨识混称中的两族族名
傣族、白族先民分布广泛,云南大部地区都有涉及且多两者相互杂居,这为其族名的混称提供了条件,也给后人在史料的辨识上留下了难题,但两族间的差异其实甚大,我们可通过双方某些特征的对比,对其作出相应的分辨和识别。
(一)从地域分布看
傣族,明代主要集中于车里宣慰司,永昌、景东、镇沅、孟定、元江等府,威远、湾甸、大侯等州,南甸、干崖、陇川等宣抚司;清代基本相同而靠内地区范围有所扩大,云南、曲靖、临安、武定、广南、元江、开化、镇沅、普洱、大理、楚雄、姚安、永北、丽江、景东15府皆有之,随各属土、流兼辖,与汉民杂处;另外,金沙江中下游川滇相邻地区历代也有散居者。白族,明代的云南、临安、曲靖、开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丽江等府均有分布,而随着大量外地汉族移民的入迁,不少地区汉族、白族杂居一起,故自清中期以后,云南仅余大理府为白族主要聚居区,其他地区则深受汉文化影响而融入汉族者甚多,其政治、经济、文化已无太大差别。
大体而言,涉及滇西、滇西南南甸、干崖、普洱等地的“僰夷”、“僰人”,文献记载的多是傣族。如康熙《云南通志》载孟定、南甸的僰夷,“男长衫宽襦,无裙。陇川、猛密、孟养,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黥足……妇人挽独髻脑后,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贵者锦绣,跣足”。(22)康熙《云南通志》卷二七《土司·种人·僰彝》,康熙刻本,第38页。而靠内渐往滇中、滇东特别是大理、楚雄一带的“僰夷”、“僰人”,所指则多为白族。如清代楚雄府定远县僰人,“始为段、高二姓分居各郡,彝人即滇中土著民家也”。(23)康熙《定远县志》卷一《风俗》,载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楚雄县“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的僰夷,(24)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八三《南蛮志三之二·种人二·僰夷》,道光刻本,第11~13页。也是白族而非傣族。
(二)从体貌、服饰看
傣族,唐代以黑齿、金齿、银齿及绣脚、绣面作为当时傣族先民的部落称呼,男女服饰则为青布衣裤、五色娑罗笼。(25)樊 绰撰,向 达原校,木 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四《名类第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黑齿即染齿使黑,金齿、银齿为以金银镂片镶裹牙齿,绣脚、绣面即在脚胫、面部刺以图案花纹。及至明清,基本特征未变,漆齿纹身,服饰多样。男子多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长筒管裤;妇女着窄袖短衣、各色筒裙,头饰丰富。如孟定、南甸僰夷,“男长衫宽襦,无裙”;陇川、猛密、孟养僰夷,“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黥足……妇人挽独髻脑后,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26)康熙《云南通志》卷二七《土司·种人·僰彝》,康熙刻本,第38页。
白族崇尚白色而受汉族影响较大,其服饰有的仿照汉民,多数则根据环境、性别、年龄,配有丰富多彩的装饰。如大理僰人,男女悉蒙青布帕,覆以毡笠。(27)康熙《大理府志》卷一二《风俗》,康熙刻本,第139页。大理八九月至二三月间多风,无昼夜狂吼,妇女出门则以十二幅布为裙,裙多褶子,加大重量以御风吹。(28)徐 珂:《清稗类钞·服饰类·滇女之裙》,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03页。楚雄府属各地的僰人,男子以帕为冠裹头,妇女出入辄以帕覆顶面,其衣服、器用与汉人相同。(29)康熙《楚雄府志》卷一《地理志·人种类》,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康熙《南安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康熙《镇南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志》中,也有类似记载。
饰齿、纹身,短衣、长裤、筒裙,成为傣族先民体貌及服饰的标志性特征。白族服饰以白色为重,内容丰富,但与傣族特征并无交集。两者的外在差异,可谓各有千秋,一目了然。
(三)从居住方式看
傣族多分布于海拔低、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的临江河地区,与其环境相适应,住所多为干栏式建筑,主要以竹子、木头和茅草为材料;分上下两层, 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口和堆放杂物。元代的金齿百夷,已有“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之载;(30)李 京撰,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2页。明清基本相同,“性耐暑热,居多卑湿棘下……滇之西南旷远多湿,僰夷宅之”,顺宁府僰夷,“男女之性爱水,四季澡浴于河中”;(31)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八三《南蛮志三之二·种人二·僰夷》,道光刻本,第5~6页。临安僰夷,“好鬼,喜浴,极寒犹然,山居构草楼”。(32)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种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98页。
白族以大理为主要聚居区,该地背倚苍山,石材资源丰富,民居房屋、城池街巷,在构筑建造时往往就地以石为材,但也深受汉式建筑影响,唐代即有“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之说,(33)樊 绰撰,向 达原校,木 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八《蛮夷风俗第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元代则载白人居屋“多为回檐,如殿制”。(34)李 京撰,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7页。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后的明清时更是如此,且不仅仅局限于洱海周边。如顺宁府居于城外村寨的僰人,居处皆与客籍同;楚雄府僰夷,居室器用与汉人同;弥勒州僰人,居室姓氏同汉人。(35)参见康熙《顺宁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光绪《滇南志略》卷二《楚雄府》,乾隆《弥勒州志》卷二一《土司·种人附》。
(四)从宗教行为看
傣族崇尚佛教,而以南传佛教影响最大。不少地区,佛事活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顺宁府缅宁厅僰夷,“不事诗书,崇信释教”。(36)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八三《南蛮志三之二·种人二·僰夷》,道光刻本,第11页。各地村寨,多建有佛寺佛塔。佛寺又称缅寺,僧人称缅僧、缅和尚。如普洱府之思茅、威远、宁洱、他郎等地均有缅和尚,社会地位极高。佛寺也是傣族后代学习受教之地,学龄时的男孩普遍要进寺当小和尚学习缅文及其他知识,几年后还俗回家。(37)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八六《南蛮志三之五·种人五·缅和尚》,道光刻本,第18页。与汉族交往较多或为流官治理之地,才有部分官学、私学等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儒学存在。
白族信奉佛教、道教、本主崇拜等。佛教兴盛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信仰的佛教有密宗阿吒力教、禅宗和华严宗,而以阿吒力教为主。清代承继元明,大理地区仍有“俗尚浮屠法,家设佛堂,人手数珠,朔望经声,比户而彻”之载。(38)康熙《大理府志》卷一二《风俗》,康熙刻本,第140页。楚雄府僰夷,“好浮屠,喜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积重难遽反”。(39)刘慰三:《滇南志略》卷二《楚雄府》,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道教影响广泛,官方于府、州、县设有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等相应机构,管理当地道教事务。本主崇拜,为白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其中混合有原始巫教、多神崇拜、道教、佛教及儒家文化内容,涉及对象繁多。
(五)从姓氏特征看
傣族先民,一般民众多有名无姓,上层土司贵族则多有姓氏,常见者为思、刀(或作“刁”)、多、放、线、罕、衎、陶、那、板、闷、曩等姓。此类姓氏者,主要聚居于普洱、顺宁、景东、镇沅、腾越、元江等地。
白族先民,其姓氏分布与历代土官土司的地望及影响有关而有所不同,大理地区杨、赵、李、董、段、张姓为多,姚安、鹤庆、永北高姓为著,其他地区则与汉族相似,各种姓氏多有。
傣族、白族先民族称的混乱,可通过其特征的分析对相关记载作出判断,并可从其特征中择取较具代表性的部分内容作为各自的识别标准和检验工具,如傣族先民的“漆齿纹身,妇着桶裙,临水而居,干栏式建筑,性耐暑热,男女喜浴”,白族先民的“好浮屠、喜为僧,多为行商、熟于厂务,风俗衣食仿齐民,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之类,即可作为两者区分的重要手段。
行文至此,笔者须强调指出:一是探究两族族名混称的原因系本文重点,而为李元阳正名乃绕不开之话题。我们的研究应坚持科学态度,重视不同时代、不同文献中的不同记载,不宜无视甚至轻易否定明初即已存在“僰夷”之称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元阳作为汉文化程度极高的白族学者,在《云南通志》中对两族族名混称的扩大虽负有重大责任,但他不过是利用了自己当时在云南学术界中掌握话语权的条件,将久已存在的现象反映在自己的书中而已。在此事的衍变中,李元阳只能算是集大成者而非始作俑者,因其真正的“发明专利权”实属于别人而非属于他,他身上所背的黑锅不该再继续背下去。二是族名混称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熟习两族历史的读者想必都有感受,本文则仅是通过对部分代表性史料作出的疏理比对,将其条理化、明朗化,以便人们能够清晰了解和观察。三是混称中的两族族名今天该如何分辨及识别?笔者在5个方面的看法和建议,只是为人们提示了一个大体方向,因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它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仍需要我们在相关史料的使用中多作分析,多作思考,不盲从古人,不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这才能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尽量避开误区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