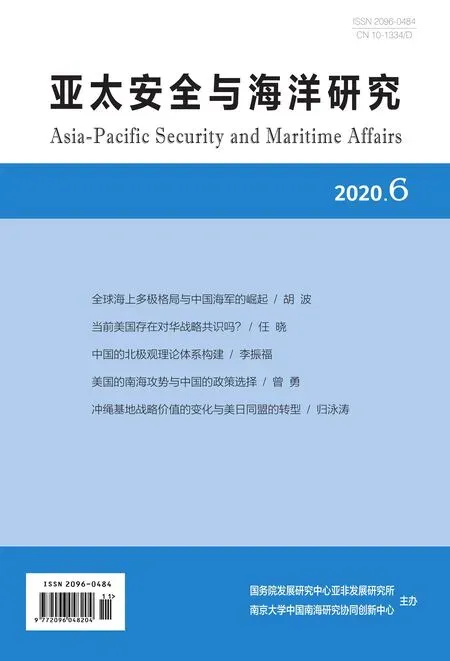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冲突及发展趋势
2020-02-20何柳
何 柳
[内容提要]“南极条约体系”在2048年前禁止任何矿产资源活动,但南极海域因其国际法属性的不明确造成了一些争议问题:是否同时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矿产资源是否享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与“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同时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活动,两套制度的法律冲突在规范层面仍未解决。但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对南极作为自然保护区地位的普遍共识,决定了在2048年后极有可能继续禁止南极采矿。
目前,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正面临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国际海底勘探活动正转向开发阶段,制定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规章不但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优先工作事项,也是国际海洋法领域现阶段最重要的国际立法之一。随着深海科技、装备水平的提升,我国进入深海领域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主体逐渐增多,已成为深海资源勘探大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与战略需求也与日俱增。
一、南极海域矿产资源及其分布
南极海域蕴藏有石油、天然气和锰结核等矿产资源。罗斯海大陆架上有一个3000—4000米的沉积盆地,罗斯海冰架下的沉积岩厚度约有4000—8000米。最新的研究表明,罗斯海盆地是南极最具有资源潜力的盆地之一,其地质资源量大约为91.5亿吨。(1)参见杜民等:《南极罗斯海盆地油气地质条件及资源潜力研究》,《极地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3页。威德尔大陆架底下是地质年代为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沉积岩,其厚度约14—15千米,比罗斯海大陆架下的沉积岩更加厚,因此威德尔大陆架有可能是南极油气储藏量更丰富的地区。(2)参见邹克渊:《南极矿物资源与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页。普里兹湾的海床上有几千米厚度的中生代晚期沉积层,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可能是东南极大陆边最有前景的石油区。其中,普里兹湾断陷盆地区的PS.3(3)普里兹湾研究区地层可以划分为五个沉积单元:包括前寒武纪的变质岩基底(PS.5),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期间和白垩纪期间的两期裂谷期沉积(PS.4及PS.3),晚始新世—中新世期间被冰川改造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PS.2)及上新世以来的冰川沉积(PS.1)。参见丁巍伟、董崇志、程子华:《南极洲东部普里兹湾区沉积特征及油气资源潜力》,《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年增刊,第103页。,大陆架外缘与陆坡深水区的PS.2上部可能是油气的潜力生成区(4)参见丁巍伟、董崇志、程子华:《南极洲东部普里兹湾区沉积特征及油气资源潜力》,《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年增刊,第103页。。别林斯高晋海存在一个大约3千米厚的沉积岩盆地,该盆地中可能有大量侏罗纪和新生代时期的沉积物。南纬60度的南极辐合带下有一个500千米宽的连续锰结核带状区,该区域是南极海域锰结核最为富集的地区,在其以北和以南地区也存在一些锰结核含量较少的区域。
目前已有的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资料数据,大多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等国家在南极大陆周边海域进行勘探性钻探所得出的结论。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马德里议定书》)签订以后,几乎没有更新的数据资料,各国对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探索仍处于“勘探”之前的阶段。(5)参见刘晓春:《南极大陆地质与矿产资源》,2018年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报告,2018年10月12日。我国于1994年批准加入了《马德里议定书》,并且严格遵守该议定书关于2048年前全面禁止南极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规定。
然而,1959年制定的《南极条约》第4条对领土主张的“冻结”,允许了领土主张国与非领土主张国等所有各方同意对领土主张的法律地位持不同意见。(6)《南极条约》第4条做出了在条约有效期内“冻结”领土争议的处理,承认并尊重《南极条约》签订前七个国家对南极大陆部分地区提出的领土主权要求,以及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不承认这些领土主张的事实,维持了条约签订之前的原状;同时又禁止了条约有效期内现有领土主张的扩大和新的领土主张的提出。第4条并没有解决南极大陆领土主权问题,而是通过“冻结”的方式,协调了领土主张国、非领土主张国和保留了领土主张权利的国家各自的利益,使主权问题可能引发的争端得到有效控制。从《南极条约》的和平目的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的宗旨、目的出发看待第4条的规定,“冻结”主权要比“禁止”主权更灵活,更能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搁置领土主权争议,实现南极国际合作的共同权利和义务。事实上,七个领土主张国以及美国、苏联这两个保留了领土主张权利的国家全都是《南极条约》12个原始缔约国的成员国。考虑到这一点,《南极条约》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了“冻结”而不是“禁止”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第4条显然顾及了上述国家的利益,不否认它们在条约缔结前的领土主张,赋予了这些条约原始缔约国作为领土主张国的特殊地位。沿海国的概念和领海基线的定义,是决定是否可以将海洋法的管辖规则适用于南极洲周围水域的关键因素。(7)Christopher C.Joyner, “The Antarctic Trea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fifty years on”,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10, p.15.这就导致了南极海域法律地位的含糊不清:七个领土主张国全部批准加入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它们依据《海洋法公约》对其“南极领土”附属的南极海域提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主权要求;(8)七个领土主张国批准加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间分别是:英国1997年7月25日、澳大利亚1994年10月5日、新西兰1996年7月19日、挪威1996年6月24日、阿根廷1995年12月1日、智利1997年8月25日、法国1996年4月11日。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及保留声明》,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2020年6月14日,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XI-6&chapter=21&Temp=mtdsg3&clang=_en [2020-10-15]。非领土主张国则一般不承认任何这些海洋主张的有效性,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没有真正的沿海国存在,“南极条约”第4条不允许在其有效期内提出任何“新”主张。
在此情况下,作为海洋的南极海域究竟适用哪一套国际法律制度?作为规范国际海洋事务的基本法,《海洋法公约》是否适用于南极海域?《海洋法公约》所创建的“国际海底区域”(以下简称“区域”)制度是否存在于南极海域?南极海域的矿产资源是否可以依照《海洋法公约》中的“区域”制度,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处理?假如南极海域是“南极条约体系”与《海洋法公约》的重叠适用区域,那么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地位又是什么?包括《马德里议定书》在内的“南极条约体系”是否规制作为陆地的南极洲与作为海洋的南极海域,即整个南极地区所有的事务,是否是与《海洋法公约》等其他国际法相背离的、可以“自成一类”的法律制度?如果南极海域只适用“南极条约体系”,那么2048年后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发展空间会存在哪些可能性?这些问题在学理上都值得明晰与探索。
随着工业金属需求的日益增长,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的国际海底区域已成为各国关注的战略新疆域。我国是世界有色金属资源的最大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也是目前拥有勘探矿区数量最多的国家。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维护我国在极地、深海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安全的规定,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出台,“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积极参与深海、极地等新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蛟龙探海”重大工程的建设,都说明了我国对极地与深海事业史无前例的重视与投入。鉴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相关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二、南极海域的国际法制度
1982年《海洋法公约》是否适用于南极海域,是一个在学理上有一定争议的问题。《海洋法公约》签订时未能考虑极地海域的法律问题,也没有对南极海域法律制度作出特殊安排。因此,有学者认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谈判者有意避开或刻意排除了南极海域(9)E.J.Sahurie,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ntarctica, New Haven Press and Dorrecht: Martinus Nijihoff, 1991, p.442; G.D.Triggs,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Some Jurisdictional Problems”, in G.D.Triggs (ed.), The Antarctic Treaty Regime: Law,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2.,《海洋法公约》文本中也刻意避免使用“南极”字眼(10)Olav Schram Stokke & Davor Vidas ed., Governing the Antarct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4.。然而,1986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南极洲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海洋法公约》是适用于所有海域的全球性公约,没有任何海域可以被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以外。因此,公约也适用于南极海域。据此,有学者认为,公约没有明示规定的条款排除适用于南极海域,(11)F.Orrego Vicuna,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New Approaches to Offshore Jurisdiction”, in C.C.Joyner and S.K.Chopra ed., The Antarctic Legal Regime, Dordrecht: Martinus Nijihoff, 1988, p.101.因而同样适用于南极海域。(12)参见阮振宇:《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33页。
《南极条约》的缔结是为了集中处理南极洲的领土争议,因此《南极条约》是一项旨在管理南极大陆本身的协定,除了第6条,条约的全文不涉及南极海域事务。《南极条约》第6条的规定(13)《南极条约》第6条规定:本条约的规定应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的地区,包括一切冰架;但本条约的规定不应损害或在任何方面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在该地区内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对公海的权利或行使这些权利。表明,条约把视为公海的南极海域交给国际海洋法(14)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是指1958年在联合国第一届海洋法会议上签订的《公海公约》《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大陆架公约》《公海渔业和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又称为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来处理,有关公海的海洋法在南极海域继续适用(15)此处“有关公海的海洋法”是指1958年的《公海公约》。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公海公约》,于1962年9月30日生效。《公海公约》规定的公海范围,是指不包括一国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但条约并没有界定南极海域公海的范围,也并没有明确海洋法的其他方面如何在“南极条约区域”内适用(16)Tim Stephens, “An icy reception or a warm embrace?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441.。但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将南极海域全部视为公海,无论是否是《南极条约》或《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任何国家都在南极海域享有科学研究自由、航行自由等公海自由的权利。《南极条约》之后的“南极条约体系”中其他法律文书,汲取了现代海洋法中的很多概念、规则、规范和原则,这一点也进一步证实了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属于现行的海洋法。(17)Christopher C.Joyner, “The Antarctic Trea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fifty years on”,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10, pp.17,15.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旨在保护南极整个海洋生态,它既是“南极条约体系”内核心的公约,同时也是一项区域渔业管理协定,宗旨是在南大洋履行《海洋法公约》及其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中促进可持续渔业活动的关键目标。(18)Tim Stephens, “An icy reception or a warm embrace?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445.又如,“南极条约体系”中主要法律文书对于南极科学研究的规定,其宗旨是为保护缔约方在南极海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这种管理责任来源于1982年《海洋法公约》明文规定的公海制度的法律义务。(19)Christopher C.Joyner,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Law of the Sea-Competing Regimes in the Southern Oce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10, No.2, 1995, p.322.
将海洋法的管辖规则适用于南极海域在规范层面的争议,主要是南极洲是否存在沿海国,以及如何划定南极洲周围水域的领海基线。七个领土主张国认为其在《南极条约》缔结之前的领土主张具有合法性,而非领土主张国则认为这些主张缺乏成为一个真正的沿海国或者甚至是一个合法领土的必要条件。(20)沿海国指的是一个特定的领土,其边界与海洋相邻,由有组织的政府统治下的人口所占领,在其外交事务中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性质。参见:Christopher C.Joyner, “The Antarctic Trea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fifty years on”,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10, p.1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沿海国”应当同时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地理要素,即陆地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邻接海洋的国家;另一个则是法律要素,即具有海岸的陆地必须属于主权国家控制的领土。参见陈力:《论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3页。《南极条约》第4条没有解决南极大陆领土主权问题,只是承认并尊重七个国家的领土主张,以及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不承认这些领土主张的事实;通过“冻结”的方式允许主权要求国、非主权要求国和保留了主权要求的国家等所有各方同意对领土主张的法律地位持不同意见。
另外,《海洋法公约》中仅有第234条涉及“冰封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冰封区域”的领海基线划定,至今也无相关的国家实践。南极洲大部分地区全年都被冰所包围,冰架的碎片经常断裂,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得任何潜在的海岸线变得不固定和不规则,因而很难确定“沿海低潮线”与领海基线。南极洲周围海域的领海基线是永久冰或冰架的边缘,还是地壳均衡变化补偿之前或之后冰或岩石界面的实际位置?(21)David W.H.Walton, “UNCLOS versus the Antarctic Treaty”, Antarctic Science, Vol.20, No.4, 2008, p.311.《海洋法公约》关于基线确定的规定无法适用于南极地区的地理状况,无法确定领海基线,就无法根据海洋法建立海洋主张区域。
“南极条约体系”与《海洋法公约》之间冲突的根源依然是《南极条约》未解决的主权问题,冲突的焦点是南极领土主张国依据《海洋法公约》建立或主张的海洋区域的合法性。七个陆地领土主张国根据《海洋法公约》提出的海洋主张,到目前为止,既不能完全合法化,也不能最终否定,关于其根据国际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分歧依然存在。(22)Patrizia Vigni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Territorial claims and coastal states”,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248.这些海洋主张的提出,并不是海洋法本身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而是领土主张国维护“南极领土主权”的举措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23)Tim Stephens, “An icy reception or a warm embrace?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449.一旦《南极条约》失效,则领土主张国将有可能恢复其已有的主张,因此海洋主张的提出是巩固其领土主张基础的一种手段。(24)David W.H.Walton, “UNCLOS versus the Antarctic Treaty”, Antarctic Science, Vol.20, No.4, 2008, p.311.
虽然“南极条约体系”与《海洋法公约》两个制度之间出现了冲突,例如,在《南极条约》有效期内领土主张被搁置的情况下,对南极海域的深海海床、大陆架等提出主张,依据《海洋法公约》是合法的,但可能损害“南极条约体系”和平、科学与环境管理的基本原则;(25)根据笔者2019年8月23日与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布莱恩·林托特(Bryan Lintott)博士的讨论整理。但南极领土主张国并没有试图在其所主张的南极海域行使沿海国管辖权。它们对南极海域提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主张的用意,是宣示及重申作为领土主张国的地位,而不是行使《海洋法公约》赋予的主权权利。(26)Marcus Haward, “Australia and the Antarctic Treaty”,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10, p.14.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它们主动选择了遵守《南极条约》第4条,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的国际义务。例如,澳大利亚于1979年宣布设立南极捕鱼区,1994年宣布设立南极专属经济区,但同时又表示,不对外国船只和人员行使其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专属权利。(27)Patrizia Vigni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Territorial claims and coastal states”,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244.澳大利亚、阿根廷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下简称“大陆架委员会”)提交了附属于其“南极领土”的大陆架划界案,但请求委员会暂不审议。
尽管关于南极海域海洋主张是否合法及有效的意见分歧持续存在,但海洋主张的存在并不妨碍“南极条约体系”的适用,领土主张国在实践中显然承认“南极条约体系”优先于适用于南极地区的其他国际规定(28)Patrizia Vigni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Territorial claims and coastal states”,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248.,它们遵守“南极条约体系”的义务而非强化《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以务实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化解了“南极条约体系”与《海洋法公约》在南极海域可能发生的冲突。
三、南极海域矿产资源制度的法律冲突
“南极条约体系”内与矿产资源制度直接相关的法律文件,有1988年的《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以下简称《矿产公约》)以及1991年的《马德里议定书》。前者从未生效,于1991年被《马德里议定书》所取代。《马德里议定书》与《海洋法公约》的“区域”制度,同时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的矿产资源活动,两者在规范层面与决策层面都存在冲突。
(一)南极矿产资源制度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初,“南极条约体系”面临体系外要求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适用于南极地区的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81年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提倡作为“无人居住”的地区,南极应像深海海床一样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交由联合国来管辖。(29)参见郭培清、石伟华:《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演变(1982年—2008年)》,《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4页。马来西亚还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批评“南极条约体系”的缺陷、南极矿产资源的公平开发等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1983年开始“南极问题”被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南极条约协商国认为,“南极条约体系”对所有国家公平开放,已经是目前管理南极事务的最好选择;强烈反对由联合国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处理南极事务,创建南极治理的新机制。然而,迫于体系外的压力,特别是为防范《海洋法公约》缔结后联合国介入南极事务的规划和管理,1982—1988年期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举行了12次会议,专门讨论矿产制度,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达成了《矿产公约》。
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矿产公约》,试图在南极海底制度设置上与《海洋法公约》达成协调。(30)参见阮振宇:《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37页。在矿产资源的法律地位方面,《矿产公约》明确规定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分配必须保证全人类的利益,同时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该公约的一些条款包含了《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支配“区域”及其资源的总原则,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31)参见《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第35条第7款(a)项、第6条、第29条第3款(b)项、第26条第3款(e)项。然而,《矿产公约》对南极矿产资源法律地位的规定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基本制度是“平行开发制度”。而《矿产公约》确立的勘探开发制度则是一种“单一开发制”,从事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主体只有担保国和经营者,没有设立类似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这样可以对“区域”资源直接开发的机构。经营者可以是公约的缔约国,或缔约国的一个机构,也可以是依缔约国法律设立的一个法人,或上述任何一方组成的有担保国的联合企业。(32)参见《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第1条第11款, 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www.ats.aq/documents/ recatt/Att311_e.pdf [2020-09-29]。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在南极从事矿产资源活动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所以这种“单一开发制”实际上只对有能力的发达国家有利。
在适用范围方面,《矿产公约》对《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规定的“区域”制度是否适用于南极地区海底的问题,保留了解释的余地。在《矿产公约》谈判中,协商国在其适用范围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一些协商国认为整个深海海底属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管辖;另一些协商国则认为“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个特别制度,南纬60度以南的海底不受国际海底管理局管辖。(33)R.Wolfrum,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 An Attempt to Break New Ground,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1, p.33.协商国为了避免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管辖权发生明显的冲突,同时为了确保协商国不同意见之间的平衡,最终找到一个折衷办法。《矿产公约》明确了其“适用范围”止于南极海域的“深海海底”,此处的“‘深海海底’是指按照国际法的大陆架的定义,大陆架地理范围以外的海床及底土”。(34)参见《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第5条第2、3款,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s://www.ats.aq/documents/ recatt/Att311_e.pdf [2020-09-29]。
198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1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法国和澳大利亚倡议缔结一项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公约,该公约应将南极确立为一个自然保护区;美国提议在“南极条约体系”各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综合的措施;新西兰建议制定全面的环境保护措施,组成一个完整、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制度;智利和瑞典等国也提出要求建立全面保护南极环境的制度。因此,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建议ATCM XV-1,(Recommendation ATCM XV-1)协商国同意将于1990年在巴黎举行一次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专题协商《矿产公约》第8条中提出的环境责任议定书的制定,“讨论有关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其附属和相关生态系统的所有建议”(35)建议ATCM XV-1,南极条约秘书处, http://www.ats.aq/devAS/ats_meetings_meeting_measure.aspx?lang=e [2020-09-29]。。
第11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SATCM XI)从1990年巴黎第一次会议到1991年10月马德里最后一次谈判,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议,最终签署了《马德里议定书》。在马德里会议上,协商国一致同意,在议定书生效之前,“目前对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限制应该继续”(36)《第11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最后决议书》,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www.ats.aq/documents/ SATCM11_4/fr/SATCM11_4_fr002_e.pdf [2020-09-29]。。议定书规定,2048年前,“科学研究除外,禁止任何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活动”(37)《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7条,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s://www.ats.aq/documents/keydocs/vol_1/vol1_4_AT_Protocol_on_EP_e.pdf [2020-09-29]。,从而暂时搁置了矿产资源开发问题。由此,“南极条约体系”开始转向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生态系统,《矿产公约》被《马德里议定书》取代,实际上未能生效。
(二)两套矿产资源制度之间的冲突
虽然《马德里议定书》没有就其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该议定书是为了补充,而不是为了修改或修正《南极条约》,(38)参见《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4条第1款,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s://www.ats.aq/documents/keydocs/vol_1/vol1_4_AT_Protocol_on_EP_e.pdf [2020-09-29]。所以,两者的适用范围是相同的,《马德里议定书》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即南纬60度以南地区,包括所有冰架。因此,无论从领土主张国、非领土主张国或第三国的角度来看,《马德里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与《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至少在南纬60度以南海底的一部分有重叠。(39)T.Scovazzi,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New Law of the Sea: Selected Questions”, in F.Francioni and T.Scovazzi eds., International Law for Antarctica,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391.因此,目前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南极海底矿产资源活动的法律制度有两套:一项制度是《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区域”,并由1994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加以补充;另一项是《马德里议定书》,特别是其第7条的规定。《海洋法公约》规制全球范围内“区域”的矿产资源活动,但《马德里议定书》在南纬60度以南地区禁止了除科学研究以外的与矿产资源有关的任何活动。然而,这两项制度都在法律上生效。那么,问题就是,在目前两套制度都适用的情况下,这两项条约对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规定是否相互冲突?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冲突?是否可能解决这些冲突?
《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都受公约第311(6)条的约束,该条规定:缔约国同意对第136条所载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基本原则不应有任何修正,并同意它们不应参加任何减损该原则的协定。《海洋法公约》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而《马德里议定书》第7条在议定书适用范围内禁止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规定,意味着“原先基于经济分配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在南极的适用失去了意义”(40)R.E.Money, “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Maintaining A Legal Regime”,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7, 1993, p.192.,《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所设想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一个基本要素,为全人类利益利用原则,在南极海底地区被有效地中止适用,公约中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开发分配“区域”内矿产资源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41)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宣告“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总原则之后,接着又对支配“区域”的具体原则作了多项规定: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国际管理原则、共同使用原因而,《马德里议定书》部分地减损了《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所载并以其第137—149条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42)则、为全人类利益利用原则、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原则;遵循国际法原则及规则原则、造成损害负有赔偿原则、保护海洋环境原则、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原则、“区域”内活动与其他活动相互适应原则。参见华敬炘:《海洋法学教程》,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5—287页。《海洋法公约》和《马德里议定书》分别在规范和禁止海底矿产活动方面令人费解的关系,直接转化为一个参与问题:只要《马德里议定书》还包括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整个海床的第7条,那么它的缔约国就不应成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43)Davor Vid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ocol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Southern Ocean Seabed, Lysaker: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1999, p.12.对于那些既是《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又是南极条约协商国和《马德里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批准加入《马德里议定书》并遵循禁止南极地区矿产活动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海洋法公约》第311(6)条?
目前为止,在实践中与《马德里议定书》禁止采矿的规定发生直接冲突的案例是,部分南极领土主张国主张其所属的非南极地区岛屿或陆地的大陆架延伸至南纬60度以南的“南极条约区域”。包括:2004年11月15日澳大利亚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凯尔盖朗深海高原地区(Kerguelen Plateau)和麦夸里海岭地区(Macquarie Ridge)外大陆架划界案;2009年4月21日阿根廷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乔治亚群岛和桑德维奇群岛越过南纬60度的外大陆架划界案;2009年5月11日英国提交的南乔治亚和南桑德维奇群岛(South Georgia and South Sandwich Islands)大陆架划界案,其延伸到南纬60度以南地区的部分与阿根廷的主张重叠。(44)参见朱瑛、薛桂芳、李金蓉:《南极地区大陆架划界案引发的法律制度碰撞》,《极地研究》2011年第4期,第320—321页。此类大陆架主张是基于明确的岛屿主权归属以及《海洋法公约》赋予的大陆架主权权利而提出的合法权利。(45)有关南极地区的大陆架主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附属于南极领土主张的大陆架主张。由南极大陆向南极海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等南极领土主张国对其“南极领土”附属的大陆架提出主张要求。此类大陆架主张直接关联到南极大陆的领土主张,因而国际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反对领土主张国对南极大陆附属海域的海床及底土提出主权要求。第二类是非南极地区、主权明确的岛屿或陆地延伸到南纬60度以南的大陆架主张。此类大陆架主张则是基于明确的岛屿主权归属以及《海洋法公约》赋予的大陆架主权权利而提出的合法权利。对澳大利亚凯尔盖朗深海高原地区和麦夸里海岭地区大陆架延伸到南纬60度以南的划界案,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审议建议是基本同意,国际社会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也说明了此类大陆架主张的合法性。然而,大陆架外部界限也是“区域”的边界,大陆架划界的同时也确定了“区域”的范围。此类大陆架划界案包括了部分“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的海床和底土,因而直接关系到南极海域海底矿产资源开发,也直接对《马德里议定书》形成了冲击。
一般国内法上判断法律效力的两项基本原则是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解决国际条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立法与司法机关,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家之间地位平等,国际法是平行主体之间的法。现代国际法不断碎片化发展,出现不同条约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像国内法那样统一明确的法律体系及立法司法机构,因而对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至今并没有普遍认可的解决规则。因此,如要将国内法上解决条约冲突的上述两种基本原则,应用于解决《海洋法公约》与《马德里议定书》关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法律地位的冲突,则会存在很大困难。
《海洋法公约》与《马德里议定书》在对“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地位这一事项的义务规范上,两者完全无法兼容。在此情况下,“后法优先原则”决定条约的适用(46)《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规定,解决条约冲突的基本原则是,两者是否针对同一事项;如果针对同一事项,两者是否订明须不违反另一条条约?如果未订明,则两者是否可以兼容?如果两者不能兼容,则按照“后法优先原则”决定条约的适用。参见:Tullio Scovazzi,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New Law of the Sea: Selected Questions”, in Francesco Francioni and Tullio Scovazzi ed., International Law for Antarctica, Amsterda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p.388-389。,然而无法判断《海洋法公约》与《马德里议定书》的“先约”与“后约”的地位(4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没有明确规定判断“先约”与“后约”的标准。参见陈力:《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页。。国际法体系中并不存在区别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明确标准,一项条约或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般法,在其他情况下又可能是特别法,而对于调整不同领域中法律关系的国际条约,要确定何者的规定更为特殊,何者为特别法,更加困难。(48)参见廖诗评:《论后法优先原则与特别法优先原则在解决条约冲突中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页。因而,使用“特别法优先原则”解决《海洋法公约》与《马德里议定书》之间的规范冲突也存在困难。
这些规范层面的法律冲突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表现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为执行《马德里议定书》而通过的国内立法对议定书和《海洋法公约》在海底矿产活动方面的关系问题有不同解释。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例如,《德国执行环境保护议定书法》(the German Act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tocol)在南纬60度以南的整个地区实施采矿禁令,从而与《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及《执行协定》的有关规定相冲突,它们同时也是《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另一些协商国则在其国内立法中豁免了南纬60度以南海床的某些部分适用《马德里议定书》禁止采矿的规定,避免与《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及其规定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权限发生冲突。例如,1994年英国《南极法》(Antarctic Act 1994)规定,在国际法规定的大陆架界限之外南纬60度以南的所有海床,不受禁止矿产资源活动的限制。(49)1994年英国《南极法》第1节、第6节,英国立法网,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4/15/contents [2020-10-10]。
《马德里议定书》与《海洋法公约》同时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的南极海域,也会带来管辖权、决策权冲突的问题。《海洋法公约》在全球范围适用,根据公约创设的机构,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讨论、决定与南极海域的海底及其资源有关的事项。同时,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以及“南极条约体系”设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也有权决定与“南极条约区域”内有关的海底及其资源事项。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谁有权决定禁止在南极海床的一部分进行海底矿产活动。由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马德里议定书》对南极海床的一部分进行采矿的禁令,是否需要国际海底管理局加以确认才能生效?或是议定书的规定本身是有效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只需要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如果对某一海底区域的豁免,只有在国际海底管理局针对每一种特定情况作出决定才生效,那么只要海管局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海洋法公约》第311(6)条不应削弱“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规定将依然适用,《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也不应成为《马德里议定书》的缔约国。(50)Davor Vid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ocol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Southern Ocean Seabed, Lysaker: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1999, p.18.因此,两种制度在决策层面的冲突,又会回到前述规范层面的法律冲突带来的参与问题。这也意味着,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南极事务的某些领域为了获得法律效力,必须得到另一个国际组织的确认。南极条约协商国的“集体管辖权”将会受到挑战,协商会议与海管局之间管辖权、决策权的划分和协调也将是一个问题。
四、南极海域矿产资源制度的发展趋势
2048年《马德里议定书》到期后,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继续禁止采矿。这样预测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正如达沃·维达(Davor Vidas)所指出的,环境因素是解决《马德里议定书》与《海洋法公约》之间法律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出路。(51)Davor Vid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ocol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Southern Ocean Seabed, Lysaker: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1999, p.23.60年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南极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地位,环境保护是“南极条约体系”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从1959年《南极条约》禁止核试验和核废料处理,到1991年《马德里议定书》承诺“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其附属和相关生态系统”,并指定“南极洲为自然保护区,致力于和平与科学”(52)Tim Stephens, “An icy reception or a warm embrace?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Klaus Dodds, Alan D.Hemmings, Peder Roberts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Antarctica, Cheltenham: Edward Legar Publishing Limited, UK, 2017, p.447.。保护南纬60度以南陆地与海洋的荒原价值和原始生态系统,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南极条约体系”在其形成的最早期就将环境保护纳入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决策过程中,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以南极环境和生态保护而不是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价值导向和优先考虑。1959年《南极条约》在解决了领土主权争端和潜在军事化这两个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的当务之急后,缔约国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1964年第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以下简称《议定措施》)。(53)1982年,《议定措施》正式生效。2011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宣布,鉴于《议定措施》的规定已被《马德里议定书》的条款所取代,《议定措施》将“不再适用”。参见《第34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34/fr/ATCM34_fr002_e.pdf [2020-10-10]。它规定,各方把条约区域视为一个特殊的保护区,对有突出科学价值的地区,为保护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应当指定其为“专门保护区”。(54)参见《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序言、第8条,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s://www.ats.aq/documents/recatt/att080_e.pdf [2020-10-10]。《议定措施》与第一届、第二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分别采纳的《保护生物资源的建议》《保植物议定措施的建议》共同构成了“南极条约体系”下第一套全面的环境保护法。
“南极条约体系”随后制定的主要国际公约,包括未生效的《矿产公约》,都集中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养护方面。《矿产公约》谈判启动的时候,南极并没有任何采矿活动或近期可以采矿的前景。(55)Anthony (Tony) James Press, “Conservation Law in Antarctica and the Southern Ocean: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uifang (Julia) XUE, Liu HE (Eds.), Law and Governance: Emerging Issues of the Polar Regions,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8, p.10.启动《矿产公约》谈判的推动力,是在允许开采之前建立严格的、预防性的环境保护制度。在矿产开发问题的讨论和《矿产公约》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协商国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以及采矿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反复地表达了这一关切。《矿产公约》规定,除非对矿产资源活动对南极环境及其附属和相关的生态系统造成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估,并确保所涉及活动不会导致大气、陆地或海洋环境、动植物种群的分布、空气和水质等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不应开展任何南极矿产资源活动。(56)参见《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第4条第2款,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www.ats.aq/documents/recatt/Att311_e.pdf [2020-10-10]。
鉴于《矿产公约》未达成共识,南极条约协商国迅速启动了《马德里议定书》的谈判,这也清楚地表明,协商国决心建立一个全面的南极环境管理制度,承诺将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将南极指定为仅用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57)参见《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2条,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s://www.ats.aq/documents/keydocs/vol_1/vol1_4_AT_Protocol_on_EP_e.pdf [2020-10-10]。
“南极条约体系”现有的主要法律文件,已构成了一个全面广泛的南极地区环境管理的条约框架。60年来,条约体系在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维护和平,增进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实践中,显示出了高度的成熟及有效性。在此情况下,2048年后,条约体系依然以环境保护为优先考虑事项,全面禁止矿产开采的可能性更大,新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很小。需要注意的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在规范层面“南极条约体系”是与《海洋法公约》相背离的、可以“自成一类”的特殊的法律制度,而是在实践中国际社会普遍倾向于对南极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给予特殊保护。
第二,南极海域采矿在极端的海洋与地球物理条件下是不切实际,也是不经济的。南极的海洋和地球物理的现实情况,使得《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深海海底采矿制度不太可能实际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的水域。南极海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冰雪覆盖,即使是在南半球整个春季和夏季的几个月,南极海域都是地球上风力最大、最冷、最严酷的海域之一。实际存在于南极海域海底的多金属结核或锰结核的岩石结核探明储量尚不明确,但相比太平洋与印度洋,南极海域深海海底结核矿床的数量相对较少。在南极海域下的海床上采矿作业,其成本将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对海上作业人员来说也极其危险。(58)Christopher C.Joyner, “The Antarctic Trea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fifty years on”,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10, p.19.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赴南极海域采矿的动力不大。
五、结 语
南极海域适用的法律制度,是由《海洋法公约》连同“南极条约体系”中规范与海洋议题相关的法律文件共同组成。作为陆地的南极洲则适用“南极条约体系”,南极国际法律制度存在陆海二元的国际法来源。(59)根据笔者2018年10月11日“2018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期间对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的访谈整理。《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区域”与其《执行协定》以及“南极条约体系”中的《马德里议定书》重叠,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活动。两套法律制度在规范层面、决策层面都存在冲突,目前为止仍未得到解决。
“南极条约体系”自创立以来的价值导向,始终是保护南极地区独特的环境与生态,而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南极作为致力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地位。此外,南极海域极端的海洋、地球物理条件,也使得南极海域采矿不但成本极高,而且不太现实。这些因素决定了《马德里议定书》与《海洋法公约》在南纬60度以南的海底矿产资源法律地位问题上的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停留在规范层面,也决定了2048年以后南极海域禁止采矿的规定极有可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