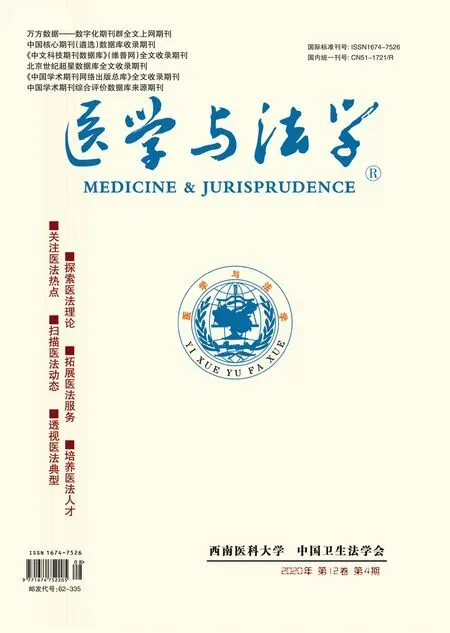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2020-02-20佘艺颖肖淞元
佘艺颖 肖淞元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人社局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20)第010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①,认定李文亮的死亡属于工伤。对于该工伤认定的结论,应无争议;而对于类似职业中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依据,是存有争议的——其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的认定采用了列举式模式,《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采用封闭立法技术限定了工伤认定的范围,导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时法律适用陷入困境。由于立法技术上的欠缺,行政部门和司法实务部门对此类型案例呈现出不同的理解,也导致实务中对该类型案例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检视涉及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探讨传染病工伤认定更好的法律适用路径并提出相关的立法回应措施。
一、传染病工伤案例的法律适用模式
从实务案例来看,传染病工伤认定存在多种不同法律适用模式。笔者以“传染病”“工伤”“行政案件”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集了相关案例,发现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模式大体分为四类,即分别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第(四)项“患职业病”、第(五)项“因外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第(七)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兜底条款作为适用依据。
从传染病工伤认定角度来看,“患职业病”系明确直接的依据,而其余三种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则显得含糊。具体而言,《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将职业传染病严格限制为炭疽等五种,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多种不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范围内但因职业中接触致感染传染病的案例,主要发生在涉及职业暴露、境外劳务受感染等情形中。此类案例不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范围内,无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患职业病”,但具有“职业性”“疾病”“接触传染病的病原生物”的要素特点。基于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实务中出现了其余三种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但由于同类型案例的法律适用依据不统一,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存有理解差异导致争议不断。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
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认定工伤。如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于某案②,于某因工作中接触老鼠撕咬物和排泄物而患肾综合征出血热,工伤认定行政部门认为传染病非事故伤害应属于疾病,不符合《职业病目录》[卫法监发(2002)108号]和《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工伤事故”;二审法院则认为,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都应认定为工伤,不支持“患传染病虽是一种伤害但非工伤事故”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司法部门对该案的法律适用系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精神的理解,认为“工伤事故”应该是指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通过对“事故”概念外延的扩张,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工业事故的理解。
(二)“患职业病”的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患职业病”可以认定为工伤。我国采用法定职业病病种的立法模式,而目前《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仅规定了炭疽、森林脑炎、布鲁氏菌病、艾滋病(限于医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莱姆病五种法定职业传染病。除此以外,即使存在与“工作相关”的核心要素,或者职务行为密切关联而感染其他种类传染病都不能适用该依据。在认定程序上,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诊断权,并对其作出职业病诊断结论负责”,即法定职业传染病工伤认定必须由享有职业病诊断和鉴定资质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书或者职业病鉴定书作为适用“患职业病”的依据。如在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延中行终字第10号案中,劳动者未提供职业病诊断书或者职业病鉴定书,仅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并不被认定为法定职业传染病。司法机关在支持了行政机关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判决中,还指出“森林脑炎属于法定的职业性传染病,即一种职业疾病,而不是直接的事故伤害”③。在缺乏提供职业病诊断书或者职业病鉴定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认为森林脑炎也不能以第十四条第(一)项“事故伤害”加以适用。可见职业传染病的认定在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上均有严格的限制。
(三)“因外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
近年来,境外工作期间感染传染病的案例增多。针对此类案例,工伤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对于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的规定存在一定争议。工伤行政部门一般认为传染病属于疾病非工伤事故,且往往新型传染病非《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明的法定职业传染病,不予认可工伤;而司法机关则往往绕开适用职业病工伤认定的路径,援引其他有关规定,采用特定的工作环境而感染疾病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理由。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5)芙行初字第332号判决④,援引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的规定,撤销了长沙市人社局不予认可工伤的行政决定;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则直接规定“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视同为工伤”。再如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所作出的(2018)粤71行终3199号判决⑤,将员工在境外感染传染病与当地特定的劳动环境必然联系作为重要的工作相关性而认定工伤。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的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模式
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湘11行终204号判决⑥,认定杨某属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防治人员,其在工作期间患结核病,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规定,予以认定工伤;其理由,是工作期间感染结核病的情形虽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患职业病”类型,但是基于国办发〔2017〕16号《“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和湘卫发〔2018〕1号《湖南省“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认定以肺结核为主的结核病属于重大传染性疾病,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故应当认定为工伤。同样,湖南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湘0511行初32号判决⑦,则更是遵循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立法精神的典型案例。
二、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困境及其成因
(一)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困境
纵观四种传染病的工伤认定模式,除“患职业病”之外,其他的三种模式都不符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之规定,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伤事故,大多只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精神、理念或者《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其他条款。现有的困境即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主观适用随意性,而这与符合工伤认定所应遵循的法定精神相悖。究其原因,主要是立法中的“工伤”法定概念缺位、《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封闭性和工伤立法的一般性条款的欠缺等问题,导致实务中出现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乃至其内部的理解偏差,以致涉工伤的行政诉讼逐年上升。
(二)传染病工伤认定之法律适用困境的成因
1.“工伤”法定概念的缺位。
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发挥着首要功能,很多时候需要由解释者对法律概念的语义进行界定或具体化。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思维和推理的根本环节。[1]
在现有的立法体系中,并未对“工伤”作出法律概念的界定。《工伤保险条例》采用全列举的立法模式,缺乏一般性条款。而这种抽象化的法律概念在立法技术中的缺失,无法给予工伤认定一般性的具体适用工具。通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归类模式,学界和司法界只能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推定“工伤”的概念的核心在于“伤害”“与工作相关”以及涉及伤害是否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即“工作过程”等问题。[2]《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工伤类型分为法定工伤、视同工伤两种类型。从所列内容上看,其既涵盖事故,也包括伤害职业病、意外等多种类型,但这仅为工伤的表现形式,是否属于工伤并没有法定的抽象概念作为判断依据,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2.“工伤”“职业病”和“职业传染病”概念之间的关系模糊。
目前《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界定⑧,强调了“职业性”“有害因素”和“疾病”三个核心概念。其中“疾病”概念是作为区分与其他类型工伤的重要概念,“其他工伤事故”是指经由外部作用有害于人身的突发性事件。职业传染病作为职业病类型,在其法律意义的界定上属于职业病的范畴。而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可以认定为工伤。因此只能从学理上推定三者概念的逻辑关系应为“工伤>职业病>职业传染病”。但是因为“工伤”没有明确的概念,导致目录外的传染病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一方面欠缺抽象“工伤”概念的指引,另一方面又受《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限制导致无法归纳为职业性传染病。
3.工伤认定一般条款的缺失。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采用全面列举方式,一旦遇到列举时未能预测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裁判将陷入困境[3]。虽然我国现有的《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了兜底条款,但是缺乏其他法律法规的指引。从前述案件中,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案例无法采用兜底条款作为认定工伤的路径,一些案例在工伤认定过程中适用的是立法原则与精神,立法的现状无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案例。许多学者提出构建工伤认定一般条款,“工伤认定一般条款”是指规定“工伤”的法律概念或者对工伤进行抽象的、概括的规定的一种具有普适性、开放性的法律规范。[4]这种立法技术旨在解决概念的开放性,工伤认定行政部门或者司法部门可以通过基础性的条款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以补充法律适用的客体范围,弥补法律漏洞。
4.职业性传染病目录具有封闭性。
尽管《职业病防治法》对于“职业病”概念作了界定,但是在职业病的认定时,目前所采取的法定职业病限定模式,即职业病必须为《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规定的法定职业病种类才会被认定为工伤。
“职业性传染病”属于职业病类型之一,需要符合职业病“职业性”“有害因素”和“疾病”的三个构成要件。2017年国家卫计委《职业性传染病的诊断》对职业性传染病作出了界定,“职业性传染病”(oc⁃cupational infectious disease)是指作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接触传染病的病原生物(病原体)所引起的疾病。[5]该定义满足了“职业性”“疾病”的概念,将有害因素限定为“接触传染病的病原生物”。此外,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又采用严格封闭的职业病目录模式,限定职业传染病为五种。适用的冲突就在于符合了职业性传染病的抽象范畴,但被《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排除在外,以至于抽象概念的范畴几乎没有适用的意义。
三、传染病工伤认定法律适用困境的解决途径
若按照文本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则新冠疫情期间的医护人员认定为工伤都存在障碍,这似乎不符合立法精神,亦有违常理。其根源在于现有的工伤认定法律规定存在漏洞,故应从立法层面予以根本解决。
(一)立法明确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
在传染病工伤认定案件中,工伤认定行政部门都提出传染病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其中的理由是对于“工伤事故”的理解分歧,认为“事故”最基本的特征是突发性、有害性及外部性[6]。因为对“事故”更倾向于工业事故的理解,工伤认定行政部门认为传染病的感染不应属于事故类型。但是有些法院对“事故”作出了更宽泛的理解,认为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都应该属于工伤,显然其对事故的理解要比工伤认定行政部门对事故的理解更为宽泛。因此,要把握工伤认定,就须对工伤的核心要义给予准确的界定。关于工伤的理解主要的观点有“急性伤害说”“事故伤害说”“伤害与职业病说”和“法律事件说”等多种学说。有学者提出“工伤”概念的核心在于“与工作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工伤认定中因果关系呈现弱化的趋势,对“事故”的要求越来越宽松。工作无须是伤害发生的起因,只要工作促进或加剧了伤害的发生,工伤就可以成立[7]。与此相同的观点还有工伤针对的是职业灾害,职业与灾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工伤定义的核心。[8]从司法实践上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法律适用方式在医护传染病案例较为普遍。因为医护人员由于职业暴露的风险高,其患职业传染病与工作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显。如四川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川1181行初172号判决⑨,法院认定王某工作岗位在皮肤科,在感染风疹病毒的原因确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应认定其所受伤害其属于工伤。该案工伤认定行政部门的思路亦是事故不应作出超出文义范围的理解而否定了工伤,而司法部门则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以感染患病与工作具有较大的关联作为审查的重点,以《工伤保险条例》基本精神和立法目的的法律适用路径认可工伤。
因此,从理论和实务角度看,工伤认定的核心并非“事故”“伤害”“疾病”,而应该是“因果关系”,即伤害或者疾病是否与工作相关。不应拘泥于起因是否为“事故”这个概念。因此对于职业传染病工伤认定除了传统的职业病认定路径,亦可以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三公要素,以工作“因果关系”作为核心规则进行工伤认定,更为周延并具有解释力。
(二)工伤认定一般条款与列举条款相结合
在涉及传染病的工伤认定适用路径中,很多案例为了追求个案的正义,多适用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于个案。但是立法精神对于个案的适用的抽象性易导致对于工伤认定的模糊性。因此,与其采用立法精神的法律适用方式,不如构建工伤一般条款。目前,部分地方立法针对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视同为工伤⑩。该条款并未限制疫区的传染病应当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的疾病,突破了以往对职业传染病的限制。基于工伤立法精神的地方条例,在实际中的操作性更强。实践中,也采用“因工外出期间受到伤害”的规定来适用在境外感染传染病而认定工伤的途径。但这两种途径都有个前提即必须是在疫区或者是因工外出才能加以适用具有局限性。如果立法能进一步规定抽象性的一般条款,对于工伤认定采用更为明确的概念性和一般性的规定,除派驻疫区或者外出工作的情形,如果符合工伤的一般条款同样适用工伤认定,则更能实现同类型案件的个案公平。
(三)设计《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兜底条款
我国的职业病是施行分类和目录管理的,根据《职业病防治法》之规定,只有列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炭疽等五种职业传染病,才能够被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病。新冠肺炎等类似传染病不在目录中,成为工伤认定法律适用的难点所在。基于此,在新冠疫情期间人社部等部门只能以临时发函的形式明确医护人员的工伤认定。从该通知内容上看,并未明确该结论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具体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 227—2017《职业性传染病的诊断》规定“职业传染病”指职业活动中接触传染病的病原生物(病原体)所引起的疾病。从这个意义看,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符合职业传染病的职业性、传染病原及疾病几个核心构成要素,因此适用“患职业病”的工伤认定依据显得更为明确。
现有的法定职业病是将与工作有关的疾病都包纳进来,其纳入的原因是基于职业病的病种与职业本身有紧密的因果关系。而传染病不一定都与职业有关,因此很多传染病并没有被列入,但并不能排除由于工作原因而导致感染非目录范围内的其他传染病。如果将此类与工作因果关系明显的传染病排除出职业病范围,则与工伤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可以考虑将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设计开放性的兜底性条款,将类似新冠肺炎等烈性传染病列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其是否属于工伤可以通过工伤的核心要素加以判定。由于接触病原生物(病原体)有可能与工作具有关联,也可能会存在有非职业原因的感染情形,所以在因果关系上就需要比传统事故类型工伤更为强有力的工作关联性证据加以证明。比如遵循职业性传染病的诊断依据确切的病原生物(病原体)职业接触史,具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及特异性实验室检查阳性结果,结合职业卫生学、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综合分析,排除其他原因所致该疾病的可能性,方可诊断为职业传染病。[9]这其中“工作因素”则是与疾病的重要因果关系,是认定职业性传染病工伤的核心要素。
(四)明确疫情期间工伤认定适用模式
2020年1月24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人社部函[2020]11号对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工伤作出了规定,但该《通知》未说明其制定的法律依据。武汉市[2020]第010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则明确表示依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此思路是对“事故”作出了扩大解释。相比之下,如果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作为《通知》依据理解更具逻辑性。疫情暴发的紧急时期,工伤认定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的条款。该规定中“伤害”的解释可以既包括工伤事故也可以包括疾病。从新冠疫情来看,医护人员与相关人员的职务行为也可视为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此适用模式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也绕开了列举方式的法定工伤适用模式。而本条规定还涵盖了“其他人员”,更偏重于从其行为目的来考虑是否纳入工伤。因此不仅仅是医护人员与相关人员,包括其他志愿者因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所受伤害亦可纳入工伤,符合法理与常理的解释。针对非医护人员,浙江高院、湖南高院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意见。由此可见,在针对非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认定上,则更靠近法定工伤的认定类型。基于以上意见属地方性规定的局限性,建议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统一司法适用。
从上述4种解决途径看,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但是通过立法明确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以及结合工伤认定一般条款与列举条款的路径,需要通过修改《社会保险法》或《工伤保险条例》,甚至单独制定《工伤保险法》来实现。这些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较长的立法或者修订过程。基于新冠疫情的特殊性,通过增加《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兜底条款的设计更为便捷。同时对于疫情期间工伤认定适用亦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减少因对法律规定理解的偏差导致行政诉讼。
注释
①武人社工险决字(2020)第0100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文亮作为医护人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并经抢救无效去世,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为工伤。
②引自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4)烟行终字第126号“于永逊与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案”的判决书。
③引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5)延中行终字第10号“朱企征与和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行政判决书。
④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5)芙行初字第332号“原告张某某不服被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案”判决,该案中原告张某某被用人单位安排至非洲利比里亚出差期间,感染疟疾。长沙市人社局认为不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职业病的范畴,应不予视同工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则援引了劳社部发电(2003)2号《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传染非典型肺炎,可视同工伤。同时依据疟疾同属于乙类传染病,根据我国行政法合理行政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或行政裁决不应区别对待而撤销了长沙市人社局不予认可的行政决定。
⑤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所作出(2018)粤71行终3199号“广州海明船舶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二审行政判决书”,李某在接受用人单位派遣前往莫桑比克工作期间感染马来热病毒死亡,其死亡与当地特定的劳动环境具有必然的联系,应视为因工作原因造成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⑥引自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湘11行终204号“上诉人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被上诉人杨某诉该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二审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为杨某在工作期间,作为医院感染科专门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医护人员,其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具有特殊性,应当区别于一般工作性质、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其在工作期间患结核病,根据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规定,予以认定工伤。
⑦湖南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湘0511行初32号判决“肖彪不服被告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邵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该案中劳动者在预防中心检验科从事结核病人肝肾功能检验工作。因患继发性肺结核而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推定劳动者所患肺结核与工作原因具有关联性,法院依据《“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立法精神撤销了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⑨引自四川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川1181行初172号“王小刚、李正英等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局”判决,王某工作岗位在皮肤科,感染风疹病毒的原因确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其受用人单位指派在泸州市中医医院参加规范化培训时发病,工伤认定行政部门认为发病不属于工伤事故,“事故伤害”的理解不能超出其文义范围进行无限扩大解释。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工伤认定要件,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应认定其所受伤害其属于工伤。
⑩《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属于工伤。
[11][12]《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11号规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