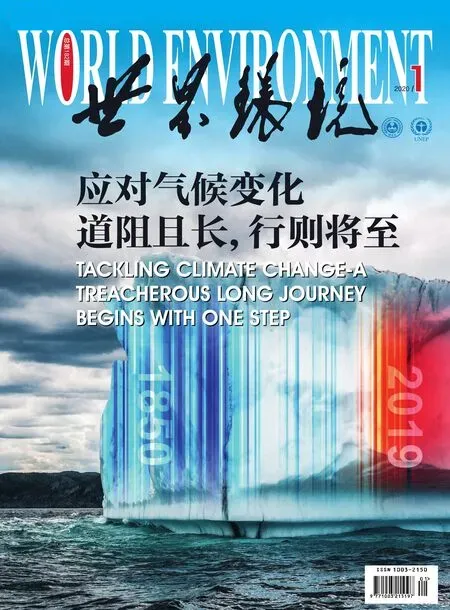目的主义对文本主义的优位性:中国前气候变化立法时代的法律解释路径
2020-02-19唐克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唐克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文本主义(textualism)与目的主义(purposivism)是两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前者从法律文本出发进行分析,寻求词汇意义的最大边界;后者从法律精神出发,分析争议对象的立法目的。从解释结果来看,两种路径通常矛盾胜于统一,最明显的对比就是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局(EPA)案和雪佛龙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这两则判例都出自大法官史蒂芬斯之手,都涉及EPA对 《清洁空气法》(CAA)文本的解读,但最终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文本主义解读:雪佛龙案
大法官史蒂芬斯在雪佛龙案中创设了著名的“雪佛龙尊重”(Chevron Deference),要求法院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就其国会所授予之权力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必须符合两个要件:其一,文本中国会之意图不明确;其二,对文本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在这种思路下,EPA扩大对“固定排放源”的解释,使任何排放源都能享受“气泡理论”政策弹性,实际上是突破了语言学上“固定(stationary)”一词的最大文义范围。但最高法院仍然认为EPA的这种解释是合理的,这至少从侧面说明了,史蒂芬斯大法官认为文本主义的解读无需受到语言学方面的限制。
二、目的主义解读:EPA案
在EPA案中,马萨诸塞州人民认为EPA拒绝规制机动车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导致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进而使自己的陆地面积减少。与雪佛龙案相似,本案也涉及对立法用语的解读,即“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是否属于“空气污染物(air pollutant)”。如果单从生活经验来看,前者确实没有超出后者的最大文义范围,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报告也证明了温室气体的污染物性质,但以史蒂芬斯大法官为代表的主要意见却认为这种解读并不合理,不符合“雪佛龙尊重”的适用条件,原因是如果采取这种保守主义的文本解读路径,《清洁空气法》保障公众健康与环境福祉的目的就无法实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语词的文义范围并非文本主义解释路径的真正边界。
三、反思与启示
通过对比雪佛龙案和EPA案可知,当行政机关对立法文本的解释与国会意图相一致时,适用文本主义的解释路径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因此,文本解释的界限从来都不是语言学上的“最大文义范围”,而是立法目的符合性。从这一点来看,目的主义对文本主义的优位性就十分明显了,这对传统法解释学中文义解释优先于目的解释的观点造成了很大冲击,这种变化对当前中国环境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一方面,从目前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看,短时间内还不存在制定国内强制性气候变化应对法的需求;另一方面,国际上不断兴起的气候变化诉讼势必会对中国环境司法起到引导作用,在欠缺专门性立法的情况下,必然涉及裁判者如何解释既有立法这个问题。从雪佛龙案和EPA案的经验来看,在前气候变化立法时代,法官不应拘泥于语言的含义边界,而是需要揣摩文本背后的立法精神,尤其是对于争议较大、现有立法不能有效澄清的事项,例如诉讼主体资格、因果关系等,即使采取扩大解释后的结论为传统“最大文义范围”理论所不容,上级法院也不宜径行发回重审或改判,以避免剥夺国内气候变化诉讼的根植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