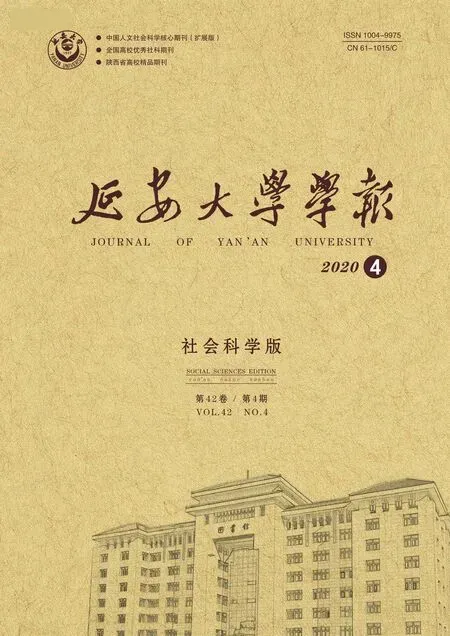马克思异化思想对精准扶贫的启示
2020-02-19杨家宸贺彩艳
杨家宸,贺彩艳
(1.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在人类社会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贫穷和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课题。[1]消灭贫困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更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总结,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驰而不息地加以推进,每到基层调研都要重点考察特困区,期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在陕西、贵州、宁夏、山西、四川等地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多次指示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在具体扶贫工作中要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在广东省连樟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重要论调,将每一户贫困家庭,每一个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纳入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一伟大课题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殷勤嘱咐,充分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人民解决贫困问题、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人民情怀和历史担当,是我们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南、根本遵循和精神动力。
一、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考
“异化”这个概念先于马克思已在许多学科领域频频出现,所以它并不是马克思所独创。从字面意思理解并不困难,其涵义是指“疏远、脱离、转让”。被引入哲学范畴之后,它是指主体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产生了客体,而被创造的客体在运动的过程中却和主体渐行渐远,发展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东西,最后脱离主体甚至反噬主体,并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的异己力量。马克思通过指谪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承接和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基础上深入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提出了异化劳动观,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异化劳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四个重要逻辑表现。
马克思认为自发的分工是产生劳动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历史根源,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由自主,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驱使着这种力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论断,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分裂,那么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就必然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为后来我们克服异化劳动提供了解决思路,即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强制分工的消灭。“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下,此时人们在物质上的需求都能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转化为按劳分配,强制性、奴役性的社会也将不再存在。”[2]通过对异化劳动细致的体征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理解异化劳动。如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工人与商品、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一样,工人生产的物质财富越多,即他所创造的产品力量个数越大,他就会变的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成分越多,工人本身就越堕落成廉价的商品而非自由人,物的世界的急剧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迅速贬值始终成正向比。[3]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规定的社会生产中,劳动产品成为了占有劳动者自身的外在附属,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丧失自己的同时,也是造成自己同劳动产品相异化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者创造的产品不再属于本身自由的支配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种归属关系的转化使得他在自己的辛勤劳动中逐渐不肯定自己,而是越发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蹂躏、精神受苛虐。这就造成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背离、相异化;再者从人的类本质方面看,异化劳动扼杀了人可以自由自觉的生产这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权利,把人的劳动行为变成仅仅像动物一样维持自己生命的活动;最后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具体表现有:工人阶级由于被压迫奴役同资产阶级相对立,工人阶级内部为了谋求生存而互相竞争产生对立,资本家为了牟取利益最大化相互打压排挤形成对立。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革,异化本身也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在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基于分工角色的扮演不同,产生了实际利益的分配与输送,实际工作中难以摆脱异化现象带来的负面作用。在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将扶贫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当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异端来批判,反而更加需要注重其在扶贫过程中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消除异化的充分条件,而且相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我们当前还处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公有制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纯粹的公有制,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仅由公有制组成,同时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以及一批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依旧在我国资源配置整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够充分,社会主义可能一定程度上扩大分工,由此加剧了异化现象的产生并且可能会影响到精准扶贫的如期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如何做到正确认识异化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遵循马克思对异化本质的揭露,同时要结合新时代我国的具体实际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异化现象
(一)扶贫主体在扶贫过程中的异化表现
扶贫主体相对于客体在扶贫工作过程中具有导向作用和决定作用。俗话说的好,“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在脱贫攻坚战中,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作为扶贫工作的主力军,是否能够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否能够将自己看作是人民忠实的仆人,走群众路线;是否能够在具体扶贫工作中持续用力,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判别一个党员优秀与否的一把标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脱贫攻坚战的成败与否。然而,在具体落实责任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权利与义务的异化现象。有不少党员干部抱着敷衍规避的应付心态,把惠民利民的手头工作当作搪塞上级的疾苦差事,工作状态得过且过,形式往往大于实干,无论是走访问计还是下乡考需,都是浮光掠影般的偶一为之,对于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残致贫、因灾致贫等不同类型的贫困群体缺乏亲力亲为、细致而精准的识别,制定措施,更是欠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许多扶贫干部到贫困户家中慰问仅仅是抱着日常签到、拍照留念、走走过场的工作态度,把贫困大众急待解决的民生问题认为是搞彩排、搞活动。形成这一荒唐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党委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淡薄,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要求,使短期扶贫成效最大化,在材料和数字上造假欺上瞒下,如此扶贫的怪象让老百姓瞠目结舌,懒政和缺乏担当的现象背后,实质上是形式主义和权力异化的表现,更是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的严重破坏。另一种现象也较为普遍,有些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自身职能的缺失也是造成扶贫异化的重要因素,政绩评价不是以实际效果、人民的满意度为准,而是盲目追求考核数据上报的任务,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浮躁和少数官员盲目作为的现象。相关负责人为了尽快完成所属辖区的脱贫任务,往往遴选某方面有特殊优势、有潜力的“贫困村”进行形式帮扶,大搞政治擦边球,结果导致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未能如期脱贫,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越扶越贫的现象,不仅严重偏离了党和国家关于精准扶贫的初衷,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背道而驰。
(二)扶贫客体在脱贫过程中的异化表现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劳动作为人维持自身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本质上体现了人自由自觉的意志特性、确定人之为人的根本力量、有意识能动性的生命活动。在每个人都应平等参与劳动过程的生产实践中,人人都应当相似地、竭尽全力地获取生产资料、享用资料、发掘和探索一切满足自身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积极自由的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4]单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出发分析,通过政策瞄准和实际措施帮助贫困家庭创造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责无旁贷,然而由于运动主体有时发力过猛,也滋生了个别主观脱贫意识差,没有危机感的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等”“靠”“要”的懈怠情绪。许多贫困家庭利用政府相关政策缺漏,把政府给予为了实现贫困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资料迅速转让变现,突击花销殆尽,坐等下一轮贫困资格认定,又重新带上贫困帽继续享受政策补助和优惠。更有甚者直接拒绝脱贫,因为当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国家规定脱贫标准时,就会失去获得财政补贴和政策帮扶的待遇。据相关媒体报道,在贵州某地区,一户贫困家庭有两个年轻单身汉,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连自己的茶园都荒着,基本不搞生产,得一天过一天,坐等当五保户。像这样持续返贫拒绝脱贫的“钉子户”在贫困地区可以说是层见迭出,折射出一些贫困人口在思想深处脱贫意识淡薄,没有正确认识到摆脱贫困与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也给我们实现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造成了不小阻力。
(三)扶贫结果在扶贫终端的异化表现
精准扶贫的初衷、过程、结果是党和国家为适应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转化,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而通过以上对主客体的异化现象阐述,就不难得出结果异化这一问题的极大可能,这也与马克思关于原因和结果相互联系、依存的辩证关系不谋而合。由于考核机制的怠忽和相关责任领导注重绩效而非实际,决定了扶贫结果在实际成效中的异化。从考核填表程序复杂到年终成绩汇总一系列过于注重形式而非成果的制度让精准扶贫异化为“精准填表”。这些扶贫行为将填写表格作为“答卷”汇报,而忽略了贫困主体这一主角,“阅卷人”不欢迎,也不需要。结果导致贫困家庭在这一系列不健康的内外因合力下必将更加贫穷,既违背了初衷、脱离了过程,也异化了结果。另外,这些基于逃避劳动而游离出来的年轻闲置劳动力会成为影响贫困村脱贫乃至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缺少良好的教育基础和正确的后天引导容易滋生破罐子破摔、一穷到底的极端错误倾向,如此恶性循环亦导致扶贫工作的事倍功半。
三、如何走出扶贫工作异化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精准扶贫中异化现象的负面作用凸显且不容忽视。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对于我们如期完成“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运用和把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内涵,密切联系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解决扶贫异化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一)夯实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政之要,莫先于人;成事之要,关键在人。党员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更是党凝心聚魄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个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每一位奋斗在脱贫一线的党员在具体扶贫进程中能否发挥关键作用兹事体大。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到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不断提升责任主体在扶贫过程中的办事效率,特别是基层党员推进扶贫任务一以贯之、深入基层调研一以贯之、夯实理想信念一以贯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键少数”深入扶贫攻坚是鼓励,体现了“真扶贫”的决心,以上率下就能把干劲鼓起来,凝聚各级干部和群众力量,向扶贫发起全面进攻;“关键少数”深入扶贫攻坚是调研,为“扶真贫”提供一手可靠资料,要想杜绝扶贫底数不清,对象搞不准的情况,“关键少数”就得带头进村进户出谋划策,让惠民举措有的放矢;“关键少数”深入扶贫攻坚是实干,为“扶贫真”保驾护航,力量联动才能资源盘活,为贫困地区贫困户出点子督促落实。[5]
(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劳动光荣的思想
有意识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特征,劳动不仅塑造人,而且可以提升劳动过程中的精神愉悦和自我认可度,辛勤耕耘创造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可以丰饶人的精神世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劳动光荣的思想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相结合,锲而不舍地定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为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痼顽疾束缚、削弱异化现象的消极影响创造有利条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面对贫困群体,要注重扶贫与扶志双管齐下、齐头并进,面对贫困群体的实际情形,我们不仅要发挥“输血、止血”疗效,更要强调“造血”功能,充分认识到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的逻辑合理性。同时关注人的主体性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育脱贫意识淡薄的贫困群体树立“人生在勤,不索何获”的价值取向,摆脱“等”“靠”“要”错误的思维定式,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主动开展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充实自己的生命,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扶贫主客体在交流实践过程中的双向互动,助力精准扶贫惠民政策向纵深推进,在贫困地区开枝散叶、落地开花,切实提高脱贫的速率效率。
(三)完善制度考核标准,注重因果辩证关系的影响
原因和结果的关系隶属于马克思基本原理的领域,是揭示客观世界中普遍联系着的事物,引起和被引起、彼此制约的一对哲学范畴。原因是物质通过主观性运动引起客体发生变化发展现象的原因,结果是由于客观原因能动作用造成的必然结果。把握好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活动中更加注重实践活动对于预期结果的影响,开展有目的、有计划、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促进结果的完满。通过调整扶贫终端考核的方式,根据客观实际为扶贫考核“瘦身”,通过减少填报表数、减少考核频次、取消不必要的考核,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注重年终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防治“一考定终身”的现象,同时强化考核的统筹整合,增加对贫困人次返贫情况的精准考核,实现由“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向“滴灌扶贫”方向性的转变,把资源用在最急切、最需要的地区,让有限资源迸发出最高的利用率,针对摘帽县、脱贫村、贫困户提出合乎自身状况的、坚实有力的后续扶贫政策,从而增加脱贫成效、提升脱贫质量。
四、精准扶贫走出异化影响的意义
通过对精准扶贫具体工作中异化现象的理性认识,以及对马克思关于异化克服科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对我们今后在脱贫攻坚战中克服异化消极影响,实现物质贫困走向物质丰富,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扶贫主体在具体工作中更加科学地解决异化现象带来的实际问题,同时增强扶贫客体积极摆脱贫困的渴望和主观能动性。
(一)有助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原则,精准扶贫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当前正值我们大步向两个一百年目标迈进的决胜时期,精准扶贫工作的圆满完成不仅关乎物质层面的极大保障,同时包含精神富裕的双向并举,不仅是党和国家强大政治号召力的鲜活体现,更是时代浪潮发展的客观需求,通过扶贫与扶志手段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体内在精神动力,补足“精神之钙”;通过对“关键少数”和贫困群体的正确规范和引导,帮助其正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树立信心,积极应对克服,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精准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如期顺利完成,有助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
(二)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建设一个强大有韧性的政党,离不开一个绿色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通过对扶贫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建设,可以切实改善整体政治生态环境,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筑筋骨、打硬铁,在今后面对扶贫过程中的难题时更加从容不迫,无愧于党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把权力运用到脱贫所需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为实现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扶贫举措,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积极投身扶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思考和反贫理论的提出,是对无产阶级自身命运和贫困问题的现象和本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的科学理论阐述。精准扶贫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为适应当前社会矛盾变化而制定的一项反贫困的惠民之举,其实质就是立足中国视角,把马克思主义反贫理论中国化向前推进,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解决中国当代问题深刻结合的产物。通过对扶贫过程中异化现象的深度思考和科学研判,逐步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消除贫困,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精准扶贫是关乎我国民生问题的一项精准化、细致化、持续性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揭示异化本质的基础上认识异化在我国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现实影响,通过全面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力求扬弃异化现象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党和国家、个人和社会日雕月琢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