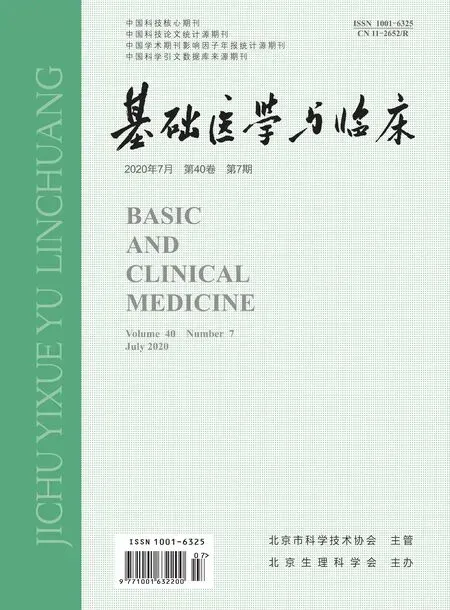中西医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020-02-12王淼蕾刘俊宏汪龙德毛兰芳符博雅
王淼蕾,刘俊宏,汪龙德,毛兰芳,张 萍,符博雅
( 1.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2.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所导致的肺部感染性疾病。其主要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有研究发现该病毒在粪便、血液、眼泪和结膜上均有存活现象[1]。该病毒可引起人和动物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疾病发生[2]。若长时间存在于体内则会引起其他各系统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医药治疗暴发性疫病已有百年的历史, 如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提出了很多温毒、热毒、温病阴阳毒的论治,各大医家也提出了许多用于解毒的方剂如清瘟败毒散、普济消毒饮、甘露消毒饮等,常用药物如金银花、连翘、黄连、黄芩、犀角、玄参等都具有解毒的作用。中医的诊疗过程注重的是个体与整体的联系,见微知著,司外揣内。如对于温病的诊断,在开始一二日是很难确诊的,需要经过细致观察,主要见有恶风、发热、咳嗽、自汗、头痛、舌苔薄白、脉象浮数等症,但不应拘泥于此类症状,还要注意传变与个体差异。正因如此,治疗温病要根据不同的分期进行准确的辨证论治,从而抓住主证,把握好主治和主方。
1 病因及致病机制的中医观点
在中医学上,COVID-19属于“温病-疫病”的范畴,“疫”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说文》中提到:“疫,民间疾也”;《字林》说“疫,病流行也”;疫病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战“疫”的记载,因此古人对传染病已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景岳全书·杂证谟》曰:“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也说:“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提出“疠气”是引起温疫的病因。《素问·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这是中医最早的传染病学说,与西方医学的传染病学说认知是吻合的。总的来说,中医认为该病的病因为感受疫病毒邪,通过皮毛、口鼻等途径侵入人体,病位首在肺,累及心、脾、肾等多个器官,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根据病情轻重、当地气候环境特点以及不同体质差异等情况来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以达到专人专方的诊疗结构。
2 临床表现与中医辨证
最新诊疗方案[3]已提出,COVID-19临床表现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状,并出现以肺脏和免疫系统为主,累及脾脏、肺门淋巴结、骨髓、肝脏、胆囊等重要器官的病理损害。方案中对中医辨证分型也有详细的阐述,主要包括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疫毒闭肺证、气营两燔证、内闭外脱证、肺脾气虚证、气阴两虚证,不难看出,该辨证思维以卫、气、营、血为纲,由浅及深,由轻及重,疠气邪毒由气入营,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很多严重证候都在这一时期发生,甚至导致死亡。另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辨证论治,如金珏等[4]从“五脏风”之“肺风”的概念入手进行论治,认为本病以脏虚为本,风邪为标,具有发病急骤、昼轻夜甚、变化多端的风邪致病特点,轻者仅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病情危重者可出现呼吸急促、面色青黄、咳血、神志不清等症状。毛得宏等[5]从吴又可“邪伏膜原”的学说出发,提出三焦、卫气营血、表里、脏腑4种辨证模型,认为本病主要以“温邪”为主要致病因素,导致的人体卫气营血、三焦所属脏腑的功能失调。舒劲等[6]则以“后天之本”为理论基础,认为“湿邪”侵入人体而致病,防御机体的卫气充足,脾胃之健运功能才能正常。因此提出在治疗肺系疾病时,从脾论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疫毒”是本病的主要发病原因,邪气从口鼻而入侵犯人体,邪正争斗,此消彼长,出现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单纯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做出正确的辨病与辨证才可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3 治疗方案
3.1 中医药治疗
中医治疗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7]中推出了清肺排毒汤的应用,明确清肺排毒汤可用于治疗COVID-19 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症患者救治中也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在试行中,该方经国内几个省份推广应用,初步总结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8],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中医治疗具有个体化的特点,患者体质不同,感受疫戾之气后的病症表现各异,各大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实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与治疗。如张勇等[9]以“湿热疫毒”为病理基础诊治24例普通型COVID-19患者临床研究中提出,将甘露消毒丹为基础方进行加减化裁,形成自拟协定方,该方以利湿化浊、清热解毒为法,针对湿热交蒸、蒙蔽清阳、阻滞气机而设,经临床试用观察得出肺部CT表现好转率80.95%,达到了满意的疗效。袁成民等[10]则从寒湿结合理论出发对35例COVID-19轻症患者进行观察,通过散寒、化湿、解毒、祛瘀并宗扶正达邪之桂枝汤、三焦分治之三仁汤或藿朴夏苓汤灵活化裁,随证加减,也获得了较好的疗效。王锐卿等[11]提出针刺疗法及耳穴干预COVID-19患者的可行性及应用方案探讨中提出,针刺可以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实施调控,并通过“分部”理论进行靶向治疗,并且针刺治疗疫病前期具有丰富的现代研究基础,另有研究[12]发现,针刺可能通过胆碱能抗炎通路,或激活交感神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神经抗炎通路途径对其发挥局部或全身抗炎效应,但目前并没有推出针灸治疗COVID-19的系统诊疗方案,后续有待进一步的推进与应用。中医药的及时应用有效降低了危重症转化率、病死率[13]。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中药同样不能有效地灭活病毒,但中医可以通过扶正祛邪达到抗病毒的目的,其作用机制可能包括抗病毒、抗炎、调控免疫机制、调节细胞凋亡、消除血栓、修复肺部损伤等[14]。在此次疫情的防治中,同时应用抗病毒药物及中药制剂的辅助加强治疗,显示出了良好的救治效果。
3.2 中西医结合治疗
目前对于COVID-19的临床治疗中医以中药汤剂为主,辅以中成药相佐。西医主要以对症治疗、氧疗、抗病毒治疗以及抗病毒药物治疗。从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可观的疗效。吴雨沁等[15]对目前有限的病例进行了中西医结合诊疗的系统评价,得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转化率,提高临床治愈率。一项临床研究[16]对103例COVID-19重症患者进行了疗效观察,结果显示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治愈出院率占76.5%,予以一般治疗的治愈出院率占65.4%,所以重症患者治疗过程中选择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明显优势。另有一项中西医结合治疗100例COVID-19的临床观察结果[17]显示,有81例患者治愈出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张伯礼院士认为[18],中西医结合治疗COVID-19,对普通型患者能改善症状,缩短疗程,促进痊愈;对重症、危重症患者,可减轻肺部渗出,控制过度炎性反应,防止病情恶化;对恢复期患者,可促进其康复进程。由此可见,此次在疫情防控期间,将中医与西医恰当的结合应用,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获得了更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普及。
4 中西医防护措施
早期发现并及时采取隔离是传染病防控的最好办法。不聚集、保持安全距离能有效避免与症状或无症状的个体密切接触而产生感染。定期清洗消毒公共触摸表面和常用的工具,常用的表面消毒剂包括75%乙醇、0.5%过氧化氢或0.1%次氯酸钠,其他生物杀灭剂如0.05%~0.2%苯扎氯铵、0.02%氯己定二氯丙酸盐对杀灭SARS-CoV-2的效果较差[19]。传统医学中,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对于健康人群,主要提倡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对于治愈出院者,疫后注意保津养阴,预防复发;在中医保健方面,提倡使用艾灸、中药香囊、中药泡脚、穴位按摩等[20]。除此之外,发现疑似病例应立即进行检测隔离,有效控制病毒的大量传播。由于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强度目前并不确定,主要措施就是及时进行检测,第一时间切断传播链,从而及时遏制疫情的再一次暴发。
5 结语
数千年来,中国先后发生过上百次疫病流行,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在这次COVID-19疫情期间,中医药在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如今医疗科技不断发展的趋势下,中医和西医相互协同显得更加重要,二者取长补短,为保障人类健康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