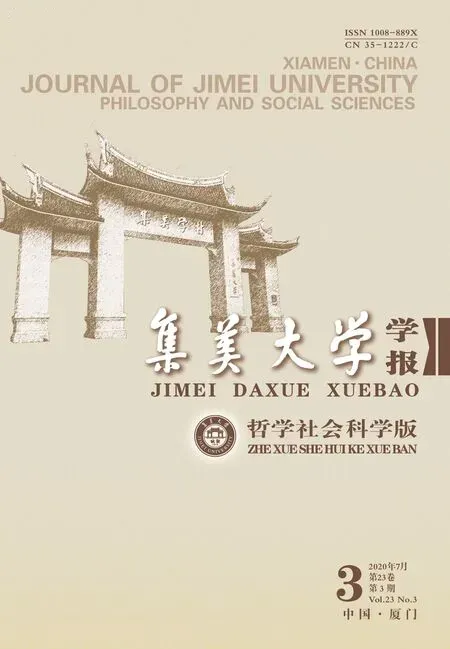从译《毁灭》看鲁迅与藏原惟人文艺观的异同
2020-02-12施灏
施 灏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藏原惟人出生的4个月后,鲁迅在日本横滨港登陆,随后到东京的弘文学院开启留日生涯。谁也不曾想到,30年后两人会有那么多的交集,小鲁迅22岁的藏原惟人给鲁迅的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许多参考信息和借鉴之处。而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代表了笔者研究的问题意识,即,从小22岁的藏原惟人那里鲁迅学习到了什么?借鉴到了什么?又怎么超越了藏原惟人?
一、鲁迅对藏原惟人《毁灭》观点的认同
根据《藏原惟人年谱》等资料记载,藏原惟人出生在日本一个社会高层的优渥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20年4月他考进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后,开始了对俄国古典文学的探索,毕业后藏原入伍从军。匪夷所思的是,在防范马列主义思想最严的军队里,藏原惟人接触到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不仅深受影响,也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奋斗方向。
退伍后的藏原选择成为一名驻苏联记者,1926年10月回国后旋即加入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团体,并以该团体重要杂志《文艺战线》为平台发表了大量文章,逐渐成长为日本左翼知名的理论家。此时日本左翼文学在青野季吉“目的意识论”导向下强调文学应当优先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之后更是将这种服务关系推至彻底的服从关系。这种对文学独立性、自主性彻底压抑的做法激化了组织矛盾,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出现了混乱、停滞和倒退现象。面对这一局面,藏原惟人1927年6月发表了重要文章《关于所谓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运动的“混乱”》[1],提出了改变文学应当服从革命的“工具论”指导思想,呼吁探寻突破困境的合理出路,从而创作出真正的革命文学。在藏原的努力下,一度陷入绝境的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绝处逢生,原本已经崩溃、分散的力量重新聚合,还吸引了新鲜力量加入。当时日本国内、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两大左翼组织——日本左翼作家联合会、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家联盟先后宣告成立,这是日本左翼文学运动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藏原因为其卓越的贡献而取代了青野季吉,成为新时期日本左翼联盟中的核心领军人物。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文学开始成为引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学,精通俄语的人相继译介了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在这方面藏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在译介的数量上非常多,而且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形成了健全的体系。他翻译的主要作品有:
《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一九○五年》(帕斯捷尔纳克)、《辩证法与辩证法的方法》(高列夫)、《马克思主义·列宁及现代的文化》(德柏林)、《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布哈林)、《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共产主义战士的管线——劳农俄国短篇集》、《阶级社会的艺术》(普列汉诺夫)、《毁灭》(法捷耶夫)、《现代欧洲的艺术》(玛察)、《第一次革命及其前夜》(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哲学·历史及文学观》(普列汉诺夫)、《我的大学》(高尔基)、《看门人》(高尔基)、《铁流》(绥拉菲摩维奇)、《社会主义思想全集》第17卷(普列汉诺夫)、《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弗里契)、《理论艺术学概论》(玛察)、《长诗恶魔》(莱蒙托夫)等等。(1)文中书目参考自浦西和彦1986 年3月主编的《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书目》。
藏原惟人所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和文论陆续传入中国后,引起了鲁迅的关注。藏原从苏联归国后翻译的第一本苏俄文论是《艺术与社会生活》,在1927年2月正式出版。是年的11月鲁迅因战乱在途中避难时就购买了这本书。另外,根据中岛长文所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2]164、《鲁迅全集》等记载,鲁迅生前共购买和收藏的藏原译介的作品有:《艺术与社会生活》《辩证法与辩证法的方法》《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新俄罗斯文化的研究》《阶级社会的艺术》《共产主义战士的管线——劳农俄国短篇集》《支那革命的现阶段》《现代欧洲的艺术》《毁灭》《普列汉诺夫选集》《艺术与无产阶级》《铁流》《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列宁与艺术》《无产阶级与文化的问题》《艺术论》《我的大学》等等。
以这份书单比对前面的藏原书单,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购买、收藏了藏原译介的半数以上作品,足见鲁迅对藏原持续的高度关注。从鲁迅的收藏和译著看,鲁迅认为藏原的译介是认真的,研究是有深度的,尤其是藏原对苏联革命文学的理解对鲁迅的文艺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藏原经过相当的努力,在大量参考苏俄左翼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发表了《走向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的道路》等论文,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者应当树立这样的信条,即:“现实就是现实,不应附加任何主义观念的东西,毫无主观粉饰的去描写自己的创作对象。”[3]146这些思想也正是鲁迅一直以来所思考的,因此让鲁迅产生了强烈共鸣,所以鲁迅评价说:“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译过许多文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诚实的俄文翻译者。”[4]215
在提出这一主张的第二年,即1929年,藏原开始翻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5]。他赞美法捷耶夫的创作手法,说:“我们可以比照此前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无产阶级现实主义”,[3]449并且认为《毁灭》才是“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典型之作,是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用现实主义手法正确描写英雄人物的先河之作。他认为:“只有这部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才算是真正描写革命大众形象的作品了,而且它还为我们解决了如何处理革命典型人物的塑造和个性描述之间存在的对立而又统一的问题。”[3]449
藏原译介出版的《毁灭》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许多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都对藏原及《毁灭》所持观点表示肯定。如内山忠吉在《帝国大学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里就说:“从形式上来看,这部小说确实是文学创作走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一大进步。”[2]北冈徹夫也认为《毁灭》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已对藏原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和《新艺术形式的探索——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目前的问题》等文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早在1928年,鲁迅就开始译介藏原惟人的译文集,如藏原惟人与外村史郎合作编译的《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鲁迅译本初定名为《苏俄文艺政策》,之后则更名为《文艺政策》。因此,当藏原把《毁灭》视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代表作译介到日本时,鲁迅于1929年5月2日在内山书店购得藏原惟人在南宋书院出版版本,阅读后便开始着手翻译。在1930年上半年,在还没有完全译完时鲁迅就急着联系《萌芽月刊》连载,并引用了藏原的文章,对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区分:“法捷耶夫的《毁灭》,许多批评家们都说是在莱夫·托尔斯泰的诸作品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实际上,凡较为注意地来读这作品的人,是谁都可以发见其中有着和大托尔斯泰的艺术底态度相共通的东西的。第一,在作者想以冷静来对付他所描写着的对象的那态度上;第二,在想突进到作中人物的意识下的方面去的那态度上。”[6]247-249“但是,托尔斯泰和法捷耶夫,在其对于现实的态度上,是完全同一的么?不是的。法捷耶夫决不像托尔斯泰似地,将人类的行为看作对于‘运命’的盲从。他决不将袭击队当作只是单单的自然发生的农民的纠集而描写。在这里,就存在着他和托尔斯泰的对于现实的态度的不同,同时也存在着他的袭击队和例如V·伊凡诺夫的袭击队的不同点……对于同一的袭击队的这态度的不同,也就正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对于现实的认识之不同。于是,法捷耶夫的这态度,和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相对,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6]247-249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藏原描述了无产阶级文学有组织性的特点,这让鲁迅感到新鲜。藏原惟人的观点和法捷耶夫依据自己的实际战斗经验创作小说的做法,与鲁迅的见解是基本一致的。从鲁迅和藏原惟人两人对《毁灭》的译后记看,他们对《毁灭》的评价基本相似,都认为《毁灭》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形式和新内容,是“决非幻想的人所能著笔的”[7]367“可以宝贵的文字”[7]371,“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百战的战士,不能写出”。[7]371可以说,鲁迅在《毁灭》中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方向,对藏原阐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特点,鲁迅感到新鲜且颇受启发,从而促成了他对革命文学的进一步思考。
二、鲁迅与藏原惟人《毁灭》观点的分歧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思考,在其与《毁灭》同时期写的杂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在1929年5月2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时,从唯物史观原理出发,阐明了各种文学是应环境、物候而生成,并非是文艺在改变这种环境与物候。换言之,是社会大环境规训与形塑了文学的形态,激发了文学的动态变化,文学文艺对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程度远远小于环境对文学文艺的影响程度。而在旧的社会形态、生产关系行将解体的前夕,往往会有很多所谓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鲁迅认为这样的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要等革命成功之后,才会产生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的形态质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质变而决定的,所以从俄到苏,鲁迅在其极力推崇的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精神世界中进进出出,也在藏原惟人、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里定等人的精神世界中进进出出。
藏原在1929年译介完法捷耶夫的《毁灭》后,以此为分界线,他的政治思想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于1929年9月加入了当时在日本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后,文艺立场发生了激进转变,极力主张“政治”“侵蚀”文学。他说:“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艺术家一定要把我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党目前所面临的课题,视为是自己艺术活动的课题,只有先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正如现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及其党把目前的产业及生活及社会主义的改革等均作为自己的课题一样,我国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也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这一方面。战斗的无产阶级应该把扩大和强化以及引导民众斗争工作的党的中心课题视为是自己的课题。处在现在的日本,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都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投放到这一方向上来才可以。”[2]170他还强调:“为了‘确保和扩大党的政治性、思想性的影响力’,我们的艺术家们应该如何去做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倘若只是在作品中反反复复地重复几十遍这样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有必要把我国的前卫们是如何展开战斗的场景真实地描写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厂、在农村是如何开展社会活动的以及是如何组织农民和劳动者的?还有怎样去引导战争的场景等,均告知大众。我们的艺术家一定要通过论文和通信等形式,加上鲜活地、有效地形式,把党的政策宣传出去,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2]170不仅如此,藏原还在他的很多文章里积极倡导文学的政治功用,甚至极端呼吁文学创作活动要自觉地为政治目的服务。
藏原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同时期的鲁迅开始出现了明显差异,而且越来越大。两人虽然同为《毁灭》的翻译者,但对于《毁灭》的理解、吸收、鉴赏都有很大的不同。藏原认为《毁灭》是一部不仅与他积极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艺思想相吻合的小说,而且对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着积极的促进煽动作用。他翻译《毁灭》的深层次目的,还是希望推动日本左翼作家们身体力行去创作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文学作品,把“扩大和强化以及引导民众斗争工作的党的中心课题视为是自己的课题”。相形之下,鲁迅认为《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本人亲身参加过战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文学家,是真情流露地创作《毁灭》,而不是靠任何意识形态引导抑或是命令下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毁灭》。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过:“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时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来做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有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8]438“为了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8]438从中可以看见鲁迅文学观至关重要的一面,也不难想象一直关注藏原的鲁迅在这一时期接触到藏原新言论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在译介了《毁灭》后藏原所持有的创建无产阶级文学新形态、新形式、新内容的立场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与批判,同时也表示了鲁迅对当时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过度推崇甚至照搬照套藏原理论的不满。较之藏原,鲁迅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文学本质上应该与其他既有的文学一样,创作动机必须源于生活本身,必须凭借创作者艺术灵感的爆发而产生,而且必须是为大众和为人生。
鲁迅对于文学过分强调阶级与意识形态甚至演变为“比如瓦进先生所代表的激进主义”[9]910是断然不认同的,到这里鲁迅与藏原的思想已经产生明显的隔阂,鲁迅在《壁下译丛》和《译丛补》中没有收入藏原一篇文艺理论作品,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鲁迅所认同的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性源于肯定、注重人本性的创作动机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文学固然有其反抗旧有的方向性,但更应遵循阶级意识形态不强加于公共话语空间与文艺规律性的基本原则,反之,就与旧有专制下的文艺形成机制无异。鲁迅认为政治应当尊重公共话语空间里的文艺创作,文艺作品的生成应当建立在此二者平等且互为主体的碰撞、协调、求同存异的周期基础上,一定是不违背规律而传承过往的,不自我断裂的健康文艺。鲁迅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文艺创作观,一直坚决反对夸大文艺的政治功用,将文艺与一切阶级挂钩,因此鲁迅与藏原惟人对《毁灭》译介的不同,实际上是表现了鲁迅与藏原惟人文艺观的差异,所以鲁迅与藏原惟人渐行渐远是必然的。
三、结 语
《毁灭》是鲁迅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曾将《毁灭》评价为最有艺术价值、精神价值的革命文学作品:“(雅各武莱夫作品《十月》)虽然临末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7]352-353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喜爱《毁灭》的深层次逻辑,《毁灭》近乎完美地契合着鲁迅的文艺观与文艺创作理论,译介《毁灭》之后,鲁迅和藏原惟人渐行渐远,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两人在对《毁灭》真正理解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作为独立的个体,鲁迅对《毁灭》的理解必然比藏原更深刻。
译介《毁灭》之后,鲁迅有计划身体力行创作出一部类似作品,也作了许多艰辛的努力,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译介《毁灭》却成为鲁迅建议、提醒青年作家们的最佳参照物,他希望青年作家们务必坚持凭借真心和切身经历去写作,“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10]17更是一再提醒青年作家们切忌因任何外因抑或是为写作而写作去犯生硬模仿的错误。如在致信李华时就说到:“现在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有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成不了艺术。”[10]372这既反映了鲁迅与藏原惟人文艺观的迥异之处,也是对最终陷入文学工具论、模式化、公式化的藏原惟人以及国内左翼生搬硬套藏原理论种种荒谬乱象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