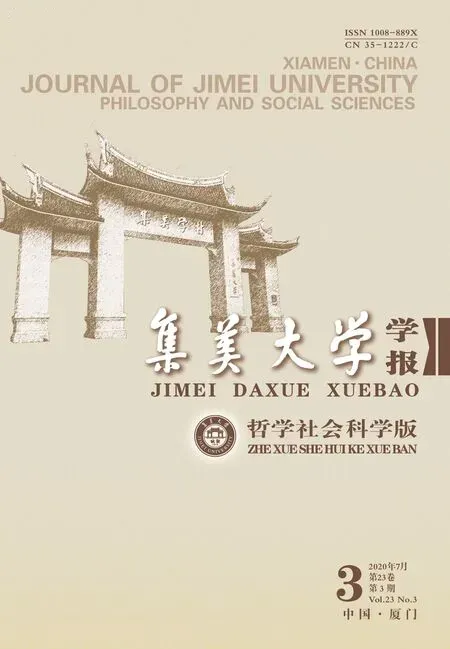《蕃薯浇米》中的海洋意象及其文化地理反思
2020-02-12管雪莲常秀秀
管雪莲,常秀秀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入围“青葱计划”的青年导演叶谦拍摄的全闽南语电影《蕃薯浇米》成功上映,影片一反当今电影的快节奏,将一位闽南渔村老人的暮年生活缓缓道来。林秀妹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长大,在儿子各自娶妻成家后,发现自己变得无关紧要,儿子在外赚钱,媳妇冷漠,孙子也不与自己亲近,还好有活泼、大胆、仗义的老姐妹青娥作伴,两个人互相逗笑、互相帮扶、互相倾诉,一起驱散悠悠岁月的孤独。却不想青娥突然离世,70多岁的秀妹陷入迷惘,在人、神、鬼的指引下,她明确了方向,决心找回那个被生活遮蔽了的自我。影片在讲述秀妹和青娥两位老人故事的主脉络下,同时展示了闽南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比如对闽南文化中人、神、鬼和平共处的视觉叙述,以及对赶海晒盐、腰鼓舞、祭拜妈祖等带有浓郁地方生活特色的镜头表现。在这些闽南特色文化的展现中,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景观所带来的视觉美感,是本影片的一个镜头亮点,更重要的是,大海已经作为一种人文景观融入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的生成,进而表达了一个新的关于“大海与人”的理解和反思。
一、《蕃薯浇米》中作为自然景观的海洋意象
电影对“海洋”的表现,有很多经典,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少年π》《泰坦尼克号》《海角七号》《海上钢琴师》等影片。电影表现海洋,既表现它自然属性的方面,也表现它人文属性的方面,两种表现交汇融合,才能提炼出有品质的美感。而对于观众来说,自然属性抓住人的视听专注力,美轮美奂、汹涌澎湃、奇景诡流,种种风格都令人兴奋、令人遐想;而人文属性则动人更深,让大海成为一种语言,成为一种叙事,有故事的大海和有故事的人结合在一起,一切通过镜头向人们缓缓道来。我们看这样的电影,解读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就像刘勰所说的:“物色尽而情有余”,[1]206及“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219刘勰这里讲的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其实对电影作品的理解这一点也是相通的。自然与人文,兴与发之间,情与景之间,所有的文艺作品,它的秘密和内涵,都可以循此而发现。
那么,电影《蕃薯浇米》对“海洋”的自然表现是怎样的呢?它又是怎样为它所要的人文表现打下基础的呢?我们来分析这样几组镜头:
镜头一:在影片开场,特写镜头下的海水层层涌起,向前推落下,夕阳的一抹余光打过来,伏起的小浅浪泛出金色,随之灭掉又起,浪在涌,光在动。紧接着开场的海洋画面,是秀妹和青娥在海边捡海蛎的场景。这一处的海洋画面不同于开场的特写镜头,采用的是全景构图,画面中有的农人挑着担子从海上满载而归,有的在用绳子拉近海的礁石,几只鸭子游过波光粼粼的海面,荡开一道长长的水纹。这两个不同视角下的海洋画面各具姿态,前者动中含静,后者静中有动,前者平远,后者活泼,这种形象上的外在风格传达出的是渔村偶有波澜的平淡生活和变化着的生活中不变的朴实。
镜头二:在影片中间部分,青娥离世后,秀妹几次去海边,海景画面主要有两处:一处是秀妹在陷入迷惘时所看到的海洋,蔚蓝无际的海水在哗哗声中浩浩荡荡地涌去,波涛不停地跳上礁石绽出无数纷飞的浪花,秀妹哼着古老的歌谣与海相望相依,此时日暮下海对岸几座高耸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海浪涌动,涛声依旧;另一处是在影片结尾秀妹坐在宗祠外的石阶上所看到的海:绿树点缀的黄石岛上发电风车转动着,大小的船行走在浮动的绿色幕布上,一位面向大海的纹丝不动的海军凝望着这一切,像在等待归船,也像即将出发远航。从影片来看,秀妹是因某件事情的发生而望海沉思,所望海或豪迈,或腾跃,心随海或释然,或坚定,海洋画面因景情相生而别具风格。
镜头三:除上述壮美活泼的动态海洋镜头外,影片中也有不少唯美的静态海洋画面。影片开头,在清晨的锣声中呈现出了一幅静海画面:天蒙蒙亮,一个打锣人走在海中长长的石道上,石道左侧的海无波无浪,任“咚咚”锣声依然沉睡不起,海水澄澈又微微泛蓝,恍若天空之境。在影片中间部分,也有一幅静海画面:海边有两个人面朝大海吹笛,茫茫海面上无数枝丫稀疏地排列着,笛声婉转明快,隐约可见浅浅的水纹在向海岸靠近,像是风起了,也像是海听到笛声微笑了。相对于动态的海洋,静态的海洋画面之美在于所表现出的海洋的纯净、悠远的形象,形象之外流露出的是这个渔乡里人们的平和与心安。这样的内外照应,正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描述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2]
影片中的静海画面与情节多无明显关联也没有角色参与,更像是一段留白,一种意境,声画结合,余味无穷,而动静不可分割。海之动与海之静是相互依存的,影片中镜头下的海洋画面动中有静,以动衬静,在动静之间,凸显了平远、活泼、豪迈、腾跃、纯净、悠远的海洋形象,形象之外各有某种内在之意,“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3],海洋画面的意象美无疑提升了影片的艺术美感。
二、作为人文景观的海洋意象
电影表现自然,但绝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然,而是要赋予它人文意味,引起人们更多的超越视听感受的深层反思和感触,思考它的文化。正如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认为的:“影像不是现实的摹写,而是艺术家的创造物,是经过文化‘过滤’的符号。影像的组合方式,是具有纯语言的约定性的重新结构的符号系统……为的是增添文化的属性。”[4]因此,作为自然景观的海洋意象或许可以相似,但作为影片人文内核的海洋表现却绝不相同。考虑到文章篇幅,这里并不能对其他电影的海洋表现做出评价。那么,以《蕃薯浇米》论,它的海洋景观的人文属性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惠安女的文化属性。
(一)惠安女的生活内容和影片的人物故事
惠安以及沿海地带的居民几百年来靠海吃海,男人们要出海打渔,女人们便担负起所有的家计。她们操持生活,任劳任怨,以勤劳为人所知。影片中的秀妹与青娥是惠女的典型,秀妹在丈夫早逝后独自将两个儿子养大,儿子成家后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儿媳孙子都不与自己亲近,为避闲语不愿接受阿水师,在好姐妹青娥去世后更显孤独迷茫,随后在一系列所见所闻中逐渐坚定、觉醒。青娥的丈夫是个酒鬼,儿子出海讨生活,她种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她自己种出的菜在集市上不受欢迎时,她几次去偷大棚里的蔬菜,想弄清楚有什么不同,怎样才能种出更好的菜。她还未明白这其中缘由就因积劳成疾而离世。以秀妹和青娥为代表的惠女们勤劳无怨,打拼度日,如海水般动而不止,朝气蓬勃,而对她们来说,这种打拼的日子是“千金也不换的尚好光阴”。
(二)影片中的人物性格
勤劳的惠女是千千万中国劳动妇女的缩影,但是与生活在内陆劳动妇女不同的是闽南女性沿海而居,以海洋为主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们不同于内陆女性的特性——敬神。沿海地带男人多以捕鱼为业,海里浪中,风险很大,特别是在过去技术设备落后,安全没有保障,当男人出海打渔时女人便在家里默默向神祈福,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惠女敬神——尤其是敬海神的性格。影片中秀妹平时会拜家里供奉的神明,在要不要接孙子回来和要不要让秀妹加入腰鼓队这两件事上,都是通过在天后宫抽签问神决定的,而天后则是海神妈祖。需要指出的是她们所信的神并不是单一的,是一种多神信仰,如秀妹在路上捡起被人丢弃的多个神像,并将它们都供奉在祠堂;土元师作为一个道士同样深受其尊重,治“腰缠蛇”、青娥丧礼、天后出宫都有他在场。除神之外,鬼也是与人一样的存在,如青娥去世后她的鬼魂夜里与秀妹床边交谈,鬼的存在是基于对神的信仰之上的,被外界冠以封建迷信之名的神、鬼对她们而言却是真实的存在。她们的精神世界因为神、鬼的存在而变得纯粹,没有功名利禄,没有勾心斗角,虔诚静谧,像一碗番薯浇米平淡质朴,与世无扰。
人是环境的产物,惠女勤劳、敬神的特性是因为要适应环境,但“人毕竟是主体,因此人物的性格可能与环境相反,并反抗环境”。[5]影片中惠女们如海水般勇进执着的特性便是人物反作用于劳苦环境的表现,如青娥并未被生活之艰辛泯灭个人的爱好追求,她摘三角梅装扮自己,跳腰鼓舞。又如秀妹一生隐忍克制,在青娥死后曾一度迷茫,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迈出了追寻自我的脚步,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情感,将自己的愤怒化为一场大火,一反从前,又无憾无悔。惠女在劳苦的生存环境下,并不是一味地失去自我,而是与环境反向而行一步步走向觉醒,秀妹的觉醒过程是环境所致,是情理之中。黑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6]即人物性格应该具有丰富性,导演在突出惠女由海洋环境所致的独特性格的同时,也展现了惠女性格的丰富性,影片因此具有了生活化的真实感。
三、影片对“海洋”意象的文化地理反思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影片中的大海表现既是一个生活场景,一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场所,也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力烘托,其实,它也是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深思、表达导演进一步深思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即海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文化符号,它还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文化符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大陆文明不一样的另一种文明——海洋文明。所以,这个电影有一个比较的视野,在比较中对“闽南”这个独特区位的文明进行了反思。它主要通过两点来完成。
(一)海村女人头脑中是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
闽南女性在海洋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有别于内陆女性的性格特点,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惠女身上的特性是海洋文化的特色?黑格尔认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与“地理上的差别”息息相关,他将地理分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7]在前两种区域中,形成了以农、牧为主的大陆文化,在海岸地区,形成了以航海贸易为主的海洋文化。在《蕃薯浇米》中可以看到,闽南地区存在海洋文化的基因,如秀妹儿媳妇卖海蛎,青娥卖菜,妇女们盐场晒盐也是为卖盐,这种重商的乡村氛围与中国内陆“重农不重商”的传统农村迥然不同。希腊民族由出海冒险所形成的打拼精神也存在于勤劳的惠女身上,经商、打拼显然是海洋民族的特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惠安女性格是海洋文化的特色,原因在于“闽南社会是源之于中原的移民社会,闽南文化在本质上是随同移民携带而南播的中原文化”[8],在此将惠女与代表海洋文化的希腊地区的女性相比较,便显而易见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男尊女卑观念是支配两性观念的核心。《三国演义》中刘备有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破,安可续。”[9]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女性只是用以建构男性主体的一种场所,一种不具有主体性的物的存在”。[10]希腊女性亦没有逃脱这种被物化的悲剧性命运,希腊神话中,宙斯创造美少女潘多拉作为惩罚人类的工具;“在‘金苹果事件’中,美女海伦被作为礼物赠给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她又被作为奖品置于‘弗律基亚人的勇气和希腊人的武力之间’”。[11]可见,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和希腊女性同样在长时间的男权社会中丧失了选择权与话语权,成为“第二性”,但受自由、竞争、平等等海洋精神的影响,希腊女性有极强的复仇意识与自我意识。典型的例子如美狄亚为了爱情,偷金羊毛,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为了报复背叛自己的阿伊宋,她杀死了阿伊宋的新妇以及自己和阿伊宋的两个儿子。希腊神话时期的女性,承受着男性的压抑,于是借助文化表象下的歇斯底里,甚至自我牺牲等极端的方式去抗衡男性社会,在复仇的极端快感中凸显自我意识。
而在以大陆文化为主的中国,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利用并扭曲儒家礼制限制女性,尤其是北宋以后,封建礼教对妇女的限制畸形高涨并走向极端,中国传统女性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逐渐定型为温柔顺从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必须唯夫是从,克制忍耐,从一而终。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通过男人的手,上帝在人间的计划得以完成,女人只是辅助者,她安分守己,维持旧章,消极等待。”[12]女性的这种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延续,在今天仍有印记。《蕃薯浇米》中,秀妹为妻为母,贤良淑德,勤俭持家,作了一辈子寡妇的她在老年时光里与阿水师相互有情,但遭到两个儿媳背后的鄙视和谩骂,又担心村邻的指点而无再嫁;青娥丈夫酗酒懒散还打人,但是相对秀妹更为大胆自我的青娥从未提过离婚,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隐忍克制、失去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的延续。不可否认,历史上也不乏自我意识觉醒的惠安女。民国时期,娃娃亲、长住娘家、角色分工等陋习将惠女们困居于狭小的封闭空间,她们之间相互结成“金兰盟”,不少结伴自杀。[13]当时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疯癫的行为,而福柯认为疯癫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综合起来的产物,是理性压迫的一种结果,并非是一种自然意义的生理疾病。[14]很显然,惠女们以死亡来彰显自由选择的意志。这种自我意识显现不同于希腊女性,是封建礼教疯狂逼仄的结果。那么惠女本身是海洋文化的产物为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受到与内陆妇女同样的“封建礼教”束缚?(1)闽人都是由中原人迁徙而来,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迁移入闽,分别是: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唐末五代的王审之入闽、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毋庸置疑,闽文化是传承中原文化而来的,早期“衣冠”士子的到来奠定了闽区儒家文化的根基,北宋儒教礼制对妇女的极端化控制自然在闽地区也同样施行;(2)虽然闽南沿海与外界有通商,但是儒家文化以其包容性足以“涵化”海外文化,加之明清严格的海禁政策,海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始终无法动摇中原儒家文化的根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3)特权的加强与地形闭塞使她们更加趋于保守稳定,在接受了既定思想统治之后也很少做出改变,比如闽南话在唐代定型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只会加强而很难逆行减少。除此之外,明显不同于希腊女性复仇的残忍性格的是惠女的善良本性。秀妹对亲人、朋友、陌生人都是极善的,她不仅待人以仁,还与人互敬互信,阿水师送她枕头之后她并没有认为理所应当而是以礼回之;她还重义轻利,为顾及青娥的脸面而将自己唯一的结婚戒指送出去。秀妹的仁、义、礼以及勤劳节俭也明显是受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个大陆与海相连的地方有其与思想观念相融的一面,但闽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与内陆一样有“崇儒”的一面,它还另外有“远儒”的一面,这种“‘远儒’更多以俗文化的形式存在,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成为一种直接的、自发的和由继承而来的经验传统、生活传统和信仰传统”。[15]如在《蕃薯浇米》中,秀妹捡神像,与青娥鬼魂谈话。这种人鬼神和谐相处状态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格格不入。多神信仰又与西方文化的一神信仰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远儒”是促成闽南女性性格独特的原因之一。综上,闽南女性性格特点的形成是以大陆文化影响为主,海洋文化影响为辅。这种双重影响又赋予闽南女性以独特性。
(二)全球化格局中的闽南现代性反思与海边女性新形象
《蕃薯浇米》的导演叶谦是国际时装设计师,他的服装设计《少女妈祖林默娘》采用了不同颜色去表现闽南人信仰的海神妈祖在人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又如另一个系列《商女》,描绘的是小时候其在沿海地区见到的各色各样的勤劳惠安女商人。这种将闽南文化与现代元素相融合的设计理念中,体现出的是作为闽南人的叶谦的全球化视野与现代性追求。他的《蕃薯浇米》虽植根于闽南文化,但是他看到了现代性为闽南生活与文化带来的变化。他想表现出的也是在这种变化影响下的一种新型海边女性形象。
闽南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成就了他的时装设计。叶谦所希望的是现代性的融入能为他成长的闽南故乡带来一些变化和新的希望。我们也确实在他的电影里看到了渔乡生活方式的现代性改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之所以为现代,就在于其和传统的断裂”。[16]影片中,男人们外出打工不再从事渔业,塑料大棚的蔬菜长成与否不再受季节限定,海对岸密集的工业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千百年以农渔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发生巨变;神像被人丢弃在路边,代表古老的信仰传统开始动摇和解构。哈贝马斯也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十八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17]除了传统分崩离析外,哈贝马斯还强调了现代性社会的自由特点,而惠女性格特点转变是这种现代性自由观的最好体现。
在同为惠女题材影片《双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残酷婚姻习俗严苛制约下,王大嫂在未生孩子之前与丈夫王大哥见面私会被村民施以“应得”的惩罚,惠花的大嫂受尽自己大哥的欺凌和母亲的种种限制而不予反抗,相比之下《蕃薯浇米》中惠女的境遇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秀妹的两个儿媳从不受丈夫与婆婆的压制来看,新型惠女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旧传统对老一辈惠女也失去了严格的约束力。秀妹与阿水师互赠礼物,一起看《陈三五娘》,但是内心仍存的旧观念与世俗眼光使得她并未接受阿水师。在青娥死后,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被旧观念尘封的自我悄然觉醒,她不顾反对与嘲笑参加腰鼓队,向阿水师表示心意——以后为他缝补衣服,放火烧了影响青娥生意的蔬菜大棚。这些举动与秀妹往常的内敛隐忍形成对比,她的爱、她的恨完全地置于镜头之下,这种自我觉醒是现代意识的萌芽,对于一个受了一辈子禁锢的老人,这种萌芽是非常可贵的。
现代文明促使惠女生活发生种种如上述的积极变化,然而《蕃薯浇米》中我们也看到惠女转变的另一面。勤劳一直是惠女被颂扬的品质,在早些时代的惠女影片《八女传奇》《双镯》中均有表现,然而《蕃薯浇米》中这种“勤劳、打拼”在新一代惠女——秀妹的两个儿媳身上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大儿媳铲盐喊饿;二儿媳看天线宝宝买六合彩寄希望于中奖。与《双镯》中婆媳关系截然不同,秀妹给两个儿媳分海蛎、送油、做早饭,而二儿媳对秀妹总是一副漠然的表情,为秀妹捣药时不耐烦,失火后又大声呵斥,对婆婆丝毫没有尊敬之情。在秀妹与阿水师踩水车被看到后,二儿媳摆出了死去公公的照片,大儿媳则上门公然辱骂阿水师丢脸。由此我们看到在这个现代化裹挟的乡村社会中,两个儿媳一方面未能很好地继承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现代文明好的方面,说明在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替期,伴随着乡土社会的解构,人们渐渐抛弃了有碍于自己的旧观念,但新的思想价值观还未形成,在一些无关乎自己的问题上依然固守旧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可以说现代文明的传入,使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集体主义开始减弱,而个人主义出现并且加强,比如秀妹与青娥两个家庭的亲情关系非常松散,秀妹的两个儿媳倾向于个人享受,她们对秀妹老年恋的反对态度又暗合了她们“要面子”的自私心理,她们停滞在自己的舒适区而不愿用传统来约束自己,也不愿进一步接受现代文明。相比儿媳,秀妹仍保留着一种精神坚守,她因为自我觉醒而有了自我超越,原因在于秀妹成长的环境中现代性未萌芽,她身上对儒家的坚韧,对佛道等多种信仰的虔诚是根深蒂固未被浸染的,她的自我觉醒因具有方向目标性而升华为自我超越。两个儿媳生活在乡土社会解构与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时期,在对传统进行否定时未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她们因失去方向而陷入迷惘,这也是现代人的迷惘。
惠女形象的转变是现代性发生的结果,而现代性的发源是海洋文明。宁波认为,大陆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的主要旋律,从中衍生并创造了海洋文化,中国的大陆文化也曾以进取和开放为主流,但为维护日益加强的封建特权而趋于守旧,[18]没能从附属于大陆文化的海洋文化中衍生出现代文明,海洋文化在逐渐保守落后的中国逐渐隐匿,成为了开放、技术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代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自于西方海洋文化的现代性无声地潜入小渔村,加速工业化进程,使惠女生活摆脱了对海洋的依赖、传统的束缚,不可否认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的优势。中国很多海洋文化研究者也都认为“海洋文明是先进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19]但是影片中新一代惠女某些优良品德的缺失,小孩沦为技术的工具,每个人陷入孤独的境地:秀妹无人陪伴的暮年孤独,青娥无人理解的种菜孤独,两个儿媳精神生活贫瘠所致的孤独……这不禁让我们怀疑,“先进的海洋文明”真的是先进的吗?
四、结 语
《蕃薯浇米》以柔和的镜头、多彩的画面再现了闽南渔村女性的暮年生活,海洋作为闽南女性的主要生活环境在影片中得到了两种意义上的表现:(1)作为自然景观;(2)作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吸引观众的视觉专注力,人文景观的融入,使得故事人物的性格和追求有了血肉相连的环境,而惠安女故事也反过来赋予了大海独特的人文属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导演在这两个特色的基础上对“大海”的地理文化与“海村女性”的文明理念进行了反思。闽南地区地处沿海,是中国社会较早接触海洋文明的地方,与海外的贸易交流在全国也处于较领先位置,然而闽南传统女性的思想仍然是带着非常明显的农业社会的束缚。
在今天,源于海洋文明的现代性加速了经济发展,加速了全球化,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有了系统性、结构性的互通的情况下,社会的大变革是如何影响到小人物的生活中引发她们的生命故事?而她们的故事又反过来启示我们如何在每天日常可见的生活中感知社会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