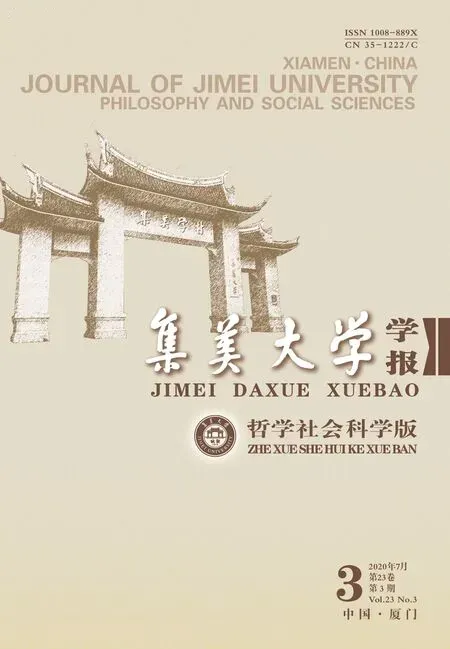马克思的机器观及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
2020-02-12孟燕华
孟燕华
(福建江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当今人工智能(机器)技术日新月异,逐渐影响和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善了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方式,同时也为人类内心世界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或多或少的焦虑、忧思。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被誉为千年伟人的哲学家马克思在其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如何看待机器技术?有哪些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仍需我们继承、运用和发展?尽管今天我们所生活时代的背景、技术层级和技术结构同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马克思关于机器重要论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为我们深入把握和推进人工智能(机器)技术运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实践遵循和价值指引。
一、哲学反思:机器并不能超越人类主体性地位
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技术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是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延伸,表征着人类主体性发展水平。从哲学角度出发,机器最终能否取代人类主体性地位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即人是机器的尺度还是机器是人的尺度。机器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的劳动能力对象化的自然物质,不具有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缺少构成人的主体性、规定性,因而机器不会威胁乃至取代、超越人类主体性地位。
(一)机器是人的劳动能力对象化的产物
机器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的劳动能力对象化的自然物质和产物,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器官的总和增强和拓展。“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1]197,“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197机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能力以物的形式展现,其受到人的智力系统控制,并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得到人为地更新和改造。可以说,机器不过是人类与外部世界关系、人类与自身关系中所外化和对象化出的一种以人的方式认知世界、沟通世界的另一种媒介。
(二)机器不具有人的意识和思维的能力
作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机器是物,其并不具有属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
1.意识和思维是人脑的产物。“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38-39自然界本身不生产机器,机器并不与自然界一起发展起来,而是随着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162
2.意识和思维是以类形式存在,具有整体性、总体性和反思性特质。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生活是一种类生活,人的意识是一种类意识。“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3]188机器不具备反思意识和思维能力,不能把握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本质性、意义性联系。
3.意识能力和思维能力是人化自然界基础上的成果,具有逻辑必然性。机器意义上所表征的“能思”能力,不是机器长期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经过人类这一中介,人为程序设计和布置而生成的。
(三)机器不具有属人的主体规定性
机器作为人化自然界而生成的产物,是为主体所用的客体性存在,不具有属人的主体规定性。
1.作为主体的人,是肉体性存在。主体是有生命的存在,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是以人化自然界的存在为基础。机器是主体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界而形成的无生命存在的物质性实体。
2.作为主体的人,是实践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01主体通过自身有目的、有计划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创造满足自我和他者需要。机器的实践活动是单一性的、机械性复现或模拟人的一些行为方式,其并不具有自觉性、发散性、想象力、创造性思维能力。
3.作为主体的人,是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机器并不能主动地创造社会关系和人的关系,其在实践中不可能真实体会到实践活动所蕴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其只是在人为的、既定的程序设计下、固定范围内完成指令性任务,因而不具备人的自由意志,不能真正超越人的主体。
4.作为主体的人,是自我超越性存在。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性存在,主体的存在样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先定的本质,而是未竟的历史性存在,是在历史实践中始终如一地求“真”、求“善”、求“美”的超越性存在。机器不会自我反思,因而不会自我改造、自我超越,“在思维能力上无法超越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整体性,对于感官和人脑的模拟仍处于机械化阶段,更不能产生人类主体性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基础”。[4]
二、现实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深刻揭露
对机器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是马克思深刻剖析机器应用的本质和效应的有利武器。
(一)经济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揭开了笼罩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上的虚假面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5]469,“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5]469由此可见,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根本目的是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那么,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真正减轻了任何工人每天的辛劳呢?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6]427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机器更新和改造,有力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节约了大量劳动,其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此“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6]373对于资本家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只要不以工人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界限,缩减必要劳动时间,绝对延长剩余时间,绝对侵占剩余价值必然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资本家一味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使机器“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7]580成为工人阶级身处绝对贫困的根源。
(二)道德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
从现实层面看,尽管机器生产和发展表征着技术的成功应用和胜利,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7]580
1.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资本家“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6]522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无限度延长工人工作日,提高和强化了劳动强度,扩大和激化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对抗程度,使工人受自然力奴役,使工人变成了需要救济的贫民。资本家同时借助机器排挤工人以消除工人反抗性,达到规训工人的目的。
2.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深刻摧残了人民的生命”。[6]311它不仅打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突破了人的纯粹、自然的身体极限,而且盗取了人体发育、成长和人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所需要的时间。当广大工人“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6]322时,资本家却置之不理,认为工人的痛苦会增加其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6]322可以看出资本家为生产利润已经丧尽天良、泯灭了人性中种种的美好和崇高。
3.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肆意蹂躏了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了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极度损害工人的神经系统,夺去工人身体和精神的一切自由活动,成为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无限侵占和奴役。
(三)生态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生态环境的效应
在资本逐利本性驱使下,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创新。以机器为核心的现代技术对生态环境产生双重效应。
一方面,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资本家进一步破坏自然界、征服自然界的强化剂,大大提高对自然力的支配和奴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因而单个劳动本身“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1]191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为例,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技术的任何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579-580另一方面,机器的改良伴随着资本逐利本性驱使而不断得以推进,这为改善生态环境境况提供了一定的、有限的技术支撑。马克思以生产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为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生产和消费排泄物的巨大浪费,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8],这对减轻生态环境压力、改善人与自然界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四)哲学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历史作用的两面性
哲学批判是对现实批判的理性反思和理论提升,反过来又能照面现实本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矛盾时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1]197可见,在资本逻辑统治中的机器技术发展表现为双重效应。
1.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文明效应。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机器生产,全面瓦解了以往旧式生产方式,有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业生产具有了现代意义。机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基础,满足了人的多样需要,培养了人的消费能力,促进了现代交通发展,积极推动了人际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加速了社会变革步伐;同时机器发明和创造也更进一步激发了人的脑力系统、神经系统,增强了人的智力能力。
2.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负向效应。这一负向效应所围绕的哲学主题是人的生存境遇。机器使用和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变革,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343机器化大生产把人变成机器技术的附属物,人内在的神圣感、尊严感和独立人格异化为具有交换价值性质的商品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机器发明、机器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580
总之,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深刻的现实批判,同时也认为机器资本主义发展和应用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性成果的人为程序,为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历史道路。虽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压制和奴役劳动者的主体性,却扮演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力增强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为无产阶级乃至人类未来迈向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三、未来建构:机器技术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实现
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主旨,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也构成了马克思机器观的根本价值诉求。马克思对人的解放实现道路的揭露并不是从意识、精神中进行探寻和分析,而是紧紧立足于现实的自然、人和社会的历史辩证视野中探寻和分析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机器技术发展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中尤为关注的,它构成了推动人的解放的内生力量,为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机器技术发展有力打破了人类受传统血缘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外在束缚,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逐渐解放乃至彻底解放。传统社会技术发展水平低下,人的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只能在有限的、狭隘的范围内发展,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和凸显,人依然身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3]527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逐渐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神秘羁绊,人性得到进一步解放,也使人获得了对自然的生存主动权、自主权,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显著的强化和彰显。自然科学通过展开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感性材料,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3]193从而为人的主体性的彻底彰显和解放作准备。
2.机器技术发展深入推进了世界历史性的人的构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作为地域性存在,而是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人的解放不是仅为地域性解放,更是世界历史性的解放。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程度相一致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527现代社会机器技术发展,创新和丰富了“历史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整个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突破了既定的规模,逐渐脱离了本国发展范围和限制,推动了民族的市场逐渐向世界市场转变,地域性交往向国际性交往转变,地域性交换向国际性交换转变,人类整个生产、消费变成世界性存在。机器技术发展有力打破了主体活动时空限制,也就是,使主体得以摆脱地域性的时空限制,扩大了实践活动范围,扩展了主体普遍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加速促进了人类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
3.机器技术发展深刻调整了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比例分配,为人享有更多自由时间以发展其全面能力奠定基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自由时间是人的解放的尺度。马克思基于历史辩证法揭示了资本逐利而推动机器技术发展,缩短了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侵占了自由时间,同时指出这样的机器技术发展也无意地促进劳动解放。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的逻辑必然。由此,机器技术资本主义应用是历史性的、暂时性的,其必然为机器技术的共产主义应用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的应用范围、应用目的和价值取向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并不相同。在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的应用旨在让每个人拥有更多自主支配自由时间的权利,达致“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3]537的生存境遇,真正达到人的充分解放和全面发展。
可以说,马克思机器观本质上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动力基础和技术支撑,克服了狭隘的历史视界,真正从“类”的历史视界上标示着机器技术发展为人的价值取向。
四、马克思机器观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
从机器演化过程看,机器形态发展历经从简单工具、工具积累、合成工具到自动发动机(智能机器)机器体系的历史进程。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机器,只不过是一种更高级形态的机器,是机器演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发展阶段。2018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上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10],因此,“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0]1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结构和功能发展代表着人类社会机器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以来的智慧成果,也是代表着现阶段一种最新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机器的理论视角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方法论启示。
(一)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属于生产力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机器大生产蓬勃发展的时代,从使用机器进行简单生产,到机器化大生产,再到自动化机器大生产,人们对机器的超常发展产生了恐惧,尤其是一线的产业工人,一度认为是机器“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爆发了砸毁机器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深刻洞察机器生产的本质,一方面肯定了机器大生产对产业工人的戕害,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产业工人受剥削的根源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本质上是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以机器为代表的科技对社会生产具有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如此,马克思的机器观超越了对机器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了科技发展的必然。
工业革命至今,人们已经习惯于机器化大生产。然而,时至今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新一代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冲击无异于马克思那个时代机器刚刚诞生时的冲击,“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进而统治人类?”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焦虑。虽时过境迁,但马克思机器观将机器视作生产力的基本观点仍然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树立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与智慧。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技术具有属人性,技术无法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人们之所以创造和不断更新技术,根本上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以至于实现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彻底解放。相对于过往的工业技术主要是人类体能的延伸,人工智能技术更多是人类智能的延伸,是机器功能在智能方面的扩展。然而,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体机能的延展。正是基于此,我们应该坚持从人与机器的主人关系去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可不必将人工智能神秘化甚至“恐惧化”。
(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必须基于社会制度背景中理解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器而在于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机器观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经济批判、道德批判、生态批判和哲学批判得出,问题的关键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使用的制度基础,不是科学技术应用而是科学技术应用的制度基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是为满足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利益乃至生命为代价。“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6]451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必须超越物化和异化逻辑,建立以人自身为中心的逻辑:以生产资料公共占有为基础,以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管控和调节,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支配、共同享有。“在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时,不能就技术而论技术,也不能仅从伦理限制上看问题,更要看到人工智能使用的社会制度背景。基于私人利益或对财富无节制贪婪的资本主义使用,人工智能的开发无疑将充满风险,它将作为少数人获利、奴役他人的比一般机器更有效的手段;而如果是基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的去使用它,则人们为了其发挥积极的效能就会自觉地去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11]因此,我们应当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与共产主义理论逻辑相统一中理解和把握,以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服务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
(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价值诉求应体现人的解放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器或技术而在于机器使用的人类命运和生存境遇,要把人工智能技术置于其与人的解放历史进程的关系中去审视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一种人为的程序,更是一种为人的公共取向。从根本上说,技术的本质和合理性在于从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又在于从改造世界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进而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技术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奴役人、主宰人,也不是通过技术发展使人同质化和平均化,更不是把人变为世界发展的客体和手段,而技术却成为人类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要以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福祉为价值本位,以人的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和理想目标。在当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把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制度优越性相结合,积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内在优势,坚守和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旗帜鲜明地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作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使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和发展“要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10]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要凸显更多公共性成分,从而更好地为实现以人类解放、实现人民的现实生活幸福的共同性价值目标开辟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