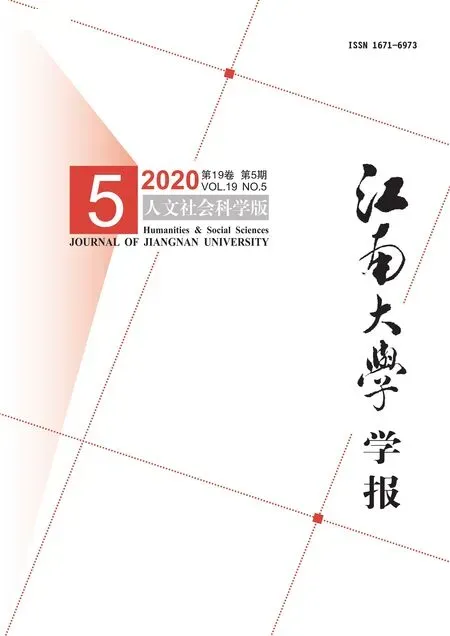“言志”批评探源
2020-02-12高文强
高文强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说到“言志”批评,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的“诗言志”说,以及朱自清先生赋予其的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这一评价。而关于“诗言志”的研究成果,百年来从《诗言志辨》(朱自清)到《诗言志再辨》(饶宗颐)到《诗言志续辨》(高华平)等等可谓多矣。不过,或许是受“诗言志”说的名气和朱先生的评价的影响,对“言志”批评的探讨,有些问题囿于“诗”的范围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如“言志”的丰富内涵包括哪些?这些内涵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远古之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言志”?为什么“诗”可以“言志”?先秦“言志”批评的意义在哪里?等等。本文拟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所言何“志”
讨论“言志”批评之前,我们先要厘清所言之“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此才能清楚所谓“言志”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关于“志”的含义的讨论,即使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文章依然不断,然而对“志”的含义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闻一多先生写于1928年的《歌与诗》一文以及朱自清先生出版于1947年的《诗言志辨》一书。因此,二人所论虽已被反复引用,但在此依然有必要赘引一二。闻一多先生在翔实的材料引证基础上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1]8其实这三个意义中,“记忆”和“怀抱”都可归于内在意识层面,大概都属于“意”的范围;而“记录”则是“意”的外在言语呈现,可以说属于“言”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志”的最初内含包括了“意”和“言”两个层面的内容。不过,当“志”和“诗”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更重视的是其“意”这个层面的内涵。朱自清先生便认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2]2“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2]3也就是说,在“诗言志”这个语境中,“志”的含义范围已缩小为“意”层面的“怀抱”了。《说文》中对“志”的解释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志,意也。”“意,志也。察言而知意也。”[3]695指出“志”就是“意”且需察言而知,而其“言”这一层面的意义则已消失不见。其实这一观点在春秋“赋诗言志”活动中也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来证明,或许这也正是朱先生确定到了“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时“志”就指“怀抱”的主要原因,而对记载“诗言志”的《尧典》他也接受顾颉刚先生的观点认为“最早也是战国时才有的书”[2]2,其“志”指“怀抱”就更不是问题了。之后论“志”者,基本没有跳出朱自清先生框定的范围,细微的差别也只在对“怀抱”或“意”的内涵的不同理解罢了。例如,有学者认为“诗中之‘志’自当取‘怀抱’之义乃为妥帖。这并不排斥诗可用来记事,但主要职能在于抒述怀抱”[4];也有学者认为“‘志’包括诗人的心、性、情、意等许多方面的内容”[5]。
从上述学者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志”置于“诗”这一文体之中来阐释“志”的含义。那么,在“诗”这一语境下将“志”的含义解释为“怀抱”是否恰当?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至少这一解释多少有一点以今释古的味道。就是说我们多少受到今天对“诗”这一体裁的界定的影响,使我们对“志”的理解有了一个预设的范围。读《诗言志辨》可以明显感觉到,对“志”的含义的探讨,朱自清先生有意避开了闻一多先生的远古探源,而直接从“诗以言志”时代开始说起,这显然有点“赋诗断章”的意味。“志”的含义演变,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而且引申义之间也往往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许多时候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内涵,很难用一个清晰界线简单划定。对“志”含义的认识,有必要从其源头开始梳理。
关于“志”的最初含义,《说文》是用“意”来释“志”。这一解释虽不能说道出“志”的全部意涵,但也指出了其最初意涵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层面,而且这里的“意”应该比“怀抱”的含义要广泛得多。闻一多先生所释“记忆”或“怀抱”都是“意”之一种。近年饶宗颐先生根据出土文献对“志”在“意”层面的含义又有了一定的补充。这里我们对饶先生的论证过程不再赘述,仅谈其结论。饶先生在《诗言志再辨》一文中指出:“古人极重视‘志’。‘志’为‘心’所主宰,故云‘志,心司’。‘志’可说是一种‘中心思维’,思想上具有核心作用。”[6]133这里指出“志”是对事物的一种“思维”。《论语》有“志于道”,《孟子》有“志,气之帅”,指出了“志”对于体道与修身的重要意义,与“思维”义有相通之处。饶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贞之哲学》则对“志”在远古占卜中的作用做了详细讨论,他根据《尚书·大禹谟》中“蔽志”一词判断:“卜者必先蔽志,即事先决断,打定主意,然后进行卜事,故云‘朕志先定’。”“可见定志之事,殷人可能有之,故《盘庚》有‘若射之有志’一语,由《皋陶谟》的言徯志,亦可证‘蔽志’不是无稽之言。占卜要先行断志,是人谋在先,鬼谋在后,两者皆能协从,是谓大同。……志,是作某种决定。”[7]所谓“断志”,就是要事先对所占之事做出判断、做出决定,再看与占卜结果是否相合,由此可见“志”在占卜中的重要作用。“志”在此又有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意思。从闻一多、朱自清、饶宗颐诸先生的讨论来看,“志”的早期含义就“意”的层面来说,至少包括了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含义,因此“志”即使如《说文》中释为“意”,其具体内含也是相当丰富的。
“志”的早期含义就“言”的层面来看,闻一多先生认为将“记忆”用文字呈现出来也称为“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1]9。如《周礼·小史》云:“掌邦国之志。”郑玄注:“志谓记也。”[8]699确实,“志”也由此成为后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文体类别,如《左传》中曾提及《周志》《仲虺之志》等,《荀子》中有《聘礼志》,《汉书》中有《艺文志》,二十四史中有《三国志》等等。根据上述“志”在“意”层面的丰富含义,闻先生的这一解释其实可以引伸为“将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意’用言语呈现出来就称为‘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言语”呈现出来会有两种方式:一是口语,一是文字。有文字的年代“志”为文字记录,无文字的远古时代,“志”恐怕只能用口语记录了。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对“志”的最初含义做一个简要概括:“志”主要是指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一类的精神活动,以及对这类精神活动的言语传达记录。
从上述对“志”的含义在具体语境中的分析来看,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关系尤应给予关注:
一是“志”与占卜之关系。《尚书·大禹谟》所言“官占,惟先蔽志”[9]95,强调了“断志”在占卜过程中的作用。按饶宗颐先生的说法,所占者其实就是占卜者之“志”,这里的“志”是一种占卜者对所占之事的思维、判断的结果,只是想以占卜来印证罢了。巫史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他们应该就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者。他们的职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法传达神的语言,这叫作‘巫’;一方面他们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这就叫‘史’”[10]。他们是那个时代知识话语权的掌管者,因此他们祈求“神明昭告”之“志”,便是那个时代精英“智慧”的代表,若记录下来,就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精英“智慧”。
二是“志”与仪式之关系。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尧典》中关于“诗言志,歌永言”等的记载表现的“是存在于仪式中的事物关系”[11]。远古时期的祭祀或巫术活动常伴有一套仪式活动,其中乐舞是必有的内容,《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大概就是这种仪式中的乐舞。在这种仪式中所传达的“志”,显然并非个人之“意”,“即使把‘志’理解为‘怀抱’,对于参与者个体而言,表达的也只是群体的愿望和要求”[12],“具有切实的群体功利性能的情意指向,正代表着那个阶段人们的普遍的‘怀抱’”[4]。这种集体怀抱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集体“智慧”,若记录下来,就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集体“知识”。
工程从规划、设计、施工到决算的每一步,虽都有专门部门进行材料成本管理,但部门间的横向联系、相互衔接工作做的还不够,未能达到密切配合、相互监督的高度.虽都已认识到成本管理是全员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的工作,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还是存在各部门间因横向联系不畅或信息传递不及时,达不到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情况.
因此,远古时期“志”虽然指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一类的精神活动以及对这类精神活动的记录,但值得记录下来的,恐怕大多都是那个时代的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庄子·齐物论》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国语·楚语》所谓“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大概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从上述对“志”的最初含义做的详细讨论再来看“言志”的内涵,我们就能跳出“诗”“言志”的预设,对“言志”有一个更为客观的理解。那么,“言志”何谓?“言”在此有言说和记录的意思,从上述分析可知,“志”的最初含义恐怕很难与个人情怀联系在一起,因此“言志”自然也非言说或记录的是个人怀抱。所谓“言志”,最初更多指向的是对集体之“知”和精英之“智”的言说和记录。
二、“诗”何以“言志”
显然,“言志”并不是“诗”的独家功能。《荀子·乐论》曰:“君子以钟鼓道志。”[13]《礼记·礼器》曰:“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14]东汉冯衍以赋显志而作《显志赋》。不过,春秋以降,“诗以言志”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至《诗大序》时代,“诗言志”已成为中国诗论的核心纲领。为什么之后“言志”与“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呢?
回答“诗”何以“言志”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到底什么是“诗”。“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含义似乎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这种明确性似乎可以上推到《诗经》时代,或许正是这种明确性,使得讨论“言志”问题时,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这一问题自然限定在了诗歌体裁的范围。那么《尧典》中所言之“诗”,是不是和后来的文学体裁之“诗”意思完全一样呢?
事实是,“诗”无论作为一个单字,还是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说文》曰:“诗,志也。”[3]142杨树达先生认为,“志”与“寺”是“古音无二”“音同假借”的关系,而其根据《韵会》所引为《说文》此处补入“志发于言”一句,为“志”的假借字“寺”转变为“诗”找到了依据。[15]简言之,杨先生认为,“寺”是“志”的假借字,“诗”则表达的是“志”的言语记录,即“寺”的言语记录,故“言”+“寺”=“诗”。也就是说,“诗”作为“寺”的引伸义字相当于代替了“寺”或“志”的“记录”这一层内涵。出土文献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云”,便有不少以“寺”代“诗”的写法。又《语丛一》云:“《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16]饶宗颐先生认为:“‘志’与‘事’对言,这和所谓记事、记言同例,《诗》是另一类记‘志’的书。”[6]132《管子·山权数》所谓“诗者,所以记物也”[17]1301,说得正是这个意思。闻一多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1]11综合以上论述可知,“诗”最初的含义是指对“志”的言语记录,是“志”的一种文本形式,其所记之“志”,至少包括了早期的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等内容,至于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记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正因为“诗”所记录的知识和智慧对文化传播与传承非常重要,因此记录所用之“言”自然也有一定讲究。《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18]570“诗”之“言”是要诵的。有学者指出:“朗诵最接近日常语言,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语言。由于这个原因,朗诵在通神仪式中得到广泛应用。从民族学资料看,这种语言包括记诵,即讲述史诗,壮族称‘末论’;包括念诵,即吟读经文,羌族称‘木吉卓’;包括祝诵,即经咒,在布依族中有‘解帮经’‘祭祀经’等项目;也包括告诵,即主持仪式时的宣示和面向神灵的通告。根据《周礼》,国子们所学习的仪式‘乐语’,有兴(起兴)、道(道古)、讽(背文)、诵(吟诵)、言(宣告)、语(答述)等品种。而从满族的《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看,仪式朗诵用于还愿、背灯祭、跳神、祭祖宗、换锁、跳舞、送净纸等项目,是巫师最重要的技能。”[11]巫史之“志”正是“诗”要记录的重要内容,在文字未发明的时代,对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记录主要依靠口传,而口传言语的诵读特征会让这些知识和智慧更便于记忆和传播;在有文字的时代,“诗”的这一特点自然也被延续了下来。“诗”之言的诵读特点,或许正是“诗”从记“志”之“言”而转变为一种韵文文体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分析可知,“诗”的最初含义是指记录“志”的一种文本形式,而“志”在早期的内涵至少包含了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等内容,因此,“诗”所记录的内容自然也相当丰富。《诗大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8]343正是遵循“诗”之本义来说的。
“诗”从记事文本向韵文文体的发展演变,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韵文文体有着多种名称,如歌、谣、诵等等,而“占卜有繇词,亦是诗的性质。殷代《归藏》的繇辞已在湖北王家台的秦简中发现。繇是诗的一种,是占卜的副产品”[6]136。显然,类似后世“诗歌”这样一种文体在殷商前就已存在,但“诗”成为韵文文体的总称,则与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有关。
西周之初文化由巫史转向礼乐,“诗”作为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的功能也开始由“昭告神明”向“礼仪规范”的方向转变;而因为“礼乐”是西周时期最为重要的制度和知识,所以作为记录前人知识和智慧的“诗”也得以开始影响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配合礼乐需要而对诗文本进行编辑整理以备礼仪之用成为时代需求。正如有学者所言:“诗文本是为仪式的目的编辑而成的。”[19]10《管子·小匡》云:“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17]396昭王穆王时期这次典籍编纂活动便应包含了诗文本的编辑。另一方面,“献诗”和“采诗”制度的出现,也对诗文本的编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西周时期,“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20],朱自清先生说“献诗”在于“陈志”,若将“志”以“怀抱”来解,所谓“献诗陈志”似乎有点说不太通。其实“献诗”就是“献知”和“献智”,只不过是以“诗”这种乐中韵文方式来表达罢了。“采诗”其实是另一种“献诗”方式,《汉书》所谓“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诗”之后是要“献之大师”的,经过加工后才“闻于天子”。采什么诗?怎么加工?这还是由公卿列士来决定,因此天子所闻,其实还是他们的“献诗”。由此看来,西周时期的“献诗”,和后世的“献策”更为相似。“献诗”和“采诗”无疑都要编辑诗文本,这种风气,对诗文本的归类编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至少在《诗经》成书之前,西周时期已有《雅》《颂》及各地之《风》这类诗文本类编的出现。[19]293各类诗文本类编的出现,会不断推动“诗”这种韵文文体的特征被认识,最迟到春秋中期“诗”成为《风》《雅》《颂》的总名时[19]391,“诗”的文体意义基本被确定下来。
这样看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所载的“诗以言志”,与《尧典》中舜所言“诗言志”,意思显然并不一样。尧舜时期的“诗”尚未形成诗歌文体的概念,那时的“诗”主要是指对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记录,所以“言志”指的是“言知”和“言智”。而在“赋诗言志”的春秋时期,那时的“诗”已有较为确定的文体特征,那时所言之“志”,已更多指向赋诗者的个人怀抱了。“这里的‘诗以言志’,已经不是告语的记忆或生活的记录,同时也不是礼乐典礼仪式,而是用来直接抒发赋诗者的怀抱和展示他们的风采了。”[12]
综上所述,现在可以回答本节标题的问题了,“诗”何以“言志”?“诗”最初就是用来记录“志”(群体知识、精英智慧等)的文本,因其多与乐、诵配合而呈现出韵文的特点,经过多年演变最终成为一种特定韵文文体的总称。但即使如此,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诗”也并没有完全丢掉其“记录”知识与智慧的意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诗”的“言志”内涵,在先秦时期至少包含了“诗言知(集体知识)”“诗言智(精英智慧)”和“诗言志(个人怀抱)”等三个方面。
三、“言志”批评之意义
“诗”从最初记录“志”的文本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韵文文体,其对“言志”的强调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朱自清先生曾将“诗言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就朱先生的这一说法来看,显然不同阶段“言志”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献诗陈志显然是为了呈“智”,赋诗言志所言多为“个人怀抱(偏政教)”,教诗明志所明者乃前人之“知”,作诗言志所言则是“个人怀抱(偏情感)”。“言志”内涵的丰富性,以及“诗”文本的广泛影响,使得“诗”的“言志”批评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乃至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面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诗歌批评的家国情怀。“诗”作为记录群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文本,一开始本就与群体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西周因礼乐文化盛行而对“诗”进行编辑归类后,其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诗文本编辑归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于仪式,服务于西周的礼乐制度,显然这与国家命脉息息相关,《颂》与《雅》多属此类。《左传》中所载一段便很好地展示了“诗”的政治功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21]另一方面诗文本的编辑归类是为了“献诗”,“献诗”同样是与国家政治紧密关联的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有利“天子听政”,采自不同地域的诗,还编成不同地域的《风》。故《诗大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18]343又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18]344如果从今天我们对诗歌体裁的认识来看《诗大序》的这种说法,会感觉令人难以理解“诗”如何可与“经国之大业”扯上关系,但从“诗”的最初的意义来看,就不难理解古人给“诗”赋予的这份厚重意义了。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中国古代诗论特别重视“诗”的“正得失”功能,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该“神理共契,政序相参”[22]。古代诗论重诗歌与政治之关系,常为今人所垢病,但了解“言志”批评的源流后,应给予古人这种观念以理解之同情。
第二,诗教传统的建构。“诗”作为远古时期的知识系统,很早就成为教育中的重要资源。远在尧舜时期帝舜命夔“教胄子”,便包含了“诗”在内。至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也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周礼·春官·太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8]607-611《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9]404春秋后期孔子删诗以教弟子,使“诗”的教化功能更为凸显。《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3]朱自清先生说:“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用在修身上,也始于春秋时。”[2]22关于学诗的意义,孔子曾有一段著名说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64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说是得“知”,兴观群怨可以说是得“智”,事父事君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了。《荀子·儒效》亦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18]177“诗”由先秦儒家不断强化的教化功能,最后在《诗大序》中得到完美确认:“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18]343-344自此之后,以诗教化便成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
当然,“言志”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远不止此,从其最初内涵的丰富性所引伸出来的广泛影响,非一篇文章能道尽,我们后续还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