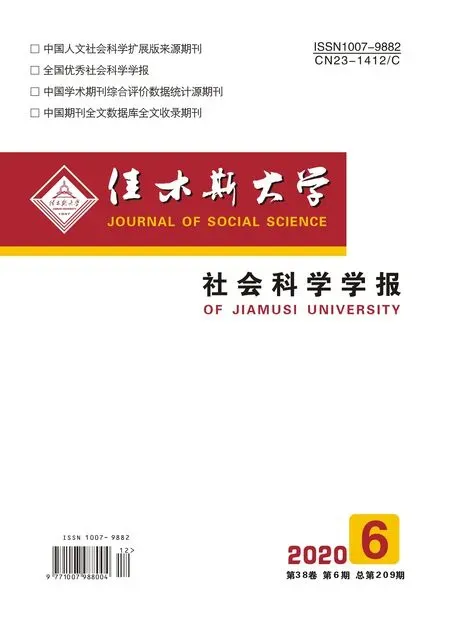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富贵闲人”的人生之叹*
——晏殊《浣溪沙》的情感解读
2020-02-11俞英英胡世文
俞英英,胡世文
(浙江海洋大学 师范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晏殊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著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评价“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浣溪沙》作为晏殊的经典名篇入选八年级上册的部编版语文教材,其中流露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对于世事无常的喟叹值得我们深思。而作为“课外古诗词诵读”中的一篇,教材编者对《浣溪沙》的分析其实并不多,这也留给了我们更多解读的空间。
一、知人论世,初步感知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后人由此概括出“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准则,几千年来一直为人所推崇。现代文学理论也认为“作家的人生经历、心理特征和创作个性等主观因素,对文学创作具有直接的影响”[1]155。新课标强调“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2]14,实现“对话”教学离不开“知人论世”,它在教学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能使学生置身于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受时代背景下的跌宕起伏,从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尤其是《浣溪沙》这类历时久远的抒情性文本,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些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作者生平及其创作背景的介绍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浣溪沙》这首词而言,抛开背景知识,单就词作的意象和情感进行分析,或许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但为何有此感叹?是偶有所感还是常有所叹?这些单凭这一首词就比较难以把握,这时就需要我们联系作者生平。
晏殊的一生颇为幸运,十四岁那年,就被江南按抚张知白举荐给朝廷,宋神宗召他赴廷中面试,晏殊神色自若,毫无紧张之态,拿到题目便“援笔立成”,得到了神宗的赞赏,赐同进士出身。之后晏殊的仕途可谓是一路畅达,做过枢密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至宰相,虽也曾遭遇过几次贬谪,但都不严重。
抛开他在文坛上的成就,晏殊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宋神宗去世时,仁宗年仅十二岁,朝中部分官员想借机独揽大权,晏殊提出了让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对稳定当时的政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他还锐意改革,建议皇帝免除监军制度,把军队指挥权交还给前方统帅;建议改革科举考试过分强调记诵的弊端。在文化教育方面,晏殊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庆历新政期间的人才聚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聚散行止,充分显示出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用。”[3]110
政治上的理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同样是写人生无常的悲哀,相较于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春晚》),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相见欢》),晏殊的情感则更显理性与节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愁绪,“他从圆满的人生中体悟到一种不圆满,即想延长这圆满的人生而苦于人生的短暂”[4]29。但这也与词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相较于李煜、李清照的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晏殊的一生实在是幸运,他的心中确也没有这么浓的愁绪。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主张,司马迁也曾感慨“诗三百,大抵圣贤之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后世大多认为诗人的处境越艰难越能成就好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经历都能成为日后的写作素材,情感思绪都是创作的灵感源泉。但晏殊却是个例外,安逸的生活并没有让他颓废丧志、沉溺声色,反而使他的词作另有一番“富贵闲人”的风格,他的出现为词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由于每位作家的性格特征、人生境遇不同,即便情感上有共通之处,在作品风格方面也往往因人而异,例如我们概括杜甫的诗风为“沉郁顿挫”,李白是“豪放飘逸”。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将客观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与体现主观情感的作品相结合,品味作者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这样既能加深学生的情感体悟,也有助于实现学习的迁移,从而引导学生阅读更多优秀的作品。
二、以意逆志,体情悟理
新课标指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2]2,而宋词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更应该将情感的体悟作为教学的重点。部编版教材将《浣溪沙》所流露的情感概括为是“一种由光阴流转、物是人非带来的感慨与惆怅”[5]148,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则是将这种“感慨与惆怅”更加地具象化,而不是始终处在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的状态。
《浣溪沙》的上阙,“一曲新词酒一杯”很能体现词人“富贵闲人”的惬意生活,同样是饮酒,他没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怀才不遇之悲,也没有“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的国破家亡之痛,而是听曲赏景的闲适自在。人生不易,晏殊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但当他看到“去年天气旧亭台”,想到“夕阳西下几时回”,却也不免愁思涌动,所见与所思形成对比,天气依稀似去年,亭台楼阁也依然如故,看似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夕阳西下何时能够复返?结合晏殊的人生境遇,他的感叹不免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甚至于无病呻吟之感,但若真是这样这首词作也不值得流传千年,细读下阙我们便能得知原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一种人生无常的哀叹,生命的无力感,花开花落自有时,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宇宙人生的真谛,不仅花如此人亦如此,人对此没有丝毫的办法。因此“‘无可奈何’,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人力无可挽回;也是一种主观心境,充满无限惋惜。”[6]67这与欧阳修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蝶恋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词人并没有沉溺于这种感伤之中而无法自拔,下句笔锋一转,“似曾相识燕归来”,归来之燕仿佛似曾相识,然而燕子自然都是长得差不多的,词人怎么可能真有印象呢?不过是自我排遣罢了。正如叶嘉莹先生评价晏殊的词有一种“圆融的关照”(《唐宋词十七讲》),他的愁绪不像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是滔滔不绝,去而不返的,他能从“大局的”“圆融的”角度看待宇宙人生。苏轼曾感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无常中包含着有常,无奈中又有着一丝欣慰,晏殊也正是如此。最后一句“小园香径独徘徊”,曲终人散,词人独自徘徊在落英缤纷的小园里,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是对落花的惋惜?是对故人的思念?抑或是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我们不得而知,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
王国维先生将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7]2在晏殊的《浣溪沙》中词人将自己的情感投注于自然景物之中,是典型的“有我之境”,故词人看天气是去年的天气,看燕子也似曾相识,通过景物表达自己对于时光易逝、好景不长的无奈与惋惜,但同时也考虑到宇宙人生的循环往复,又有一种自我排遣的意味。
新课标重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要求教师“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2]14,自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学生由于他们各自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教育基础不同,从文本中生发出来的理解和体悟也是有差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文本的解读是无边界的。在《浣溪沙》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在把握情感基调——人生无常的悲哀的基础上,再结合自身体验进行生发和阐释,那可能是亲人离世后的感念,可能是小镇开发后的变迁,也可能是大灾大难后的幸存……美国教育家华特科勒涅斯曾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学习的最终落脚点也应是学生的生活。
三、千古同悲,拓展升华
对于人生无常的哀叹,早已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如果能将《浣溪沙》的教学与其他本文相联系,既能突出教学的重点,也有助于加深理解和体悟。那些名家名作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初中生正处于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更应注重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如果能由《浣溪沙》的教学引发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并联系当下,懂得珍惜光阴,勤学发愤,不失为一个好的教学角度。
从横向来看,晏殊的《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就有不少涉及此类题材。他的另一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词的上片感慨人生短暂,匆匆几十年却要经历无数次的别离,因此更要珍惜短暂的相聚,杯酒交盏之间既是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也是一种自我排遣,很有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的豁达。词的下片劝诫我们珍惜当下,立足于现实,不要太过执着于触及不到的将来和已经过去的美好。这两首《浣溪沙》的整体风格是非常相近的,同样是对时光流逝、好景不长的无奈与叹息,但“在悲苦中总隐然有一个解决的办法”[8]185,他劝诫我们“不如怜取眼前人”,不光是“眼前人”,眼前之物、眼前之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此外,“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晏殊《木兰花》),“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晏殊《破阵子》)等词句中亦不乏此类忧思。
从纵向来看,我国自古以来也有不少文人墨客都曾有过对于人生无常的感叹,并在诗词文赋中得以体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是对好景依旧但昔人不复的无奈与叹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的是老当益壮,渴望继续为国家效力的热忱;“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曹雪芹《红楼梦》),“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琵琶行》)抒发的是红颜易老、美人迟暮之悲;“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虞美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春晚》)既有身世浮沉之叹,又有国破家亡之悲,读来字字泣血。
“如此众多的文学家。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艺术风格和艺术种类,讲述不同的故事,塑造不同的形象,却沿用一个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母题。”[1]165这既是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许多学生对古诗词不感兴趣,觉得它们晦涩难懂,脱离现实,如果能将其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既有助于理解,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陆机在《文赋》中曾言“诗缘情而绮靡”,朱自清先生也曾说过“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这里的“诗”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诗歌,包含词的范畴。基于诗歌的抒情性特征,在《浣溪沙》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立足于情感这一基点,并结合学生实际,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千古同悲”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其中“知人论世”是起点与基础,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融合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无论是体情、达意或是言志都是以客观现实为载体。文本解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要剖析作品本意、体会作者用意,而脱离“知人论世”的本文解读往往容易陷入过度阐发的误区,挖掘得越深,偏离得也就越远。因此,“知人论世”是帮助我们“以意逆志”,正确把握作品情感的桥梁与媒介。“以意逆志”,体悟情感,则是教学的核心与重难点,是读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解读作品的过程,也是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我们将客观的背景知识与主观的人生经历相结合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千古同悲”则是基于“以意逆志”的拓展和升华,它使情感超越单一文本和时空的局限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旨在寻求不同文本间情感的共通性,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三个阶段层层相因,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联系,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审美情趣,也提高了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